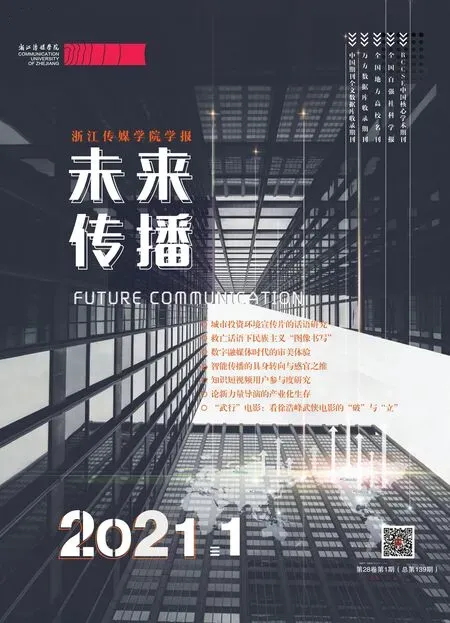路阳:新力量导演的“体制内武侠”
2021-11-26孙茜蕊
孙茜蕊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北京100732)
一、体制内导演的武侠“突围”
“电影制作的商业和文化现实大大抵消了(导演)希望成为一个个性化创作者的愿望,抵消了(导演)希望拥有自己的主题风格和个人化的世界观的愿望,世界范围内的电影产品的经济现实和绝大多数电影观众的口味抵消了这种愿望。”[1]我国“第六代”导演之后开始集中显现出这种世界性的趋势,相较于“第六代”导演科班出身、推崇欧洲艺术电影、作品追求个人化艺术风格的代际群像,之后的“新力量导演”则具备多元化背景,推崇好莱坞类型电影,吸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影响,作品更加尊重市场和受众的需求,艺术风格有别于传统的作者化。
陆川曾在论文中将新好莱坞导演科波拉定义为“体制内的作者”,认为体制内作者既尊重个人艺术信念,在创作中坚持对于人类命运的探索,又尊重体制的核心要求(好莱坞体制的核心是:观众),自觉地从自身电影体制所赋予的土壤中出发(吸收并突破成规)进行创作;并且以高度的自觉区分个人创作和大众艺术创作的创作姿态,尊重体制的期待。[2]由此看来,我国当下兴起的新力量导演群体亦是体制内的作者,诸如刁亦男、杨庆、程耳等,他们在题材的选择和视听语言风格上充分尊重了普遍受众的题材偏好和观影习惯,同时又以个人化的表达成就了艺术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因此也可以这样认为,每位体制内作者的创作实践都是在艺术与市场的博弈中实现的一次“突围”。
路阳作为新力量导演的典型人物,同时体现出新力量导演和体制内作者的特征。本科就读工科专业的路阳严格来讲并非科班出身,但在父辈电影人的熏陶下养成了对电影的热爱。工作后选择考取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成为“半个”学院派,正式走上电影创作之路。1979年出生的路阳和许多八零后、九零后导演一样,青少年时期见证了我国对外开放、文化百花齐放的繁荣。这一时期,北京的文化艺术娱乐化、商品化的大潮和外来文化产品的大量涌入,使路阳等新力量导演成为看着日本漫画长大的一代。“我很喜欢看日本动漫,(沈炼)这样的角色在漫画里挺多。我们这波人除了电影、小说之外,也会看漫画、打游戏,游戏、动漫也不一定是肤浅的,可以说有些中二,但有可能是存在光彩的。”[3]《绣春刀》系列两部影片均讲述了“蝼蚁”在盘根错节的黑暗朝堂杀出一条生路的故事,将二次元文化标志性的热血气质化入了武侠电影的血肉中;影片“跑酷”式的追逐戏、追身镜头和动作戏凸显力量感、精确感的风格均给传统武侠崇尚飘逸、写意的美学理念带来了充满动感和趣味的变革。
与此同时,路阳作为导演在行业中突围的过程也与新力量导演普遍的发展路径不谋而合。新力量导演在国际电影节展上初试啼声的作品多是小成本剧情片,选择含有悬疑、喜剧元素的,大众接受度较高的题材和故事,如刁亦男的《白日焰火》、杨庆的《火锅英雄》;叙事技法和视听语言虽具有技巧性,能展现导演功力和匠心,但绝不曲高和寡。可以说,新力量导演的创作道路从起点开始就探索了未来驾驭中高成本商业片的艺术潜能,亮出体制内导演身份的同时逐步形成自身的作者性。2010年,路阳导演的处女作《盲人电影院》在第15届釜山国际电影节首次亮相并获得最受观众欢迎奖,以及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导演处女作奖。和许多新导演一样,《盲人电影院》不俗的成绩没能为路阳带来更大的投资和创作空间,“带着《盲人电影院》参加完釜山电影节就开始酝酿《绣春刀》的剧本。那个时候预计到了,刚拍了一部100多万的电影,现在写一个两三千万投资的电影,没人会投我们。”[4]《绣春刀》几经辗转获得了中影集团的投资,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完成了拍摄。2014年《绣春刀》上映,以写实的风格、扎实的叙事、原创的态度成为当年电影市场的一匹黑马。尽管票房不尽如人意,但对于当时IP盛行、资本当道、流量主导、叙事奇观化的国产电影来说具有可贵的意义。2017年,《绣春刀》前传《绣春刀:修罗战场》上映,无论是投资规模还是制作水准都是对前作的一次全面升级,不仅延续了前作的口碑,还获得当年暑期档票房第二名的成绩,为已经处于衰落期的武侠电影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此外,由乌尔善、郭帆、文牧野、姚婷婷等导演组成的小群体,正在或已经从中高成本的高质量商业片出发,步入电影工业化的创作探索,路阳亦在其列。这一小群体的出现依赖于国家文化部门搭建的平台。2013年,国家广电总局与美国电影协会达成协议,发起“中美电影人才交流计划”,选派新生代青年导演赴美国好莱坞学习先进的制作经验和制片管理体系。几年间,宁浩、陈思诚、肖央、郭帆、路阳、薛晓路、张猛、乌尔善、徐峥、韩延、大鹏、姚婷婷、彭大魔、闫非、田羽生等新力量导演均通过这一平台,学习了好莱坞电影高度工业化的制作体系,其中不少导演由此开始探索国产电影的工业化道路,例如郭帆执导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乌尔善执导的玄幻史诗系列《封神三部曲》、姚婷婷执导的奇幻爱情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陈思诚执导的《唐人街探案2》等等。这批电影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工业化探索的成果,即电影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由此带来的题材突破和视觉效果的升级。路阳的新作《刺杀小说家》则讲述了现实世界和小说家笔下的故事世界相互影响的都市奇幻故事,大型实景搭建与大量特效制作齐头并进,采用了与《阿凡达》《猩球崛起》《头号玩家》等影片相同的虚拟拍摄技术,是中国首部使用虚拟拍摄技术的真人电影。[5]可以想见,《刺杀小说家》将是路阳关于电影工业化课题交出的第一份“答卷”。
值得注意的是,新力量导演中工业化创作群体的出现,不仅来自国家对电影产业发展的背后推动,还来自当下“互联网哺育的几代人对虚拟现实和想象力消费的需求”[6]。而新力量导演担负的这份时代使命正是新力量导演“体制内”身份所必然赋予的使命,即将自身的创作生涯与国家发展、时代脉搏、电影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
从上述创作历程不难看出,路阳这位以“新武侠”为观众所熟知的导演,并非同张彻、胡金铨等老一辈大师一样,是一位彻底的武侠导演。路阳作品的题材较为多元化,涵盖喜剧、公路、武侠、奇幻等多个种类。武侠电影之于路阳,更多的是一种表达手段而非目的。路阳自身也不止一次在采访中表示,创作《绣春刀》的出发点是描述身边的人与生活之间的冲突和挣扎,[7]基于这样的主题,后来才找到武侠电影作为故事与价值的容器。我们不妨这样认为,《绣春刀》系列和武侠电影之于路阳,是其作为体制内导演的个人化突围方式。
那么,路阳为何选择武侠电影作为自己突出重围的“兵器”?《绣春刀》系列作为新武侠电影又体现了路阳哪些突破传统武侠电影成规的变革?路阳新武侠电影的变革为什么仍旧符合武侠电影类型的本质规定性?《绣春刀》系列又是如何体现路阳导演的作者性的?
二、“体制内武侠”的写实追求
上文提到,体制内作者能够自觉地从自身电影体制所赋予的土壤中出发(吸收并突破成规)进行创作。[2]实际上,从武侠电影作为电影类型的角度来看,“对惯例化形式的持续不断的改写”[8]亦是类型电影的内在演变动力。克里斯蒂安·麦茨在《文本性与一般性》中提出电影类型内部的演变经历了类型惯例的模仿到论争,再到批评的过程。路阳作为体制内作者,在吸收武侠电影类型惯例的同时做出了突破性的改变。总的来说,路阳新武侠电影的“新”是一种“体制内武侠”的新,路阳新武侠美学的“新”是一种写实美学的追求。《绣春刀》系列无论是侠客的身份认同还是影片的叙事空间,都体现出“体制化”的特征;而该系列的美学风格与“体制内武侠”相辅相成,一改传统武侠电影飘逸恣肆的写意美学理念,追求富有重量感、力量感的写实之美。
自古以来,江湖与侠客相连,侠客属于江湖,江湖中必有侠客行走,已经成为一种“近乎常识的判断”[9]。电影作为现实的镜子,传统武侠电影中侠客作为“江湖中人”的身份认同并非艺术的凭空捏造,而是源自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侠。侠成形于战国时期,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分化而来。“士即战士,平时肆力于耕耘,有事则执干戈以卫社稷者。”[10]战乱频仍的春秋时期,士被选拔后不再务农,专门充作精兵,称“国士”。可见,作为侠的前身的“士”就已经来自民间,但仍旧从属于权力阶层。随后,“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11],国士与国主的关系并不牢固,而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12],国士便从身负从属关系的固定职位变为了自由流动的“游士”。此时的士与权力阶层的关系由固定的依附转为自由流动,离侠的形态更近了一步。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随着列国纷争的态势愈发激烈和复杂,民间风气变为重利轻义和重才轻德,这与游士所秉承的尚义重德、崇尚气节的信念背道而驰,游士从而“独立特行,以对抗社会的姿态,取极端的行为引起世人的瞩目,以图造成心灵的震动”[13]。如果说国士是通过武力的效忠与权力阶层进行政治、军事的联合,实现自身抱负,那么这一时期的游士则多了叛逆与对抗的姿态。至战国末期,典籍中已经开始用“侠”字指代这一时期的游士群体,标志着侠作为社会阶层的独立和成形。由此可见,侠的民间属性古已有之,后经过文学艺术浪漫化、传奇化的二次加工,武侠题材特有的叙事空间和文化符号“江湖”从现实的民间社会和世俗空间脱胎而生,成为一个“一定意义上与朝廷相对立,与市井红尘有联系,但是又使市井细民感到神秘”[14]的世界。武侠小说出现后在诗歌的基础之上把这个幻想的空间与世俗拉得更远。从唐宋传奇开始,侠客便称“吾乃剑侠,非世人也。”[15]“唐宋小说家开始将侠客神秘化,其中一个重要步骤是建立起一个‘世人’与‘剑侠’相对立的虚拟世界。”[16]由此,文学作品中的侠客也就与江湖密不可分。
《绣春刀》系列的主角沈炼则告别了江湖,从一开始就有着体制化的鲜明的世俗身份。锦衣卫的飞鱼服、绣春刀则是沈炼体制化身份的视觉编码。值得讨论的是,近年亦有其他新武侠电影弱化了侠客“江湖中人”的身份,《绣春刀》系列(2014、2017)所做的变革并非首创。苏照彬执导的《剑雨》(2010)和陈可辛执导的《武侠》(2011)分别在市井城镇和乡野村寨中塑造了强调市民、乡民身份的侠客。因此需要明确的是,《绣春刀》系列的突破并非在于沈炼不再属于江湖,而在于沈炼进入了一种比市民社会、乡民社会更加等级化、体制化的权力统治结构,也正如大众所理解的那样,沈炼是一名挣扎于“官场”“职场”的“公务员”。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虽然武侠电影主角具有体制内身份并非《绣春刀》系列首创,但《绣春刀》系列的主角具有体制内身份的同时,影片叙事空间也以体制内官场为主,在武侠电影中实属突破。因而本文的“体制内武侠”所指的是以《绣春刀》系列为典型代表的,主角身份和叙事空间都着力刻画有别于传统武侠江湖叙事的“体制内”叙事武侠电影。
相比之下,早于《绣春刀》的两部电影《锦衣卫》(2010)、《血滴子》(2012)主角身份都尝试了体制化,前者主角身份为锦衣卫首领,后者主角身份则是清代暗杀组织“血滴子”的成员。然这两部影片不能称为“体制内武侠”,差别正在于叙事空间的选取。侠客身份和叙事空间的双重体制化是《绣春刀》系列的突破之处;同时正如传统侠客“江湖中人”的身份认同由该群体活动、存在的叙事空间所定义,体制内侠客的身份认同也很大程度上由影片的叙事空间所成就。因此,若要论及沈炼及《绣春刀》系列的突破之处,还得进一步阐释《绣春刀》系列在叙事空间上的体制化突破。
首先,叙事空间的概念与物理空间和物理场景并不能全然画上等号,因为“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形式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容器。”[17]无论现实中的空间还是文艺作品中的空间,都承载着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具有物质性和文化性的双重属性。电影类型作为一种特征相近的电影的集合,在“空间”上自然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共性,例如美国西部片的经典空间是蛮荒的西部,侦探片的经典空间则是潜藏罪恶的都市。武侠电影则有着特征鲜明的、独有的叙事空间——江湖。之于电影,空间的双重属性则不妨理解为物理场景、人物关系、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甚至包括戏剧冲突和价值冲突的总和。[18]传统武侠电影以江湖为叙事空间,这当中就自然包含了以自然景观为主的物理场景,流动性强、地缘性弱的侠客社会关系,以及云游四方、仗义行事,随性洒脱的人物关系。具体而言,陈平原先生认为江湖的三大典型场景是悬崖山洞、大漠荒原和寺院道观。[9](159)“无论是山林海岛,还是大漠荒原,到处都有江湖人的踪迹。”[19]至于传统侠客的人物关系与社会关系,则从“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氏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等诗句可以看出。
《绣春刀》系列中,庙堂和市井的物理场景取代自然景观成为影片的叙事空间,武侠电影的叙事空间在这里得到了体制化的革新;尤其是由锦衣卫衙门、官员宅邸、信王府邸等组成的“庙堂景观”承载了《绣春刀》系列以朝堂争斗、权力阴谋为基础的核心戏剧冲突。而伴随物理场景的变革而来的,是沈炼的人物关系也深深扎根于官场等级体制之中,围绕沈炼的一众配角,若仅以社会关系来看,也可分为上级、同僚和下级。正如上文提到的,路阳本人表示《绣春刀》旨在讲述“身边人与生活之间的冲突和挣扎”,认为沈炼及其身边的人物不似传统侠客一般来去自如、随心所欲,而是“不自由”[7](328)的,体制化身份的禁锢和朝堂市井空间的包围正是这种不自由的呈现形式。
回到前文提到的问题,相比之下,《锦衣卫》《血滴子》的主角虽然也有着体制化的身份,但影片的叙事空间仍设置在传统武侠电影的自然景观之中。前者讲述主角青龙意外丢失玉玺,追出关外,黄沙大漠的域外景观是影片的主视觉;后者讲述血滴子一行人奉旨剿杀反清组织首领,影片的故事则在世外桃源般的反清组织聚居地展开。
浪漫辽阔的自然景观、随性流动的人物关系为传统武侠电影塑造出飘逸自由的写意之美。叙事内容上,传统武侠电影继承了武侠小说传奇式的叙事风格,或像金庸武侠对真实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戏说式的二次创作;或干脆另起炉灶,虚构门派、神功、神兵,极尽神奇之能事。传统刀剑武侠片的动作设计也在此基础上将视觉奇观发挥到极致,从武侠电影的摇篮《火烧红莲寺》开始,武侠电影和古装动作大片就走在实践电影视觉技术的前端,“飞檐走壁”“排山倒海”等违反物理规律的视觉奇景早已是传统武侠电影的常见景观。
《绣春刀》系列最大程度上尊重了锦衣卫历史及明朝相关历史背景,以关键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节点为框架,遵循历史的“肌理”填入“血肉”。《绣春刀》系列两部作品分别围绕崇祯铲除阉党和天启帝溺水、阉党猖狂等重要历史节点展开。《绣春刀》讲述崇祯帝扳倒魏忠贤后扫除阉党余孽,沈炼奉命捉拿魏忠贤,在此过程中发现大明正面临国库空虚、无人可用的隐忧。《绣春刀:修罗战场》作为第一部的前传,讲述天启帝意外落水后病危,阉党横行致使人人装聋作哑,沈炼受人要挟不得已执行秘密任务,却在此过程中发现天启帝落水的真相和信王觊觎皇位的野心。在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所构筑的舞台上,沈炼虽为虚构人物,却作为政治棋局的“闯入者”发现了某种历史的真实。《绣春刀》系列通过历史和虚构的精巧互构实现了叙事上的写实。
“为了坚持更纪实的手法,把武戏拍摄中威亚的使用部分拿掉了非常多。其实当时拍的时候拍了很多,但后面我把威亚部分能剪的都剪掉了。动作场景也是,人不可以一跳就跳上墙,飞那么高,或者飞得很远,这些都是我看起来觉得不舒服的,不像这部电影里应该有的东西。特别是那些我认为看起来画面上违反了物理规律的部分,全部拿掉了。”[20]《绣春刀》系列在动作设计和视听语言上继续坚持了写实的美学风格。不仅避免出现以往武侠电影惯用的威亚特技、夸大动作效果的视觉特效,还多选用刀、长刀、狼牙棒、流星锤等兵器,追求虎虎生风的重量感和力量感。
此外,路阳还大量使用手持摄影和第一人称视角镜头拍摄动作场面,力求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亦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生动细腻的外化。手持摄影产生的晃动镜头是路阳偏爱的镜头类型,频繁使用于自身所有类型的作品中,在《绣春刀》系列得到了更加炉火纯青的运用。手持摄影在“拍摄过程中摄影机机身上下、左右、前后摇摆的拍摄”[21],通过晃动传递出呼吸式的视听美学,比起固定镜头有着更强的沉浸感和参与感。《绣春刀:修罗战场》中,沈炼误杀凌云铠后的镜头剧烈晃动,与动态环境镜头、粗重的呼吸组成鲜活的蒙太奇,展现了沈炼的惊慌与未来处境的危险。这里的手持摄影一改影片前半部分的相对平稳内敛,在视听上顿时将沈炼拉入无法控制的巨大变故中,昭示着剧情的骤然加速和沈炼命运的重大转折。“火烧案牍库”一场戏,沈炼视角的镜头中流星锤迎面向银幕飞来,力量感、速度感带来极大的威慑力,使观众切身体会到沈炼被这种新兵器所压制的窒息感。《绣春刀》中沈炼捉拿许显纯的“跑酷”戏,手持摄影紧紧跟在沈炼的背后,展现出沈炼飞檐走壁、袍角翻飞的动态,也让观众感受到行进中沈炼所看到的一切,仿佛自己也参与到这场紧张刺激的追捕中。
基于《绣春刀》系列呈现的种种变革,我们需要回到前文曾提出的问题上来:沈炼作为侠客和《绣春刀》系列作为武侠电影为什么仍旧符合武侠电影类型的本质规定性?
三、“体制内武侠”的叛逆内核
总体而言,《绣春刀》系列之所以为新武侠,沈炼之所以为侠客,除却“武打”这一显而易见的外在形式之外,在于它们不仅体现了侠义精神这一武侠电影类型的价值内核,还具备了侠义精神所必须具备的叛逆气质。
“文艺作品中的侠形象的构成方法,……是善之义的演绎绘制,即集中人类的优点及人性的正面特征。”[22]而关于侠义精神的具体内涵从古至今的论述浩如烟海,观点不一而足。本文以为,关于侠最早的历史记载,《史记·游侠列传》已经将这些内涵勾勒出了大致的轮廓,并提供了“个人—他者”的基本论述框架,后世的论述均可视为它的丰富与扩展。个人层面,它是助人为乐、公正、自由、忠于知己、勇敢、诚实且足以信赖、爱惜名誉、慷慨轻财[23]等正面个人品质的综合。“他者”层面又可分为个体的“他人”和群体的“社稷社会”两个层面。前者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牺牲奉献精神,我国最早记载侠的文字《史记·游侠列传》早已点明此义,“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24]后者是凌驾于既存的法律和统治秩序,驱逐黑暗的法外执法者,所谓“世何以重游侠?世无公道。民抑无所告诉,乃归之侠也。”[25]
《绣春刀》系列的价值表达均从较为“自私”的个人福祉出发,最终落于侠义精神的他者层面。沈炼、卢剑星、靳一川三兄弟均为了各自小我的愿望接受追拿魏忠贤的任务,其中沈炼面对魏忠贤的金钱诱惑,同意为魏忠贤制造假死助其逃脱。然而在隐瞒魏忠贤假死真相的过程中,三兄弟在官场争斗中险象环生,卢剑星、靳一川接连殒命,沈炼最终在认清官场黑暗后选择了兄弟之情和国家大义,奔赴边疆与杀害兄弟、背叛大明的宦官赵靖忠决一死战。《绣春刀:修罗战场》开篇即塑造了锦衣卫治下人人自危的政治高压背景中,沈炼只求自保的冷漠态度。沈炼为保护心爱的画家北斋失手杀死同僚,因此被人要挟执行火烧案牍库的任务,在卷入北斋、明王等人布下的谜局过程中,发现了信王朱由检的政治阴谋,最终奋起反抗。由此不难看出,沈炼虽不同于典型侠客从一开始便践行侠义精神的正面形象,但经历人物成长后完成了由“非侠”到“侠”的价值转变。
然而,无论是个人、他者层面还是社稷层面,我国传统文化中均存在着正面价值表达的人物形象。若论个体的良好修养、优良品行和奉献精神,有儒家礼法中的“君子”;若论对社稷社会的公义与责任感,忠臣良将、国士大夫亦可当之。这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探究,侠客及武侠电影的价值内核除了侠义精神之外,还需有某种本质规定性的元素。
陈墨先生在《中国武侠电影史》中提出电影《荒山得金》当为中国武侠电影的滥觞,并评价道:“这理由当然是,其中不仅有动作、有打斗,还有侠气,也有侠义。”[26]尽管武侠电影最为公认的本质规定性是武打和侠义,“侠气”却也频繁地出现在武侠电影的讨论中。我们总是从感性的层面使用侠气这一概念,形容武侠电影的人物“有侠气”,形容电影“侠气十足”,却鲜少辨析侠气的含义,探究侠气从何而来。《中国哲学大辞典》引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的说法解释“气”的概念:“阴,刑气也,阳,德气也”,可见“气”不仅指代精神气质,还带有道德性和情感性。本文认为:侠气是践行侠义精神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正义的精神气质,带有道德性;侠气还是侠义行为带给旁观者心灵的震撼和冲击,带有情感性。
相比起正义的道德气质,侠气中叛逆的情感气质更为重要。因为同是具备正义的价值体系、高尚的道德品质的人物,叛逆的侠气使侠客区别于“君子”“英雄”等等,成为独树一帜的文化符号。而叛逆的情感气质,正来自于侠客践行侠义精神的独特行为方式,即打破庙堂与民间的体制与律法,超越既存的世俗秩序,仅以个人心中的价值信念为准则,做出善恶判断,主持正义。
“叛逆,也就是敢于反抗社会,敢于打抱不平,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做常人不敢做之事。”[27]侠客的反抗不仅面向统治秩序,还面向世俗的各种条条框框,《不服从的江湖人》一书形容为“对国家体制不屑一顾,又对宗法伦理敬而远之的离经叛道的边缘人”[28]。侠客如果在统治秩序、法律条文、世俗规则的约束下主持正义,便不能称之为侠客。有趣的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以《水浒传》为源流,《三侠五义》《施公案》为代表的“公案小说”刻画了许多“守规矩”的侠客。公案小说大多讲述清官在众侠客的辅佐下破获奇案、主持公道的故事。虽然属于武侠小说的一支,但长久以来对公案小说的批评不断,正集中在侠客形象的奴性和侠义精神的衰弱上。例如鲁迅先生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一文中谈到:“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贫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29]可见鲁迅先生也认为,典型的侠客应当不守规矩,应当是“庙堂的主流文化、社会秩序的非主流、非秩序”[30],应当具备叛逆的侠气。
《绣春刀》系列中沈炼的体制内身份不禁使我们要将公案小说及相关的影视作品拿来作比较。公案小说中的“侠”作为清官忠臣的辅佐,在侠义精神的表达和侠气上都大大削弱。沈炼虽为体制内身份,但体制内的底层地位和置身事外的边缘化态度令沈炼成为“蝼蚁”,沈炼的人物选择则是逆势而为、向死而生、充满叛逆的侠气。
同时值得提及的是,传统侠客的叛逆普遍存在限制条件,它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我国古代社会传统的君臣意识之上,有着维护皇权的政治底线,通常“反贪官不反皇帝,除恶贼不除纲纪”[9](144)。因此,侠义精神的内涵有着这样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比君子、忠臣等同样代表善良正义的传统文化符号多了对法度和体制的超越和反叛;另一方面,它的反叛又是有限度的,维护的还是皇权及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统治。然而,沈炼在两部电影中的反叛行为不仅指向了明代黑暗的官场,更是鲜明地指向了统治者(崇祯皇帝)的不义之行。可以说,路阳和他的《绣春刀》系列将武侠电影的叛逆推向了一个更加彻底的立场,体现出“一黑到底”的决心。
美国电影理论家安德鲁·萨里斯在《关于作者论的几点认识》中提出如果导演满足以下三个标准,那么他就享有“电影作者”的称号:第一,技术的标准。导演能否娴熟地驾驭电影技术;第二,风格的标准。导演在自己所有的电影作品中注入一贯的特殊的主题内涵、电影语言的风格特征,从而烙下明显的、统一的个人印记,而且是不从众、难以复制和易于辨认的;第三,内在意义的标准。导演从个人风格和矛盾冲突中体现影片内在的意义,不受商业因素和行业制度的束缚,是导演独有的“热忱的灵魂”。[31]
武侠电影作为路阳突围的“兵器”而非专注探索的类型题材,留给我们研究的影片和资料并不多,解答路阳为什么选择武侠电影作为体制内突围的“兵器”,以及路阳的作者性问题,仍需要更多的研究对象。2020年11月,路阳新作《刺杀小说家》发布新预告片,首次披露了“凡人弑神”的故事主线。尽管《刺杀小说家》全片尚未面世,但“一介凡人,竟敢弑神”的标志性台词使我们窥见了影片与《绣春刀》系列相似的叛逆热血气质。或许可以认为,路阳作为一名新导演,《绣春刀》系列作为路阳创作生涯早期的转折性作品,标志着路阳作者性的初步成型。叛逆的内核和精神气质是路阳这一阶段所呈现出的有别于其他新力量导演的独特作者性,而这一作者性的诞生与武侠电影类型本身的“侠气”正是相互赋予、相互成就的关系。随着路阳创作生涯的不断延展和导演艺术的逐步成熟,这一作者性或许会发生变化,但《绣春刀》系列作为新世纪以来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武侠电影,使路阳成功“突围”的同时,也迈出了体制内作者稳健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