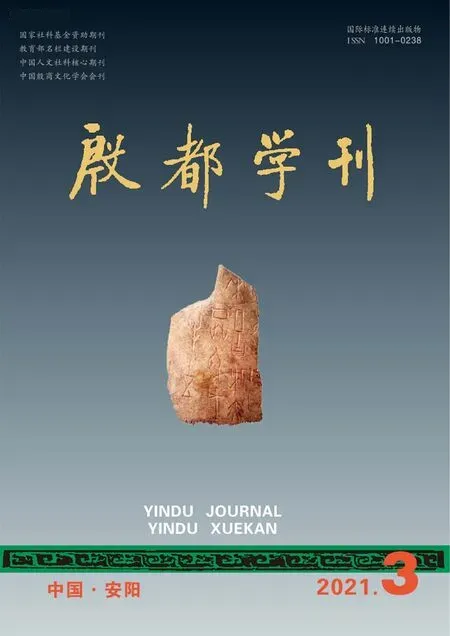论李渔的政治态度与民族情感
2021-11-26张成全
张成全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甲申、乙酉之变,明清之际的文人士大夫都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沉重考验。士大夫们或抗争以至于死,或隐居不予合作,或投诚以效忠新朝,或甘心以做顺民。战乱使士大夫殊途异辙,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明末清初的鼎革之变对李渔的人生选择、政治立场、生活态度甚至是性格构成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甲申(1644),李自成乱起,李渔刚过而立之年,这时的李渔颇富慷慨任侠之气。丁澎《笠翁诗集序》作于康熙十七年戊午,忆及顺治初的李渔,有言曰:“予与李渔交最久,顺治初即识于婺州,谈说时务,欢然无所忤。时李渔年方少壮,为任侠,意气倾其座人。”对此有论者曰:“李渔此时的慷慨任侠,或许染有明季士人尚义气、好大言的积习,未必切于世用。”(1)黄果泉:《雅俗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0页。但应该注意的是,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这种慷慨任侠之气在青年士大夫中是一种常态表现。李渔此时正值盛年,尚义气、好大言似更多的与时局现状、性格年龄有关,而与晚明习气关系并不紧密。至于是否切于世用,不是我们讨论的范畴。丁澎在婺州初识李渔,他的印象应该大致符合李渔当时的情况,不会有很大的夸饰成分。从李渔现存的早期诗文来看,丁之所言基本准确。
目前,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李渔在国变之际那些慷慨任侠的诗篇,列出的诗篇主要有《吴钩行》《古从军别》《赠侠少年》《乱后无家暂入许司马幕》《婺城乱后感怀》等。以此证明李渔在鼎革之际的政治态度。但事实上,这些诗并不是为同一事件而发,也不是在同一时间段内所作。仔细区别这些诗的产生时间及意义对了解李渔国变前后的政治态度很有价值。在五古《古从军别》中,妻子支持丈夫的“义举”,支持丈夫从军 “言雪君父耻”。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这位女子首先想到的是师儒的教诲:“人生学何事?忠孝而已矣。”支持丈夫为国为君效忠。此诗既为拟作,诗里所言就可能不是确指。但“君父耻”似不能浪言,应该是实有所指。联系当时情况,所指事件有两种可能,一是崇祯后期的明朝接连不断的辽东败绩,二是甲申之乱、崇祯煤山自杀。而前一种可能更大。因为从《一家言》的编年次序来看,《古从军别》上承《问病答》,下远接《甲申纪乱》,而《问病答》,单锦珩撰《李渔年谱》(2)单锦珩:《李渔年谱》,《李渔全集》第12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认为明显作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之前,《古从军别》所作时应该也在此前后,至迟也在甲申之前。《单谱》并未给《古从军别》编年,因为其确未有明确编年的痕迹。这样看来,《古从军别》就极有可能作于崇祯甲申之前。这个时期,李渔为诸生,忙于应举。国家屡遭外侮内乱,朝野不安,作者藉此抒发自己甘愿从军,实现忠君报国的志向,当符合其实际情况。李渔诗中张扬为忠为孝的儒家道德理念,充满了慷慨任侠之气。七言律《赠侠少年》创作时间则更早。《单谱》认为应在崇祯十四年之前:“生来骨格称头颅,未出须眉已丈夫。九死时拚三尺剑,千金来自一声卢。歌声不屑弹长铗,世事惟堪击唾壶。结客四方知己遍,相逢先问有仇无?”类似的还有七绝《少年行》:“睚眦相争过便休,相逢仍上酒家楼。宝刀不肯轻尝试,留报人间二大仇。”这些诗实唐人《少年行》之流亚,抒发少年轻财好侠、睚眦必报的豪爽气概。李渔的《交友箴》曰:“譬遇非其主,岂敢自称臣。郑重父母字,不敢呼他人。”表达了谨慎择友、忠孝两全的观念。这些诗从内容及其编年位置来看,应属于李渔的早期诗篇。
《甲申纪乱》之后,李渔尚有写豪侠的诗作,如《赠郭去疑》《胡上舍以金赠我报之以言》《戏赠曹冠五》等诗。然此时的李渔已今非昔比,遭逢丧乱,李渔虽尚有脱不去的游侠情结,但对游侠豪气又有了新的认识。如《赠郭去疑》诗曰:“长安贵游侠,尔独持清狂”,“借伪全吾真,庶几两无怨”,“我闻此谠论,不觉心神怡”。在游侠与清狂之间,李渔何以更肯定郭的清狂?其原因是世事变了,“自言今世情,所忌惟冰霜”。另外,国变之后,李渔迹近赤贫,诗中多有对那些裘马翩翩的公子和侠士的礼赞,无非他们都慷慨好施、以结贫交而已。如《戏赠曹冠五》:“尔非公子行,裘马何翩翩。呼卢凭一掷,博取黄金千。长安游侠儿,睥睨目睊睊。结徒思报复。岌岌囊中膻。”可以看出,李渔此时对游侠关注的兴趣,已不在对君父国家的忠孝上面,而在于游侠轻财乐施的属性,在于游侠是否能够扶危济困、接济像他这样的贫士。此时作为贫士的李渔,已经渐渐消失了以往的誓“雪君父仇”的豪侠志气,变得极为现实。他要做鲁仲连,为人消难解纷。他劝曹饮酒享乐,弃金如土,散尽财产。如此看来,李渔此时的“散财”主张已渐渐远离了早期豪侠诗中的“轻财仗义”之内容,使人很容易与李渔的贫穷联系起来,这不仅成为他后来颐养哲学中“劝富人分财”主张的先声,而且也是李渔人生哲学中自我色彩的初步显露。李渔此诗虽是戏言,然字里行间仍然掩饰不住当时他的困境和苦衷。
从当初的豪侠义气到后来实际实用,李渔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转折点应该是甲申、乙酉之变,或者说是战乱与弃举的偶合。
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李渔三十三岁,他准备再度应乡试时,中途闻警折回,作有五律《应试中途闻警归》,其中有句“诗书逢丧乱,耕钓俟升平”、“中流徒击楫,何计可澄清”。李渔认为自己空怀壮志,但无力澄清天下,只有隐居避难以待升平。诗中透露出的悲愤和无奈,仍不乏儒生的治平之情怀。《甲申纪乱》则是直接记述甲申之乱的诗篇。 此诗仿杜甫五言诗,记述当时的战乱和自己的感受。“兵去贼复来,贼来兵不至。兵括贼所遗,贼享兵之利。如其吝不与,肝脑悉涂地。纷纷弃家逃,只期少所累。伯道庆无儿,向平憾有嗣。国色委菜佣,黄金归溷厕。”作者将官兵与盗贼、土匪同视,将他们对百姓大众的交相残害刻划得入木三分。诗中充满了诗人对受难民众极其真实深切的悲悯之情。在这场战乱中,李渔不只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在战乱中东躲西藏、辗转挣扎,历经饥寒困危,备尝忧患。人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伤时忧民的情怀,故吴修蟾评为:“痛愤不堪再读!”
然需要指出的是,“忧国”和“忧民”历来是儒者在战乱时的高尚情怀,但在具体的个人身上,有时就很难兼顾。杜甫就有着这种执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3)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仇兆鳌:《杜诗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他不管穷达,都要 “致君尧舜”、“忧民爱物”以天下为念,成为令后世景仰的楷模。而李渔的态度明显趋向于后者。在李渔的心中,对被战争伤害的民众的同情远胜于对君主国家的忧虑。他对官军无休止的占有与索取颇为气愤,视之与绿林、黄巾辈为同类,认为三者都是戕害人民的盗贼,这里就有着明显的政治取舍。他说:“人生贵逢时,世瑞人即瑞。”这里的“世瑞”只是一个太平盛世的泛泛概念,并未指向哪个具体的朝代。与杜甫相比,李渔更倾向于“忧民”的一面,即关注战乱中“蜉蝣即同类”的芸芸众生,体现了儒家思想民本关怀的一面。《甲申纪乱》里淡化了前期报国从军誓雪君父耻的古道热肠,淡化了杜甫致君尧舜的政治志向,而以极大的同情给予战乱中的民众。简言之,就是忧民胜于忧国。
二
但这并不是说李渔已彻底忘掉了儒生的责任,对君父国家漠不关心。如果说《甲申纪乱》写的是内乱时李渔的政治态度,那么随之而来的满清入关而出现的“华夷之辨”则进一步考验着李渔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感情。国变之际李渔对入关的满清政权如何看待?他的政治态度如何?李渔当时没有留下多少可资征引的言论,后来在诗文中谈到过,但时过境迁,那些言论已不能作为考察李渔当时政治态度的主要依据。如此,李渔当时的诗文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时期李渔作七古《避兵行》、五律《乙酉除夕》、七律《乱后无家暂入许司马幕》及《婺城乱后感怀》五言律、七律各一首,五律《丙戌除夜》、七古《婺城行吊胡中衍中翰》、五律《挽季海涛先生》等。这些诗作无疑是了解李渔当时的状况与心态最直接和最真实的资料。
顺治二年乙酉五月,清兵屠扬州,下江南,六月,清兵入杭州。明各镇溃兵骚扰浙东。同时明总兵方国安与金华总督朱大典有隙,率兵攻金华。这时的浙西,鼙鼓四起,马乱兵慌。李渔率家四处躲避。《避兵行》记录了当时的状况:“八幅裙拖改作囊,朝朝暮暮裹糇粮。 只待一声鼙鼓近,全家尽陟山之岗。”
此诗题下注为:“乙酉岁各镇溃兵骚浙东时作。”面对明朝溃兵的骚扰,李渔携家逃难,东躲西藏,一直处于惊恐焦虑之中。由于这些明朝溃兵和贼寇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使得李渔感到“上天入地路俱绝”。于是决心“舍身取义”,“先刃山妻后刃妾,衔须伏剑名犹烈”。这里“舍身取义”之“义”为何物?是在溃兵流寇的骚扰中保一己之清白,而不至于降志辱身,还是对即将来到的满清政权的不满所生发的君臣大义呢?答案当然是后者。乙酉之际明朝许多士大夫行为可以作为最直接的诠释。他们舍生取义,或自杀身亡,或全家赴难。所谓“衔须伏剑名犹烈”,正是指此。在外族入侵、国家危亡的时节,士大夫的志节声名才显得非常重要,这也可以从他后来的诗文中找到旁证。顺治三年丙戍(1864)清兵破金华,李渔有《婺城乱后吊胡中衍中翰》中有“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轻则鸿毛重泰山,志士谁能不沟壑”,“既喜君能殉国难,复喜君能死知己”。又《挽季海涛先生》云:“服官无冷热,大节总宜坚。师道真堪表,臣心不愧毡。” 《乙酉除夕》有“忠魂随处有,乡曲不须傩”之语。这里既有对清兵暴行的愤懑,又有对殉国大节的激赏,这就是李渔“舍身取义”的真实含义。
但李渔并没有这样做,他未食明禄,没有在君臣大义道德防线的风口浪尖上,没有必要担当志节有亏的罪名。但作为儒生,他并未丢失君臣大义的道德理念。不能殉身为国,只能转而伤时忧民起来。乱后归来,李渔写了一首五言律《婺城乱后感怀》,诗曰:“骨中寻故友,灰里认居停。”还有七律《婺城乱后感怀》。李渔一直保持着甲申之乱以来的伤时忧民之情怀,对连续不断的战乱的痛恨以及对和平的渴望是如此强烈。除此之外,“有土无民谁播种,孑遗翻为国踌躇”之叹透露出稍许亡国之恨与故国之思。在这样的时局下,李渔对身家性命的关心远远超出了对明王朝命运的关心。他最大的希望是战乱早平,过上和平的生活。五律《乙酉除夕》:“鼙鼓声方炽,升平且莫歌。天寒烽火热,地少战场多。未卜三春乐,先拼一夜酡。忠魂随处有,乡曲不须傩。”就表现出这样一种期待。
从顺治二年乙酉(1645)到顺治四年丁亥(1647),是李渔民族情感最为复杂激烈的时期,顺治二年五六月,清廷下了剃发令。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清军攻占南京,多尔衮即遣使谕令多铎:“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4)《清世祖实录》卷17,《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51页。剃发令先是在京城严酷的实行,后又扩展至江南,朝野为之震惊,当时执行的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剃发令下,江南本来已经归顺的地区又掀起了抗清浪潮。太仓、秀水、昆山、苏州、常熟、吴江、嘉定等广大地区义民纷起,纷纷杀死清军安排的地方官吏,开始了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功。顺治三年六月,清兵破金华,守城总督朱大典自焚。李渔这个时期的诗作中有一些是关于剃发的,如五律《丙戌除夜》:“髡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屋留兵燹后,身活战场边。几处烽烟熄?谁家骨肉全?借人聊慰己,且过太平年。” 顺治四年,李渔作七绝《剃发》诗二首。其一云:“一束匀成几股分,不施膏沐也氤氲 。趁伊尚未成霜雪,好去妆台衬绿云。”其二云:“晓起初闻茉莉香,指捻几朵缀芬芳。遍寻无复簪花处,一笑揉残委道旁。”另有五律《丁亥守岁》:“著述年来少,应惭没世称。岂无身后句,难向目前誊。骨立已成鹤,头髡已类僧。每逢除夕岁,感慨易为增。”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在顺治三年六月金华被攻下之前,李渔至迟在顺治二年的除夕已经剃发,当了大清朝的顺民。但此次剃发,李渔实是出于保全性命的需要,而不是心悦诚服的去接受它。顺治三年之《丙戌除夜》,其中有“髡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之句,表达了对清廷剃发制度的强烈不满。剃发后第二年的《剃发二首》,则于戏谑与自嘲中显出浓浓的无奈。《丁亥守岁》曰:“骨立已成鹤,头髡已类僧。”对剃发的厌弃与憎恨仍很强烈。
顺治四年丁亥(1647),清兵已肃清了浙东福建的残明政权,清朝在江南统治渐趋稳定。此时李渔究竟有没有一点反清情绪呢?这个时期的文字中,李渔除了一些对剃发表示激愤的文字外,尚有一些触及时忌、不敢公开的文字。李渔曾在一些诗中暗示过。前引《丁亥守岁》:“著述年来少,应惭没世称。岂无身后句,难向目前誊。”暗示他那时有过一些触及时忌的作品。还有《吊书四首》(其三):“文多骂俗遭天谴,诗岂长城遇火攻。切记从今休落笔,兴来咄咄只书空。”这种“难向目前誊”“兴来咄咄只书空”表现出的忌讳与无奈,应该是惧怕政治高压的结果,而不是心悦诚服的顺民做派。联系李渔此时的诗歌所表达的情绪,没有理由认定李渔是在矫情,没有理由否定李渔反清倾向的存在。对明亡清兴,不无遗憾,但有时还似乎透露出一丝对明王朝恢复的期望,《如梦令·慨世》云:“逝水滔滔可挽,世事悠悠必返。何故得前知,物极当从势转。不远,不远,眼见冲和气满。”此词具体作于何年尚不清楚,但“逝水”“世事” 云云,指明朝灭亡,当无疑义。李渔从“物极必反”的古代哲学中,预期了明朝的恢复。但时局并非总如他所料。其实,李渔的政治态度呈现出实用多变的特征,而最终的政治取向仍依赖于时局的变化,但随着清王朝统治的进一步稳定,李渔身上的反清倾向渐趋消解了。
需要说明的是,李渔顺治初年的反清倾向并不是仅仅源于王朝的更替,在更深的层次上,还是一种文化上的排斥。王朝更替,对于士大夫来说,其归顺与反抗客观上反映出其道德情操的好坏,然就绝大多数的平民和相当一部分官绅地主来看,改朝换代却很难刺激他们的政治感情。在他们看来,一朝天子一朝臣,谁当皇帝都无所谓。但要改变习俗沿传的汉家衣冠,会使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文化拒斥。在这些国民的意识里,其民族认同感远甚于国家认同感。顺治初年发生的剃发与反剃发的斗争,在表面上看是一场政治斗争,然在更深层次上它实际是一场文化较量。满清用武力强迫原来的汉族仿效自己而改变原有的服饰衣冠,在汉人看来,这不啻是摧毁其文化,是一种屈服的标识,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清初的文人用“髡”或“髡刑”指代清廷的剃发令。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髡”即强制剃发是一种刑罚。是对人身体人格的摧残。如常被人引用的屈大均《长发乞人赞》:“哀今之人,谁非刑余,为城旦舂,髡也不如。”(5)屈大均:《翁山文外》卷12,清康熙刻本。强制剃发确实被看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另外,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又是儒者尊严的堕落。孟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 剃发近乎阉割——几乎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因此,杨廷枢说: “杀头事小,剃发事大。”无论官绅还是平民,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夷狄”,在这种保卫汉人传统上,士大夫和平民百姓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李渔剃发诗歌中所透露出的情绪无疑就是这两种情绪的融合。他的反清情绪大多来自于剃发带来的文化和身体上的屈辱,但和明清之际许多士大夫相比,李渔反清倾向并不强烈。李渔剃发诗叙写剃发后的无奈与失落,时而伤感,时而愤怒,但终究属于一种情绪的即时展露,并不能转变为一种恒定的政治态度。明清之际不乏拒绝断发、誓不屈服的士大夫,这些士人在剃发事上表现出激烈的政治情绪,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归庄等遗民。他们或死节,或归隐,或逃僧,不与新朝合作。而更多的士人则迫于饥饿,屈节事清。《不下带编》卷六谈到这一点时说:“仇少宰沧柱尝谓埴曰:‘少陵之投书京兆,邻于饿死;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饿。两公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量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少宰此言,两公知己,亦忠厚之旨也。埴按:宋齐丘与人书云:‘其为诚恳万端,只为饥寒二字。’盖人即品行至高,而饥寒不可忍,古今有同叹耳。”(6)金埴:《不下带编》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62册,第480页。而李渔本无什么政治情结,又为生存所迫,故一旦时局发生逆转,他的政治态度就可能发生转变。
三
顺治四年丁亥(1647),李渔三十七岁,回故乡做 “识字农”。一直到顺治八年辛卯。李渔过着避乱隐居的生活。这期间,鲁王政权败走厦门,清朝统治渐趋巩固,明朝已成强弩之末。如果说李渔乡居初期的顺治四年,他尚有一些诗篇表现对剃发的激愤情绪,那么随着时局的稳定,伊山别业的建成,李渔似乎已忘掉了曾有的不满,开始蜇居乡下,倾心品味起田园生活的快乐。此时的李渔写了不少描写伊园和山居之乐的诗文。固然,李渔的这种快乐来自于长期乱离之后难得的宁静以及劫后余生的庆幸,但在这快乐生活的后面,还有静观时局、及时调整自己政治态度和生活状态的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渔彻底抛弃了对满清政府的反感,当起了顺民,并且成为一个新朝统治狂热的鼓吹者。
在乡居三年之后,顺治六、七年,李渔将伊山别业“悉书所有而归诸他氏”,(7)李渔:《卖山券》第1卷,《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移家杭州。虞巍《怜香伴序》有“笠翁携家避地,穷途欲哭。余勉主馆餐”之语,李渔《卖山券》有“兵燹之后,继以凶荒,八口啼饥”之语。可以看出,生存问题确是导致李渔移家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多年以后,李渔忆及当时的乡居生活,每每生出留恋向往之情。如《闲情偶寄》中说:“计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仅有三年。”李渔后来的感受与当时实际状况何以差距如此之大?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其一;与城市生活相比,乡居期间简朴疏淡的生活此时更具吸引力。移家杭州之后,李渔“卖赋以糊其口”,以创作来维持其并不简朴的生活,后又经营书铺,组建家乐。终其一生,李渔一直奔波于途、惨淡经营、常常处于焦虑困苦之中。时过境迁,乡居三年生活自然隐去的是痛苦,而留下的是舒适美好的回忆。其二,李渔移家杭州,其实也有急于享乐、不肯终老山中的因素存在,而城市繁华生活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治圃》诗说:“老农不可为,圃事尚堪娱。宁为夫子薄,吾愿学樊须。”(8)李渔:《治圃》,《李渔全集》第1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7页。顺治八年元旦,李渔作《辛卯元日》,透露出这种心愿:“又从今日始,追逐少年场。”此年,李渔四十一岁,明鲁王被逼走厦门。战乱已平,清朝统治大局已定,隐居乡下的李渔开始出山。此时,他最关注的是怎样找到途径,以过上一种富裕而又体面的生活。因此,所谓“华夷之辨”之民族意识以及 “忠君报国”的家国意识在性命和安乐面前显得十分的轻微,政治上的衡量几乎已退出了他的思考领域。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操觚染翰、卖文糊口的谋生之路。可以说,像大多数国人一样,李渔此时并不时刻以家国为念,只要生活能够安逸,谁掌政权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李渔此时已经默认了清朝的统治,做起了大清的顺民。山居生活固然美好,但远远不能满足他的享乐追求,所以,一旦时局稳定,他就忍不住寂寞而重返城市。明朝遗民们那种由于明朝灭亡而表现出的寂灭感和负罪意识,在李渔的身上很少看到。从顺治八年一直到康熙十二年三藩乱起,李渔涉及政治的文字非常少见。
康熙十二年癸丑(1672),平西王吴三桂反,三藩之乱开始。李渔此时有诗文记载此事。三藩之乱虽然是清王朝的一次内乱,但它又是一次满汉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在平静多年之后,三藩的倒戈使当时许多汉族士大夫重又燃起了排满黜异、恢复故明的希望。而在李渔诗文中却找不到一点排满情绪。如《督师尚书李邺园先生靖逆凯歌》二十首,(9)李渔:《笠翁诗集》卷3,《李渔全集》第2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55-399页。其十二有,“首级累累动满千,不竿惟向树头悬。旧红未褪新红继,权当花开日日鲜。”又如其十六、其十八、七律《赠郑辅庵协镇》、七律《赠叶修卜使君》等,在这些诗文中,李渔对三藩之乱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极为明确,视之为“狂氛”“妖氛”,褒扬那些平定叛乱而立下军功的将士,承认并维护清王朝“王土”统一。此外,李渔涉及三藩之乱的作品还有《制师尚书李邺园先生靖逆凯歌序》、《祭福建靖难巡海道陈大来先生文》、七古《军兴三异歌为督师李邺园先生作》等。这些作品显示,李渔此时已没有了当初“华夷之辨”所带来的困惑和不满,心悦诚服地做了清王朝的顺民,并且成为清朝统治的狂热拥护者。如《督师尚书李邺园先生靖逆凯歌》是对靖逆战争中立下赫赫军功李将军的赞扬,但其中对其大开杀戮、将叛贼悬首枝头示众的赞赏态度(其十二),使人感到李渔已彻底站到清廷的立场上了。那些挂在树枝上的头颅都是三藩的汉族士兵和一同起事的普通民众,他却有近乎残忍的描述:“旧红未褪新红继,权当花开日日鲜。”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李渔极端谄媚的颂辞中,其人性扭曲和残忍何至于如此?他早期的那种忧民爱物的情怀究竟哪里去了?其实,李渔的这种政治态度并不是三藩之乱时才有的。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李渔客居汉阳半载,作诗文很多,其中《汉阳树》可见鼎革之际他对李闯、明朝、清朝的态度:“明君死逆闯,国祀同朝露。宫阙既已灾,城廓亦非故。安用登眺资,犹然备诗赋。不如假贼手,尽伐无所顾。兴朝既鼎革,江山若重铸。”(10)同上书,第17页。诗借景抒怀,实是李渔对明清易代历史的一个全面的总结。诗中说:“明君死逆闯,国祀同朝露。”李闯为贼寇,明朝灭亡于逆闯,是李渔对明清易代基本史实的认定。他还认为,明朝灭亡乃国运使然。“寻其所以然,曰斩同明祚”,清王朝的出现,似乎也是运之使然,“兴朝既鼎革,江山若重铸”。此时李渔虽对明王朝不无留恋,但已没有了顺治初年对满清王朝的排斥感。他承认清王朝的合法地位,承认朝代更替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这应该是李渔在经历甲申、乙酉乱后才形成的的政治见解和王朝更替史观。这种观念,李渔终其一生未有改变。
然也应该看到,李渔后期的政治观中明显存有一种机会主义的成分,他奉行的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哲学。比如其《严陵纪事》八首其七:“未能免俗辍耕锄,身隐重教子读书。山水有灵应笑我,老来颜面厚于初。”(11)同上书,第370页。坦露出自己的矛盾心态。但又说:“晋风偷薄,凡为七类者,只知得禄之为荣,不念失身之可耻,当(桓)元受禅之日,蛇行鼠伏于其庭者,不知凡几。”(12)李渔:《论桓玄伪旌隐士》,《笠翁别集》卷1,《李渔全集》第1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30页。嘲笑那些晚节不保、失身于新朝的官吏,但在小说诗文中却又大肆颂扬满清王朝的统治。在现实生活中,他既与明遗民杜濬、毛先舒、陆圻、孙治、胡彦远、沈亮臣、余怀、包璿等遗民交好,又与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张缙彦等降清的“贰臣”来往。龚鼎孳死后,李渔作诗悼念,诗云:“公历天街四十年,不止为民解倒悬。在在少陵开广厦,庇尽寒士无迍邅。俸钱不足继以货,日积月累成逋仙。”(13)李渔:《大宗伯龚芝麓先生挽歌》,《笠翁诗集》卷1,第55页。龚曾对李渔有援手之恩,诗中对龚的赞许,并非全为溢美之词,也有李渔的真情流露。这些看上去非常矛盾而又荒唐的观念,其实在当时是很有市场的。对于这种现象,陈寅恪先生曾有论述: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尚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标准及风习,以应付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作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14)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2页。
而李渔则显然属于其所说的“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标准及风习,以应付环境”之人。考察李渔的人生道路可以看出。早期的李渔无疑受到了儒家忠孝节义及侠义意识的影响,当战乱来临之时,他虽然也肯定儒家的大节,抨击战乱、同情百姓,但当战乱危及自己身家性命的时候,李渔则更多的是考虑实际的生存。他对故明政权虽然也有感情,但这种感情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此时他将个人的利益置于家国的利益之上,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汲取道德中比较有利的成分,建立自己的实用哲学。因此,李渔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传统的儒家道德,他的这种道德实用主义事实上就是一种市民哲学。
结语
概言之,李渔一生的政治态度凡三变:一是明崇祯后期,李渔为诸生,此时正值盛年、血气方刚,所做诗文充满了为忠为孝的儒生情怀和慷慨轻财的豪侠之气。二是甲申之乱至顺治八年之间,是李渔政治态度和情感极为复杂的时期,也是李渔顺应时局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政治立场的时期。对于甲申之乱,李渔表达了自己痛恨战乱、同情百姓、祈望和平的心愿,展现了其伤时忧民的儒家情怀。而随之而来的乙酉之乱,在四处避难的奔波之中,李渔也曾有过舍生取义的想法,但最终都不可能实施。面对清廷强制剃发的命令,李渔也有过激愤,也有过无奈。这时,等待观望中的李渔,他的政治取向其实具有实用多变的特征,这与他的处境与个性有关。三是顺治八年之后,此时李渔已经成为清朝的顺民,由于生活的需要,他经常周旋于达官显贵之间,作了不少赠答应酬之作,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地透露出他的这种政治倾向。尤其是三藩之乱时,他的作品反映了其反对叛乱、褒扬忠臣、维护清王朝“王土”统一的政治倾向。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清王朝就忠心耿耿,李渔没有恒定的政治情结与道义追求,当战乱危及自己身家性命的时候,李渔则会更多的考虑实际的生存,而非君臣大义。他将个人利益置于家国利益之上,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政治态度。因此,李渔这种实用的政治态度背离了传统的儒家道德,显示出明显的市民哲学的特征。
弃举后的李渔虽然经常混迹于公卿士夫之中,自称贫士,但事实上他已经逸出士人行列。李渔虽弃士籍,但并未彻底地沉入社会底层。像明末的山人一样,李渔此时实游荡在士、民之间,既是逸士又是游民。不确定的社会身份地位便容易招来评价上的歧异,如此,对李渔的褒贬不一就容易理解了。所以,一味地用士人标准来衡量他的个性行为实为不妥。康熙六年丁末(1667),周亮工为《资治新书》二集作序曰:“笠翁虽以高才未遇,无经营天下之责,而读书观理,专以时务人情为符合。”周氏之言可谓允当矣!李渔自弃士籍,自然也就“无经营天下之责”,不用承担士大夫应有的社会责任。社会对此也给以很大的宽容,全祖望说:“布衣报国,自有分限,但当就其出处之大者论之,必谓当穷饿而死,不交一人,则持论太过,天下无完节矣!”(15)全祖望:《春及堂文集序》,《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20-1221页。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对李渔政治态度的实用多变,当时人很少谈及,或者说不把它作为评价的重点,并给与更多的宽容,自然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