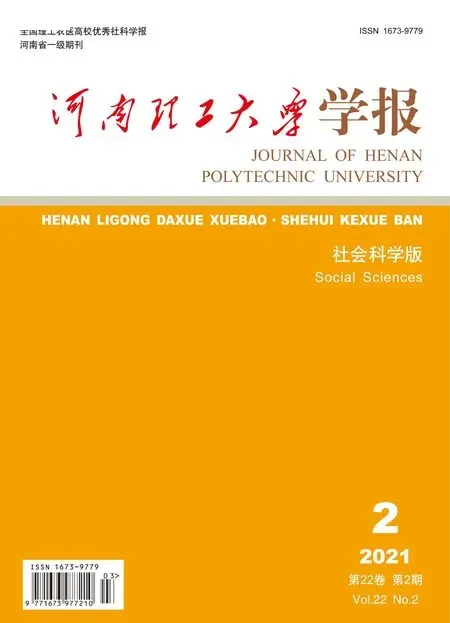共情匮乏与共情提高
——从共情角度解读《好邻居日记》
2021-11-26沈珏莹吴兰香
沈珏莹,吴兰香
(东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多丽丝·莱辛(1919—2013)是著名的英国作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享有国际盛名。莱辛勇于触及老年女性书写这个“禁忌话题”,在她的小说《好邻居日记》中特意描写了一位年逾90的老年女性的身体、心理状态,以及她与一位中年女性间的友谊。《好邻居日记》于1983年以多丽丝·莱辛的笔名(简·萨默斯)出版,故事围绕着两位中年老女性展开:独立、高效、能干的职业女性简娜,驼背、体弱、衰老,住在又脏又乱的房子里的莫迪·福勒。一些学者讨论了《好邻居日记》中人物间的关系,例如,罗格斯大学弗吉尼亚·泰戈教授(Virginia Tiger)分析书中简娜与莫迪的“双女性”特征以及“替身母亲”的作用。在她看来,传统观点认为年轻女性的魅力与年老女性的肮脏常常是对立的,但书中双女性手法的运用则打破了这种对立[1]7。此外,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小说的“老年化”问题上。西班牙学者匹克拉斯借用“消失的身体”这个概念,说明西方社会中老龄化现象严重,但“老年”一直带有负面的文化含义[2]。戴安娜·华莱士教授探索了老年化的过程,指出老年化与身份、女性气质及身体等方面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3]。我国学者林斌则用“恐老症”的概念分析了小说中的“越界之旅”,简娜在工作、家庭及社区中穿行,这使得她意识到老年女性在城市中一直为人所忽视,并在过程中获得了个人的成长[4]。除了探讨人物关系与老年化问题,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苏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将小说与现实相结合。她指出,社会对于步入人生第三阶段的女性作家常常抱有过高期许,并对此表达了她的质疑[5]。这些研究从多个角度对《好邻居日记》进行了剖析,也很有启发。然而,笔者认为简娜、莫迪两人各自生活态度的转变、以及她们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与共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笔者将从“共情”角度,试图给文本提供新的解析。
“共情”(empathy),也常常被译作“移情”“同理心”“通情”等。学界对于“empathy”没有统一标准的译法,本文参照西蒙·巴伦-科恩作品《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的中文译本,将empathy译为“共情”。“empathy”一词在20世纪早期由德文单词Einfuehlung翻译而来,特钦纳于1909年在其著作《思考过程的基础心理学》里介绍 Einfuehlung 时使用了“empathy”一词。在20年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对“共情”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现象学家斯坦因认为,“共情就是我们感知他人意识的过程,并把共情描述为“主体间性体验的基础”和“可能对外在世界认识的前提条件”[6]。近年来,学界涌现出更多对“共情”研究的著作,其中巴伦研究了“共情”对人类残酷行为的影响,哲学家迈克尔·斯洛特研究了“共情”在关怀伦理学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斯洛特指出,“共情是利他主义关怀或关心他人(幸福)的一个重要来源和支撑”[7]15。本文基于上述两位学者对“共情”的研究,分析简娜与莫迪在各自家庭和生活中的共情匮乏与两人相处过程中的共情能力的提高。简娜共情能力的匮乏导致其与丈夫、母亲的冷漠关系;而莫迪周围的人普遍缺乏共情能力,因而她需要独自面对生活的不幸,这进而导致她对陌生人缺乏信任。正是由于共情能力的提高,简娜和莫迪之间得以形成一段特殊而真挚的友谊。
一、家庭中的共情匮乏
在巴伦看来:“共情就是我们放弃了单一的关注焦点,而采取了双重的关注焦点。”[8]20“所谓‘单一’的关注,指的是我们只关注自己的内心、自己当下的想法和知觉。而‘双重’关注的是我们在关注自身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别人的内心”[8]20。也就是说,当人们具备共情能力的时候,也会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当人们缺乏共情能力的时候,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简娜缺乏共情能力,莫迪生活在没有共情的家庭生活中,这种共情匮乏导致了她们各自家庭生活的不和谐。
小说一开始,叙述者简娜便告诉读者她的丈夫弗雷迪死于癌症。令人惊讶的是,简娜对于弗雷迪的去世十分冷漠。在她看来,两人的婚姻是一种利益关系。那个时候,简娜便是一个具有“单一”关注的人,她所考虑的仅仅是她的个人利益,对于自己能够持续工作挣钱养家而感到十分自豪。更重要的是,工作成为她逃避弗雷迪的借口,从而避免了两人的尴尬相处。可以看出,简娜是故意避免与弗雷迪感同身受的。当弗雷迪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当弗雷迪想要尝试交流时,简娜总是躲开;而当弗雷迪生病卧床、瘦地皮包骨头时,简娜则把工作作为借口来避免照顾与安慰弗雷迪。在斯洛特看来,共情指的是当我们看到另一个人痛苦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这种感觉[7]13。从这点来判断,简娜的共情匮乏导致了她与弗雷迪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她无法感受弗雷迪的痛苦。当她听说母亲患癌症时,同样的情况又一次发生,她的第一反应是这对她而言不公平。她拒绝身体接触,也反感母亲身上的味道,而姐姐乔姬则跟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乔姬能够与母亲谈论任何话题,简娜与母亲独处时却感到尴尬、不自在。简娜将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体面的工作和光鲜的外表上,她也试图去体会与理解母亲所遭受的身体与心理痛苦,但以失败告终。因此,在这个阶段,简娜仍处于共情匮乏的状态中,她拒绝身体接触,也拒绝情感交流,不愿感受他人的痛苦,这也导致了她不和谐的婚姻生活和母女关系。
如果简娜是缺少共情能力的人,莫迪则是生活在共情匮乏的环境中,无法得到来自父亲、继母与丈夫的关心。在莫迪的回忆中,她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但自从父亲变得富有后,他便与波莉产生了婚外情。后来,波莉对她十分刻薄,让她睡在房子最顶层的阁楼上,连最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莫迪在她的回忆中陈述道:“她从来没想过我天天都要在那些楼梯上爬上爬下,也没想过我就住在这冰冷的地方。”[9]70然而,波莉却丝毫感受不到她的痛苦与恐惧,是一个典型的只顾自身利益、不顾她人感受的共情匮乏之人。更糟糕的是,莫迪的亲生父亲对她也十分残酷,他不顾莫迪是否能够活下去,也从未回复过莫迪姨妈的信,完全沉浸在对金钱、享乐与性的追逐当中,将他的女儿们视为累赘,或者物品。巴伦认为:“如果人的注意只有单一的焦点,也就是说,你关注的只有自己当下的兴趣、目标、愿望或计划,对别人的想法或感受毫不在意,那么你的共情实际上就关闭了。”[8]21对待女儿时,莫迪的父亲显然缺乏共情能力。此外,莫迪的丈夫劳里在儿子约翰尼出生后,对莫迪的态度急剧转变。有一天,劳里甚至趁莫迪不在的时候从保姆那里偷走了约翰尼。劳里的行为十分符合巴伦所提出的零度共情概念,他指出,“零度共情并不等于有些人所说的‘恶’。但如果你接近了这样一个毫无共情的人,你就可能受到他的语言辱骂或身体袭击,你也可能觉得他对你毫不关心、一点不为你考虑”[8]41。尽管从法律上来讲,劳里没有犯罪,但他却从未考虑过莫迪的处境并再三地伤害莫迪——他追求、抛弃莫迪,又突然出现,再突然消失,最后偷走了他们的儿子——不能将莫迪的痛苦与绝望感同身受。
综上所述,简娜缺乏共情能力,以一种冷漠的态度对待家人,她拒绝任何形式的肢体及心理接触,将自己生活的重心放在工作与外表之上。莫迪则生活在缺乏共情的家庭当中,独自体会痛苦、不幸与绝望,得不到家人真正的关心。这种共情匮乏使得简娜与莫迪无法体验温暖幸福的家庭生活。
二、社会中的共情匮乏
人们常常把老人当作儿童,认为养老院和医院才是最适合安置他们的地方。然而,老人也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并渴望真诚的陪伴和关心,而社会上很多人不能真正了解老人的真实需求。在书中,“好邻居”是被市政府雇佣的一群妇女,这个组织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好邻居”并没有发挥理想作用,反而恰恰暴露了社会中的共情匮乏。巴伦将共情的定义扩展为“共情是一种能力,它使我们理解别人的想法或感受,并用恰当的情绪来回应这些想法和感受”[8]21,同时指出共情至少包含两个阶段:识别和反应。这意味着共情不仅需要意识到他人的感觉与想法,而且需要以合适的情感和行为来对这种感觉和想法做出回应。在“好邻居”这个体系里,两者都没有得到实现。“好邻居”们并不能给予老人真正关怀,她们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为了简单地完成任务,不掺杂任何特殊情感,也并未真正进入到老人的生活当中。因此,“好邻居”及其他政府人员的错误“意识”又进一步导致了错误“反应”。莫迪提到,在医院的时候,“你感觉你的思想给弄没了。他们待你像小孩子一样。我不想要……”[9]44。整个社会倾向于把老年人看作“第二童年” ,这也进一步导致人们像对待没有自理能力和独立想法的小孩一样对待老年人[2]。的确,有些老人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自理能力或思考能力,这时候养老院或医院不失为一个合适的选择。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应该忽视莫迪这一类群体——她们虽已年迈,但仍有一定的自理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与正常的成年人除了生理上的衰老之外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莫迪希望得到正常的关心,社会却认为她脆弱、需要人照顾,这种认识的不同导致了社会中的共情匮乏,人们无法正确理解老人的真实需求,也无法用正确的情绪和行为做出正确回应。
此外,社会中的共情匮乏并不仅仅存在于“好邻居”体系中,而是广泛地存在于整个社会当中。“好邻居”无法对老人将心比心,而生活中真正邻居之间的感情也十分疏远。简娜的邻居彭妮太太是个70岁的独居老人,她一直以来都想与简娜交朋友,但简娜却不愿意,简娜生病的时候,彭妮太太提出要照顾简娜,也被她拒绝了。事实上,彭妮太太自己也需要他人的注意与关心,她在关心他人的同时也想要被他人关心。但是,简娜对此只觉得不耐烦,认为彭妮太太是个累赘,这表明真正的邻居也并不明白对方真正的想法,无法与对方感同身受。在陌生人之间,共情匮乏也普遍存在。简娜给莫迪雇的电工吉姆,在看到莫迪的房子后感到十分惊讶与困惑,他对屋里子的气味和肮脏感到十分反感,他问简娜“她怎么不住养老院?她不应该那样过”[9]24。 这表明,吉姆实际上对莫迪是抱有同情的,因为他觉得莫迪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然而,同情并不是共情。斯洛特指出,人们会对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感到难过,并希望他们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并不能真正感受到这种痛苦,因而仅仅是一种同情[7]13。吉姆为莫迪感到难过,认为她应该在养老院中渡过一种更体面的生活,这是一种积极的期许。但问题是,他没有真正理解莫迪真实的内心——虽然年老孤单,但却充满能量。吉姆的想法是简娜一开始接触莫迪的想法,也是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想法。
可以看出,人们常常认为老人是无用的,在社会中处于隐形地位,老人的正常诉求不能得到满足。“好邻居”体系并未发挥出真正作用,生活中真正的邻居也十分疏远,没有能够相互照顾。共情匮乏,尤其是对老人的关心缺失,广泛地存在于整个社会当中。
三、简娜与莫迪:共情能力的提高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简娜是一个缺乏共情能力的人,而莫迪生活在缺乏共情关怀的家庭和社会当中。然而,在简娜与莫迪建立友情的过程当中,简娜的共情能力得到了增强,而莫迪也因此得到了真正的关心,不再将他人拒于千里之外。莫迪与简娜之间的“替身母女关系”弥补了双方在家庭中的情感缺失,简娜虽不是“好邻居”,但却发挥了这个体系应有的社会功能。因此,从简娜和莫迪的关系当中,可以看到家庭及社会层面共情能力的增强,这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泰戈认为简娜照顾莫迪并不是完全无私的,命令和控制使她拥有母性的统治权,而不是孝顺的从属地位[1]13。然而,笔者认为,她们之间的母女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关系之上,她们是互补的:在照顾莫迪的过程中,简娜的共情能力得到了提升,对生活、死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通过与简娜交流,莫迪找到了可以分享喜怒哀乐的人,填补了她几十年来感受到的孤独感与被忽视感。简娜第一次遇到莫迪时,将她描述为一个“老巫婆”[9]14,但她又同时承认,“莫名其妙地,从那一刻起我就很喜欢她”[9]15,这种第一印象为她们后来建立特殊关系奠定了基础。在后来接触的过程当中,简娜体验了亲密的肢体接触和情感接触,而这些都是她之前的生活中所缺乏的。当简娜为莫迪清洗身体的时候,简娜看到了莫迪蜡黄蜡黄、满是褶皱的身体,瘦骨嶙峋的胳膊、下垂的乳房。在清洗过程中,简娜不断回忆起弗雷迪和母亲,因为简娜从未见过他们的身体,更从未为他们清洗过。这种身体上的接触对于简娜而言是全新而特别的体验,使她更加深刻了解莫迪以及她所代表的老年群体的生活状况。更重要的是,在清洗的过程中,简娜“感受到她身体内勃勃的生机:生命力。它是如此之强大,生命”[9]51。这也是她在之前的生活中从未思考和体验过的,她体会到莫迪的活力、对生活的热情。一开始,简娜只是同情莫迪,因为跟其他人一样,简娜认为莫迪又老又弱又没用,活着只是苟延残喘罢了。但之后,她对莫迪产生了共情,因为她开始真正了解莫迪,知道她仍然充满活力、充满感情。简娜全面进入了莫迪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她帮莫迪做各种家务活:购物、洗洗刷刷等她之前很少甚至从未做过的事情。在情感交流上,她倾听莫迪的故事,与莫迪谈心,想象莫迪过去的生活,了解到她自身永远不会经历的人生,并被莫迪顽强的毅力所感动。
因此,在照顾这个“替身母亲”的过程中,简娜弥补了她与亲生母亲、甚至是与丈夫弗雷迪之间的情感缺失。简娜可能对母亲感到愧疚,她与莫迪的关系也摆脱不了母亲的影响,但对简娜而言,莫迪并不仅仅是母亲的替代物。莫迪让简娜对于人生、死亡有了更多的感悟和思考。当莫迪病重躺在医院里时,简娜思考了生活与死亡的意义,承认“不管是健康还是生病,莫迪都对别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关于她自己,关于生命,关于她所经历一切的本质,她做了如此这般的表述;莫迪如此强势地走过人生,我才不信她会消融飘逝,像随温度上升而蒸发的水雾”[9]219。是莫迪改变了她对老年和死亡的看法,使她感受到生命力的顽强。在那个时刻,简娜能够真实地感受到莫迪遭受的痛苦和她对生活的渴望。另一方面,莫迪也从简娜那里收获了关心与爱。如前文所述,莫迪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都非常艰辛,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她排斥他人,对陌生人缺少信任。当简娜进入她的生活后,她终于可以与人分享那些或是甜蜜喜悦、或是悲伤痛苦的往事。尽管过去的故事是一种“欺骗性的怀旧”,它们却代表着莫迪对生活的向往,而讲述它们也是一种情绪宣泄。尽管莫迪常常把自己武装得刀枪不入,“总是在批判、挑剔,绷着冷冰冰的嘴”[9]121,她的内心仍然渴望着温暖,希望简娜可以经常过来,甚至留下来陪伴她。她们就像家庭成员一样,向对方大声嚷嚷,又很快地在一起欢笑。在这段关系中,莫迪得到的还有简娜的尊重。简娜逐渐学会不把想法强加给莫迪,而是从莫迪的角度和莫迪对世界的看法考虑,因为那些真正深刻关心别人的人能够接受别人的想法、渴望和恐惧,他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现实[7]12。“共情是一款万能溶剂。任何问题只要浸泡在共情中都能解决”[8]143。简娜与莫迪之间形成关心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便是诺丁斯所说的“相互认同并且赏识对方的反应”[11]53。简娜的关心和莫迪对简娜这种关心的回应共同促成了这段特殊的友谊。莫迪没有拒绝简娜的关心,而是期盼着简娜去她家里,听她讲述往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样,简娜又能够从莫迪的回应中得到更多信息,了解莫迪的需要和兴趣。因此,她们共同的努力保持和发展了她们之间的关心关系。如果莫迪一直漠视简娜的关心,她们之间也不会形成这种特殊的友谊。无论是简娜还是莫迪都从这段关系中受益匪浅,简娜从一个共情匮乏的人发展成一个具备共情能力的人,莫迪则收获了真正的关心和温暖,在自己生命的末期得到了他人真正的关爱,走出了孤独的一人世界。
四、结 语
巴伦指出:“没有了共情,人际关系就濒临破碎,使我们伤害彼此并挑起冲突。有了共情这项资源,我们就能解决矛盾,团结社群并为他人缓解痛苦。”[8]141由于采取“单一的关注焦点”,简娜一开始无法对别人产生共情,婚姻与家庭关系冷漠,而身处共情匮乏环境中的莫迪度过了孤独、不幸的大半人生。在社会中,无论是政府安排的“好邻居”,还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对老人的身体与身心状况都存在着误解,无法与老人感同身受。幸运的是,简娜与莫迪遇到了彼此,建立了关心关系。简娜在与莫迪的肢体及情感接触的过程中提升了共情能力,改变了对老人固有的、偏执的看法,加深了对生命、老年及死亡的理解。同时,莫迪也遇到了真正的“家人”,收获了真正的关心与爱护。
在《好邻居日记》中,莱辛以独特的眼光与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中老年女性的生存处境与情感建设。运用社会学中的共情理论分析莱辛的《好邻居日记》,不但拓宽了莱辛作品研究的角度,而且进一步探究了莱辛作品中的社会关怀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