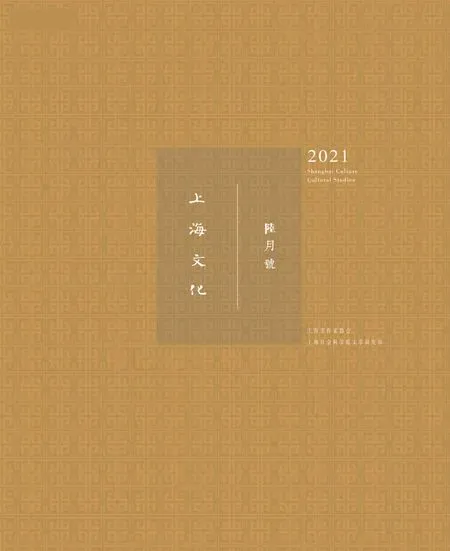世界文学视域下的中国革命书写
——以马尔罗和横光利一为中心
2021-11-26侯茗予
侯茗予
卡尔·马克思曾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4页。马克思这一精准论断,成为20世纪历史发展的重要主题。翻看20世纪的世界历史,“革命”成为不可或缺的主角。近代上海作为中国开埠最早的城市,吸引着世界资本不断汇集,进而成为各种先进文化思想的交融共生之地。同时在世界性革命运动推动下,上海一跃成为东亚革命的中心。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作家横光利一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开启他的中国之旅,并于1932年发表以这座城市命名的作品《上海》。②需要指出的是,横光利一在1928年11月就开始在日本《改造》杂志上连载其中章节, 并最终于1931年(昭和六年)完成了长篇小说《上海》。详见童晓薇:《横光利一的〈上海〉之行》,《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3期。与此同时,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也以中国的革命运动为题材,在1933年发表其成名作《人的命运》。这两部作品都是以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为创作背景,《上海》描述的是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日本商人甲谷、参木以及高重等人在上海的见闻经历。上海在他们眼中是一座物欲横流的“魔都”:戒备森严的西方租界与摩登时尚的十里洋场,西式风格的高楼洋房与破旧不堪的老式弄堂,西装革履的商人政客与衣衫褴褛的穷苦大众,强烈的形象反差构成相互对立的二元空间。与《上海》中大量都市描写不同,贯穿于《人的命运》全书的主题是不断地“行动”,“行动主义”成为马尔罗革命书写的关键词。小说采取镜头体的方式去还原大革命前后形形色色的人与事件,整部作品采用日期和时间为标题,渲染革命行动的紧迫感。这让两部作品的节奏和基调截然相反。横光利一笔下的革命循序渐进、娓娓道来,马尔罗笔下的革命则是激进的,不断行动的。值得注意的是,横光利一的《上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尔罗革命叙事的“逆写”。①横光利一在其随笔中曾提及马尔罗的作品,同时文中注释指出,据其自述,横光利一写这部小说的部分动机,是因为当时马尔罗以同一时期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征服者》《王家大道》在西方名噪一时,故而意欲以这部作品与之相颉颃。具体内容见横光利一:《感想与风景:横光利一随笔集》,李振声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第43页。横光利一试图勾勒出一座“欲望的上海”,来对抗马尔罗笔下“革命的上海”。本文通过对两部作品互文性比较研究,揭示出世界文学视域下的中国革命,如何通过域外作家的文化想象完成其“跨文化旅行”,进而展现在世界舞台上。
一、作为“他者”的上海
1928年,横光利一从日本远渡重洋,开启他的上海之行。横光利一此行目的一方面是受到已故挚友影响,“让我去上海看看的是芥川龙之介。在亡故的那一年,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去见识见识上海,所以翌年我便去了上海”。②横光利一:《感想与风景:横光利一随笔集》,第47页。另一方面,横光利一也是为了暂时摆脱喧嚣不安的日本文坛,“那时候,朋友们都左倾了,如果我不去上海,我想我也会左倾的”。③刘妍:《论旧上海中游荡的外国人形象——横光利一〈上海〉与马尔罗〈人的状况〉的比较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年第5期。横光利一在上海停留期间,花费大量精力去感受上海的“细节”:他每天既游走在繁华的都市中心,又穿梭于城市边缘的弄堂里;他希望把这座城市的繁华与贫穷,美好与罪恶都尽收眼底。与横光利一对上海的切身体验不同,马尔罗并未在上海驻足,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其多年来对亚洲革命运动的考察和亲历,以及在香港和广州的生活见闻。马尔罗将上海视为世界都市,来自各个国家的革命者在这里展开自己的“革命行动”。《人的命运》一经发表就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并获得1933年龚古尔文学奖。但无论是横光利一还是马尔罗,他们都是以“他者”的视域去观察上海。物理空间所带来的疏离感,让个人欲望书写与宏大革命叙事在这座“魔都”相互碰撞,相互融合。
在小说开篇,横光利一描绘了夜色中的上海:“在茫茫夜雾之中,海关的尖塔显得烟气迷蒙起来。堆放在堤坝上的木桶坐着许多苦力,他们的身上湿漉漉的。残破不堪的黑帆随着钝重的波涛东倒西歪地吱吱嘎嘎向前移动。长着一张白皙明敏的中世纪勇士面孔的参木满街转悠之后回到了码头。河畔长条椅上坐着一排满脸倦容的俄国妓女。逆潮行驶的舢板上蓝色的灯光,在他们默默无语的眼睑前一刻不停地旋转着。”④横光利一:《寝园》,卞铁坚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3页。坐在堤坝上“湿漉漉的苦力”和长椅上“满脸倦容的俄国妓女”与“一张白皙明敏的中世纪勇士面孔”的参木,构成视觉感极强的画面。苦力和妓女的形象都化约为身体欲望的能指符,与参木清晰明朗的轮廓形成对比。横光利一试图把参木比作中世纪的勇士,通过这一角色去对抗这座现代化的“恶之都”。横光利一的意图显然失败了,他后来意识到“上海不仅是世界上最新型的城市,而且还是一个不管你的民族有着怎样了不起的思想和传统,都将在这里显得一无用处的地方”。①横光利一:《感想与风景:横光利一随笔集》,第44页。参木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在掌握上司贪污的罪证后不愿与其同流合污,结果却是被上司解雇。失业后的参木无所依傍,只能依靠好友甲谷接济,进入到日本人开设的纱厂中谋生。甲谷是参木多年的挚友,在他身上几乎寻不到理想主义者的痕迹,更多的是作为商人的贪婪。在甲谷眼中,上海是世界财富的流转地:“一走进商业中心地带,便可以看到外汇经纪人的马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向并排耸立的银行疾驶。拉动马车的蒙古马,以它飞快的速度,每时每刻都在拉动纽约和伦敦的外汇行情。坐在车上的经纪人几乎全是欧美人。他们股票买卖的差额,每时每刻都作为东洋和西洋动力的源泉而消长。”②横光利一:《寝园》,第29页。迷恋资本的甲谷走进处于财富漩涡中心的股票交易所:“市场正好处于交易高峰,大厅里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墙壁上挂着成排的电话机,场内显得微暗,人群满脸油汗,摩肩接踵地向买进和卖出这两个中心拥挤过去。”③横光利一:《寝园》,第29页。眼前一幕深深刺激了甲谷,他励志成为一名经纪人跻身上流社会。
与横光利一的表述机制不同,马尔罗笔下的上海到处充斥着死亡气息和浓浓的火药味。小说以一次暗杀事件为开端,革命者陈受组织委派去暗杀一名军火经纪人,目的是拿到他手上的武器交接单。陈承袭夜色来到经纪人的房间,紧张压抑的气氛让他在慌乱中刺向目标:“只听蚊帐布撕裂的声音与刀进肉沉闷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那躯体不再滑动了。”④安德烈·马尔罗:《人的命运》,李忆民、陈积盛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4、5、16、16页。经历过杀戮的陈“陷入了极度的狂热之中。他的手指攥得越来越紧,整个手臂如同一根绳索,不停地抖动起来。这不是胆怯,而是一种自童年后为他所淡忘的既残酷又庄严的焦虑不安:他独自一人同死亡在一起,独自一人呆在一个渺无人迹的所在,虽被恐怖和血腥味儿憋得透不过气来,但他仍然无动于衷”。⑤安德烈·马尔罗:《人的命运》,李忆民、陈积盛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4、5、16、16页。这次暗杀事件的成功让组织得到大量武器,但不幸地是恐怖主义逐渐成为陈的人生信条,以至于有组织的革命运动逐渐演变为极端个人主义的暗杀行为,这也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马尔罗眼中的上海,处处潜藏着一触即发的危机景象:“兜满汽笛长鸣的冷风,带着这座处于戒严状态的城池里近于平息的嘈杂声,带着那些正在向军舰靠拢的快艇的嘶叫声,掠过每一条死胡同和弄堂深处的那些闪烁着惨淡光芒的路灯;将那些死胡同和弄堂两侧的颓垣断壁连同上面的斑斑污秽,从冷清的阴暗处显露出来。”⑥安德烈·马尔罗:《人的命运》,李忆民、陈积盛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4、5、16、16页。江边兵工厂里制造着镇压革命者的武器,而深夜弄堂的商店里则聚集一群准备起义的革命者;在这些商店的墙壁后面,“藏匿着五十万人:纱厂里的人,自童年时代每天就工作十六个小时的人,患溃疡病、脊柱侧凸病以及食不果腹的人”。⑦安德烈·马尔罗:《人的命运》,李忆民、陈积盛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4、5、16、16页。军舰、兵工厂、潜伏的革命者和数以万计患病的底层工人,形成了镜头感十足的画面,将革命风暴前夕的上海生动展现出来。
二、充满“复调”的革命书写
马尔罗作为闻名世界的革命家,亲历过很多革命运动现场。他创作的亚洲三部曲《征服者》《王家大道》和《人的命运》,都是以表现亚洲革命为主题。马尔罗希望寻找一座国际都市去呈现世界革命的宏阔图景,而上海无疑是最佳选择。20世纪初的上海国际化程度极高,遍布在金融街上的证券交易所能够影响世界各国股票价格,大量西方资本家在上海设立公司,为了攫取利润拼命压榨身处底层的中国工人:“千百万卑微的生命被另一种生命压得透不过气来,他们日夜操劳的景象正在消失。街巷尽头那些租界地,那些富人区,连同那些被雨水冲刷过的铁栅栏,变成了一种威胁,一些屏障,一些没有窗户的监狱的长围墙:这些充满残暴的地区倒是突击队人数最多的地区,在那里,人们群情激奋,严阵以待。”①安德烈·马尔罗:《人的命运》,第16-17、107页。此时共产党领导人京和卡托夫,正行进在深夜无人的街道上,他们要为即将开始的武装起义做最后准备。这次起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联手策划,其目的是为了配合北伐军南下。起义的枪声在第二天下午打响,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相继攻陷车站、兵工厂和警察署等多个要害机构。起义军的接连胜绩,引起外国资本家的恐慌,法国—亚洲康采恩公司的中国代理人费拉尔,忧心忡忡地来到警察署长马夏尔的办公室。费拉尔公司的货物,由于工人起义的爆发已经全部在站台发霉,他认为如果共产主义苏维埃在上海取得政权,那么上海所有法属企业将全部垮台。因此,他希望马夏尔出手镇压共产党缓解眼前危机。在马夏尔办公室,他遇见前来谈判的国民党代表,这位代表前来征询马夏尔的态度:“我以我党的名义向您表示感谢……他们背叛了我们,背叛了他们忠实的盟友。本来已经谈好,我们先一起合作,社会问题待中国统一以后再说。可是现在他们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因此,我想问问您署长先生,要保障将军的人身安全,法国警察该不会有什么异议吧?”②安德烈·马尔罗:《人的命运》,第16-17、107页。马夏尔欣然接受来者建议,一场幕后交易就此达成。国民党代表口中的“社会问题”,指的是国共两党打倒军阀后实行土地革命,将土地分发给穷苦百姓。共产党代表的是底层劳苦大众的利益,对这一政策当然热烈响应,这也是他们进行革命的动力。而国民党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和地主乡绅的利益,平分土地无疑是在掠夺他们手中的财富,必然会受到激烈抵制。国民党在起义关键时刻,开始暗中联合大资产阶级和国外资本家合力绞杀中国共产党,而汉口共产国际也对国民党的行为表示默许,并命令上海共产党组织停止斗争,上缴武器给国民党。京和卡托夫即将面临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陈则领导他的小组开始暗杀蒋介石的恐怖行动。
在《人的命运》中,作者采取一明一暗两条叙事线索来展开叙述。一条明线是京和陈等革命者跌宕起伏的武装斗争,一条暗线则是以吉索尔为中心展开。关于吉索尔这一人物形象,很多研究者只是将他视为作品中的“边缘人物”。但笔者在文本研读过程中,却发现吉索尔是全书隐藏的“灵魂人物”。文中第一次提及吉索尔的是陈,暗杀事件后陈惊魂未定,死亡的阴霾久不能散去,陈向京提出要去见他的父亲吉索尔,“每当需要让人理解的时候,陈总是下意识地去找吉索尔”。①安德烈·马尔罗:《人的命运》,第11、67页。陈作为共产党组织成员,为何不选择向组织倾诉,而是第一时间去见吉索尔?首先,我们需要确认吉索尔的身份。文中介绍吉索尔曾经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因为教学原因被张作霖解雇。究竟是什么样的“教学原因”呢?吉索尔透过自己的回忆给出过答案,他曾经在课堂上宣传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信条,而是一种意志。对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对你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相互了解的意志,象无产阶级那样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意志,象无产阶级那样取胜的意志,你们不应该只是为了表明自己正确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为了取得胜利而不背叛你们自己。”②安德烈·马尔罗:《人的命运》,第11、67页。而陈曾是吉索尔的学生。另外文中还提及京作为华北地区最优秀的革命干部,实际上得益于吉索尔的精心培养。通过以上两条线索可以推断出,吉索尔曾经是一位资深革命者,因为某种原因被迫远离革命。吉索尔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起义,但在暗中一直帮助京和陈。开篇被陈刺杀的经纪人,就是京通过吉索尔在柯拉毕克那里得到的消息。后来京在被捕之后,吉索尔又为京四处奔走实施营救。吉索尔始终游离于宏大的革命叙事之外,化身为无处不在的“革命符号”。
横光利一作为新感觉派代表作家,其创作理念的“新”体现在“物质中蕴含了作者的生命。感觉则能使作者的生命得以最直接最现实的展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③王天慧:《横光利一与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6期。但在《上海》这部作品中,笔者认为横光利一并未将“感觉”直接诉诸笔端,作者将底层暗涌的革命洪流隐藏在繁华都市风景中,采用隐微修辞的叙事策略去窥视中国革命的复杂面向。“革命”潜移默化地浸入到社会生活的内在肌理中,它需要等待时机蓄势而发。因此,作者塑造芳秋兰这一角色隐喻中国革命。芳秋兰是一名美丽的女共产党员,在日本人高重的纱厂中担任女工。她的身影出现在上海滩各个角落,她拥有倾倒所有男性的美貌,她时而现身于夜晚霓虹灯下的十里洋场,时而劳作在拥挤不堪的纱厂车间。她行迹如鬼魅,让试图追求她的人无迹可寻。芳秋兰第一次登场是在外国人林立的舞厅中:“山口突然从正在跳舞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个典雅的中国女人。他低声说道:‘你看,那是芳秋兰!’‘芳秋兰是做什么的?’甲谷的眼睛第一次发出了亮光,把头凑近了山口。‘她是共产党里了不起的人物。你哥哥高重认识她。’”④横光利一:《寝园》,第36、14、19页。甲谷被芳秋兰深深地吸引,“那个女人真是出色。她能做我的妻子,今生今世足矣!”⑤横光利一:《寝园》,第36、14、19页。芳秋兰究竟有多么美丽呢?作者对她的形象有着细致描述:“秋兰桥形的鼻子不时转向左右两侧的店面,穿过林荫道上的树阴向前飞驰。吐着痰的乞丐、在马路上敲着铜币的车夫、嘴上泛着油光走出饭馆的食客、叼着香烟望着人的面孔的占卦者,都回头望着坐在马车上飞奔而去的秋兰的面孔。当这些人一起回首观看时,甲谷便又想起了刚才竟然忘却了的秋兰的美貌,像他们一样感到新鲜。她那紧闭起来的嘴角、又大又黑的眼睛、鹭水式的刘海、蝴蝶形的首饰、银灰色的上衣和裙子。”⑥横光利一:《寝园》,第36、14、19页。芳秋兰第二次登场是在高重的纱厂车间。失业的参木来到纱厂帮忙,高重带着参木去女工车间。“‘你看,那个角落有个漂亮的女人。她正面朝这边。’在纵横交错的管道中间,有一个冷艳的女工在盯着参木这边。参木感到她的眼神就像手枪瞄准那样锐利。他对高重耳语道:‘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她就是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共产党芳秋兰。她一举右手,这个工厂的机器便会马上停下来。’参木一边欣赏着芳秋兰的美艳,一边凝望着她那慢条斯理的动作。”①横光利一:《寝园》,第19、72页。这是参木和芳秋兰首次相遇,而接下来车间内的一场暴乱,让两人有了再次接触的机会。参木不顾危险在混乱的人群中找到芳秋兰,并保护她逃离现场。芳秋兰为感谢参木,邀请他共进午餐。参木在席间与芳秋兰就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展开争论,参木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为日本在中国的资本蚕食作辩护,而芳秋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去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结果显而易见,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横光利一曾在杂文《诗与小说》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几乎折磨了我半生的文学生涯,从我19岁到31的13年间,马克思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②转引自童晓薇:《横光利一的〈上海〉之行》,《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3期。文中参木对芳秋兰的暧昧态度,正是横光利一对马克思主义复杂情感的投射。
在《上海》的角色谱系中,阿杉和奥尔嘉的漂泊者形象也颇具代表性。阿杉从小失去双亲,她也不记得自己如何流浪到上海。阿杉失业前的工作在土耳其浴室,参木是她的老主顾并十分喜欢她,而阿杉也“总是隔着女人们的肩头如醉如痴地望着他的脸庞”。参木对阿杉的宠爱引起老板娘阿柳不满,恼羞成怒的她辞退了阿杉。阿杉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没办法只能去寻求参木的帮助。在参木公寓前,阿杉遇到了前来借宿的甲谷,甲谷热情地招待阿杉,并让她进到寓所休息。但没想到的是,甲谷趁着夜色欺凌了阿杉,孤立无助的阿杉只能选择隐忍,这也为她的悲剧人生埋下伏笔。阿杉流浪的命运是日本军国主义大肆扩张的结果。大量日本人被迫迁居中国,利用他们的身体去占领异国“空间”:“在这里,一个人的肉体不论如何无为无职,只要他漫然着呆着,只要其肉体占据一个空间,那么除俄国人以外,都将是一种爱国心的表现。”③横光利一:《寝园》,第19、72页。参木和阿杉,还有许多日本移民都将自己的身体视为领土,他们留在上海,肉体所占用的空间便会成为“日本的领土”。奥尔嘉作为一名流亡的俄国贵族,在苏维埃革命之前过着幸福生活。突如其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让她和家人一路逃亡,流浪到上海变得穷困潦倒,最后被当作奴隶一样被买卖。她先是被日本商人木村买去做小老婆,木村在一次赛马比赛中输钱,便将奥尔嘉处理给山口。在小说结尾部分,横光利一借奥尔嘉之口道出革命的恐怖和残忍。奥尔嘉一家在得知苏维埃起义之后,沿着铁路线一路逃亡,可谓是险象环生。奥尔嘉每次提到这个场景,都会“癫痫般的抽搐”。革命让奥尔嘉由一个孝顺的孩子变成了只求果腹的禽兽,她所期待的沙皇时代已一去不返。阿杉和奥尔嘉作为漂泊的“他者”,最终被卷入世界革命的漩涡中无处逃遁。
三、革命:消亡或重生
法国著名文学史家加埃唐·皮康在谈及马尔罗笔下人物形象时曾指出:“在英雄的颂歌中,在以悲剧和热情著称的时代里出现的强烈人物形象中,在这一与各种宏大形式紧密相连的召唤中,我们似乎听到了某种痛苦的控诉。到处都出现了一股黝黑而不见底的水流,到处都看到一种无形的忧虑,一种浓厚的黑暗,没有向世界敞开的出口,也毫无光明的希望。”①加埃唐·皮康:《马尔罗》,张群,刘成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页。《人的命运》中聚焦的另一主题,就是人类在面对生存困境时表现出的孤独与虚无。陈在暗杀任务完成后去见吉索尔,向他表示自己特别孤独。在经历死亡和鲜血之后,陈发现他与同志之间产生强烈的疏离感。吉索尔无法解答陈的疑惑,枯燥的言语只会让陈感到空洞和无聊。陈对吉索尔道谢之后便起身离开,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吉索尔意识到“陈已堕入凶杀世界而不能自拔;他以自己的顽强精神投身于恐怖主义的生活之中,如同投入监牢一般。不出十年,他就可能被捕——被拷打或被杀害;在这以前,他会象一个着了魔的人一样坚定地生活在这个决心和死亡的世界之中。他的理想促使他活下去;可现在,却要置他于死地”。②安德烈·马尔罗:《人的命运》,第62、237、238、333、338页。吉索尔这段内心独白,一语成谶地言中陈的悲剧命运。在最后的刺杀任务中,陈决定牺牲自己,“他欣喜若狂地向它奔去,闭上眼,扑到了上面”。③安德烈·马尔罗:《人的命运》,第62、237、238、333、338页。炸药包的轰天巨响让陈失去知觉,在他醒来后,“浑身上下没有一块肌肉不疼,除了痛苦还是痛苦。他试着去摸裤兜——兜没了,裤子没了,腿了没了。只剩下一堆烂肉。另一只手枪放在了衬衣兜里,他抓住了枪筒,本能地用大拇指扣动扳机。愤怒的警察将陈从车上踹飞,陈使出平生最骇人的力量,终于把手枪筒拉到了自己的嘴里。他开枪了,可是他已经感觉不到了”。④安德烈·马尔罗:《人的命运》,第62、237、238、333、338页。陈以恐怖主义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他终于用死亡祭奠自己孤独虚无的一生。京和卡托夫也在监狱中服毒自杀,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革命者们接连牺牲,是否意味着革命的彻底消亡?马尔罗在小说结尾给出答案。京的妻子梅带着同志们的期盼,来到日本神户去迎接吉索尔。吉索尔在日本友人帮助下在这里定居,并成为大学艺术系的客座教授。梅向吉索尔转达了海默希里对他的思念:“请告诉吉索尔,我们都在等他……革命刚刚经受一场可怕的疾病,但并没有夭折。是京和他的同志们——不管他们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不管他们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把革命传播到人世间来的。”⑤安德烈·马尔罗:《人的命运》,第62、237、238、333、338页。吉索尔静静地聆听并陷入冥想:“他头一次想到,将他推向死亡的光阴在他身上流过,并没有使他与世隔绝,反而在一片宁静和谐的气氛中将他与这个世界联结在一起了……‘人人都在受苦’,他冥想着,‘每个人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有思想’。”⑥安德烈·马尔罗:《人的命运》,第62、237、238、333、338页。吉索尔拒绝了梅的邀请,岁月让他失去革命的热情和勇气。吉索尔准备在他乡度过余生,但他的革命精神将继续激励前仆后继的共产主义者。
《上海》中酝酿已久的工人罢工终于在高重的纱厂爆发,共产派工人与反共派工人在车间中肆意厮打,场面极度混乱。在制止骚乱的过程中,高重和警察开枪打死打伤几名工人。中国工人因为“这具尸体而变得更加牢固了”。高重隐约感觉到芳秋兰正是这次罢工的幕后策划者。中国人的爱国情绪被史无前例地调动起来。无数群众和工人涌入各国租界领事馆,要求严惩凶手。在慌乱的现场,参木看到被警察逮捕的芳秋兰。“秋兰斜靠在巡警的胳膊上,在他眼前静静地观望着周围的骚乱。这时,她看见了他。她笑了。”①横光利一:《寝园》,第117、120、121页。参木不顾一切地冲向警察,再一次救出芳秋兰。芳秋兰和参木逃离到安全地点后,芳秋兰热情地拥吻了参木。“参木从秋兰那向上挑起的眼角中看出了她恍如隔世的激情,同时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向冰冷的北极移动。”②横光利一:《寝园》,第117、120、121页。参木无法克服自己内心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恐惧,他突然间开始害怕接受芳秋兰的爱意,他忽然变得语无伦次,无情地驱赶秋兰离开。“秋兰向他靠过去。她让苦闷隐藏在眼睫毛下面,有一次吻了他。他从秋兰的嘴唇中感受到的已不再是她的爱情而是轻蔑了。”③横光利一:《寝园》,第117、120、121页。芳秋兰在离别前希望能再次见到参木,但没有得到回应。参木甚至拒绝告知自己的名字,一段美丽的邂逅就此谢幕。参木在小说结尾最后一次见到男扮女装的芳秋兰,并收到芳秋兰递给自己的一张字条,它记录了可能找到芳秋兰的地址。参木没有选择再次相见,而是回到阿杉身边。横光利一同时借山口和甲谷的对话,透露出一个不确定的消息:芳秋兰可能以间谍名义被同伙枪杀,起因是她涉嫌与一名日本男子私通。中国革命最终还是消亡在横光利一笔下。
四、结语
马尔罗的《人的命运》和横光利一的《上海》,都是世界现代文学史上难得的佳作。两位域外作家通过自己的笔触深刻剖析了中国革命,让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场”呈现在世界文学图景中。值得注意的是,马尔罗和横光利一的创作背景与世界范围内左翼文艺运动有着密切关联。20世纪世界性左翼浪潮在革命的激荡下,迅速成为一个全球性事件。马尔罗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自然对中国革命充满了向往和憧憬。《人的命运》所要追问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如何面对残酷的战争。无情的杀戮和死亡让人的存在变得荒诞不经,每一个革命者都试图找寻投身革命的原因和意义。马尔罗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去唤醒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但遗憾的是,马尔罗的世界革命经验与中国革命现实情境存在着某种隔阂。正如戴望舒对他的评价:“无可置疑,马尔罗十分友善,拥有难得的写作才华,但他最大的缺点在于错误理解中国革命的精神。看看《人的状况》的人物,近乎所有人物都是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亦只是出于个人关系,他们将革命视为一种逃避人类命运的方法。小说里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人物担当重要角色。所有这些描述都是虚假的,也使中国革命显得滑稽可笑。另一方面,近乎所有人物都是欧化的,或更确切地说是法国化的。这些都予我们中国人触目惊心的印象。他避免描写典型的中国人,不敢面对上海的无产阶级,因为他未能充分理解他们。结果:他在我们眼前展示的是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图像,属其他地方的,很遥远的。总而言之,马尔罗是个极具才华的作家,但他没有能力理解革命。”④转引自邝可怡:《黑暗的明灯——中国现代派与欧洲左翼文艺》,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第3页。
马尔罗笔下的中国革命者没有具象称谓,仅仅是一个姓氏代名词,如陈、京等。它意味着马尔罗只是将自我经历的革命实践镶嵌到中国革命背景中,缺乏“斗争的实感”。横光利一笔下的中国革命不同于马尔罗所描绘的宏大革命现场,他所感受的中国革命仿佛河底的暗流潜伏行进,只有在暴风雨来临之际才能喷涌而出。横光利一眼中的中国革命更像是触不可及的神秘力量,参木对芳秋兰情感的复杂心态正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心投射。横光利一一方面希望了解马克思主义,了解中国革命;一方面却与其保持着距离。他和马尔罗一样,都是透过“他者”视角去俯瞰中国革命,而未能平视彼此并投身其中。但瑕不掩瑜,马尔罗和横光利一毕竟是通过自己的笔触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革命,将上海——这一东亚革命中心呈现在世界文学舞台上,这无疑是一个开拓性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