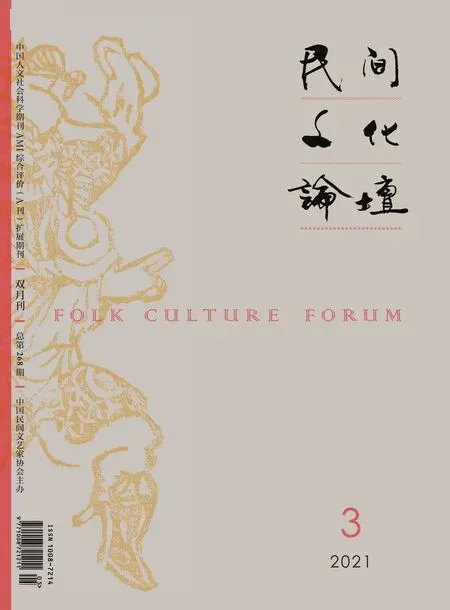重审中国民间文艺的“民研会时代”
2021-11-26祝鹏程
祝鹏程
在中国民间文艺发展史上,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民研会时代”,这一时代横跨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三十余年的时间。这段历史曾经被认为是民间文艺发展的黄金时代,近年来随着学术范式的转型,这一时段的学术遭到了新一代学者的严苛批评。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民间文艺的“民研会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重审其意义和价值。
自“五四”运动到延安时期,草野中的民间文艺、市井中的通俗文学因扎根民间、受众广大,一直被现代知识分子视为开展社会改造的利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人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实践。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成立。研究会的章程指明了其职责:“本会宗旨,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70年发展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20年,第18页。由此可见民研会的时代特色: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文艺组织,它是在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文化的语境中形成的。
中国民间文艺事业一直有“为学术”与“为文艺”的两种侧重,新中国的天平倾向于后者。民间文艺被认为是人民的口头创作,体现劳动人民的生活、理想与斗争。将民间文艺中的积极因素转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正面资源,顺理成章地成为时代的命题。郭沫若在民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民间文艺研究的五个目的:“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在创作中)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即观风知政)”“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创造新民族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①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70年发展史》,第12—13页。,无疑点明了民间文艺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在此后的三十余年里,中国的民间文艺事业一直是由民研会主导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横向的职能上讲,民研会是一个全能型的机构,包含的门类极为多样,成立之初,就包括了民间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部门,因而有“小文联”之称。在国家体制的支持下,半官方性质的民研会主导着民间文艺学的学术发展,规划着学科走向,掌控着学术资源的分配,组织成员深入基层进行采风。与此同时,民研会还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组织相关作品和著作的出版;创办《民间文学》与《民间文学论坛》杂志,展开学术讨论。新中国民间文艺发展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如1957年关于搜集整理的探讨、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发动、1964—1966年对《玛纳斯》的调查采录和翻译工作、20世纪80年代的“三套集成”的搜集出版与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等等,都离不开民研会的组织与协调。
从纵向的组织上讲,民研会是民间文学工作者的群众团体,是社会主义文艺生产与权力运作机制中的有机组成。系统的顶端是全国性的民研会,辐射到各省、市、县(区)的民研会。同时,民协还与政府文化机构(文化部、各省市区文化局、文化馆),各省、市、县级宣传部,各地高校,以及基层民间文艺爱好者形成紧密的联系,各机构存在着复杂而细密的互动与协作。以1984年编辑出版“三套集成”的文件为例,这是由民研会联合文化部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下发的,“三套集成”编辑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文件则由中宣部转发,收文单位为各省市的党委宣传部、文化厅(局)、文联,从中不难看出存在着一张从中央到基层的文化权力网络。
民研会的这些特点使中国民间文艺事业具有了一些显著的特色。首先,注重对民间文艺学诗学传统的挖掘与发扬。当时的民间文艺在“五四”运动与延安时期的基础上,又深受苏俄影响,将民间文学视为文学的一部分,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对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②刘锡诚:《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自序”,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7—11页。正如贾芝所说:“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③贾芝:《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70年发展史》,第21—33页。通过深入的采风,将民间的文本搜集上来,再以新社会的价值标准对其展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整理,使其成为适合阅读的文学文本,再将其传播到民众中去,一方面起到审美的作用,给大众以美的感染;另一方面达成教化的目的,培养民众的国家观念与阶级观念,激发民众作为“劳动人民”的主体意识。因此,民间文艺的首要任务是搜集整理文本,发掘人民口头创作中蕴含的“民众心声”(尤其是政治性、阶级性的进步因素),其次才是学术研究与阐释。
其次,民间文艺的生产机制极为复杂。这表现在多个方面:
一、和创立之初的民俗学一样,新中国的民间文艺学也是多学科参与的。民研会是专业组织,但其文化事业又有很强的“非专业性”。民研会的成员与工作人员,如郭沫若、老舍、林山、柯仲平、吕骥、张庚、古元、汪曾祺等,包括了不同的职业身份,其中尤以作家为多,他们往往是从各自的知识结构出发来从事民间文艺的,他们搜集的民间文艺作品也是在多部门、多背景的从业者的协作中产生的,并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
二、从口传文本转化为书面文本的过程,需经历采录、誊写、整理、编辑与出版等一系列过程,要经过搜集、集体讨论、确定主题、分头修改、定稿润饰等多个步骤。因此,无论是技术性的问题,还是现实政治的规约,乃至于具体人事的牵扯,都会对文本的最后生成产生影响。
三、民研会有一批基层的会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基层的“采风”制度。这批基层文艺工作者包括了地方文化馆干部、乡村中小学教师、工厂文艺积极分子等,也有国家干部,但更多的是“编外人员”,代表人物有肖甘牛、张士杰、陈玮君等。他们是传统乡土社会的一分子,深谙地方文化传统,主要从事基层文化普及和教育事业,业余投身于民间故事与歌谣的采录。他们的身份更具草根性,所以他们能搜集到大量当地流传的精彩文本,并以地方性的语言呈现之;同时,他们的从业姿态往往较低,面对国家的号召,他们会比注重创作个性的精英作家更具配合意识,并不将“改写”与“再创作”视为搜集整理的歧途。借助这套“采风”制度,基层工作者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条件,也使自己的影响超越了地方,并将地方的“小传统”推向国家;国家则将自身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基层文化的毛细血管中。
最后,民间文艺对民众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当时民间文艺工作的重点是产出适合大众阅读的文本,这些文本与民众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从业者是以文学性和可读性为首要考虑目标的,因此,他们往往对材料进行大胆的整理、改编与重写,使之成为“结构严谨、形象丰满、风格统一”①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阿诗玛〉整理的真相》,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撒尼族叙事长诗〈阿诗玛〉专集》,内部出版,1979年,第9页。的文艺作品。我们看到的《阿诗玛》《一幅壮锦》《刘三姐》等均是经过大胆编排的文艺作品。借助故事文本、动画、绘画、戏剧等不同文类载体,这些作品和最广大的普通民众产生直接联系(其影响远大于文艺作品),深度参与了民众精神世界的塑造。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等人通过搜集改编,再造了彝族长诗《阿诗玛》的时代主题,在此基础上改编的电影被大众所喜爱,在宣传婚姻自由、塑造西南民族同胞的形象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借助谢德铣、陈玮君等人的搜集与再创造,徐文长的故事得以脱去猥亵的趣味,成为褒扬民众智慧的生动典型,由此家喻户晓。相声由原先京津一带的市井“玩意儿”,成为全国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艺术”,也离不开老舍、吴晓铃和罗常培等作家的编写与鼓吹。20世纪60年代,各地对义和团、太平天国、捻军和其他近代农民起义与反抗外国侵略者故事的搜集,对于激发民众的国家意识居功至伟,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渔童》等作品,成为很多人爱国情感的启蒙与想象西方的媒介。在这些实践中,民间文艺当仁不让地扛起了大旗,在文化建设、社会整合、民众娱乐上起到重要作用,乃至对当代文化建设有积极的反哺。
在上述实践中,一些个案不乏意识形态争议,撇开这些因素,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大加肯定的:尽管当时的民间文艺有粗粝草莽之处,但气魄是非常大的,民间文艺事业与民众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是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干预、塑造民众的精神世界,鼓舞民众参加社会建设的利器。在民研会的规划与设想中,民间文艺在国家整体文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位置,从业者们没有把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高雅艺术分开来,而是将其看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事业。
当然,这一体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造成了重搜集、轻研究的局面。在很长时间内,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是比较薄弱的,停留在主题思想分析等表象领域。施爱东曾批评民间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囿于20世纪50年代的概论框架、低级重复等一系列问题②施爱东:《民间文学的“概论教育”与“概论思维”》,《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不能不说与20世纪50—70年代轻视研究的取向有关。再如,对文本的肆意修改,不仅造成相关的伦理问题,也使学者无法获得可靠的“原生”文本,使研究的“科学性”大打折扣,阻碍了研究者进入文本内部做细致分析。此外,由于受政治的影响,民间工作缺乏可持续性,很多工作有具体的规划,但往往没有实行,不了了之,不少辛辛苦苦搜集到的文本没有得到充分的整理和研究,就因为政治风向的变换或工作重心的转移而被封存起来。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1964至1966年的玛纳斯搜集工作,民研会的陶阳、郎樱等人和中央民族学院学者、新疆地方专家合作,辛苦调查采录了大量文本,协作翻译完成6部《玛纳斯》,但因“文革”爆发,这些资料只能束之高阁,最终造成部分文本遗失。当然,还有过分强调政治性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
不过,对政治与民间文艺关系的思考,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维度和更开放的视野。民间文艺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与民众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是包含了影像、声音与文字的综合文本,其生产包括了对文本的整理、改写、传播等方方面面,这些方面的互相牵制往往会削弱意识形态的影响。此外,在传播的过程中,民间仍然有一定的“闪转腾挪”的空间,整理后的文本未必能被地方民众接受,当地人传承的很可能仍然是未经整理的传统文本。更有甚者,民间会采取狂欢化的方式解构权威文本。因此,纯文学研究中采用的“一体化”概念并不适用于概括当代民间文艺的局面。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文艺市场化的推进,既定的文艺生产机制面临着转型。1987年,民研会的内部资料登载了一则有深远影响但未被学者充分重视的消息:
在最近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四届二次理事会上,理事们反映个别省市在给予中国文联各协会会员知识分子待遇的同时,却不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包括在内。1986年11月20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书记处向中国文联汇报了上述情况。经中国文联秘书长会议讨论,认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中国文联的团体会员,是与其他全国各协会一样的全国性专业群众文艺学术团体,它的会员理应与中国文联其他协会的会员享受同等待遇。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应享受中国文联各协会会员同等待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中国民间文艺界通讯》,1987年第1期。据笔者2020年12月22日对刘锡诚先生的访谈,这一事件是民研会改名为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重要动因。
从这个材料可以看出,一直以来,民研会比文联的其他组织更具基层性。而随着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基层工作者对编制、待遇等有了明确的要求,原先那套广泛发动编外人员的“采风”机制,以及“但问耕耘,莫问收获”的“螺丝钉”式的工作伦理遇到了问题,民研会的体制酝酿着改变。同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此后不久,随着行政对学术影响力的减弱与学术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影响力越来越大,民协体系在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格局中不再“一枝独秀”,民研会的时代最终结束。民间文艺学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民协和高校有了明确的分工,高校负责学术生产,民协则在民间文艺学的组织和联络等工作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与此前“非专业化”的运作相比,当下的民间文艺学更加学院化、专业化、科学化。这一转变带来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学者突破了单纯的收集与整理,对旧有的问题意识、基本术语与概念体系、学科使命、学术伦理等展开深刻的反思。学科日益从纯文学、溯源式的研究转向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由描述性的学科逐渐转为阐释性的学科。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学科也构建出了一套更加科学的话语体系。
这一转型既和客观形势变化相关,更是思想解放和学界主动追求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变化同时也是以失去部分昔日的荣光为代价的,民间文艺失去了草创时期淋漓的元气,日益边缘化,它对民众生活的参与度降低,对整个文化事业的反哺力度也大大削弱。学术在日益理论化、精细化的同时,也失去了观察与把握宏大议题的兴趣与能力,“日益盛行的区域研究和个案描述,使民俗学的知识体系日趋破碎,研究也不断走向碎片化”①安德明、杨利慧:《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民间文艺从原先全社会的文化事业,退缩成为了一个学科。在学科的转型中,既有得,也有失,对得失的衡量,以及对背后学科深层问题的揭示与检讨,恐怕还远远没有完成。
如今,在回顾“民研会时代”时,流行的叙事往往采取了一种断裂的姿态。站在当下的立场,勾勒出一条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文本搜集到立体描写,再到表演和语境研究的发展脉络。在这一立场上反观过去的历史,强调当时的学者不注重语境、忽略对本真文本的记录、缺乏对表演各要素的关注等。这种叙事既基于一定的历史观察,也难免有现实的考虑,即通过反思、批评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学术史,来确立当下重视“民俗生活”和“整体研究”的民俗学范式的合法性。实则历史并不完全如此,如果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我们会发现,“民研会时代”的研究仍然保持了相当的丰富性,学者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劳动人民的讲述技巧”和“田间地头的讲述情景”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说,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他们甚至比当下学院派的田野调查更强调与受访人的平等相处与情感沟通②可参考李星华的《搜集民间故事的几点体会》、董均伦与江源的《行万里路,找千人谈》、孙剑冰的《略论六个村的搜集工作》、张士杰的《我的体会和认知》等,以上文章均见钟敬文主编:《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时代》,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92—297、298—308、309—318、326—335页。,只是对于他们而言,这些不是那个时代最迫切的使命。上述的批评道出了部分的真实,但也难免有“自说自话”,将历史简单化、标签化之嫌。当然,并不是说那段历史不需要学术反思,而是说学术反思应该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不应该简单地用“后知之明”来否定之前的学术传统。须知,不同的学术传统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产生了不俗的成就,也各面临一系列需要克服的问题。
因此,要回顾这段历史,就需要打破成见,到具体的历史、政治与文化语境中去,从民间文艺学思想史与民间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对民研会与民协的历史展开系统的研究。对其的考察不仅应该包括民研会自身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组织方式等宏观的制度方面,也包含与之相关的机构组织、媒体媒介、教育机制、普通民众等生产主体,还涉及搜集、记录、整理、编写、研究、传播等具体的运作实践,以及其在民众中被接受、解读、评价、再创造等社会效应。这样做,对于明确民研会在民间文艺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调整民协在当下的工作,展开民间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有着积极的作用。适逢中国民协成立70周年,民协编写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70年学术史》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70年发展史》全面总结了民协在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事业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不仅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历史记忆,还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我们期待这样的研究早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