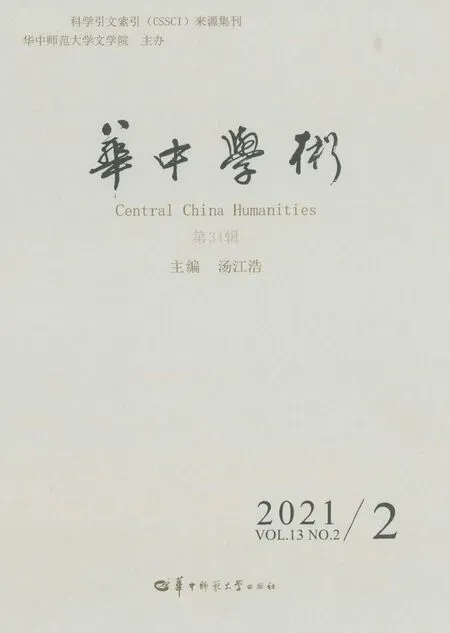朝鲜半岛“花王”题材系列文章述论
2021-11-25路成文
路成文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牡丹素有“国色天香”之誉,宋代以来士大夫文人及寻常士庶,多以“花王”目之。宋人所撰《洛阳牡丹记》等谱录类著作,常罗列各种花卉,以王、后、卿、相诸品目视之。宋元以后,牡丹及相关风俗文化东传朝鲜和日本,故朝鲜、日本文人亦常咏及牡丹。
大约相当于中国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前期,朝鲜史家金富轼编纂《三国史记》,其中的《薛聪传》包含了朝鲜第一篇花王题材文章——《花王说》的主体部分。大约相当于中国南宋中期(光、宁、理宗前期),朝鲜高丽王朝出现过一次以李奎报(1168—1241)为中心的唱和题咏牡丹的盛事,此为朝鲜文人明确仿效中国文人游赏及歌咏牡丹(或各种花卉)之始。此后,经过几个世纪的潜滋暗长,朝鲜文人先后写作了一批以“花王”(牡丹)为题材的传记、诏册类文章。具体包括蔡绍权(1480—1548)《花王传》,金寿恒(1629—1689)《花王传》,李瑞雨(1633—1709)《拟封牡丹为花王诏》《拟牡丹谢花王表》,赵龟命(1693—1737)《花王本纪》,李森焕(1729—1813)《花王即位诏》,李颐淳(1754—1832)《花王传》,李载毅(1772—1839)《封花王诏》等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内容以传述、演绎悠久深厚的中华花卉文化为主,同时,又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讽喻意识和训练各种文体写作能力的目的。
一、朝鲜“花王”题材文章之始
朝鲜最早的一篇“花王”题材文章,可能是托名薛聪的《花王说》。该文首见于11至12世纪朝鲜史家金富轼编纂的《三国史记·薛聪传》:
薛聪字聪智,祖谈捺奈麻,父元晓,初为桑门,淹该佛书,既而返本,自号小性居士。聪性明锐,生知道,待以方言读九经,训导后生,至今学者宗之。又能属文,而世无传者,但今南地或有聪所制碑铭,文字缺落,不可读竟,不知其何如也。
神文大王以仲夏之月,处高明之室,顾谓聪曰:“今日宿雨初歇,薰风微凉,虽有珍馔哀音,不如高谈善谑以舒伊郁。吾子必有异闻,盍为我陈之。”
聪曰:“唯!臣闻昔花王之始来也,植之以香园,护之以翠幕,当三春而发艳,凌百花而独出,于是自迩及遐,艳艳之灵,夭夭之英,无不奔走上谒,唯恐不及。忽有一佳人,朱颜玉齿,鲜妆靓服,伶俜而来,绰约而前曰:‘妾履雪白之沙汀,对镜清之海,而沐春雨以去垢,快清风而自适,其名曰蔷薇,闻王之令德,期荐枕于香帷,王其容我乎?’又有一丈夫,布衣韦带,戴白持杖,龙钟而步,伛偻而来曰:‘仆在京城之外,居大道之傍,下临苍茫之野景,上倚嵯峨之山色,其名曰白头翁。窃谓左右供给虽足,膏粱以充肠,茶酒以清神,巾衍储藏,须有良药以补气,恶石以蠲毒。故曰:虽有丝麻,无弃管蒯,凡百君子,无不代匮。不识王亦有意乎?’或曰:‘二者之来,何取何舍?’花王曰:‘丈夫之言,亦有道理;而佳人难得,将如之何?’丈夫进而言曰:‘吾谓王聪明,识理义,故来焉耳。今则非也。凡为君者,鲜不亲近邪佞,疏远正直,是以孟轲不遇以终身,冯唐郎潜而皓首,自古如此,吾其奈何!’花王曰:‘吾过矣,吾过矣!’”
于是王愀然作色曰:“子之寓言,诚有深志,请书之,以谓王者之戒!”遂擢聪以高秩。
世传日本国真人赠新罗使薛判官诗序云:“尝览元晓居士所著《金刚三昧论》,深恨不见其人,闻新罗国使薛即是居士之抱孙,虽不见其祖,而喜遇其孙,乃作诗赠之。”其诗至今存焉,但不知其子孙名字耳。我显宗在位十三岁,天禧五年(1021)辛酉,追赠为弘儒侯。或云薛聪尝入唐学,未知然不。[1]
检《三国史记》及《中日朝三国历史纪年表》[2],神文王政明在位十一年(681—691),相当于中国唐朝的高宗开耀元年至武则天天授二年,薛聪既为神文王侍臣,则其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我国的初盛唐之际。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即《薛聪传》中神文王与薛聪的这段问对,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后人附会的?盖当时中国唐朝“禁中初重”牡丹,不仅“花王”之号尚罕见用,而且传记中对于“花王”的描写,也与初盛唐之际的情形不符,反而与中唐以后以迄北宋中期长安、洛阳牡丹游赏之风尚相契合[3]。至于“花王”这一专属性称谓,更是迟至北宋初才频繁出现。由于《薛聪传》中对于“花王”的描述,与中晚唐迄北宋中国文人对于牡丹及风俗文化的记录高度趋同,因此,可以断定《薛聪传》中所称的“花王”就是牡丹。而薛聪的时代,牡丹尚无“花王”之美称,则薛聪与神文王问对一段,恐怕并非实有其事,而极有可能是后人附会。
《三国史记》作者金富轼(1075—1151)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我国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前期,该书成书于1145年。而据《三国史记·薛聪传》、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三、李种徽《修山集·东史列传·薛聪崔致远列传》等史料,在此之前124年,即朝鲜高丽王朝显宗十二年(北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显宗曾追赠薛聪弘儒侯,则薛聪在当时朝鲜人心目中地位颇高,朝野上下对他相当熟悉。关于他的功业,最重要的一项,便是通过“花王”故事对神文王进行讽谏。李种徽《修山集》卷十一《东史列传·薛聪崔致远列传》中特别强调了他辟佛崇儒之力,称其“为东方儒者之始”[4],则其对于朝鲜儒学而言,亦是一早期标志性人物。
金富轼既为我国北、南宋之际人,稍晚于他的李奎报已多次在诗歌中以“花王”指称牡丹,则中唐以后、北宋中前期,中国牡丹游赏风俗之盛况,以及宋代关于牡丹为花王的记载或题咏,应已普遍为东人所知。薛聪借花王故事劝谏神文王之事,应即在此背景下产生并为金氏所记录。或者,这个故事的编撰者,即是金氏。总而言之,《薛聪传》中所记载的这则故事,以及包含在传记中的文章或“问对”,最早不应早于唐亡至宋兴(10世纪前半期),最晚不会晚于《三国史记》撰成之1145年。

当神文王时,高句丽百济已亡,而国家无事,薛聪为翰林,念丰豫之易怠也,老成之多疏也,谄佞之数进也,妖冶之易惑也,于是进《花王说》。其辞曰:(中间部分本于《三国史记·薛聪传》,文字稍有修饰,从略)
…………
王曰:“子之言,讽喻深切,请书之以为戒。”[8]
从文体角度来看,《讽王书》在《东文选》是被作为一篇“奏议”来看待的,但李种徽所整理的《花王说》,更接近于中国早期问对体的、带有讽谏性的赋。比如,在“薛聪”正式进谏之前,设置了一段交代背景的“序”,而以“其辞曰”三字领起正文,颇类于中国古代早期赋的开篇(或赋序),在进谏结束之后,补入《三国史记》中原有,但在《东文选》略去的“神文王”有所感悟的一类描述,也与中国早期赋的结尾颇相类似。
值得注意的是,较之一般意义上的君臣问对体,《花王说》设置了两个层次的君臣问对体制,即薛聪与神文王之间的问对、白头翁与花王(含蔷薇)之间的问对。
除文本演进值得关注外,这篇文章带有明显的传奇性和讽喻性。就文章的主体部分来看,文章述“花王”之盛:“花王之始来也,植之以香园,护之以翠幕,当三春而发艳,凌百花而独出,于是自迩及遐,艳艳之灵,夭夭之英,无不奔走上谒,唯恐不及。”确乎王者气象。以下设计了蔷薇、白头翁(一妖娆之佳人,一丑拙之丈夫)两个“人物”形象,分别向“花王”表达向慕或辅之之意,而请“花王”作出选择。再借白头翁之口,对“花王”予以讽谏。最后以“花王”顿悟而连称“吾过矣,吾过矣”作结。在这里,花王、蔷薇、白头翁,都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三者之间的交流问对,本身构成一个完整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9]。
考虑到在文章流传的过程中,以及薛聪本人被赋予朝鲜“儒学之始”的特殊性,这篇文章的讽喻性尤其值得关注。与文章叙述的双重结构一样,其主旨也按两个层次申述。第一层次是白头翁对花王的讽谏。其主旨为:“凡为君者,莫不亲近老成而兴,昵比夭艳而亡。”批评花王在蔷薇与白头翁之间取舍失据,终落“夭艳易合,而老成难亲”的窠臼,并最终使花王醒悟,自识其过。第二层次是“薛聪”对国王的讽谏,即“念丰豫之易怠也,老成之多疏也,谄佞之数进也,妖冶之易惑也”。经其陈《花王说》之后,王“愀然作色”,认为其言“讽喻深切,请书之以为戒”[10]。这两重主旨,内容相近,都是儒家思想中比较常见的处理君臣关系及治国理政的思想。只不过前一层次中所传达出来的主旨,恰是后一层次所欲达成的目的。
综上,作为朝鲜古代文人第一篇“花王”题材的文章,托名薛聪的《花王说》(或称《讽王书》《花王对》等)经历了从11—12世纪《三国史记·薛聪传》之附会创成,到15—18世纪朝鲜历代文人不断复述、离析与整饬完善的过程,最后定型于李种徽《修山集》之《东史列传·薛聪崔致远列传》。这一文本演进过程,就内在动力而言,乃是塑造和不断丰富“薛聪”这一朝鲜民族“先贤”之聪慧、睿智形象,使其传说中的功业更加富有传奇色彩。就其所接受的外在影响来看,则中国古代早期辞赋中常见的君臣问对体制及政治讽喻性,实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朝鲜“花王”系列文章的主要内容:传述演绎中华花卉知识谱系
不同于托名薛聪的《花王说》以塑造朝鲜民族先贤之传奇功业为动机或目的,16世纪起渐次出现的“花王”题材文章的主要内容大都以传述演绎中华花卉知识谱系为主。
中国古代花卉审美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已有山经、地志、本草类著作涉及花草树木,花卉知识谱系也随之不断积累和丰富。汉魏以后,基于经典解释而出现的《尔雅》《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离骚草木疏》等著作,基于博物学兴趣而出现的《竹谱》《茶经》《益部方物略》等谱录类著作,以及《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的编纂,都通过不同的形式建构着中国古代花卉知识谱系。特别是宋代以后,随着广大士大夫文人博物学兴趣的勃兴,《洛阳牡丹记》《梅谱》《菊谱》《兰谱》等花谱类著作大量涌现,汇集花卉知识和咏花诗词歌赋的大型总集如《梅苑》《全芳备祖》等的编纂,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元代耶律铸以赋为谱,并有意编纂《花史》。这些都为中国古代花卉知识谱系的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至明末,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编成,清康熙年间,刘灏等编成规模更加庞大的《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遂集中国古代花卉知识谱系之大成。
朝鲜“花王”系列文章,就内容而言,体现出鲜明的传述与演绎中华花卉知识谱系的特点。先看蔡绍权《花王传》:
王,其先赤帝也,国于洛阳,以火德为纪,色尚赤。王勤于治国,德惟馨香,宵衣旰食,受朝花班,自此芳名远播。王弟将离,封于花县,其风流浩态,略与王相捋。辇来蜂午昵侍花幔,日游花萼楼,造次扶持,未尝小离,人以常棣友爱称之。时菊先生隐居花岩,王迎以蒲轮,即拜四香阁博士,相与松大夫、莲君子,点缀补成,庶几开太平之基矣。自魏紫选入宫,能解语,媚悦王意,自是沉湎怠荒,花事渐堕,国政大小,皆由之出。凡拖青曳紫者,皆出其门,人谓之桃李盈门。赏赐金钱,以巨万数。红愁碧怨,国事日非。自是蜂王屡侵边境,绿战红酣,靡有宁日。王甚患之,筑城御之,号芙蓉。又建薰香阁于国之东,莲房芝室,花砖椒壁,拟于青帝。王尝笑隋炀帝剪彩为花,令东君毕集洛阳,陈百戏于建春门西,执催花羯鼓者以千计,自昏达朝,岁以为常,号探花宴。俗尚侈靡,大夫及士庶皆衣绮罗锦绣,无别上下之分。唐开元中,始通中国,贡献相望,蝶使不绝,经历郡县,香闻十里,帝以天香国色名之,馆于沉香亭,供御帐幄,皆用赤为之。引太真赏玩,命青莲居士赋之。浓腻之态,被之章句,斯宠之极也。及其还也,以梨园弟子数十部,与五花马数十匹赠焉。重王来朝也,梅兄竹弟,咸迎于路,香车追风,芳菲满堂。于联芳楼西设万花会,竹夫人、妆梅公主侍,橘奴千头,各执其物,驰风奔走,椒房戚畹,承恩雨露,移红变白,与夺无常。五花判事以上,重足屏息,莫有言者。独薇垣御史草疏争谏曰:“人君莫不以酒色亡其国者,周之褒姒,吴之西施是已。”叩谏谴谪者颇多。已而白帝遣兵伐之,以飞廉为前锋,蹂以铁骑,王国殄瘁,孑无遗焉。锦衣霞裳,零落于荒草,魂为花月之妖,往往迎风泣露矣。太史公曰:嗟夫!王之亡,萌于富贵而由于侈丽然也。富贵奢侈,固人之所欲,若纵而不已,则危亡自至。使王恒如初日,则金枝玉叶,袭美联芳,当本支百世而不衰。奈何蛊惑妖艳,流连酣醉,以致白帝之祸,使繁华不拔之业,委之于地而莫之惜也。悲夫!为人主者,亦当以为菱鉴焉。[11]
“花王传”,顾名思义,就是以“花王”(牡丹)为传主,为“花王”作传。众所周知,所谓“花王”,不过是人们对于众多花卉中某一种或某一个品种的带有赞赏性和戏谑性的评定,“花王”只是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这一点在中国古代题咏花卉(牡丹)的诗词、文章中,几乎是一以贯之的立场。但在朝鲜古代文人的“花王传”系列文章中,“花王”就不仅仅是花,更是堪与人间君王相比拟的花界之“王”,而所谓的“花王传”,主要内容是花王(牡丹)作为花界之“王”从受命称(封)王、立国到“王者”的行政、事功、王朝兴衰乃至花王陨落的“王朝”的历程。
作为朝鲜文人写作的第一篇《花王传》,这篇文章叙述了“花王”从立国到陨落的过程,文末且借薇垣御史和太史公之口,对“花王”陨落的原因作了带有借鉴意义的分析和总结。不过,熟悉中国古代牡丹文化的读者不难发现,这篇《花王传》通篇其实是在传述和演绎包括牡丹在内的中国古代花卉文化。比如,文章开篇称王“国于洛阳”,实际上是基于中国古代“洛阳牡丹”这一文化符号;所谓“魏紫选入宫,能解语”,实撮合宋洛阳名品花王姚黄、花后魏紫及唐杨贵妃“解语花”故实;所谓“日游花萼楼”“筑城御之,号芙蓉”乃用长安花萼楼及芙蓉城之事;所谓“令东君毕集洛阳”“执催花羯鼓者以千计”“探花宴”乃合唐武则天令牡丹冬天开放的传说、《羯鼓录》及科举进士放榜之“探花宴”故实;“帝以天香国色名之,馆于沉香亭……引太真赏玩,命青莲居士赋之”及“以梨园弟子数十部,与五花马数十匹赠焉”等句,则演绎唐玄宗杨贵妃沉香亭赏牡丹、李太白醉赋清平调典故;所谓“薇垣御史”则用唐代改中书省为“紫薇省”之事。至于“梅兄竹弟”“万花会”“竹夫人、妆梅公主”“橘奴千头”“椒房戚畹,承恩雨露,移红变白,与夺无常”等等,也无不是传述中国古代花卉文化中常见的典故。
金寿恒(1629—1689)《花王传》是朝鲜文人所创作的第二篇《花王传》:
花王姓姚,名黄,其先居于丹州,后移居延州,苗裔散落青州越州之间。宗英居洛阳,至唐始蕃。明皇时,有献莱红者,待诏金銮殿,为禄山陷杀。王生于赵宋天圣间,资质拔萃,闲雅甚都,有富贵气象,最为康节邵公、尧夫范公、君实司马公、永叔欧阳公所艳称。
王承东皇之命,立为花王,妻魏紫封为王后,妾粉娥娇封为花蕊夫人。春阳元年,即位于土阶之上,以木德王。芍药等数十余种皆归附焉。遂封芍药为扬州侯,封桂为月中侯,封桃为左艳阳侯,封李为右艳阳侯,封杏为曲江侯,封梨为大谷侯,封海棠为蜀中侯,封葵为向日侯,封萱为忘忧侯,封榴为安石侯,以梅为冰玉处士,以菊为傲霜处士,以兰为香远处士,以莲为清净处士。如紫薇侯、杜鹃侯、来禽侯、樱桃侯、朱槿侯、水仙侯、牵牛侯、金凤侯、鸡冠侯、瑞香侯、含笑侯、山茶侯、栀子侯、酴醾侯、茉莉侯等,亦皆率其职焉。
二年,两衙侯黄蜂、漆园侯白蝶入朝。蜂善歌,蝶善舞。是日,王受朝开宴,蜂奏霓裳羽衣之曲,蝶和而舞。丘隅侯黄栗留亦以善歌笙与焉。君臣相悦,终日尽欢而罢。人皆荣之。
一日,王曰:“左艳阳侯、右艳阳侯等,谄谀妖冶,病于夏畦,皆黜之。冰玉处士、傲霜处士、香远处士、清净处士,隐迹于山林江湖之间,而贞操凛然,香名振于京师,其裂土而封,以褒其立懦之风。”于是封梅为罗浮侯,封菊为东篱侯,封兰为九畹侯,封莲为若邪侯。皆不起而终。
三年,祝融使风姨作乱于王宫,王遂殂落于土阶之下,群臣从死者甚众焉。
后一年,两衙侯、漆园侯、丘隅侯入朝,则花王已亡,有殷墟黍离之叹,遂为之歌曰:“昔余来朝兮,歌舞纷纷。今余来朝兮,旧迹成陈。吁嗟花王兮今已亡,一声哀歌兮空自伤。”歌竟,痛哭而去,人莫不怜之。王之孙枝流散于中国,或寄身于人家,或托迹于荆棘,更无蕃息者云。
太史公曰:花王气度天然,威仪棣棣,待处士,黜奸人,莫不得其宜,宜其长久,而数年而亡,悲夫!黄蜂之歌,同于箕子麦秀之曲,亦可尚也。[12]
这篇《花王传》题下注云“十六岁作”,可知这篇文章是作者少时习作,创作时间为公元1644年。
这是一篇“少作”,同时也是一篇“仿作”和“戏作”。文章显然带有模仿蔡绍权《花王传》的性质,但相比于蔡作,这篇《花王传》显得更加层次井然,有刻意为文的性质。花王在金寿恒的笔下确乎就是“王”,她有自己的国家(“花园”)、国号(“春阳”)、历运(“土德”)、宫殿(“土阶”)、后宫嫔妃(“王后”“夫人”)、诸侯及朝廷百官(百花封侯、各有职司)、朝贡者(蜂、蝶与黄栗留即莺)、朝廷典章制度及宫廷礼乐歌舞、朝廷政事及赏罚黜陟,有自己作为王者被“弑”的际遇和王朝的败落、“国家”的灭亡,还有自己的缅怀者(“殷墟黍离之叹”)和传述者(“太史公”)。明明只是一种花,明明只是一个小小的花园,却被作者煞有介事地写成一篇仿佛人间君王及其朝廷完整记录的“史传”。这明显带有以文为戏、游戏笔墨的性质。
这种以文为戏、游戏笔墨的核心内容,是以人间朝廷拟喻花界朝廷。人间和花界,如何才能建立起彼此“拟喻”的关系?这显然需要具备必要的前提,即二者之间的类似或同构,以及可以通约的知识谱系——关于花卉的知识谱系和关于人间宫廷、朝廷的知识谱系。
我们知道,基于特定的地缘关系,朝鲜半岛从远古时期即与中华历代王朝保持紧密关系,甚至很长时间都是作为中国的藩属国而存在的,朝鲜国君需要中国政府册封和认可,朝鲜历代王朝在制度、礼仪、文化乃至语言文字和文学,莫不仿效或直接套用中华体系。因此,关于宫廷、朝廷的知识谱系,中华与朝鲜古代文人之间,未必有太大隔阂,毋宁说,二者之间是基本类似的。
但是,关于花卉方面的知识谱系,朝鲜古代文人对于中国而言,可能就先天不足了。朝鲜半岛地理空间相对仄狭,不可能像中国那样能够形成足够丰富的花卉文化和花卉知识谱系。尤其是后者,因花卉及其知识谱系本身无法脱离于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而独立存在,比如姚黄、魏紫、花蕊夫人以及芍药之于扬州,桂树之于月宫,海棠之于蜀中,梨之于太谷,葵花向日,萱草忘忧,桃杏之艳冶,梅、菊、兰、莲之“冰玉”“傲霜”“香远”“清净”等等,这些地理、人文意涵,本身植根于中华深厚悠久的花卉文化,不是古代朝鲜所能生成的,更不可能是金寿恒自己独创和拟构出来的。《花王传》所呈现出来的知识谱系(包括花卉知识谱系和宫廷、朝廷知识谱系),无疑是对中华花卉文化知识谱系的受容。
反观中华花卉文化知识谱系,有没有给予朝鲜古代文人这种以人间朝廷拟喻花界朝廷的最直接的启示性范例?
循此思路,我们发现,在宋人为数众多的花木谱中,张翊的《花经》和邱濬的《牡丹荣辱志》,为品第各种花卉,有意识地按照人间的方式,比较集中“安排”各种花卉的品秩或职司。如张翊《花经》云:
翊好学,多思致,世本长安,因乱南来,尝戏造花经,以九品九命升降次第之,时服其允当。
一品九命:兰、牡丹、蜡梅、酴蘼、紫风流(睡香异名)
二品八命:琼花、蕙、岩桂、茉莉、含笑
三品七命:芍药、莲、簷葡、丁香、碧桃、垂丝海棠、千叶桃
四品六命:菊、杏、辛夷、豆蔻、后庭、忘忧、樱桃、林禽、梅
五品五命:杨花、月红、梨花、千叶李、桃花、石榴
六品四命:聚八仙、金沙、宝相、紫薇、凌霄、海棠
七品三命:散花、真珠、粉团、郁李、蔷薇、米囊、木瓜、山茶、迎春、玫瑰、金灯、木笔、金凤、夜合、踯躅、金钱、锦带、石蝉
八品二命:杜鹃、大清、滴露、刺桐、木兰、鸡冠、锦被堆
九品一命:芙蓉、牵牛、木槿、葵、胡葵、鼓子、石竹、金莲[13]
张翊将71种花卉按照一品九命至九品一命“升降次第之”。所谓品,乃是指朝廷官员的官阶,从正一品到从九品,共十八阶;所谓命,《礼记·王制》云:“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不过九命。次国之君,不过七命。小国之君,不过五命。大国之卿,不过三命,下卿再命。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14]按,一品为最高品秩,九命乃荣宠之极之意。张翊虽然还没有完全以人间朝廷拟喻甚至拟构花界朝廷的意思,但其以人间爵禄品秩拟喻各种花卉的等第高下的思致,对于构建花卉知识谱系,还是富有创意的。故“时服其允当”,得到当时人的认可。
邱濬《牡丹荣辱志》亦借人间职官(特别是后宫)品秩模式品第牡丹及其他花卉:

张翊《花经》、邱濬《牡丹荣辱志》显然也都带有游戏笔墨的性质。不过,这种以官品拟花品、以朝廷职官职司拟牡丹及各种花卉的思致,本质上是借朝廷职官谱系来建构花卉知识谱系。这一思致,在元初著名文人耶律铸《花史序释》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条理化。
耶律铸是元初最热衷于以牡丹为主的花卉艺植与研究的文人之一,其《天香台赋》《天香亭赋》以赋为谱,构建了元初最完备的花卉知识谱系。不仅如此,他还有志于撰成《花史》一书。其《花史序释》云:“双溪主人因移接牡丹,尝作《天香台》《天香亭》《天香园》三赋。后分种芍药,有《芍药花选辞》三十三首,由是继编《花史》……”为此,他在《花史序释》中,除“命”牡丹为花王之外,又对梅花、芍药等80种花卉逐一“命”以官职和职司,构建了一个基于人间朝廷知识谱系的花卉知识谱系:
牡丹姿艳万状皆绝,故以牡丹为花王。
梅有和羹之任,故曰梅为上公。
槐为三公之位,故曰槐为三公。
松有大夫之封,故为大夫。
竹有刚颜之资,故曰竹为毅士。
芍药有近侍之称,故曰芍药为近侍。
紫薇本署以中书,故曰紫薇为中书。
文冠策名于翰苑,故曰文冠备翰林。
木笔有可书之状,故曰木笔备太史。
拒霜有捍抿之义,故曰拒霜备致师。[16]
从《花史序释》正文及自注来看,耶律铸所构拟的花卉知识谱系是严密且有依据的,比如他在自注中写道:“开元中,改中书省为紫薇省”,以此为“任命”紫薇为中书的依据;“《唐会要》云:文冠花,学士院有之”,以此为“任命”文冠花备翰林的依据;其他如“梅有和羹之任,故曰梅为上公”“松有大夫之封,故为大夫”等等,将中国古代典籍中一些涉及花木的熟典,引入花卉知识谱系之中。与张翊《花经》、邱濬《牡丹荣辱志》相比,耶律铸《花史序释》,不仅对于各种花卉及对应职司安排取义均有依据,而且最主要的是对花卉知识和文化进行了集成,使各种零散的只言片语的涉及花卉的典故或说法,归总到一篇文章之中。

三、朝鲜“花王”系列文章之政治讽喻意识
尽管“花王传”系列文章或多或少带有以文为戏、游戏笔墨的性质,且呈现了相当丰富的花卉文化知识谱系,但这显然只是朝鲜文人写作“花王”系列文章的一个方面,通过对这些文章的具体解读,我们发现,其核心宗旨和目的之一,乃在于表达一定的政治教化观念,体现出鲜明的政治讽喻意识。
蔡绍权《花王传》借“薇垣御史”和“太史公”之口,表达了“酒色亡国”“富贵奢侈,固人之所欲,若纵而不已,则危亡自至”的政治讽喻。金寿恒《花王传》以人间朝廷拟喻(花界朝廷)花园群芳,一方面,强调“花王”之“威仪棣棣,待处士,黜奸人,莫不得其宜”,勾画了一个理想君王的形象,同时隐含人间朝廷不如花界朝廷之意;另一方面,“祝融使风姨作乱于王宫,王遂殂落于土阶之下”,花王并无过错,却“数年而亡”,借“太史公曰”表达对于这一结局的困惑,同时隐喻人间朝廷(宫廷)之险恶秽乱。特别是,这篇作品恰好作于崇祯甲申之变,明思宗朱由检因李自成等攻破京城而煤山自尽。在当时,明朝与朝鲜,是典型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这篇《花王传》是否隐然有为明朝之亡唱挽歌的意味,也未可知。
赵龟命《花王本纪》的政治讽喻意味更加明显。赵龟命(1693—1737),字锡汝,号东谿,丰壤人。少颖悟,不慕荣利,屡受荐举征辟而不就,浸淫涵蓄于古文辞,而尤以苏轼文章为依归。著有《东谿集》十二卷。《花王本纪》收录于该集卷七“杂著”类。
《花王本纪》从题目来看,似乎步武中国古代正史本纪体例,但事实上仿效的却是《尚书》(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等篇章)的体制。节选文章后半段如下:
王曰:“咨!诸支群种,搜芳扬侧陋,予其师。”佥曰:“于菖蒲,厥节九,不恒有于天下,人见则福,服则仙,昔出兰陵,萧王蹶,厥生以帝,有江左。”王曰:“吁,异种可乎?”佥曰:“然哉!曼陀罗可。昔释迦于祗树,讲法华华严,维时曼陀罗,自天而降,五体投地,发深妙义,俾诸菩萨顿悟,大迦叶传厥灯心,花开果结,式至于黄梅,惟王念功!”王曰:“吁,咈哉!”
王曰:“咨!诸支群种,材必有种,以时发荣,女其又之。”师锡王曰:“有英在泥涂,曰莲,茂叔称之曰君子。”王曰:“俞!予闻馨香如何?”曰:“厥心通,厥仪直,亭亭独立,英华外发,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王曰:“都!”乃以芝盖蒲轮,逆于草泽,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莲见王,王立于沼上,命之曰:“启乃心,薰朕心,罔俾莘(‘新’,引者注)野诸葛,专芳于古,茂哉!”莲拜舞稽首,有泪如珠。
王曰:“咨!莲,杂种猾华,大道榛芜,惟菖蒲既曼陀罗,为厥渠魁,予将折厥萌,锄厥根,其先风告天下。”莲曰:“都!薇掌草麻。”王以命薇,薇拜舞稽首,对扬曰:“王若曰,嗟予同种,低尔头,鞠尔躬,其听朕披心,惟菖蒲,掇拾李庄绪余,诪张服食之说,匿迹秘影,闪倐恍惚,俾一世,欣慕左道,流涎匪望。惟曼陀罗,厥性不根,助簷葡邪化若雕人粪,为旃檀形,如恶义果,一枝三子,暨优昙钵,私立名字,妄称瑞物,薙人毛发,灼人支体,俾人父母妻子不相保。兹皆草昧之奸萌,圣道之匈蘖,先民有言曰:‘蔓草难图,予其为天下芟夷’,若颠木并除由蘖,无俾易种。”
王曰:“咨!莲,惟兹世人,眼目不真,空花用幻,术眩天下,畴克来兹。”莲曰:“都!决明允明四目,王拂拭之。”王曰:“我其试哉!”
王曰:“咨!莲,惟彩花,假借我形貌,僭窃我名号,乃杨氏文餙,兹栽成兹,诳耀诈伪,寔繁树党,朕甚痛之!其亲伐。”莲曰:“粤若重华,舞于阶,苗顽格,刘秀不违,舂莽首传,王毋忧,当有金华仙子,暨我同类者,发于陇西,披杨氏而彩花自散,其自今天下华盛,我其益封,而礼绝诸方哉!后李氏果代杨尊宠,花王甚封于雒,置邸于长安,礼视杞宋,天下艳之,而彩花望风而降。”
王乃放空花于广莫,投曼陀罗于有昊,沉菖蒲于水,磔彩花于市,四罪而天下之化乃正。
王曰:“予当阳,甲子再周,衰悴理至。比者,天作淫雨,风乃鸣条,花花光晦,予其殆而。”旦日,王洮颒水,朱衣绿裳,凭文石几而出顾命。王若曰:“咨!诸支群种,四时之序,成功者去,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予何悲为?藐兹诸子稚弱,年弗可待,惟女莲迈种德,时哉时哉!禅朕位!”莲俯伏揖逊,激昂飏声曰:“都!嗣子冲哉,仁克肖王,实心法是传。萌芽则见王,念兹在兹!予安陆沉燥湿异厥性,其敢辱高位!”
王曰:“咨!妃梅氏,尔惟予配,思齐芳闻,期于岁晏,朕今先朝露,呜呼!家有主母,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茂哉!”妃曰:“王百岁后,畴可代莲者?”王曰:“菊可,寔类夏黄,逃朕哉,其必左右嗣子。”问其次,曰:“冬栢可。栢重厚哉,非民望,难独庇,惟尔族大如古栢根,多贞节士,予弗欲用违厥时,留以护嗣子。呜呼!天数难逭,否极则泰回,积阴反诸阳,必在尔族。”又问其次,曰:“兹后,亦匪乃攸知。”
王徂落,是日,疾风雷雨,自殉以下,从者不记其数,僵横道途,人不忍践,葬王于两阶之间,弗封弗树。莲乃居上流,遥奏嗣子,以待其壮。
季年,天降白衣神,人名雪花,横行作乱,天下萧然,花王之族几灭。群种戢伏,莫敢发。惟妃暨诸梅,精白厥心,敦本施化,不出户闱,不变色而默消其势。乃冬栢与有勋,卒巩花王之故基。树屏既密,本枝繁增,维新受命,子子相承,重熙累洽,于千万叶。[17]
这篇文章除一般性的分命百官外,特别突出演绎了花王对于群花的赏罚黜陟及禅让保嗣情节。
首先,因师锡王之荐,花王认识到莲花的品性与才智,因而重用莲花,甚至以三国蜀汉良相诸葛亮视之,以下通过与莲花商议及处理朝政,惩四凶,保继嗣,各得其宜,完美演绎了一段花界朝廷君臣遇合的佳话。花王对于莲花的赏识,与莲花对于花王的忠悃,这是人间朝廷稀世罕觏的明君贤臣之遇合。《花王本纪》浓墨重彩地演绎这一情节,无疑是对理想朝廷政治的期待,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对于现实朝廷政治的规谏和讽喻。
其次,花王之惩四罪,“放空花于广莫,投曼陀罗于有昊,沉菖蒲于水,磔彩花于市,四罪而天下之化乃正。”惩戒四罪的理由分别是,“菖蒲,掇拾李庄绪余,诪张服食之说,匿迹秘影,闪倐恍惚,俾一世,欣慕左道,流涎匪望。惟曼陀罗,厥性不根,助檐卜邪化若雕人粪,为旃檀形,如恶义果,一枝三子,暨优昙钵,私立名字,妄称瑞物,薙人毛发,灼人支体,俾人父母妻子不相保”;“空花用幻,术眩天下”;“彩花,假借我形貌,僭窃我名号”,“诳耀诈伪,寔繁树党”。这实际上是对道教、佛教以及幻诞、僭伪等不合于儒学思想的旁门左道、异端邪说的批判与斥逐,惩四罪以正人心,化天下。
再次,花王与莲相及后妃商议禅位保嗣之事。
一方面,花王对于生命不可能长久之事,有清醒的认识,因而敬天顺命;另一方面,欲行上古禅让之制;禅让不成,乃与莲、菊、栢等共议保嗣继统之事。这是从花王角度演绎其志。花王这种敬天顺命、禅让贤能、保嗣继统的价值观念和远见卓识,无疑符合人间理想君王的形象。这与一代代君王恋栈固位、服食求仙以及缺乏对于宫廷王位继承之重要性的认识从而造成一出出宫斗悲剧相比,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从莲花、梅妃的角度来看,这一段又树立了理想臣子及后妃的形象,臣子忠心耿耿,一心奉主,绝无任何僭越之心;后妃亦顺从花王之意,预为保嗣继统之计。这与诸多臣子飞扬跋扈甚至谋逆篡位、后妃专宠乃至随意干预朝政、秽乱宫廷相比,俨然也是理想的大臣、后妃形象。
很显然,《花王本纪》通过树立理想典范,讽喻、鉴戒人间朝廷、君王、臣子、后妃,讽喻意味流露于字里行间。
赵龟命之后,又有李颐淳《花王传》。李颐淳(1754—1832),字稚养,真城人,退溪先生九世孙。少颖悟,潜心经籍,能秉承家学。“少嗜读昌黎文,晚乃约之于先生遗集。其为文端洁淳雅。”著有《后溪集》十卷,所撰《花王传》,收录在《后溪集》卷六“传”类。
与金寿恒《花王传》、赵龟命《花王本纪》相比,李颐淳的《花王传》在讽喻性方面体现两个新的特点。
其一,改变了花王“光明正大”“知人善任”“敬天顺命”的形象,突出了花王因形势、地位变化而产生的性格、心态方面的变化。前期的花王,与其他《花王传》中描写的一样,同样德之所在,天命所归,勤于政事,知人善任,从而治下之国“熙熙然如在春台寿域之中”。但接下来,花王开始得意忘形:“王春秋鼎盛,奢靡日甚,闻海棠有倾国之色,以蝴蝶为使,迎而至。王见之,美而艳,置于别宫,日夜耽乐。”竹谏之而不听,最终“神慌色惨,殪于商郊,国遂以亡”。这样的设计,使得这篇《花王传》的讽喻性大大增强。前面两篇花王之亡,皆因外力,此篇花王之亡,则因“奢靡日甚”,咎由自取。这实际上是在警醒人间朝廷的君王应勤勉理政,而不应奢靡误国。
其二,这篇传对于梅、竹、菊命运的描写,也带有一定的讽喻性。在前两篇《花王传》中,梅、竹、菊作为被花王安排的对象,在花王崩亡的过程中,其命运如何,并没有被特别强调,但在这篇中,则被作了特别安排:
药进于王曰:“德不孤,必有邻。《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西湖有处士,淇隩有君子,江城有隐逸不仕者,曰梅曰竹曰菊。此三子者,皆有清修苦节,真天下之第一流也,可召而致。”王乃嫣然笑,使人以币聘之。菊不至,梅与竹至。拜梅为蜀郡太守,竹为通平侯。
…………
王春秋鼎盛,奢靡日甚,闻海棠有倾国之色,以蝴蝶为使,迎而至。王见之,美而艳,置于别宫,日夜耽乐。竹谏于王曰:“臣闻内作色荒,未或不亡。是以吴王以西施沼其宫,唐皇以贵妃迁于蜀。是不可以不戒也。”王不听,一朝蓐收从西方起,金风骤至,铁马横奔,肃杀之气,盈于天地。所过摧拉,无有遗类。王神慌色惨,殪于商郊,国遂以亡。顾片时之繁华,等槐安之一梦。芍药与王俱死,竹仅保其节,梅弃于大庾岭。惟菊超然独免于祸难之外。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菊有之矣。[18]
梅、竹因未能坚持其初心,遂因花王之败而受累;竹因尝向王进谏,乱亡之际,“竹仅保其节”;菊因未受花王之封赏而免祸,有见机之智,故文末特别强调菊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生存智慧。这显然是对于世人进行某种形式的劝诫和讽喻。
总体而言,李颐淳的《花王传》考虑或反思的层面更加丰富,讽喻的内涵更加明确,同时也更贴近普通人的命运及人生哲学。
四、以文为戏和文体训练
早在唐代,朝鲜就大量派遣文士、僧侣来华求学,甚至参加科举考试和做官。在20世纪废止汉字以前,汉语乃是朝鲜官方语言,各种文书乃至文学写作,皆用汉语。翻检朝鲜10至20世纪文人文集,我们不难看出,彼时文人文集,与中华无异。这表明,古代朝鲜文人参与政治生活,以及教育、经济、文化和文学等,熟练掌握和运用汉语及各种文章体制,乃是基本要求。上文所引金寿恒《花王传》、赵龟命《花王本纪》对于中国古代史传、诏诰文体的模仿、学习和操练,即是显例。除此之外,李瑞雨(1633—1709)《松坡集》卷二十“俪文”类收录《拟封牡丹为花王诏》《拟牡丹谢封花王表》。这两篇文章模仿朝廷诏册之文及谢表体例,先代朝廷草诏封牡丹为花王,次代牡丹向朝廷拟谢表,体制上属于庙堂应用之文。李森焕(1729—1813)《少眉山房藏》卷之六“杂著”类收录《花王即位诏》、赵载毅(1772—1839)《文山集》卷十“杂著”类收录《封花王诏》,这两篇文章也是模仿朝廷诏册之文,命花王即位或封牡丹为花王。史传文体也好,诏册谢表之类的文体也好,对于古代朝鲜文人而言,无疑都是需要熟练掌握和运用的。
不过,这些文章所带有的比较明显的以文为戏、游戏笔墨的性质,似更多继承和仿效韩愈《毛颖传》以来以文为戏同时又寓含讽喻意味的创作传统。这类文章在宋元时期,实际上曾结集为一本比较特殊的书——《文章善戏》,其中一篇题名郑楷的《拟封花王册》,从题名来看,与李瑞雨《拟封牡丹为花王诏》、赵载毅《封花王诏》非常相似。
郑楷《拟封花王册》全文如下:
《洛阳牡丹记》云:姚黄千叶黄花,魏紫千叶肉红。钱思公云:人谓牡丹花王,今姚花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妃也。近丘濬作《牡丹荣辱志》,自姚魏以下,列世妇嫔御凡三十余种。
红紫随时,孰是三春之冠;容光绝世,斯为万卉之荣。兹因物以稽畴,俾称尊而建号。尔英华外发,富贵天成。当祥风丽日之暄,下游尘土;若景星庆云之见,照耀乾坤。中九域以储精,殿群英而独步。积是磅礴扶舆之气,溢为休显文明之祥。观风裁露剪之奇,见天巧神工之大。姿诚绝配,品道逾高。萧闲悲后土之琼,琐屑陋广寒之桂。千车赏胜,羽仪复会于东都;十里护晴,供帐已如于王者。是用履黄中而正位,司丹券以莅盟。按行一百六候之风光,悉归长治;调护二十四番之花信,各正事权。於戏!物有常尊,礼无二上。为君子为隐逸,何莫非臣;有世妃有妃嫔,克昌厥后。俾延世袭,益茂流芳。其牡丹姚氏黄,可封花王。[19]
李载毅《封花王诏》:
青帝若曰:辟草莱而任土地,曰嘉乃功;披荆棘而立朝廷,爰册徽号。何彼秾矣,亦足王之。惟卿系出洛阳,素有繁华之姿,宜乎众人之爱。香闻天下,兼得富贵之相,冠于百花之中。风流悠扬,恍如公子王孙之设绮筵张绣幕;态度浓艳,依然玉女素娥之倚纱窗卷珠帘。正当暮春之时,初发两种之色。玉葩争洁,还嫌海棠之无香;锦蕊斗红,羞伴桃李之献媚。惟厥美之最贵,岂众芳之能当。兹命册卿为王,是所谓宁有种乎,庶可曰拔乎萃矣。环深丛而奠基,土阶三等;披香枝而开殿,木德元年。嫣姿映霞,玲珑罘罳之帐。娇容夺日,妆点锦绣之宫。芙蓉苑中,时接君子之白。沉香亭北,长侍贵妃之红。蝶使来朝,摇摇翠华之引路。蜂王入贡,屹屹御榻之临阶。满园芳菲,咸囿雨露之泽。出门警跸,半接莺燕之啼。葵藿倾阳,表丹忠于卫国。蔷薇有刺,施薄谴于出墙。身被绛纱之袍,可使南面。头戴珠饰之冕,分付东风。叶兮满枝,愿春风之长在。花而不实,恐夏日之先萎。姚黄魏紫之同根,无非玉叶。芍药凤仙之争绽,犹是花奴。经百岁而流芳,千片红雨。殿三春而饰彩,一朵彤云。故兹诏示,想宜知悉。[20]
《文章善戏》,《四库提要》有著录,今仅见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金程宇教授《唐宋稀见文献丛考》之《静嘉堂文库所藏〈文章善戏〉及其价值》一文后辑录佚文54篇,其中即有题名郑楷《拟封花王册》。朝鲜文人是否见到过《文章善戏》这部书,难以确考,但《文章善戏》早已东传日本,而朝鲜文人则写作了很多与《文章善戏》题材、性质、体制相仿的文章,则是事实[21]。撇开其他文章不谈,单就这几篇花王题材的诏册、谢表之文来看,与题名郑楷《拟封花王册》在性质和文章体制方面显属同类。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现象,游戏笔墨、以文为戏,因其取径相同,是一方面原因。寓讽喻于戏谑,是另一方面原因。这些原因,最终落实到文章体制的训练,则是可以想见的另一层原因。
比如,金寿恒《花王传》,题下注云“十六岁作”,李颐淳《花王传》,题下注云“少时作”。这两篇《花王传》是否他们在读书期间完成的命题作文,不得而知,但肯定属于少时习作,带有训练文体写作的性质。
赵龟命《花王本纪》训练文体写作的性质更加明显,甚至颇具匠心。
其一,他通过选取特定的文体和语体,突出强调牡丹作为花中“天子”的身份。在命题方式上,赵氏没有选取一般意义上的“传”(列传),而是直接题为“本纪”。《史记》张守节“正义”引晋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22]唐刘知几《史通·本纪》云:“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23]题名“花王本纪”,是以牡丹为“天子”,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王”(诸侯或王侯将相)。在文章体制选择上,他没有按照一般的秦汉以后的散体文体制,而是仿效《尚书》,以记言体的形式,述花王行使“天子”之事。大量使用《尚书》中的常用语气词,如“咨”“俞”“都”“吁”“厥”“惟”“兹”“钦若”“粤若”“攸”“允”“毋”等等,使文章古奥庄严,极似尧、舜等上古先王口吻。
其二,通过述牡丹所行之事,突出其为花中“天子”的身份。

《花王本纪》前半段虽然也像金寿恒《花王传》述花王册妃及分命百官、赏罚黜陟之事,但在细节方面则大大加详,每一段君臣对话,都是在执行册妃、命官及赏罚黜陟之事,并进行解释和说明。特别是黜陟“四罪”(菖蒲、曼陀罗、空花、彩花),经过几番举证辩驳及拟草诏书,“放空花于广莫,投曼陀罗于有昊,沉菖蒲于水,磔彩花于市,四罪而天下之化乃正”。这一节完全模仿《尚书·舜典》中舜惩“四凶”一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这些详细的细节描写,较之金寿恒《花王传》中相应的所有事迹的一语带过,显然更加符合花王作为花中“天子”的身份和地位。
与金寿恒《花王传》相比较,《花王本纪》增设了禅让保嗣的情节,更加符合“天子”身份。《花王传》在述蜂蝶入朝,侧面呈现花王之威仪与其国(“花园”)之繁盛后,遂以风姨作乱、花王殂落、百花摧残,再借蜂蝶之再次入贡,以写黍离麦秀之感。固然简洁而启思,但作为“天子”,继嗣问题不容回避,故《花王本纪》特设禅让保嗣一节,先欲禅位于莲,莲拒之,而以竭力保护花王之嗣子为词;又与梅妃交代后事,在莲之后,继推菊及冬柏以代莲保嗣。这一节亦颇效《尚书》之尧禅舜,舜禅禹,以及禹传子,武王托周公以保成王。其所增设之情节,较金寿恒《花王传》更符合“天子”身份。
其三,在古奥的言辞下,这篇《花王本纪》依然有较强的故事性;其体察物理,体现出花卉文化与花卉生物属性相结合的特点,俨然一部群芳谱;以人事喻花事,部分情节讽喻意味依然比较强。
故事性方面,花王册妃、分命百官、赏罚黜陟、禅让保嗣、殂落及中兴等,虽以记言体呈现,但环环相扣,故事情节依然比较强。在君臣对话中,百花之生物属性逐一得到了揭示。这些生物属性,并非随便杜撰,而是来自对物性的体察,比如各种花卉开放的季节、季节变化与花园景象的对应关系等等。同时,若干花卉,如梅花之贞及傲雪凌霜、芍药之和(调和五味)、桂之在月宫、稻之为食、桃李之有花有实、菊花之特立芳节、冬柏岁寒之性、莲花之品性高洁、紫薇之省(草诏)、葵之忠(向日)、杜鹃之伤(望帝)、萱之忘忧、兰之义、菖蒲之仙(服食成仙)、曼陀罗之佛(天女散花)等等,这些在中华文化漫长历史中被赋予的特定意蕴,也得到了揭示,因而俨然如一部小型群芳谱。讽喻性方面,《花王本纪》充分演绎了曾经存在于《尚书》中的知人善任、赏黜分明及禅让保嗣的情节与观念,对于人间实王有一定鉴戒意义。除此之外,文章增加了花王知命顺命及安排后事的情节,对于人应持何种生命态度,有借鉴意义,同时,花王合理安排继嗣问题,既体现了某种道德理想,同时又不乏影射宫廷政治的意味。
其四,在继续渲染牡丹花王地位的同时,突出莲花的地位,一方面显示周敦颐《爱莲说》的强大影响,另一方面又将莲花纳入朝堂政事体系,同时赋予其诸葛亮式的智慧与忠诚。《花王本纪》用了大段笔墨,把莲花刻画成一个品性高洁、观人精准、忠诚循矩的形象。
王曰:“咨!诸支群种,材必有种,以时发荣,女其又之。”师锡王曰:“有英在泥涂,曰莲,茂叔称之曰君子。”王曰:“俞!予闻馨香如何?”曰:“厥心通,厥仪直,亭亭独立,英华外发,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王曰:“都!”乃以芝盖蒲轮,逆于草泽,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莲见王,王立于沼上,命之曰:“启乃心,薰朕心,罔俾莘野诸葛,专芳于古,茂哉!”莲拜舞稽首,有泪如珠。

不过是描写一种花卉,虽然含有一定的讽喻意义,但作者别出心裁,苦心经营,匠心独运,显然有刻意为文之意。
至于《拟封牡丹为花王诏》《拟牡丹谢封花王表》《花王即位诏》《封花王诏》等文章,除以文为戏、游戏笔墨外,明显强调对于体制的把握和对于辞采的追求。其主要写作目的,显然是训练文体及辞章。
余论:朝鲜“花王”题材文章的文化观照
通过对于朝鲜花王题材诗文之创始及其流衍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深厚的中华文化背景(比如博物学、地域文化、风俗、诗词、典故等等)、鲜明的儒学思想阐发(为政、为人)、充盈的政治讽喻意味(宫廷政治、兴亡悖论、政治鉴戒)、特殊的文体研究意义(故事性、纪传、诏册、小说、游戏笔墨及训练辞章),是这类文章所呈现出来的鲜明特点。
首先,中国古代牡丹及花卉文化文献之东传,对于朝鲜文人的知识储备和文章写作具有根本性和奠基性的意义。伴随这些文献的东传,有关中华文化基本知识谱系,如博物学、地域文化、文化习俗、经典诗词、典章制度、文学典故等等,也一并得以东传。没有这些文献的东传,没有对于这些文献、文学、文化的学习,不可能产生花王题材文章。
其次,中国古代文史文献的大规模东传,以及朝鲜长期以汉语、汉文作为官方语言和文章写作的载体,使得朝鲜文人的文章写作,从形式到思维皆深沐华风。朝鲜花王题材文章所涉各种文章体制,如列传体、本纪体、编年体、尚书体、史论体、诏册、谢表等等,无不植根于中华文化。与此同时,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朝鲜文人游戏笔墨之谐趣,辞章训练之热忱,以及有意识的集成与创新。
最后,朝鲜花王题材文章对于儒学话语和政治讽喻的执着,令人印象深刻。朝鲜儒学传统之深厚醇正,前人之述甚备。透过这些花王题材的文章(或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中华儒学之政治讽喻传统、先秦儒学迄宋明理学之标举和建构君子人格的传统、对于清明理想之朝廷政治的描绘与期待、对于观物阐理思想之儒学根底的接受与实践,对于儒学的弘扬以及对于佛、道的排诋等,无不深刻影响着朝鲜文人及其文章写作。从托名薛聪的《讽王书》(或《花王说》),到频繁出现的“花王传”,一以贯之的正是强烈的政治讽喻和为人为政之理想阐发。
注释:
[1] [朝鲜]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四十六,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第529~530页。
[2] 徐红岚:《中日朝三国历史纪年表》,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3] 《薛聪传》云:“臣闻昔花王之始来也,植之以香园,护之以翠幕,当三春而发艳,凌百花而独出,于是自迩及遐,艳艳之灵,夭夭之英,无不奔走上谒,唯恐不及。”所谓“植之以香园”,对应的最早典故是唐玄宗沉香亭牡丹:“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同时代的杨国忠亦有类似举措:“国忠又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泥饰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友于此阁上赏花焉,禁中沉香之亭远不侔此壮丽也。”所谓“护之以翠幕”,唐康骈《剧谈录》载:“通义坊刘相国宅……阶前有花数丛,覆以锦幄。”白居易《买花》云:“上张幄幕庇,傍织笆篱护。”又《牡丹芳》云:“共愁日照芳难驻,仍张帷幕垂阴凉。”余靖《与宋景文公唱酬牡丹诗》云:“翠幕遮蜂蝶,朱栏隔绮罗。”欧阳修《答西京王尚书寄牡丹》云:“却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为白发翁。”韦骧《州宅牡丹盛开蒙剪栏中奇品见赠仍属短歌于席上》云:“牡丹开处彩为栏,翠幕障风怯风紧。”所谓“无不奔走上谒,唯恐不及”,前引刘禹锡、白居易诗句,堪作注脚。又,唐李肇《唐国史补》载:“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暮春车马若狂。”宋钱易《南部新书》载:“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关于唐宋牡丹游赏风习的相关论述,参见路成文:《国色天香见证历史兴亡——唐宋牡丹诗词的文化观照》,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
[4] [朝鲜]李种徽:《修山集》卷十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47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古典翻译院),2000年影印版,第530页。
[5] [朝鲜]徐居正编:《东文选》卷五十二第5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古典翻译院),1968年影印版,第52页。
[6] [朝鲜]李瀷:《星湖先生全集》卷七,《韩国文集丛刊》第198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古典翻译院),1997年影印版,第166页。
[7] 按,参安鼎福:《东史纲目》卷四下,首尔:[韩国]朝鲜古书刊行会编,1975年,影印本,第78页。
[8] [朝鲜]李种徽:《修山集》卷十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47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古典翻译院),2000年影印版,第530页。
[9] 李岩认为这“是一篇成熟度极高的作品”。从寓言或传奇故事的角度来看,有一定道理,但从文章体制的完整性来看,这篇文章即使在《三国史记·薛聪传》之后,其实还经历了数个世纪整理与完善,称之为“高度成熟”,似言过其实。参见李岩、李杉婵:《朝鲜寓言拟人传记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9页。
[10] [朝鲜]李种徽:《修山集》卷十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47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古典翻译院),2000年影印版,第530页。
[11] [朝鲜]蔡绍权:《拙斋先生文集》卷二,《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253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354~357页。
[12] [朝鲜]金寿恒:《文谷集》卷二十六,《韩国文集丛刊》第13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古典翻译院),1994年影印版,第507页。
[13] (宋)张翊:《花经》,《笔记小说大观》第五编,台北: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78年,第1641~1643页。
[14]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2~358页。
[15] (宋)邱濬:《牡丹荣辱志》,《笔记小说大观》第五编,台北: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78年,第1623~1630页。
[16] (元)耶律铸:《花史序释》,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四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2~45页。
[17] [朝鲜]赵龟命:《东谿集》卷七,《韩国文集丛刊》第215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古典翻译院)1998年影印版,第141页。
[18] [朝鲜]李颐淳:《后溪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269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古典翻译院),2001年影印版,第215页。
[19] 金程宇:《静嘉堂文库所藏〈文章善戏〉中的宋元俳谐佚文辑存》,《稀见唐宋文献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2页。
[20] [朝鲜]李载毅:《文山集》卷十,《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112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古典翻译院),2011年影印版,第149页。
[21] 李岩、李杉婵对此类题材多有论及。参见李岩、李杉婵:《朝鲜寓言拟人传记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翻检《韩国文集丛刊》中朝鲜文人文集,也能大量发现此类文章。
[22] (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页。
[23] (唐)刘知己:《史通》卷二,四部丛刊本,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重印本,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