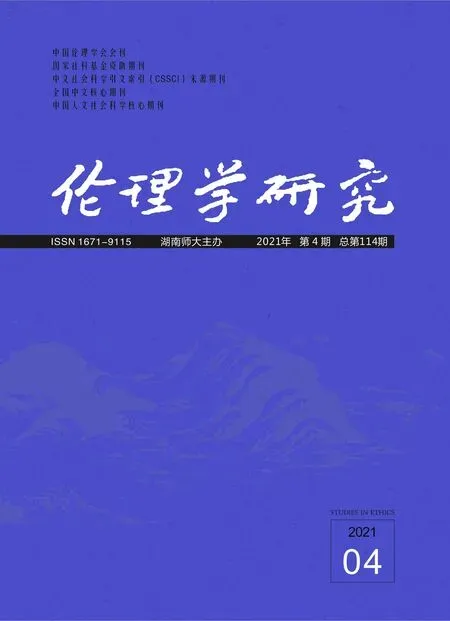论“好人”观念
2021-11-25王江伟
王江伟
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对传统儒家有一种批评,认为它无法处理陌生人之间的伦理关系①。然而,倘若实际地考察中国人与陌生人的日常交往活动,就会发现其中自有某种相应的伦理规范发挥着指导作用,后者落实到日常语言之中就呈现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好人”观念。“好人”观念在中国人的常识道德中居于一种基础性的地位,但是关于它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对它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揭示传统伦理思想在日常观念层面的总体显现,进而剖析中国人常识道德中的基本意识结构,而且有助于阐明传统伦理思想对“如何与陌生人交往”这一现代问题的潜在因应,进而把握伦理传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因此,本文尝试从伦理学的视角对这一日常观念进行考察:首先从日常语言层面辨识两种不同的“好人”观念,作出全称性与特称性的区分;其次从常识道德层面分析“好人”与“好父亲”“好员工”之间的关联,揭示“好人”观念的公共性特质;最后从伦理传统层面讨论由“好心”“好事”“好人”“好报”等观念群构成的意识结构,从总体上勾勒出其对“陌生人问题”的可能回应。
一、两种“好人”观念
根据《汉语大词典》的总结,自古以来的“好人”一词有如下义项:a.美人;b.品行端正的人,善良的人;c.和事佬,老好人;d.健康的人[1](282)。其中,a和d 都是在非道德意义上使用,涉及生理方面的善,只是前者侧重于相貌,后者侧重于身体;b 和c都是在道德意义上使用,涉及品性方面的善,只是前者为积极的肯定,后者为消极的否定。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之中,“好人”的义项只剩下b、c、d 三种,“好人”在“美人”方面的含义和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2](522)。而就现实使用的日常语言来看,“好人”一词主要是在b、c 两种义项上使用,其在“健康的人”方面的含义虽然存在,但在日常语言中已不再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因此,本文讨论的“好人”观念,主要是就具有积极道德意义的义项b而言——义项c 可以被视为b 在日常生活中的庸俗化蜕变。
不过,即使仅仅聚焦具有正面道德价值的“好人”观念,也依然面临着极为庞杂含混的语言分析空间,因而有必要借助交往的分类进一步加以区分。对每一个交往主体来说,基于其在交往关系中对自身的不同定位,至少存在三类不同的交往活动:一是私人交往,即交往主体将自身定位于“一对一”的私人关系之中而进行的交往活动,交往双方都在彼此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着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位置;二是职业交往,即交往主体将自身定位于“一对多”的职业关系之中而进行的交往活动,具体体现为交往主体作为某种特定的职业角色与不同职业对象之间的交往活动;三是公民交往,即交往主体将自身定位于“多对多”的公民关系之中而进行的交往活动,交往双方都将对方看作政治共同体的一般成员,彼此共享由政治制度赋予的公民关系,并以之作为交往活动的基点②。这样一来,当人们把伦理判断引入对交往的评价时就会发现,对个体而言,在私人交往活动中表现良好的人,可以根据彼此的特殊关系而相应地称之为“好父亲”“好妻子”“好朋友”等;在职业交往中表现良好的人,可以根据其自身所属的职业类型而相应地称之为“好医生”“好教师”“好演员”等;而在公民交往中表现良好的人,则可以根据其自身所具有的公民身份而被一般性地称之为“好公民”。据此,就可以从上述交往的区分中,引申出两种不同的“好人”观念。
第一种是全称性的“好人”观念。它要求个体在所有类型的交往关系中都能拥有良好的表现,从而使交往生活的整体呈现为一种完满的状态。换言之,一个“好人”不仅意味着要努力成为一个“好父亲”“好妻子”“好朋友”,还要成为一个“好员工”和“好公民”,进而在属于人的所有交往活动中都达到一种“好”的状态,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好”“人”。这种“好人”观念可能会被视为道德教育的理想范型,并被用作个体进行伦理反思所依据的参照对象。不过,也正因如此,这种“好人”观念是高度理想化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日常性,不构成本文的主要讨论对象。
第二种是特称性的“好人”观念。与前者相反,它并不要求个体在交往生活的各个方面尽善尽美,而只要求个体在某个或某些方面达到一种“好”的状态。例如,个体可以在私人交往生活和职业交往生活未臻完善的情况下,成为一种特称性的“好人”③。这种意义上的“好人”既与私人交往范围之内的“好父亲”“好妻子”“好朋友”相分离(尽管并不冲突),因而人们可以说:“某人是一个好父亲,但不是一个好人”;也与职业交往范围之内的“好员工”相分离(尽管同样不冲突),因而人们也可以说:“某人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好员工”。正是在这样一些具有充分的可设想性和可理解性的日常语言里,这种特称性的“好人”观念得以凸显出自身的公共性特质。
二、“好父亲”“好员工”与“好人”
为分析这一特质,就需要分别对“好人”观念与私人交往和职业交往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为简便起见,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将把“好父亲”作为良好私人交往关系的一个例子,把“好员工”作为良好职业交往关系的一个例子,从而使其分别简化为“好人”与“好父亲”“好员工”之间的关系。
1.“好人”与“好父亲”
首先来看“好人”与私人交往的关系。如有学者指出的,私人交往属于一对一的特殊交往关系,其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各种私人交往关系之间是彼此独立而分离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不同关系具有不同的要求和规范,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好父亲,却不是一个好丈夫,反之亦然;第二,每一种特殊的私人交往关系的双方多数时候面临不同的要求和规范。例如,同是属于父子关系,但是对父亲的要求和对儿子的要求是不同的,所谓“父慈子孝”就是如此[3]。因此,私人交往一般呈现为某种一对一的特殊义务关系,私人交往的良好状态需要建立在交往双方良好履行各自承担的特殊义务的基础之上。而这样一来,个体在私人交往关系中的良好表现就总会被分化为某种特殊角色的“好”——比如“好父亲”等——从而与“好人”区分开来。
为使二者的区别更加鲜明,可以设想如下三种情境:
情境a:一名父亲奋不顾身救出了落在水里的儿子。
情境b:一名父亲奋不顾身救出了落在水里的继子。
情境c:一名父亲奋不顾身救出了落在水里的陌生人的孩子。
在情境a 中,父亲与落水者之间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父亲的行为是对自身应当承担的私人义务的履行,行为中最先浮现的情感是对亲子生命的看重和爱护。因此,人们也将其行为看作属于父亲基本义务的“分内之事”,从而更多把他单纯地视为一个“好父亲”。在情境b 中,父亲与落水者之间具有法理上的父子关系,同时缺乏实质的血缘关系。双方虽然依旧存在一定程度的特殊义务关系,但一般被认为不如情境a 那样紧密和强烈(日常观念中对继父母的成见是其体现之一)。所以,继父的行为既可以看作对自身应当承担的“父亲”义务的履行,也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世俗观念里对于继父身份的既定成见,从而兼有了“好父亲”和“好人”的意味。而在情境c 中,父亲与落水者之间不具有任何私人关系,也不承担任何特殊的私人义务。这种情况下的出手相救只是纯粹出于对生命的仁爱,无法被归化为任何特殊角色的“好”,因而只能被一般性地称之为“好人”。
由此可见,以“好父亲”为例的良好私人交往与“好人”的区别在于:前者总是以某种一对一的特殊私人义务关系为基础,所谓的“好”往往是对自身所承担的特殊义务的良好履行;后者却总是超脱于任何一对一的私人关系之外,并不需要以某种特殊义务的存在和履行为前提。不仅如此,某种特殊义务关系的存在还往往会妨碍“好人”的生成,因为它总是使其分化为某种特定角色之“好”,而不能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好人”与“好父亲”是截然分裂的,二者之间仍然可以相互转化。例如,儿女既可以将自己的父亲称为一个“好父亲”,也可以将其称作一个“好人”。只不过,前者往往是针对父亲与儿女自身相关的分内之事,后者则往往是针对父亲与他者相关的分外之事。而且,在后一种情境下,作为评判者的儿女已从私人关系的语境中脱离出来,将自身暂时性地放到了一个生活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父亲的行为,并依据常识道德对其做出一种中立性的评判。
2.“好人”与“好员工”
接下来考察“好人”与职业交往的关系。如前所述,职业交往属于交往主体作为某种特定职业角色与众多职业对象之间一对多的互动关系。职业交往的双方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义务关系,但它与私人交往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区别:第一,其义务关系一般源于外部工作的强制性规定,而非个体情感的内生性诉求,最终表现为抽象的职责;第二,其义务关系以满足具体需求的技术性要求为主导,而非侧重情感与心理的沟通和交流,最终落实为量化的指标。这样一来,所谓的“好员工”实际就是对自身作为某种职业角色所承担的工作职责的良好履行。
不过,虽然“员工”是个体在特定时空扮演的社会角色,所谓的“好”是对其良好履行工作职责的肯定。但是,员工在下班或退休之后的业余时间或者在与职业场所无关的私人或公共空间里便可以被还原为普通的个体。就此来看,职业交往生活对个体来说既是必要的,又是有限的——尽管它可能占据着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而“好员工”与“好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好”在于个体对职责的良好履行,具有明确的主体定位和特定的时空限制,后者的“好”则超脱于任何特定的职业关系和时空范围之外;前者主要以自身对他者提供的技术性服务来获得生产生活资料,不排除以自利作为主导因素,后者则是不需要预设任何功利性前提的友善关爱,以纯粹的利他作为主导因素。
不过,这同样不意味着“好员工”与“好人”是截然断裂的,而是存在两种可能的转化路径。第一,“好员工”可以在与职业无关的行为中成为“好人”。例如,一名推销员送迷路的儿童回家,一名售货员将捡到的财物交还失主。在这些事情里,个体的行为与他们自身的职业角色无关,而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去做自身认为正确的事。第二,“好员工”可以在与职业有关但与职责无关的行为中成为“好人”。例如,一名医生无偿救助贫困的病人,一名教师帮贫苦的学生代交学费。这些行为并非基于外在职责的强制性要求,而是基于个体对交往对象的友善关爱。它们虽然与个体所属的职业角色相关,却在其自身必须履行的工作职责之外,因而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被视为他们的“分外之事”。
3.“好人”观念的公共性特质
综上可知,“好人”与“好父亲”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具有任何特殊的私人义务关系,“好人”与“好员工”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具有任何特殊的职业义务关系。“好人”总是存在于剥离了私人关系和职业关系之后、纯粹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它所指向的是不具有任何特殊义务关系的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交往的伦理状态。这里将其具有的这种特质称之为“好人”的公共性。它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好人”对应的交往关系是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交往,具有最大程度的涵盖范围。它比私人交往和职业交往都更为基础,因为任何私人交往和职业交往最终都可以被还原为一般性的“人”与“人”的交往——尽管这种“还原”往往伴随着私人交往关系与职业交往关系的解构和消亡。第二,它总是从社会整体的视角出发并以公众生活中的道德共识作为评判标准。“好父亲”的评价只是相对于儿女而言,“好员工”的评价只是相对于职业对象而言,“好人”的评价则是相对于社会全体而言。当人们说一个人是“好人”时,他们并不是把自身放在某个特殊的私人关系或职业角色的位置上,而是尽力收敛起自身的个性因素,从一般社会公众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好人”观念虽然具有公共性,但在个体的交往生活中未必具有优先性。相比而言,私人交往在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处于核心地位。如何成为私人交往中的好父亲/好母亲、好丈夫/好妻子、好儿女、好恋人、好朋友等,这些对一般人来说基本等同于“做‘人’”的全部内容。职业交往则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被看作满足生产生活资料需要的必要路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分工协作和平等交换。与二者相比,“好人”既不像“好父亲”所代表的私人交往那样具有情感优先性,也不像“好员工”所代表的职业交往那样具有现实必要性。所以,在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世界里,“做好人”有时会被看作一种“分外”的“义务”:选择去做一个“好人”当然会受到社会的褒奖,但是选择不去做一个“好人”也会在某种意义上得到社会的“理解”——这种“理解”尤其体现在“好人不长命”“人善被人欺”等俗语俚谚之中。
由此可知,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为“好人”,是因为他不仅善待那些具有特殊义务关系的“分内之人”,而且还善待那些不具有任何特殊义务关系的“分外之人”。个体对妻子儿女和职业对象的友善关爱,是他的“分内之事”,虽然可以证明他是“好父亲”和“好员工”,却无法表明他是一个“好人”。当且仅当他不但友善关爱那些具有特殊义务关系的交往对象,而且对不具有任何特殊义务关系的陌生交往对象也施以同样的友善关爱时,才能使他真正地成为一个“好人”。换言之,“好人”的精义不在于“老吾老”“幼吾幼”,而在于“及人之老”“及人之幼”,其间的“推己及人”这个过程正是“好人”之所以成为“好人”的关键。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好人”观念可以被视为在私人交往、职业交往与公民交往没有获得明确区分的情况下,对陌生人交往的一种总体性的伦理指导。它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去对待那些与己无关的“分外之人”,并以此作为私人交往伦理和职业交往伦理的必要补充,从而内含了对“陌生人问题”的一种可能回应。
三、“好人”观念的意识结构
不过,一种可能的批评是:这样一种“好人”观念在应对“陌生人问题”方面是否过于软弱无力?对此的回答在于:倘若把视野从单纯的儒学扩展到整体上的中国伦理传统,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观念虽然稍显软弱,却也并非如所批评的那样无力——否则“好人”观念便很难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如此持久的影响力。因为这一理念并非单纯依托纯粹的道德情感,而是同样纳入了功利论的元素,从而使自身得到了双向的支撑。与之相应,常识道德中的“好人”观念并非茕茕孑立,而是存在于与“好心”“好事”“好报”等观念的联系之中,从而构成了一个以“好人”为中心的观念群。这个观念群得到了包含儒释道在内多种思想资源的共同支撑,形成了中国伦理传统在常识道德层面的基本意识结构:出于好心而做好事,由做好事而成好人,因成好人而得好报。
“好心”是这一观念群的始点。所谓“好心”是好人之所以成为“好人”的基础,它将个人内心的仁善从具有特殊义务关系的交往对象推扩到原本不具有特殊义务关系的交往对象之上。这种推扩基于两个条件:一是内心仁善之情的丰厚充盈,若是内心的源泉凋敝干涸,连父母妻儿尚且弃如敝屣,又何谈“及人之老”“及人之幼”呢?二是内心仁善之情的纯粹无私,不得有丝毫私欲混杂于其间。因此,一种纯粹的“好心”的状态应当是这样的:
(1)首先,在看到他人遇到苦难的时候,能够想到自身处于类似境况中的痛苦[“举斯心加诸彼”(《孟子·梁惠王上》)]。
(2)其次,由于想到自身的类似处境,因而会对苦难中的他人产生怜悯与同情[“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
(3)最后,由于对他者的怜悯与同情,因而
第一,不会去做那些导致对方如此痛苦的事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第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对尚未摆脱痛苦的对方进行抚慰和救助[“及人之老”“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个过程就是从“仁之端”到“仁”本身的过程。当一个人内心的“仁善”达到相当丰厚的程度,就不仅能够滋润身边的亲人和熟人,还能从本应承担的“分内之事”中流溢出来,惠及那些与自己没有任何特殊义务关系的陌生人——而这个过程也就是从“好心”到“好人”的过程。
不过,虽然“好心”是“好人”的本质特征,却只能为个体自身所体察,他者看到的只是个体出于“好心”留下的实践印迹,即外在的道德活动,俗称“好事”。对个体自身来说,只要有一颗“好心”便足以自认为是“好人”;但对他者来说,只有实实在在地做“好事”才能印证“好心”的存在,进而使一个人成为“好人”。因此,人们看重的“好事”不能是偶然和单一的,而必须是常态化和复数性的。面对作为单数的“好事”,人们往往很难判断它究竟是发自本心还是一时凑巧,是常态的出于好心还是偶然的合于好心。只有看到作为复数的“好事”时,人们才能更准确地判断某个人的本心如何,并依此判断对方能否被称为好人。因此,“好事”的最终指向仍然是“好心”。“好事”只不过是使内心的仁善在实践中得到呈现和验证,从而把必须履行的特殊义务(“老吾老”)推扩为鼓励践行的一般行为(“及人之老”)。这种推扩一方面扩大了既定交往原则的适用范围,使得陌生人对象能被囊括其中;另一方面也抽空了既定交往原则原本具有的强制性,使其蜕变为人们眼中的“分外之举”。但幸运的是,它并未因此而完全丧失其现实力量,因为常识道德为其寻到了一个重要的外部支撑:“好报”。
“好报”是以“好人”为中心的观念群的终点,是对“好心”和“好事”的回馈与奖励。“好心”和“好事”内蕴于“好人”观念之中,“好报”则作为一种外部性的观念与之相关联。“好人有好报”被常识道德设定为一种基本信念,并假定有某种经验性或超验性的力量在保证着这种信念与现实生活契合一致。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由于佛教、道教等宗教力量的加持,这一信念尤其得到强化,而“好人”观念也随之产生了更大的现实影响力。因此,古人常说“积德行善”,行善的过程就是积德的过程,而积德的目的则在于求得福报——此类观念在善书、家训等传统民间作品中俯拾皆是。然而,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宗教淡褪、科技昌明的现代社会,人们也依旧非常自然地追随着此类信念。例如,网络上流行的“人品”一词原本源于游戏,现在则已不着痕迹地融入日常语言之中。当一个人遇到抽签中奖等具有偶然性的好事时,会被赞为“人品好”;当遇到失窃、比赛失利等具有偶然性的坏事时,则会自嘲“人品差”;当自己平时做好事帮助别人的时候,也会自称是在“攒人品”,以求能够得到好运气。这样一套话语虽然不乏戏谑的口吻,但之所以能流行开来,恰恰因为它依然契合当下社会某种整体性的道德期望。因此,无论“好人有好报”是否属于客观事实,它都属于人们意识中的观念事实。这一观念事实为常识道德提供了另一个根本支点,从而使得“好人”观念避免了曲高和寡的窘境④。
综上,传统的中国社会虽然缺少对私人交往、职业交往和公民交往的精确区分,但借助这样一种以“好人”为中心的观念群,得以为“陌生人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回应。这种回应尽管略显简陋,但并非完全无力。它告诉人们,应当尽可能将特殊交往关系的伦理义务推扩到陌生人之上,从而让自己通过做“好事”而成为一个“好人”。至于为何应当这样做,彰显道德纯粹性的“好心”和具有鲜明功利性的“好报”可以同时从两个截然相反的端口为其提供论据支撑。“好心”观念的道义论色彩使其能够与追求崇高的道德精英直接贯通,而“好报”观念的功利论劝谕则使其赢得了一般民众的普遍欢迎。这一双重的支持使它具有了现实的效力和影响,从而成就了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影响深远的“好人”观念⑤。
[注 释]
①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台湾的经济学家李国鼎指出了传统“五伦”在工业社会中的困境,进而提出处理个体与陌生人关系的“第六伦”,吴惑(孙震)响应李国鼎的提法,为其命名为“群己”关系,以与传统的“五伦”相对应(详见韦政通:《新伦理的讨论》,载《伦理思想的突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82—211 页)。无独有偶,进入21 世纪以来,大陆学界也出现了“儒家与‘陌生人问题’”的讨论,其中以赵汀阳的批评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儒学在面对陌生人困境时存在两个技术性困难:第一,“推己及人—推近及远”的方法实际无法推到很远,因为其间的情感很快就渐趋稀薄以致消失了;第二,“君子德风—小人德草”的方法实际上也是基本没有效果的,因为人们只会根据逐利的冲动去模仿成功的行为,而非道德的行为(详见黄万盛等:《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开放时代》2008 年第1 期)。
②学界一般采用私人交往和公共交往的二分架构,但本文将职业交往独立出来,并通过将公共交往置换为公民交往,从而变成一种“三分”的模式。这样处理的理由在于:第一,“职业—工作”在现代人生活中占据的比重和影响越来越大,职业交往生活事实上已构成独立于私人交往生活和公民交往生活之外的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第二,一般认为职业交往介于私人交往和公共交往的混合地带,但通过将公共交往置换为公民交往,就能将其与职业交往和私人交往的界限厘清,而界定的标准就是交往主体在交往关系中的自身定位以及由此伴随的义务关系的程度差异;第三,私人交往、职业交往与公民交往的指导原则已经相互分离(如下文关于“好父亲”“好员工”等的讨论所表明的),它们构成现代人三种主要的交往活动,也由此构成了一种相对较为完备的分类。此外,哈贝马斯在对现代社会进行结构分析时,将以策略性行为为主导的系统独立于作为生活世界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外,也构成对本文“三分”模式的一种启发(参见芭芭拉·福尔特纳:《哈贝马斯:关键概念》,赵超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87—106 页)。
③尽管本文采取私人交往、职业交往、公民交往的“三分”模式,而且这里提到的这种“特称性的‘好人’”不属于私人交往和职业交往,但是它同样不属于公民交往,因而不同于“好公民”。事实上,“好人”观念根源于一种更为历史悠久的交往“三分”,即根据交往对象的亲疏远近而自然形成的与亲人的交往、与熟人的交往、与陌生人的交往,并主要指向最后一类交往(如下文将要论证的)。在现代政治共同体基础上形成的公民交往与陌生人交往相关,但却属于两类不同的交往体系。
④虽然对“好报”的超验论证随着现代科学的兴盛已逐渐失去其影响力,但在科技手段的辅助下,现代社会更有机会通过巧妙的制度设计为“好人/坏人”提供正当有效的现世奖惩,从而使“好人”与“好报”之间的一致性获得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撑。
⑤现代社会对“陌生人问题”的一般解答方案是使其转化为受到政治—法律保障的公民交往。公民的交往活动具有“公民—国家”和“公民—公民”两个面向:前者是指公民与政治共同体及其代表之间的交往;后者是指公民作为一般成员与其他公民之间的交往——这里说的主要是后者。公民交往是对政治共同体内部的陌生人交往的进一步规范,它把不具有任何特殊义务关系的陌生人转化为具有同等基本权利义务的公民,把他们之间进行一般性交往的指导原则由柔软的良心提升为坚硬的法律,从而为其提供了更可靠的法律规范和权利保障,保证了由陌生人集聚而成的现代社会里构建起有序公共生活的可能性。不过,这一方案虽然有着种种优点,却也至少存在两点可能的局限:第一,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固然为公民交往提供了坚实保障,但也易于凸显和强化公民之间在权利方面的可能冲突,并且使得这种冲突在理论上绝对化从而带来种种无法消解的两难困境;第二,公民身份及其所拥有的公民权利依托于特定的政治实体和政治制度,是一种契约论式的政治设定,只能在政治实体内部获得一种有限的普遍性,无法超越于国籍之外。借用列奥·施特劳斯的话来评论就是:“在希特勒德国的一个好公民在别处就会是个坏公民,好公民与政权是有联系的”(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载《现代政治思想》,杨淮生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80 页)。与之相比,“好人”观念由于依托人的自然情感,恰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好公民”观念的不足,从而凸显出一种灵活性和普遍性。因此,或许可以乐观地期望,中国传统的“好人”观念不仅不会因“好公民”观念的兴起而失去力量,而且可能会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中获取更加深厚的生命力,从而与“好公民”观念一起持续地完善着对“陌生人问题”的现代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