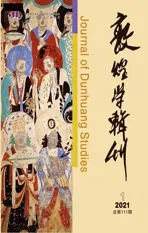1913年狩野直喜、泷精一调查英藏斯坦因搜集品之经过考补
2021-11-25王冀青
王冀青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近代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1868-1947)与美术史家泷精一(1873-1945),均属日本第一代敦煌学家。他们于1913年同赴英国伦敦,在大英博物院(British Museum)调查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8年)所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这次调查活动堪称国际敦煌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故笔者曾在拙著《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中专设3节,介绍其来龙去脉,即第11节“狩野直喜和泷精一制定的斯坦因搜集品调查计划”、第12节“狩野直喜、泷精一和滨田耕作对斯坦因搜集品的调查”和第13节“狩野直喜和泷精一关于斯坦因搜集品的汇报”。(1)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考古档案日本敦煌学史文献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11-137页。近年来,笔者在整理、研究欧洲藏斯坦因考古档案的过程中,又发现若干与本事件相关的新资料,似可补入国际敦煌学史资料中。于是不揣浅陋,草成此文,敬请方家教正!
一
斯坦因结束其第二次中亚考察后,于1909年1月21日返回英国伦敦。装满93箱的斯坦因搜集品,稍后也运抵大英博物院,暂存于靠近东方写本与印本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的地下室库房(斯坦因等人戏称其为“洞窟”)里,等待开箱与注录。在斯坦因的推荐下,其老友弗里德里克·亨利·安德鲁斯(Frederick Henry Andrews,1866-1957)负责开箱工作。后因工作繁重,斯坦因又聘任佛罗伦斯·玛丽·格兰·罗里梅尔小姐(Miss Florence Mary Glen Lorimer,绰号“记录天使”,1883-1967)给安德鲁斯当助手。陆续取出的斯坦因搜集品中,敦煌汉文写本等文书类文物暂由东方写本与印本部主任莱昂纳尔·大卫·巴尔奈特(Lionel David Barnett,1871-1960)主管,敦煌绢画等美术类文物暂由版画与绘画品部(Department of Prints and Drawings)副主任罗伯特·劳伦斯·宾雍(Robert Laurence Binyon,1869-1943)主管。敦煌汉文写本出箱后,东方写本与印本部管理员莱昂纳尔·翟理斯(Lionel Giles,汉名“翟林奈”,1875-1958)负责编写一份简单的清单目录。
斯坦因返回欧洲后,以各种形式为其搜集品中的各类文物征召编目、考释与研究者。斯坦因的老友、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最早承诺考释斯坦因在新疆、甘肃所获简牍等类汉文文书。斯坦因所获敦煌绢画,定由宾雍负责整理与考释。宾雍自知功力不足,又邀请居住在巴黎的比利时汉学家拉斐尔·皮特鲁西(Raphael Petrucci,1872-1917)进行具体考释,而他本人则进行一些概论性、理论性的宏观研究。斯坦因搜集品中的印章、封泥等类文物,交由英国汉学家金璋(莱昂纳尔·查尔斯·霍普金斯,Lionel Charles Hopkins,1854-1952)考释。在斯坦因搜集品的18位考释者中,沙畹表现最好,最早接受并完成了任务。从1909年夏季开始,大英博物院通过法国驻英国大使馆,分批将斯坦因简牍实物从伦敦寄给巴黎的沙畹,1910年3月1日寄出了最后一批简牍。至1910年11月,沙畹基本完成了对斯坦因简牍的考释工作后,于11月28日托法国驻英国大使,将最后两箱子汉文简牍和考释成果带回伦敦。斯坦因于12月5日代表大英博物院,接收了沙畹寄来的文书箱子及考释手稿。(2)关于沙畹考释斯坦因所获简牍的过程,参见王冀青《金绍城与中国简牍学的起源》,《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2期,第135-151页。
1910年1月14-16日,斯坦因在法国巴黎逗留期间,第一次见到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斯坦因与伯希和会面期间,邀请伯希和为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制目录,伯希和初步答应。1910年5月7日,伯希和从巴黎给斯坦因写信,正式表示愿意为英藏敦煌汉文写本编制目录。(3)1910年5月7日伯希和致斯坦因信,法文手写原件藏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斯坦因通信第8号,第1-63张。1911年1月10日,大英博物院将第一批两箱子汉文写本寄往伯希和在巴黎的地址,伯希和开始着手为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目。但不久之后,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于1911年2月为伯希和特设“中亚历史学与古物学讲座教授(chaire d’histoire et d’antiquités de l’Asie centrale)”职位。从此以后,伯希和因科研、教学、编辑工作繁忙,逐渐放缓了他为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目的工作。(4)关于伯希和为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目的起始、经过与结局,参见王冀青《伯希和为英藏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写文献编目始末》,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91-335页。
斯坦因于1911年11月29日离开英国伦敦,返回印度工作。行前,斯坦因于1911年11月26日给合作者们写了一封通函,安排此后的文物考释工作,该函主要内容如下:
马·奥·斯坦因博士兹通知他的朋友们与合作者们如下:他正准备前赴印度,就任设在白沙瓦(Peshawar)的印度考古局(Archaeological Survey)边境大区分局局长(Superintendent of the Frontier Circle)一职。在他于11月29日或此日期前后离开伦敦后,他的第一助手和主要朋友、前拉合尔艺术学校校长(Principal of the Lahore School of Art)弗·亨·安德鲁斯先生(Mr.F.H.Andrews),将接手主管斯坦因博士第二次中亚考察带回来的文物搜集品,这些文物搜集品现在是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院的共同财产。
正在好心地帮助斯坦因博士详尽阐述他的考察所获科学成果的诸位,如果你们为了检查或研究的目的,有关于材料的出借或复制方面的任何直接请求,那就请将你们的请求寄给弗·亨·安德鲁斯先生,地址是:伦敦,西中区,大英博物院,斯坦因搜集品室。
凡是卡片条形式的材料,如果打算在斯坦因博士详尽报告书的描述性目录中有所体现,也请寄给弗·亨·安德鲁斯先生。弗·亨·安德鲁斯先生将做出安排,先将它们打字誊写,然后设法转寄给斯坦因博士。大英博物院东方写本与印本部主任(Keeper of the Oriental Books and Manuscripts)莱·巴尔奈特博士已经非常好心地同意,要在与斯坦因搜集品的写本材料有关的事情上,向安德鲁斯先生提供帮助和建议。(5)1911年11月26日斯坦因致所有合作者通信,英文打字抄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以下简称“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39号,第54-55张;英文打字抄件藏巴黎吉美博物馆(以下简称“巴吉博”),伯希和手稿,Pel.C.62a.,暂编第15件,第32-33张。
斯坦因此次离开伦敦后,一直在印度工作。1913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伯希和为斯坦因写本编目的工作进展越来越缓慢。1913-1916年,斯坦因又在中国西北等地进行了他的第三次中亚考察,直到1916年5月4日才重返伦敦。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狩野直喜与泷精一到访大英博物院并调查斯坦因搜集品的事情。
二
1912年6月,日本美术杂志《国华》社主干(总编)兼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泷精一,奉东京帝国大学之命,赴欧洲进行第一次学术调查活动。几乎与此同时,狩野直喜也奉京都帝国大学之命,赴欧洲考察诸国汉学和东方学研究的状况,主要目的是调查欧洲藏敦煌及中亚出土文物。狩野直喜与泷精一的实际出发时间,都在1912年9月,但西行路线不同。泷精一离开日本后,先历游印度、埃及一线,再经地中海赴欧洲。狩野直喜离开日本后,经俄国西伯利亚赴欧洲,于9月21日到达俄国圣彼得堡。9月26日,狩野直喜离开圣彼得堡,经德国柏林,于10月18日到达法国巴黎。泷精一于1912年底到达巴黎后,与狩野直喜会合,随后两人经常一起活动。
狩野直喜在巴黎逗留期间,与沙畹、伯希和、皮特鲁西等人交往频繁,主要在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阅览、抄录伯希和所获敦煌文书。在此期间,狩野直喜从沙畹等人那里了解到英藏斯坦因搜集品的情况,并计划未来在英国伦敦逗留2-3个月时间,调查、阅览斯坦因搜集品。当时,斯坦因正在印度克什米尔斯利那加工作,于是狩野直喜先请沙畹给斯坦因写信,提出阅览斯坦因搜集品的要求。据狩野直喜后来回忆说:“我在巴黎留居期间,得到了(沙畹)博士的种种帮助。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国家图书馆中典藏的敦煌卷子,与博士的竭力帮助是分不开的。而且,博士还特意给斯坦因氏写信,极力促成了泷(精一)教授和我去伦敦研究大英博物院所藏敦煌遗书和古画这件事情。”(6)[日]狩野直喜《聞沙畹博士訃後》,《藝文》第9年第5號,1918年5月,第56-58頁。
关于沙畹给斯坦因写推荐信之事,我们在有关档案资料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可提供某些细节。沙畹应狩野直喜的请求从巴黎给斯坦因写信的时间,可确定在1912年11月18日。沙畹此前给斯坦因写信时,曾介绍过辛亥革命后流往日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1866-1940)拟考释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的事情。因此,沙畹在这封为推荐狩野直喜而写给斯坦因的信中,特意提到狩野直喜与罗振玉之间的关系。沙畹致斯坦因的这封信中说:
京都大学(Université de Kyōtō)的中国文学教授(Professeur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狩野先生(M.Kano)马上就要从巴黎前往伦敦了,要在那里逗留3个月时间。他与目前暂居京都的罗振玉先生(M.Lo Tchen-yu)非常熟悉。他打算要解读您的印章。请您给您在大英博物院里的助手写信,允许狩野先生参观一下您的发现物。他也许能从中看出问题,并提出一些很好的见解来。狩野先生在巴黎的通信地址是:巴黎第八大区(Paris VIII),包荣路(rue Beaujon)21号。(7)1912年11月18日沙畹致斯坦因信,法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69号,第178-179页。
沙畹在信中提到的“印章”,指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各种印章,当时已委托给金璋进行考释。沙畹向斯坦因提供狩野直喜在巴黎的通信地址,显然是希望斯坦因能直接给狩野直喜写一封授权信。斯坦因收到沙畹来信后,于1912年12月16日从斯利那加给沙畹回信说:
在您的心里,还如此忠诚地保留着有关我的印章的事情,我必须为此向您表示大大的感谢!现在,印章的印文也许已经落入了金璋先生(Mr.Hopkins)之手。正如您所建议的那样,我已于几个星期前给金璋先生写过信。但是,他也许对这项任务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我马上就向大英博物院的罗里梅尔小姐提出要求,让她直接与狩野先生取得联系。请让狩野先生知道,当他来到伦敦的时候,弗·亨·安德鲁斯先生(大英博物院,斯坦因搜集品室)肯定会非常高兴地向他展示我们的资料。如果能提前寄出一封短信,将有助于确定一个方便的时间。(8)1912年12月16日斯坦因致沙畹信,英文炭纸复写抄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69号,第180-180v页。
斯坦因在信中默许狩野直喜赴伦敦参观斯坦因搜集品。他在信中提供了安德鲁斯的通信地址,显然是希望狩野直喜能提前直接与安德鲁斯取得联系。
到1913年1月,狩野直喜与泷精一基本上完成了在法国的工作计划。他们从沙畹处获悉斯坦因允许他们参观搜集品的信息后,确定了1913年春季前往伦敦工作的计划。据狩野直喜于1913年1月22日从巴黎致日本汉学家桑原骘藏(1870-1931)和内藤虎次郎(1866-1934)的信中说:
在本地,听沙畹氏和伯希和氏说,斯坦因氏的发现物从数量上讲比巴黎藏品还要多,而且其中的贵重物品也不少,还有大量的绘画品。在日本有一种传说,说是斯坦因氏的发现物中没有汉字写成的东西,这是讹传。但是,现在要想看到这批东西还是很困难的,因为斯坦因氏眼下正在印度。听说他搜集的古书被贮藏在大英博物院的地下室里,连个目录都没有,不会让别人看的。小生先麻烦沙畹氏帮忙,让他给印度的斯坦因氏写了一封信。斯坦因氏在回信中的态度是恳切的,看样子他对小生的阅览之事是感到很高兴的。只是,图书馆这种东西在中国也好,在西洋也好,都有相同的方面,麻烦的事情令人讨厌,果真能否成功,那还是一个疑问。不过,有斯坦因氏的面子,又有塞伊斯氏的介绍信,想必不会被断然拒绝吧。假如阅览之事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小生打算在伦敦也住上两、三个月。(9)1913年1月22日狩野直喜致桑原骘藏、内藤虎次郎信,转引自《海外通信:狩野博士書信》,《藝文》第4年第4號,1913年4月,第79-80頁。
根据信文可知,狩野直喜除了请沙畹给斯坦因写推荐信之外,还请斯坦因的好朋友、牛津大学亚述学教授阿奇巴尔德·亨利·塞伊斯(Archibald Henry Sayce,1845-1933)给大英博物院写了介绍信。
三
狩野直喜计划去英国调查斯坦因搜集品的过程中,于1913年1月中旬收到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校长松本文三郎(1869-1944)的通知,让他和同校讲师滨田耕作(1881-1938)一起代表京都帝国大学,出席定于当年4月份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3届国际历史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tudies,旧译“万国史学大会”,以下简称“史学大会”)。狩野直喜与泷精一考虑到时间宽松,计划在去英国之前,先在欧洲大陆各国做一次旅行。狩野直喜与泷精一离开巴黎之前,前去向沙畹辞行,在沙畹家中见到了皮特鲁西。据狩野直喜回忆:“泷(精一)教授和我在临别巴黎的时候,抽空前往(沙畹)博士处辞行,恰好东方美术研究家、布鲁塞尔的皮特鲁西氏也正在做客。皮特鲁西氏和泷(精一)教授在很早以前就有通信关系,我记得他们就美术理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0)[日]狩野直喜《聞沙畹博士訃後》,第56-58頁。狩野直喜、泷精一与皮特鲁西约定,不久的将来要在伦敦共同调查斯坦因所获敦煌美术品。
随后,狩野直喜在欧洲大陆旅行,泷精一同时也在意大利、奥地利游历。我们可以推断,狩野直喜和泷精一在欧洲旅行期间应该是在一起活动的。至于滨田耕作来到欧洲的时间,则晚得多。滨田耕作于1912年12月3日接到命令,让他以考古学研究为目的,于次年赴德国、法国和英国留学考察,为期三年整。其间,他先要到英国,与狩野直喜一起代表京都帝国大学出席史学大学。滨田耕作于1913年3月1日被提升为助教授,然后起程赴欧洲。当狩野直喜和泷精一在欧洲大陆旅行的时候,滨田耕作正经俄国、德国前往英国伦敦。1913年3月末,狩野直喜和泷精一从欧洲大陆到达伦敦。1913年4月上旬,滨田耕作也到达伦敦。
狩野直喜、泷精一与滨田耕作会集伦敦后,狩野直喜与滨田耕作首先参加了史学大会。史学大会于1913年4月3日在林肯法学会大厅举办开幕式,共有各国代表680人参会。(11)孟德楷《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37-38页。狩野直喜与滨田耕作代表京都帝国大学第一次出席国际会议,但因参会代表以欧洲各国学者为主,日本学者的地位无足轻重,未获得报道。狩野直喜与滨田耕作出席完史学大会后,便与泷精一会合,开始实施他们对斯坦因搜集品的调查计划。
狩野直喜与泷精一于1913年4月10日来到大英博物院,联系到大英博物院院长兼图书馆馆长弗里德里克·乔治·肯雍(Frederic George Kenyon,1863-1952),以及巴尔奈特、安德鲁斯、宾雍等人。在征得他们同意后,开始入馆调查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写本以及敦煌绢画。4月11日,安德鲁斯从大英博物院给正在斯利那加为第三次中亚考察做准备的斯坦因写信说:
本星期的来访客们占用了我一些时间。我现在已经向托玛斯(Thomas)、巴尔奈特、宾雍和其他人宣布,搜集品尚未处于展览中。昨天,巴尔奈特介绍来两位日本教授,即狩野直喜和泷精一,他们是沙畹推荐的。他们想要在这里花费一段时间。毫无疑问,他们作为学者,是我们所需要的。他们也已经承诺,在他们得到您的准许之前,绝不刊布任何东西。实际上,他们提出了如下请求:既然他们现在已身处英格兰,只要能让他们研究搜集品,您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他们施加任何条件。他们已经见过了伯希和、冯·勒考克和其他人,似乎想要对所有的搜集品进行一番比较研究。我已经设法让他们等待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巴尔奈特建议,您可以通过海底电缆拍发许可电报。但这样做似乎没有必要。假如您发现有理由不允许他们工作的话,那么您可以拍发海底电缆电报,只用一个词“不允许”就可以了。否则的话,我就会在得到适当保护的前提下,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让他们看一些绘画品和写本。(12)1913年4月11日安德鲁斯致斯坦因信,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41号,第95v-96张。
安德鲁斯说他让狩野直喜、泷精一“等待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也就是等到1913年4月26日前后,为的是给斯坦因发来电报指令争取时间。但因斯坦因早已向沙畹承诺过,允许日本人阅览部分敦煌文物。于是,斯坦因在收到安德鲁斯的4月11日来信后,于4月29日给安德鲁斯回信,其中说:
对于那些不请自来的访客们所造成的时间浪费,我感到非常痛惜。我相信,您的态度将会是坚定的。鉴于您在离开前需要完成的任务非常紧迫,请您向巴尔奈特、宾雍解释说,您希望受到保护,要从这类妨害中解脱出来。如果大英博物院想要展示他们保存在“洞窟”里的东西,那他们自己可以提供一名导游。“记录天使”的时间也不应该浪费!
至于那些日本学者,允许他们检查一些绘画品和写本,我并不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提供一份书面承诺书,形式是给您或给我写的一封信,内容是他们在没有事先获得批准的情况下,绝不刊布任何和我们材料有关的东西。我们将这种做法归因于皮特鲁西,他非常敏感地关注他的优先权。对于这些学者们的监管,不能由您或“记录天使”来做。最好是由宾雍出面,在印刷品和绘画品部接待他们,可以把材料送到那里去。我认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13)1913年4月29日斯坦因致安德鲁斯信,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41号,第110v-111张。
可以推测,狩野直喜与泷精一开始调查敦煌文物的时间,应在1913年4月底。狩野直喜与泷精一在调查前,向安德鲁斯提交了书面保证书。1913年5月15日罗里梅尔致斯坦因报告信中,第一次提及狩野直喜在敦煌文物中的发现:“狩野先生在写本中正在发现大量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关于这些发现,我们随后将给您寄去札记。”(14)1913年5月15日罗里梅尔致斯坦因信,英文打字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9张。
四
滨田耕作在参加完史学大会后,决定先在英国留学一段时间。他起初希望在牛津大学跟随塞伊斯学习考古学研究法,于是计划去拜访塞伊斯。1913年5月18-20日,滨田耕作和狩野直喜、泷精一前往牛津大学拜访塞伊斯。5月20日,狩野直喜、泷精一和滨田耕作结束了在牛津的三天访问,返回伦敦,继续在大英博物院的调查工作。5月22日,滨田耕作从伦敦给京都友人写了一封信中说:“上午,大概要和泷精一、狩野直喜两氏一起去大英博物院阅览斯坦因氏搜集品,非常忙碌。”(15)1913年5月22日滨田耕作致京都友人信,转引自濱田青陵(濱田耕作)《ペトリ氏方にて》,《藝文》第4年第7號,1913年7月。後收入濱田耕作先生著作集刊行委員會編《濱田耕作著作集》,第7卷(《青陵隨想》),同朋會,1987年10月,第183頁。
狩野直喜在大英博物院工作期间,除了自己的调查工作之外,还积极地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详尽报告书《塞林底亚》推荐拟制作图版的汉文写本。1913年5月21日,皮特鲁西来到大英博物院,逗留了4天时间,与狩野直喜、泷精一合作,将敦煌绢画全部翻检一过。1913年5月9日安德鲁斯从大英博物院写给斯坦因的信中,附记部分说:
顺便说一下,泷先生已经发现,画在丝绸上的大车里的佛陀像,其实际年代应该是9世纪。我已经要求“记录天使”将确切的年代给您寄去。泷先生说,伴随的天神是星宿!这是非常恰当的,但也许只是表达天王等等的另一种术语。(16)1913年5月9日安德鲁斯致斯坦因信,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41号,第120v张。
1913年5月22日安德鲁斯从大英博物院给斯坦因写信时又说:
毫无疑问,“记录天使”正在向您报告说,皮特鲁西现在正忙着与狩野先生以及泷先生合作,将绘画品从头到尾全部仔细检查了一遍。关于各种题材的重要性,他们的意见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都达成了一致。皮特鲁西将于星期日(5月25日)离开伦敦。(17)1913年5月22日安德鲁斯致斯坦因信,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41号,第138v张。
1913年5月22日罗里梅尔写给斯坦因的报告信中,第五部分说:
皮特鲁西先生现在就在这里。关于他有可能需要的附加照相铜版,我将问问他。当最近一次邀请他时,他只要求一幅(照相铜版B,现在已经寄出)。
如果他不需要全部其余的4幅,我想您也许会喜欢一幅多出来的汉文写本图版,那是狩野(直喜)先生特别推荐的一些写本的图版。
后者实际上没有任何日期,但是它们的日期显然是可以确定下来的,不会有任何疑问。其中一些是非常早的,——在唐代以前。
我们已经拍摄好了照片,将于下一个星期给您寄去,连带一些细节,供您做出决定。(18)1913年5月22日罗里梅尔致斯坦因报告信,英文打字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21张。
罗里梅尔在同信的第六部分又说:
在我为狩野(直喜)先生拿出来的写本当中,发现了另一件画幡的顶部,提供了粉红色和绿色绵羊图案织锦的其余部分。……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和它缝在一起的,是另一件残片,带有类似风格的鸭子图案。(19)1913年5月22日罗里梅尔致斯坦因报告信,英文打字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22张。
皮特鲁西完成合作调查研究后,于1913年5月25日离开伦敦,返回布鲁塞尔。
斯坦因收到安德鲁斯的1913年5月9日来信后,非常关心英藏敦煌文物的版权保护问题,不允许日本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刊布任何东西。斯坦因于5月27日给安德鲁斯写信说:
日本人发现了大量让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对此一点都不感到惊奇。但是,对于因他们的长时间访问而造成的时间损失和诸多不便,我感到痛惜。我希望,已经按照计划,与他们签订了书面协议: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绝不能发表任何东西。——关于坐在大车里的佛像,其年代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皮特鲁西此前难道没有发现这一点吗?他肯定辨识出了星宿的代表物。(20)1913年5月27日斯坦因致安德鲁斯信,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41号,第144v张。
斯坦因收到罗里梅尔的1913年5月22日来信后,于6月15日给罗里梅尔回信,其中说:
对于已经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低估了插图照片所需照相铜版的数目,而犯了这个错误。制作更多印刷版的工作,必须要停止。
我很遗憾,不得不将这一否决权延伸到对狩野直喜先生那幅图版的否定上去。我们只是不能超出已知的预算。然后还必须牢记,《塞林底亚》并不提供任何关于汉文写本的“附录”。因此,图版实际上并没有适当的位置。只是在显示这些写本的外貌时,可以例外。(21)1913年6月15日斯坦因致罗里梅尔答复信,英文打字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21张。
斯坦因于1913年6月15日还根据罗里梅尔来信内容,编写了一份目录:“我了解到,为‘插图照片’等等而制作的‘印版’图版内容如下:……超出这一授权数目(参见出版社的1911年预算)而拍摄成照片的部分包括:……(2)狩野先生的汉文写本图版,1幅。”(22)1913年6月15日斯坦因致罗里梅尔答复信,英文打字抄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23张;英文打字抄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76张。罗里梅尔收到目录后,于7月2日答复斯坦因说:“我们一直没有将狩野的写本送去制作照相铜版,今后也不打算这样做。”(23)1913年7月2日罗里梅尔致斯坦因答复信,英文打字抄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76张。
五
皮特鲁西返回布鲁塞尔后,继续给罗里梅尔寄送研究成果。1913年5月30日罗里梅尔写给斯坦因的报告信中,第四部分说:
皮特鲁西先生现在又从布鲁塞尔给我寄来一些札记,关于他想要拍摄照片的一些主题,用于制作多出来的照相铜版图版。现在已经为他完全拍摄好了两幅,还有为狩野先生的那件写本拍摄的有疑问的一幅照片。我期盼着能立即得到他答应提供的附加目录,然后让您知道,它们会填满两幅图版还是三幅图版。在后一种情况,狩野先生的图版就不得不取消了。
皮特鲁西先生曾在这里逗留了4天时间,在泷(精一)先生的帮助之下,对于那些最有疑问的问题,显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24)1913年5月30日罗里梅尔致斯坦因报告信,英文打字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27-27v张。
1913年6月12日,当罗里梅尔给斯坦因写报告信时,还附寄了一张由伯希和、狩野直喜等人提供的《塞林底亚》图版说明。据罗里梅尔信中说:“我今天给您寄上如下内容:……(2)溴素纸相片第164幅、第165幅,附有伯希和先生撰写的有关第164幅所印写本的札记。”(25)1913年6月12日罗里梅尔致斯坦因报告信,英文打字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42张。
罗里梅尔附寄的这张纸,由两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主要由伯希和用法语写成,标题是“伯希和先生撰写的有关图版第164幅上所印写本的札记”。上面记录了5件写本:(1)Ch.6号写本,《普曜经》卷五结尾部分,断代为400年左右,括号里用英语记录:“狩野先生和泷先生也认为这是相当确定的”;(2)Ch.401号写本,断代为522年;(3)Ch.478号写本,没有札记,断代为601年,括号里用英语记录:“莱·翟理斯确定”;(4)Ch.79号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断代为700年左右;(5)Ch.365号写本,断代为991年,括号里用英语记录:“翟理斯先生和泷先生无法建议更好的宋代写本”。第二部分由狩野直喜用英语写成,标题是“狩野先生撰写的有关第6件写本的札记”。其内容如下:“Ch.1283号,尼姑灵惠在死床上写下的遗书,纪年为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十月廿三日。”(26)1913年6月12日罗里梅尔致斯坦因报告信,英文打字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45-46张。最终于1921年出版的《塞林底亚》第4卷中,图版第168幅上刊布了Ch.6号、Ch.401号、Ch.478号、Ch.79号、Ch.365号、Ch.1283号这6件汉文写本的照片。
由于滨田耕作的主要任务是留学,学习考古学方法,所以他只是在调查过程中给狩野直喜、泷精一当助手。1913年6月,狩野直喜和泷精一结束了在大英博物院里的调查工作,离开伦敦,经由欧洲大陆回国。据罗里梅尔于6月27日写给斯坦因的报告信的第六部分说:“泷先生和狩野先生已于本周离开。关于他们的调查工作,他们自己正在亲自给您写信汇报。”(27)1913年6月27日罗里梅尔致斯坦因报告信,英文打字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69张。斯坦因收到罗里梅尔的6月27日来信后,于7月21日给罗里梅尔回信说:“我将会对他们的来信感兴趣。但愿他们会牢记他们的承诺,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绝不刊布任何东西。皮特鲁西先生也许可以作为他们的先例。”(28)1913年7月21日斯坦因致罗里梅尔答复信信,英文打字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69张。
据滨田耕作于1913年7月24日后不久从英国写给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同僚的第二组通信中说:“(1913年)6月27日,去车站送狩野(直喜)、泷(精一)两先生往德国。”(29)[日]青陵生(濱田耕作)《英國通信(二)》,《藝文》第5年第3號,1914年3月,第72頁。可知,狩野直喜、泷精一离开伦敦前往欧洲大陆的确切时间是6月27日。狩野直喜和泷精一离开英国后,狩野直喜游历了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等国,泷精一游历了德国、俄国等国,然后陆续返回日本。泷精一于9月回国,(30)『國華』第23編(總第273號),1913年2月,雜錄部,第214頁。泷精一回国时间一说是大正二年(1913年)8月,见[日]藤悬静也《瀧博士の追忆》(上),《國華》第55編(總第651號),1946年6月,第66頁。狩野直喜则于10月返回日本。
狩野直喜和泷精一在大英博物院的工作成就,尤其是狩野直喜的汉学功力,给肯雍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于当伯希和为英藏敦煌文献编目的工作越来越缓慢、一度想放弃时,肯雍等人竟想到由日本人替换伯希和的主意。
六
1913年6月4日,肯雍给斯坦因写了一封信,对斯坦因搜集品的编目、分配、展览等工作提出一些建议。其中,肯雍建议让日本学者取代伯希和,为敦煌汉文写本编目。肯雍的意见如下:
您将汉文写本的编目工作委托给了伯希和先生,有人告诉我说,他取得的进展很小,或干脆没有任何进展。您的搜集品在大英博物院与印度事务部之间进行瓜分之前,这里需要这批写本,时间都快要到了。因此在我看来,有必要向伯希和先生提出要求,请他把写本退还给我们(如果他无法承诺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他的工作)。还有人告诉我说,到了那时,我们可以让一位能胜任的日本学者来为我们编制这份清单目录。不过,由于与伯希和先生之间的协议安排是由您进行的,我不愿意采取任何让您感到为难或看上去对您不礼貌的行动。因此,我给您写这封信,想问一问,对于我建议采取的步骤,您是否有任何反对意见?(31)1913年6月4日肯雍致斯坦因信,英文手写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89号,第132-133张。
斯坦因对于让日本人替代伯希和的想法非常生气。他于1913年6月28日给罗里梅尔写信时,针对肯雍建议由日本人代替伯希和为英藏敦煌文献编目一事,询问道:
我刚刚收到弗·肯雍先生写来的一封信,其中表达了一种疑虑。这条消息打消了这个疑虑。弗·肯雍先生在信中提到,有一个日本人想要做编目工作。这个日本人是狩野先生吗?是谁鼓励他向一项已经说好了的任务提供他自己的服务呢?(32)1913年6月28日斯坦因致罗里梅尔答复信,英文打字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32张。
斯坦因收到肯雍的1913年6月4日来信后,于6月30日给肯雍回信。关于伯希和编目的问题,斯坦因向肯雍表达的意见如下:
我无需冗长地解释,有种种特殊的理由,让我于1910年迫不及待地想要让伯希和先生承担起这项任务。关于这个主题,我于1910年9月向印度事务部提交的官方推荐信中,已详细说明了这些理由。毫无疑问,在您的同意下于1910年底为他编写清单目录事做出安排时,这封推荐信也被呈交给了您。但是我认为,提一下后列各点,对他来说才是公正的。众所周知,伯希和教授具有承担这项任务的特别资质,肯定无人匹敌。他不仅对他在敦煌本地工作时涉及的中国文献学若干分支的图书文献了如指掌,而且还从同一座敦煌寺院藏经洞中精选了大量搜集品,并带回了巴黎。因此,他比任何在世的学者都更有资质去处理我的搜集品中所包含的数以百计的当地文书。因此,他愿意编写清单目录,就代表了一种未来很长时间或永远也不可能再出现的好机会。
还必须要记住,1911年法兰西学院为他特设了讲座教授的职位,必定会在一段时期内大大缩减他可以利用的闲暇时间。既然他的讲座课程等等已经组织起来了,那还是应该有理由指望他的工作可以稳步进展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肯定,他现在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完成这项任务;由他编写、由大英博物院出版的一份清单目录,其所拥有的价值,要比其他任何人编写的目录持久得多。还有一种出于实际方面的考虑,根据目前已获批准的安排,伯希和先生几乎是在有名无利的情况下愿意承担这项工作的。他能得到的酬金,只有200英镑,而且是由印度事务部提供的。我虽然不是汉学家,但是我认为,我可以蛮有把握地确定,如果编写清单目录的工作委托给其他任何人的话,那结果会是:其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其花费则要大得多。(33)1913年6月30日斯坦因致肯雍信,英文手写草稿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89号,第134-137张。
总之,斯坦因反复强调,只有伯希和才有资格为敦煌汉文写本编目,不赞成由日本人接替编目工作。
1913年6月13日,巴尔奈特从大英博物院给斯坦因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伯希和想放弃编目工作的原因:
您也许已经从安德鲁斯先生那里获悉,伯希和最终还是同意,要在他的编目工作方面,继续往前走。您听到这一消息后,应该和我一样感到欣慰。原因也许是这样的,他知道了我们的日本来访客们正在我们的搜集品中工作,他以为这就说明编目工作可能会从他的手中被剥夺,要进入日本人之手。不管怎样,他已经屈服了。狩野(直喜)在写本当中正在取得惊人的发现。史书、类书,还有佚失了的经典,正在大量地涌现出来。昨天,他还让我看了一件《道藏》(TaoistTripitaka)序言的写本,这是一个极为珍贵的发现。(34)1913年6月13日巴尔奈特致斯坦因信,英文打字原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65号,第17-17v张。
斯坦因收到巴尔奈特的1913年6月13日来信后,于7月4日从斯利那加给巴尔奈特回信如下:
您与伯希和打交道时所取得的成绩,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安慰。罗里梅尔小姐将会向您展示一封信的抄件,您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我还不得不就此话题给弗·肯雍爵士写了信。我最真诚地希望,关于搜集品、展览会等等,他将会总体上赞成我的建议和请求。对您能够提供的任何帮助,我将感激不尽。您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了解,在那些请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面临的特殊困难又是什么。对于我的工作来说,罗里梅尔小姐在搜集品室提供的持续不断的帮助,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我高兴地获悉,在我们的敦煌劫掠物里,您的日本来访客们持续不断地取得了有趣的发现。这么说来,毕竟还是有好运气指引着我,进行那些“为进一步研究而进行的挑选”。(35)1913年7月4日斯坦因致巴尔奈特信,英文打字抄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65号,第38-39张。
1913年7月31日,伯希和给巴尔奈特写了一封信,正式宣布他放弃为斯坦因写本编目的工作。此后虽经多次反复,但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伯希和应征入伍,不久出任法国驻华公使馆武馆,再也没有考虑过为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目的事情。
七
1913年8月8日罗里梅尔给斯坦因写报告信时,在第六部分汇报说:“巴尔奈特博士告诉我们说,伯希和先生已经得出最后的结论:他肯定不能再做汉文写本了。不过,关于这件事,巴尔奈特博士马上就会给您写信的。”(36)1913年8月8日罗里梅尔致斯坦因报告信,英文打字抄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97张;英文打字抄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101张。斯坦因于1913年9月24日给罗里梅尔回信时说:“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但完全不感到惊奇。请代我向巴尔奈特博士问好。”(37)1913年9月24日斯坦因致罗里梅尔答复信,英文打字抄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101张。
1915年1月22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长弗里德里克·威廉·托玛斯(Frederick William Thomas,1867-1956)代表印度政府,在大英博物院与巴尔奈特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写成《1915年1月22日托玛斯博士和巴尔奈特博士之间达成一致意见的关于写本分配建议的札记》,其中第1条规定:“所有的汉语文写本,包括沙畹考释过的木牍文书,归大英博物院。”(38)《1915年1月22日托玛斯博士和巴尔奈特博士之间达成一致意见的关于写本分配建议的札记》,英文打字抄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94号,第219张。此后,为英藏敦煌汉文写本编目的事情,再次提上大英博物院的议事日程。
1916年4月,刚刚结束第三次中亚考察的斯坦因返回英国,此后经常在大英博物院地下室整理他的文物搜集品。1916年6月初,日本净土宗学者矢吹庆辉(1879-1939)到达伦敦,调查英藏敦煌汉文写本中的佛教典籍。矢吹庆辉结识斯坦因后,在斯坦因以及罗里梅尔等人的帮助下,于1916年6月上旬至11月上旬调查了英藏敦煌汉文佛教文献,同时有选择地对其中的古逸佛教典籍拍摄了照片。(39)关于矢吹庆辉及其对斯坦因搜集品的调查活动,参见王冀青《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与矢吹庆辉往来通信调查报告》,《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第109-118页;王冀青《矢吹庆辉(公元1879-1939年)》,陆庆夫、王冀青主编《中外敦煌学家评传》,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7-205页;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第174-204页,第238-276页,第318-338页,第414-423页;王冀青《矢吹庆辉与英藏敦煌文献摄影》,《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296-319页。
狩野直喜、泷精一、矢吹庆辉等日本学者调查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成就,给斯坦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斯坦因在《塞林底亚》第2卷的“关于图版第166-169上刊登的千佛洞出土写本的札记”中,涉及到Ch.6号写本卷子时说:
Ch.6号写本卷子,显示《普曜经》(Samantaprabhasa-sutra,即南条文雄《目录》第160号,但略有不同)卷五的末尾。这件写本没有纪年,但是伯希和教授认为,其书法比魏代书法更古,因此将其年代确定在公元400年左右,这个观点也被狩野直喜先生和泷精一先生完全接受。(40)Aurel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Vol.II, p.918.
斯坦因在《塞林底亚》的“补遗与勘误表”中提到上引一段话有误,指出“将泷精一改为矢吹庆辉”。(41)Aurel Stein, Serindia, Vol.I, p.xxiii.但关于狩野直喜的提法,看样子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斯坦因没有说明狩野直喜等在什么场合接受伯希和的观点。又如《塞林底亚》第2卷讨论罗里梅尔所编敦煌出土绘画品注记目录时,感谢了泷精一和矢吹庆辉:
在这份注记目录中,也包含了许多有用的信息,譬如从弗·亨·安德鲁斯先生(Mr.F.H.Andrews)那里得到的有关艺术问题的信息,从莱·翟理斯博士(Dr.L.Giles)和亚·魏礼(A.D.Waley)那里得到的有关题记的信息,以及诸如泷精一教授、矢吹庆辉先生这样的日本专家学者在访问参观本搜集品时就造像学问题好意提供的富有价值的指点。(42)Aurel Stein, Serindia, Vol.II, pp.835-836.
当1915年确定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写本划归大英博物院所有之后,斯坦因为了恢复敦煌汉文写本的编目工作,首先征询了许多欧洲汉学家的意见,其中包括金璋。1917年7-8月,斯坦因通过巴尔奈特,或自己亲自出马,多次邀请金璋为敦煌汉文写本编目,但均遭婉拒。
至此,斯坦因感觉到,在欧洲一流汉学家当中,无人愿意或有能力为敦煌汉文写本编目。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斯坦因想起狩野直喜、泷精一和矢吹庆辉等日本学者在大英博物院的工作业绩,建议大英博物院出面,邀请日本学者为敦煌汉文写本编目。
八
斯坦因在从英国返回印度的前夕,于1917年9月25日从大英博物院给肯雍写了一封建议信,其中说:
在与有能力的东方学家朋友们和合作者们商议之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和结论:要想令人满意地尽早实施这项庞大的工作,不可能指望实际上愿意效力的任何欧洲汉学家去完成这项任务。这项任务所暗含的资质要求是如此多种多样和特殊,以致于在欧洲学者当中,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有可能具备那些资质。而这极少数的几个人,也不可能指望他们会掌握有足够的闲暇时间,去完成这项任务。或者,也不能指望他们会心甘情愿地让自己承担起这项任务。
因此,在我的顾问们看来,同样在我看来,最合适的一个办法,就是设法获得一位有能力的日本学者的帮助,他必须对汉文文献了如指掌,尤其是佛教方面的汉文文献,同时也在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方面受过训练。在我的顾问当中,我特别要提到的是前驻华领事机构的金璋先生(Mr.L.C.Hopkins),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汉学家。狩野(直喜)教授和泷(精一)教授这样的日本学者,都已经怀着巨大的兴趣,研究过我们的搜集品。矢吹(庆辉)先生也分别于1914年和1916年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致力于对搜集品的稳步研究。这些都证明,在日本学者当中,他们都赋予搜集品以重要性。对于一些受过适当训练的日本青年学者来说,编制一份计划中的草目肯定是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作;从科学角度讲,也是非常有收获的工作。因此,如果大英博物院董事会能通过合适的渠道邀请日本政府推荐一位合适的人选,来从事这项工作,我们有种种理由可以指望,他们会仔细谨慎地保证,由他们的文部省(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进行选拔工作,最终在东京的帝国学士院(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协助下,遴选出一位完全有能力的学者来。由印度事务部已经提供的200英镑的酬劳,大概足以满足最终承担任务的这位学者逗留本国期间的实际花费。他走一条日本轮船线路的旅行花费,并不会在已做预算中牵扯进很大的追加部分。
如果本建议得到了您的支持,并获得大英博物院董事会的采纳,那么最佳程序应该是向日本驻这里的大使馆寻求帮助,以便能实施方案。要么直接联系,要么通过英国外交部联系。无论情况如何,都有理由相信,这样一项为了学术援助而由大英博物院董事会提出的请求,必将在日本受到理所应当的满意对待,也许还会得到一个心甘情愿的答复。(43)1917年9月25日斯坦因致肯雍信,英文打字抄件藏牛包图,斯坦因手稿第89号,第153-157张。
在斯坦因的心目中,狩野直喜、泷精一和矢吹庆辉这三人,是与翟理斯同样有资格为敦煌汉文写本编目的日本人。斯坦因提出的由日本学者为敦煌文献编目的建议,最终并没有得到肯雍和大英博物院董事会的采纳。
1919年,大英博物院任命翟理斯为助手,正式接手为英藏敦煌汉文写本编目的工作。关于翟理斯接替伯希和为英藏敦煌文献编目的事情,斯坦因在《塞林底亚》第24章“千佛洞所出纺织品遗存和写本”第4节“藏经洞出土婆罗迷字和汉文写本”中记录说:
1910年秋,第一批写本被及时地寄送给了在巴黎的伯希和教授,为的是它们能够获得编目。但是,由于伯希和教授个人的情况以及其他科学工作的压力,直到1914年夏天,对它们的编目工作还没有完成。这时,战争爆发了,伯希和教授应征入伍,在法国军队里服兵役。由于其他方面的职责,伯希和教授后来一直没有能够重新捡起编目工作来。因此,编制一份详细目录的任务就落在了大英博物院的莱·翟理斯博士的肩上。(斯坦因附注:在本书付印时,至少已有2000件以上的独立写本被编了目。)在这一段时间里,搜集品的这一部分吸引了日本国内的理应关注。有好几位非常能干的学者,都为它们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和劳动,譬如狩野(直喜)教授(Professor Kano)、泷(精一)先生(Mr.Taki)于1912-1913年,矢吹(庆辉)先生(Mr.Yabuki)于1916年。他们检查了一些特殊的写本,尤其是那些对于研究佛教造像学以及类似学科具有特殊意义的写本。(44)Aurel Stein, Serindia, Vol.II, pp.916-917.
翟理斯于1919年接手英藏敦煌汉文写本的编目工作之后,经过长年不懈努力,至1952年才完成原稿。1957年,翟理斯的目录《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由大英博物院董事会出版。(45)L.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57, xxv+1334 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