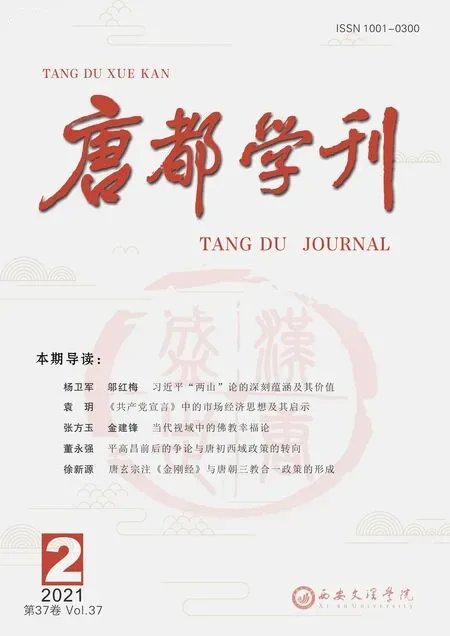《庄子》与《紫文要领·物哀论》“情”观异同论
2021-11-25雷晓敏
雷晓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州 510420)
《庄子》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情”。五彩缤纷的“情”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首先是“物情”,它包含有人的情绪、感情与本真之情;其次是“气情”,它是情与理性相结合,人经过理性思考的情感;第三是“道情”,这是庄子的核心追求,指人的精神愉悦、精神自由之情。《庄子》的核心内容就是遵照、顺应人生命的本真实情[1]。本居宣长在《紫文要领》中提出的“物哀”论,强调写作要追求“真实”,不要道德、伦理的束缚,不要教训、教诲[2]37,其“物哀”论所主张的“人情”汲取了庄子的“物情”,放弃了更高层次的“气情”,更不及“道情”。庄子强调人应该摆脱对“物”的依赖与执著;而本居宣长“物哀”论之“情”则深陷偏执之中,不知自拔。
一、《庄子》的“物情”观与本居宣长“物哀”论的“通人情”
《庄子》关于“情”的表述有不同的指涉,也有高低之分,有取舍之别。陈鼓应认为:“《庄子》中的‘情’具有‘真’‘实’和‘感情’等多重意蕴,在生命的智慧哲学里,隐喻了人的伦理观,对于艺术境界而言,含藏着中国古代道德的意蕴,它开启了中国人性论历史绵延而波澜的抒情传统。”[3]庄子“情”观的内核是他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本居宣长“物哀”论中对于“情”的论述也有三个方面,分别是“通人情”“表现人情”以及追求“真实人情”,这三者均与“不伦之恋”息息相关。关于本居宣长“物哀”论,笔者在拙作《本居宣长“物哀”论的学术价值探讨》一文中已经详述其成败利钝[4]。本文的重点在于细究庄子的“情”观与本居宣长“物哀”论之“人情”的内在关联。
本居宣长“物哀”论之“人情”来自于《庄子》的“物情”层面,而且本居的文学观止步于此。他把“通人情”与“物哀”相结合,并使二者融合。甚至,他认为“物哀”是日本和歌与物语的宗旨[2]110-111。庄子的“物情”是追求“真实”。然而,“气情”比“物情”更可贵之处就在于人的理性与“情”的结合,它规避了“情”的感性与极端化。庄子的“道情”观是比“气情”更高的追求,即“人的精神自由”。庄子的“气情”“道情”观远高于本居宣长所理解的人的“自然”性。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强调的是不受伦理规范约束的、抛弃理性的“情”。客观地讲,这是狭隘的、偏执之“情”。
有学者统计,《庄子》一书中,“情”字出现了62处[5]。也有学者认为,《庄子》中“情”字出现了50次[6]。具体的数字与版本相关,在此不做赘述。仅就庄子之“情”的含义及其哲学思想与本居宣长的“人情”观进行比较。陈鼓应认为:“从概念分析的角度追溯,在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情’观首先是由庄子提出的。”[3]由此可知,研究庄子之情,以及本居宣长“物哀”论之“人情”是中日文学理论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
因为《庄子》中,关于“情”的表述有多种含义,所以常常令读者产生困惑。对此,我们首先要了解庄子哲学的内核,同时根据不同的语境,准确地把握庄子的“情”观。研究《庄子》之情,需要联系庄子的时代背景以及庄子的哲思理路,才能做出相对全面而合理的阐释。“《庄子》的内篇把‘人情’提升至‘气情’‘道情’的哲学形而上的境界;而外篇则由‘道情’‘气情’反向流动为‘任情’‘安情’的现实人性。根据史料记载,庄子与屈原几乎是同时涉及‘情’论,前者的情观可归纳为想象哲学,而后者则可以总结为想象文学,一个是‘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另一个则是‘发奋以抒情’。二者汇合而为后世畅叙‘情’意的历史序幕。”[3]《庄子》中的“物情”具有“本真、实情”的含义,即事物的真实状况。它是客观的、自然运行的规律。它强调的是一种对本真、实情的描绘与体悟。庄子认为:“人如果能够做到‘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才能够与大道相通。”[1]《庄子·大宗师》也就是说,人如果能够安静时如同秋之静默、萧索;开朗时,愉悦的心情如沐春风。人的喜怒哀乐与四时相通,随季节的变化而自然地调适自己的心境,顺应自然。这就是庄子之“物情”,也是人的自然情感。也有人说这是“本然”。这里的“物情”与人的生理因素紧密相关,是一种浅层次的情感反应。比如,当人看到美景,就会自然地感到赏心悦目;看到污浊的环境,就会产生反感,甚至是厌恶之情。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人的赏心悦目与反感厌恶都是外在的景物与环境触动的。这种情感是由客体引起的一种无意识的反应。作为主体的人并没有参与其中,只是油然而生的一种喜悦或者厌恶。这样的“情”是直接性、短暂性与自发性的。
这个观点与本居宣长阐述“物哀”曾经举的例子如出一辙。“人看见樱花盛开,就会表现出开心与愉快;看到别人痛苦,就会伤心难过一样,这样的人就是‘通人情’‘知物哀’的。”[2]57本居宣长的“通人情”与庄子的“物情”是一个层面的表述。对于“通人情”,本居宣长格外推崇。他在“物哀”论里认为:和歌与物语中,有“通人情”与“不通人情”之分。“通人情”就是“知物哀”,不通人情就是“不知物哀”[2]37-38。具体而言,本居宣长认为:将人情如实地描写出来,让读者深刻地认识与理解人情,也就是让读者“知物哀”,像这样呈现人情、理解人情,就是善,即“知物哀”。看到他人哀愁而哀愁,听到别人高兴就高兴,这就是“通人情”,就是“知物哀”。而那些看到他人悲伤而无动于衷,看到别人忧愁而熟视无睹、麻木不仁的人,就是“不通人情”“不知物哀”的恶人。在这里,本居宣长用“物哀”的概念替换了人类日常生活中“善恶”的判断,并把“知物哀”与“善”及“不知物哀”为“恶”划上了等号。研究他的“物哀”论,让读者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放弃人的善恶判断,只追求物哀”的文学观是一种正确的审美观吗?甚至,本居宣长认为:应该凡事都是以“物哀”为先,即使是恶行,也可以弃而不论。柏木奸淫他人之妻,即女三宫,光源氏的妻子,并生有一子,这样作奸犯科的恶行,也是好人[2]41。这样的文学观是狭隘的,其观点是错误的,这是一种完全没有伦理道德的表述。
人因为经历不同,所以选择就不同。庄子认为,有的人可以超凡脱俗,比如姑射山神人的追求,就是超越了凡夫俗子的神人。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反。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迳庭,不近人情焉。”[1]《庄子·逍遥游》肩吾认为接舆所言的神人“不近人情”。神人是超出常人的。此处的“人情”指人的自然而有的生命特质,是人生命的本真情实,而姑射山神人的体貌、行为皆不是常人。庄子的这个寓言故事把常人与神人进行了比较。大多数的普通人有着常人的追求,其实就是争功求名。与“常人”相对而言的是“神人”,神人之所以是神人,就在于其超脱的思想境界,不为名利所累,以精神自由为最高的目标。庄子赞赏的是神人,是超脱的人而非“常人”。这里,庄子的“人情”是普通人的一般情况。
本居宣长在京都游学之际,曾经研读过《庄子》,并做了相关的摘录[7]。据记载,本居宣长曾经给《庄子》做过注释[8]。因此,本居宣长学习并借鉴了《庄子》的观点,在“物哀”论中所表述的“通人情”,就是要作者在写作时呈现人情、理解人情。本居宣长为了“通人情”而放弃人类的道德价值,仅是为了追求描写人的真实情感。从境界的角度讲,这是比较浅层面的文学观。
二、《庄子》之“气情”与本居“好色”的不伦之情
庄子之“气情”是相对于“物情”而提出来的。“气情”区别于“物情”之处,就是“气情”是“情”与理性相结合,经过理性思考的情感。其主体具有自觉性、主动性与理解力,其特点是真挚、稳定、持久与笃诚。主体的领悟力越高,其“情”越深刻、越炽热。陈鼓应认为:“中国儒、道两家是同源而异流的理论。关于心性而言,孟子开辟出心性的道德领域,而庄子拓展出心性的审美向度;孟子侧重于人性的善,而庄子倾向于人性之真。可以说,在人性的问题上,儒、道两家的理论呈现出互补的关系。[3]”概而论之,庄子的道家思想与孔子的儒家思想在道德、伦理方面的追求是同中有异、异中存同的。
在“老聃死,秦失悼之”[1] 《庄子·养生主》的寓言里,“遁天倍情”一词的意思是人要“遵循生命的本然之情,保持本真之情”。庄子认为:“人不应该放纵自己的情感戕害身心;也不应该人为地延年益寿。”也就是“不以好恶内伤其身”,或者“不益生”。正确的态度是“常因自然”,即“顺应自然的生命,把握生命的本然”。庄子之“气情”通常表现为“无情”与反对“常礼”。
关于庄子的“无情”。庄子与惠施有一段对话:“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1] 《庄子·德充符》惠子对庄子说:“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也就是说,圣人有俗人的外在人形,而无俗人的内在。因为有俗人的外在形状,所以能存在于人群之中。无俗人的名利追求,因此可以摆脱许多是非之争。普通的外形等同于俗人;超脱世俗的内涵是为了顺应天命。惠施问:“圣人难道不是人吗?既然是人,他真的能超脱人的情欲吗?”庄子说:“能。”惠施问:“如果人无情,还能算是人吗?”庄子说:“人按照阴阳变化的规律,继承了父母给他的相貌、身材、血型、气质、灵魂,大自然所提供的空气、阳光、水等物质,塑造了人的骨骼和身体,怎么能说他不算人?”惠施又问:“既然算是人,又岂能无情?”庄子回答:“你把人的内在精神当作了人之情。此处的内在精神,凡是人,则皆有之,他当然有,但他的内在精神不同于世俗的人。我说的圣人无情,指圣人没有俗情,即摆脱了是非,忘掉得失,能勘破死生,能淡化欢爱,能化解仇恨的能力。他不让俗情之斧砍伤灵性与身体,而不是说他的心冷若冰霜,像岩石一样坚硬。他的心温暖,四季如春。他顺应自然,即顺应天命,不炼丹服药,不求所谓的长生不老。”
以上的寓言故事阐述了庄子的“无情”。庄子的“气情”是高尚的情感,是脱离了低级追求之情。与之相对的是本居宣长的“通人情”。本居宣长为了说明“情”的唯一性,他在“物哀”论里认为最能体现人情的,莫过于“好色”,因而“好色”者最感人心,也最知物哀。不写好色则不能深入人情深微之处[2]65。不能很好地表现“物哀”之情如何难以抑制,如何主宰人心。本居宣长认为,日本的物语文学作品详细地描写恋人的种种表现,目的是使读者感知“物哀”。本居宣长“物哀”论里的人情是“俗情”,是不受理性束缚的滥情。
关于庄子的反对“常礼”。庄子反对人执着于“礼”的外在形式,而违背情感的真实。他反对的仅仅是世俗的人情世故,而不是“道”“德”与“仁”本身的高尚情操。因为世俗的人情具有“虚假化、程式化、规范化”的特点。庄子主张的是“情感的自然而然,反对情感的放纵与压抑”。也就是为了表现“仁”与“礼”而人为地做出符合人之常情的外在动作与表现。本居宣长在“物哀”论中排斥儒学的道德伦理是反对理性,反对理性对“情”的约束。即“以理制情、以理化情”。
笔者认为,本居宣长在“物哀”论里,把“好色”作为一个表现人情的手段是不可取的。人之所以是人,人区别于动物的正是人的理性与人的道德伦理观。正如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解,由于理性的成熟,人类的伦理意识开始产生,人才逐渐从兽变为人,进化成为独立的高级物种。把人同兽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就是人具有理性,而理性的核心是伦理意识[9]。具体地说,庄子的“气情”与本居宣长“物哀”论里的“通人情”的区别就在于,庄子反对的是儒家道德观中的“礼”以及“礼”的外在形式,他并不反对“道”与“德”,也不反对理性对“情”的制约,而本居宣长反对的则恰恰正是人的理性对情感的克制。相比之下,庄子推崇人的真实、本然的情感,反对人对自身情感的放纵。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所注重的审美尺度与伦理选择。
《庄子》的“气情”与本居宣长“物哀”论中对“性”的宽容相比,是云泥之别的审美追求,二者有着巨大的差异。《庄子》认为,人生于天地间,要遵从道德规律而行,敞开生命境界而活。庄子期望人顺应“物情”“气情”,体悟“道情”。寻求真情,不以好恶损害自己的本性,顺其自然而不用人为去增益。本居宣长汲取了《庄子》反对儒家“礼”“仁”“道”“德”的规范化,并彻底抛弃了中国儒道文化中对“礼”“仁”“道”“德”至高追求,以“好色”之名,把日本传统的“不伦之恋”奉为日本文学文化审美的终极关怀。
三、庄子之“道情”与本居的“愚懦”的真实人情
庄子之“道情”,即指“道之实情”。庄子之“道情”指情感与理智的合二为一,表现为“精神上的愉悦”,也可以说是“精神上的自由”。《庄子》中的“道情”是庄子的人生论与自由观的集中体现,他主张人摆脱世俗中对物的依赖,他一生都向往超脱,希望获得精神的自由,实现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这是庄子之“情”的最高期待。
庄子破除了对“生死的执着”。庄子曰:“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1] 《庄子·大宗师》概括而言,庄子认为:“道是有情有信的”。虽然道无为无形、不可描述,也看不见,却是可以传播的,道与人心存在着某种联系,人可以通过修养去体会道、感悟道、进而上升到“道”的境界。“道情”也指天地运行的规律、自然四季变化的时间,人生于天地间,就要遵从道德规律而运行。庄子在思考人与人生时,不仅把人看作为社会的个体,而且更注重于个体生命在宇宙存在的意义。此处的“道情”强调生命要顺应自然,顺时而生、应时而去。庄子认为,生死变化不过是气的聚散,面对生死要能“安时而处顺,哀乐而不能入”。人要服从时代的需要,顺从自然的规律。心安理得的人,对生命的欢乐,对死亡的悲哀,不会悬挂心头。生死不再成为人的终极追求,绳结就解开了,古人称之为自然的悬解。
庄子曰:“死生亦大矣”[1] 《庄子·德充符》,即生死都是天地自然的安排。接受生死,不把情绪上的喜悦与悲哀植入其中,顺应自然造化的安排。人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庄子却能转化生死的命题。庄子曰:“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不尽也”[1] 《庄子·养生主》,即“燧人氏的第一盏灯,灯油早被灯芯燃尽,可是灯火传遍九州,灯光夜夜照明,从荒古,照到今”。因此,庄子曰:“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1] 《庄子·大宗师》也就是说,古代的真人,不知道生活有什么可爱,不知道死亡有什么可憎;生从虚无来,不必庆幸;死回虚无去,不必抗争。
庄子如此豁达的生死观。可以看出庄子的“道情”是摆脱了生死的偏执,以通达对生和命的参透。庄子曰:“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1] 《庄子·达生》庄子认为,通晓生命实际情况的人,不会努力追求生命本身以外的东西;通晓命运实情的人,不会努力追求命运中不可改变的无可奈何的事情。同时,人不应该执著、沉溺与放纵于自己的喜、怒、哀、乐、气、意、恶、欲与色等情感,而应该摆脱人世间种种物欲对人的限制。人应该充分发挥人自然而有的生命特质。这与本居宣长的“物哀”论的“好色”是完全不同的。
本居宣长“物哀”论里关于“情”的第三个论述是“真实的人情”。本居宣长认为,“真实的人情就是像女童那样幼稚和愚懦。他认为,坚强而自信不是人情的本质,常常是表面上有意假装出来的。”[2]106对于本居宣长的这个表述,笔者也无法苟同。人的性格各种各样,有的人生性懦弱,有的人威武坚强。而本居宣长却认为人的真实性情只有一种,那就是“幼稚和愚懦”。显然,他的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偏执的,他的表述是以偏概全的说法。如果一个人表现得坚强或者自信,在本居宣长看来,那就是装出来的。这显然是错误的,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充分地表现出其学术观点的感性与偏执。《庄子》的“道情”超越了“生死”,追求的是“人的精神自由”。而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却局限在庄子的“物情”之中,纠结于所谓的“真实的人情”。本居宣长所指的“真实的人情”,也仅仅只是大千世界中人的秉性的一种类型。由此可知,本居宣长的“物哀”论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文学观,也是一种狭隘的文学审美观。
综上所述,本居宣长的“物哀”论里有《庄子》所提倡的人的“真情”;而其“物哀”论从本质上讲是丢掉了《庄子》之情的根基,那就是人的品德与人的理性,以及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之心。庄子主张“人”应该成为摆脱名利诱惑的“神人”,应该成为不被各种情、欲与物所“奴役”与限制的人,而本居宣长的“物哀”论是陷在“好色”之中,丧失了“人”的伦理底线的文学审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