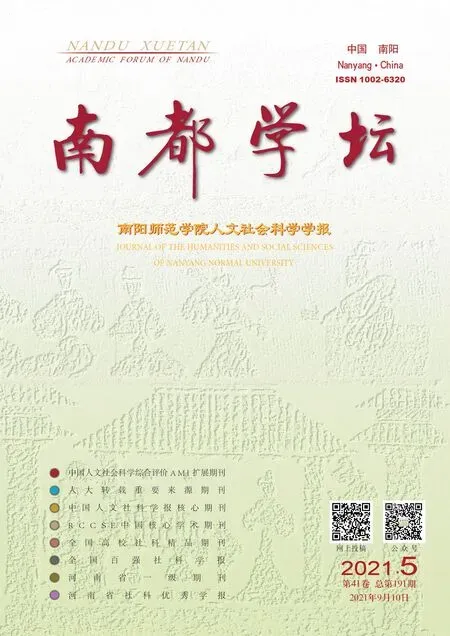汉武帝时瓠子河决及两次堵口问题探析
2021-11-25冯乐辉
冯 乐 辉
(1.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2.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郑州 450121)
黄河孕育了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时也给沿岸人民带来许多灾难。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1]21之一。西汉中后期,黄河中下游多次决口为患,尤以汉武帝时期瓠子决口为甚,其泛滥区域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围绕汉武帝时期瓠子河决及堵口问题,学术界已做过相关的研究(1)郑肇经在《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一书中提及瓠子之决,后来诸多水利史、灾害史的专著中多有所论及,不再赘述。相关论文有李民:《试探汉代黄河的一次大决口及其治理》,载《学术研究辑刊》1980年第2期;罗庆康:《谈西汉黄河的溃决》,载《益阳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史真:《汉代的瓠子大决口及其治理》,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6期;梁向明:《汉代治黄述论》,载《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段伟:《汉武帝财政决策与瓠子河决治理》,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宋祎晨:《浅析西汉黄河瓠子决口的成因及治理》,载《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等。,但仍有值得深入探讨之处。
人地关系存在互动性,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活动影响自然环境,而反过来自然环境的变化也影响到人类社会。对汉武帝时期黄河瓠子决口带来的水患与其治理的相关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汉代应对灾害的模式,或能从新的角度获取对当时人与环境关系的认知。
一、汉武帝时期瓠子堵口始末
据《史记》《汉书》《水经注》等书记载,西汉中后期黄河频繁地在下游相近区域决口导致河道多有改动。史载西汉首次黄河大决口发生在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2]1409。黄河于酸枣县(秦置县,西汉地属东郡,今河南省延津县西南)决口,向东冲毁了金堤,东郡征发了大量劳役来堵塞决口。随后汉武帝时期,黄河决口泛滥多次,而元光三年(前132)春,顿丘(西汉置县,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先发生决口,紧随其后夏季又在瓠子发生大决口,也是在黄河下游相近区域。瓠子,古堤名,研究者多认为其位于今河南省濮阳县内,杜冠章指出瓠子位于今滑县附近[3]。
《史记·河渠书》载“其(文帝金堤堵口)后四十有余年”[2]1409,此处误,《汉书·沟洫志》改作“其后三十六岁,孝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颜师古注曰:“钜野,泽名,旧属兖州界,即今之郓州钜野县。”[4]1679《史记·孔子世家》:“狩大野”,裴骃《集解》引服虔曰:“大野,薮名,鲁田圃之常处,盖今钜野是也。”[2]1942因服虔是东汉人,其论更让人信服。钜野泽也称大野泽,故址在今山东巨野县北,今天已经消失,历史上的钜野泽水域广阔,其东南通泗水、淮水入海。黄河在瓠子决口后,改道注入钜野泽后向外溢出,向东南流入淮泗,黄河与淮河两个水系合在一起入海。《汉书·武帝纪》载:“三年(元光三年,前132年)……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4]163历史上这次黄河决口地在濮阳(秦置县,为东郡治所,西汉沿置,今河南省濮阳县南)瓠子决口,因发生于元光三年,故也被称为“元光河决”,决口后汉武帝派十万人前往堵口,可见其规模不小。瓠子决口后,“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2]1409,汉武帝派汲黯、郑当时率领十万民众堵塞决口,刚堵好又被冲开,徒劳无功。黄河一旦决口,很难彻底堵上,给黄河下游沿岸居民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和潜在的再次决口的风险。《史记·河渠书》载:“自河决瓠子(前132)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2]1412-1413这一拖延,便拖到汉武帝封禅泰山(元封元年,前110年)的次年(元封二年,前109年)才进行堵口,与元光三年(前132)已经时隔23年之久。《史记·平准书》:“先是(元狩二年,前121年)往十余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集解》引徐广曰:“观,县名也。属东郡,光武改曰卫,公国。”[2]1424-1425清代学者梁玉绳认为:“‘观’乃‘灌’之讹,《汉志》是‘灌’字,连下‘梁楚之地’作一句读。徐广以为县名,非。”[5]828在其看来,“观”系“灌”的讹传,元狩二年往前推十余年确与元光河决时间相仿,这是一种可能。另外,观县(西汉置县,地属东郡,今河南省清丰县东南)在当时确实存在,其地离瓠子很近,在其临近黄河处也发生决口是可信的。因黄河的决口是连带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可能瓠子决口波及到东郡黄河沿线的其余堤防。无论怎样,瓠子决口影响到大片的区域,河患给灾区民众带来深重的苦难。《水经注》卷24《瓠子河》:“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暨汉武帝元光三年,河水南泆,漂害民居。”[6]572瓠子决口后,黄泛区因长年农田受淹,沙化、盐碱化导致连年粮食歉收,百姓缺衣少食、生活困苦,以致民怨沸腾。
汉武帝在巡幸时意识到瓠子决口问题的严重性,先派汲仁、郭昌调动数万人服役,后亲临指挥,并令官员负薪填决口,当时薪柴缺少,便砍伐淇园竹林的大量竹子,编成竹楗,再用石、草填充去堵决口,最终堵口成功。据《史记·河渠书》载:“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窴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2]1412-1413汉武帝先派大臣督导治河,后亲临指挥,在瓠子进行了大规模的祭祀仪式,官吏民众一起上阵背薪柴参与堵口,帝亲作《瓠子歌》两首,历数堵口的艰难,并为庆祝堵口成功于原址筑宣房宫,古“房”字与“防”通用,寓意求得堤防稳固。在今人的考古发掘中,宣房宫遗址的黑龙潭是瓠子决口处,“从南侧的断崖处可看出古代土质的夯土层,从遗址采集到的17件陶件中,有蓝灰色的汉瓦片,汉砖头”[7]76,考古发现证实史书记载大体无误。此次堵口后受灾区域终于恢复了安宁。汉武帝时期黄河在瓠子大决口的原因是什么?元光河决之后汉廷竟任由其泛滥长达23年,显得很不正常,是否有原因可寻?汉武帝瓠子前后两次堵口作为大型的集体治水工程,其间的功过得失值得探究。
二、汉武帝时期瓠子决口原因探讨
两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灾害的密集暴发期,当时无论是灾害次数还是危害程度都比较突出。有研究者认为两汉时期灾害群发与太阳黑子活动有关,太阳活动极度衰弱,或称其“两汉宇宙期”[8]322。灾害的自然属性在特定的时期集中暴发。2012年《自然》杂志上有科学家发文对过去两千年世界上甲烷含量的分析,其中着重指出西汉中后期碳排放量已颇惊人[9],说明当时各种灾害的发生与自然、人为因素共同导致的环境变迁有关。西汉灾害类型中以黄河水灾尤为突出,其中汉武帝时期瓠子决口具有一定典型性。
汉武帝时期瓠子决口的原因非常复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学者做过大量探讨,多将原因归结为人类活动的影响造成黄河上游的水土流失和泥沙的淤积,进而导致中下游河患的产生。李民认为瓠子大决口的主要原因是“黄河泥沙的大量淤积”“严重的水土流失”“封建政权对黄河的长期失修以及贵族割据势力对治河的破坏”[10]92。其观点较有代表性,黄河上游的水土流失、河道泥沙淤积的原因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因素,而政府决策层的疏于管理是强调人的影响。罗庆康认为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严重“完全是汉武帝一手造成的”,原因有四:即一是“汉武帝迷信天命,对黄河决溢不予治理”;二是“汉武帝向黄土高原大量移民,变游牧区为农业区”;三是“武帝在关中大力修渠,造成‘岸崩’‘移徙’,大量泥沙带入黄河”;四是“武帝塞河重‘堵’不重‘导’”[11]65-66,其观点强调汉武帝个人因素。谭其骧认为:“对黄下游水患起决定性作用的中游……在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情况的改变,是决定黄河下游安危的关键因素”[12]26,把西汉水患严重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结于黄河中游关中平原的过度开发导致的水土失衡。辛德勇则从地理环境的改变来谈河患发生的原因,指出自然因素亦不容忽视:“河道流经地点的地理环境、叉流宣泄洪水的能力、堤坝的坚固程度,乃至海平面和降雨量的变化等项因素,同样也会起到重要作用”[13]14。他还提到“黄河中游土地……垦殖活动都发生在元光三年之后,不管规模多大,都与元光河决毫无关系”[13]35。元光河决除其所说的几点自然原因之外,还与黄河河道变化带来水的流向变化,能量流固有模式被打破,从而局部水生态系统失衡有关。生态学家孙儒泳在其编写的教材中指出:“生物和非生物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物质不断地循环、能量不停地流动的生态系统。”[14]190依据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流的流动是生态学研究的重点,“水生生态系统(湖泊、河流、溪流、泉等)常被生态学家作为研究生态系统能流的对象”[14]219。黄河流域能量流的流动应作为黄河水量变化的重要依据。《汉书·武帝纪》载“三年(元光三年,前132)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渤)海。夏五月……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4]163。顿丘紧邻濮阳县,黄河于元光三年(前132)当年春季在顿丘东南改道入海,夏季复在濮阳瓠子决堤,泛滥成灾,危害百姓。可见此前黄河在瓠子附近顿丘的改道导致黄河中下游水生生态系统失衡,造成该年夏季雨水季节黄河局部水量大增,是瓠子决口的主要诱因。王子今论曰:“黄河在西汉时期决溢频繁,而东汉时河患则明显减轻……而气候转而干燥寒冷对于洪水流量大小的直接影响,更是不应忽视的。”[15]19长时段看,气候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两汉水患程度的变化,而短时段不同季节内气候的差异性也是水患发生的重要原因。
由于当时北方以旱作农业为主,大量河道周围的荒地被开垦,垦殖活动对黄河河床的改造造成的水土流失,是造成瓠子决口的原因之一,但不应是主要原因。而近年来河南内黄三杨庄遗址的发现,能为瓠子堵口提供一定的借鉴。三杨庄聚落与瓠子的古迹发现地相距很近,都在汉代黄河故道周围,且都在西汉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黄河决口。结合对三杨庄的两次考古发掘,三杨庄作为汉代的农业聚落,之所以聚集了大量人口且农业经济发达,可能与黄河河岸附近土质肥沃有关。孙家洲分析三杨庄汉代聚落是“在黄河滩地新垦殖区出现的新起庐舍。其庭院的‘无邻独居’现象,反映的是垦殖的自然进程”[16]5-6。新莽始建国三年(11),黄河在魏郡(郡治在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决口后改道利津入海,洪水肆虐,新莽政权因统治开始动摇导致应对河患不力,造成三杨庄聚落最终被淹没在黄河的泥沙下。当然,三杨庄的例子晚于瓠子堵口,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民在黄河河道周围耕种能对黄河的水文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汉武帝时期对西北的开发与治理、移民屯边、关中修渠等造成财费紧张与瓠子堵口的拖延也有一定的关联,朝廷失职造成的堤防失修与疏于管理也是实际情况。但历史时期人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到底达到何种程度尚待探讨,自然界的变化还是有其普遍的自然规律,自然环境的一些变化导致灾害呈现出一定的不可逆性。蓝勇认为,“干涉限度差异”理论决定了“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人类改变自然环境行为中的影响客观上差异明显,所以我们应该差别认知,具体分析”[17]1。秦汉时期,限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的开发与资源的利用停留在较低水平。所以客观来看,当时包括瓠子决口在内的一些灾害的主因,更多是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而非人的活动。
三、汉武帝瓠子河决治理经验探讨
汉武帝时期,瓠子决口后经历了两次大治理,其成败得失也是众多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可试从以下两方面来对瓠子河决治理经验进行总结。
(一)汉武帝瓠子堵口拖延二十余年的原因及认识
围绕汉武帝瓠子堵口拖延二十余年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少争论,主流观点是瓠子决口未能及时治理与汉武帝对田蚡的偏听偏信、迷信天命有关。但也有学者认为区域地位不够重要是导致瓠子决口后受灾区域被忽视的原因[18],然而此说并不足信,细查史料可证梁楚之地非常重要。梁国主要位于今河南省东部和山东省西部,是瓠子决口的主要区域,汉文帝嫡子刘武被改封为梁王,都于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而且刘武一直深得窦太后的喜欢,在七国之乱中守城成功,拱卫了国都长安,更凸显出梁国地位的重要。
瓠子堵口拖延二十余年未能及时治理的主要原因正如史书记载,来自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史记·河渠书》载“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2]1409。田蚡虽是汉武帝娘舅,但此时已不受汉武帝重视,且田蚡在瓠子决口不久就去世了。田蚡的言论主要出于私利考虑,但汉武帝是受其上书影响的,这反映出古代社会天命观、天人感应思潮对社会的深远影响。在古代社会,由于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人们很早就关注天人关系,至汉代达到了顶峰。汉武帝认为瓠子第一次堵口未成功是上天的故意安排,故不管不顾以顺应天意。当然,除此之外,瓠子决口拖延二十余年与当时财政、经济、社会等方面原因也有一定关系。段伟把瓠子堵口拖延未治的根本原因和朝廷的财政政策失误相联系[19]。此说虽颇多新意,但如果非要说因为与匈奴作战或其他财费紧张而导致瓠子堵口的失策,那元光河决后,汉武帝就不会调十万之众去堵口了。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调动民众堵河并不难操作,财费紧张不是朝廷疏于治河的根本原因,而瓠子再次决口后放弃再堵的主因应是受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这与古代社会围绕治河的“堵”与“疏”两种手段之争有关。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开始,中国古代社会中就开始围绕堵塞与疏导两种治水的策略进行利弊分析,客观地讲,朝廷的决策与执政者不同时期对治水的认识不同有关。在第一次瓠子堵口失败后,汉朝廷的长期放任不管确实是严重的失职行为,对灾区民众造成了长期的苦难。因为当时朝廷苦于找不到治河的其他方法,简单地堵口造成修堤后再决口、决口后再修堤的恶性循环中,只能归结于天命。后来朝廷大规模发动民众进行第二次瓠子堵口正是这种社会矛盾持续激化的产物。但其过程中,拖延二十多年的时间,不是简单的财政问题导致的,或主要与社会风尚的扭转有关。《汉书·武帝纪》载:“赦所过徒,赐孤独高年米,人四石。还,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4]193,说明汉武帝在瓠子堵口之后全国范围内积极地赦免囚徒、安抚百姓、作祭祀场所祈求通天意、达廉洁,把河患看作是上天对其执政的惩罚,祈求上天的宽恕。
(二)汉武帝瓠子两次堵口从失败到成功的原因
汉武帝瓠子两次堵口从失败到成功不是偶然的,既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
首先,治河者在治理河患时合理利用自然环境条件很重要。第一次瓠子堵口记载发生在五月决口之后,虽未明言气候状况,但明显正当夏汛期,不利于堵口。而第二次大堵口时,及时抓住干旱期的有利时机,史书明确记载“是岁(元封二年,前109年)旱”[2]1399,“(元封二年)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4]193,“旱,干封少雨”[2]193。关于“干封”一词之意,另见于《史记·孝武本纪》:“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干封三年。’上乃下诏曰:‘天旱,意干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裴骃《集解》:“苏林曰:‘天旱欲使封土干燥。’如淳曰:‘但祭不立尸为干封。’”颜师古曰:“三岁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2]479这样看来,“干”意“干燥”,而“封”意“祭祀封坛”,“干封”即泛指天旱。初夏干旱少雨会使黄河水流变小,甚至部分河段断流,易于封堵,河道也便于工人施工。汉武帝在《瓠子歌》中说:“瓠子决兮将奈何?晧晧旰旰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2]1413,他生动描绘出一幅瓠子河决时的场景:浩浩荡荡全是黄河之水,地方不得安宁,河工不得休息将吾山夷平,钜野泽水溢出,水中的鱼多到接近冬季还在增长。对于“吾山平”的解读,《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东郡东阿有鱼山,或者是乎?”这说明“吾山”应是指距决口较近处一座特定的山;如淳曰:“恐水渐山使平也”,韦昭曰:“凿山以填河也”,《沟洫志》颜师古注曰:“韦说是也”。平山填河虽有夸大之嫌,但确因治水工程浩大需要而挖掘大量的土石,这也是因“吾山”之便。而“鱼沸郁兮柏冬日”的解读,《集解》引徐广曰:“柏犹迫也,冬日行天边,若与水相连矣。”骃按:《汉书音义》曰“钜野满溢,则众鱼沸郁而滋长也。迫冬日乃止。”《沟洫志》作“弗郁”,颜师古注曰:“孟说非也。弗郁,忧不乐也。水长涌溢,濊(秽)浊不清,故鱼不乐,又迫于冬日,将甚困也。”[4]1682-1683清代学者王念孙对此考据甚详,他否认颜说,认为“河水本浊,不待泛滥而始浊,鱼本生于河中,亦不以水浊而不乐也,余谓弗郁读沸渭(《河渠书》作‘沸郁’),沸渭犹汾沄,鱼众多之貌也”[20]275。黄河的急剧涨水,导致水温上升,河中之鱼由于不适应水温便聚集而出,直到将近入冬。洪灾带来黄河水文环境的一些变化,是西汉时期治河者留意观察到的,属于为治水所作的调查准备工作,值得充分肯定。在此次大规模的堵口中,由于木材短缺,所以动用了邻近的卫地淇园中的大量竹子。《史记·河渠书》中“淇园”,《集解》注引晋灼曰:“卫之苑也。多竹筱。”[2]1413《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绿竹青青……绿竹如箦。”[21]99-100淇奥,位于今河南省淇县北部淇河弯曲之处,此地历史上以盛产竹子闻名。在我国,由于竹的文化内涵和可观的经济效益,竹子的栽培一直很受重视。王子今认为:“秦汉民间礼俗、学人论著以及法律文书中,都有反映山林保护意识的内容。”[22]65汉武帝为治理河患不得已砍伐竹林违背保护山林的初衷,他在《瓠子歌》中对卫人也是心生歉意。但客观上说,由于大量竹子做楗,为堤防的成功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北宋以后,由于气候变冷的原因,北方竹子产量明显下降,淇园难复昔日之盛。今人发现“黑龙潭,是当时瓤子决口处。当地群众在打井至12米深处发现有竹竿、木桩和柴草,是当年堵塞瓠子口的材料”(2)参见濮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王桂荣等于2000年编写的《濮阳名胜古迹》,第195页。,直至今天还保留下了瓠子堵口的实物遗存。这些都说明瓠子堵口的成功是充分利用了附近淇园盛产竹子的环境条件。
其次,有效发挥人的因素应是此次河患治理的主要原因。李民认为“就以这次的治河而论,其决定力量也是来自人民群众”[10]94。瓠子堵口中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是堵口成功的基础,同时如此之众的人员如何组织和调度是一大难题,依靠集权制适时调整对策是一个积极的策略。西汉时期,编户民编入名籍,受政府保护的同时也要承担赋税、徭役等各种义务。前文说过,汉文帝时期黄河第一次大决口后“东郡大兴卒塞之”,汉武帝时期两次瓠子堵口在东郡当地都调动了大量“卒”。这里的“卒”,便是指当时服临时性徭役的编户民,很多研究者把此简单地理解为军卒,是不准确的。《说文解字》:“隶人给事者衣为卒。卒,衣有题识者。”[23]173“卒”指穿有特殊标志的衣服侍奉旁人的奴隶,引申为从事劳役的人。日本学者藤田胜久指出:“成帝时期以前,由中央派遣的类似军事组织的机动力量,基本上用于黄河治水的工程。”[24]263由于治黄采用的是类似军事行动的方式,故将纪律性与机动性相结合,这就需要对工程的组织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汉武帝第一次瓠子堵口时,任用的汲黯、郑当时都是当时有名的能臣。据《史记·汲郑列传》载,汲黯是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人、郑当时是陈(今河南省淮阳县)人,都是本地人,熟悉灾情,且汲黯以敢于直谏闻名,郑当时以推荐人才闻名,司马迁大赞“汲郑之贤”[2]3113,班固也随着直呼“汲黯之正直,郑当时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4]2326然而其二人奉命指挥调动十万人瓠子堵口却还是很快溃堤。汉武帝第二次瓠子大堵口所任用的汲仁、郭昌虽有才能,但明显不及前二人。汲仁是汲黯之弟,曾位列九卿,也是本地人,熟悉当地灾情;郭昌是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人,武将出身,此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离不开汉武帝亲临指挥的作用。当然,汉武帝瓠子堵口有功也有过,他在《瓠子歌》中直言“不封禅兮安知外!”[4]1682,其不知灾情很难讲得通,从第一次堵口他指派两位名臣、调发十万人堵口来看,汉武帝对瓠子堵口非常重视,其后二十余年对灾区疏于管理是不争的事实,是明显的过失。没有众多普通劳动人民的广泛参与,治水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要对参与两次堵口工程的服役百姓致敬,正是他们的血汗付出,才换来堵口的胜利完成。第二次瓠子堵口时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劳动人民发明的埽技术。对于《史记》中提到的“楗”,裴骃《集解》引如淳曰:“树竹塞水决之口,稍稍布插接树之,水稍弱,补令密,谓之楗。以草塞其里,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为之。”司马贞《索隐》:“楗者,树于水中,稍下竹及土石也。”[2]1413这说明楗是以竹、石为主要结构的堵口技术。李民认为瓠子堵口中“以竹竿为骨干的楗,发展到后来则称之为‘埽’。《河工器具图说》卷三《大埽》条下曰:‘埽即古之茨防,高自一尺至四尺曰由,自五尺至一丈曰埽,《史记·河渠书》下淇园之竹以为楗是也。’这里,实际上指出了楗就是‘埽’的前身。”[10]94周魁一也持这一观点,“竹楗和石菑是埽工的起源……用竹条纵横编织成的竹络中间填块石的构件,与埽之结构相类似”[25]331。闻人军注解《考工记》时提到“车辐两头出榫,插入毂中的称为菑”[26]19。汉武帝在瓠子第二次堵口以竹、石为主料堵口的方法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平堵法”。此种技术的起源与当地缺少木草有关,发挥了当时群众的集体智慧,是水利技术工人在工程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最后,瓠子堵口成功最为关键的应是集权制的统一调度。中央集权制的形成与不断发展是在人改造环境的条件下形成的,如黄仁宇所说,黄河“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1]21。在大型水利工程的执行过程中,朝廷的政令在地方得到具体贯彻,中央的权威得以加强。反过来,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进一步推动环境治理的行动。汉武帝时集权制已经较为系统化、体系化。汉武帝两次瓠子堵口是从其时年25岁到时年48岁,其权力更为集中,执政更为成熟,妥善处理了匈奴外患、财政紧张等棘手问题。以汉武帝为首的朝廷最终协调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反复听取了治水专家的经验总结,最终在技术完善、运作有序的前提下堵口成功。第二次大堵口调动的人员为数万人,人员数量上或不如第一次,但效果却超过第一次,这与汉武帝时期集权制逐渐地完善有关。在权力的集中制衡下,中央的政令能及时地贯彻到地方的事务中,发挥其实效性。客观来看,中央集权制下组织有方、调度合理,是瓠子堵口最终成功的重要支撑条件。
汉武帝瓠子堵口后,黄河水患减少,“自是之后,用事者皆言水利……然其著者在宣房”[2]1414,唤起了朝野上下对水利工程的重视。但问题是,遇到黄河决口后堵口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理黄河水患。瓠子堵口后,黄河水患短期内虽得到一定的遏制,但西汉末至东汉初仍很突出,汉哀帝时治水专家贾让提出有名的“治河三策”,从理论思想上为治黄做出指导,其中有论“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资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4]1696,把在原有河道修固堤防视为治河的“下策”。而至东汉明帝时,王景、王吴主持采用“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27]116,将固堤法与堰流法结合,黄河与汴水分流,黄河下游两岸居民生活才趋于稳定,至唐末黄河较长时段内未发生较大规模的水患,有“八百年安流”之说。
四、结语
总体来看,汉武帝时瓠子决口后对黄河的两次堵口体现出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有助于理解黄河灾害治理的历史模式。当时河决的原因包含自然与人为因素,主要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即物质循环中能量流的失衡造成的。瓠子第二次堵口虽然不如汉武帝所自夸的那般成功,而且当前学界多强调其浪费了大量民力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患,但客观来看不能以今人眼光苛求古人,两次堵口历尽艰辛最终成功体现了朝廷应对危机时策略的提升,中央集权制的有效调度在治理水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解决黄泛区民众的生计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