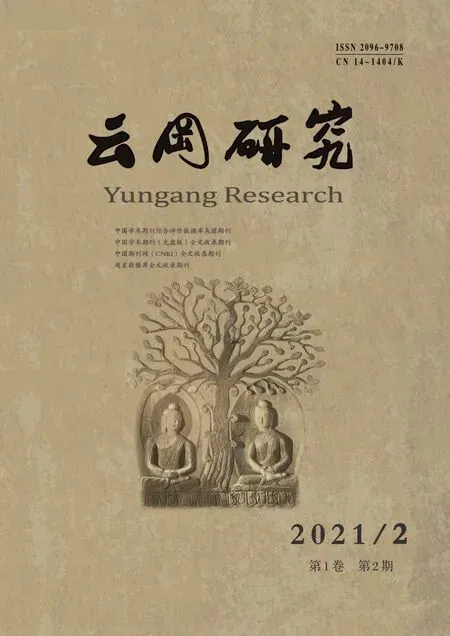拓跋祭天方坛上的木杆
2021-11-25罗新
罗 新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1)
平城时期北魏国家的常规祭祀,以西郊祭天最为崇重。祭天大典的细节仪程,见于南北史料者,只有《魏书》记道武帝天赐二年(405年)祭天仪式,以及《南齐书》记齐使所见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的“蹋坛”、“绕天”仪式。两者一在北魏国家制度草创之初,一在迁都改制尽弃旧俗前夕。两者之不同,既可能反映空间差异,即记录者因身处南北对大典环节各有不同了解,又可能反映时间差异,即90年间祭礼细节随人事代谢与形势推移或多或少地发生变迁。西郊祭天礼制的延续与改变,对于北魏王朝的历史意义,前贤论之详矣。[1](P165-197)本文关注此祭天大典中南北史料都提到的一个因素,即祭坛上所树的木杆,探讨其属性、功能与来历,以明内亚诸人群文化传统之相关与连续。
一、《魏书·礼志》所记西郊祭天之仪
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以前,北魏最重要的国家祭祀是每年四月的西郊祭天。不过,这么重要的祭祀事件,见于《魏书》帝纪者只有5次:一,神元帝力微三十九年(258年)迁都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2](卷1《序纪》,P3)二,道武帝登国六年(391 年)“夏四月,祠天”。[2](卷2《太祖纪》,P26)三,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四月“帝祠天于西郊,麾帜有加焉”。[2](卷2《太祖纪》,P36)四,道武帝天赐二年(405年)“夏四月,车驾有事于西郊,车旗尽黑”。[2](卷2《太祖纪》,P47)五,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四月“甲子,帝初以法服御辇,祀于西郊”。[2](卷7下《高祖纪下》,P191)太和十年的四月甲子是四月四日(486年5月22日)。仅孝文帝太和十年的四月祭天标出了具体日期,前四条都只说是四月。不过,正如下面还要举证说明的,四月祭天的日子并非任意选择,而是固定不变的,都在四月四日。
太和十年的祭天大典,还见于《魏书·高允传》:“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诏以御马车迎允就郊所板殿观瞩,马忽惊奔,車覆,伤眉三处。”[2](卷48,P1199)板殿很可能是指大型帐篷,下面还要提到。另外,孝文帝时西郊大典之地还有乐阳殿。《魏书·阉官·抱嶷传》记抱嶷为泾州刺史(在太和十五年至十七年之间),“将之州,高祖饯于西郊乐阳殿,以御白羽扇赐之”。[2](卷94,P2193)另外,《魏书·尉元传》记他正坐镇新征服的徐兖之地时,于献文帝皇兴四年(470年)受诏,专程回平城参加祭天大典:“诏徵元还京,赴西郊,寻还所镇。”[2](卷50,P1227)
对祭天仪程较为细致的记录,见于《魏书·礼志》。为便于分析,谨迻录其文如下:
(道武帝)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东为二陛,无等。周垣四门,门各依其方色为名。牲用白犊、黄驹、白羊各一。
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内朝臣皆位于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青门内,近北。并西面。廪犧令掌牲,陈于坛前。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
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
自是之后,岁一祭。[2](卷108之一,P2988)
西郊祭天的中心场所是一个方坛,坛上树立七根木杆(木主)。方坛只在东边设置了登坛的两个台阶,台阶“无等”,就是只有一级,不是多级阶梯,说明方坛不高。四堵墙把方坛及坛前空地围起来,形成一个封闭式庭院。四墙各开一门,“各以其方色为名”,东门称为青门,北门称为黑门,那么南门和西门应该分别叫赤门和白门。祭祀用的牺牲是一头白牛犊、一匹黄马驹和一只白羊。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称帝建都时,“定行次,正服色,……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2](卷108之一,P2986)牛羊白色,符合“牺牲用白”,但为什么马驹用黄色呢?这个还难以理解。另外,虽然史书没有明言,但这些马牛羊是否有性别要求?从本文随后要举证的契丹祭祀牺牲都用雄性来看,拓跋时代很可能也是要求使用雄性动物。
到了祭天之日(四月四日),皇帝乘大驾前往平城西郊的祭天场所。按魏初制度,皇帝舆车分为三驾:大驾、法驾与小驾。三驾的区别不在车舆本身。《南齐书·魏虏传》说北魏有大、小辇,名分大小,但都是四轮大车,车上有五层楼,以人力牵引,牵引者多达二三百人,为防车楼倾倒,四面都用绳索牵曳。①《南齐书》卷57《魏虏传》(修订本),中华书局,2017年,第1092页。这里的大小辇,也许就是《魏书》卷108之四《礼志四》所说的郊庙所乘的大楼辇和小楼辇,不过大楼辇以20头牛牵引,小楼辇以12头牛牵引,似乎并非使用人力(第3064页)。也许《南齐书》所说的二三百人牵引仅用以四面牵曳以防车楼倾倒。三驾的区别在仪仗规模所显示出的等级。大驾仪仗卤簿最为隆重:“设五辂,建太常,属车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隶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仆御从;轻车介士,千乘万骑,鱼丽雁行。”[2](卷108之四,P3065)就在天赐二年这次祭天之前,北魏的大驾制度略有改动,鱼丽雁行改为方阵卤簿,改变了81辆属车的排列方式。同时,也改变了车辆之外的步兵和骑兵的排列方式:“列步骑,内外为四重。”步兵和骑兵的组合形成四层护卫,犹如四层可移动的城垣,拱卫着最中心的皇帝。四层城垣当然是内重外轻,自内而外分别是具装甲骑(重装骑兵)、旗幢骑兵、长矟步兵和刀盾步兵。官贵随从者总称“导从”,在前为导,在后为从。导从贵人的车乘按爵位等级分列在这四层护卫之内。
爵分四等,是天赐元年官爵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据《魏书·官氏志》,改革之后王爵10人,公爵22人,侯爵79人,子爵103人,合计214人。[2](卷113,P3233)天赐二年四月祭天大典时,这214人的车乘就分列在四层护卫之间:最高等级的诸王最靠近皇帝,在重装骑兵队列之内;公爵在重装骑兵之外,旗帜飘扬的幢骑之内;侯爵在幢骑之外,银光闪烁的长矟步兵之内;最低等级的子爵车乘在最外层,他们外侧的护卫队列是刀盾步兵。按照天赐元年的新制度,四等爵同时涵盖了官品九品中的上四等,无爵的朝官共有五品。先爵后官,反映了胡鸿论证过的北魏早期的“爵本位”特征。②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第七章《北朝华夏化进程之一幕:北魏道武帝、明元帝时期的“爵本位”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2-274页。《魏书·礼志》称“五品朝臣使列乘舆前两厢,官卑者先引”,即指四等爵之外的所有朝官。行进方向的刀盾步兵队列之外,五至九品的朝臣乘车导行。他们腾出中间大道,分在道路两侧前行,排列次序是官位低者在前(即“官卑者先引”),同样是等级越高越靠近皇帝。所有车辆的車旒麾盖、旗帜和官员服装,“一皆纯黑”,故本纪云“车旗尽黑”。
大驾仅用于军戎与大祀,而平城时期的常规祭祀,皇帝亲行的并不多,其中称得上大祀的可能只有西郊祭天。所以平城百姓见识大驾卤簿的机会并不多,当然真到了动用大驾之时,普通百姓也不可能被允许在路边看热闹,即使看也是隔着千军万马。从平城皇宫到西郊祭坛,即便洒水湿路,千乘万骑之上,也必定黄尘飞扬。黄尘掩映着黑云般的步骑车乘,即所谓大驾卤簿。天赐二年四月四日(405年5月18日),道武帝的祭天大军,就是这样出平城西门(可能在天亮前),迤逦西行(可想而知行进非常之慢),抵达我们至今仍不知其所在的祭天方坛场所。由前引史料知孝文帝时西郊有板殿与乐阳殿,可能魏初仅有帐篷(板殿),以供祭祀准备及帝后休息。
张帆用“圈层结构”描述蒙古政治体的政治与社会结构。③张帆:《元代蒙古人的圈层式结构》,待刊稿。张帆已在多处座谈和讲座中使用这个概念,可惜相关文字迄今还没有正式发表。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概念,可能绝大多数内亚游牧政权都适合用这个概念加以描述和分析。圈层结构的关键是内外有别,所谓内外不是绝对的二元结构,而是相对的、多层的和流动的复合结构,内中有内外,外中亦有内外。拓跋集团的成长史,就是一部构造圈层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庞大的历史。立体的内外圈层更像是一个球体,以拓跋皇室为球心,以“帝之十族”为内核,①“帝之十族”又可作“帝之十姓”,详见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第35-47页。构成拓跋集团的“最内圈”,但在这个最内圈里,皇室是内,拓跋之外的九族是外。当这个核心球体越来越大,如滚雪球一般,加入越早的就越属于靠内的圈层。早期附从和后来经结盟或征服而加入的,依其加入时间的早晚或其重要性的重轻,次序井然地就位于各相应圈层。决定性的因素是加入的时间,其他因素如语言亲疏、宗教信仰、族群认同和文化面貌等等,都没有那么重要。必须说明的是,一方面,内圈和外圈各自都有极为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分层,另一方面,不仅外圈向外无限开放(因此游牧部落可以发展为游牧帝国和征服王朝),而且内圈也绝非一个封闭结构,其边界也是相对开放的(因此游牧帝国和征服王朝才可能向定居社会的官僚制国家过渡)。
拓跋历史也时时处处表现出自己的内外圈层,西郊祭天大典的制度安排就是其内外圈层结构的形式化呈现。
天赐二年四月四日,跟着道武帝参与祭天大典的,是所谓“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百官指北魏的官贵,“宾国诸部大人”的范围则不太明确,大致上是那些表示服从却相当独立的部族领袖。前引《魏书·序纪》记神元帝力微三十九年(258年),迁都于定襄之盛乐,说明拓跋部在摆脱纥豆陵部的控制后,迅速发展成阴山地带的最大势力,因而四月祭天大典时,“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徵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助祭”是一个华夏概念,但借来描述大型游牧政治体的外圈,似乎也是有一定效力的。游牧政治体的核心,是以部族之名而急剧扩张的政治集团(如拓跋部),其边缘外层,则是保持了一定独立性的部族(如“诸部君长”),他们承认核心集团的统治地位,但在该政治体内的权利与义务都是有限度的,很大程度上甚至仅仅是象征性的。不过,当白部连西郊祭天这样具有强烈象征性的活动都不肯参与时,就可能面对极为严重的后果。天赐二年跟随道武帝到平城西郊祭天的“宾国诸部大人”,和一个半世纪前当神元帝力微在盛乐祭天时前来“助祭”的诸部大人一样,都属于这种游牧政权圈层结构中的最外层。
《魏书·礼志》接下来描述祭典本身的典礼程序。道武帝从东边的青门进,然后左转,来到祭坛以东靠南墙的位置,向西面对祭坛而立(《魏书》“近南坛西”后应脱“面”字)。道武帝与所谓内朝官从青门入,六宫女性则不能走青门。《魏书》说“皇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就是绕到北边,从黑门进入。她们进黑门后并不停留在方坛北侧,而是左转来到皇帝所在的方坛东侧,只是皇帝等男性在南,六宫女性在北。所有人都向西站立。
只有内朝臣可以跟随皇帝进入青门,外朝臣和“宾国诸部大人”都只能留在青门之外。在青门之外的,与进入青门的,隔着一睹墙垣,墙垣的高度大概足以遮挡视线。也就是说,留在青门之外的实际上看不到祭典的具体内容。魏初朝臣如何分内外,学者多有讨论。②讨论北魏平城时期内朝官的论著很多,这里特举有代表性的两位学者,一个是川本芳昭,参见川本芳昭:《内朝制度》(1977年),收入《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书院,1998年,第189-227页;《北魏内朝再論——比較史の観点から見た》,《東洋史研究》第70卷第2号,2011年,第1-30页。另一位是佐藤賢,参见佐藤賢:《北魏前期の“内朝”、“外朝”と胡漢問題》,《集刊東洋学》第88号,2002年,第21-41页;《北魏内某官制度の考察》,《東洋学报》第86卷第1号,2004年,第37-64页。近20多年来,以文成帝南巡碑碑阴题名为依据的研究,似乎大大推进并深化了这一论题。③川本芳昭:《北魏文成帝南巡碑につい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28号,2000年。松下憲一:《北魏石刻史料に見える内朝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の分析を中心に》,见《北魏胡族体制論》,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57-86页。窪添慶文:《文成帝时期的胡族与内朝官》,载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80-199页。不过不能忘记《魏书》这里把朝臣分为内外可能只是比附汉制,未必忠实反映魏初的制度实际。黄桢已经指出这一点,并放弃内外二分法,把文成帝南巡碑碑阴题名所见的北魏职官区分为侍臣、内职与外臣三个类别。[3]这一取径对于思考北魏前期制度非常重要。当然,北魏平城时期长达百年,文化与制度的变革与时俱进,文成帝时期的制度并不足以涵盖道武帝时期,只是两者间总有某种较强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这里不讨论内外朝官问题,但很愿意提出一个设想,那就是把前面说到的拓跋内外圈层结构,与道武帝祭天大典上立于青门内外的差异联系起来,青门墙垣是不是一道物质化的圈层界限呢?
祭典开始前,负责牺牲动物的掌牺令把祭祀要用的动物(一头白牛犊、一匹黄马驹和一只白羊)牵到方坛前(应该也是在东侧)拴好。这时女巫登场,她手执巫鼓,站在方坛东侧的台阶前,面向方坛。她南侧排列着7个少年,人人捧着盛酒器(很可能是北人习用的皮囊),也都向着方坛而立。这7个少年是从所谓“帝之十族”同龄人中选出来的,7这个数字和举毡立汗时的7人数字相同,一定深植于拓跋乃至更大范围的内亚传统。既然祭天执酒的7个少年必须来自“帝之十族”,那么可想而知,传统举毡立汗的7人,也应来自这个范围,因为他们才是拓跋政治体的内核。
女巫登坛,标志祭典开始。她走台阶上方坛,在坛上摇动手中的鼓,必定还要以吟唱某种固定的歌词(这个环节虽不见于《魏书》,但根据一般的萨满仪式知识,以及后面要引据的清代史料,可以肯定是必不可少的)。然后是皇帝下拜,皇后跟着“肃拜”。这里肃拜是比附华夏古典的所谓女性正拜,也许意在强调男女下拜的动作是有不同的。皇帝与皇后拜后,“内外百官尽拜”,内外可能指青门墙垣之内外。墙内墙外的行礼下拜,大概都是听典礼官员口唱指挥。这样的下拜会有几个回合(我猜测一共是七轮),都由女巫摇鼓吟唱和众人依次下拜为主要内容。这几个(7个)回合结束,进入杀牲献祭阶段。《魏书》没有说是由女巫亲自动手还是由掌牲令动手宰杀拴在坛前的三个动物,也没有说之后如何处理动物的牲体。大概在处理牲体之后,排列坛前、手捧酒器的七个少年向西朝着方坛,把手中酒器所盛的酒洒向“天神主”。这里的“天神主”应该就是前面说的坛上所立的七根“木主”。洒酒之后,“复拜,如此者七”,即重复杀牲之前的女巫摇鼓吟唱和众人依次下拜,重复七轮,才算典礼结束,于是“礼毕而返”。
天赐二年这次祭天大典为北魏国家大祭确立了规则与仪程,《魏书·礼志》说“自是之后,岁一祭”,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后的祭天都遵循完全一样的制度,祭典仪程的许多细节都会发生变动。
二、《南齐书》所记北魏西郊祭天礼制
萧齐永明十年(太和十六年,492年),齐武帝派人出使北魏,正使是萧琛,副使是范云。他们回建康后报告北行见闻,其中提到受北魏孝文帝邀请观礼西郊祭天,这一部分进入后来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魏虏传》:
十年,上遣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北使。宏西郊,即前祠天坛处也。宏与伪公卿从二十余骑戎服绕坛,宏一周,公卿七匝,谓之蹋坛。明日,复戎服登坛祠天,宏又绕三匝,公卿七匝,谓之绕天。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为繖,一云百子帐也。于此下宴息。次祠庙及布政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观视。[4](卷57,P1097-1098)
萧琛、范云这次北使,是对前一年(永明九年,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北魏李彪、蒋少游来使的回报。萧琛出使亦见于《梁书》萧琛的本传:“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衔命至桑乾。”[5](卷26,P436)传称萧琛“再衔命至桑乾”,可是他前一次北使不见记载,我怀疑在永明九年的九月。《魏书·高祖纪》记太和十五年九月辛巳(491年11月9日)“萧赜遣使朝贡”。[2](卷7下《高祖纪下》,P200)而这次萧齐来使,应该是对同年四月北魏派李彪和公孙阿六头使齐的回报。《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五年四月甲戌(491年5月6日)“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尚书郞公孙阿六头使于萧赜”,因而有九月萧齐之报使。这应该是萧琛第一次前往平城。
永明十年出使之前,萧琛和范云都在竟陵王萧子良司徒府任参军(略有疑问的是,据《梁书》的《范云传》和《萧琛传》,二人担任的都是记室参军)。《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六年记“萧赜遣使朝贡”在三月辛巳(492年5月7日),这个日期可能是萧、范二人抵达平城的时间,也可能是他们正式见到孝文帝的时间。而在八天前(三月癸酉,4月29日)孝文帝刚刚下诏“省西郊郊天杂事”,[2](卷7下《高祖纪下》,P201)即减省了祭天的某些仪程,不过西郊祭天并没有废除。萧、范二人三月下旬到平城,恰好在四月四日(5月16日)的祭天大典之前。据《魏书·高祖纪》,三月到平城的还有高丽、邓至使臣。自北魏的制度传统而言,包括萧齐在内的这些外国来使都是“宾附之国”的代表,理应参与祭典。前引《南齐书·魏虏传》说北魏孝文帝的重大典礼“皆引朝廷使人观视”,似乎萧齐使人受到了特别礼遇,其实不过是内亚古老的“助祭”传统,自神元帝力微以来即是如此。
萧琛、范云虽然是隔着青门墙垣参与西郊祭天,见不到祭典的核心内容,但他们的报告仍很有价值,多为《魏书》所不载。首先,他们看到祭典前一天就有皇帝亲自参与的“蹋坛”活动。“宏与伪公卿从二十余骑戎服绕坛,宏一周,公卿七匝,谓之蹋坛。”孝文帝与公卿众人绕坛骑行,可能发生在方坛四垣之外,因为垣内空间有限,众骑施展不开,且制度上大概也不允许任何人骑马进入青门、黑门等四门。正是因为蹋坛在墙外,萧琛等才能见到。然而他们对墙内的典礼几乎一无所知,可能无从了解。也因此,他们的报告一言不及大祭的具体仪程,只说“明日,复戎服登坛祠天”。蹋坛之时,孝文帝自己绕坛骑行一圈,其他人绕骑七圈。大祭之日,“宏又绕三匝,公卿七匝,谓之绕天”。绕天与蹋坛的区别是孝文帝自己多绕两圈。问题在于,绕天之仪,是在前引《魏书·礼志》所述的祭天典礼之后呢,还是之前?也就是说,是在孝文帝一行进入青门之前呢,还是从青门退出来之后?从《南齐书》前引文叙事次序看,绕天似在结束坛前典礼、从青门退出来之后。萧琛等人见证了祭天大典的开始和结束,恰恰可以补充《魏书·礼志》。他们的报告中还有很特别的一点,就是注意到孝文帝等以军戎盛装(戎服)参与祭天。戎服祭天,应该是拓跋的古老传统,但《魏书》并未提到。
受邀“助祭”的萧琛、范云在抵达西郊祭天场所后,还体验了专供参与祭天人员休息的一种特殊建筑:“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为繖,一云百子帐也。于此下宴息。”周一良先生指出,百子帐即毡帐,[6](P266)中古史书又称为毡屋、毡庐、穹庐,方便移动,为内亚游牧人之传统居室。《魏书》里的“板殿”,大概就是指这种百子帐。《魏书》两次提及板殿,一在西郊祭天处,见前引《魏书·高允传》;一在平城西宫,见《魏书·太宗纪》,永兴四年八月庚戌(412年10月3日)明元帝完成秋猎北巡,归还平城,两天后“幸西宮,临板殿,大飨群臣将吏,以田猎所获赐之,命民大酺三日”。[2](卷3,P60)很显然,板殿不是殿名,而是一种建筑类型。板殿之以板为名,即因“纽木枝枨”,强调其有异于版筑土墙的建筑特征。板殿之得名殿,因皇帝所用,即便是普通毡房,也可鸡犬升天称宫称殿。
前引《南齐书·魏虏传》云“宏西郊,即前祠天坛处也”,谓孝文帝让萧琛、范云参与祭天之地,就是同书同传先前所提到的“祠天坛”所在之地。有关“祠天坛”的文字,见于《魏虏传》开篇总述拓跋种姓源流与文化特征的部分:
(平)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4](卷57,P1091)
这段文字明确说祭天日期固定在四月四日,为今存史料所仅见者,却是准确无误的,可见其珍贵难得。同样不见于它处的,是对祭坛上所立的木杆(木人)有非常细致的描述,包括长度(长丈许)和装饰(白帻、练裙、马尾被)。一丈多高的木杆,顶上覆盖着白布(如同头巾),下半截包裹白色绢布(如同裙子),中间悬挂拼接连缀在一起的多条马尾。“盛陈卤簿”说的是祭天时皇帝的大驾仪仗。而“边坛奔驰奏伎为乐”,则既包含了前面分析过的蹋坛和绕天,又有别处都不曾提及的“奏伎为乐”。伎乐当然应该是祭天大典的一部分,这里把它与蹋坛绕天放在一起说,显示是南来使人的目击见证,因为他们仅仅见到仪式的这一部分,青门之内的仪程是他们见不到的。
与前引《魏书·礼志》明显不同的是,《南齐书》称祭天方坛上的木人(即木杆)数量不是七根,而是四十九根。方坛上木杆数量的变化,其实《魏书·礼志》也提到了:“显祖以西郊旧事,岁增木主七,易世则更兆,其事无益于神明。初革前仪,定置主七,立碑于郊所”。[2](卷108之一,P2992)时在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六月。据此,历代皇帝在位时,每年祭天大典都会在方坛上增加七根木杆,换了皇帝则从七根重新开始。献文帝的变革就是不再每年增加,长期保持七根木杆的数量。
《南齐书·魏虏传》这一部分材料,来源混杂,所记并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之事。比如记“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其中“国记”显然指崔浩主持编修的北魏国史。《魏书·崔浩传》:“著作令史太原闵湛、赵郡郄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2](卷35,P913)据《南齐书·魏虏传》,碑石版北魏国史立在城西三里处。据《魏书·崔浩传》,立碑石的地方在“天郊东三里”。由此可知,平城西郊祭天方坛在平城西六里处。碑石版北魏国史已在崔浩案后被毁,南来使人见此,必在太武帝后期、崔浩案发的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五月之前。
祀天方坛上有四十九木人,说明皇帝在位已七年。我怀疑这条材料出自刘宋使者的观察或听闻,其事极可能就在延兴二年。这一年四月,是献文帝即位后第七次祭天。而在这年正月,“诏假员外郞、散骑常侍邢祐使于宋”。《魏书》记此年四月“辛亥,刘彧遣使朝贡”。[2](卷7上《高祖纪上》,P163)这是宋人对正月魏使的报使,时间正在四月祭天之后,因而他们可以看见或听说祭坛上有四十九根木杆。献文帝为什么要改变“岁增木主七”的旧规呢?前一年八月他已禅位给孝文帝,自己做了太上皇帝。那么这到底算不算“易世”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延兴二年四月的祭天,是献文帝做皇帝后的第7次,同时又是自己禅位后的第一次。他一定还在这次祭天大典进行时,就已察觉到了这一理论、实践以及政治上的尴尬。于是两个月后他做出决定,“初革前仪,定置主七”,规定方坛上只允许立七根木杆,不再逐年递增。决定之后,献文帝还下令“立碑于郊所”,显然是要给自己找一个圆场,以应付来自方方面面(特别是冯太后)的质疑。
三、祭天方坛上木杆的性质
前面根据南北史料所记北魏西郊祭天仪式,立在方坛上的木杆被称为“木主”、“木人”或“天神主”。“主”这个词又是借自华夏祭祀礼制,在华夏传统中代表祭祀的对象,①郑玄注《周礼》之《春官·司巫》:“主,谓木主也。”见孙诒让著,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13年,第2066页。在这里似乎就是指天神了。当然,正如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这一理解是错误的,表明按照史书中被借用的华夏概念来理解内亚传统,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误导。
首先,被宰杀的马牛羊如何处置呢?也就是说,牲体如何敬奉给天神呢?史料完全没有交待。《魏书·礼志》记道武帝天兴二年正月“亲祀上帝于南郊”,从阳则焚燎,从阴则瘗埋,属于模仿华夏传统。天赐改革的一大特征是重回拓跋传统,西郊祭天的隆重举行就是一大标志。那么,在遵循拓跋传统所举行的祭天大典上,如何处置牲体呢?
《魏书·礼志》记太武帝遣使到乌洛侯国西北的所谓拓跋祖先的石室致祭:
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郞李敞诣石室,吿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谓魏国感灵祇之应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2](卷108之一,P2990-2991)
1980年夏,文物工作者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的天然山洞嘎仙洞石壁上,发现了太武帝所派使者在这里祝祭后所刻的祝文,文字与《魏书》所载基本一致,仅略有出入。可见这个嘎仙洞即《魏书》所称的鲜卑石室。[7]上引文字中对本文主题最重要的地方是对李敞(其实李敞只是副使,主使是代人库六官)等人祭祀细节的记录:“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他们砍了一些桦树,插在地上,然而把牲体挂在桦树上。选择桦树也许是随机的,因为那一带只有桦树。但所立桦树的数量一定不是随意的和随机的,只可惜我们无从知道李敞他们砍了多少桦树,从“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看,是不太少的。
在嘎仙洞的祝祭仪式上,李敞等人把宰杀的动物分割之后,悬挂在所立的桦树上。可见他们砍桦树并插在祭祀场所的目的,换句话说,祭祀时所立木杆的功能,就是悬挂牲体,敬奉给祭祀对象。悬挂牲体是祭祀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史料没有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些悬挂在木杆上的牲体,在祭祀仪式结束之后如何处理呢?可以设想,用于敬奉给祭祀对象的牲体,最后是由参与祭祀的人所分食的。甚至可以说,分食祭肉本身,也是祭祀仪程的一部分。
由此可知,西郊祭天方坛上的木杆,虽然史书中比附华夏传统而称之为木主、木人或天神主,其真实功能并非代表天神,也就是说,它们不是或不代表祭祀的对象,而只是用来悬挂祭祀中被宰杀的马牛羊肉。在重要的露天祭祀中把牲体悬挂在木杆上,这种祭祀实践普遍存在于内亚各时期的各语言各人群之中。下面所举数例,当然不是史料中相关事例的全部,要之足以说明这一内亚实践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普遍与广泛。
《史记》、《汉书》提到匈奴的蹛林,研究者据此探索匈奴的祭祀。②江上波夫:《匈奴の祭祀》,载江上波夫:《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京都:全国书房,1948年,第225-279页;该文有中译本,江上波夫著,黄舒眉译:《匈奴的祭祀》,收于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6页。不过因史文过于简略,深入研究的空间很有限,是否与本文关注的木杆相关,似乎很不明确。因此,我们把视线转向晚于拓跋的内亚人群。《周书·突厥传》记突厥葬礼,提到宰杀动物的处理方式:
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一诣帐门,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葬之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又以祭之羊马头,尽悬挂于标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饰,会于葬所。[8](卷50,P910)
初死之时,“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也就是要杀羊马在帐前致祭。史书没有提这些羊马牲体如何处理,我猜想绝大部分牲体要吃掉。帐前同样要“立标”,即竖立木杆,以悬挂牲体的全部或部分。墓前所立之石,即所谓杀人石,很多学者认为鄂尔浑突厥文碑铭所提到的balbal就是指这种墓前立石,象征被死者杀掉的那些人。墓前所建之标,显然指竖立的木杆,其功能是悬挂为祭死者所杀的羊马的头颅,意味着羊马身体的其余部位已在葬礼上吃掉了。
《辽史·礼志》记契丹“祭山仪”,其祭祀仪程颇有可与拓跋祭天仪程相比类者。兹节引如次:
设天神、地祇位于木叶山,东乡;中立君树,前植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皇帝、皇后至,夷离毕具礼仪。牲用赭白马、玄牛、赤白羊,皆牡。仆臣曰旗鼓拽剌,杀牲,体割,悬之君树。太巫以酒酹牲。
……皇帝、皇后升坛,御龙文方茵坐。再声警,诣祭东所,群臣、命妇从,班列如初。巫衣白衣,惕隐以素巾拜而冠之。巫三致辞。每致辞,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皇帝、皇后各举酒二爵,肉二器,再奠。
……皇帝、皇后六拜,在位者皆六拜。皇帝、皇后复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祇位。执事郎君二十人持福酒、胙肉,诣皇帝、皇后前。太巫奠酹讫,皇帝、皇后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皇后一拜,饮福,受胙,复位,坐。在位者以次饮。皇帝、皇后率群臣复班位,再拜。声跸,一拜。退。[9](卷49,P928-929)
契丹祭山仪与拓跋祭天仪当然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有关祭祀仪式的描述,某些差异可以视为史书各有详略所造成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互相补充,或至少彼此映照。比如,牺牲马牛羊“皆牡”,这是过去的史料中所没有提到的,但是,以雄性动物为祭祀牺牲,在内亚世界很可能是普遍做法。又如“巫衣白衣”,亦不见于北朝史书,这条材料提醒我们,平城西郊祭天的女巫所穿的衣服颜色,必定是有特别讲究的。“巫三致辞”也可以补充拓跋祭天之仪,因为典礼上的巫人(萨满)应该是有说有唱,且歌词用语都相对固定。还有,典礼结束前“执事郎君二十人持福酒、胙肉,诣皇帝、皇后前”,就是把酒具中所剩的酒(福酒),以及牺牲动物的肉(胙肉),呈送皇帝和皇后,让他们“饮福、受胙”。这个分食牺牲的环节也可以补充拓跋祭天之仪。可以想象,天赐二年四月西郊祭天的末尾,那七个选自“帝之十族”的少年(类似契丹的“执事郎君二十人”),会把酒肉送到皇帝、皇后面前,作为规定动作,后者必须现场吃喝一番。还可以设想,在皇帝、皇后品尝之后,同一批酒肉也会轮到旁边的一众陪侍贵人。
但对本文论旨而言,前引契丹祭山仪文本中,最重要的是记录了祭祀仪式中,切割开来的牺牲动物同样要悬挂在插立于地的木杆(君树)之上:“杀牲,体割,悬之君树,太巫以酒酹牲。”前引《魏书·礼志》所省略的,是“体割,悬之君树”这两个环节,所不同的,是“以酒酹牲”者为执酒七子弟。《辽史·礼志》随后记辽太宗和辽兴宗改动祭山仪某些细节,称“神主树木,悬牲吿办,班位奠祝,致嘏饮福,往往暗合于礼”。[9](卷49,P929)悬牲于神主树木,描述的是同样的场景。
《蒙古秘史》第43节提到蒙古人一种非常重要的传统家族祭祀,其明代总译是这样的:
孛端察儿又自娶了个妻,生了个儿子,名把林失亦剌秃合必赤。那合必赤的母从嫁来的妇人,孛端察儿做了妾,生了个儿子,名沼兀列歹。孛端察儿在时,将他做儿,祭祀时同祭祀有来。[10](卷1,P13)
总译最后一句的“祭祀”,对应的蒙古语词汇是“主格黎(ǰügeli)”,旁译“以竿悬肉祭天”。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对这一句的英译特别纳入了明代旁译,再译成中文就是:“一开始,沼兀列歹(ǰe’üredei)是可以参加ǰügeli祭祀的,这种ǰügeli祭祀就是把肉悬挂在木杆上供奉给上天。”[11](P8)罗依果对这个“主格黎”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几乎囊括了学界所有重要的研究。[11](P280-283)从罗依果所列举的学界研究中,可以看到一种倾向,就是认为《秘史》此处所说的祭祀并不是祭天,而是祭祖。他们的理由是,《秘史》在这里说沼兀列歹本可以参加“主格黎”的仪式,说明孛端察儿在世时是承认他为自己儿子的,因而他在宗法血缘的意义上具备了某种资格。孛端察儿死后,沼兀列歹被排除在“主格黎”仪式之外,意味着他不再被承认为孛端察儿之子了,也就是被剥夺了宗法血缘的资格。研究者认为,既然能否参加祭祀,完全取决于血缘资格,那么祭祀对象就不会是天,而是祖先。
我不赞同这种很大程度上基于定居社会历史经验的理解。在草原游牧社会的祭祀活动中,祭天也是宗族事务,并不是开放性社会活动。“主格黎”这种类型的祭祀,对参与者有严格的资格要求,只有某一社会范围的人员可以参加。元初王恽《中堂事记》记中统二年四月八日己亥(1261年5月8日):“天日极晴朗。上祀天于旧桓州西北郊,皇族之外,皆不得预礼也。”①王恽:《中堂事记》,顾宏义、李文:《金元日记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值得注意的是,王恽还记录四月六日忽必烈汗对汉臣说,次日(也就是祭天的前一天)“朕郊祭骊马、酮马,卿等不必扈行”。这很可能说明,蒙古的祭天和拓跋人一样,都要在前一天去“热身”。至于蒙古的祭天“热身”,是不是如拓跋那样绕坛跑马,我暂时没有找到证据。王恽写得很清楚,忽必烈参加的是“祀天”大典,不是所谓祭祖,然而参与者仍然是以皇族血亲为限,皇族之外的人员是不能参加的。很显然这就是一个高规格的“主格黎”。可以想见,在忽必烈参加的“主格黎”祀天大典上,也必定有把动物牺牲悬挂在木杆上的仪式。因外人不得预礼,祭典细节便无人知晓、不见记录。
祭祀时悬在木杆上的肉最后怎么处理呢?《蒙古秘史》第70节讲述诃额仑夫人一家被排挤在烧饭祭祀之外的故事,明代总译是这样的:
那年春间,俺巴孩皇帝的两个夫人斡儿伯、莎合台祭祀祖宗时,诃额仑去得落后了,祭祀的茶饭不曾与。诃额仑对说,也速该死了,我的儿子将来怕长不大么道,大的每的胙肉分了为甚不与?眼看着的茶饭不与了,起营时不呼唤的光景做了也。[10](卷1,P42)
现代学者提供了方便理解的译文,谨录札奇斯钦译文如下:
那年春天,俺巴孩可汗的可敦,斡儿伯与莎合台两个人,在祭祖之地,烧饭祭祀,诃额伦夫人到晚了。因为没有等候她,诃额伦夫人就对斡儿伯、莎合台两个人说:“因为也速该·把阿秃儿已经死了,我的孩子们还没有长大吗?你们为什么在分领祭祖的胙肉和供酒之时,故意不等我们呢?你们眼看着,连吃也不(给),起营也不叫了!”[12](P41-72)
无论祭天祭祖,祭祀的核心环节都是向祭祀对象供奉酒肉,而绝大部分酒肉最终要由祭祀参与者分享。分享这种福酒胙肉(当然福酒胙肉也是借用了华夏-汉社会祭祀传统用语),对于参与者来说,是社会身份获得重新认定(renewal of membership)的物质化呈现。所以可以肯定,在“以竿悬肉祭天”的主格黎祭祀结束时,无论是孛端察儿家人的主格黎,还是忽必烈亲自参加的主格黎,祭祀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应该是分领酒肉。对于衣食无忧的权势人物来说,福酒胙肉只有象征意义;对于贫穷牧民家庭来说,参与祭祀的目的之一就是最后分领一点酒肉。
罗依果所举讨论主格黎的论著中,匈牙利学者Lajos Bese1986年在《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AOH)上发表的《蒙古秘史中的萨满术语主格黎》一文,[13]一方面吸收语言学和宗教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充分考察了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民族志和人类学田野资料,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立杆悬肉问题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据Bese此文,Cheremisov在1951出版的《布里亚特蒙古语-俄语词典》已收有züxeli一词,此书1973年的增订版这样解释züxeli:献祭动物之皮(带头与四蹄)放置在木杆上。词典收有一个词根züxe-,解释为把带头与四蹄的动物皮、杂有干草的动物肝脏肾脏等,放置在木杆上;另一个意思是刺穿。由此可知,ǰügeli是动词词根 ǰüke-加上名词性后缀 -li形成的名词。
Bese指出,中古蒙古语ǰükeli的形式和词义,以及它所指代的萨满教仪式,在西布里亚特蒙古语人群中至今仍颇有保留。文中引鲍培(Nicholas Poppe)1972年的文章《19世纪布里亚特有关萨满教的一条文献史料》说:“挂在高树上祭神的绵羊皮或山羊皮被称为ǰüxeli,对应《蒙古秘史》之ǰükeli。当我1932年在西布里亚特的Bulagat布里亚特人中搜集民间歌谣时,我见到很多很多这类ǰüxeli献祭。”又引Manzhigeev的话说:“布里亚特语züxeli的词义是:献祭的动物头部、四肢、皮、尾挂在一棵白桦杆上,如同被充塞起来的动物,木杆插入地里。动物头部饰有许多彩色布条,牙齿里塞了冷杉树皮,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对于分食祭肉,Bese这样总结,献祭动物的肉分成三份,一份敬神,一份分予氏族或家族成员,一份给来宾。仪式参与者若未分得祭肉,会被鄙视,显得低人一等。
同为阿尔泰语人群(Altaic Peoples),即使同为某一语族甚至更小亚文化圈的人群,每个时代、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与文化语境。同源(或因长期接触相互影响而近似)的宗教实践也会有众多细节变异,仪式更是如此。在我们理解内亚文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时,不是差异,而是相似,使可比较性和相关性的秩序从历史混沌中浮现。
13世纪前往蒙古高原的欧洲人,目睹或耳闻了各种突厥语人群和蒙古语人群的奇风异俗,其中有与我们这里关注的立杆悬肉相关者。比如加宾尼(John of Plano Carpini)记蒙古人的葬礼:
如果他不是最高等级的贵人,死后会在野外选中的地方秘密埋葬。随葬物中有他的诸多帐房之一,他坐在帐房正中,面前放一张桌子,桌上有一大盘肉和一杯马奶。陪葬的还有一匹配有鞍辔的母马及其马驹,以及一匹配有鞍辔的牡马。他们把另一匹牡马的肉吃掉之后,在皮下充塞干草,悬挂在二或四根木杆上。这样,他在另一世界里就有帐房住,有母马产奶,还可以繁育更多的牡马,可供骑乘。①John of Plano Carpini,“History of Mongols,”in:Christopher Dawson ed.,The Mongol Mission,London&New York:Sheed and Ward,1955,p.13。需要说明的是,此书有中文译本(道森:《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与引文有关的部分,见第13页),但本文的译文是我参考吕浦的译文之后按英译本自译的,特此说明。下文引《鲁不鲁乞东使记》亦同。
加宾尼的关注点是祭祀结束后,献祭的公马肉被分食,剩下连着马头和四蹄的马皮塞入干草,重新缝合,形成近代“马标本”的样子,再挂在木杆上。这一景象是如此醒目,旅行者很容易看到,记录下来或转告他人。加宾尼没有说明的是,当祭祀进行中,被分食之前的马肉,放置在哪里呢?我猜也应该是悬挂在木杆上的。只是这一环节不对外人开放,旅行者是看不到的。鲁不鲁乞(William of Rubruck)见到库蛮人(Coman或Cuman)墓前木杆上悬挂马皮,没有提祭祀时的立杆悬肉,当然同样是因为他并没有看到葬礼过程:
库蛮人在墓上建一个巨大的土堆,为死者立一座雕像,面向东方,放在肚脐位置的手里握有杯子。他们也为富人建锥形塔,也即小小的尖顶屋。我在一些地方见到用砖瓦砌筑的高塔,在另一些地方见到石头房子,尽管其地其实不产石头。我还见到,他们为一个前不久死去的人在多根高高的木杆上悬挂十六张马皮,每个方向各四张马皮。还放马奶酒供他喝,以及供他吃的肉。②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in:Christopher Dawson ed.,The Mongol Mission,p.105;《出使蒙古记》之《鲁不鲁乞东使记》,吕浦译本,第123页。
10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记录乌古斯突厥人的葬礼安排,也提到把连着马头与四蹄的马皮悬挂在木杆上。兹据费耐生(Richard Frye)英译本转译如下:
如有要人死去,……然后他们在墓前把他的马都杀掉,一匹至二百匹不等,直到最后一匹。他们吃掉马肉,剩下头、蹄、皮、尾,都挂在木杆上,并且说:“这是他的骏马,他要骑着去天堂。”如果他杀过人,是个英雄,他们就照他所杀的人数雕刻木像,立于墓前,说:“这些是他的仆人,在天堂服侍他。”[14]
西蒙·圣宽庭(Simon de Saint Quentin)《鞑靼史》(Historia Tartarorum)记蒙古人的葬礼,也提到用木杆把裹草的马皮悬挂起来:
鞑靼人中的富贵者死后穿上贵重的衣服,埋葬在偏远隐蔽的地方,因为这样就没有人能偷走他的衣服。他的父母将他的马从头至尾剥皮,首先切开一个窄条,随后他们将草填进马皮之中,作为怀念死者的遗物。他们在马的屁股上插入一根木桩直至颈部,将其水平悬挂在两个木叉上。之后他们将作为献给逝者灵魂的贡品的马肉吃掉,然后为他哭丧,有的人要哭三十天,其他人有的时间短一些,有的时间长一些。[15](P255)
在木杆上悬挂连带马头与四肢的马皮,这种做法在西伯利亚地区保持到非常晚近。苏联考古学家杰烈维扬科《黑龙江沿岸的村落》提到考古发掘所见的古老习俗:
在发掘东阿尔泰尤斯蒂德河畔的一些茔墙时,考古学家注意到茔地中央木杆下面的残存……行葬之余,他们在这种木杆上悬挂连带马头的马皮和马的四肢。在一些突厥-蒙古牧民那里,主要是崇拜马和树木。这些民族把许多远古时代的殡葬仪式,以马祭神的仪式和某些萨满跳神的仪式等等,一直保留到今天。[16](P294)
四、清代堂子祭天的神杆
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性质上,清代的“堂子祭天”都与北魏平城时代的西郊祭天具有极高的可比性。尽管要确知祭天的仪程细节还是非常难,[17](P36-67)但几乎所有相关材料都会提到“立杆”这个重要因素,这就与本文关注的话题有了直接联系。清代“堂子祭天”仪式中的“设杆致祭”、“立杆大祭”,在该祭典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所谓“神杆”,也就是前面所讨论的北魏西郊祭天中的木主,契丹的“君树”,蒙古“以竿悬肉祭天”的“竿”,是数千年间内亚文化传统连续性的鲜明表现。
所谓堂子(Tangse),即祭天场所,类似北魏平城西郊以方坛为中心的祭天之地。清代的“堂子祭天”出自满洲旧俗。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说:“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18](卷7,P81)昭梿《肃亭杀录》:“国家起自辽沈,有设杆祭天之礼”。[19](卷8,P231)但因为有资格参与祭天大典者属于一个严格限定的人群,如吴振棫所说,“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18](卷7,P81)这一祭典的封闭性及其显然有别于汉文化传统的异质性,营造出一种神秘氛围,种种牵强附会随之而起,比如把堂子之祭与邓将军联系起来,[20](P311-323)等等。连朝鲜燕行使都注意到了,深以为奇。[21](P165-178)这些事项学者知之已悉,兹不赘列。
所谓“立杆”、“设杆”,或所谓“神杆”,其功能也是悬挂牲体。福格《听雨丛谈》卷五“满洲祭祀割牲”条:
满洲祭祀之礼,各族虽不尽同,然其大致则一也。荐熟时,先刲牲之耳、唇、心、肺、肝、趾、尾各尖,共置一器荐之;或割耳、唇、蹄、尾尖,献于神杆斗盘之内。又有荐血之礼、刲肠脂幂于牲首之礼,旧俗相沿,莫知其义者多矣。[22](P129)
又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三“跳神”条:
又主屋院中左方立一神杆,杆长丈许。杆上有锡斗,形如浅椀,祭之次日献牲,祭于杆前,谓之祭天。[23](P61)
姚元之所记神杆上的锡斗,是用来盛放所献牲体的,其本义正同古代内亚悬挂牲体于木上的传统。
如前所论,不同时代不同内亚人群祭祀所立木杆的数量可能差异是很大的。昭梿《啸亭杂录》:
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即汇祀诸神祇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稍后两翼分设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为诸皇子致祭立杆石座,诸王、贝勒、公等各依次序列,均北向。[19](卷8,P231)
方濬师《蕉轩随录》卷十一“祭神”条:
堂子之祭,为我朝敬事天神令典。乾隆十九年四月,谕礼部等衙门:王公等建立神杆,按照爵秩等差设立齐整。寻议神杆立座每翼为六排,每排为六分,皇子神杆列于前,其次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各按排建立,从之。[24](卷11,P423)
清代堂子祭天中献祭的动物牲体,最后都要由与祭者分食,称之为“吃肉”。方濬师《蕉轩随录》:“满洲士庶家均有祭神之礼,亲友之来助祭者,咸入席分胙,谓之吃肉。濬师官京师时,曾屡与斯会。”[24](卷11,P423)清帝大祭之后“赐王公大臣吃肉”,史料中屡屡可见。清代曾短暂地实行把肉煮熟之后献祭,不过以生肉献祭应该是内亚各时期各人群的普遍做法。
清代堂子祭天最重要的史料是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皇帝命和硕庄亲王允禄主持编写的满文《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清人亦称之为《满洲跳神还愿典例》),[25]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由大学士阿桂、于敏中等奉旨译为汉文,收入《四库全书》。全书分为六卷,包含各类祭神祭天的仪注、祝词等,都是极为珍贵的资料。近年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叶高树教授据此书的满文本重新汉译并给出详细注释,是为阅读此书最好的译注本。①叶高树:《满文〈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译注》,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8年。我得知并使用此书,全拜蔡伟杰先生惠赠,谨此致谢。本文所引,均出叶高树教授译本。此书第三册有《堂子立杆大祭仪注》,对祭天神杆的获取、尺寸和安置有明确规定:
每岁春秋二季,堂子立杆大祭。所用之松木神杆,前期一月,派副管领一员,带领领催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隶延庆州,会同地方官,于洁净山内,砍取松树一株,长二丈,围径五寸,树梢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用黄布袱包裹,赍至堂子内,暂于近南墙所设之红漆木架中间,斜倚安置。立杆大祭前期一
日,立杆于亭式殿前中间石上。[26](P224-225)
《清史稿·礼志》“堂子祭天”条近似上文,细节微有出入:
立杆大祭,岁春、秋二季月朔,或二、四、八、十月上旬诹吉行,杆木以松,长三丈,围径五寸。先一月,所司往延庆州属采斫,树梢留枝叶九层,架为杆,赍至堂子。前期一日,树之石座。[27](卷85,P2555)
所用的松木杆并不是砍削得光光净净,而要在顶部保留九层枝叶,这样其实看起来更像一棵树而不是木杆。不知道古代内亚祭典上的木杆是不是也保留枝丫。从功能上说,保留枝丫至少有利于悬挂牲体。
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祭天仪注,祭礼最为繁复的部分是几个萨满(saman,即拓跋时代的女巫,清人译为司祝、祝神人)的行礼与歌唱,许多环节都是一再重复,参与祭礼的人也要配合萨满的行礼和歌唱而一再齐声高唱“鄂啰啰(orolo)”。书中有《堂子立杆大祭飨殿内祝词》,即萨满歌唱的歌词,内容是为主祭人祈福,所祈的福就是健康长寿:让他头发变白,让他口齿变黄,让他年纪大、岁数多,让他活得长久,让他生命之根深远。[26](P236-237)祝词的朴素正足以说明其来历的原始。堂子立杆大祭仪注的最后部分是关于皇帝参与祭礼,他在祭礼中所扮演的角色:
皇帝进飨殿内,行礼。又进亭式殿内,行礼。行礼毕,武备院卿铺皇帝坐褥于西间正中。皇帝南向坐,尚膳正、司俎官以小桌列胙糕恭进,尚茶正捧献福酒。皇帝受胙毕,分赐各王、公。礼成,皇帝还宫,所余糕、酒,分赐扈从之侍卫、官员、司俎等。[26](P234-235)
堂子祭天的典礼之末,也是分领福酒胙肉等献祭之物,这和本文前述内亚其他人群的祭礼仪程是一致的。
祭典用过的木杆如何处理呢?如前所述,北魏西郊祭天每年使用过的木杆要予以保留,直到皇帝死去。内亚其他时期其他人群的做法,已无从考知。清代的做法是每年除夕(次日就要举行新年祭天大典)把包括神杆在内的前次祭典用物都烧掉。“故事,神位所悬纸帛,月终积贮盛以囊,除夕送堂子,与净纸、神杆等同焚。”[27](卷85,P2554)
最后,举康熙间浙江山阴人杨宾(1650-1720年)在东北亲眼所见的立竿跳神。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九月,杨宾前往东北探望流放在宁古塔近三十年的父亲,在那里生活数月,回家后结合塞外见闻与读书心得,写为《柳边纪略》,最终成书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书中记录了宁古塔地方满人跳神的仪式:
满人病,轻服药而重跳神,亦有无病而跳神者。富贵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岁终则无有弗跳者。未跳之先,树丈余细木于墙院南隅,置斗其上,谓之曰竿。祭时著肉斗内,必有鸦来啄食之,谓为神享。跳神者,或用女巫,或以冢妇,以铃系臀后,摇之作声,而手击鼓。鼓以单牛皮冒铁圈,有环数枚在柄,且击且摇,其声索索然。而口致颂祷之词,词不可辨。祷毕,跳跃旋转,有老虎、回回诸名色。供祭者,猪肉及飞石黑阿峰。飞石黑阿峰者,粘谷米糕也。色黄如玉,质腻,糁以豆粉,蘸以蜜。跳毕,以此遍馈邻里、亲族,而肉则拉人于家食之,以尽为度,不尽则以为不祥。[28](P420-421)
杨宾说祭礼食物中的飞石黑阿峰是一种色黄如玉的粘谷米糕,其实即今华北北部常见的黄糕,以去皮的黍子(俗称黄米)磨成面粉制作而成。《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列献祭食物中的“糕”,就是这种黄米糕。全祖望《跳神曲》所谓“飞石黑阿峰,粢饵有佳名”,也是指这种食物。杨宾对跳神所立之竿的描述,与前引清代其他文献所述亦基本相符。只是他说的“不可辨”的“颂祷之词”,是否在形式和内容上与《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记萨满歌词一致,就难以确知了。
小结:内亚传统的连续性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拓跋西郊祭天方坛上的木杆,其现实功能,或其礼制渊源意义上的功能,是用以悬挂献祭的动物牲体。这一点,比较拓跋之后许多内亚人群的祭祀仪程,大概已然明了,毋庸赘言。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南北朝史书中借用华夏礼制传统的“木主”、“木人”或“天神主”,来描述这些文化属性显然不同的木杆,无论是出于误解还是想当然,都会造成误导,后之读者望文生义而把这些木杆放在华夏传统中理解,把它们看成代表祭祀对象的那种所谓的“主”。
介绍一种异质文化,特别是那些差异比较大的文化时,大量参照和借用自己文化已有的概念、观念、词语和表达方式,一开始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如中古佛教初来时的“格义”),但因此一定会造成一些失实、失真或信息流失。随着接触增多、理解深入,原先那些借用的概念或词语要么被放弃,要么词语或概念本身被改造而变化。这是文化交流史上的常态。不过也存在另一种情况,那就是误解得以延续,真相持续隐藏或流失。和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历史一样,中国历史也是多元文化共生互动的历史,中原的华夏-汉文化与内亚各人群的文化有着漫长持久的互动与交流,汉文文献对内亚文化的记录当然是丰富的、宝贵的,但某些场合的确存在隔膜和失真等问题。南北朝史书把拓跋祭天方坛上悬挂牲体的木杆记为木主、天神主,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文化间孤立的和个别的误读(misreading)、误译(mistranslation),无法在孤立与个别的语境中获得纠正,而要放到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通过比较建立历史理解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内亚文化的连续性是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的保障。
如何理解内亚文化的连续性呢?内亚历史上各时期各人群当然有各自独立和独特的文化与传统,甚至可以说,全世界各基本人群都一样有其各自独立和独特的文化与传统。但是,地理条件、经济生产方式及历史发展等多种因素,使得世界上人群之间的历史联系是高度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决定了文化差异的不均匀分布,有的人群间文化差异小,有的人群间文化差异大。内亚尽管也是多文化、多经济形态的,但其中心世界是草原,其主体人群是游牧人,而因为整个社会都在马背上,不同游牧人群间的互动规模往往非常大,其空间尺度常常大到定居社会难以理解的程度。历史时期虽然草原地带的政治体更换未必比定居社会更频繁,但其震荡规模和地理覆盖面总起来看要大得多。这些条件使得内亚各人群间的深度互动持续发生,造成语言、风俗和信仰等方面的高度近似,使得内亚各人群之间看起来似乎是共享着同一个文化遗产,特别是当与非内亚如中原的华夏-汉人群进行比较时。必须说明的是,正如阿尔泰语(Altaic)各语言之间的语言亲缘性是接触的结果,①关于“原始阿尔泰语”假设的批评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最具代表性的是Gerard Clauson,“The Case against the Altaic Theory,”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2(1956),pp.181-187。近 20年来这一派已渐渐成为主流,见Claus Schönig,“Turko-Mongolic Relations,”in:The Mongolic Languages,edited by Juha Janhunen,Routledge,2003,pp.403-419。内亚各人群之间的文化亲缘性,也是接触和互动的结果——正如并不存在一个原始阿尔泰语(Proto-Altaic)母体,同样也不存在一个原始内亚文化母体。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历史地理解内亚文化的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是指内亚许多(当然不能说是全部)人群,在许多(当然不能说是所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文化亲缘性。认识到这一点,至少有助于前面所说的跨时空文化比较,因而也就有助于校正对内亚文化的误读和误译。本文论证拓跋平城西郊祭天方坛上的木杆不是代表天神的“主”,而是悬挂牲体的祭祀道具,所用的方法便是求助于广阔的内亚资源,以拓跋之后多个内亚人群(内亚政治体)的祭祀实践作为比较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说内亚是一种方法,不是指任何孤立的、个别的内亚人群,而是要尽可能多地拓展历史内亚的时间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