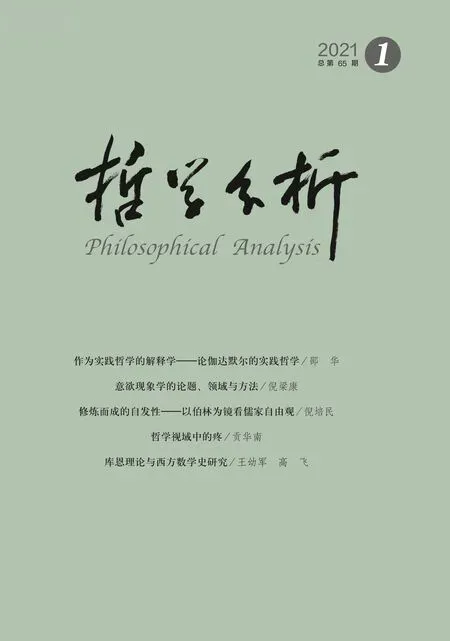意图独特性的信号博弈辩护
2021-11-24张巍
张 巍
一、意图与信号
意图(intention)作为一种意向状态(intentional state),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y)在桥接心灵与行动时的体现。对意图的研究是行动哲学自诞生以来最为核心的主题之一,也是分析哲学界对意向性问题研究的重要线索之一;可以说,对于意图的哲学研究构成了分析风格的行动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意图在协调行动者的意向状态与行动实践时,会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信息传递与处理机制。因此,这启发我们,可以尝试从信号与信息的视角对意图的形而上学属性进行新的刻画与辩护,而这些属性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意图区别于信念、愿望等其他意向状态的独特性。
近年来,关于信号的哲学研究逐渐成为信息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时常出现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行动哲学、生物学哲学等众多研究领域中,因此也逐渐成为近年来形而上学和知识论共同关注的论题之一。①Bryan Skyrms, Signals: Evolution, Learning & Inform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4.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不同,信号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携带着信息,因此,信号的发生和传递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信息处理的过程。人类的语言、心智以及行动在某种意义上讲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信号互动与信息处理的过程,其中都涉及了大量的信号表征与信息交互。于是,如何理解这种信息处理过程,并且以信号互动与信息处理为线索去研究相关的传统哲学问题,就成为了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行动哲学等相关领域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框架。随着20世纪信息论、博弈论等相关理论学科的兴起,信息哲学有了很多新的研究工具。其中,对于信号的哲学研究影响较大的是刘易斯(David Lewis)的信号博弈模型。②David Lewis, Convention: A Philosophical Stud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30—131.这类模型的提出对于理解信号的发送与接收,以及这其中所涉及的信息传递机制,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易斯信号博弈的均衡状态是一种带有协同性质的约定,而这种协同性恰好是意图在行动者的实践推理过程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个体行动的成功实施可以被看作行动者在前后时刻的意图相互协同的结果,而集体行动的成功实施则可以被看作多个行动者在一段时间内的意图的相互协同的结果。因此,意图可以被看作是行动者在实践推理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广义的信号,该意图所涉及的意向内容则可以被看作相应信号所携带的信息的语义内容。一般说来,意图所表征的信号是实践推理过程中理性程度较高的一类信号,因为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行动的协同性,从而进一步保证行动的合理性。而且,也正是这种协同性的特质,使得意图在众多的意向状态中呈现出一种形而上学层面上的独特性,从而保证了行动者能够结合所处的情境与已知的信息,合理地规划与实施一个合适的行动。当然,在本文的后续论述中会指出,集体行动中行动者所持有的、承载者为复数第一人称主体的意图类型会对协同性有着更为特殊的体现和要求。
二、刘易斯信号博弈模型及其均衡
刘易斯信号博弈模型的参与者主要有信号的发送者与接受者,他们之间通过信号的传递和相应行动的选择进行策略互动,从而获得最终的收益。刘易斯信号博弈是一类博弈模型,它可以刻画相当复杂的信号互动过程。从理论上讲,多个参与者、多个信号以及多个候选行动的信号博弈都可以用刘易斯的理论进行展现。当然,从论述简明的角度出发,本文只选择刘易斯信号博弈中最简明的模型,即两个参与者、两个信号以及两个候选行动的模型。当然,如果对局只有一个参与者时,上述模型就可以用来刻画一个纯粹的决策问题,即把信号的发送者看作自然界。不过,由于本文后续的论述会涉及集体行动,因此两个参与者的设定是合适的。
具体而言,最简明的刘易斯信号博弈可以表述如下:在两个对局者中有一个是信号的发送者,而另一个则是信号的接收者。自然随机决定世界的某个状态,发送者可以直接观察到这个状态,并相应地发送某个信号(此时就是备选信号集中两个候选信号中的任意一个),接收者无法直接观察到世界状态,但是可以通过观察发送者的信号而作出相应的行动(此时就是备选行动集中两个候选行动中的任意一个)。如果该行动刚好与世界状态相匹配,那么博弈双方都会获得一定数量的回报,如果行动与世界状态不匹配,那么博弈双方就没有任何回报。①Bryan Skyrms, Signals: Evolution, Learning & Inform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7.如果是对应到行动者的实践推理过程,那么此时的回报就是某个个体行动或者集体行动的成功实施,行动目标的达成所带来的收益就是此时的信号博弈参与者的回报。
从博弈论的角度讲,刘易斯信号博弈属于协同博弈的一种,这类博弈要求博弈的参与各方的策略选择具有某种协同性,从而最终实现博弈的均衡状态。如同上文中提到的这个最简明的信号博弈模型,通过信号互动所实现的行动与世界状态的匹配就是该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此时任何一个参与者选择放弃这个均衡中的策略选择都会带来各自回报的下降。但是,协同博弈经常会出现多个纳什均衡同时存在的情况,上述博弈中也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因为每一个候选信号都可以实现一个纳什均衡。因此,如何在这些均衡中进行合理的选择就成为了信号博弈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不过,随着演化博弈论的发展,一系列的动力学机制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处理这个问题。①Bryan Skyrms, Signals: Evolution, Learning & Inform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0—11.如果再考虑到实践过程中的某些相关的文化及社会因素所带来的凸显性的影响②Ibid., p. 8.,信号博弈的均衡实现与选择是可以进行合理分析的。当然,本文不过多涉及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是如果把意图作为信号去理解,那么均衡的选择与实现实际上就是行动的成功实施。在这个意义上,如何找到那些动态稳定的均衡实际上也是行动者理性能力的重要体现。
信号博弈的均衡对于刘易斯的研究而言,其哲学意蕴其实在于其对于“约定”的刻画。刘易斯提出这个博弈模型的初衷并不是专门为了对信息或者行动展开说明,而是为了应对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对于“约定”的质疑。③Ibid., p. 136.不过,恰好是这种对于约定的理解,使得我们在用它来理解心灵与行动时,更能够体现出意图区别与其他意向状态的重要特征,就比如一致性、融贯性、稳定性等等。而所有的这些特性集中起来就表明了意图作为一种特殊的意向状态,其理性程度及要求是各种意向状态中最高的,反映的是一种关乎实践的理性承诺。换言之,用信号博弈模型的均衡实现过程去理解意图运作的机制,是对意图的独特性的一种新的辩护路径。
三、意图与信号博弈
用信号去刻画意图,或者说提出一种关于意图运作的信号博弈模型,实际上是给出了一种关于意图的形而上学框架。这个框架区别于之前的意图理论,因为不管是视角,还是方法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但是,关于意图的信号博弈模型中所反映出的意图的特质却并不新奇,这套理论依旧是为意图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独特性作出辩护。而且,意图的信号模型在某种程度上与布莱特曼(Michael Bratman)给出的关于意图的计划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从合理性的角度较为清晰地刻画出了意图在行动者心灵中的特殊地位。
一般说来,行动者所具有的主动性的最显著特点包括:行动者需要协调自己在不同时刻的意向状态以及相关举动,使某个行动最终合理地实施;而且还需要协调同一时刻自己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意向状态及相关举动,使某个集体行动合理地实施。布莱特曼用自己的计划理论很好地论证了这一点,说明意图作为行动者的一个计划,或者一个计划的某个部分,可以很好地实现上述这些主动性。①Michael Bratman, Intentions, Plans, and Practical Rea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pp. 9—10.各个意图之间的相互衔接和融贯,使得一个简单的,或者复杂的行动得以实现,而这种实现同样可以通过上文中的信号博弈模型进行展现,而且在技术层面上更加细节化,相应的拓展空间也更大。
此处的论证还是以最简明的刘易斯信号博弈为论证框架,当然随着理论推演的不断深入,这个模型所涉及的参与者数量、信号数量,以及行动数量都可以进行拓展,以用来说明更加复杂的情形。针对上文提及的主动性的两大特征,本文结合不同的行动类型分别阐述如 下:
第一类为个体行动(跨越时间的协同),假设行动者A在时刻T1形成意图I1,此时意图I1作为信号S发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行动者A于时刻T2需要形成意图I2,或在此基础上实施某个行动。那么对应到刘易斯信号博弈模型中,上述过程可以被看作一个历时的信号博弈,信号即为意图I1,信号的发送者为前一时刻的行动者,信号的接收者为后一时刻的同一行动者。信号博弈的均衡要求需要行动者通过协同信号与相应的行动选择,也就是说针对之前形成的意图,行动者需要选择相应的与之匹配的意图或者行动,从而实现某个行动目标,即获得该信号博弈的最大回报。
第二类为集体行动(跨越行动者个体的协同),同上,在某个时刻T,行动者集体G中的每个个体都有着关于某个共同目标的集体意图CI,按照塞尔(John Searle)的集体意图理论,每个参与者的大脑中会从此意图中衍生出一个关涉自己行动的意图CIi(i=1,2,3…,n),其中n为参与者数量。那么对应到刘易斯信号博弈模型,考察最简单的情形,即两个参与者的情况,此时参与者所持有的意图即为信号,而参与者各自均可承担信号发送者与接受者的角色,然后通过信号的互动实现各自意图之间的匹配,从而使该集体行动得以成功实施,获得该信号博弈的最大回报。相比较而言,这个模型比上一个模型要复杂,因为信号的发送者与接受者是不固定的,而且这种角色也取决于这个群体的组织形式,可以是领导者与追随者的模式,也可以是彼此平等的互动模式。
从上述两个模型中均可以发现,意图作为一种广义的信号,它的运作机制可以由信号博弈进行刻画,通过这种信号博弈机制,我们可以将行动者对于某个行动的实现在不同时刻,以及不同个体之间的协同体现出来。这种协同保证了行动的成功实施,而其基础还是在于行动者的主动性中的相关理性要求,如与该行动相关的意向状态及其实现情形之间的一致性、融贯性、稳定性等等。在上述博弈模型中,回报的极大化取决于行动者的意图与其他相关选择之间的匹配性,而这种匹配可以是多方面的,既可以是前后意图及其与所要实现的目标之间的融贯性,也可以是意图与相应行为之间的一致性等等,而且一旦形成并发送了这个信号,也就意味着在没有新的信息出现之前,该信号是稳定有效的。于是,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意图的计划理论中所涉及的重点在这个关于意图的信号模型中均得到体现,而且由于信号模型可以用具体的博弈模型刻画,从而可以将之前众多关于意图的形而上学理论中描述性的部分变得更为规范化。
对于上述论证,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作出说明。上文通过信号博弈模型分别对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中行动者所持有的意图进行了刻画,但是在刻画集体行动中的意图运作机制时,上文选择了塞尔的“We-intention”理论框架,而并没有继续沿着“计划理论”选择布莱特曼的“shared intention”理论框架,这其中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本文在后续论述中,希望在通过信号博弈对意图的独特性进行辩护的基础上,将这种辩护思路继续拓展到对于集体意图的独特性的辩护之上,而对于集体意图的独特性的辩护主要就在于如何论证其在本体论层面上的原初性,也就是论证形如“we intend”的意图承载者为复数第一人称主体的意图类型,不能还原为形如“I intend”的意图承载者为单数第一人称主体的个体意图的叠加。在上述两个关于集体意图的理论框架中,相比较而言,塞尔对于集体意图的理解,其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在本体论层面上坚持集体意图的“原初性”,而布莱特曼通过参与集体行动的行动者之间的“子计划契合”与“共同知识”对于集体意图的理解则带有“还原式”的意味;而且,基于上述对于集体意图独特性的理解,集体意图要求集体行动中行动者在实践推理过程中保持一种从“我们”出发的推理与决策视角,而这种视角是塞尔对于集体意图的理解的重要衍生。相比之下,布莱特曼的集体意图理论框架在处理类似实践推理问题时,大体上还是延续了经典的从“我”出发的计划与决策模式,而实际上当我们考察协作的实质及其实施机制时,比如当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人机协同的实现,要求行动者在协作中从“我们”的视角出发进行团队推理,或许是一种有启发性的思路。不过,布莱特曼对于集体意图的理解,同样也是可以基于信号博弈模型展开的,而且其一以贯之的关于意图的“计划理论”,对于理解集体意图依然很有意义,尤其在认识论层面上可以为集体意图的融贯性与协同性进行细致深刻的说明。也就是说,在对集体意图的认识论特质进行展开论述的过程中,塞尔的“We-intention”理论框架可以融入计划理论,从而变得更为精致。因此,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通过信号博弈模型对集体意图进行刻画时,优先考虑了塞尔的理论框架,这么处理既保持了与计划理论之间的融洽,同时也为后续的论证作好新的理论预备。
当然,用信号博弈模型去处理意图的形而上学,需要面对信号哲学自身所需要回应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信号博弈过程中信号的损耗、错失,甚至于产生错误、虚假的信号。但是,正是这些问题及其回应的存在,使得意图的信号模型较之之前的各种意图的形而上学理论更加地贴近真实的决策与行动。因为在现实的行动决策过程中,行动者的意图是否得以实现将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制约,人类作为一种有限理性能力的行动者,只可能在这些制约之中去实现自己决策的优化,真实行动场景中的信号博弈模型肯定要远远复杂于本文所讨论的情形,但是不管多么复杂的刻画,其基本的逻辑起点依然是本文所阐述的这类信号博弈模型。
四、对意图独特性的新辩护
意图的形而上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意图的本体论地位。在现今的行动哲学界,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意图是一种意向状态。但是对于进一步如何去认识意图的本质,学界一直以来就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分歧的焦点就在于意图是否是一种原初意义上的、不可还原的意向状态。换言之,意图作为一种意向状态,是否具备其他意向状态所不具备的独特性,而且这种独特性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针对这一问题,学界的回答分为两派,一种观点认为意图应该被还原为信念或愿望,或者二者的叠加;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意图是一种独特的意向状态,与信念、愿望的本体论地位是同一层次的。其中,前一种观点在行动哲学研究的早期比较主流,代表人物就是戴维森①Donald Davidson, “Actions, Reasons, and Causes”, in Donald Davidson, 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 Oxford:Clarendon Press, 2001, pp. 3—4.;但是随着一批新兴的行动哲学研究的出现,到了20世纪后20年,后一种观点逐渐成为了主流。但是近年来,“还原论”的观点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辩护。而本文所提倡的这种关于意图的信号哲学研究,作为一种新的关于意图的形而上学框架,恰好可以为“原初论”提供相关的新辩护,从而在一个新的视角下论证意图是一种独特的意向状态。
一般说来,还原论中较为典型的代表观点认为意图可以被还原为信念与愿望的叠加。行动者持有关于某个行动的意图,意味着他想要实现这个行动,并相信自己能够实现这个行动。当然,在还原论的众多理论中,还有将意图还原为信念,或者将意图还原为愿望的理论。不过这些理论的相同之处就是认为意图在本体论意义上只是一种为了描述行动者心理的概念工具,并不是一种真正存在的意向状态,真正存在的只是比意图更为基础的信念,以及愿望。在行动哲学研究的早期,除了戴维森之外,还有不少哲学家都持这样的观点,如戈德曼(Alvin Goldman)在自己的行动哲学著作中也有较为明确的表述。②Alvin Goldman, A Theory of Human Action, NJ.: Prentice-Hall Press, 1970, pp. 54—55.
但是,随着行动哲学与心灵哲学研究的不断推进,研究者们发现意图并不如上文阐述的那么简单。上文中提到的这种还原式的分析在很多时候并不能真正把握住意图的各种重要特性,这其中就包括意图的合理性、稳定性等等各种方面。于是,一大批研究者开始转向意图的“原初论”阵营,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包括塞尔与布莱特曼等人。塞尔从意图的满足条件与适应指向两个方面论证了意图的原初性与独特性,指出在众多意向状态中,只有意图的适应条件是行动,而且意图的适应指向刚好与信念相反,是一种“世界向心灵”的方向。③John Searle,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pp. 7—8.而布莱特曼则是从他自己提出的计划理论的视角出发,指出意图对于行动者的实践推理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意图区别于信念与愿望的显著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意图掌控着行动的可预见的结果;第二,行动者在没有获得相关的新信息之前不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意图所涉及的意向内容;第三,在已有意图的统摄下,行动者会产生与已有意图相匹配的、实现该意图所需的各种子意图以及各类实现手段。①Neil Sinhababu, “The Desire-Belief Account of Intention Explains Everything”, Noûs, Vol. 47, No. 4,2013,pp. 688—689.因此,意图对于行动者而言,提供的是一种实践承诺,而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承诺。意图对于行动者而言,其合理性、指向性、稳定性等方面的要求都要高于信念与愿望。
那么,回到本文提出的关于意图的信号哲学框架中,上文中提到的塞尔与布莱特曼的论证都可以通过信号模型得以重构。换言之,本文提出的这一理论框架在论证意图的原初性上可以整合已有的相关论证,因此是一种较为全面的关于意图的形而上学体系。首先,意图作为一种信号,行动者作为信号博弈的参与者,意图的满足条件可以通过信号所携带的信息的语义内容进行表征②Fred Dretske, Knowledge and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81, p. 65.;而适应指向则表现为行动对信号的匹配,其方向性与塞尔的理论是一致的;至于意图的合理性、指向性与稳定性等理性要求,在信号博弈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信号博弈反映的是一种信息处理机制,在信息的交互过程中,信号的合理性、指向性和稳定性是信息的发送、传递和接收的基础。而且,信号与行动之间需要通过某种带有一致性与融贯性要求的匹配原则进行对应,从而保证信号博弈的参与者得到最大的回报。
参照上述这些要求,信念和愿望都不足以作为一种理性程度较高的信号出现。其中,信念并不直接与实践相联系,信念的对象并不一定需要通过实践途径去得以实施,因此信念作为信号出现,对于行动者在接收信号后的实践选择并不具备明显的指导意义;而愿望在某些时刻是可以相互矛盾的,但是信号传递过程中如果长时间出现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号,这将直接导致信息处理的失败;而且愿望的稳定性不足,这会使得信号极易受到信道中其他噪声的干扰,信号发送和接受的质量大大降低,信息处理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从信号博弈与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意图明显区别于信念与愿望,是一种具有独特性的原初意向状态。
五、意图的信号模型的拓展空间
至此,本文已经基于信号博弈模型对意图所具有的独特性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辩护,而通过上述辩护的全部论证,实际上本文也指明了一种运用信号去刻画意图的理论框架,从而为意图的形而上学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同时上述辩护也展示出这一框架整合了之前各种意图理论的优点。与此同时,由于意图是心灵与行动之间的桥梁,因此对于整个行动哲学研究而言,这种关于意图的信号模型的优势还远不止上述这些,以下是这一理论框架的一些有待进一步拓展的线索。
第一,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意图的信号模型可以启发我们用信号哲学以及信息哲学中的模型去进一步展开对于其他意向状态的研究。如果放宽对于信号的理性要求,信念与愿望是否也可以通过信号去刻画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而关于信号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指出信号的理性程度是有区别的,也是可以进行演化的。因此,将信号模型全面引入意向性理论的研究中,可以帮助研究者们更好地去理解各种不同的意向状态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去思考心灵与行动之间的关系。
第二,意图理论势必会与行动的责任等伦理学问题发生深刻的联系,而意图的信号博弈模型同样可以帮助处理这类问题。在更为复杂的信号博弈模型中,我们可以考察各类学习与强化机制对于信号博弈和信息处理的影响,从而找到外界因素对于一个完整的信息处理结构形成的影响机制。按照演化博弈论的观点,此时的外界因素可以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也可以是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如果再进一步按照协同演化的理论框架去思考,我们可以按照信号博弈中参与者在发送和接收信号时的策略选择去追寻他们各自对于该信息处理过程所承担的角色及相应的责任。因此,意图的信号模型可以拓展到一种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伦理学研究之中。
第三,意图作为一种信号,可以在不同的行动者之间进行传递和交流,从而导致各种各样的集体行动的实现。因此,意图的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对于集体行动的说明,尤其是关于集体意图的形成及其原初性,集体主动性的特征以及集体合理性的标准的研究。如果意图是一种信号,那么集体意图也应该是一种更为特殊的信号,这类信号在发送之前就已经满足某些更为苛刻的合理性要求,它们的发送与接收将直接决定某个集体行动是否合理,以及是否能够被成功实施。而且,运用信号博弈模型去刻画意图对于集体行动哲学研究而言,还会带来一个技术层面的启示,那就是对目前人工智能哲学领域中关于人机互动的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技术实现的路径。如果意图被理解为信号,那么智能机器对于意图的识别和理解得以算法化的可能性就会提升,随之而来的就是智能机器参与社会互动的可能性和稳定性的提升,人机互动作为一种智能时代非常特殊的“集体行动”,其中涉及的行动意图也会因为意图的信号博弈模型而变得更为清晰。
当然,意图的信号模型的拓展空间还远不止这些,因为信号博弈模型以及信息哲学框架可以介入的哲学研究领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随着信息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信号的哲学研究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意图的信号博弈模型还会继续因为这种理论发展而不断地被应用到更多的哲学研究领域之中。
六、基于意图的信号模型理解集体意图
基于上文中提及的对于意图的信号博弈模型的拓展思路,本文试图简述其中一种思路进行例示,即从信号与信号博弈的视角对集体行动中行动者所持有的集体意图进行解读。
所谓集体意图,简言之就是集体行动中行动者所持有的形如“我们意图做某事”的意向状态,其承载者为复数第一人称主体。类似于关于意图的形而上学探讨,集体意图的形而上学讨论中最令人棘手的问题也是关于集体意图的本体论地位的界定。但是区别于关于意图的独特性的论证,集体意图的独特性是体现在其是否能被还原到形如“我意图做某事”的承载者为单数第一人称主体的个体意图之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本文在此处并不打算对争论的细节进行全景式的描述,而是试图通过对于意图的信号解读为集体意图的原初性提供一种新的论证思路,从而表明集体意图是一种原初性的意向状态,是一种独特的意图类型,不能被理解为承载者为单数第一人称主体的个体意图的叠加。
集体意图是意图的一个子集,因此关于意图的信号刻画应该同样适用于对于集体意图的刻画,换言之,集体意图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类信号,而且这类信号更为特殊,因为它们的使用涉及多个行动者,是策略互动在心灵层面的直接体现;而集体意图在行动者心灵中的形成机制也是一个信号博弈的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形成之后的集体意图理解为一种高阶的信号。从个体的行动到集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信号的互动模式有了一种质的飞跃,除了一致性、融贯性等方面的合理性要求之外,策略互动所体现的信号之间的动态协同性成为了更高级的合理性要求。从信号博弈的角度出发,参与同一个集体行动的不同行动者所持有的关于该集体行动的集体意图能够最终得以形成,其博弈表现应该是相应的信号博弈的某个动态均衡状态的实现,这里涉及的信号来源可能不只是某些简单的、承载者为单数第一人称主体的个体意图,应该还会涉及参与该集体行动的行动者们各自对于这个集体行动的认知状态,比如对该集体行动的目标以及实现手段的理解,以及对于其他参与者的意向状态的判断等,而这些内容作为形成集体意图的信息来源,依然可以运用不同的信号去进行刻画。
信号博弈作为协同博弈的一种,其动态均衡的实现需要博弈各方的策略选择满足某种协同性,因此,博弈各方在选择策略时需要从团队的视角出发,考虑其他参与者的策略选择。对应到关于集体意图的论述,即是指集体意图作为某个协同博弈的动态均衡,其实现是一种团队推理的结果,换言之,集体意图作为一个较为复杂的信号博弈的均衡,其策略选择的逻辑起点是“我们”,而不是单独的“我”,这体现的是集体行动所特有的一种协同性,而这一点正好就是承载者为单数第一人称主体的个体意图在桥接心灵与行动时所不具备的特征。结合前文中的论证,集体行动能够得以成功实施的一个重要理性前提就是参与该集体行动的行动者们的集体意图之间的有效协同,这是集体意图原初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它不能被还原的关键所在。
而且正如上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集体意图也可以运用信号博弈模型与相关信息处理机制进行理解,那么这对于集体意图在技术层面上的体现意义重大,这也将会成为人工智能设计中的一个可能的理论支撑,尤其是对于具有人机协同功能的社会机器人的设计而言。真正意义上的人机协同,最终实现的肯定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行动,而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行动的最为核心的特质就是协同性,体现这种协同性的,也正是集体行动参与各方所持有的关于这个集体行动的集体意图。因此,如果集体意图的实现以及具体运作也可以通过信号与信号博弈去刻画,那无疑是为人机协同的技术实现提供了一种更为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关键是相比之前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基础在技术层面上的可实现性与可操作性更强。
七、结语:再论意图独特性
行动哲学界经历了几十年的争论,逐渐对意图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意向状态的独特性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而近年来随着信息哲学的不断发展,新的理论资源也在倾向于认可意图独特性的本体论地位,而且也强化了这种独特性对于理解意图本质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认知科学研究从实证的角度也逐渐加入到对于意图独特性的研究之中,这说明对于人类心灵与行动的理解,终究离不开一个关于意图的形而上学框架,并且这个框架是有其自身独特性的,因为这种独特性是基于意图对行动进行合理说明以及价值评判的基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