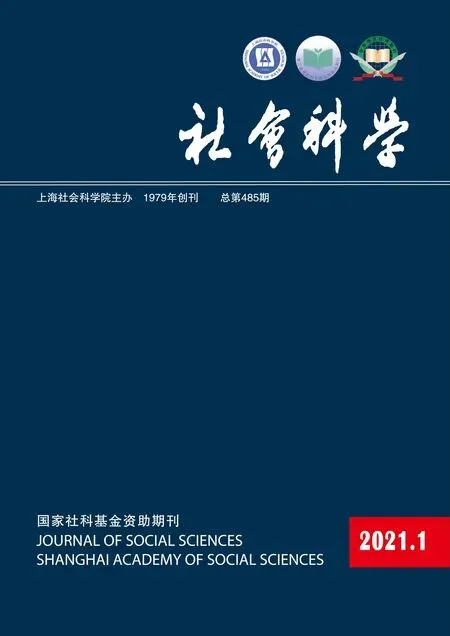休谟与社会契约论的理性主义
2021-11-24程农
程 农
按照传统的解读,休谟以批判社会契约论而著称,他的批判重点是契约与承诺的观念。在休谟的时代,英国政治思想中流行的契约论是经过辉格党通俗化的洛克理论,重点强调被统治者的自觉同意。休谟的批判被认为是在哲学上对这种理论的犀利打击。(1)关于传统解读的例子,参见刘训练等编译的《社会契约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David Ritchie, Ernest Baker的文章与Michael Lessnoff著作的第五章。边沁认为休谟的批判彻底摧毁了“原初契约”的概念。[英]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9页。然而,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界对契约论的复兴改变了这个局面。这个契约论复兴不再强调自觉的承诺与缔约,而是着重从利益权衡与博弈来说明制度的效用。(2)Will Kymlicka, “The Social Contract Tradition”, A Companion to Ethics, edited by Peter Sing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3,p.188.基于这种新的契约论理解,当代学者对休谟提出了新的解读,认为休谟的政治理论是“契约论式的”(contractarian)。(3)David Gauthier, “David Hume,Contractarian”,Philosophical Review, Vol.88, No.1,April 1979,pp.3-38.
休谟的确有一个从理性的利益考量与博弈说明制度的论述。当代的新解读有力地揭示了这个论述的原创性,改进了我们对休谟的理解。但是,本文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因此断言休谟的政治论述是“契约论式的”?他强调利益权衡的论述与他对社会契约论理性主义的排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追问这些问题就是在追问休谟究竟如何应对契约论的理性主义。
一、休谟的利益论述与当代的新解读
传统解读与当代解读的分歧提醒我们,休谟思想与契约论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为了便于讨论,我们需要先概括一下近代社会契约论的逻辑结构。近代社会契约论虽然有不同版本,但它们原则上都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人类利益说明国家等制度存在的理由。这个方面描述自然状态的困境,说明建立政府是基于利益计算的唯一合理选择,可以称为契约论的“利益论”。第二个方面则聚焦于自然权利、契约建国和政府的正当性问题。这个方面强调自然人天然独立,任何政治权威都必须获得被统治者的自觉同意。因为人的自由意志是同意概念的基础,我们可以将这个方面称为契约论的“意志论”。
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当然是复杂的,(4)很多论者强调这两个方面承担着不同功能,是互相补充的。例如A. John Simmons, “Justification and Legitimacy,” Ethics,Vol.109, No. 4, July 1999,pp.739-771。但也有论者强调两个成分之间的紧张,例如Deborah Baumgold, Contract Theory in Historical Context: Essays on Grotius, Hobbes, and Locke ,Leiden: Brill, 2010, chap.4.但与本文主旨相关的是这样一种关联:首先,契约论的意志论逻辑上预设了契约论的利益论。人们只有明确了创立政府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才可能进入相互承诺与缔结契约的过程。其次,意志论与利益论这两个方面逻辑上又都预设了人们普遍具有足够的理性能力。这个理性能力可能常常为欲望与激情所压制,但“自我保全”的欲望或者对暴死的恐惧可以唤醒理性自觉,激发理性能力。人们由此可以认清自身利益,发现解决办法,约束激情的冲动。本文所说的“契约论的理性主义”,核心就是这个有关人类理性能力的观点,而这个观点又与契约论的利益论述密切关联,因为诉诸利益动机必定意味着诉诸理性与反思的能力。为了讨论的便利,我们将社会契约论看作是涉及了三个层次:意志论、利益论、与有关人类完备理性的预设。
休谟与这三个层次是什么关系呢?一方面,休谟对意志论方面有集中的批判,对于自觉的契约和“承诺”的观念,他有系统的反驳。另一方面,休谟也很清楚契约论涉及人的完备理性的预设:“如果所有的人都具备完美的理解力,总是能认清自己的利益,那么就只有一种形式的政府能够得到人们的服从,那就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并为每个成员所充分盘察的政府。但这样完美的状态远远超出了人性的可能。”(5)Hume,“Of the Original Contract”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78,p.474.休谟知道,仅仅反驳意志论并没有触及契约论的根本,契约论更深的基础在于它的理性主义前提。只要坚持这种完备理性的预设,意志论的核心概念——同意——就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得到维持。
休谟对意志论与完备理性预设的反对都很明确,问题在于,他对契约论的利益论述究竟是怎么看的?
“利益”(interest)概念是一个近代发明。(6)Stephen G. Engelmann, Imagining Interest in Political Thought: Origins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在17世纪的社会契约论里,虽然从利益与效用看待政治的论述已经成型,但人们对“利益”概念的运用还处于早期阶段,自然权利、契约与意志的语言更加引人注目。系统独立的利益论述在18世纪才逐渐成熟,休谟本人就是这个趋势的典型代表。(7)Albert Hirschman, Passions and Interest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art One.
休谟知道近代契约论有自己的利益论述,也指出契约论那种近代自然法式的思维遮蔽了利益这个终极基础。他说:“如果细究那些自然法的作者,你总会发现,无论他们从什么原则开始,最后都肯定要在这里终结,要将人类的便利与需要看作是他们确立的每一个规则的终极理由。”(8)Hume, Enquiri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p.195.他对承诺概念的批判,典型地揭示了这种对利益基础的遮蔽。契约论的承诺概念似乎很清晰:为什么人们要服从政府?因为他们同意并承诺服从。但是休谟却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服从政府的理由是有过承诺,那么遵守承诺的理由又是什么呢?他犀利地指出,意志论错误理解了承诺这个行为的性质。它以为承诺是一个特定的心灵活动, 即“意愿承担某种义务”(willing an obligation), 以为单凭这个心灵活动就可以产生道德责任。在休谟看来,这种心灵活动纯属形而上学的虚构。承诺不是一个孤立自足的行为,而是人类为了确保相互协作而摸索出来的一种习俗性安排。依照这个安排,人们为了利益交换,彼此就将来的行为作出保证。所以,承诺这个行为本身不能产生约束力,它必须以社会有相应的习俗性安排为前提。遵守承诺需要理由,这个理由说到底就是利益考量。承诺不是重点,利益才是。只要政府能维持根本利益,人们无论当初是否有过承诺,都会服从政府。(9)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by L.A.Selby-Big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516-525.
某种意义上,休谟是排斥了契约论的意志论,保留了契约论的利益论。但是,在摆脱了近代自然法那套法律与意志的语言后,单单保留契约论的利益论述是不足以解释社会与政府的形成过程的。休谟不仅保留契约论的利益观点,而且实际上超越了它,发展出一个完全经验主义的利益论述。他强调人类社会的根本制度都是以利益为基础。他从人们的利益权衡与博弈来解释制度的形成与维系,并且把财产制度与政府都看作是通过利益博弈而达成的“默契性约定”(convention)。在休谟的时代,这个利益论述是高度原创的。但是,学界传统的诠释将这个利益论述不是并入功利主义思潮,就是纳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脉络。即便是晚近强调休谟与近代自然法传统的联系的解读,也不足以显示休谟利益论述的原创性。(10)这种晚近的解读认为,将休谟与近代自然法传统对立的传统看法是表面化的,休谟的正义与财产理论可以看作是世俗化与经验主义的自然法论述。参见Duncan Forbes, Hume’s Philosophic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Kund Haakonssen, The Science of a Legislator: The Natural Jurisprudence of 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传统解读的后果是,休谟的利益论述得不到清晰认识,他与契约论的利益论的关系也就模棱两可。更麻烦的是,鉴于利益权衡与人类理性能力的内在关联,如果休谟利益论述的内涵得不到澄清,它的理性限度得不到说明,那么休谟与契约论理性主义的关系就仍然含混不明,所谓休谟对契约论理性主义的批判,就只能是一个笼统浮泛的论断。
当代的解读改变了我们对休谟利益论述的认识。20世纪晚期,随着以罗尔斯为代表的道德与政治哲学在英语世界的复兴,契约论得到了某种形式的复活。在这个新动态里,契约论的概念有了改变:重点不再是意志论,而是利益论述;更重要的是,利益论也不再像近代契约论那样简单,而是发展成了新的系统论述。学者们放弃了自觉缔结契约的意志论图景,致力于从平等个体的利益推演与互动,来揭示制度的内涵与效用。当代的这种契约论论述在不同学者那里有不同的侧重点。一个典型的侧重点是将契约论当作一种理解规则与制度含义的思考方式,设想平等的个体根据对个人利益的理性考量,决定是否同意某种规则或制度。这个类型将契约论看作是“假设性的”,是基于理论家视角的思考,不涉及真实生活里的人们,因而就不需要预设人们普遍具有强大的理性能力。(11)罗尔斯与高蒂尔都是这个侧重点的代表。参见John Rawls, John,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David Gauthier, Morals by Agreemen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这种类型的讨论也会涉及博弈论。另一个典型的侧重点是根据博弈论来改进契约论的利益推演,强调一个制度的形成与维系实际上是人们经过利益博弈达成了某种协调的格局(coordination)。平等的个体基于各自利益的盘算,在彼此的持续互动中能够摸索出一种利益协调的局面,形成一种互惠的“默契的约定”(convention)。这种“默契的约定”是通过人们的持续互动而逐渐演化出来的,无需诉诸自觉的承诺与契约,也不需要预设人们具备完备的理性能力。然而,因为这个利益协调的格局是互惠的,原则上可以说得到了所有参与者的默会的“同意”。这种基于博弈过程的利益推演,本质上是对真实过程的一种逻辑简化与重构。它不可能精确重现复杂的现实,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12)典型例子是Jean Hampton, 参见其Hobbes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Tradit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olitical Philosoph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1998.
当代契约论的这种发展,与休谟的利益论述有明显的重合,激发了对休谟的重新认识。一方面,休谟有关利益是制度基础的论述早就勾勒出当代学界有关“假设性契约”的基本观点,即平等的个体基于自我利益权衡对制度进行理性选择,这样产生的制度具有明确的互惠性(mutual interest 或mutual advantage)。另一方面,休谟从利益权衡对制度形成的描述,明显地具有博弈论特色,尤其是吻合通过重复博弈以求得“协调”(coordination)的博弈类型。休谟提出的“默契性约定”(convention)的概念也准确描述了这种“协调”的成果。基于这些理由,一些学者提出,休谟的政治观点实际上是契约论式的(contractarian)。有学者甚至认为,鉴于休谟的利益论述既避免了意志论的麻烦,又保留了契约论的核心意思,因而与霍布斯与洛克相比,他是更加精致的契约论者。(13)对休谟的利益论述作契约论与博弈论式解读的代表学者有David Gauthier(即高蒂尔),Jean Hampton 和 Russell Hardin。Gauthier,见前引“David Hume, Contractarian”; Hampton,见前引Political Philosophy,以及The Intrinsic Worth of Persons: Contractarianism in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Daniel Farnha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p.6; Russell Hardin, David Hume: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i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休谟的利益论述直接影响过博弈论的某些发展,见David K.Lewis, Convention: A Philosophical Stud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p.3。这个论述也影响了一些公共选择论者(如布坎南)与经济学家(如萨格顿)。从博弈论式思路解读休谟的较新的代表著作,参见Andrew Sabl,Hume’s Politics: Coordination and Crisis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这个新解读揭示了休谟利益论述的核心特质,改进了我们对休谟的理解。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改进,休谟与社会契约论理性主义的关系问题重新被突显出来。我们不得不追问:休谟的政治论述可以用“契约论式的”来概括吗?他究竟怎么看待人的理性能力问题?当代解读着重从博弈论模式来理解休谟的利益论述。博弈论的确与近代契约论不同,没有预设人有完备理性,甚至会强调理性的有限。但是,博弈论的焦点是人们基于利益的互动,它预设了人们一直在自觉地基于有限信息进行理性盘算与决策,人的行为都被看作是追求利益的策略性行为,制度也被看作是利益博弈达成的默契性约定。这个图景的本质依然是把人看作是理性人,一直在理性地权衡得失,按照理性的选择来行动。虽然没有预设人的完备理性,但这个论述依然是强烈理性主义的。用这种理性主义的分析来诠释休谟,是否会导致对休谟观点的歪曲?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重新梳理休谟对契约论理性主义的批判。
二、休谟政治论述的两个层次与两类问题
要解释休谟对契约论理性主义的确切应对,必须从休谟政治论述所采取的形态说起。西方近代思想拒绝了古典的自然概念,但依然以存在普遍的自然人性为基本前提。近代理解的自然人性以自然科学为参照,强调人为欲望和激情主导,理性只是人追求欲望满足的工具。基于这种人性理解的政治论述是非历史的。对于从不变的自然人性如何能够产生复杂的人类制度这个问题,近代契约论实际上是诉诸人的理性来解决。无论是否明说,近代契约论逻辑上都需要设定人们普遍可以具有高度的理性能力。理性自觉的人们可以理解总体形势、自己的根本利益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想避免做这样理想化的预设,明显的替代思路就是诉诸人们的社会互动与历史演化, 说明理性有限的人们如何通过长期的交往互动逐渐摸索出各种制度。这也正是18世纪的典型进路。启蒙时代谈论社会互动与历史演化,以承认存在共同的自然人性为前提,描述的是禀有相同自然人性的人们的互动的历史。这种论述强调人类社会有着类似的演化轨迹,从野蛮走向“进步”与“文明”。借用康德的概念,它描述的是人类的“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14)Kant, “Idea of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ed. Hans Reiss, trans. H.B.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41-53.
休谟因为其特定的人性论哲学,格外需要诉诸社会演化这种论述形态。(15)Norman Kemp Smith, “The Naturalism of Hume (I)”, Mind, New Series14,No.54,April 1905,pp.149-173;“The Naturalism of Hume (II)”, Mind 14, No.55,1905, pp.335-347.他的人性论哲学激烈地强调理性的限度,强调主导人性的是本能、情感与观念联想。在他看来,人类生存所依赖的世界框架是由人性自然给定的一系列本能、倾向与情感套路决定的。自然人性的固有倾向不仅使得我们必然设定实质自我、外部世界与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而且意味着我们的观念联想遵循一定的套路,我们的情感作用也呈现一定的模式。休谟将这些人性自然给定的内容称为“人性的原始原则”(the original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或“原始特性”(original qualities)。(16)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by L.A.Selby-Big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295,280.这些人性自然的倾向与原则,对于我们来说是给定的事实,不可能从理性予以论证或说明。相反,人的理性需要依赖这个以本能、感觉和情感为基础的人性框架,在这个框架里运作和发展。(17)Norman Kemp Smith, The Philosophy of David Hume: A Critical Study of Its Origins and Central Doctrine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但是,在这些人性自然的倾向与复杂的人类社会与政治现象之间,显然存在着一道鸿沟,休谟不可能像契约论那样,指望通过人的理性自觉来跨过这道鸿沟。他只能转向人的社会与历史的维度,通过人们的交往互动的持续过程来解释社会与国家的产生。启蒙时代的人类进步史常常是泛泛而谈,但休谟因为对理性限度的系统强调、对情感与观念联想套路的详细描述,就面临着非常具体的压力,要给出一种详实的论述,他必须具体地解释,如果人性如同他所理解的那样,那么具有这些特定情感与联想倾向和有限理性的人们,如何通过相互交往和持续地互动,一步步演变出各种复杂的习俗、惯例与制度,产生财产秩序与政府。休谟在道德与政治方面最原创的工作,都是在这个具体解释的努力中产生的。(18)John B. Stewart,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David Hu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由此,休谟政治思想的基本形态就是一种基于自然人性的社会演化论述。这个论述在《人性论》第三卷有系统地展现,是休谟的《道德原则研究》以及各种政治论文与历史著述里的基本背景。
对本文主题特别重要的是,休谟的这个社会演化论述涉及两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论述的焦点是理性的利益考量。《人性论》第三卷“论正义与财产权的起源”、“论政府的起源”、“论政治忠诚的根源”等章节是典型例子。这个层次关注的是人们基于利益考量的互动博弈,揭示人类制度的终极理由都是利益,其中的核心制度——财产秩序与政府——更是为了维系社会本身,为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即和平与安全。(19)通过契约形成制度的观点,可能运用于任何人类基本制度与规范。对于其适用范围,契约论者的看法差异很大。在休谟的社会演化论述里,社会秩序的关键是财产制度,而政府的任务就是维护财产制度。在讨论这两个主题时,他都反驳了相关的契约论观点。所以,本文不仅要涉及他的政府论述,而且也涉及他的财产论述。他对财产秩序起源的博弈论式描述是这个层次的典型例子:两个人划船可以通过动作感应很快达成节奏的协调,无需刻意地约定。与此类似,在人类早期的小型社群里,围绕财产的冲突促使人们直接意识到维护财产稳定的重要性,也直接感受到没有规则的危害。这种基于利益考量的面对面互动逐渐产生了有关财产稳定占有的“默契性约定”。(20)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by L.A.Selby-Big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490.
休谟社会演化论述的第二个层次的焦点转移到了人性的情感与观念想像方面,描述情感与观念联想的各种给定倾向与原则如何影响各种制度的塑造。《人性论》第三卷里“论决定财产权的诸规则”与“论政治忠诚的对象”等章节是典型例子。在这个层次里,休谟强调感觉与情感活动在复杂的社会互动中会呈现出一定的套路,彷佛遵循着某种“通则”(general rules)。(21)Thomas K. Hearn, “‘General Rules’ in Hume’s Treatis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8,pp.405-422.我们不可能证明这些自然倾向与通则有理性的理由,但它们为人性普遍具有,因而在具体制度的塑造上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休谟社会演化论述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对应着两类不同的问题。第一个类型的问题追问: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财产秩序?我们为什么需要有一个政府?这种问题是原则性的,只涉及“财产制度”与“政府”的根本含义。第二个类型的问题则涉及制度的具体规则或形式,比如财产制度的具体规则,或者政府的具体形式与领导人人选。第一类问题是原则性的,答案也是唯一的:没有财产制度与政府,人类就不可能在一起共同生活。它们维护的是人类最根本的利益:和平与秩序。回答这一类问题无须涉及特定社会的具体内容,只需要基于人性根本利益的理性推演,这也就是休谟社会演化论述第一层的工作。第二类问题涉及财产秩序或政府的具体形式,这类问题显然有多种可能答案。休谟强调,这类问题不可能从理性的利益推演得到普遍认可的解答。在解决这类问题的实践中,情感、想像与习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就是他的社会演化论述第二层次要做的工作。
区分两类问题、区分社会演化论述的两个层次,这个格局构成了休谟政治论述的基本框架。休谟指出:“使得我们愿意服从政治权威的是利益考量。但也正是为了这个利益,我们在选择服从哪个权威的问题上,不能再诉诸对这同一种利益的考量。我们将自己与某个形式的政府绑定(bind us down to),与某个特定的权威绑定,而不允许自己追求绝对的完美。”(22)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by L.A.Selby-Big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555.这段话鲜明地把利益考量限制于解释为什么要有一个政治权威,断言政府形式与领导人选问题不能直接诉诸利益权衡。对于财产制度,他的观点同样明确:“财物归属要清晰区分,这种区分要稳定持久,这是社会诸利益所绝对要求的,由此就产生了正义与财产权。至于某种财物归属于哪个特定的人,这个一般说来无关宏旨。这些具体规则通常是由非常无关紧要的观点与考虑来决定的。”(23)Hume, Enquiri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p.309.所谓“无关宏旨”(indifferent),所谓“无关紧要”(frivolous),同样都是强调,对于具体的财产规则不要强求以利益推演追求理性的答案。
这里的关键在于,休谟的第一类问题是底线的问题,他是将利益考量限制在最底线的问题范围里。现代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将政治的目标降低到底线问题,以“和平、安全、舒适的生活”为人类的根本利益。在这点上,休谟与霍布斯、洛克是相似的。但是,霍布斯、洛克都认为只有通过理性论证的特定制度才能保障这个根本利益,休谟却认为,如果在具体制度上一味追求理性标准,就很容易危及根本的利益、危及和平与秩序。 导致这个立场的要害显然是休谟对人类理性限度的高度敏感。休谟对契约论理性主义的批判,已经根本地体现在这两个层次与两类问题的框架里。他虽然有一个从利益考量与博弈说明制度的论述,但是他的这个框架已经严格地限制了这一论述的适用范围。
三、第一类问题与对利益论述的限制
休谟将其利益论述原则上限制在对第一类问题的讨论里。本节将说明,甚至在第一类问题的范围里,休谟对其利益论述可能由于过度理性化的问题也表现出高度的警觉,对利益论述的含义施加了若干特定限制。
近代契约论的利益论述描述了自然状态的总体困境,勾勒了社会与国家的概念,论证社会与国家符合人们的根本利益。如果这个论述仅仅被当作理论家的思考,仅仅被看作是对制度的理性逻辑的揭示,不涉及政治实践中的行动者,那就不需要预设人们具有完备理性。问题在于,近代契约论自一开始就不仅要追寻人类制度的理性逻辑,而且试图解释这些制度如何地人为产生,并且试图直接教化人们,指导实践。这就意味着它不仅是理论家的理论探讨,也涉及行动者的视角,涉及人们是否能够具备相应理性能力的问题。
在休谟看来,近代契约论的这种理性主义论述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财产制度(休谟“社会”概念的核心)与国家都不是显而易见的、自明的概念。实际上,它们都是相当复杂的事物,需要在长期实践中缓慢形成,逐渐地为人们所理解。休谟揭示,最早的人们是在同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里,一方面逐步摸索出这些制度的概念,另一方面逐步意识到这些制度的终极理由就是自己的根本利益。
他说:“为了组成社会,不但需要社会对人们是有利的,而且还需要人们觉察到这些利益;人类在未开化的野蛮状态下,不可能单凭研究和思索得到这个知识。对这类根本需要的解决办法是遥远而模糊的。幸运的是,与这类需要相关的另外一种需要却有着近在眼前,容易看到的应对办法。因而可以把这种需要看作是人类社会最早和原初的原则。”(24)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by L.A.Selby-Big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486.这个需要就是两性间的欲望,它会导致家庭与生育,形成人类社会的开端。休谟这里的意思很清楚:人们不可能一开始就能理解何为社会,何为财产秩序。他们只是在应付当前需要的尝试中不自觉地走向那个方向。财产制度是逐渐形成的,是缓慢地获得力量的。(25)Ibid.,p.503.
同样,政府不是一个简单自明的概念,它涉及行政、司法、财政机制的建立,武装力量的塑造,整个社会关系的转型。休谟说:“不能期望人们事先就能发现这些道理,或预见它们的作用。政府的起源毋宁是不经意的,摸索尝试的。”(26)Hume, “Of the Origin of Government”,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78,p.39.国家的起源应该是一个曲折的、不期而然的过程。休谟认为,很可能是部落之间的战争促使部落产生了最早的政治权威。这个最初的权威完全是为了特定战事的目的,一旦冲突结束,军事首领就丧失权威。但是,人们由此第一次感受到权威的好处。在以后发生冲突与纠纷时,就容易再去诉诸权威。
休谟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各种特定事件不断积累的过程:“首领每次的权威运用必定都是针对特定的事端,都是由眼前的迫切问题引发的。人们感受到从这些权力干预中产生的便利,使得类似的行为日益频繁。通过这种频繁的权威运用,民众逐渐对权威产生了一种脆弱的、习惯性的默认,如果你乐意,也可以把这叫作自愿地接受。”(27)Hume,“ Of the Original Contract”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78,p.468.此时的权威还不等于政府成型,而是“还在脆弱的阶段。进一步地发展是确保有财政收入,这样首领就能对行政组织的人员给予报酬,对桀骜不驯的人施加惩罚。在达到这个阶段之前,首领每次的施加影响都只是一个特定事件,是基于特定形势,针对特定问题的”(28)Hume, “Of the Origin of Government”,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78,p.40.。
基于对历史复杂性和理性限度如此强烈地体认,休谟对自己的利益论述施加了三重限制。首先,他的利益论述的一个基本方面,是从理论家视角,也就是上帝的全知视角进行的。这个方面超越行动者的有限视野,揭示财产制度与政府的理性逻辑,揭示制度与利益的根本关联。休谟从“资源的有限”与“利他心的有限”来推论财产制度的必要,就是这种论述的一个范例。这种思考不涉及行动者的视角,也就不涉及人们理性能力的问题。休谟对这两个视角的差异高度自觉。他在许多地方强调利益是制度的“基础”或“终极理由”,这些论断是基于理论家的视角;他又在许多地方谈论利益是“最初动机”或者人们“对利益的觉察”,这些段落显然是从行动者的视角描述实践过程。
其次,当休谟从行动者的视角描述利益博弈的过程时,他往往明确地把范围限制在人们面对面互动的情境里。这种面对面互动的典型例子就是人类的早期小型群落。早期小型社群是熟人社会,人们在面对面的互动里容易直观地认识制度与利益的关联。一旦进入大型社会,制度与个人利益的联系就变得间接而模糊。财产制度与政府作为一个根本制度能够带来什么利益,个人很难直观感受:“我们在自己的行动中往往看不到我们从维持秩序里所得到的利益”。(29)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by L.A.Selby-Big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499.
第三,甚至即使就早期小型社群而言,休谟也意识到,利益博弈的解释只是一个简化的逻辑模拟。他深知“所有政治社会的起源都远不是这样精确与规整(much less accurate and regular)”。(30)Hume,“Of the Original Contract”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78,p.474.制度的实际演化过程曲折复杂,常常是不期而然的结果。自觉的利益盘算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四、第二类问题与对利益权衡的排除
如果说在讨论第一类政治问题时,休谟对契约论理性主义的批判是间接的,那么在讨论第二类政治问题时,这种批判就是直接的了。他这里的基本立场就是,在第二类问题即具体制度形式的问题上不能诉诸理性的利益权衡,其根本理由就是人类理性的限度。他写道:
……显而易见,人们如果在这种特定问题上根据他们对特定利益——公共利益或者私人利益——的看法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们就会陷入无穷的混乱,使一切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丧失效力。每个人的私人利益是不同的,而公共利益本身虽然不会因人而异,可是由于各人对公共利益会有不同看法,诉诸公共利益也会导致同样严重的纷争。(31)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by L.A.Selby-Big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555.
休谟第二类问题与第一类问题不同,它们涉及具体制度安排。这类问题没有唯一解,而是有多种可能方案。更重要的是,在这类问题上以理性的利益权衡来寻求答案,实际上就是要求对一个社会的利益状况进行通盘的判断,对一个特定规则或者特定制度的表现作出总体的评价。休谟强调,人类事务复杂曲折,除了少数极端情形外,人们对通盘状况的判断几乎总是会有尖锐分歧,而这样的意见争执,很难有一个理性的解决办法。“理性的指导太不确定,总是要面临怀疑与争执”;(32)Hume, “Of the Coalition of Parties”,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78,p.494.“政治上的争论在许多时候是得不出结论的”。(33)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by L.A.Selby-Big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562.剧烈而无解的争论会动摇秩序,危及和平。
在休谟眼里,公共利益与事务究竟是如何复杂呢?他的社会演化论述指出,人们只能在早期小型社会里可以直接感受规则与自身利益的关系,一旦进入大型社会,群体事务错综复杂,事情的因果链条也漫长曲折,个人就难以直观地理解公共利益的状态。首先,休谟强调,试图以理性标准来选择具体的财产规则,其典型的方式就是:要么以是否取得最大利益与效用来决定财产归属,要么证明某个个体因为其特定品质或才能而“应得”某个特定物品。(34)Ibid.,p.502.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是另一种例子,他试图根据人是否施行了一个特定行为(即劳动)来决定一个物品的归属。(35)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sect.27.休谟强调,这些方式都意味着单独衡量每一个财物的归属,而其标准又都是含混的。(36)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by L.A.Selby-Big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502, p.506.“它很容易导致无休止的争执,而人们在判断这些争执时又会非常偏私与激动。所以,奉行这样一个含混与不确定的规则,人类社会的和平就绝无可能。”(37)Ibid.,p.502.更重要的是,不能根据单个行为的后果是否有益来决定是否要维护一个制度。一个社会的财产秩序,是作为一个规则体系而起作用的,其涉及公共利益的总体效应,个人难以直观地把握。休谟竭力渲染公共事态的这种曲折复杂:“单独的一个正义行为常常(frequently)违反公益;而且它如果孤立地出现,而不伴有其他行为的话,它本身就可以危害社会。”对恶人履行还债的义务就是这样的例子。“益处与害处是不可能分离的。财产必须稳定,必须被一般的规则所确定。在某一个例子中,公众虽然也许受害,可是这个暂时的害处,由于这个规则的坚持执行,由于这个规则在社会中所确立的安宁与秩序,而得到了充分的补偿。”(38)Ibid.,p.497.在对特定政府形式的判断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休谟强调:“政府的事务总是涉及变化多端的情势。一个强有力的执政长官的权力行使,在一个时候可能是有利于公众,而在另一个时候又可能成为有害的和暴虐的了。”(39)Ibid.,p.563.除了政府明显等同于暴政的极端情况外(下面会讨论这个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政府的施政如何影响公共利益,显然不是好坏分明的,人们对此会各有各的意见。
公共事务的曲折复杂是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人性在感受与认知上的自然弱点。休谟反复强调,自然人性普遍存在一种基本倾向:“人类总是强烈地趋向于追求眼前利益,而忽略间接与遥远的利益;而且他们也不容易因为担心一种遥远的灾祸,而抵制他们可以立即享受的任何利益的诱惑。”(40)Ibid., p.539.休谟将此倾向称为“人性的自然脆弱”(natural weakness of human nature)或“灵魂的狭隘”(narrowness of soul)。休谟描述的这个倾向比古典思想谈论的那种 “意志薄弱”(akrasia)要更加复杂,因为它也涉及人类感觉与认知能力的局限。他喜欢以视觉对远近物体的不同呈现来形容人们认识与感知上的局限。“人类是大大地受想像所支配的,他们的感情多半取决于他们对任何对象的观察位置与角度,而不是取决于这个对象的真实的、内在的价值。”(41)Ibid., p.534.政府与秩序所能带来的长远利益,具有一种根本的间接性与模糊性。人们更容易执迷于各自的眼前得失,把它当作是首要利益。
这里的关键在于,休谟这些讨论改变了第二类问题的重点。按照通常的认识,探究财产制度或政府的具体形式,就是探究什么样的制度形式才合乎利益,合乎理想。但是,鉴于人事的复杂与理性的限度,休谟是如此担心这种追求会导致争斗,以至于主张:在制度的具体形式上,需要操心的首要问题是避免引发争执,是众人如何达成共识。共识未必合乎理性,但只要有共识,就可以避免争斗。
这就引出了本节的第二个问题:人们如何在第二类问题上达成共识呢?休谟的答案是:“我们必须依据通则来处置此事。”(42)Ibid., p.555.情感与观念联想的作用方式可以帮助人们在这类问题上达成一致。情感作用与观念联想有其人性给定的套路,彷佛遵循着某种“通则”。我们不可能根据是否产生最大的利益,或者根据特定个人的“应得”,来为这些“通则”提供根本理由。但是,这些观念联想与情感的作用方式,的确提供了“汇聚点”(focal point) 以聚集人们的观点,使他们能比较容易地达成一致。能够提供“汇聚点”本身就是我们奉行这些“通则”的理由。(43)“focal point”是借用博弈论学者谢林的概念。博弈论描述人们自觉地在各种可能选项中进行理性选择,有过度理性化之嫌。实践中的人们为情感与联想的通则所引导时,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个引导的含义。但我们从旁观者反思的立场,可以借用这个概念揭示这个过程的含义。见Thomas 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57.
在谈到具体的财产规则时,休谟指出:“我倾向于相信,这些规则是由观念联想,或者我们意识与概念的某些比较肤浅表面的特质所决定的。”(44)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by L.A.Selby-Big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504.在实践中,财产的具体规则往往是通过人性的各种 “通则” 来得到解答的。比如,财产的先占权原则是人类社会普遍接受的,而休谟就是以情感“通则”来解释这个现象。又如,人们一般都承认长期占有或者时效(prescription)这个原则。继承权也是确定财产归属的典型方式。(45)Ibid.,pp.501-513.在这些情感与观念联想的“通则”作用下,在具体情境里,人们会普遍觉得在某种特定物品与某个特定个人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容易有这种感受,采纳它们就可以避免争执,达到稳定财产占有的根本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财产权不是在对象中存在着的实在物,而是情感的产物”。(46)Ibid.,p.509.
政府问题也是类似的情形。契约论总是设想人们可以“从零开始”(start from scratch),追求合乎理想的政府形式。而休谟强调,常人在政治实践中往往是在情感与观念联想的“通则”的作用下,决定自己对当前政权的态度。在当时欧洲的政治实践中,当前的占有(present possession)与继承权都是“通则”的例子,它们帮助人们对当前的特定政府形成一个一致的态度。休谟特别强调,长期占有(long possession)是一个突出的“通则”。只要一个特定政府足够长时间的存在,其治下的人们就很少会质疑其正当性。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强调时效与习惯在塑造政治态度方面的作用。“时间在人们心理上逐渐地起了作用”,人们习惯于对眼前政权的服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过习惯,使任何情感对我们有一种更大的影响,或使我们的想像更为强烈地转向任何对象”。(47)Ibid.,p.556.情感、联想与习惯的作用,集中体现为对当前成例与传统的尊崇,休谟曾经对此总结道:“统治的真正规则就是尊崇当下既定的实践状况。”(48)Hume, “Of the Coalition of Parties”,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78,p.498.同样根据这个意思,他认为,如果一个政府有一套经历长期实践的根本法,那么就这个根本法能够为人们提供共识而言,就是应当尽量尊崇的。(49)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by L.A.Selby-Big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561.
总之,在契约论的理性主义看来,政体与财产规则的问题是一个在多种可能方案中进行理性选择的问题。而在休谟看来,这首先是一个如何避免争议、求得共识的问题。在这个第二类问题上,诉诸各人的理性权衡只会导致争执与冲突,而情感与观念联想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们能够提供意见的“汇聚点”,帮助人们达成共识、避免冲突。
五、常规政治、极端情形与反抗权
休谟的上述立场显然会引发一个问题:如果当前的政府蜕变为暴政,人们该怎么办?在我们对安全与财产的根本利益的关心与我们基于情感与习惯的服从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了解了休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就可以更加确切地了解休谟批判契约论理性主义的要义。
休谟明确声明:人民在遭受暴政时应当反抗,就此原则而言,自己与契约论没有分歧。(50)Ibid.,p.550.这完全合乎他的原则立场:人们接受政府统治的原因,是为了秩序与安全。原因停止,结果也就停止。政府变成了极端压迫,政治服从的责任也就自动无效了。他说:“在极度专制与压迫的情形下,甚至对于最高权力进行武装反抗也是正当的。”(51)Ibid.,p.553.
休谟质疑契约论的地方,还是在于契约论处理这个问题的理性主义方式。休谟认为,大多数政府在大多数时候,尽管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如人意之处,但大致都能履行维持秩序与和平的基本功能。政府总体上堕落为暴政,是一种例外情形,是一种极端的形势。基于这个判断,休谟提出要区分政治生活的常规状态与极端情况。暴政一旦发生,人性自然不会束手待毙,我们不必操心人们面临暴政应当如何处置,我们需要操心的是在常规状态里如何维持和平与秩序。(52)Ibid.,p.552.
契约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几乎与休谟正相反。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将注意力对准休谟眼里的极端情况,以极端情况为基准,要求人们时刻警惕暴政的发生。这个立场实际上否定了常规状态与极端压迫的区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立场将休谟眼里的极端情况看作国家政治中常规的可能。
契约论与休谟的观点之所以如此对立,根本原因还是双方对人性理性与情感的不同理解。在对待政府态度的问题上,契约论不相信人性自然情感的反应。洛克强调,人性的倾向容易趋于被动服从,面对暴政也很难轻易反抗,所以他们需要契约论的鼓励来实施自己反抗的权利。(53)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sect.223.契约论诉诸人们的理性自觉,要求人们自觉审视政府的表现,自觉以公共利益总体状况来对政府表现作总体评估。这个观点又意味着预设人们普遍具有足够的理性判断能力。针对契约论的这种理性主义逻辑,休谟强调人类理性的限度,他的观点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他相信自然人性在面临暴政时不会坐以待毙,无须时刻保持理性的警惕;另一方面,他更担心人们在自觉意识里对政府时刻警惕,会在根本上伤害政治秩序,违背建立政府的初衷。
就前一个方面讲,只要政府履行职能没有出现严重问题,大多数人是不会思考政体是否正当这样的问题的。(54)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by L.A.Selby-Big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555.日常实践中的人们忙于应对眼前的麻烦,操心各种当下的得失。他们即便就某个公共问题发生争执,也是就事论事,不会上升到对整个政权进行质疑的层次。但是,人性对于自身受到的侵害很敏感。(55)Ibid.,p.499.一旦政府堕落为暴政,越来越多的人们会遭受各种损害,这种普遍性的遭遇会唤醒人们对根本利益的自觉,诉诸反抗。他认为,“它 [契约论的反抗权理论] 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在[自卫反抗]的极端必要性迫近的时候,没有人会因为没有法律宣言的指导,就茫然失措,无法发现恰当的矫正方式。即便那些在平日通过经院式推理否定所有反抗的人,在严格遵循那些虚假原则就肯定带来毁灭的情形下,也会诉诸这个自然的呼吁[按:指反抗]”。(56)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Vol.6, Indiannaplis: Liberty Classics, 1985, p.294.
就后一个方面讲,休谟触及了一个悖论性的现象:人们根据政府是否能维护根本利益来决定对它的态度,但反过来看,政府是否能顺利履行职能的一个必要前提又是人们信任政府、积极配合。在休谟看来,契约论致力于强化人们对当前政府的警惕,要求人们时刻以根本利益是否得到满足来评估这个特定政府,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如果一个社会中多数人都处于这样的自觉意识里,那就意味着人们普遍对政府持不信任的态度,意味着政府时刻都在被以怀疑的眼光审视。一个时刻被反思、被审视的服从是非常脆弱的服从。这个现象本身就足以使得社会脱离通常的状态,整个政治秩序已经开始不稳定了。休谟甚至批评说,契约论不区分常规状态与极端情形,一味宣传对政府的警惕,会在人们中间塑造出“一种叛逆的倾向”(a disposition to rebellion)。(57)Hume, “Of Passive Obedienc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474,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78,p.490.而且人性本来容易偏重眼前得失:“强大的眼前利益可能使我们无视自己从维持社会的和平与秩序里获得的长远利益,起而叛乱。”(58)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by L.A.Selby-Big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543.
基于对常规状态与极端情形的区分,以及对人性的理解,休谟提出,政治理论家应当着意做的不是宣传反抗权,而是鼓励对当前政府的服从。他强调:“通常的规则(the common rule)就是要求服从,只有在严重暴政与压迫的情形下,才能有例外发生。”(59)Ibid.,p.554.他解释说:
这里我必须承认,我将总是倾向于站在那些人一边,他们拉紧政治服从的纽带,把放弃服从看作是公众面临暴力与僭政高度危险的绝境下最后的步骤。…… 鉴于政治服从是常规事态下我们的责任,应当着重就此点进行教育。最荒唐不过的就是充满焦虑与担忧地去陈述所有那些允许反抗的情形 。…… 比起忙于揭示特殊的例外,理论家更应当去传播适合一般情况的学说(the general doctrine)。(60)Hume, “Of Passive Obedienc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78,p.490.
到这里,休谟有关“尊崇当下既定的实践状况“的观察,已经发展为明确的政治建议。
结 论
本文试图论证,休谟对契约论理性主义有一个系统批判。这个批判的关键是对自觉的利益推演在人类实践中的地位予以严格限制。休谟的核心意思是:第一,社会的秩序与安全是如此重要,又是如此脆弱,以至于我们不应当在制度的具体形式上,还去追求理性的利益推演。因为理性权衡在这类问题上必定导致分歧与争执,危及秩序与安全这个根本目标。第二,在确定制度的具体形式时,问题重点不在于是否符合理性权衡,而在于如何避免纷争、找到共识。人性共同的情感与观念联想模式之所以重要,既有的习惯与实践之所以重要,都是因为它们无须借助利益推演就能够为形成这种共识提供自然的“汇聚点”。
这个论述无疑有强烈的保守主义特征。保守主义强调秩序,强调历史演化,强调习惯与成例,警惕从理性的抽象原则来改造现实。这些观点在休谟这里都有鲜明体现。
不过,这个保守主义并不否定休谟思想的自由主义特征。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略指出两点:第一,休谟强调秩序与安全的关键是财产秩序,这里已经蕴涵了他对个人自由的基本关怀。近代契约论将自由首先看作一个原始事实,自然人有“天然自由”。社会与政治意义的自由都以此为依据。休谟则认为,自由不是先验给定的,而是在人类社会的自然演化中产生的一种社会与政治状态,而其核心就是财产秩序。洛克与休谟在自由概念上的分歧,典型地体现于两人的财产理论。洛克的财产权是基于自然人的个人劳动,而休谟的财产权是由社会演化产生的财产制度界定出来的。第二,休谟也关心进一步的政治与宗教自由,但他对这些自由有明确定位:“自由是对社会的完善。…… 权威却对社会的存亡不可或缺。”(61)Hume, “Of the Origin of Government”,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78,p.41.两者如果冲突,社会存亡当然是优先考虑。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保守型的自由主义。休谟与契约论的对立是两种类型的自由主义论述之间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