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关于“词”的修辞语法功能阐释
2021-11-23毛毓松
毛毓松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汉代是文字训诂学的初创期,已经开始对实词、虚词进行分类,训释虚词已有专门的术语。西汉毛亨《毛诗诂训传》(以下简称《毛传》)把《诗经》中不具实义即前人所谓“不为义”的词释作“辞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易“辞”为“词”,并特立司部,给“词”作专条解释:“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言。”[1]对某个“词”,也有明确的界定,如“矣,语已词也”,“尔,词之必然也。”许慎所说的“词”就是虚词。
清代文字训诂学大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段注》),对“词”作出了全面而又精辟的阐释。他在“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言”下注云:“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词。此语为全书之凡例。全书有言‘意’者,如‘,言意’,‘出欠,无肠意’,‘啬欠,悲意’,‘亻然,膬意’之类是也。有言‘词’者,如‘日欠,诠词也’,‘者,别事词也’,‘皆,俱词也’,‘,词也’,‘鲁,钝词也’,‘智于,识词也’,‘曾,词之舒也’,‘乃,词之难也’,‘尔,词之必然也’,‘矣,语已词也’,‘矧,兄词也惊词也’,‘旡咼,屰恶惊词也’,‘,屰鬼警词也’,‘臮,众与词也’之类是也。意即意内,词即言外。言意而词见,言词而意见。意者,文字之义也;言者,文字之声也;词者,文字形声之合也。凡许之说字义皆意内也,凡许之说形、说声皆言外也。有义而后有声,有声而后有形,造字之本也。形在而声在焉,形声在而义在焉,六艺之学也。‘词’与辛部之‘辞’,其义迥别。辞者,说也,从辛。辛犹理辜,谓文辞足以排难解纷也,然则辞谓篇章也。词者,意内而言外,从司言,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1]429-430又在“从司言”下注曰:“司者,主也。意主于内而言发于外,故从司言。”[1]430
本文以段玉裁此注为基础,结合段氏其他注释,对《说文》“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言”的阐释与理解进行讨论。
一、《段注》对“词”的性质特征的理解及词、辞含义之别
《说文》“词,意内而言外,从司言”的含义,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段氏的解释是:“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词”“意者,文字之义也;言者,文字之声也;词者,文字形声之合也”“意即意内,词即言外。”“词”是个从司从言的会意字,《说文》“司”篆云:“臣司事於外者”,徐锴《说文解字系传》“词”下云:“故於文司言为词。司者,臣主事於外也。”[2]316段氏在“从司言”下注曰:“司者,主也。意主于内而言发于外,故从司言。”因为“意主于内”,故段谓“意即意内”;“言发于外”,故段谓“词即言外”。这都在说明“词”无实义而有语法意义的虚词性质。段氏对“词,意内而言外”的理解,虽然只是一家之言,所述不够明确。但段氏此注把“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言”最终归结为“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则十分清楚地解释了“词”的性质特征及修辞语法功能。所谓“摹绘物状”,是说一部分“词”有绘声绘色地揭示事物状态的修辞作用;所谓“发声助语”,则完全是在阐释“词”的各种语法功能和修辞功能。
“词,意内而言外”,这是许慎对虚词所下的一个定义,也是关于虚词的一个总纲,纲下有目。段氏在《说文叙》“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下注曰:“建类一首,谓分立其义之类而一其首;同意相受,谓无虑诸字意旨略同,义可互受相灌注而归于一首……有纲目其辞者,如‘词’为意内言外,而‘矤’为兄(况)词,‘者’为别事词,‘鲁’为钝词,‘曾’为词之舒,‘尔’为词之必然,‘矣’为语已词,‘乃’为词之难是也。”[1]756
这段话虽是解释“转注”之义,但对虚词的分类确有纲目观念。“有纲目其辞者”之“纲”,就是“‘词’为意内言外”,而“目”就是“矤”“者”“鲁”“曾”“尔”“矣”“乃”等各别虚词。“目”并不限于这7个字,这里只是举例而已。“矤”是递进连词;“者”,许慎称之为“别事词”,现今古汉语教材都称作特殊的指示代词;“曾”是语气副词;“尔”是指示代词;“矣”是句末语气词;“乃”是副词。段氏认为许慎《说文》已有虚词划分的类目观念,而其总纲就是“词,意内而言外”。
其中有个“鲁”字,需要略加说明。“鲁”字,按现代人的观点看,是形容词,不是虚词,但在许慎看来,“鲁”是与“意内而言外”的“词”有关,具有“词言之气”的虚词性质,《说文》:“鲁,钝词也。从白(zì)。鲝省声(段作鱼声)。《论语》曰:‘参也鲁’。”“鲁”的本义是言语迟钝,故其字从“白”,“白”即自(鼻)字。《说文》“白”下曰:“此即自字也。省自者,词言之气从鼻出,与口相助。”段注:“词者,意内而言外也。言从口出,而气从鼻出,与口相助,故其字上从自省,而下从口,而读同自。”“鲁”在“白”部,白部列有“皆、者、鲁、、智于、百”等6字,都与“词言之气”的“词”搭上了关系。再说,“鲁,钝词也”也可说成“鲁,词之钝也”,与“曾,词之舒也”同为一例,“钝”从“屯”声,声中有义。《说文·部》:“屯,难也。屯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难。”[1]21“鲁,钝词也”之“钝”,指言语“屯然而难”,即说话困难、迟钝。“钝词也”之“词”,即意内言外之“词”,这里指“词言之气”的虚词性质。许引《论语》“参也鲁”,是说曾参生性迟钝,言词口气“屯然而难”,故许释“鲁”为“钝词也。”“鲁”字既入“词言之气”的“白”部,也就有了虚词的性质,就可以进入“词”的行列。
为了深刻理解“词”的虚词性质特征,段玉裁还将“词”与辛部之“辞”作了比较。段在“词”篆注中指出:“‘词’与辛部之‘辞’,其义迥别。辞者,说也(1)“说也”应作“讼也”。大徐本《说文》作“辞,讼也。”《系传·通论》“辞”下曰:“辞者,讼也;所以理也。”[2]316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辞”下曰:“讼也。朱按:‘分争辩讼谓之辞’。”[3]170,从辛。辛犹理辜,谓文辞足以排难解纷也,然则辞谓篇章也。词者,意内而言外,从司言,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辞”的本义是诉讼,即打官司的文辞,故段谓“文辞足以排难解纷也”。《说文·覀部》:“覈,实也……其辞得实曰覈”,此“辞”即打官司的讼辞,是本义用法。“辞”字从“辛”得义,《说文》解“辛”为“辛痛即泣出”。其义与犯罪有关。段氏“辛”下注曰:“辛痛泣出,罪人之象,凡辠(罪)宰、辜、、辞,皆从‘辛’者,由此。”[1]747按《说文》的解释,辠是“犯法也”,辜是“罪也”,“”是“罪也”,皆有罪之义,它们都是实词。而“词”隶司部,司部只列词一字,从文字构件角度说,“词”从司从言,是个会意字,而其义则为“意内而言外”,段氏释为“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既是“意于内”,就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词”与“辞”一虚一实,差别很大,故段言“其义迥别”。
除了“词”与“辞”的虚实之义不同外,段氏还从解释虚词的“《毛传》之例云‘辞也’”与“《说文》之例云‘某词’”进行比较,藉此说明“词”的虚词特性。段氏在“白”(zì)部“,词也”下注曰:“凡《毛传》之例云‘辞也。’如《芣苡》之‘薄’(采采芣苡,薄言采之)、《汉广》之‘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草虫》之‘止’(亦既见止,亦既觏止)、《载驰》之‘载’(载驰载驱、归唁卫侯)、《大叔于田》之‘忌’(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山有扶苏》之‘且’(不见子都,乃见狂且)皆是;《说文》之例云‘某词’,白部外,‘日欠’为诠词,‘矣’为语已词,‘矤’为况词,为出气词,‘各’为异词,为惊词,‘尔’为词之必然也,‘曾’为词之舒也,皆是。”
所谓“《毛传》之例云‘辞也’”,是指《毛传》以“辞也”注释《诗经》中“不为义”的虚词,段氏所举“薄、思、止、载、忌、且”等字,《毛传》均释以“辞也”,它们或置于句首,或置于句尾(见上举括号内诗句),在句中确实不具有词汇意义,然而在《说文》中,这些“辞也”之“辞”,都是有形可依、有义可释的实词。请看:艸部“薄,林薄也”、思部“思、(大徐本作“容”)也”、止部“止,下基也”、车部“载,乘也”、心部“忌,憎恶也”、且部“且,荐也”这些所谓“辞也”之“辞”,不符合《说文》“词,意内而言外”的虚词特性,也不符合许慎以“某词”为释的说解方式,当然不为许慎《说文》所取用,所以许慎必须易“辞”为“词”,给“词”以一个确切的定义和说解方式。段氏所谓《说文》之例云“某词”,是许慎说解虚词的通例,如段谓白部“皆”等6例及“矣、矧各尔、曾”等字,都属于“意内而言外”之“词”,除“鲁”字外,都是没有词汇意义的虚词。“词”与“辞”的本义区分与虚实之别,十分明显,在释义方式上,《说文》以“某词也”解释虚词比《毛传》单纯以“辞也”解释虚词进了一步,以“某词也”释义的方式使虚词的性质与类别更为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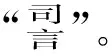
二、“词”有“摹绘物状”的修辞功能
摹绘,即具体生动的描绘、描写;物状,指人与事物的情状。《说文·牛部》:“物,万物也。”“万物”,指天地间一切事物。又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段注:“性,古文以为‘生’字”,意即天地之生,人为最贵,人为万物之灵。因此,“摹绘物状”包括人与事物两个方面,凡人与事物的声音、色彩、气味及情状、心态都可以借助“词”得以摹绘,“摹绘物状”是语言文字中通过对事物的具体描绘能使人感觉得到的一种修辞手段。
段玉裁在“词”篆注中,谈到“全书有言‘意’者,有言‘词’者。”“有言意者”之“意”,即是“意内而言外”之“意”,也是心意、志意之“意”。《说文·心部》:“意,志也。”“意”,就是心意、志意及表现出来的情状。“摹绘物状”,就是摹写人内在之心意、情状。
此外,还有一些散见于许书别的“言意者”的例子,如八部:“,从意也,从八豕声。”段注:“有所从则有所背,故从八。”段氏从字形上分析“”字得义于“八”,“八”是相背的意思,“有所从则有所背”,说明“”字造字之初本是有形可据的实词,然而从文献实际用例看,则已成了虚词,故《说文》释为“从意也”。段氏解释说:“从,相听也;者,听从之意。司部曰:‘词者,意内而言外也。’凡全书说解,或言词,或言意,义或错见。言‘从意’,则知‘者,从词也’;言‘词之必然’,则知‘尔者,必然意也。’随从字当作,后世皆以遂为矣。”[1]49,段氏认为《说文》全书说解,“或言词,或言意,义或错见”,故“,从意也”即“,从词也”;“尔,词之必然也”即“尔,必然意也。”“”(遂)在上古文献中是个表时间的副词,没有实义。段氏在“日欠,诠词也”下注曰:“遂者,因事之词。”[1]413杨树达《词诠》“遂”字下云:“副词。《仪礼·聘礼郑注》云:‘遂犹因也。’《谷梁传》云:‘遂,继事之辞也’”[4]339。“因事之词”、“继事之辞”,都表示“遂”是表前后相因相随的副词。它的作用是从相听相背上描绘随从者的心理状态。
又如“趖”字,《说文·走部》:”趖,走意。从走、坐声。”段注:“《花间词》曰:‘荳蔻花间趖晚日’,今京师人谓日跌为响午趖。”[1]64段释“趖”义,提供了三条信息:一是《说文》释“趖”为“走意”;二是“荳蔻花间趖晚日”的“趖”义;三是“今京师人谓日跌为晌午趖”。趖字从“走”,本为动词。把“走意”“趖晚日”“晌午趖”联系起来看,“趖”的词义在逐渐虚化,而《说文》所谓“走意”,是“走”的一种感觉。“趖晚日”“晌午趖”都是一种感觉,即感觉时间“走”得快。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趖,走意”下云:“按今京师谓日昃时为晌午趖,此其谊也。”所谓“此其谊也”,是说以清代口语中的“日昃时为晌午趖”来解释《说文》“趖,走意”,是非常合适的。这说明“走意”之“意”,是一种感觉,一种状态,也是词义虚化的一个标志,“意”与“词”互相映衬,故段谓许书“全书说解,或言词,或言意,义或错见。”
段氏“词”篆注中又谈到“全书有言‘词’者”,一些比较特殊的“词”,如鬼部的几个字,其所含词义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而是人在受到惊吓时所发出的一种惊叫之声、受惊之状,这些“词”也有“摹绘物状”的作用。
如旡部:“旡咼,屰恶惊词也。”段注:“遇恶惊骇之词曰‘旡咼’,犹见鬼惊骇之词曰‘’也。”[1]414又《鬼部》:“,见鬼惊词。从鬼,难省声。读若《诗》‘受福不傩。’”段注:“见鬼而惊骇,其词曰‘’也。‘’为奈何之合声。凡惊词曰‘那’者,即‘’字。”[1]436
三、“词”有“发声助语”的语法功能
“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中的“发声助语”,指的是“词”的语法功能。
“发声”,是汉代以来学者训释古经古书的一个术语,一般用于句首。如《诗·邶风》:“式微、式微,胡不归?”《毛诗传笺》云:“式,发声也。”[5]53也有用于句中的,如《尔雅·释丘》:“夷上洒下不漘。”《尔雅注疏》注:“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为漘。不,发声。”[6]卷七
《段注》在“洒”篆下引《尔雅》此句作“夷上洒下漘”,无“不”字[1]563,在“漘”篆下引此句亦无“不”字,说明《尔雅》句中“不”字仅为“发声”而无义[1]552。又段氏在马部“驚”篆注中引《小雅》毛传“不警,警也”,“不”字无义,亦为“发声”之用[1]467。
《段注》中仅一处提到发声,即“焉”篆注中云:“古书多用焉为发声。”[1]157其实,上引《尔雅》例中的“不”字,段氏亦认为是“发声”。因体例所限,很多“发声”之字未曾注明。
“发声”既无词汇意义,亦无语法意义,但并非毫无用处。若“式微”去掉“式”字,“於越”去掉“於”字,则读起来不顺口,词义表达也不太明确。《经传释词》“於”字下云:“於,发声也。《左氏春秋》定五年:‘於越入吴。’杜注曰:‘於,发声。’《正义》曰:‘夷言有此发声’是也。”[7]22“夷言”,指春秋战国时期越国民族的语言,“有此发声”是说越国民族有这种“发声”的语言习惯,可见“於越”之“於”不是可有可无,它至少有把单音节词构成双音节词的修辞作用,使文字产生音乐美,也使“越”国的含义更加明确。
助语,即“助语之词”,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词”之“转注”下亦云:“为助语之词”[3]170。《段注》与王引之《经传释词》多称“语词”,刘淇《助字辨略》则称“助字”(助词),它们都是虚词。
助语之词,所助者何?简言之,它有足词完句、顺接逆转、承上启下、领起一篇文字的语法功能,说得明白些,运用好虚词,能使说话或写文章语意完备,词气顺畅。
《段注》一书,对各别虚词已作分类,并有“某词”的称呼,与现今古汉语虚词的分类相近。如称“矤”、“况”为“增益之词”[1]227,即今之递进连词;“若”为“兼及之词”[1]42,即《词诠》所云“转接连词,说一事别提一事时用之”[4]247;“顾”为“语将转之词”[1]418,即转折连词;“傥”为“或然之词”[1]784,即假设连词;“颇”为“间见之词”[1]761,“间见”即间或见之,为轻微的程度副词;“且”为“粗略之词”[1]716,“聊”为“且略之词”[1]591,“粗略”“且略”均表示对人与事的态度,有姑且、暂且之义,属今之情态副词;“亦”为“重累之词”[1]493,即今之副词“也”;“又”为“更然之词”[1]114,即《词诠》所云“副词:复也,更也”[4]388;“骤”为“暴疾之词,古则为屡然之词”[1]466,“暴疾之词”则今之时间副词;“屡然之词”则今之表数副词。“凡”为“最括之词”[1]766,即范围副词;每为“不一端之词”[1]21,即表数副词;“遂”为“因事之词”(“日欠”篆下注[1]413),亦称“继事之词”,即时间副词;“与欠”为“语末之辞”[1]410;“谁、何、孰”为“问词”[1]371,即疑问代词;“耳”是“不足之词”[1]591,《词诠》称之为“语末助词,表限止。与‘而已’同”[1]468;“邪”为疑辞,“也”为“决辞”(邪篆注[1]298);“者”为“别事词”[1]137,“所”为“分别之词”[1]717,者、所,即今特殊的指示代词;“盖”为“发语之端”[1]42,又为“承上起下之辞”[1]736;“惟(含唯、维)为“发语之词”[1]505,即语气词,等等。
有时不言某种词类,但在表述中已见涉及。如在“否,不也”下注曰:“不者,事之不然也;否者,说事之不然也”[1]584,说“事之不然也”,指“不”为一般的否定副词;“说事之不然也”,即为应对副词。
段氏还谈到虚词的特点和用法问题,如“焉”字,段在《说文》“焉鸟黄色,出於江淮”下注曰:“自借为词助而本义废矣。古多用焉为发声。训为‘於’,亦训为‘於是’。”[1]157段言“焉,训为‘於’”,即“焉”可作介词“於”,训为“於是”指“焉”兼有介词“於”与指示代词“是”的语法功能。“於”作介词的用法在“爰”篆注中见之。段在“爰,引也”下注曰:“凡言於者,两物相於,自此引而之彼。”[1]160所谓“自此引而之彼”(“之”是动词“往”的意思),指“於”可引进对象或处所,这是介词“於”的常见用法。
又如“之”字,《说文》:“之,出也。”段注:“引申之义为‘往’,《释诂》曰‘之,往’是也。按‘之’有训为此者,如‘之人也,之德也’、‘之条条,之刀刀’。《左传》:‘郑人醢之,三人也。’《周南》毛传曰:‘之事,祭事也。’《周南》曰:‘之子,嫁子也。’此等‘之’字,皆训为‘是’”[1]272。《说文》训“之”为“出也”,“之”为动词。段氏所下按语,是对“之”字虚词用法的说明。段谓“之”训为“是”,则“之”为指示代词。至于“之”可作为结构助词,因无义,故段不加注。
再看“而”字。《说文》:“而,须也。”段注:“……引申假借之为语词,或在发端,或在句中,或在句末,或可释为‘然’,或可释为‘如’,或可释为‘汝’……”[1]454“而”字用法较多,但主要是用作连词,联结短语或句子,表示承接、转折、假设等各种关系。“而”在句中的位置可用于发端、句中或句末。“而”字的主要用法和语法意义,段氏注中均已提及,“或可释为‘然’”,指“而”用为转折关系,“或可释为‘如’”,指“而”用为假设关系。试以《诗经·相鼠》解之。诗云:“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前句“人而无仪”的“而”,表转折,可释为“然”或“却”;后句“人而无仪”的“而”,表假设,可释为“如”,用段氏对“而”字的认识来解读《诗经·相鼠》就很清楚。至于段氏所谓“而”可释为“汝”,那是指用作第二人称代词。
语气词既是语法的标志,同时也有“摹绘物状”、助表情态的作用。如“乎”字,是个句末语气词,可表疑问,亦可表感叹。《说文·兮部》:“乎,语之余(馀)也。从兮,象声上越扬之形也。”段注:“乎余叠韵,意不尽,故言‘乎’以永之”[1]204。“永”是咏叹之义,是对“意不尽”的尽情咏叹。
段氏对“乎”字的诠释,深得许慎释“乎”之神旨。段氏自己在“夭”篆的注语中也用“乎”字来描摹圣人孔子的神态。他说:“《论语》:‘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上句谓其申,下句谓其屈,不屈不申之间,其斯谓圣人之容乎!”[1]449段氏以《论语》“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之描绘孔子闲居之姿,而由衷发出“其斯谓圣人之容乎”的咏叹,“乎”字与另一语气词“其”相配合,组成“其……乎”式,圣人孔子不屈不伸的悠闲神态跃然纸上,这正好说明段氏对“乎”字咏叹作用的深刻把握。刘淇《助字辨略》谓“乎”字有两义:“一是咏叹之辞……一是不定之辞。”[8]卷一刘淇将“乎”的咏叹作用突出在“不定之辞”(即疑问)前,与段氏“言‘乎’以永之”的说法不谋而合。虚词既有“助语”作用,又有“摹绘物状”、修饰渲染之功能,于此可见。
又如“岂”字,它是个语气副词。段在“岂”篆下曰:“岂本重难之词,故引申以为疑词,后人文字言岂者,其意若今俚语之难道。”[1]207所谓“重难之词”,指“岂”可表肯定否定两重语气,“岂”用于反问句,有很强的反问语气,又可增强表达效果。又“盖”字,有多种用法,而其语法功能与修辞功能结合在一起,很难分开。段氏在“盖”篆下云“为发端语词”[1]42,即用于句首的发语之词,有领起下文的作用。而在《说文叙》“盖文字者”下注为“承上启下之辞”[1]763,在“簋”篆下又注为“意拟之辞”[1]193,即表疑问的词。所谓“发端语词”、“意拟之辞”和“承上启下”之辞,既是语法又属于写作手法,也包含了修辞手法。又“爰”篆下段注:“爰、粤、于、那、都、繇、於、也,八字同训,皆引词也……此八字皆由上引下之词也。”[1]160(笔者按:爰、粤、于、於四字同训,皆出自《尔雅·释诂》)。刘淇《助字辨略》“爰”字条引《尔雅》邢疏:“(爰、粤、于)皆为语辞发端。”[8]63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爰”篆云:“假借为于、为粤、为曰,皆发声之词。”[3]696杨树达《词诠》训“爰”为“无义”的“语首助词”“语中助词”[4]447,此三书与《段注》所训虽然不同,但皆为不具实义的虚词。爰、粤、于、於等字,如“爰居爰处”(《诗·击鼓》)、“粤若来三月”(《汉书·律历志》引《书武成》)、“黄鸟于飞”(《诗·葛覃》)、“於越生葛絺”(《淮南子·原道训》),皆有舒缓语气、引起下文、修饰词句、增强表达效果的作用,语法、修辞两种功能兼而有之。
《助字辨略·自序》谓:“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盖文以代言,取肖神理,抗坠之际,轩轾异情,虚字一乖,判于燕越,柳柳州所由发晒于杜温夫者邪!且夫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一句之误,通篇为之梗塞。讨论可阙如乎!”[8]序这段话包含了虚词在语法与修辞两方面所起的作用及其重要性。《马氏文通》谓“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9]19,把虚词描写“性情”、助表“情态”的性质与作用也说得很清楚(2)朱星《古汉语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出版),该书第五章第三节在讲到“虚字的性质和研究法”时说:“什么叫虚字……前人的说法很多,到马氏文通才把虚实字和词类结合,以为‘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第679页),这与《段注》“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的表述大体一致。
《经传释词·自序》云:“语词之释,肇於《尔雅》……盖古今异语,别国方言,类多助语之文。”又云:“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段、王所言“助语之文字”“助语之文”及“助语之词”,应是同一概念。“词者,意内而言外,从司言,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段氏这一精确论断,是从大量的古代文献及文字训诂书中总结归纳出来的,与王氏《经传释词》可谓异曲同工,体现了乾嘉学派在语言文字上的极大功力与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