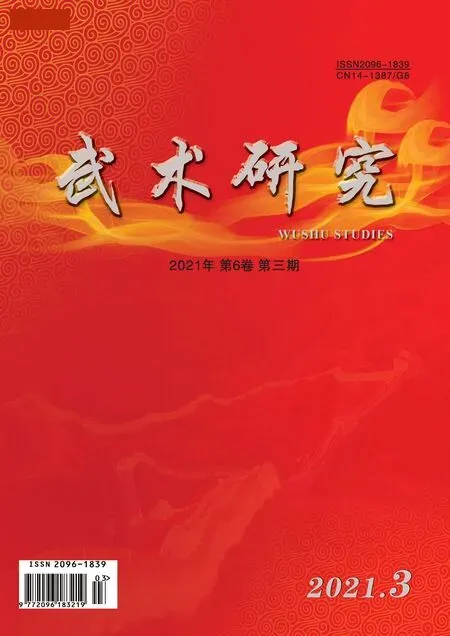武术的演艺传承
2021-11-23闫士芳马振磊
陈 青 闫士芳 马 威 马振磊
河北体育学院 武术系
武术从冷兵器战场下退役之后,转战于为镖局、演艺、授徒等战场。能否在这种新的战场上立足,同样需要具备高超武术技法水平。其中,武术演艺作为能够满足民众娱乐之需的内容,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备受世人关注,是武术退役后的主战场。武术演艺者的专业演艺水平决定着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武术技法的传承程度。
1 演艺的传统
剑被刀取代,剑由军用转入民间普及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学剑、击剑之风很是盛行。曹丕在《典论·自叙》中称:“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盲背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曹丕自豪地讲述了比剑经历:“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芊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剿,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技,更受要道也。”这是“一对一”的击剑记载,与军事战争的剑法不同,可进行比赛,更可观赏,与先秦击剑相比,技术、战术已有发展。转入民间的武术依然保留着浓烈的格斗意向,秉持着技法的精湛较量的水平,同时开始显露演艺的苗头。曹魏时出现了“力士舞”类的演艺内容,《魏书·奚康生列传》载:“正光二年三月,肃宗朝灵太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为力士舞,及于折旋,每顾视太后,举手、蹈足、瞋目、颔首为杀缚之势。”[1]这是武术在寻求新生存的空间的表现,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趋势一发不可收拾。
无论是将军还是舞者,武术演艺都是显示武技水平的重要方式。据《独异志》记载:裴旻将军为吴道子表演时,只见他“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人,无不悚栗。”可见,其高超的武技演艺水平。公孙大娘作为开元盛世时唐宫的舞者,舞“剑器”闻名于世,赞美之声流传至今,大家耳熟能详。
宋代中国的市民阶层的出现,有了浓厚的市民娱乐生活需求,武术演艺当之无愧地占据了一定市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小儿相扑、杂剧、掉刀、蛮牌,董十五、赵七、曹保义、朱婆儿、没困驼、风僧哥、俎六姐。”“驾登宝津楼,诸多诸军百戏呈于楼下。乐部复动《蛮牌令》,数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2]能够在大庭广众的众目睽睽之下,尤其是在皇上面前表现武术,必须有好身手。没两下子,可是要掉脑袋的。
连阔如在《江湖丛谈》中记载了近代挂子们走镖、护院、卖艺的故事,其中走镖时“无论来了多少绿林人,全瞧镖师的‘尖挂子’(受过训练的练把式卖艺的人)‘鞭上’(打的)如何了。若是镖师凭‘尖挂子’把绿林人惊得扯活啦,然后,还得叫伙计各处‘把合(看)’到了,防备贼人藏起来。”护院是镖局渐趋惨淡后的新产业,护院一点也不比走镖安逸。“若是雇佣四五十岁的人,那全是上过道(他们管走过镖说行话叫上过道)的,只要上过道,他的武艺错不了,经验阅历一定丰富。如若遇见黑门坎的人,不用动手,几句话就能把他说走了,永不来偷。”卖艺也不轻松,“挂子行的人将地打好了,到了游人最多的时候,师徒们扛着刀枪靶子到了地内,将刀枪架子支好喽,不能净说不练,得先大嚷大闹的招来人看,调侃儿叫诈粘子。等人围着瞧啦,才能连点小套子活儿,把人吸住了,四周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才算粘子圆好了。圆好粘子,就得使拴马桩儿(用话留你,让你走不了),用话将围着瞧的人们全都栓住了,没有走的人啦,才能看可看的把式哪!”[3]在过去,习武人真的不容易,自己要练得好,还要掌握产业营销的技能。
时至今日,习武人更加的不容易,社会文化活动日趋丰富,习武人欲在社会找到一片天地,专业技能自不多言,需要借助新媒介,新途径寻找立锥之地。在习武人苦苦寻觅中,武打影视为习武人打开了一扇窗,李小龙、成龙、李连杰、吴京等充分地借助新媒介实现了武术新跨越。可是,这种途径只能允许个别的知名运动员、演员入围,广大的习武人难以跻身演艺圈。面对这种情况,习武人自然不甘落伍,除了参与各级各类的竞赛,他们通过诸如《风中少林》《武颂》《少林武魂》《盛世雄风》《武林时空》《竞艺武术》等功夫舞台剧和专业竞赛等形式,以中国武术为重要元素而创作的艺术成果,是武术深入挖掘自身的文化潜质,丰富自身的表现形式,形成完善的创新体系的举措。对此,马文友、邱丕相甚至认为武术的艺术性很可能遮蔽武术的技击性而成为其主要外显特征。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武术自古至今,武术演艺是一种武术重要的存在形式,武术演艺具有悠久的传统。
2 武术演艺的竞技
武术技法应该包含两部分组成:一是随意活动,大多属于原始的武术元素;二是成型技术,为传统武术的主体。纷繁的原始武术元素有益于传统武术素材的积淀,但是无益于武术演艺,更无益于直接推动传统武术发展和传承。成型的、娴熟的、精湛的、自动的技术是武术演艺的重要依托,能够直接促进传统武术延伸和传承。
武术演艺是有习武人有意识地运用专门的身体技术去完成特定任务的武术表现形式。[4]在武术演艺中,武术演艺者主要是以身体行为为主体。身体行为包含着各色的武术技术,当成熟技术出现了明显的意向性,技术完善成体系后,技术又有机构成了武术演艺的专门身体行为。身体行为具有意识嵌入、内容广泛、形态各异、完整系统、明确目标等基本属性的人体活动。身体行为明显别区于肢体活动,是构建在肢体活动基础上的凸显内在意识、专有方法、明确目的的人体活动。武术演艺中的身体行为包含着突出的专业性身体素质、技术规范、运动内容、特定目标等技术成分。专有技术是载体,专有技术完成着将意识与行为目的相衔接,使意识指向并落实于目的之上,实现目标相关任务。《吕氏春秋·剑伎》云:剑技乃“持短入长,倏忽纵横之术也。”表明了剑术是武术演艺者使用长度有限的剑,用“短兵长用”意识,借助“倏忽纵横”短兵技术,实现长兵的技击效果。此刻可以清晰地看到,短兵灵活的技术是“短兵”连接“持短入长”的载体,“倏忽纵横剑走青”演练风格是区别于其他拳种特殊身体行为表现能力的技术中介。可见,始终保持拳种固有的“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技术技巧,可防止身体行为因为缺失技巧的专业技术性维护,而出现“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唯有当技术技巧被根深蒂固地纳入身体行为,身体行为便会保持长久的、特有的身体控制能力。试看,《说剑》:“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之技巧,方得“剑使之家,斗战必胜,得曲城越女之学。”(《论衡》)之行为表现。的确,技术与身体行为的高度关联中也存在着不可相互替代的差异,技术是局部具体的,身体行为是整体系统的;技术是惯习性的,身体行为具备明显的指向性的;技术是人的客体活动,身体行为是人的主客体合一的;技术是生物技能的,身体行为隐含着社会文化的人体活动。
如何使武术演艺的身体行为满足民众的娱乐需要,实现自身的生存发展,关键在于身体行为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使用现代学术用语,即竞技状态。竞技状态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武术演艺身体行为的水平。如果从竞技角度分析,竞技是一种为了自我、相互抗衡,经过长期系统习练储备起来的身体控制能力。在运动训练学中重点强调竞技是一种技术动作的自动化程度,当技术动作熟练到一定程度,技术表现出较高的自主、自如状态。在武术演艺中除了这种基本属性外,更有特殊的身体抗衡、协调、控制能力。抗衡的方式和方法非常繁杂,远不只为一种竞赛活动,竞赛仅仅是一种外显的抗衡方式,但不是唯一。相互的抗衡可以比较明显地表现出竞争的色彩,与竞赛活动的表现形式相似。武术演艺的竞技是一种被人们忽略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不仅需要自我的抗衡,也需要与演艺的同伴或对手进行抗衡,更有与观众的互动抗衡,这种抗衡对武术演艺者来说难度更大,在前述的例子中可以鲜明地看到圆粘子、拴马桩儿过程的艰辛和技巧,当下武术演艺者如何搏得观众隔空式的票房认可,除了噱头,更为关键的是演员的技术竞技状态,以及个人技术、人格魅力的影响,无人否认李连杰、吴京出色的武术专业功底才是帮助他们确立为武打影星地位的关键。由此看来,武术演艺同样是一种竞争、竞技,是一种与单纯的体育竞赛活动不同的,形式更为丰富的竞技。
3 悬置是竞技的核心能力
武术演艺者的身体控制能力,主要表现在在自我抗衡。武术技术体系异常的繁杂,加上众多的拳种,以及拳种的各异风格,武术演艺者必须在掌握武术基本功的基础上,通过悟性,精确地掌握某个拳种,出神入化地表明拳种的风格。在这种自我抗衡过程中,武术演艺者的技术向着日趋娴熟、精湛、高超的方向迈进,逐步达到了游刃有余的身体控制状态,此刻武术演艺者具备了应有的竞技状态。在这种竞技状态的背后是十分重要的武术演艺者的悬置能力,这种能力是身体控制能力的一种。只有武术演艺者能够悬置技术,完全沉浸在演艺之中,方可说达到了“应有的”竞技状态。比如,裴旻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这种状态,已经完全将抛剑与持鞘承之技术熟练到无需丈量,无意专注如何承之,而将精力灌注于走马如飞的迅疾利索表现上。大家非常熟悉的庖丁解牛,故事中说道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庖丁置牛、刀于不顾,而是“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就是典型的技法悬置。时至今日,在武术影视演艺中,这种悬置得到了现代科技的帮助,武术演艺者完成不了的技法,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实施,武术演艺者只需关注影片的情节表达,可以悬专业技术于不顾。这种情况导致了武术影视脱离于现实,误导习武爱好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武术传承的一种阻力。在现场的武术演艺中,这种情况可就没有这么乐观了,必须依托于武术演艺者可见的身体行为悬置能力,通过高超、娴熟、精湛的武术身体行为在悬置技术中,实现了对技术的超越,展示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实则是有效促进武术生存的关键所在。
身体行为的悬置能力是身体控制的重要构成,是达到竞技状态的核心环节。老子主张“道”要“绝圣”“绝学”“弃智”要“涤除玄览”。老子认为“能无疵乎”的经验和成见就像蒙在人们心灵上的灰尘一样,妨碍了人们对于真知的认识,必须保持内心直观镜子的清洁。采借老子的理论,可以从中看到,武术演艺者的技术动作中必然保留着大量的,类似于经验和成见的技术成分,比如技术惯性,对技术意向的认知等等,这些内容虽然有益于技术体系,但是同时也存在有尘埃效应,阻碍着武术演艺者对精细技术的掌握和表现。需要对此进行“涤除玄览”的悬置,防止思维惰性、身体惰性、技术惰性等所衍生的迟滞和倒退。庄子进一步告诫人们在特定情境中将自身利益置之度外,将过分的欲望化诸无形,以“忘其身”“墮形体”等超脱身体桎梏,实现高远目标。《淮南子》进而阐述顺乎自然必须“不治而治”“达于道者,反于清净,究于物者,终于无为。”[5]老庄等思想提供了充分发挥身体行为之竞技僭越须至悬置状态的逻辑基础。
武术演艺者的身体行为更受制于除了技术之外的思维、意识和心理等内部因素影响,比如武术的尊祖,凡是祖上传下来的技法是不容改变的,这种意识严重地制约着武术演艺的水平。前文中提及的各色挂子们的圆粘子的路数和套话如出一辙,难出新意,挂子们认为这是传统。殊不知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了观众们的感受。到了当下,武打影视的故事情节也百变如一,一点一滴的小事儿便开打,而且打斗贯穿始终不可开交,似乎人的血肉之躯是金刚之体,这种情况并不符合人际互动的常理,即使在先前走镖的镖师们也多是靠智慧避免武力冲突。这种情况更不符合暴力冲突的实际,根据研究暴力的专家柯林斯的研究表明:“事实上,正是双方互相关注之下所产生的紧张感,才导致这种内在的矛盾。面对面冲突会激发肾上腺素的分泌,并制造出紧张感;对此,我们能够从人们的面部表情与身体姿态中看出端倪。随着心跳上升到每分钟140次以上,人们在举枪瞄准等精细动作上的协调性会出现下降,当上升到每分钟170次以上,人们的感知会变得一片模糊;当上升到每分钟200次以上,人们就可能会动弹不得。”[6]通过这种理性分析,我们看到实际的打斗就是短短的几招,之后人的生理限度将人困住,而且人是非常脆弱的,几招之后便会结束打斗。另外,人们始终认为武术就是以技击性为本质的,这种一成不变的意识和思维使习武人面临着无穷的窘境,也使得武术演艺者无论是影视、舞台剧、竞艺竞赛中清一色的武打场面。如此看来,这种尘埃式的内容需要涤除,需要主动地使用悬置之法。
关于本文涉及的悬置,采借于胡塞尔为了追求纯粹,对前人的知识予以悬置后的自我辨明,从而在这样的方法中获得相应的“洞见”品质,[7]强化“洞见”能力,以此进行事物还原,用中立、存而不论的自然态度,对事物进行本真的纯粹研究的“悬置”措词。本文的技术动作、身体行为悬置与哲学中的“涤除”“忘身”“无为”和悬置在有意无意地忽略身体行为方面有一定关联。然而,本研究中悬置概念舍哲学悬置之还原,求武术演艺的技术动作悬置之进取,重自如悬置专门技术之能力,以期演艺不为技术羁绊之本。认为身体行为悬置,就是武术演艺中的身体行为控制能力已经达到了驾轻就熟、无需特别关注的全自动运行状态。悬置是身体行为的竞技状态的高级表现形式,不仅反映技术完备程度和技能成熟程度,更是身体所具备的高度自主、有效控制其行为的能力。当拥有这种控制能力的人,娴熟地运用身体行为去完成各种有较高难度的任务时,他们根本无需考虑如何运用各种具体的技术动作,身体行为是实施各类目标的助力而非阻力。如同演讲人不会关注舌头如何运动一样。只有达到这种状态和拥有这种能力,武术演艺者的身体行为就处于竞技状态。但见,只有身体行为达到了悬置状态,方可身械合一,演艺者方能如《剑俞》所云:“剑为短兵,其势险危。疾喻飞电,回旋应规。武节齐声,或合或离。”身法回旋、剑法飞电、起伏开合、节奏轻快怎能不“俞,美也。”拳种演艺达精至湛,悬置技法、竞技自如便备受称颂:“进退疾鹰鹞,龙战而豹起。”“如乱不可乱,动作顺其理,离合有统纪。”(傅玄《矛俞》)“手盘风,头背分。电光战扇,欲刺敲心留半线。缠肩绕脰,耈合眩旋。卓植赴列,夺避中节。前冲函礼穴,上指孛慧灭,与君一用来有截。”(陆龟蒙《矛俞》)[8]
在中西体育文化中,身体行为的悬置能力和类型不同,大体上可分为单独的和复合的身体行为悬置两种能力和类型。胡塞尔在提出了悬置的概念后,发现世间不存在绝对的悬置,人毕竟在“生活世界”中生存,所以在生活世界中的人在看待世界的时候必然附带着相应的“视域”,[9]这种客观存在影响着人的身体行为悬置状态。在西方主客两分的文化氛围中,身体行为与主体难以作为有机体整体来悬置。身体行为作为人们进行竞赛活动的手段,被人们高度重视,始终被作为改造的对象,身体行为日趋精细完善,并成为专业的独立体系。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固存着合一的意识,天与人、人与物、内与外、知与行等合一决定了人的主客合一倾向,身体行为复合地运用在社会活动中,很少单独地专门地用于体育竞赛、演艺,身体行为更倾向于对人教化与娱乐,身体技能不是主体首先关注的对象,身体行为缺乏必要的空间和氛围形成细化、特化的独立技术体系。在“忘我”语境中,身体行为跟随主体一同悬置则更加彻底。两种文化追求的终极目标更是大相径庭,西方竞技体育是以挖潜为主,中华民族体育则以养育为主,不同目标对身体行为的利用明显不同。为了实现挖潜、竞争,需要精湛的技术,必须练就高超的身体行为,并能够在特定时间段内随心所欲地保持高度的身体行为悬置,阶段性的悬置能力十分强大。娱乐、养生是一个悠哉的终生过程,无紧迫的时间要求,娱乐、养生弥散于生活之中,然娱乐、塑生之重任,乃人生之浩大工程。为了有效地完成娱乐、养生,特别是养生更需要意向性控制、专门性技能,且需强化身体行为的缄默、涤除羁绊,以“忘身”“堕尔形体”[10]的悬技娱人、塑生形式自如践行。悠闲的娱乐追求、悠缓的养生效应促使身体行为形成身心合一的终生性悬置能力,实施生命塑造的身体行为来不到的半点虚假和偏差。武术演艺者立足社会,其身体行为悬置能力,也须具备高度精细的竞技状态,“功夫”的武术演艺是常人在短时间内难以掌握的。不然,武术演艺便成为人人唾手可得的技能,而非寥若晨星的精英专利。
4 武术的演艺传承
精英式的武术演艺专利,可以概括为娴熟、精湛、高超的技术,化作容意识倾向、任务目的为一体的身体行为,自如、自在地悬置能力,表现出高层次的竞技状态,在实施自娱、他娱的目标时,表现出曲高和寡的地位,受世人仰慕,不经意间有效地传承着武术文化。《梦梁录》记载宋代市民们观赏武技表演时,武术演艺者们首先是“先以女飐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由此看来,套路类型的演艺格外引人注目。武术演艺必须具有高超的水准,才能发挥引人注目的效果。观众虽然明白这是非技击的表演,但是演艺者要有逼真的表现能力,《清稗类钞》记载:“两两挥拳,双双舞剑,虽非技击本法,然风云呼吸之顷,此来彼往,无隙可乘,至极迫时,但见剑光,人身若失,为技至此,自不能不使人顾而乐之。”逼真的演艺,可以将观众带引特定的场景,产生共鸣,生发爱好,由此使得这类武术演艺得以代代相承。为了能够达到这种状态,成为武术演艺精英,站稳社会地位,演艺者必须勤学苦练。必须经历“三膘三瘦”的形体变化,劲始入骨,又须经“三伏三九”的刻苦磨炼,劲始归根。王宗岳概括为“招熟”“懂劲”后才能达到“神明”状态。苌乃周则也强调:“炼形合气,炼气归神,炼神还虚”是武术演艺者习武的三部曲。其中的“神明”“归神”包含有悬置色彩,“还虚”更强调悬置能力。练到这种“功夫”,要经历“三年一小成,十年一大成”的漫长过程,越是见功夫的文化,越能被世人所珍重。在这些精英武术演艺者们出色演艺,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留下撼人心魄的印象,感召人人习武。这种途径和氛围使得这种个体,或者是集体记忆逐渐扩充至节庆、演艺等文化事项中,成为文化记忆的有机构成,被世人铭记在心,习练随身。
武术个体、集体记忆尚不足以长久传承,须将个体和集体记忆向文化记忆转移。“有历史研究者指出,交往记忆的传承一般在三到四代人中延续,40年是一个重要门槛,80年是一个边界值。从‘交往记忆’传承来看,超过了80年的上限,就会进入到扬阿斯曼所说的‘文化记忆’的状态。”[11]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是具体的自我所能够看见的表现,身体与文化记忆类似于自己的右手触摸左手,都是主客合一的身体记忆,相互的转化易如反掌。竞技化的身体行为有效地将传统武术的身体记忆、集体记忆向前推进,优雅地跨越了记忆时间门槛,成为文化记忆,代代相承,始终与国人相伴,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正是“凡是曾经有记忆的地方,就该有历史。”[12]在当下,武术演艺这种特殊传承形式,更应充分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优势互补,保障武术文化传承。
呵护武术演艺市场,是延续武术传承场域的合理选择。呵护武术演艺精英,是传承武术文化的必然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