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中“库车毛驴”的文化记忆
2021-11-22周秀英
□ 周秀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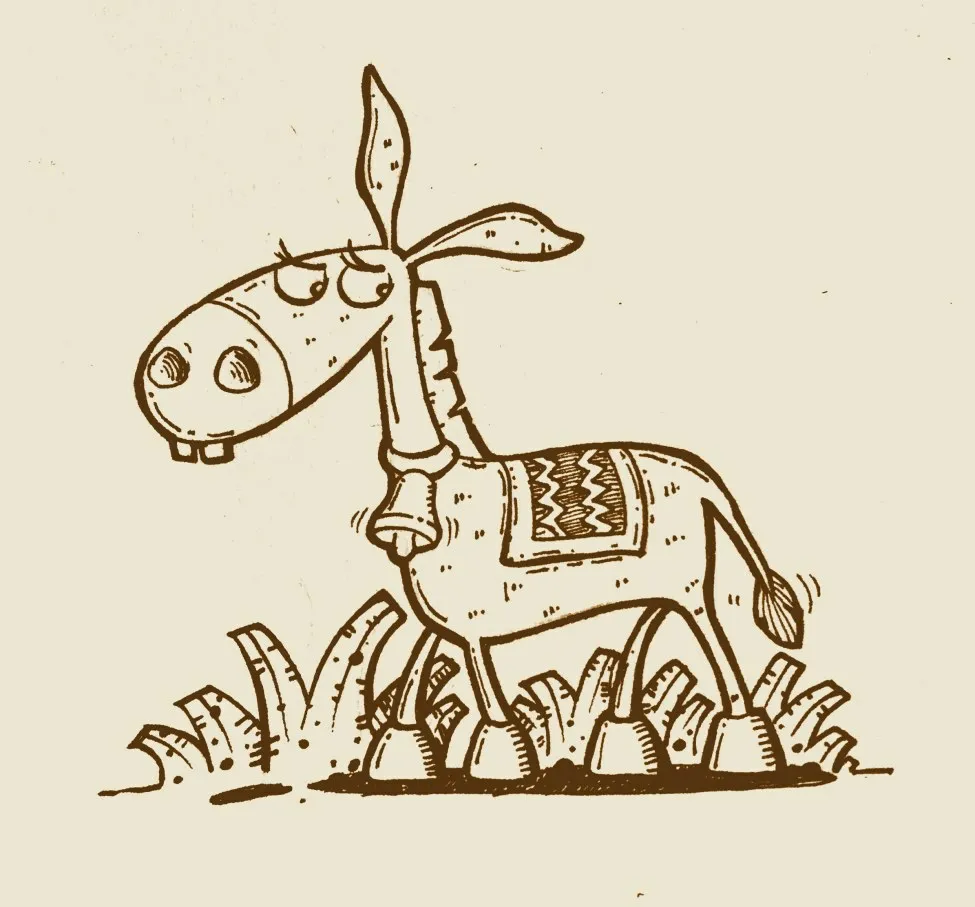
《在新疆》是作家刘亮程近年出版的一部新的散文集,该年散文集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在新疆》中,“库车毛驴”这一艺术形象反复出现,并深入维吾尔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笔者以此为基点追寻“库车毛驴”艺术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记忆值得探寻。
笔者借助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对《在新疆》文本中的文化记忆相关元素进行解析。
一、驴车与龟兹:交往记忆的载体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文化记忆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它是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但不仅仅)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在记忆文化中,文学的基本功能是集体记忆的建构和图像增加……又保存着对文化记忆的过程和问题的批判性反思。一个特殊的‘集体记忆的修辞学’,和它多样的模式(经验的、纪念性的、对抗性的以及反思的)意味着文学作品可以根据不同的回忆方式来(重新)构建过去”。

行走在巷子里的毛驴
文学作为一种存储记忆,其文本多义性多表现在记忆循环往复之中。《在新疆》正是基于个体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基础上建构南疆地域形象范式。2007 年,刘亮程出版散文集《驴车上的龟兹》,也是《在新疆》第一辑“半路上的库车”的主要内容。龟兹即南疆库车。
驴车这个古老原始的交通工具曾经是龟兹文化的象征物。存储着库车这座古老县城历史文化记忆。通过文学转化为刘亮程散文中的文化符号。《在新疆》再现了即将消逝的库车文化记忆。记录了库车历史文化的变迁。库车毛驴历经上千年时光的洗礼,成为人类忠实可靠的伙伴。
驴车构成龟兹独一无二的风景,毛驴与龟兹地域之间的渊源愈发凸显历史文化的记忆的久远。文化记忆作为一种物质与精神的铭刻,是交往记忆中文化价值观、标准、规则、礼仪的系统呈现。驴车承载着龟兹的历史文化,成为库车这座古老县城的精神遗产。驴车在巴扎(集市)上整合集体记忆。
《在新疆》书写了许多南疆文化记忆,如托包克游戏①、割礼、逛巴扎等,而这些文化记忆由驴车作为交往记忆的载体穿梭于龟兹历史文化的尘土之中。“个体记忆在不断交往过程中得到深化,交往记忆存在于个人之间,具有社会记忆的属性”。驴车在驮载人们前进的路途中,保存千百年来交往记忆中的个人历史体验。
古老的托包克游戏成为《在新疆》中个人记忆与群体记忆的交汇点。这种可以不限制时间玩一辈子的游戏形成交往记忆,象征着参与游戏的人永不磨灭的印记。羊髀矢成为连接记忆的符号。《在新疆》中,与吐尼亚孜玩托包克游戏的那个人更是通过不断与人交往,将铭刻有自己的姓名的羊髀矢散落出去,收回一群群羊。而驴车充当着交往记忆的载体。吐尼亚孜第二次输给自己的对手,就是因去草湖割苇子而害怕丢失拴在皮条上的羊髀矢,便取下了羊髀矢。对方却骑着毛驴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苇丛里向吐尼亚孜索要羊髀矢。这种被逐渐取代的古老游戏囊括了个人记忆与群体记忆。个人在不断交往中完成群体记忆的双重镜像。如若个体记忆模糊了事实的真相(即个体不承认自己曾经与对方玩托包克游戏的承诺),个体终会在某一时刻恢复昔日的交往记忆,做出忏悔式兑现承诺的举动。
在龟兹这片古丝绸之路的西域重镇,驴车作为交往记忆的载体构成无意识记忆。驴车与库车人悠然共处,成为库车文化的象征物。大学毕业后的买买提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库车做着剃头生意。他的剃头师傅牙生常提起收旧货的玉素甫,说他总是架着驴车坐等生意上门,驴车上的旧货就是他的招牌,牙生劝买买提要像玉素甫一样,安然守住自己的小事业。很多时候,无所事事的买买提只能看着停在门口的驴车发呆。在这里,“驴车”成了库车代际传承间的隐喻。潜移默化之中形成了库车人交往记忆中的文化符号。
二、库车毛驴:不可逾越的文化记忆
在库车数千年历史中,毛驴的地位经久不衰。人驴比例几近一人一驴的库车,毛驴成了库车文化记忆的显著符号。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记忆的三个维度:神经维度、社会维度、文化维度。记忆由载体、环境、支架三个协同工作的部分相互作用而成。三者关系在文化记忆中,以符号、物体、媒介、程序及其制度等可传输、可流传的客体为载体,替代了寿命有限的人并通过其可传递性保证了长久效力,环境以不断改变、更新和激活此基础的方式保持与这种符号一致性的群体,支架是占有并研究这些符号的独立个体。”
毛驴作为库车文化记忆流传的客体,在库车历史文化长河中,延续了文化代际相传的特质,“在库车两千多年的人类历史中,小黑毛驴驮过佛经,驮过古兰经。我们不知道驴最终会信仰什么”。龟兹在汉代丝绸之路北道中段居于关键位置,是佛教文化东传的重要驿站。在文化记忆环境不断改变的情况下,库车毛驴变成一种可传输、可流传的符号媒介。通过毛驴这一文化记忆载体,印证了生活多样化并存的事实。“那头小黑毛驴没变,驴上的人没变,只是手里的经变了。不知毛驴懂不懂得这些人世变故”。
库车是毛驴大县,在库车毛驴享受了其他动物不曾有的待遇。库车人像对待朋友一般对待库车毛驴。毛驴如同库车老城传统手工制品,在社会现代性衍变过程中,其地域传统文化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到“我”与驴互通心意,这是将驴置于与人对等的位置。
《一个人的村庄》1998 年出版。两部散文集都对乡村进行了哲学层面的再现,不同的是前者关注新疆北部乡村特质,后者聚焦南疆乡村风土。刘亮程曾说:“《一个人的村庄》中的‘乡村’早已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存在了,我的那些文字也许复活了一种乡村的精神记忆。”《在新疆》中的库车乡村更具刘亮程所说的这种文化记忆特质。
库车乡村的文化记忆体现在毛驴与巴扎(集市)间的密切关系上,两者逐渐演变成一种库车巴扎的“文化空间”。“库车四万头毛驴,有三万头在老城巴扎上,一万头奔走在赶巴扎的路上”。巴扎上的买卖在驴车上做,没有库车毛驴,就没有库车巴扎独特的交易形式。在不同的文化空间中,巴扎又以每周一天划分为不同的时间区域。文化记忆是一种高度成型的庆典性交际活动,是象征性的传统编码。巴扎不止于做生意,“每个巴扎都是一个盛大节日”。在库车巴扎文化空间中,每个逛巴扎的人或驴都有各自的兴趣,各取所需。库车人在巴扎做买卖的同时,也像是在过一场传统的节日,通过节日庆典的形式,在巴扎不变的位置传承着文化记忆。
除此之外,毛驴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还表现在地名上。《在新疆》中,每一条沟的名字都是一段历史文化记忆,反映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民俗文化。“有一条与维吾尔族人有关的沟:叶勒吉根。哈语意为‘毛驴’。在博尔通古牧场北部前山丘陵内”。这条含义为“毛驴”的沟记录了维吾尔族商人用毛驴驮货与哈萨克人交换物品经商的文化记忆。沟名即地名,“地名是文化的镜像,是人们社会行为产生的结果,透过地名的种种镜像,可以观照到文化在社会心理、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投影”。人们可以从这条叶勒吉根沟的地名中,了解到“毛驴”对此地的意谓。
毛驴以符号媒介形式存在于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中。《在新疆》共分为五辑,每一辑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毛驴”,从龟兹历史,库车巴扎、麻扎,地名等场域诠释“库车毛驴”的文化记忆符号形态、文化空间、历史记忆、生活印记。
三、库车老城:记忆场
《在新疆》中,库车老城是集巴扎、麻扎于一体的旧城,库车老城的每一寸角落都留有毛驴的印记。因而,围绕库车老城形成的记忆场,便不再是单纯的历史纪念场所,而具备了物质、象征等层面的含义。在刘亮程散文中,库车老城汇聚了不同类型、功能聚合体记忆,占据了记忆的文学形式,形成“集体记忆”②。
毛驴作为文学文本中集体记忆的媒介,在库车老城记忆场中成为活跃因子。毛驴反复出现在库车老城记忆场,以此存储库车人千百年来生活方式的独特体验。即使伴随着现代性进程下的文化空间演变,库车毛驴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功能依旧存在于《在新疆》的文本结构之中,从而辐射到整部散文集中的文学空间。
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的形象很大意义归功于一个社会可支配的媒介”。库车毛驴的符号媒介性体现在传播功能方面,在刘亮程散文、小说等文学文本传播过程中,对库车地域文化形象进行了创造性的塑造。散文集《在新疆》、小说《凿空》中,刘亮程均描写了有关驴叫声音的颜色——红色,并将其符号化。驴在阿不旦村的鸣叫有着独特的功能,在这个村里,所有生命的叫声,包括人声,都要借助驴叫的声音传播四方。即使最终还是驴的叫声占据上风。红色有着强烈的视觉效果,文学文本凸显驴叫声音为红色,其意义在于对“库车毛驴”符号媒介传播价值的再现。“毛驴”这一古老的家畜,被刘亮程不断书写,存在于阿不旦村,存在于库车老城,更存在于“我的记忆”里。毛驴和村庄相伴相生,毛驴就是村庄的腿。“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村庄是一个长着几千条驴腿的东西……没有驴的阿不旦村一下变成另外的样子,它没腿了,卧倒在土里”。

新疆毛驴车
由此,“库车毛驴”是在集体无意识层面,发展的集体记忆,具备一种暗示作用。刘亮程自述“我作品的仪式感通篇都有,如《喀纳斯灵》中,‘我把头伸进风里’,属于倾听的仪式,也可称为主客对位叙述方式”。库车老城因非物质文化的丰富性,为刘亮程创作《在新疆》散文集提供了鲜活的素材。是成为一种仪式感的集体记忆。驴车记忆着主客体间的交往体验,毛驴往返于不同的历史、文化生活之中,作为符号媒介,使得个人与集体层面的记忆不断转换。
库车毛驴暗含的集体记忆包括“我”的个人记忆与库车历史记忆。作者在《凿空》序言叙述“我”的出生是由驴叫出来的,在“我”的记忆里,驴叫的声音就是村庄的整体印象。集体记忆在两个文本间相互关联,毛驴的叫声是互文性的符号媒介。
《在新疆》第三辑“新疆时间”里,以“墩玛扎村禁地、夏尔希里、喀纳斯灵、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等为记忆场。首先,墩玛扎村禁地并非是不能去的地方,是留在村庄的古老记忆。高岸上的墓地在村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之前,就已然存在了。村民把高岸上不是自己祖先的墓主人当做神灵供奉,并将屋顶上的佛窟作为文物保管,仿佛是对千年以前信奉佛教那段历史的尊重。孤独红山中的萨满教、佛教、伊斯兰教残存痕迹,在墩玛扎村的建筑物上留下历史的印记。墩玛扎村高地上古老的历史记忆,与现代文明进程中的村庄具有不同的面貌。
其二,夏尔希里曾是中、哈两国领土争议区,由于很少有人员活动,这里的自然资源保存完好。夏尔希里的草木保留了这段争议区的历史记忆,这一地域的草木也有了象征祖国边界不可侵犯的神圣感,印刻着夏尔希里在历史、时代中产生的变化。这也符合有些学者提出的“记忆场是一种必须有历史、时代、变化参与影响的纪念场所”的理论。夏尔希里地方的风景与特定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铭刻过往的历史记忆,构成集体记忆中记忆场的暗示媒介。
其三,喀纳斯灵中,对风流石传说的记忆保持了一种仪式感。刘亮程曾说,他作品的仪式感通篇都有,在《喀纳斯灵》中,“我把头伸进风里”“萨满把头伸进风里”,属于倾听的仪式。刘亮程将传说中风流石的故事与喀纳斯湖怪、喀纳斯灵、树、山和月亮等象征符号同构、形成具有魔幻含义的记忆场。风流石的神奇魔力、喀纳斯湖怪的藏而不见、喀纳斯通灵的萨满、被树压死的牧民、阿勒泰山的寂寞、追寻月亮的梦境,这些元素建构出了一种神秘记忆场,具有强烈的仪式感,增强了集体记忆的呈现。
最后,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记忆场中,“我”从童年熟悉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历史记忆展开叙述。沙漠中的黄沙、梭梭、红柳、胡杨等植被混合而生,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整体与局部的空间,昔日成吉思汗大道、废墟、魔鬼城的再现,以及对由于沙漠植被遭过度破坏、地下水过量开采导致的荒芜镜像的预见,综合形成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记忆场,在历史与未来中架起了一座桥梁。
《在新疆》中刘亮程对库车毛驴的书写,毛驴与驴车形成的形象符号意义,成为库车历史文化记忆中的媒介符号。驴车不仅作为交通工具而存在,而且是穿梭在库车历史文化记忆之间交往记忆的载体。刘亮程将自己对库车毛驴的个人记忆与库车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融合在了一起。同时,驴车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库车人交往记忆的集合,融入了库车人千年的历史之中,毛驴以媒介符号的形式存活于库车人的生命之中。库车毛驴不再单纯是动物式的艺术形象,它与驴车、库车老城共同建构出库车特殊的地域文化形象。
刘亮程对于库车毛驴特殊性的呈现,还体现在与北疆毛驴的对比之中。在刘亮程不同的文本中,我们都能发现毛驴的身影。但是,库车毛驴在库车地域文化中却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刘亮程选择库车毛驴作为文化记忆的符号,强化了库车在地域文化性中的集体记忆。在这段集体记忆之中,库车毛驴特殊的地位,取决于库车人生活方式与记忆场之间的相互关系。
综上所述,刘亮程散文集《在新疆》,已成为一种文化文本。文学文本转化成文化文本在基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文化记忆的建构。在文本符号意义上的,库车毛驴作为文化记忆中的符号媒介,是库车历史地域风景的特殊表达。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呈现方式,库车毛驴体现的文化记忆,不仅是对库车历史生活环境的想象的历史再现,更是在历史传播中,以文化记忆的方式,建构库车特殊的地域文化形象。
注释:
①通过交换刻有对方姓名的羊髀矢,约定两年至五六十年时间,甚至于有时可长达一生里,可随时随地问对方要刻有自己姓名的羊髀矢,如拿不出来,即败给对方。除非自己认输,对方不喊停止,游戏绝不终止。
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古老习惯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举行传统大型综合性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形式,遍布在我国各地各民族的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集市(巴扎)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见乌丙安的《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民间文化论坛,2007 年第1 期。
②阿斯特莉特认为集合记忆是打上社会文化烙印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必须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共同作用才能产生影响,集合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区分,即“记忆作为文化现象”和“文化作为记忆现象”。见[德]阿斯特莉特·埃尔的《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冯亚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