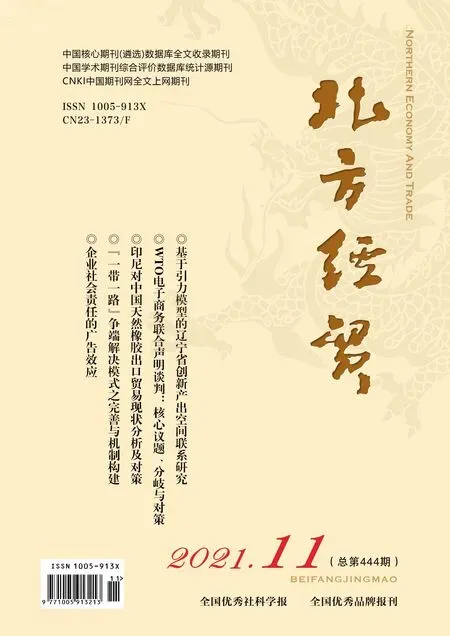“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模式之完善与机制构建
2021-11-22单渊
单 渊
(扬州大学,江苏扬州 225000)
一、“一带一路”对配套争端解决机制的需求
(一)“一带一路”贸易争端解决困境
我国构建的“一带一路”并非一个封闭、排他的国际组织,而是以其开放包容的姿态欢迎每个有意愿加入的国家,因此其并无绝对边界。然而,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文化背景、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等各不相同,使得贸易争端的表现形式复杂,暴露的问题亦尖锐多样,从而导致贸易争端面临各种问题。本文以法律风险与政治风险为例作以探讨。
首先,目前参加“一带一路”的六十多个国家中,有来自蒙俄地区以及中亚、东南亚、南亚地区等不同区域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前,这些国家就分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及其他经济组织的成员国,这导致了成员身份的重合性。而这些区域与经济组织之间法律规则的差异就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法律困境来源。在诸多法律困境中,首先面临的即是管辖权的归属问题。一件贸易纠纷的发生会牵涉到多个国家以及多个组织的相关规定,此时基于不同利益的衡量,既有可能发生相互争夺管辖权的积极冲突,也有可能相互推诿管辖权的消极冲突。除管辖权的归属外,部分国家立法技术层面较低,存在诸多法律空白,缺乏良好治理体制等,也是“一带一路”争端解决面临的法律问题。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几乎包含了几个世界上地缘政治最为复杂,恐怖主义组织及活动频繁的高风险区域及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交融的地区。这些国家的国内仍然存在社会阶层问题、民族宗教问题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此外,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还将不可避免地同时面临东道国政权更迭、法律和语言对接不畅甚至反华排华等各类风险。因此,形态复杂的政治风险也是投资者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
(二)现有机制不足以应对“一带一路”实际需求
当前,国际投资活动主要通过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以及区域投资协定加以规范,这是由于各国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的差别与分歧无法弥合,而通过双边及区域投资协定是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法。同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六十多个国家中,我国与五十多个国家签署双边BITs。这些投资协定在为我国投资者提供充分法律保障的同时,其中不甚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亦不利于我国投资的纠纷解决与救济。
首先,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差不齐的法治化水平,导致“东道国救济”这种属地保护主义倾向明显的救济方式往往可能造成投资者利益受损。具体而言,截至2016 年,在我国与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有的56 个BITs 中,将“东道国救济”作为可供争议双方选择的争端解决途径之一的国家有41 个。该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势在于维护东道国的国家主权及其利益。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多存在法治化水平较低、市场过度干预以及透明度不高等问题,相比较拥有透明、完善的投资法的发达国家,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得到公正合理的法律救济。而从目前来看,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投资关系中处于“资本输出国”的地位逐渐凸显。更多基于“东道国”利益保护的“东道国救济”反而会挫伤投资者积极性,阻碍“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
其次,中国除了与泰国之外的各沿线国家的BITs中均对“投资国—东道国”争端解决(Investor-Sate Dispute Settlement,ISDS)约定了仲裁方式,该种方式相比“东道国救济”更具有表面上的公正性,其包括临时仲裁与常设机构仲裁,但二者在适用的过程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
临时仲裁虽然具有灵活程度高、便捷高效等优势,但现有BITs 中多数争端解决条款为投资者和东道国选择临时仲裁设定条件,仅适用于征收或国有化补偿纠纷。此外,临时仲裁的高度自由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延长了仲裁前的准备时间,增加了救济成本。而每个相互独立的案件之间组成的临时仲裁庭的不同可能也会导致“同案不同裁”的结果发生。
常设仲裁机构虽然没有临时仲裁机构的灵活性,但其节省了前期的约定成本,不拖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BITs 中,主要采取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UNCITRAL Arbitration)以及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ICSID Arbitration)。UNCITRAL 仲裁的最大优点同时也是其缺点,即当事人享有自主权,这会导致双方当事人约定成本增加,不利于高效解决投资争端。而ICSID作为唯一专门解决“投资者-东道国”争议的常设机构,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签订BITs 时的首选。但ICSID 存在管辖权过大、仲裁诉讼化、中立性不足等缺点。上述缺点连同其内生性缺陷,是很多国家退出ICSID 的主要原因。因此,通过BITs 条款实现沿线国家全面接受ICSID 的可能性较小。
二、BIT 基础上“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一)弱化“东道国救济”之适用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多数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不佳,包括俄罗斯、印度等大国评级均在中级以下。且如前文所述,受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不同因素影响,这些国家法律的透明、稳定性都相对落后。这种偏向于东道国的救济方法不仅难以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还会有较高的救济成本和损害扩大的可能性,反而有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因此,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典型的资本输出国,不论是从维护我国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东道国的角度考虑,在重新签署BITs 时关于争端解决机制条款时,采用以国际仲裁为主的机制将更有优势。由此,弱化、避免“东道国救济”的适用,尤其类似将“用尽当地救济”作为采取其他救济方式的先决条件来变相扩大“东道国”管辖范围的约定应当予以避免。对于涉及公共利益或国家安全等特殊争端可以除外,但应当明确其适用范围并作严格限制。
(二)国际仲裁的区别适用
根据上文分析,不论是临时仲裁还是常设机构均是利弊并存。对于常设仲裁机构ICSID 来说,已加入《ICSID 公约》的沿线国家,通过“条约仲裁”的方式接受ICSID 的管辖仍然是合理选择。而不是《ICSID 公约》的成员国则可以选择临时仲裁的解决途径。此时,东道国和投资者在临时仲裁中法律地位的平等性也是有效避免“东道国救济”下的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的重要优势。
三、设立适应“一带一路”投资需求的争端解决专职部门
“一带一路”各沿线国家贸易争端日益增多,投资风险不断提高。然而,现有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现状存在诸多不适应性。为了顺应投资仲裁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维护我国投资者的利益,以提高其投资积极性,同时为了摆脱对国际仲裁机构的依赖,我国可以牵头为“一带一路”创建常设性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制定适应“一带一路”实际情况的争端解决程序规则。
(一)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的宗旨与思路设计
首先,有学者认为该争端解决机构可以取名为:“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法庭”(以下简称“法庭”),以表明该“法庭”是类似于WTO 争端解决机构的“准司法机构”,而非仅仅具有仲裁功能。笔者赞同该名称并认为该“法庭”的建立应当以解决“一带一路”域内投资争端为首要任务,在其他非“一带一路”成员国当事人达成合意的情况下亦可以将该“法庭”作为解决投资争端的选择。且为实现其宗旨,该机构应当是国际法主体,具有完全独立的国际法人格。
其次,在建立“一带一路”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时,要尊重、了解沿线各国法律文化,理清各个国家同领域的不同法律规定。此举既有利于规避法律风险从而降低贸易摩擦风险,也有利于增加各国成员对争端解决机制的认同感。各国可以在“一带一路”这个开放包容的大舞台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共同发展。
最后,“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尚未建立,目前的争端的解决只能适用其他争端解决机制。当该机制建立后,其与其他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应当如何协调,是彻底抛弃其他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还是将选择权交给争端方?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大特点就是包容性强,因此在“一带一路”的成长阶段,和其他争端解决机制协调关系,是有利于建设和完善自身的机会。
(二)如何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
首先,“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应当避免ICSID 的缺陷,结合“一带一路”实际情况,建构上诉纠错程序。ICSID 的裁决撤销程序仅纠正权利瑕疵,对于实体权利义务不会在错误裁决的基础上做出新的裁决。“法庭”可对初裁中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实体错误进行纠正。此时,为避免仲裁丧失高效、便捷等特点和优势,应当对“上诉”的期限做严格限制。
其次,应当建立磋商前置和调解结合仲裁的制度。国际投资仲裁实践表明,虽然以规则为基础的对抗式投资仲裁是解决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的绝对主导方式,但已经不再是最佳方式。刚柔并济的争端解决方式可以并存于一起投资争端的解决。其一,是以实力为基础的磋商方式。事实上,当争端方争议发生时,磋商是必经之路,但磋商时间过长也可能导致部分国家利用该制度拖延审结期。因此,当磋商被规定为前置义务时,磋商期应当适当缩短。其二,是以利益为导向的调解方式作为补充。调解与磋商相比,一般应当是提倡性质。调解因其特有的优越性被国际社会称为“东方瑰宝”。建立仲裁为主、调解为辅的程序可以有效减少诉讼,节约法庭资源,维护诉讼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避免损失扩大。此外,调解的启动应当设定为争端解决期间的任何阶段均可以启动调解程序,尤其应当提倡在仲裁中调解。
最后,应当提高审理以及规则的透明度。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色,多数国家法律政策透明度低,政府干预市场程度高。这使得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可预期性与稳定性难以预测。故“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应当以公开审理为原则,不公开审理为例外,特别是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投资争端时更应如此。投资者不仅能使投资者根据公开情况合理评估、做出预判,更有利于形成公平透明的投资秩序。
四、结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我国应重新审视投资中存在法律风险、政治风险。有学者认为,根据现阶段的国际国内现实,构建全新机制的可行性较低,现阶段“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可以先依托目前的双边、多边或区域安排,待条件成熟时再构建全新的争端解决中心。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特色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一个全新的事物,需要经历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才应当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断探讨其存在的价值,探索适合“一带一路”特色的规则体系。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对现有争端解决机制模式进行完善,在重签或续签BITs 时,应限制“东道国救济”的适用,建立以机构仲裁调解为主、临时仲裁为辅的争端解决机制,从而有效维护我国沿线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域内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同时,应当充分吸收和借鉴ICSID 等现有机制的经验,与沿线国家协商创设“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法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法律化与制度化,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由“政治导向”向“规则导向”演进,尝试进行域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规则的中国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