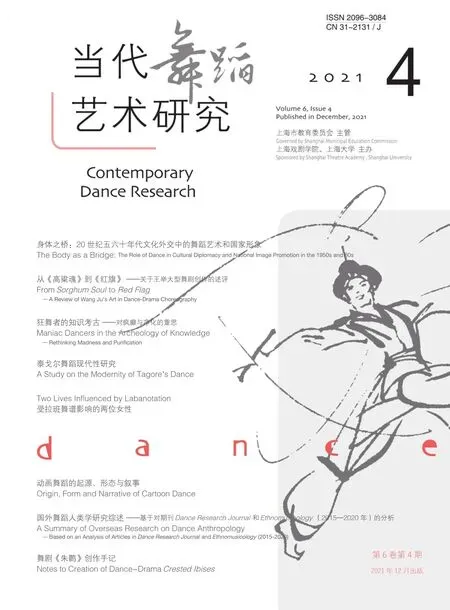时代·语言·审美
——当代中国“新古典舞”创作分析
2021-11-19陈苗
陈 苗
本文对中国“新古典舞”概念的界定与分析,是基于学界长期以来对“古典舞”的讨论而展开的。自20世纪40年代舞蹈人对“中国古典舞”的探索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舞蹈学院为筹建本科教育系中国古典舞专业进行的“36次会议”,再到以北京舞蹈学院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的创建与发展,“中国古典舞”的学科建设在百家争鸣中形成了“身韵古典舞学派”“敦煌古典舞学派”“汉唐古典舞学派”,学界围绕“中国古典舞”的讨论和实践至今仍未停止。吴晓邦认为中国古典舞建设的核心在于“古典精神”:“中国古典舞的概念应与中国古代作家与民共忧患的精神内涵一致,因此要从舞蹈的内容出发,它首先着眼于古代社会人民大众在苦难生活中真情实感的流露。”①于平整合了吴晓邦先生“从舞蹈内容出发”“与民共忧患”“古典精神”等观点后进一步分析:“中国古典舞‘是从舞蹈内容出发的’(不能纠缠某种历史形态),而这种‘舞蹈内容’又应该以‘中国古代作家与民共忧患的精神’为根据”;[1]116“‘古典’绝不仅仅是个时间或者时代的范畴,‘古典精神’也绝不仅仅是指某个特定时代里特有的东西,现代生活中也有‘古典精神’”[1]116。孙颖在《四论中国古典舞——关于古典精神》中谈道:“中国古典精神说到底,就是从物质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所体现的民族智慧、民族个性、民族的道德风尚和民族文化的品位。”[2]66刘青弋也曾指出:“中国古典舞的学科建设不仅仅是技术、动作、风格以及运动的方法问题,还有在其中显现的文化问题。”[3]我们必须“注重区分古典舞及其相关的文化建设的不同层次、不同方向和不同任务:本体形态——称谓‘古典舞’(其任务是将活态传统进行历史博物馆式的保存、展示,让后世将其作为有启发意义的历史进行不断的回顾)。而其发扬形态——称谓‘新古典舞’(其任务是对传统以继承为主的发扬,通过实现传统文化推陈出新,使得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4]
这些讨论让笔者以审慎的态度思考那些被冠以“古典”之名的舞蹈创作。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古代舞蹈语言形态表现“古典精神”的剧目统称为“新古典舞”。“新古典舞”不受时间的限制,但因时代差异,剧目的身体语言及审美风格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民族精神一直是其建构与发展的核心追求。故而本文进一步将1949—2021年国内有关“新古典舞”的创作划分为四个时期。四个时期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一是1949—1966年,语言形式探索与民族精神初建时期;二是1976—1989年,多维视角审视与民族精神塑造时期;三是1990—2012年,个体生命张扬与民族精神深化时期;四是2013—2021年,“一体多元”呈现与民族精神升华时期。本文将依托“新古典舞”剧目,分析不同时期“新古典舞”创作的意识、形式与语言,并提炼其所蕴含的“古典精神”。
一、“新古典舞”的历史分期与精神风貌
社会转型与政治制度变革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政治制度变革必然影响人类的社会活动,影响文化的变化、发展,“社会转型是推动社会文化形态转型的动力,分别体现在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5]176。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则是时代的号角。“一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高擎民族精神火炬。”[6]中国的“新古典舞”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四个时期的剧目所体现的“古典精神”始终契合时代风貌与群众心理,亦可由此清晰寻觅到国家意识对“新古典舞”文艺创作的影响。
(一)1949—1966年:语言形式探索与民族精神初建时期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舞蹈的状况是:“舞蹈同时并存着三种政治文化核心意识:‘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7]在此文化氛围影响下,这一时期,以《飞天》《宝莲灯》《荷花舞》《春江花月夜》《长绸舞》《小刀会》等为代表的“新古典舞”剧目,在救亡图存的回溯中,重塑民族精神,创作的重点突出表现为中华民族不畏强权、砥砺前行,重拾民族自信,恢复生产生活,积极建设新中国的主题。另外,以“新古典舞”名义存在的“红色舞蹈”也体现着古典精神和古典品格。“在中国,‘红色舞蹈’是中国舞蹈创作的主流。‘红色舞蹈’的创作既是舞蹈家的个人意志的体现,也是全社会基于同一文化心理的精神所需,这一文化心理的精神需求和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密不可分。”[8]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新古典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歌颂民族坚贞不屈的意志和精神,如民族舞剧《小刀会》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宁死不屈》中男女主角对恶势力的反抗;《宝莲灯》中三圣母、刘彦昌、沉香与宗法维护者二郎神、哮天犬及巨龙的搏斗,表达了正义的力量。这些剧目中男女主角对于正义的坚持,面对恶势力时大义凛然的气势,面对困难时百折不挠的坚持,表现了人民大众反封建、求解放的斗争精神。二是歌颂社会主义祖国与美好生活,如《荷花舞》和《春江花月夜》等。《荷花舞》中,戴爱莲先生一方面借鉴民间舞蹈的形态,另一方面模拟荷花在自然环境下的生长状态。舞蹈中的手臂动作、步法、队形和服饰,营造出朵朵莲花水上漂的意境,更表现出新中国如荷花般生长的蓬勃气象。三是塑造新社会、新人形象,尤其是工农兵和英雄的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劳动人民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农兵群体“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豪迈表现在“新古典舞”中就是对工农兵形象的歌颂,也映射出人们对英雄气概和英雄精神的崇尚。尽管上述三个方面的主题表现各有侧重,但都有共同的特点——人民群众成为主角和颂扬对象。这样的主题转变,使得舞蹈脱离“女乐”的历史认知,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大语境与时代的推动下创新舞蹈的表现形式,这类剧目的题材和内容不乏“红色舞蹈”。有学者认为这类作品不符合古典舞对“古典人物”的要求,但是从舞蹈语言上分析,这些作品大多采用传统京昆戏曲动作。笔者认为,这些剧目符合前文所定义的以“古代舞蹈语言形态表现‘古典精神’的剧目”,应属于“新古典舞”。“对于‘红色舞蹈’而言,舞蹈是载体,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思想和信念是灵魂。它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传达的是价值观念”[9]。这种意识在中国“新古典舞”剧目中表现为对英雄人物的塑造,不论是民族舞剧《小刀会》中周秀英、刘丽川、潘启祥这样的英雄,还是《炸碉堡》《黄继光》中的军人楷模,或是《风暴》《刘胡兰》中的人民群众,都在借塑造“舍小我,成全大我”的民族精神,展现对英雄的歌颂,以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昂扬风貌。
(二)1976—1989年:多维视角审视与民族精神塑造时期
经历了文化创伤的中华民族,迫切需要重拾文化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外开放”等文化和政策导向,也为文艺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一时期,文化领域面临着究竟是回归传统还是全盘西化的激辩以及“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讨论,“新古典舞”的编导们逐渐在迷惘中找到平衡,更注重立足本土、回归传统,也在中西文化碰撞、古今文化交汇中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新古典舞”在延续与拓展中强化“民族”概念的认知。这一时期“新古典舞”剧目的精神内涵,延续“十七年”时期自强不息、无畏牺牲的精神,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来突出典型形象。代表作品有《金山战鼓》《木兰归》等。在《金山战鼓》中,梁红玉的勇敢退敌化为清晰的三段体式结构。作品借用京剧中的武旦技巧,巧用道具,通过“大五花击鼓”“大甩腰击鼓”等击鼓方式突出身段上的闪转腾挪;节奏上强调轻重、刚柔、强弱的对比;情绪上围绕着“抗敌人、保家园”的情怀,在动静之间展现梁红玉御侮折冲、大义凛然的气节。“新古典舞”编导还进行了新的探索,从古今文化交汇中挖掘传统的精髓,以今人视角进行艺术创作。如舞剧《文成公主》,将唐代仕女图中的人物形态融入古典舞身体语言,创造性地结合了藏族舞蹈,成功地塑造出文成公主的形象,并刻画出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伉俪情深的感人故事,以此追溯中原与边疆地区的历史渊源与血脉交融。此类剧目的典型代表还有《醉剑》《盛京建鼓》《长城》《昭君出塞》等。
其次,“新古典舞”还在寻根中转变创作题材选择方向,表现内容更加丰富。“许多编导开始注意从民族文化最深层的底蕴中寻找最富于舞蹈精神的东西。”[10]92以《丝路花雨》为首,编导深入研究了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形象,并将其中独具特色的“S”形体态及具有代表性的“反弹琵琶”舞姿进行提炼,将其与古典舞语汇融合,开创了后来被称作“敦煌古典舞学派”的先河。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仿古舞蹈之风,被称为“中国古代乐舞复兴”[10]86。以历史学和图像学的视角审视“新古典舞”,编导们通过深入研究文献、文物壁画等史料,提炼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舞蹈姿态进行艺术再创造。“仿古乐舞”再现了我国古代乐舞艺术之风采。应该说,“仿古乐舞”的出现,亦是对传统“雅乐”的再认识,如《仿唐乐舞》中有《观鸟扑蝉》《白纻舞》《面具金刚力士》等舞段,分别体现出轻盈飘逸之“文”韵与雄健古朴之“武”风,展现出唐代舞蹈的多元与繁荣。除“仿古乐舞”,“新古典舞”编导们还将视角聚焦在花鸟鱼虫类自然景观,选取与时代风格和个人意志相契合的事物,借鉴传统语汇对舞蹈本体进行研究。如《小溪·江河·大海》中借助古典舞“圆场步”的“形”,精心设计的队形调度流转蜿蜒,塑造出小溪、河流、大海的形象,由此实现“新古典舞”身体语言的“意象化”创造。
再次,“新古典舞”在中西对话中推动创作思维革新,表现手法更为丰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大量西方思潮涌入中国。“新古典舞”编导的观念受人文主义和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打破了常用的传统叙事手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交响编舞法的运用,编导在保持舞蹈艺术“独立自主权”的同时,从音乐形象出发完成意象化的舞蹈创作,群舞《黄河》是“新古典舞”编导们运用这一创作手法的成功果实。这部作品以古典舞身体语汇为基础,根据“黄河”意象塑造所需,编导在作品中弱化了古典舞动作中源于传统戏曲动作的固有审美及艺术表达,结合音乐的交响化手法为动作赋予了新的内涵。动作的起伏、强弱和音乐的起伏、力度一同营造了不息的河水、澎湃的波涛和奋勇抗争的身躯;调度的分合和音乐的结构暗中呼应,表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的团结之力。作品“避开了用动作交代外在故事情节,也避开了对于抗日战争的各种事件的表面描绘,而是把黄河所代表的精神做了大大的抽象化处理”[10]105,这是中西编创思维融合对传统舞蹈元素的解构与重构,把“新古典舞”创作推向了更高的阶段。
(三)1990—2012年:个体生命张扬与民族精神深化时期
这一时期,伴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文艺创作呈现多元态势,“强调对个人自由价值的追求和保障”[5]158。中国“新古典舞”创作沿着上一时期的方向走上更加宽广的道路。
这一时期,“新古典舞”创作中重视对个体生命境遇的表达,突出对人的信念、欲望、精神状态的表现。如孙颖先生的“汉唐”系列,还有《秋海棠》《窦娥》《旦角》等作品,均将人文关怀聚焦到个体生命之上。《秋海棠》与《旦角》以三段式结构展现戏曲艺人的生命历程与境遇,出袖、收袖、抖袖、扬袖,起落间饱含着艺人对舞台的热爱;身体的舒展与佝偻,双足的收拢与跃起展现主人公命运的高潮与低谷。如此以情感人、关怀个体生命境遇的“新古典舞”剧目还有《九歌·山鬼》《萋萋长亭》《窦娥》《孔乙己》等。《九歌·山鬼》通过祭祀山鬼的舞动,隐喻今人内心的躁动与渴望。舞蹈突破传统剧目中女性单纯、善良、坚韧、贤惠、无欲等刻板形象,通过古代楚地巫舞的想象,创造性地展现女性应有的欲望与情思,山鬼的迷狂在肢体夸张的造型与扭动中展现。这是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重新认识与发现,是人道主义关怀带来的对人正常欲望的尊重、理解与释放。《踏歌》《绿带当风》《丽人行》《春闺梦》等莫不如此。
这类富有人文关怀的作品以及其所体现的个体生命抒发的转变是值得注意的,这种变化不仅是社会开放程度提高后对个体生命境遇的观照,亦是“民族精神”的立体挖掘。此类剧目数量渐增,创作向度跨越古今。如男子独舞《风吟》便是在自由的创作氛围中,编导向内寻求个体生命感悟的佳作。《风吟》的创作动机源于编导张云峰儿时在高高的草垛上体会风儿拂过面颊,扬起衣襟,随风飞翔的记忆。这化为“新古典舞”对传统美学“无垠、自由”的身体折射。《风吟》没有使用传统叙事方式造境的做法,转而尝试以抽象的动作展现传统文化意蕴,正是当代人对“远思长想、舒意自广”的哲思延续。此类剧目还有《轻·青》《碧雨幽兰》等,这些剧目无疑是“新古典舞”编导们汲取传统文化精神的自由言说。
除了个性的抒发和张扬,这一时期“新古典舞”对民族精神的探索不断丰富和深化。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学热、“唐装汉服”热、历史题材电视剧的高收视率等文化风尚,都是民族精神的新表达。“新古典舞”对民族文化精神建构的重视,正是这一时期民族精神建构内涵的丰富、民族情感整体共鸣丰厚的结果。如《秦俑魂》等作品的出现,无疑是“新古典舞”建设初期“斗争”“解放”的深化。孙颖先生的《谢公屐》等“汉唐”系列作品,展现中国文人的通透、质朴的情怀,剧目貌似潇洒的“游山玩水”,其实心中依然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与操守。孙颖先生借“新古典舞”剧目重现文人风骨,是对古代文人精神风貌的尊敬与推崇,亦是其在挖掘民族智慧、民族个性、民族道德和民族文化品格过程中的有力印证,是从古至今中国文人的家国意识与自我身份认同。进入21世纪,政策和文化导向的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强调“文化自信”,使中国以大国姿态走向复兴。“新古典舞”的创作也表现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与探寻,题材选择与民族精神塑造方面,既关注个体生命,也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化传承的深入探索与大胆构思,体现出中国文化传承的自信与担当。从《秋海棠》到《爱莲说》《屈原·天问》,从《谢公屐》《风吟》到《扇舞丹青》《书韵》《我欲乘风归去》,均可看出这一时期艺术家们在个体生命张扬与民族精神建构方面的探索、继承与深化。
(四)2013—2021年:“一体多元”呈现与民族精神升华时期
借鉴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主任王伟教授提出了古典舞发展的“一体多元”概念。她认为,中国历史传统舞蹈文化长河中,“新古典舞”的定义与发展依靠一家之言难以尽述,“身韵古典舞”“汉唐古典舞”与“敦煌古典舞”共同构成了“新古典舞”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批“新古典舞”中彰显着民族精神。近年来,国家一级编导马家钦的“昆舞”探索,刘青弋教授的“雅乐回家”“追问古典:中国古典舞‘名’‘实’之辨”系列,刘建教授的汉代壁画身体实践工作坊和田湉副教授的“俑”系列演出,表现出对“新古典舞”独特的历史的阐释与解读。
在汉唐“新古典舞”方面,孙颖先生开拓的多元路径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此时期的《心存汉阙》、舞剧《李白》中的《踏歌》、舞剧《孔子》中的《采薇》、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2015级汉唐“子衿班”的《响屐舞》等,再探新韵。在敦煌“新古典舞”方面,《大梦敦煌》《并蒂莲》《迦陵频伽》以及史敏的敦煌教材和剧目系列,均为立足艺术、文化、民族精神的综合探索。在“古舞新风”方面,《唐宫夜宴》《唐印》等作品在不同的向度中呈现艺术家们对“新古典舞”中的“古代题材”的情有独钟,随着网络平台的兴起,一些作品掀起民族文化的新热潮。如舞剧《杜甫》中的群舞片段《丽人行》。在舞的挥洒中展现出女性的力量,在忽而连贯、忽而顿挫的动作中体现女性的掌控力,在身体重心的小范围快速调度中描绘出唐朝宫娥青春健美的游春图。
这也是民族情感的整体共鸣。这一时期,中国新古典舞创作体系中歌颂民族精神的内容表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入传承与自信展现上。身体语言的选择上,“新古典舞”在“古典”的限定之下,在解放与限制的矛盾中寻找出更为“自由”的身体舞动:一方面不再拘泥于前两个时期探索的,或已经形成的新的程式性身体语言,选择更加开放自由;另一方面在舞蹈身体语言表达上追求准确中的丰富和多元,体现出中国文化传承的自信与担当。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新古典舞”创作,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民族精神升华,是在民族自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中言说中国表述。
从以上分期可以看出,中国“新古典舞”始终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探索作为内在追求,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将形式、语言和民族精神同个人“言语”相结合,传达出展现时代风貌的“新古典精神”。从1949—1966年,舞蹈语言的形式探索与民族精神的初建,1976—1989年,多维视角审视与民族精神塑造,到20世纪90年代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关注,再到近10年间在“文化自信、民族复兴”意识下对传统文化的赓续与发展。1949年至今的探索,“新古典舞”从传统文化中不断挖掘,投射到“新古典舞”剧目中,呈现出一种随时间延续内涵逐渐扩大的趋势。
二、“新古典舞”舞蹈语言与审美风格的演变
从舞蹈语言体系建构和审美风格的变化来梳理“新古典舞”,实际是回到开篇提及的学界关于“古典”两字之争下形成的不同古典舞学派。“它们集聚起来的历史碎片形成的训练体系,建立的属于语言体系中的语素和语汇部分,而非语言体系的整体,而在其中他们一些想象的、创新的、吸收的外来文化的成分则不属于古典舞之列。”[11]本文认为“身韵古典舞学派”“敦煌古典舞学派”“汉唐古典舞学派”三大学派虽然“语源”不同,但三种古典舞蹈语言形态的建构与发展都体现“守正创新,笃行致远”的“古典精神”。下文将基于“新古典舞”剧目的历史分期,阐释“新古典舞”语言的当代表达与审美风格演变。
(一)“新古典舞”舞蹈语言的继承与当代表达
20世纪50年代,脱胎于戏曲的“身韵古典舞学派”作为最早的语言形态探索,拉开了“新古典舞”“言语”构建表达的大幕。1957年,北京舞蹈学校古典舞教研组的教员们在“京、舞、体”三种语言的作用下,借鉴芭蕾经验,做出了诸多尝试。“一、有选择地把戏曲训练的基本功、身段和毯子功合并为一门课。……二、身段教材,从不同‘行当’,表现不同感情的千变万化的手的动作和姿势中,提炼了常用的‘手的八个基本位置’……‘脚的基本位置’……。统一了动作的规格和要求,把原来的戏曲动作给予了新的规范。三、初步借鉴芭蕾教材的结构方法,从繁杂的戏曲技巧动作中,寻找共同的基本能力……。四、采用音乐进行练习:从最简单的单一动作开始,直至组合练习,均配上音乐伴奏。”[12]教员们也创造了“穿掌蹦子”“倒踢紫金冠”等富含民族审美意味的技巧。《牧笛》《春江花月夜》《东郭先生》《风暴》《白毛女》《刘胡兰》《为了祖国》《张羽煮海》《宝莲灯》等小品和大型舞剧也在这一时期孕育而生。“对于中国古典舞的认知来说,能从‘戏曲舞中的舞蹈动作’扩大到‘戏曲舞蹈’、扩大到‘戏曲舞蹈’之外的‘古典舞蹈’,超出了‘李正一时代’封闭状态的‘科学训练’的有限理论,因为属于美学和艺术范畴的古典舞主要是一种人文学科的身体认识。”[13]614毫无疑问,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古典精神”同当代发展相结合基础上的“古典舞身韵”系统,经过近12年的实践,取得了可喜成绩。
1979年,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以佛教艺术——敦煌莫高窟的历史遗存为蓝本,选取、提炼敦煌舞特有的“S”形曲线运动规律和反弹琵琶伎乐天的舞姿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此后,孙颖等编导们尝试将静态历史资料变成动态形象的做法,给“新古典舞”注入一针强心剂。通过挖掘汉代画像、画砖、敦煌壁画等图像资料研究语言本体形态,并尝试将其重置于历史语境中,给“新古典舞”进一步传承传统文化打开了新思路。“汉唐古典舞学派”重在“立”,“塑形、重心、平衡、速度力量,跳、转、翻,向在流动中训练重心平衡,训练速度,训练气息,侧重肩胸,侧重腰臀。再将课堂结构调整为上肢、下肢、气韵、心态,而后再转向意境化、情调化、个性化以表演为主的终结阶段”[2]135。敦煌舞的语汇体系“在手姿、手臂、脖颈、身腰、跨步、腿脚的形态上,形成的弯弧、高度倾斜、拧曲动作及连接组合,以及贯通身心的‘S’形内在韵律曲线,构成敦煌舞表演体系与戏曲舞蹈身韵学派的中国古典舞体系的基本分野,同时构成敦煌舞独特的美学价值与艺术风格”[14]。通过分析不同古典舞学派的语言及形态,不难发现,不论何种形式都无法避免需要思考和研究“古”与“今”的关系,究竟是“作古”还是“诉今”,或许“新古典舞”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寻觅语义构建当代人心中的‘古典’”,即要解决核心“语义”的问题。“当中国古典舞以异质化的芭蕾基训元素、体操训练元素(本质上同样是异质的西方体育文化)、戏曲元素与武术元素充当自己的科学训练保护伞时,其身体文化和身体美学便被依次同质化,形成共时状态的杂糅,而不是细化自身的‘动作体系’。”[13]616从20世纪80年代舞剧《铜雀伎》以及“寻根述祖谱华风”等二十多个剧目的创作实践,内含了“新古典舞”创建者对古代舞蹈的创造与挖掘,“强调民族化,强调对历史传统的接续,强调我自成章,强调文化特色”[2]135。同时也展现了这一时期“新古典舞”建设者们对传统文化的执着探索。“新古典舞”创作应当正视古今之文化审美差异,认识到“舞蹈的历史是舞蹈不可割裂的精神流变史,历史的舞蹈在当代还值得被重新提起的理由,其实是当代舞者精神的无所归依或灵魂的出窍走火”[1]176。不论是戚夫人的“翘袖折腰”、杨贵妃的“霓裳羽衣”,还是曹子建的“凌波微步”、李白的“歌月舞影”,对于当代人而言,真正的意义或许在于通过不同的舞蹈形态体悟历史文化、反观当下的精神文化。传统与现代新的矛盾是现代化运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15]
“新古典舞”语言融入现代文化因素正是先行者深入传统文化、深入现代文化,对两者进行语言分析、取舍后,按照现代民族审美的要求成功融入现代文化因素所致。2000年以后中国“新古典舞”的语言选择呈现现代审美影响下的多元化态势,如《扇舞丹青》《碧雨幽兰》《孔乙己》《我欲乘风归去》《爱莲说》《且看行云》《月满春江》《济公》《点绛唇》《丽人行》《满江红》《墨舞流白》《故国》《大河三彩》《西施别越》等。这些剧目题材多样,但语言上却不约而同地根据主题、人物形象、舞段结构所需,采取为我所用的表达方式,是“新古典舞”创作者们有意识地将“古典精神”置于当代文化语境中,阐释民族传统当代身体语言建构的有益实践。
《碧雨幽兰》《爱莲说》《丽人行》等作品是“新古典舞”舞蹈语言的当代表达。这些作品的舞蹈语言看似自由、随意,并不刻意追求传统舞蹈之形,但在舞蹈中却刻意保留并强调“圆”“流”的舒展线条,将舞蹈的身体语言和独具匠心的服饰、道具与音乐设计合为一体,呈现至关重要的古典女性身体语言。这些“新古典舞”的身体不仅塑造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出淤泥而不染”的古代丽人,更舞动出现代的佳人和清新可人的女子形象。舞蹈语言再现“撑着一把油纸伞”的丁香姑娘的漫步,又或是借唐代丽人的端庄舞姿与荷塘莲花的造型,在熟悉的动作程式中轻盈的跃起与落下,在油伞的开合中,在丽人的拧身回首与莲女的身姿柔韧盘旋中,仿佛让我们看到历史画像和文献中“袅娜腰肢温更柔”的倩丽与莲步轻移的风流。这些身体语言也展现了当代女性中灵动与热情的时尚身姿,仿佛是21世纪初升的太阳,少了一份惆怅与彷徨,多了一份现代人的自信与欢跃,更一改学界对中国“古典舞”“怨妇”似的抱胸缩肩、自怨自艾的批判。而《孔乙己》《济公》等剧目在动作语言创造上另辟蹊径,以幽默、轻快的动作主体,辅以生活化动作和情景性动作的“鼠窜”“醉酒”等,表现人物的生活日常与命运,动作语言的整体格调让人耳目一新,中国传统文化的幽默感在“新古典舞”剧目中得以展现。除此之外,“新古典舞”的现代探索一方面继续在本体上开掘,如“昆舞”“雅乐回家”“汉代壁画身体实践工作坊”“俑”系列等实践从不同侧面对“新古典舞”语言进行探索和充实,呈现出舞人的自觉和反思精神;另一方面,借鉴融合武术、书法、传统仪式等的身体语言实践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化中。
中国“新古典舞”的创作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并建构中国的舞蹈身体语言体系。因此,无论是选材、立意、结构,一切创作环节和技法都是应围绕“新古典舞”这一核心关键词展开。只有把握住这个关键,方能将经过选择的、适合中国“新古典舞”发展的文化因素融入创作。在借鉴现代观念和语言的过程中,中国“新古典舞”创作中现代因素的融入应更好地利用现代理念、创新手段与方法来传承传统文化。《扇舞丹青》便是成功的范例,作品中的身体语言借鉴了现代观念的“解构与重构”以及空间的大开大合,但身体语言行云流水,气韵绵绵不断,充分展现了中国人从古至今对“和”的追求——小中见大、以简胜繁、均齐和谐、对称平衡、阴阳相合、主从有序、对比反衬,相得益彰,在动态的调节中,身体的各部分重心牵制,以保持平衡稳定,体现出“和谐”的意味。其身体语言充分表达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辩证关系:矛盾对立之中的渗透与互补。此类优秀剧目如《书韵》《醒狮》《龙儿》等的大量产生,一方面与“李唐身韵体系”的挖掘与推广有直接关系,表现了创作者们在动作语言体系与审美风格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再反思与再阐释,表现“新古典舞”创作者们对民族精神的尊重、继承与深思;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创作者们对现代元素和现代观念“为我所用”的创造性借鉴与发展。
(二)审美风格的单一与多元
“风格是艺术的精魂和个性体现,舞蹈的风格又蕴含在语言体系、语言形态、语言的文化属性之中,构成艺术形式。”[2]126艺术家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艺术作品亦必然带着时代的风尚。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人的审美意趣也在不断转变,中国“新古典舞”的审美由探索时期的单一尝试,逐渐随时代而变,在继承中不断突破审美局限,赋予“古典精神”现代审美意味,尤其是在大量以女性为主要表达对象的“新古典舞”剧目中,不同时期女性审美的变化或可以镜鉴“新古典舞”审美风格的单一与多元。
“在中国古典舞创建之时,我们的目标是要‘创建现实主义的舞剧艺术’,因而在路径选择上必然‘关注中国舞蹈现实主义的传统’。”[1]4“新古典舞”创作和审美也秉承这一原则,尤其是在第一个历史分期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不爱红装爱武装”,几乎所有女性都迷恋绿军装、蓝工装。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人和“建设者”,人们对女性的审美趋于中性。20世纪50年代的“新古典舞”中,被广为认同的女性审美是《小刀会》中英勇无畏、热情高涨闹革命的周秀英;60年代是《红色娘子军》中的共产主义战士吴清华。即使在1976—1989年“多维视角审视与民族精神塑造”这一分期的早期“新古典舞”剧目中,爱情题材的表达仍较为隐晦,甚至被忽略,爱情和忧思让位于宏大叙事和民族精神的追求。如《新婚别》中,编导用翻身、急速旋转、跳跃、连续的跪步行走揭示女主人公内心的痛苦和担忧;用跪、拜来表现男主人公内心的挣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不舍与依恋还被“物化”在服饰和道具运用上:一方面新婚夫妻分离的痛苦在舞袖与舞剑中绵延;另一方面用舞袖与舞剑斩断儿女情长。女性的舞蹈语言同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建构和英雄崇拜呼应,是中性的,是阳刚、坚毅的,是带着革命力量型的审美形象,对于“封、资、修”的批判使女性温柔、娇媚与阴柔的特质被富有革命气息的铿锵有力的审美取代。
然而,特殊的历史时期总是短暂的,特殊时期的女性美学追求也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回归到女性与生俱来的美学形态之上。20世纪80年代之后,女性的温婉之美、阴柔之美和女儿之态在大量“新古典”剧目中得以展现。这也表现在对“女乐”审美的辩证认识上。作为中国古代舞蹈史上的一脉传统,“女乐”是一道文化风景,也暗隐诸多沧桑,弃其“女乐误国”的奢靡,取其阴柔、娇媚、灵动俏丽以及玉帽锦衣的潇洒爽利,女性美的彰显为“新古典舞”赋予无限风情、无限意味。
古代舞蹈的资源被重视、被挖掘,继而以多元审美被表现。无论是基于“身韵”建立的“圆流周转”的身体美学,还是由泱泱汉风中取形而来的“厚重质朴”,抑或从敦煌壁画中挖掘的带有异域和宗教特质的美学,都使“新古典舞”的审美由单一走向多元。这也有赖于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动态分析,跨时代的文化“要去并行研究当代文化及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16]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舞台上,“新古典舞”剧目中佳人翩舞其间,美姿、美意、美德并现,女子群舞《踏歌》便是其代表作品之一。孙颖先生将自己50年的心血倾注其中,从动作到服装、从音乐词曲到舞美灯光无不自己设计。其作品既有女性的婉转柔媚之美,舞者双肩内敛,下颌侧含的体态是二八年华的古代少女遇见心上人时的不安与羞涩,诉说着对心上人浪漫而执着的爱情期待;又有汉代的厚重质朴之美,侧倾的头、回旋的躯体、松弛自得的踏步让人流连忘返,观之沉醉。搭在肩头半遮面的纤手、摆动的身体中一次次回眸的娇羞,都诉说着“但愿与君长相守,莫作昙花一现”的柔媚。这典型的东方女性审美和表情达意是柔和、曲回,让人迷醉、不可抗拒,全舞在令人心旷神怡的流动转踏中使无数中外观众为之倾倒。审美的多元体现作品还有《相和歌》《俏花旦》《丽人行》《绿带当风》《舞绸伎乐》《楚腰》《桃夭》等。这些“新古典舞”作品不仅展示了成熟女性的端庄柔美,还有少女的活泼天真,更有巫女的迷狂与豪放,表达了现代社会对于女性审美的多元向往。
“新古典舞”中女性审美形态的变迁折射出编导们对中国审美精神的思索和艺术转化,“中国文化的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17]中国“新古典舞”为何在20世纪的中国重建,并且得到专业舞者的关注与大众的欢迎,除政治因素之外,正是因为“新古典舞”建设与发展契合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更进一步说,是契合了当代中国社会大众的审美心理需求。
因此,作为中国“新古典舞”的舞蹈编导,要想在作品的审美形态上进行创新,编出既有“古”韵,又符合当代的审美需求、广受观众欢迎的作品,要立足创作本体、舞蹈本体,树立“本体意识”。一方面,需要坚守古典精神和古典文化的土壤;另一方面,要以艺术家的智慧超前一步,将古今结合的艺术思索转化成艺术形象。当然,对“新古典舞”从创立至今的各类身体语言的掌握更是审美把握的根本前提。
结 语
综上所述,“新古典舞”在当代的发展中,“民族精神”“古典意蕴”“语言形式”“当代构建”“文化认同”等话题依然是永恒的热点。“新古典舞”的创作和发展并非静止的概念,而是在变化中将“名”与“实”的矛盾与融合统一在“新古典舞”身体语言的继承与创造上,从自由与限制中开拓出一条古今结合之路,在艺术表达与文化自信的塑造中寻找最佳路径,传承与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中国“新古典舞”的创作活动同新中国一起成长,欧阳予倩、吴晓邦、戴爱莲、唐满城、李正一、孙颖等先辈们筚路蓝缕,艰难探索“新古典舞”语言的同时,也进行着民族精神的重塑;陈维亚、张羽军等创作者们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积极汲取传统文化养分,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如今“新古典舞”的编导们对个体生命情感的诉求和多元文化审美的追求,使他们回归“新古典舞”语言之源,既要海纳百川,又要守正创新,寻找符合古代舞蹈语言形态的身体语言,挖掘“新古典精神”。70余年“新古典舞”的创作实践说明:中国“新古典舞”的当代建构不是一般时间意义上的“当代”,而是背靠传统、对应当下的“当代”。中国“新古典舞”的当代建构,不应受“古”字的限制,不是异域语言的移植与拼贴,更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简单迁移,而是追寻“古典精神”价值之源。这也就要求“新古典舞”创作时注意当代语境,借“古”之形,完成“借古喻今”的文化输出,使“古典精神”深入人心。唯此,才算完成“新古典舞”的使命。
【注释】
① “中国古典舞”和“古典精神”之关系的辩证思考,需要从人民立场和社会环境的角度认识。吴晓邦进一步论述道:“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杰出文人如屈原、司马迁和杜甫等,都具有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与黑暗现实拼死抗争的伟大情操,因此,他们能够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不惜忍受巨大的痛苦,历尽艰辛,创造出了不朽的作品。这就是他们的古典精神。”参见:吴晓邦舞蹈文集编委会.吴晓邦舞蹈文集:第3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159—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