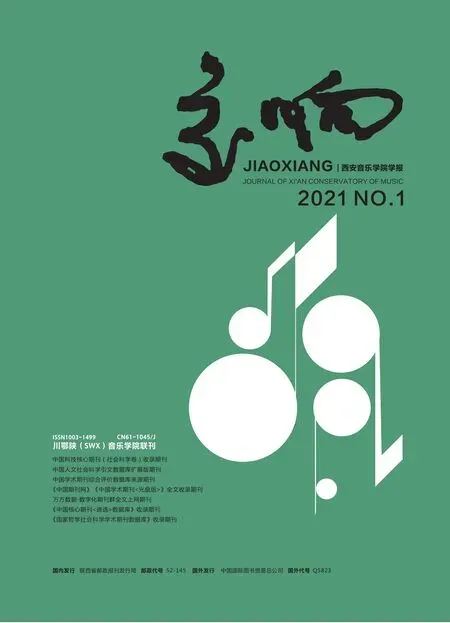解构“笛上三调”
2021-11-19刘永福
●刘永福
解构“笛上三调”
●刘永福
(扬州大学音乐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笛上三调”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乐学概念,而是历史上已有的“相和三调”“清商三调”的延续和拓展,是秦汉以来古代“旋宫”理论和技法在“律笛”上的实践性探索。“正声调”“下徵调”“清角调”术语的正式提出和使用,说明中国传统宫调理论话语体系中的“调关系”原理早在魏晋之前就已经形成,同时标志着与此相关的乐调实践不断发展和相对成熟。中国历史上的“三调”之名以及所形成的“调关系”原理,丝毫不逊色于西方的“主调”“属调”“下属调”概念,而且比西方的“近关系调”话语体系要早大约1400余年。
笛上三调;还相为宫;正声调;下徵调;清角调;调关系
在“笛上三调”问题上,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迄今尚未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和结论,主要有“调式说”“音阶说”和“调高说”。从表面上看,三种学说各自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从概念的生成基础(律笛)、内涵属性及乐学逻辑的角度深入解析,三种学说都不能深刻反映出“笛上三调”之本义,可谓三种“假说”。以往,由于缺乏对“笛上三调”问题的准确揭示,使我们尚未认识到“笛上三调”原理在构建中国传统宫调理论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性和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本文将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三种假说的深入解析,以及对“笛上三调”原理的重新解读,试图探赜索隐,求其本义。
一、“笛上三调”假说辨正
关于“调式说”。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中,对荀勖笛的设计理念、结构原理及其特征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同时指出了荀勖笛律存在的两种主要矛盾。
在荀勖笛律中间,存在两种矛盾情形:(一)既然有了一律一笛的十二笛,同时每笛又有三宫(据其《注》是三宫,而非三个调式);后者实际上否定了十二笛之必要性,既然一笛可吹三宫,则吹十二宫,并不需要十二笛。(二)其一笛三宫中,清角调是吹不准的。[1](P169)
在杨先生看来,“两种矛盾情形”的产生,“暴露了荀勖笛律脱离传统和脱离实际的缺点”,因此提出了“笛上三调”是三种调式的观点。
荀勖的十二支笛,每笛适于演奏一宫。他每笛上的三种“调”,看作三种调式,更为合理。……正声调就是一个古音阶,相当于现代的fa调式;下徵调就是一个新音阶,相当于现代的do调式;清角调相当于现代的la调式。以笛上的三调和以前已有的相和三调和清商三调相比,正声调就是平调,清角调就是瑟调;只有下徵调是一个新的调式。这一调式的流行,将在我国历史中造成了新音阶的确立。[1]
时隔不久,三种“调式说”作为“笛律”词条中的内容被写入了《中国音乐词典》。
荀勖所说的“三宫”指三种调式,即:“正声调”(古音阶宫调式)、“下徵调”(古音阶徵调式)和“清角调”(古音阶角调式)。“二十一变”说明每支笛都能吹出上述三种七声调式所需要的各音。[2]
不难看出,同样是三种“调式说”,但在音阶属性和调式类别的认定上却出现了分歧。
首先,杨先生的三种“调式说”建立在古音阶和新音阶两种不同属性的音阶基础上,而《中国音乐词典》则都以古音阶为前提。其次,在调式类别的认识上也存在明显不同。杨先生认为,正声调是古音阶fa调式,下徵调和清角调分别是新音阶的do调式和la调式。而《中国音乐词典》中的正声调、下徵调、清角调,分别对应的是古音阶宫调式、徵调式和角调式。这也反映出,随着时间的变化,对“笛上三调”的认识也在发生改变,同样是“调式说”,结论却不一致,“调式说”的不确定性显而易见。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和《中国音乐词典》是20世纪最具权威性的两部学术著作,对于国人学习、了解中国传统音乐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学术影响力不言而喻。“笛上三调”的“调式说”之所以能够引发关注,不外乎两部著作的学术影响力。但是,随着史料考证及学术研究的深入,学界对“笛上三调”的“调式说”有了反思,先后出现了“音阶说”和“调高说”。然而,很多学者在阐述“音阶说”和“调高说”的同时,并未对“调式说”作出否定性结论,个别学者只是在评介杨荫浏的“调式说”时,简略地发表了一点看法,而且主要针对的是“新音阶”产生的年代问题。其中谈到:“至于说‘下徵调是一个新的调式,这一调式的流行,将在我国历史中造成了新音阶的确立’,这肯定是不对的。曾侯乙编钟等大量可信资料业已证明:‘新音阶’不新,新音阶至晚已在春秋战国时期流行,放到西晋再‘确立’未免太晚了。”[3]
愚以为,“调式说”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为“调式”问题处于整个乐调系统的“末端”,并不受乐器(人声)种类、音律逻辑、音列结构等“数理因素”的限制,而主要取决于音阶属性、乐曲音调、地域风格及情感表现等“人文因素”。无论是“五音列”“七音列”,还是“三音列”“四音列”,也无论是“古音阶”还是“新音阶”,各自均具有宫、商、角、徵、羽五种调式选择的可能。因此,言及宫调式、徵调式、角调式,必须以实际作品为依据,而且还要辅助“听觉”感悟。就荀勖笛而言,无论它属于一种“七音列”还是三种“七音列”,都不可能只体现三种调式,仅通过史料对“律笛”音列结构设计的简单描述,就断定“笛上三调”是三种调式,缺乏实践基础和可信度。另外,既然每笛能够实现“三宫二十一变”,也就不可能只限于三种调式。以上几点足以证明,“正声调”“下徵调”“清角调”不属于“调式”概念。
关于“音阶说”。黄翔鹏先生在论证“同均三宫”问题时曾经将荀勖笛上三调作为源头和立论依据。其中谈到:
荀勖笛律的每均三宫,正是魏晋清商乐兼用的三种音阶:古音阶、新音阶加上俗乐音阶的商调式。……荀勖把第三种音阶在笛上的排列形式称作“清角之调”是用了特殊的命名法,并有当时“清商乐”的艺术实践作为依据的。他不给正式的音阶名称,不称“调”而称“之调”,实在是把宫、调分为两层,称为清乐之调式,即以清乐正声调为准,当做清乐正声调之角来称呼的。[4]
对此,有学者认为“黄翔鹏的意见是合理的”。并阐发了如下观点:
以此观之,荀勖的笛上三调,正好构成了“同均三宫”这三种音阶结构不同的调式。……三调问题,自建国初起就是研究者们所热衷的焦点。黎英海《汉族调式及其和声》一书将三调归入一个系统而相提并论,有着首倡之功。不过他所定的三个名称“雅乐音阶”“清乐音阶”“燕乐音阶”则不甚确切。自黄翔鹏提出“同均三宫”的理论,这一问题就比较清楚了。他所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正是荀勖的笛上三调。[3]
首先,通过对“调式说”的分析论证不难发现,“音阶说”的问题与“调式说”存在共通之处。也就是说,既然是俗乐音阶为何只限于“商调式”?如上所述,音阶属性和音列结构与调式类别关系不大,仅依据一种音阶的七音列结构无法确定调式类别。三种不同的音阶或音列结构均可以表现同一调式;反之,三种不同调式完全可以隶属于同一属性的音阶或音列结构。因此,“俗乐音阶的商调式”的说法不能成立。
其次,“清角”与“俗乐”“清商”等概念的属性完全不同。在“笛上三调”中,“清角”是作为“阶名”出现的,应该与“正声”和“下徵”为同一层次的概念,“正声”即“宫”(声),“下徵”即“徵”(声),这在有关“笛上三调”的一系列史料中都有明确记载。如“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5]、“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5]等等。“正声”“下徵”“清角”作为“阶名”概念,与“俗乐”或“清商乐”无必然联系。因此,将“清角之调”说成是“俗乐音阶的商调式”逻辑上讲不通。即使“清角之调”是音阶概念,也不能仅局限于“商调式”。
另外,如果“笛上三调”的设计旨在强调“三种七声音阶”(同均三宫),根本不存在“下徵之调”以及“假用黄钟以为变徵”等问题,因为“新音阶”不存在“变徵之声”;又因为三种七声音阶(三宫)在同一个七音列(同均)上,故无需采用“哨吹令清、假而用之”的按半孔吹奏。总之,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将“笛上三调”的“正声调”“下徵调”“清角调”与三种七声音阶相提并论,有悖音律逻辑。
关于“调高说”。近些年来,在“以宫定调”传统的影响下,“宫”等于“调高”的观念被普遍接受。由于在“笛上三调”的史料中,有“三宫二十一变”的文字记载,这样便产生了“调高说”,“正声”“下徵”“清角”也就成为了“调高”概念。比如,有学者为否定“音阶说”,明确指出:“所言‘三宫二十一变’,其‘三宫’并非‘同均三宫’理论作为三种音阶的‘三宫’,而是上面所阐明的一种音阶之三种调高的‘三宫’(三均)。‘三宫二十一变’的实质含义,其实是说三种调高的三宫,每宫七声,三宫则有二十一种音级变化的意思。”[6]又如,针对“其御府笛正声、下徵各一具”等史料记载,有学者认为,“御府笛中原有正声、下徵笛,正声、下徵是笛上原有的调名,于此则指两具不同调高的笛。”[7]这里,“正声”和“下徵”不仅成为了“调高”概念,甚至被认为“是笛上原有的调名”。
“调高说”究竟能不能够成立,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对“调高”概念作简要界定。严格地讲,“调高”起码涵括“宫”(声)和“律”(高)两部分内容,单纯的“宫”(阶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调高”概念,真正的“调高”是“宫”(声)的音高标准,即某一音律的律高。关于“律高”的“定调”作用,古代文献中也有明确解释。即:“十二律为定名,宫商角徵羽为虚位。故朱子谓审音之难,不在于声而在于律”[8]。离开“律高”,“宫”是不存在的。如简谱中的“1(do)=C”(调号),其“调高”是“C”,故被称为“C调”。以往,人们之所以将“宫”视为“调高”,只是一种“借声论律”的通俗性“口语”表达方式。明确这一点,对解读“笛上三调”尤为重要。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宫”等于“调高”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不利于“调关系”的形成和建立。不可否认,“三宫二十一变”中的“三宫”的确说的是三种调高,但如果单凭此就认定“笛上三调”仅仅是调高概念,实在是降低了荀勖“笛上三调”所应有的学术价值,也失去了研究的必要。不难理解,无论是杨荫浏的三种调式说,还是黄翔鹏的三种音阶说,各自不仅没有否定“调高”,而且都是以三种调高(即黄钟宫、林钟宫、姑洗宫)为前提的,这在杨荫浏和黄翔鹏所列的“笛上三调表”中都有明确体现,史料中也有明确记载,而且一目了然。另外,如果仅仅说的是三种调高,后人也就不会在此问题上产生疑惑和纠结,因为“笛上三调”本身就是三种调高。可见,“调高说”只能算是一种大实话。古人之所以用“正声”“下徵”“清角”来指代“三种调高”,显然不是单纯地在阐述三种调高,更不是为了揭示三种调高,而是为了探求和验证与三种调高密切相关的更深层次的内涵原理。
“正声调”“下徵调”“清角调”虽然都含有“调高”因素,但它们凸显的是三个“阶名”。由于缺少音高标准,其“调高”会依律高的不同而变化,文献对此也有明确的记载,亦即前面提到的,“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这也就是说,不论“黄钟之笛”还是“大吕之笛”,都可以产生“正声调”和“下徵调”,其“调高”概念既无法认定,更无以言表。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正声调”“下徵调”“清角调”三者之间是相互参照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各自均不能单独存在(见下述)。在前面提到的“其御府笛正声、下徵各一具”的史料中,古人为什么把“正声”和“下徵”绑定在一起,所强调的就是各自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参照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假如文献记载的是“其御府笛正声一具”就会令人无所适从。再举一简单例子,说某人手里只有“G调梆笛”无可厚非,而如果说某人手里只有“正声笛”,则会让人匪夷所思。当然,文献中的“其御府笛正声、下徵各一具”的记载,也不排除有两种不同型号(即中、低音)的“律笛”的因素在里面。总之,“正声、下徵”两种“阶名”的使用,不是单纯地在强调两种“调高”,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两具不同调高的笛。如果认为“笛上三调”是“调高”概念,试想:哪有“调高”不能单独存在和使用的道理?这也足以说明,有学者认为“正声、下徵是笛上原有的调名”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阶名”只能作“调式”之名,不能作“调高”之名,“笛上三调”的“调高说”不成立。
二、“笛上三调”原理解读
根据文献记载可以看出,荀勖笛的七个音律是按“三分损益法”设计的,反映的是“雅乐七声”(古音阶)。对于十二支荀勖笛来说,凡以第一孔为“宫”的“调”都属于“正声调”(本调),以“正声调”为基准,通过改变调高位置,从而获得“下徵调”和“清角调”,这就是所谓的“笛上三调”。以黄钟笛为例,除了调高为黄钟的“正声调”外,还可以产生林钟为调高的“下徵调”和以仲吕为调高的“清角调”。
关于“下徵调”,文献记载的很清楚,“下徵之调,林钟为宫,大吕当为变徵,而黄钟笛本无大吕之声,故假用黄钟以为变徵也。”[5]从这段文字记述来看,“下徵调”仍然属于“雅乐七声”。由于黄钟笛没有大吕,对于以林钟为宫的“下徵调”来说,要获得“变徵之声”,需将黄钟高半音吹奏,即文献中所说的“假用黄钟以为变徵也”,从而获得“下徵调”。
关于“清角调”,文献中的记载是:“清角之调,以姑洗为宫,即是笛体中翕声。于正声为角,于下徵为羽。清角之调乃以为宫,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清角之调,唯宫商及徵,与律相应,余四声非正者皆浊,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5]这里需要考证是,以“姑洗为宫”的“清角调”之所以出现有角、变徵、羽、变宫四声对不上的情况,不是“清角调”本身的问题,而是古人的论证有误,其根源在于固守“三分损益法”,而且忽略了音律相生的数理逻辑关系。对于七律(声)而言,“仲吕”(清角)可以生出“姑洗”(角),而“姑洗”(角)则无法生出“仲吕”(清角),即使姑洗能够生仲吕,也早已超出了七律范围。所以,姑洗升高半音作为“清角”(宫),有悖七律(声)相生的基本原理和音律逻辑关系法则,故造成“正声调”与“清角调”有四个音对不上,致使“正声调”与“清角调”无法形成良好的“调关系”,更无法用语言将其表述清楚。这也正是“注文前后不一,根本就表述不清”以及“在其后十一律笛的记述中,每笛三调中也只提到了正声调和下徵调,没有清角调”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今天很多学者错误地认为“转清角调实际不可能”[6]的主要原因。
就荀勖黄钟笛而言,“清角之声”必须由“蕤宾”(变徵)降低半音获得。通俗地讲,“清角”是“4”(fa),而不是“♯3”(♯mi),但“三分损益法”产生不了“4”(fa),只能产生“♯3”(♯mi)。如此一来,就涉及到了“五度相生法”。仲吕(清角)是黄钟(宫)下生五度所得,用“仲吕”(宫)取代“蕤宾”(变徵),便产生了“清角调”,而不是将“姑洗”(角)升高半音成为“仲吕”(宫),更不能用“仲吕”取代“姑洗”,因为“仲吕”(清角)为“宫”时,“姑洗”为“变宫”。在“正声调”与“清角调”的关系上,这种严密的音律逻辑关系不能有任何差错,否则就会出问题,将会给后面的实验论证造成极大困难,文献中有关“清角之调”的错误设计和论证就是最好的例证。
实际上,“笛上三调”的理念是“五度相生”,而非“三分损益”,其中,“清角”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清角”是“宫”的下方五度音,“三分损益法”永远无法获得“清角之声”。换言之,“清角调”是“正声调”的下方五度调,相当于今人所熟知的“下属调”,而“三分损益法”无法获取到“下属调”。不明白这一点,就永远无法破解“笛上三调”之谜,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调关系”原理及话语体系,也就会因此丧失建立和传承的可能。在“笛上三调”问题上,古人虽然有“五度相生”的意识和理念(魏晋之前“五度相生”就已付诸于理论和实践,如“新音阶”“琴五调”等),但在其论证的过程中,却固守“三分损益”,因而导致各种矛盾的产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疑惑。下表是在黄钟律笛上所产生的“笛上三调”。
表格告诉我们,作为“正声调”的上五度调(下徵调)和下五度调(清角调),各自只改变了一个音级(律),完全符合“近关系调”的理论要求。无论“雅乐七声”(古音阶)还是“清乐七声”(新音阶),其“笛上三调”的“调关系”(五度相生)原理是不会改变的。假如是按“清乐七声”设计的“律笛”,要获得“下徵调”,只需将“正声调”的“清角”高半音吹奏成为“新调”的“变宫”即可;要获得“清角调”,只需将“正声调”的“变宫”低半音吹奏成为“新调”的“清角”即可。可见,“笛上三调”(包括其它“三调”)并不受音阶类别和音列结构的限制,这是建立我们自己的“调关系”原理的基石,也是今天探究荀勖“笛上三调”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孔序筒音第五孔第四孔第三孔第二孔第一孔背孔 音 律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南吕应钟黄钟大吕太簇 正声调角 变徵徵羽变宫宫 商 下徵调羽 变宫宫商角 变徵徵 清角调变宫宫 商角变徵徵 羽
通过以上的论证不难理解,“笛上三调”所要探究和揭示的是一种“调关系”原理,而这种“调关系”早在魏晋之前就已经存在,即“相和三调”和“清商三调”,荀勖“笛上三调”的最大贡献,就是采用“阶名”形式使“三调”理论更加明确和具体化。虽然在求证过程中没有摆脱“三分损益”的束缚,但是将“正声调”“下徵调”“清角调”纳入同一个系统中,以及明确使用“清角”这个“宫调”术语,已经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因而具有里程碑意义。
关于“三调”之名,古代文献中早有明确记载,即:“三宫,一曰正声,二曰下徵,三曰清角。”[5]作为一种“调关系”原理,“正声调”“下徵调”“清角调”三者之间,围绕着“正声调”(本调或称主调)形成了相互依存和相互转换的关系。所谓“相互依存”主要表现在:“下徵调”和“清角调”是基于“正声调”而产生的,“正声调”又因“下徵调”和“清角调”而存在。亦即,“下徵调”是“正声调”的下方四度或上方五度调,反之,“正声调”又是“下徵调”的上方四度或下方五度调;同理,“清角调”是“正声调”的下方五度或上方四度调,反之,“正声调”又是“清角调”的上方五度或下方四度调。所谓“相互转换”主要表现在:原“下徵调”或“清角调”可以转换成为新的“正声调”,而原“正声调”也可以转换成为新的“下徵调”或“清角调”。所有这些都是以“五度相生”为原则的,如果固守“三分损益”,“笛上三调”(包括其它“三调”)将无从谈起,更不可能得到利用和传承。由此也说明,“五度相生”在建立中国传统宫调理论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性是“三分损益”无法替代的。一言以蔽之,所谓“正声调”“下徵调”“清角调”,相当于西方乐理中的“主调”“属调”“下属调”。
不论是西方乐理中“主调”“属调”“下属调”,还是我们自己的“正声调”“下徵调”“清角调”,其“调关系”的提出和建立,都是为了“转调”或“旋宫”的需要,“笛上三调”的理论及实践探索,其目的也在于此。关于荀勖“笛律”中的“还相为宫”之法,《宋书·律历志》中有明确记载,而且,文献中所述的“三调”内容均与“旋宫”问题有关。如:
下徵调法,林钟为宫,第四孔也。本正声黄钟之徵,徵清当在宫上,用笛之宜,倍令浊下,故曰下徵。下徵更为宫者,记所谓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也。[5]
由此可见,“笛上三调”中的正声、下徵、清角之名,是为“还相为宫”技法的形成所创设的“调关系”术语,这一点,毋庸置疑。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回到前面曾经提到的杨荫浏先生所说的“第一个矛盾”上来。杨先生认为,“既然一笛可吹三宫,则吹十二宫,并不需要十二笛”,甚至认为“这里暴露了荀勖笛律脱离传统和脱离实际的特点”。但笔者认为,“一笛吹三宫”,从理论上讲,是建立“调关系”的需要,从实践上讲,是乐曲“旋宫”的需要。对于乐曲中出现的“正声调”与“下徵调”或“正声调”与“清角调”的“旋宫”,只需在一支笛上就可以实践和完成,无需(也不可能)临时更换另一支笛子。此外,在同一支笛上吹奏“三调”,也是为了获得不同的音域和音色。以上两点,早已在笛乐实践中被广泛应用。至于杨先生所说的第二个矛盾(“清角调是吹不准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古人的论证或文字记载有误,而非“清角调”本身的问题,这些已在前面的论述中作了探讨,在此不赘。可见,杨荫浏先生所认为的“两个矛盾情形”,对于“笛上三调”来说,都是不存在的。
不仅如此,“笛上三调”原理中所采用的“正声”“下徵”“清角”之名,使原有的“三调”术语(相和三调、清商三调)更具有可操作性和传承性。在“夫宫,音之主也”的理念统领下,古人将“宫声”视为“正声”。即,“其宫声正而不倍,故曰正声”[5]。所谓“下徵”就是“宫声”下方的“徵声”,二者又与“琴调”密切相关,“笛上三调”中的“正声调”与“琴调”中的“正调”(三弦为宫)相似相近,由此演绎出了“下徵”之名,而且与乐调实践关系密切。“正调”的最低音就是“宫音”的下方“徵音”,故曰“下徵”。这一点西方也如此,在早期的西方音乐实践中,“属音位于主音上方纯五度的概念,也只能说是存在于抽象意义之中,因为在大量的音乐环境中,属音本身经常出现在主音‘下方’的纯四度,而不是‘主音’上方的纯五度。”[9]同样道理,作为“阶名”的“清角”与“正声”(宫)的下五、上四的关系也是十分明确的,对于“清角调”的识别和确立,不会存在任何认识上的问题。
总之,“笛上三调”所采用的“正声”“下徵”“清角”的“三调”之名,以及所形成的“调关系”原理,丝毫不逊色于西方的“主调”“属调”“下属调”,而且比西方的“调关系”理论要久远得多。因为,西方的“主调”“属调”“下属调”之名及其“调关系”理论,应该在拉莫(1683-1764)“确立调性中的主、属和下属和弦”[9]之后,比起荀勖(?-289)所处的魏晋时期,大约晚1400余年。另外,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上讲,中国传统宫调理论中的“近关系调”原理,比西方大小调理论中的“近关系调”概念,更具有民族性和继承性。这主要是因为,“笛上三调”中的正声调、下徵调、清角调以“调高”为理据和实践基础,体现了“以宫定调”的传统和“夫宫音之主也”的理念。西方的主调、属调、下属调以“调式音阶”为依据,在体现“主调”及其所属“调关系”问题上,“调号”的作用并不十分明确,也就是说,“主调”究竟是G大调还是e小调,仅通过“调号”无法确知。“笛上三调”则不然,由于“笛上三调”中的正声调、下徵调、清角调,代表的是三个“同宫系统调”,其“调号”不仅在“正声调”(主调)的明确上能够做到一目了然,而且对包括“下徵调”“清角调”在内的“三调系统”的揭示也十分明了,因而具有理论与实践认知上的高度一致性和易操作性,其话语体系的构建清晰、完满,特色鲜明。
结 语
通过对“笛上三调”的辨正和解读,可以确信,“笛上三调”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乐学概念,而是历史上已有的“相和三调”“清商三调”的延续和拓展,是秦汉以来古代“旋宫”理论和技法在“律笛”上的实践性探索。“正声调”“下徵调”“清角调”等相关术语的正式提出和使用,说明中国传统宫调理论体系中的“调关系”原理早在魏晋之前就已经形成,同时标志着与此相关的乐调实践不断发展和相对成熟。如果否认“调关系”术语的存在,自古以来的“旋宫转调”理论和技法将无法成立,在努力构建中国传统宫调理论话语体系的当下,这一问题值得学界重视和思考。因此,解构“笛上三调”,探究“旋宫古法”,是整理、规范中国传统宫调术语的重要内容,不仅有利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话语体系中的“调关系”原理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也将为解惑“相和三调”“清商三调”等相关宫调术语提供思路和借鉴。在提倡文化自信、文化传承的今天,用哲学的理念、逻辑的思维以及运用现代技术和方法,对包括“笛上三调”在内的传统宫调术语的研究考释以及整理利用,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责任,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2]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Z].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
[3]王子初.荀勖笛律研究[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4]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5]丘琼荪校释.历代乐志律志校释(下)[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
[6]杨善武.史料史实与“同均三宫”[J].中国音乐学,2013(2).
[7]冯洁轩.调(均)·清商三调·笛上三调[J].音乐研究,1995(3).
[8]王小盾,洛秦.中国历代乐论(清代卷)[M].桂林:漓江出版有限公司,2019.
[9]托马斯·克里斯坦森编;任达敏译.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
J609.2
A
1003-1499-(2021)01-0013-06
刘永福(1960~),男,扬州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传统‘宫调’术语考释”(项目编号:17BD072)的主要成果之一。
2021-01-29
责任编辑 春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