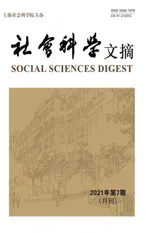郊区社会:城乡中国的微观结构与转型秩序
2021-11-15杜鹏
文/杜鹏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化与市场化等现代性力量的影响下,乡土中国渐行渐远,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城乡中国时代。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差异虽然继续存在,但城乡关系日益紧密,逐渐迈向城乡融合。随着城市快速扩张,位于城市边缘的村庄逐渐成为城市化的前沿地带,并环绕城市形成一定绵延性的郊区。郊区已经构成城乡中国时代的重要景观。作为城乡密集互动的空间地带,郊区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涵,呈现出不同于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独特属性。
1.被遮蔽的郊区社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形成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城乡资源配置的差异逐渐沉淀为城乡社会区隔,并深刻塑造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实践逻辑。城市化主要包含两个维度,分别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人口城市化和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土地的土地城市化,二者在郊区交汇。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限制了郊区农民的身份转变和集体土地直接入市,从而在郊区形成典型的“半城市化”现象。“半城市化”即“未完成的城市化”,其中隐含了村落终结的规范性预设。在城市社会的参照下,郊区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外部视角,即主要站在城市的视角看待郊区,其视野难免聚焦郊区“亦城亦乡”状态引发的问题,缺乏关于郊区本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的深入分析,凸显了城市化进程中郊区的负面与无序的色彩。
若着眼于城市化过程的长期性和渐进性,郊区事实上具有动态的相对稳定性。作为城市边缘的郊区始终是一个客观存在。郊区演化更替的动态过程中逐渐浮现出一个相对稳定且具有普遍意义的郊区社会,它既作为根据地承载了流动人口的城市梦,又是郊区农民通往城市的起点。因此,郊区社会是城乡中国的微观结构和经验缩影,本文试图以内部视角阐释郊区社会的构成机制与演化逻辑,合理定位城乡中国时代郊区社会的意义。
2.作为社会实体的郊区社会
郊区不仅是一种空间形态,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本文试图跳出郊区城市化的生命历程,基于郊区村庄的内部构成,探究郊区社会的基本结构。城市辐射之下的郊区村庄依然是作为社会实体的郊区社会之建构的基本单元。郊区的人口、土地等要素深度参与城市经济社会运行,在开放的经济社会系统中形成以郊区村庄为内核、以郊区农民为主体的“再结构化”。为此,本文致力于在村庄层次揭示郊区社会的实体性,其中隐含了研究视角的转换,即以“结构”替代“转型”,从而为模糊性的体制结构与过渡性的地理空间注入丰富的社会学内容,在城乡互动中发掘郊区村庄的秩序机制。“农民—市场”的关系与“农民—集体”的关系是编织郊区社会的主线:一方面,便利的区位条件使其直接处于城市辐射之下,意味着郊区具有更丰富且低成本的市场机会,这不同于一般乡村社会的市场压力有余而市场机会相对稀缺的状态;另一方面,郊区村庄的集体体制意味着郊区农民与集体土地依然保持着相对紧密的利益联系,因而有别于城市社会的利益结构。
郊区社会的形成基础
郊区社会是城市化的产物。首先,郊区是一个空间概念。作为空间意义上的郊区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市场机制的辐射效应,具有较大的动态性。其次,郊区是一个制度概念。郊区的经济社会要素配置不仅服从于市场逻辑,而且受到集体制度规定。郊区村庄的集体体制维系了农民与土地的关联,限定了要素配置方式与方向,郊区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可见,郊区始终处于市场机会辐射与集体体制限定的双重因素影响之下。
1.郊区社会的空间区位
郊区社会的空间区位主要表现为邻近城市中心的市场距离。较近的市场距离赋予郊区社会三个鲜明特点。第一,本地市场就业。较近的市场距离孕育了郊区的本地就业市场,这不仅降低了郊区农民劳动力市场化的成本,而且强化了农民社会资本的可积累性。第二,城市生活面向。邻近城市的市场距离强化了城市的辐射效应,城市生活的内容、观念笼罩着郊区社会。第三,流动人口集聚。郊区的区位条件吸引流动人口集聚,由此释放的消费需求构成郊区农民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影响了郊区农民的家庭策略和关系运作。较近的市场距离使郊区村庄深深地卷入城市系统。
2.郊区社会的制度基础
郊区虽然位于城市化的前沿地带,但是,郊区的集体体制限制了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郊区农民依然是集体成员,郊区土地主要是集体土地,农民基于集体成员享有土地权利和土地利益。城市扩张、土地开发与宅基地资本化提高了郊区的土地价值,强化了集体的土地开发意愿和农民的土地权利意识,集体因而呈现为“福利共同体”的形态。农民与集体的利益关系增强,集体趋于实体化。集体内部的利益分配和关系协调塑造了郊区的社会形态。作为郊区社会形成的制度基础,集体体制不仅避免了郊区村庄资源的过度流失,而且降低了郊区农民市场化的风险,维系了郊区社会的相对稳定性。郊区的空间流变因集体体制的规定而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
3.郊区社会的动力机制
郊区村庄的空间区位和制度结构重构了郊区社会再生产的动力机制。其中,邻近城市空间区位为郊区社会注入市场机会,集体体制为郊区社会搭建了制度框架。城乡关系在郊区村庄的微观场景中呈现为市场化和集体化的双重动力,扩展了农民行动的机会结构,这有助于避免郊区农民陷入家庭内部动员的压力结构和村庄关系的疏离状态,为郊区村庄社会学内容的生长提供了空间:第一,市场动力深度参与郊区村庄社会的形成过程,不仅推动了农民的劳动力市场化,而且改变了集体的经营条件,重塑了农民与集体的关联模式;第二,随着土地财产性价值凸显,集体不再只是若隐若现的制度背景,而是贯穿于郊区社会再生产实践,并围绕集体土地利益分配凝聚为动态稳定的郊区社会结构。可见,集体化虽然存在制度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市场化的动力激活,进而呈现出与其相反相成的动力机制。市场化和集体化的动力改变了传统村庄秩序机制,重构了农民家庭与村庄社会的关联模式。
郊区社会的基本形态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乡村社会的认识绕不开“熟人社会”这一概念。在理想类型的意义上,熟人社会植根于农民与土地的实践性关系,并孕育了伦理本位的家庭形态与人情连带的村庄关系,二者相互联结,赋予熟人社会以公私融通的特征。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原初关系,市场化和集体化的动力机制触发了家庭形态与村庄关系的调适,它不仅释放了家庭关系的情感实践空间,而且稀释了城市化进程的压力。郊区村庄的空间区位与制度基础赋予其适应城市化转型的比较优势。
1.郊区社会的家庭形态与情感实践
传统家庭绵延是以家庭伦理责任为核心的代际互动和代际更替,家庭关系中的情感互动处于依附性地位。在紧密的城乡互动中,郊区农民家庭再生产面临着不同的约束条件。首先,郊区的区位优势降低了郊区农民家庭再生产的成本。郊区农民在婚姻市场中居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婚姻成本较低,婚姻风险较小。其次,郊区农民多元化的家庭经济收入来源稀释了家庭再生产压力,维系了父代人生任务的边界。具体而言,郊区农民经济收入主要有务工、务农、福利性岗位、房租收入、集体分红等五个方面。可见,郊区社会的区位条件和制度结构显化了市场化的“机会”而非“压力”的面向,弱化了代际互动的伦理刚性,呈现出父代相对自主和子代温情“啃老”的代际关系格局。
父代的相对独立并不意味着代际关系的松散,而子代的“啃老”也不同于当前在中西部农村普遍存在的“代际剥削”。在子代成家以后,作为资源供给者的父代家庭具有较大的主动权,他们向子代家庭的资源让渡不纯粹是出于刚性的伦理义务,也不是为了“交换”子代的养老预期,而是父代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父代以何种方式、什么程度支持子代主要取决于其自主意志,而较少伦理责任的考量。子代也不认为父代的支持和付出是理所当然,“啃老”并不心安理得。这样一来,父代对子代的支持具有情感增量,促进了代际之间的情感互动。可见,父代人生任务的伦理边界为代际关系中的情感析出提供了可能,情感不再封闭于家庭伦理轨道之中,而是沿着代际间的资源流动获得日常化的实践通道,情感实践因而成为家庭关系的中心,具有塑造家庭关系的独立意义。
2.郊区社会的关系结构与压力配置
郊区社会是村庄社会关系结构化的产物。村庄社会关系兼具功能性与价值性,维系了合作与竞争的均衡。随着人口流出,非郊区村庄内生性价值生产能力趋于弱化,村庄社会关系的功能性侵蚀价值性,导致村庄社会交往失范和社会竞争失控。与此不同,在本地市场就业模式下,郊区虽然处于城市化的前沿地带,但其村庄社会形态却在现代性压力面前保持了完整性。郊区的空间区位和制度基础抑制了郊区社会的竞争程度与分化程度,并通过村庄关系的资本化和集体的去分化机制塑造了低度压力配置的村庄结构,为郊区村庄的城市化转型营造了缓冲空间。
第一,村庄关系的资本化。劳动力市场化和土地资本化的预期激活了村庄社会关系的功能属性。农民交往逻辑趋于理性化,在突破村庄关系网络的同时导致关系的“圈子化”。村庄关系的资本化促进了功能性扩张且与价值性分离,抑制了郊区村庄中社会竞争压力的传递扩散,郊区村庄呈现出理性而平和的关系结构。第二,集体的去分化。郊区集体具有鲜明的福利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市场动力的实践路径,抑制了市场的分化效应:一是集体的公共服务弱化了郊区农民对于市场的依赖;二是集体的福利保障降低了市场风险。福利性集体不仅弱化了郊区农民的竞争动力,而且缓解了郊区农民城市化过程中的风险及其引发的社会焦虑与心理紧张。因此,郊区社会相对平和理性的关系抑制了竞争压力的扩散,有助于维系郊区社会的结构稳定性。
3.城乡融合视野中的郊区社会
郊区社会的家庭形态与村庄结构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情感导向的家庭形态与低度压力的村庄关系相辅相成:一方面,压力稀释的村庄关系结构为家庭关系的情感实践提供了宽松的外部条件,且缓冲了城市化压力;另一方面,家庭关系中的情感实践从基本生活逻辑的层次塑造了郊区社会的关系结构,奠定了社会压力稀释的家庭基础。家庭的情感实践与村庄的压力配置维系了郊区社会的自主性和统一性。这种自成一体的社会形态在其内在秩序机制层面并非无序和紊乱的,而是通过家庭关系的情感实践和村庄社会的压力稀释维系了进退自如的社会生活模式,且沿着市场化和集体化的动力机制不断再生产,从而奠定了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有序变迁的基础。学界关于郊区社会的问题化建构旨在确证市民权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对于郊区农民而言,权利是在市场的区位条件与集体的制度条件下定义的,本地市场与集体福利共同编织了郊区农民的生活世界,不仅彰显了家庭的情感维度,而且抑制了村庄竞争压力,赋予郊区社会理性且富有温情的特征。
郊区社会的空间梯度与转型逻辑
空间意义上的郊区并非均质状态,而是呈现为从城市向乡村逐渐绵延过渡的状态。郊区村庄面临的市场化动力和集体化动力事实上存在着不同强度,进而形成郊区社会内部的空间梯度,这自然意味着家庭情感强度和村庄压力配置的差异。若着眼于城市化的转型过程,平和理性的郊区社会形态虽然具有稳定性和包容性,却也可能在特定空间梯度上呈现出保守性和排斥性。因此,需要将郊区社会再生产机制纳入制度的反思性调控,维系市场化动力与集体化动力的均衡,实现郊区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动态匹配。相对于市场化动力的自发性,集体化的动力服从于土地制度的调控,因此,立足郊区社会的空间梯度,通过土地制度调控农民与集体和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促进郊区社会的转型。
空间梯度不仅体现了郊区社会结构的非均质性,而且蕴含了郊区社会转型的基本秩序。从空间区位上看,越是靠近城市,郊区社会的市场化和集体化的动力愈强,二者的张力愈强;越是远离城市中心,郊区社会的市场化和集体化的动力愈弱,二者的互补性愈强。在城市化过程中,郊区空间动态演化的基本逻辑是,核心区域逐渐融入城市社会,原来并非郊区的农村社会逐渐进入郊区的边缘区域,而边缘区域逐渐转变为中间区域和核心区域。这个动态接续的过程维系了郊区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相对稳定性。郊区社会的空间演化不仅取决于城市扩张的能力和限度——它决定了边缘区域向外推移的程度(即郊区社会的外部边界),还取决于动态演化中的郊区社会能否适时地融入城市社会——它决定了核心区域回应城市化并转变为城市社会的可能性(即郊区社会的内部边界)。问题是,核心区域的郊区社会形态也蕴含着排斥城市化转型的可能性。如何使郊区社会再生产的动态过程合乎城市化节奏,依赖针对集体化动力的土地制度调控。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扩张设定了郊区社会的外部边界,而地权调控设定了郊区社会的内部边界,二者共同塑造了郊区社会转型逻辑,维系了郊区社会良性的动态循环。在政策层面,地权调控意味着国家在保护郊区农民正当土地权利的同时,也要避免郊区农民土地财产权意识的过度扩张甚至蜕变为城市化的反对者,从而使郊区社会在由外围向核心地带的演进中维系其结构弹性与社会活力。
结语
由“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的演化逻辑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推进,而是一个复杂的、长时间的城乡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郊区既处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切割之下,又能发挥市场化的区位优势和集体化的制度优势,在郊区村庄的微观场景实现人口、土地等要素的社会性重构。因此郊区不仅是一个空间地理概念,而且具有鲜明的社会学意涵。农民与市场和农民与集体的关系定义了郊区的社会坐标。相对于城市社会而言,郊区的集体体制维系了郊区农民与土地的(财产性或生产性)关联,相对于一般农村社会而言,郊区的市场距离维系了本地化的劳动力市场格局,其集体体制也由此呈现出高度福利化的特征。郊区农民的生产生活虽然越出村庄范围,但依然与村庄保持着或隐或显的关联,进而在郊区村庄的微观层次促进了城乡要素的深度融合与郊区社会的形成。情感导向的家庭形态与低度压力的村庄结构共同构造了郊区社会的基本形态,展现了不同于城乡二元对立视角的社会形态,对于理解城乡中国时代的微观结构具有经验窗口的意义。在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郊区的社会学意义,既要看到郊区社会为郊区农民提供的情感庇护和压力稀释,又要立足郊区社会的空间梯度,通过公正有效的土地制度调控郊区社会的动力机制,从而维系郊区社会的均衡统一,促进城乡关系的良性互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