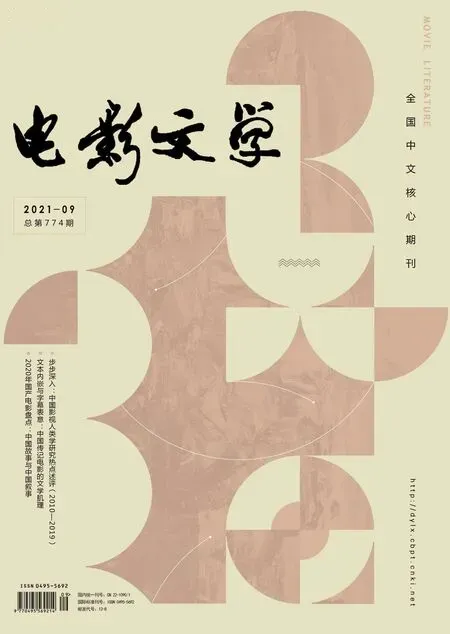“史诗”与“传奇”:1940年代末东北题材电影的家国之思
2021-11-15刘雪姣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25
刘雪姣(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间内,国产电影中出现了一批以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为表现对象的影片。其中既有“纪录片”《看东北》(张天赐编辑,1947年整理,1948年上映),也有以抗战时期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片”《松花江上》(金山导演,1946年11月开拍,1947年9月28日在长春电影制片厂首映)、《小白龙》(朱文顺导演,1948年)、《哈尔滨之夜》(张天赐导演,1948年)。这些影片的集中出现,首次将东北地区的山川风貌搬上银幕,对当时那些以低俗趣味吸引观众的影片产生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国产电影的发展方向。然而,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这类影片的关注远远不够,除了有限的几篇文献提到了《松花江上》之外,关于《看东北》《小白龙》《哈尔滨之夜》等影片,尚未出现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从艺术表现风格及其传递出的家国意识上来看,这一时期集中出现的几部东北题材电影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
一、“史诗”意识的影像表达:《松花江上》
1940年代末,首先出现的东北题材影片是新闻纪录片《看东北》。该片由日伪时期“满洲映画协会”前职员张天赐根据以前拍摄的新闻素材剪辑合成。“《看东北》自日俄战争日本占领旅顺、大连,掌握辽东半岛起,一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无条件投降止,把‘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七七’、伪满傀儡溥仪及汪精卫等尽收镜头,是一部抗战的‘史纪’。”如果说《看东北》这部纪录片提供给观众的是一系列珍贵的“史实”材料,有助于观众进一步了解抗战期间东北沦陷区的真实情景的话,那么,《松花江上》则因为“用血和泪,讲述出东北人民的悲愤和哀愁”而具有了“史诗”的品格。
在《松花江上》这部影片开头,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农家院的场景,随后镜头切入室内,展现的是一家人温馨的生活场景。外景方面,随着大车队的到来,镜头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街上繁华的场景。而当镜头再次切换至室内时,王人路饰演的“表哥”从外地给张瑞芳饰演的“妞”以及“妞”的母亲带来了“花布”和“针线”等礼物的情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经典再现。而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日军的入侵先后造成了“妞父”与“妞母”的惨死。影片借“爷爷”之口道出了侵略者给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带来的灾难:“哎!现在这个家成个什么样子了!你看院子没有人收拾,马厩里也没有牲口,房子也塌了,鸡呀,猪啊都让鬼子给抓去了”,镜头也随着“爷爷”的倾诉将破败的院落呈现在银幕上。这里强调的,是普通老百姓家园被毁之后的凄凉景象。影片没有直接展现老百姓为“国”捐躯,而是处处强调发生在普通农民身上的悲剧,但当影片将这些悲剧串连起来时,其背后却清晰透露出“国”的意识。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影片将“九一八”之前东北人民平静、祥和的日常生活作为整个故事展开的“底色”,才使得后面展现的“家仇”与“国恨”更能唤起观众的切身感受:日本侵略者给中国普通民众带来的苦难正是对这种日常生活的破坏,从而使得影片对苦难的呈现更加接近现实生活本身。“家”这一基本单位不仅是《松花江上》展开叙事的基础,由不同的“家”所组成的“家园”遭到破坏也是东北民众奋起反抗侵略者的直接原因。由于这种反抗行为在客观上表现出的“革命性”与“国”产生的必然联系,并且,“为革命而死之所以被视为崇高的行为,也是因为人们感觉那是某种本质上非常纯粹的事物。”因此,“国”的概念在这里便具有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色彩。
围绕影片展开的评论也大多强调其“真实性”,原因在于它“描写了一个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包含着血肉,也表现了人民的抗战的农民性格”。换句话说,在当时人眼中,《松花江上》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真实”。更重要的是,《松花江上》以普通农民在战争环境下的生活作为表现对象,以此来展现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老百姓在战争中的艰难困苦:“出现在这戏里的,没有英雄,没有俊杰,他们都是平凡的乡下人,怀着一颗善良、温厚的心,过着劳苦而忍耐的生活”。这就突破了以往国产影片以都市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取材手法。正是基于上述观点,有人指出《松花江上》这部影片为中国电影开辟了新的方向:“由于这部戏的适度的成功,更给中国电影的取材开辟了一条新路,即不取材于都市的繁华生活,也同样可以拍出好的影片。”而《松花江上》的这种表现方式也被当时的评论者认为是摆脱了当时国产电影普遍的低俗趣味,进而开辟了中国电影的“新路向”。实际上,这种对电影真实性的讨论早在1940年代初期就已经出现,并且提出了“新的写实主义”的创作论,讨论的结果是:“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在于揭示生活真实。强调电影的真实性,坚持政治需要与生活真实的统一,也就抓住了提高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关键。”由此看来,围绕《松花江上》“真实性”的讨论是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对该片成功原因的分析自然也应当注意到这种理论背景。
除了以上讨论之外,该片的成功也引起了当时文艺界的注意,并且,从来自文艺界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该片的评价更注重其社会现实意义与思想性。冯雪峰在《谈〈松花江上〉》一文中便指出:“《松花江上》可以说明作者已走近历史,也就走近艺术和艺术的思想性。”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冯雪峰认为该片不仅仅体现了当时电影界的“新路向”,它还“在电影对人民的艺术趣味和现实认识的教育上,能够和以小市民支配论为根基的市侩主义观点开始剧烈的斗争,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思想斗争。”
无独有偶,在同一天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胡风的《从〈松花江上〉看电影艺术》一文。胡风认为《松花江上》的成功在于它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展示提示出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即胡风所说的“通过这个现实感所表现的东西”。并且,他还指出了该片在技术层面的重大突破,即它“超过了用连环图画来叙说故事的水准;一般地说,没有为了交代情节的所谓‘过场戏’,没有为了解释故事发展的说明,一个一个的画面都是作为企图达到表现内容要求的总的旋律构成底谐和的成分”。这与此前的那种夹杂着“旁白”“补白”式的影片相比,实现了技术层面的重大突破。
但另一方面,影片中一再重复的情节设置还是容易使人感到理念化的成分过于突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松花江上》这部影片中,主人公“表哥”几次历险最后都幸免于难,这里面除了如当时有人指出的“这正和旧小说中的‘戏不够、神来凑’一样”之外,更与导演试图通过这种多少有些牵强的“偶然”来串连故事情节,并且以此突出这部影片的积极色彩有关,即“剧作者和导演人,在这片子中原是想表现出东北民众在敌伪压迫之下是怎样生活的”,“假使这一对主人翁和别人一样地死去了,这故事也就无法发展下去了。”也有人看到了该片风格上的“知识分子”气息:“许多剧中人的情绪,思想上的转换,都颇有着知识分子罗曼蒂克想象的痕迹,展现在银幕上,就使人觉得有点‘传奇’或不切真实之感。”
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该片通过对比日本侵略者入侵东北前后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化,将“国恨”植入“家仇”的情感逻辑之内,从而使得该片在表现东北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时毫无生硬、牵强之感。局部的瑕疵并不会削弱影片的整体价值。因此可以说,《松花江上》的“史诗”品格是以“家园”为“底色”将“家仇”与“国恨”勾连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审美价值与现实意义完美结合。
二、抗日“传奇”片:《哈尔滨之夜》
如果说《松花江上》是“在平凡中发现内在的深度,从单纯中发现无穷的真理,且表现了壮伟的时代和坚实的人生”,并因此被视为是一部表现东北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史诗”的话,那么,围绕《哈尔滨之夜》的评论则呈现出较大的分歧。原因在于该片在情节设置方面将表现的重心放在了韩二虎个人性格的转变方面,并未展现出宏观层面的民众抗日图景。
从该片的“电影剧本提要”中可以看到,影片的故事背景是:“傀儡溥仪登基第八年,正是他的主子日本加紧统制在它魔手下的东北的时候。对号称小莫斯科的国际都市哈尔滨更是箝得无孔不入。”然而,随后的情节设置则逐渐转向了以“家庭”“情感”“伦常”为主旋律的发展方向。先交代了女主角芳华“虽是安娜酒家的红歌女,回到家里,她却是个贤良的主妇”,她不仅孝顺婆婆、照料女儿,而且“她更日夜思念着几年未归而复渺无音信的丈夫志强”。这种情节安排无形中突出了人物对“家”的团圆的期待。并且,男主角韩二虎一出场就带有一种“侠义”之风:他先将被盗香烟归还给芳华的女儿小华,随后又不费吹灰之力便摆平了前来惹事的地痞流氓。这种情节设置同样使我们想到中国传统人伦关系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文化元素。但是,上述温馨、平静的生活随着日军的出现而被彻底打破。先是韩二虎被日军长官松田收买做了汉奸打手,接着又是义勇军首领志强被韩二虎打死,这又间接导致了志强的老母亲气绝身亡。至此,影片开头部分展现的关于“家”的美好图景彻底被摧毁。而后,当韩二虎得知自己杀死的正是有恩于他的人时,顿时良心发现,跪在芳华面前痛哭流涕,请求原谅,并放走了芳华和小华,等待与松田、上野等人拼命。寡不敌众的韩二虎在射杀了上野之后被松田杀害,随后,松田追赶上芳华并当着她的面将小华杀死,孤身一人的芳华最终引爆了船上的炸药与松田同归于尽。
从影片讲述的故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该片实际上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园”“互助”“侠义”等元素,展现了日本侵略者的入侵打破了这种民间伦常,继而引发了韩二虎的“报恩”以及“杀身成仁”等一系列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尔滨之夜》与《松花江上》最大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二者对待“家”与“国”的情感态度上,而在于表现角度的不同。如果说《松花江上》是将“家园之仇”与“民族之恨”放在同一叙事框架之中来展现抗战时期东北沦陷区人民与侵略者之间展开的正面冲突的话,那么,《哈尔滨之夜》则更加侧重于表现“家仇”与“民间生活秩序”遭到破坏之后,个人的情感转变。在这里,全民抗战的时代环境被推向后台,作为影片故事情节的大背景,而重点表现了人物被抛出原本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后的反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韩二虎的“杀身成仁”,还是芳华最后与日军长官同归于尽,都体现出较为鲜明的传统文化心理特征。
正是由于《哈尔滨之夜》是从个体、情感、家庭等叙事单元出发来表现抗战主题的艺术手法,相对弱化了整部影片的主题思想,因此该片上映之后反响平平,甚至引来不少非议。尽管有人指出《哈尔滨之夜》与《松花江上》分别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东北人民抗击日寇的英勇行为:“如果说《松花江上》是一部从正面暴露敌寇如何凶暴地蹂躏东北同胞的血泪史,那末《哈尔滨之夜》正是从反面揭示敌寇又如何阴险恶毒的残害东北同胞的解剖图。”但这种声音很快被淹没。有人认为该片情节设置方面缺乏内在关联:“在《松花江上》里,我们在在有一种强烈的印象,统治者的横暴和人民的受难与英勇的对比,差不多每一寸胶片都由这强烈的对比在牵导着,因此故事的发展也就是合理而自然的。但《哈尔滨之夜》里,这对比倒似乎落入了陪衬的地位”,“我们没有看见整个戏的发展按置在如《松花江上》那样明显而强烈的主题上”。有人指出《松花江上》所表现的是作为“集体”的普通老百姓在日寇压迫下奋起反抗的故事;而《哈尔滨之夜》则侧重表现个体(韩二虎)从“糊里糊涂地做了日本人的走狗”,到后来良心发现之后与日寇同归于尽,强调个体在战争环境下的人性转变。除此之外,“我们万万不可能像在《松花江上》里那样的找到一股使人奋发有为的感召力量,启示着观众:只有坚决的参加抗日,日寇才能覆灭,个人方有出路”。还有人指出从影片人物韩二虎的转变中并不能看到这种转变与日军的凶残、民众抗日的高昂情绪有什么关联:“片子太强调了韩二虎自身的愚钝上,而忽略了那大处的着笔,如像在《松花江上》这部片子中所表现的,敌人之凶残、毒辣、野兽的行为等。”甚至有人直接说《哈尔滨之夜》是一部失败之作:“整个说来,《哈尔滨之夜》没有《松花江上》那样代表着真实的地方性和表现了时代的特质,因此,它不能算是成功的作品。”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到,针对《哈尔滨之夜》的批评大多数是从该片的主题立意方面着眼,指责其未能像《松花江上》那样体现出东北民众与日本侵略者的整体性对抗,这便导致韩二虎这一人物形象的转变显得“失真”、志强领导的义勇军也没有和普通民众发生关联,从而使得整部影片的主题显得十分散乱。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哈尔滨之夜》中韩二虎这一人物形象的转变,不难看出其良心发现的背后透露出的人性光辉。其实,《哈尔滨之夜》除了表现韩二虎的性格转变之外,还有一条潜在的叙事线索使得该片的叙事框架带有明显的伦理色彩,即对芳华与志强一家人的生活由平静到家毁人亡的表现。这里面固然体现了抗日主题,但对芳华一家来说,“家”的毁灭才是切切实实的悲剧,这与抗日主题之间形成了某种潜在的叙事张力,也就使得这部影片的内在意蕴变得丰满起来。
也就是说,在《哈尔滨之夜》这部影片中,“故事发生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尽管“讲述故事的年代”距离“故事发生的年代”并不十分遥远,但这种“讲述”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想象的力量对故事“本事”重新进行“排列组合”,以便使影片可以从特定角度展现“故事发生的年代”的某个侧面。然而,“讲述故事的年代”毕竟不同于“故事发生的年代”,因此,如何“讲述”便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说《松花江上》在某种意义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并且为当时的社会普遍认可的“讲述故事”的方式的话,那么,影片《哈尔滨之夜》所选取的恰恰是有别于《松花江上》的“别一种”角度:以个体、家庭的维度来展现“大时代”中的“小悲欢”。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小悲欢”又的的确确是“大时代”中每一个个体、家庭所经历的切切实实的感受,这些经历串连起来,便构成了一个鲜活生动的“大时代”。
在这一点上,法国电影批评家安德烈·巴赞在评论美国西部片时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对这一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巴赞认为,在1930—1940年代的美国西部片中,仅有少数影片展现了真正的“史诗风格”,大多数“西部片无非是讲一些稚气十足的故事,是幼稚的虚构物,根本不注重心理、历史、甚至纯粹物质的真实”。换句话说,仅仅对西部生活进行简单的再现,并不能展示出西部片的内在价值。而在影片《哈尔滨之夜》中,导演并没有像《松花江上》那样以较为写实的风格凸显主题思想,而是借助“家庭”和“人性转变”这样的视角作为切入点,从情感维度展现东北沦陷区人民在抗战过程中的某些侧面。
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可知,此时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影片只有主题鲜明地表现出“民族抗战”的历史感,才符合战后特定历史语境的期待,才能获得观众的好评,而“在《哈尔滨之夜》里,我们看到的只是片面的、局部的,只限于武装义勇军的行动,这力量是太单薄了,若把人民愤怒及间接地支援抗日运动,也显著地表现出来,这力量就雄厚了,对被压迫的人民,就更能强调出胜利的必然性”。因此,“全剧来说,《哈尔滨之夜》是一个很惨的失败,不仅使人会有‘传奇’,‘侦探’,‘卖弄’之感,而且也并没有越过公式主义的泥沼”。
另外,由于强调电影应当从现实中取材来表现东北民众在抗战中的真实经历,所以当《小白龙》这部同样以抗战为主题的影片上映之后,才引来了意料之外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小白龙》使观众感到的并不是现实而是作者虚构的故事”,“破坏了剧本原有的真实性”。在这里,“真实”与否的标准特指影片是否能够从生活本身的逻辑出发,展现出“自然”状态下民众的生存境遇以及对敌斗争。然而,电影本身作为一门艺术,不可能按照生活原本的样子来展现过去的历史。即便是在当时受到普遍赞誉的“史诗”级影片《松花江上》中,同样可以看到“传奇”的成分。或许可以这么说:1940年代末出现的东北题材电影在展现东北沦陷区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时,既有“史诗”的品格,同时也夹带着某些“传奇”的成分,从而使得这类影片呈现出“史诗”与“传奇”的双重艺术风貌。
结 语
抗战胜利后,将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的深重苦难,以及中国民众不畏日军的残暴奋起反击的史实搬上银幕,成为194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界努力的新方向。在这种时代潮流下,出现了一系列以东北沦陷区民众的抗日斗争为题材的国产影片。这些影片在表现抗日主题的同时,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沦陷时期东北的历史样貌。其中既有以纪录片形式出现的《看东北》,也有表现东北沦陷区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史诗”级影片《松花江上》,还有抗日“传奇”片《哈尔滨之夜》《小白龙》。从其艺术风貌上来看,这些影片都探讨了战争环境下“家”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纪录片《看东北》除外),并且,无论是“史诗”还是“传奇”,其故事展开的基本“底色”都离不开“家”以及与之相应的“民间伦理秩序”等明显带有传统色彩的文化元素,这种艺术表现方式在展现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还寄寓了电影拍摄方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家国之思”,从而使得这类影片同中有异,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尽管这类影片在当时毁誉不一,但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角度来讲,其艺术探索同样值得肯定。此外,从这些影片所表现出不同审美取向来看,它们对沦陷时期东北地区的影像表达不仅为我国国产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而且为后世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史实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