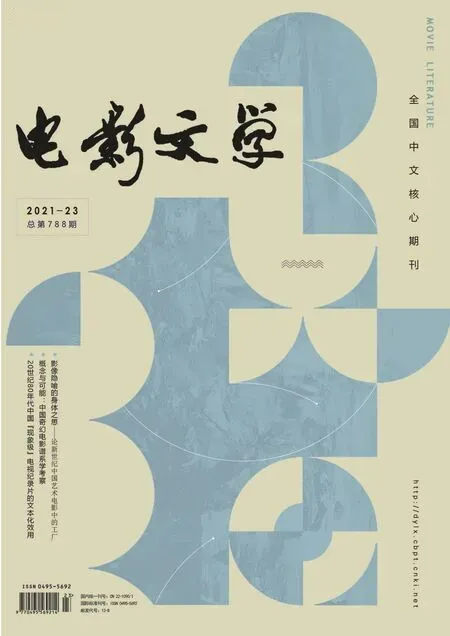《兹山鱼谱》:士人心史的诗化重构
2021-11-14侯力
侯 力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韩国导演李濬益新作《兹山鱼谱》(2021)以诗化改编模式和诗意风格影像呈现李氏朝鲜后期流配士人丁若铨(1758—1816)著书寓志终老海岛的真实故事,影片取名自丁若铨1814年撰成的博物学著作,该书序文也是影片改编依据的原始材料之一。
李濬益以往的历史片作品如《朴烈》(2017)、《思悼》(2015)等大多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兹山鱼谱》则别出心裁地选择了一名由庙堂走向边缘的人物。在历史书写中,边缘人物事迹隐微,多因高洁人格与超俗思想流芳青史,与之对应的“隐逸书写”则寄托历代史家的人格理想与价值评判。达德利·安德鲁认为,电影“对改编模式和改编原型的选择,是很说明问题的,它说明在每一时期电影怎样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和抱负”。称《兹山鱼谱》代表“一时期”显然为时过早,但电影人物的选择以及电影情节对历史本文的改编确实反映出导演长久以来的思考与抱负。概括而论,李濬益导演向慕丁若铨的旷达风骨与超逸人格,在广泛搜集传记、书信、诗文等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展开艺术加工,“以意逆志”地想象历史人物应对流配苦难、边远海岛及思想争端的态度方式,又通过拼接改编、合理虚构来重建叙事、纯化主题,更付以优美冲淡、饶有韵味的影像。影片叙事模式与影像风格相得益彰,呈现出冲淡、高洁的美学品格。
比较电影叙事与历史本文,发现《兹山鱼谱》在改编模式上体现出显著的“诗化”特征,电影创作者从情感、道义与思想的真实出发,对历史本事予以取去裁剪、拼接置换、斟酌损益。电影中的人物、情节与时空并非史料文本的复刻翻译,而是有着导演的虚构想象和主观重塑,带有创作者史观与价值观的映射痕迹。在“诗化”叙事逻辑运作下,古代士人流配著书的苦难本事演变成纯洁生活、实学淑世的山水田园电影诗,进而给当代观众带来情感共鸣、心灵抚慰与道德感召。本文尝试对读历史本文与电影叙述,细致分析影片的诗化叙事模式及其诗意影像呈现,以期为我国诗意历史片创作提炼有益参照。
一、渡海回忆:苦难记忆的诗化复述
历史片叙述人称的选取与叙事距离的建构会影响影片整体的叙事模式。帕索里尼提出电影“自由的、间接的主观化”能够创造诗意,他主张“作者完全深入其人物的内心”,并运用风格化的技巧方式刻画人物心理。帕索里尼最早揭示“镜头视角”的主观化赋予电影诗意,延伸此论,“叙述视角”的主观化也能营造诗意。叙述视角的主观化,是从人物的主观视角展开叙述,从情感的真实出发筛选情节、重构事件,由此统合事与情、言与意。影片《兹山鱼谱》前段即采取叙述视角主观化策略,通过人物的渡海回忆叙述其由起用到流放的苦难历程,并对“记忆”进行抒情化的重构改写。
主观化的叙述视角使《兹山鱼谱》无须像史诗那样“客观”“全面”地铺陈背景,而是可以像抒情诗一样灵活抓取和改编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的情节片段,“记忆”复述的顺序、前后关联与细节填充则隐含着创作者观点。在“渡海回忆”中,电影先后呈现“问对、入教、兴罪、审问、丧亲、流放”六个主要片段。这些片段间原本缺乏因果联系,电影运用跳跃衔接将其串联起来,尤其前三个片段的过渡反复使用“声音先入”的转场手法,后一事件不停打断、覆盖前一事件,剧烈压缩了事件间实际的时空距离。时空压缩凸显情节选取的主观化意图,即以记忆闪回、诗化复述建立人物,以此含蓄表达创作者对人物的评价。
影片将“正祖问对”选为回忆的首个场景,不只因为其发生时序在前,更因为它对建立人物性格具有种子性、始基性的作用。在君臣问答中,正祖告诉丁若铨之所以被选用是因其才学有益国家民生,并告诫丁若铨避免因思想不同而与同僚发生冲突,一旦面对灾祸要学会忍耐、坚持所学、静候正义。这段对话看似平淡、说教,但它作为回忆的首个片段出现,借助君主之于臣子的“神圣性”作用,赋予人物“学以淑世”的价值理想和“持志坚忍”的应事态度。这一情节来自电影的合理虚构,它借明君之口将“淑世”“坚忍”的精神像种子般植入人物性格底层,并随着情节展开与人物成长见证这些高尚品质的发挥与成熟。
电影对丁氏三兄弟应对士祸不同反应的对比呈现是作者诠释人物心迹、含蓄表达立场之处。三兄弟性格不同,应对士祸的方式不同,其人格形成比照互文。面对审问,三弟丁若钟为保全兄弟而自揽罪责,他的慷慨赴死可谓悲壮刚勇;四弟丁若镛则因心中纠结选择沉默,显示出他性格的优柔沉郁;丁若铨的行为最为反常,他果断“变节”矫词自辩,并替丁若镛驳斥指控。电影中丁若铨的反常行动实则是其“坚忍”性格的外化显现,他已经洞观所处危局的险恶,为了保全手足他必须反击抗辩。三兄弟形象的并置呈现,隐含电影作者对于人物的臧否评论。电影对于三弟“刚勇”性格的刻画最为直白,对丁若铨“刚勇”性格的表现则较为曲折、含蓄,但是二人刚勇之气相通,只因所涉境地不同而各有选择,形成人物形象的互文修辞。需要指出,电影此段改编与史实不尽相符。历史上丁氏一案有着特殊的时局背景,案件牵连广泛、获罪者甚多,由于审判不公而上奏申辩、援救者更多。电影改编有意剪去这些“枝蔓”,重点描绘丁氏兄弟的刚毅与友恭,可见叙事并非对历史本文的客观实写,而是从情感道义的理想化重塑人物,寄托电影作者对人物的同情与深意。
影片栗亭分别一段是对丁若镛《栗亭别》诗的改编。原诗从弟弟的视角描写二人泣别之景并抒发对兄长前路的担忧,电影则从兄长的主观化视角对诗歌的物象与情境进行“夺胎换骨”式的重铸加工。电影运用旁白、升格镜头和无声源音乐将“兄弟分别”的顷刻拉长并灌注诗意。旁白低沉平淡地念诵《栗亭别》诗文,人声对愁绪的刻画低回而克制。在仰视视角与升格镜头中,兄弟二人由数名解差监视、背对镜头前行,仰视、背影与慢镜头的综合凸显了行动的踟蹰。无声源音乐则在强弱对比中重复简单的乐句,并不过分渲染哀伤情绪。旁白“强欲转喉成呜咽”的诗文与镜头中丁若铨的临别微笑和言辞宽慰形成情绪张力,文学与图像间的不对称造成含蓄、特别的表情效果。影像虽然保留诗作中的伤感,却过滤掉诗中哀痛的情绪,给诀别的离愁添加一抹旷达的异色。从诗文到影像,“分别”情境经过由“哀痛”向“旷达”的转化,痛感与悲戚被刻意过滤掉,而这种改编恰好符合历史上丁若铨“俊伟”、丁若镛“妩媚”的性格差别,于此可以管窥李濬益导演对于历史人物个性的领会之深。
电影作者细读历史人物,敏锐把握到人物“淑世”“坚忍”“旷达”“俊伟”等性格与心态,影像的呈现以传达人物情感世界的真实性与典型性为指归,对相关历史文本予以拣选、打乱、重排和改编,通过人物主观化视角的复述重塑历史时空,赋予故事哀而不伤的诗意境界,也赋予电影人物高洁不污的诗性人格。
二、温情黑山:边远社会的诗化重构
“黑山”是历史上丁若铨的流放地,在电影中被重塑成温情的诗意空间。“黑山”即“兹山”,位于朝鲜半岛西南海域。对十八九世纪的李氏朝鲜而言,“黑山”是其疆域边缘的贫瘠海岛,时人留下“沧溟路绝岭云孤”“茫茫小岛海中孤”(《退堂先生诗集》卷四)等诗句,直写黑山的边穷可怖。电影镜头中的“黑山”却与诗文记述迥异。电影塑造的“黑山”自然风光旖旎、乡民淳朴善良,空间形象质朴鲜活、宛如桃源,影像氛围也由前段的阴鸷压抑转为明朗开阔。电影通过自然美、人文美、人物美三个层面的诗化改编,塑造出迥异于历史本文的温情黑山。
(一)自然美的诗意呈现
影片首先从自然美的表现来诗化“黑山”空间。影片前段丁若铨对于都城的回忆总是拘于某个封闭空间,无论是宫阙、密室还是牢狱、茅店,人物的生存空间总是狭小逼仄,即便是露天审问也因夜幕的封锁渲染出浓郁的压迫感。与此形成对比,黑山岛开阔、晴朗、静谧、悠然。空间的前后对比形成微妙的影像隐喻,在这种表现下,人物从都城流配海岛并非从中心走向边缘,而是从封闭走向开阔、由樊笼复归自然。这种隐喻在影像对黑山自然美大段的、反复的细描中得到强化。影片运用了大量长镜头、空镜头、静态镜头捕捉黑山岛景物,在光影调节、均衡构图、蒙太奇及剪辑节奏中呈现有“上镜头性”的黑山。黑白画面中,黑山显露出水墨画般的影像质感,古代山水画中平远、深远两种构图方法被巧妙地转化为镜头构图,入镜景物与元素显然根据经典视觉美学原则加以挑选和安排,“让人物走进或走出画面……这些人物仿佛是闯进了这个体现了纯粹的画面美的世界,他们服从于这种美的法则”。
正如爱泼斯坦所言,“上镜头性”不只是美的事物的再现,更通过再现为事物增添“精神特质”,“电影的语言能够赋予它所要描写的那些最没有生命的物象以一种最强烈的生命力”。电影对“黑山”的诗化影像呈现同样赋予无生命的自然以强烈的生命力。诗人笔下的“黑山”是阴森海域中的死寂孤岛,影像中“黑山”则是生养民众、庇护生命的自然之母。影像“黑山”无关恐怖,它总是天气清朗、阳光充足,人们可以畅览海的宽博宏大;海岛上村舍前后通透,穿过厅堂可以饱览远处粼粼海面;海洋还孕育水族、供给岛民物产,给人类繁衍传续带来希望。可以说,诗文“黑山”是落魄士人遭受竄逐忧惧前程而对边远海岛产生的阴森恐怖的扭曲与想象,影像“黑山”则对这种迷思加以拨正、还原和祛魅。电影刻画的“黑山”,是丁若铨栖居的“黑山”,一个樊笼以外的自由空间,一个接纳羁旅士人的德行空间。诗意影像的自然美呈现使“黑山”道德化和伦理化,它不再是“国都—边境”两极叙事之下给士人带来苦难的恐怖空间,而是可以游观栖居的诗意场域。电影对黑山岛的影像塑造并非对诗词文献的背离和曲解,而是从同情边缘、发觉远方的诗意情怀出发进行的艺术再造。
(二)社会美的诗意重塑
电影从社会美的虚构诗化“黑山”空间。史料描绘的黑山岛民悍勇豪强,丁若镛甚至称之为“渔蛮”“岛氓”“豪杰”“恶人”,并且细致地记录下丁若铨与黑山岛民间的冲突。辛酉士祸风波稍平、平反之声渐涨时,丁若铨曾想到牛耳岛与丁若镛会面,就当时情形看此行或成兄弟二人的最后晤面,未承想此行遭到黑山岛民的阻挠。丁若铨去意已决,趁夜色发舟牛耳岛,“黑山人觉之,急以船追至中洋夺还之”(《与犹堂全书》第一集卷十五)。此后,丁若铨经过反复央求才被允许暂住牛耳岛等待胞弟,黑山岛民风强悍可窥一斑。但在电影中,“渔蛮”“岛氓”“豪杰”“恶人”等负面形象被刻意隐去,取而代之的是素朴淳良、温柔顺服的岛民群像,黑山社会在电影中得到诗化重塑。
电影里的黑山岛民初遇“大逆罪人”丁若铨,不是讨论如何远离、孤立或迫害他,而是讨论如何供给他所需的居所与食物;岛上司职征税与惩戒的小吏常在执行中暗护岛民,避免催征过苛或司刑过重激化冲突;掌岛别将读书不多、贪财吝啬,全无两班士族的文采与风骨,却有着小人物的无奈和可笑可怜之处。这些岛民形象乃是电影作者对边远社会心怀温情的想象与虚构,其观照角度与丁若镛卑视、仇视岛民的角度不同,反倒贴近丁若铨的自述。影像中诗化的“黑山岛民”并非不愿读书习文、接受教育,只是生活贫苦、缺少必需的书籍和教师;他们并非士族眼中卑贱的“蛮、氓、夷”,而是被苛政杂税掠去财富而陷入贫苦的受压迫者。电影对黑山社会的诗化重塑,暗含导演对边远乡村的向往,也蕴藉为受压迫者鼓与鸣的良知。
(三)人物美的诗意拼接
人物的拼接虚构是影片诗化“黑山”的又一策略。据丁若镛记述,丁若铨登岛后确有一房妾室并育有二子,但关于这名妾室着墨极少甚至未详其姓名。丁若镛的记述显然受到古代性别伦理惯习和宗族观念规训的约束,当时社会压抑女性,妾室更是常被物化为繁育后代的“工具”而非值得着墨记述的“人物”。在当代人看来,这种叙事存在严重的伦理缺陷,如若照搬史料内容,势必引起观众的反感。对此,影片围绕可居嫂展开想象加工,不仅虚构情节厚描人物的善良勤劳,还创造性地拼接史料来增加人物的思想厚度。
丁若镛曾在写给丁若铨的信札中记述一位“卖饭妪”的言论。老妇以为“父母恩同、母更劳多”,她将父亲比作“种子”、母亲比作“土壤”,正是由于土壤的滋育,播下的种子才能成活、繁衍。这则公义妙论使得久持朱子之学、坚信父尊母卑的丁若镛大受启发,遂作为趣闻写在信中寄呈兄长,这也是丁若镛笔下为数不多有关女性的正面记述。电影借鉴了这则故事,但将对话人置换为可居嫂、丁若铨和张昌大,可居嫂成为正色凛凛、直斥儒教厌女的智慧女性,而丁若铨则成了聆听教诲、深受教益的儒者。经过史料拼接,可居嫂的人物美得到突出,她所赋予“黑山”的诗意也越发浓厚。可以假想,如果她只被塑造为勤劳能干的渔村妇女,那么电影的伦理意识就还停驻在旧社会的纲常中,难以穿透历史痛击如今复炽的性别偏见,影片的诗意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而经过人物美的拼接加工,黑山岛不仅有旖旎风光、淳朴岛民、真挚爱情,还闪耀着公义真理的光辉,其“桃花源”“治心药”的理想性质与诗意价值更加凸显。
电影有意识地筛除文献描述中“黑山”的可怖与暴力,历史中黑山的种种负面形象成为电影的“不可叙述者”和“不应叙述者”。净化的“黑山”显露出故乡般的温情包容,它宁静明朗、不包藏祸心,它庇护受贬寒士如同慈母迎接游子,它陈说公义真理反对压迫剥削。如此,电影“黑山”既用如画影像传达视觉美感,更以德行理想映照当下,引发观众对自身生存体验的比照联想,扭转都市乡村、中心边缘的刻板秩序。因此,“黑山”是电影作者蓄意构造的象征空间,它既是导演想象中庇护流寓士人的温情渔村,也是导演理想中接纳当代都市失意者的诗意家园。
三、撰著裕民:超俗志向的诗化诠释
丁若铨撰写鱼谱的超俗志向及其时代意义构成电影诗化诠释的重点对象。《兹山鱼谱序》载丁若铨登岛后以黑山的海鱼、海禽、海草编制谱录,目的是“治病、利用、理财”兼供文人吟咏之需。电影作者则发挥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旁征博引、合理虚构,将人物的个人抉择与社会思想的时代变迁纽结起来。在电影的诠释下,撰写鱼谱不仅是人物追求纯洁生活的德行选择,更寄托知识分子富国裕民、实学淑世的高尚抱负。
在中国汉晋以降的文化实践中,转向自然、回归日常是退隐士人追求纯洁生活的普遍选择。隐退士人怀才不遇、心存苦闷,常会远离尘世、寄情山水或躬耕田亩,以自然风光调适心态、以劳作生产实践道德,在日常生活与劳作中探索真理、救赎自我。士人群体这种典型的出处方式演变为独特的山水田园诗学与隐逸美学精神,也传播到效仿古代中国典章制度的东亚国家,形成“汉文化圈”共同的人格理想与文化心理。《兹山鱼谱》导演对丁若铨登岛后生活的想象与改写,蕴含中国古典山水田园精神的文化基因,情节的虚构改编也以中国文化的“隐逸母题”为原型。
丁若铨舍弃同代人以经史诗文为学的学术惯例转而研究海洋物产,关于这种抉择与转折,电影从“隐逸精神”的原型予以诗化阐释和故事赋形,将其解释为人物对污浊世道的主动逃离和对纯洁生活的追求向往。传统“隐逸精神”涵括“不受世俗所污染”的高逸、“纯洁生活”的清逸和“超脱世俗之上”的超逸,本意为“逃跑”的“逸”,是古代士人对“政治、社会的黑暗混乱”的“消极而彻底”的反抗。从这种文化心理原型出发,电影将丁若铨的抉择解释为因失望于人心世道的善变无常而在精神上选择逃避,他在逃避污浊尘世的精神旅途中邂逅清朗澄澈的黑山。“逃离”浊世的丁若铨拥抱自然,从经史诗文构成的观念世界“沉入”日常活计构成的现实世界,切身感受到海洋物产是“通透、明净的事物”,由此立志研究海洋物产,沉浸于明净的事物、消解对浊世的失望。“明净的事物”实则映照人物的明净德行——面对“人心/物产”的“恶/善”对立,高洁之士不难做出抉择。电影甚至认为这是丁若铨较其胞弟、实学巨擘丁若镛更为高明之处,因为后者的研究对象局限于“人心”与“人世”的范畴。
中国古代的“隐逸书写”在史观上逐渐区分出庸俗隐士与真隐士,庸俗隐士专注于自我消遣,真隐士则心怀劳动人民的苦难艰辛。“只有包含烈士精神的隐逸才是真隐,而隐逸的烈士精神同样可以用于经世济民的事业”。电影《兹山鱼谱》显然将丁若铨阐释为“真隐士”,在别具匠心的故事改写下,海产研究从人物的“私人消遣”升华为“裕民之术”。当然,电影艺术以其独特的媒介传达思想,它无法也不应当像历史著作般安排大段议论,那样只会使影像沦为说教,削弱影片对观众的感召力。电影的“言志”需要在故事机制和镜头语言上下功夫,用故事和影像引领观众默会、认同。
影片在“言志”方面做了多种尝试,尤其对人物本事进行大幅改动,虚构人物“张昌大”及相关情节。关于电影与文献中张昌大的事迹区别,历史学者丁晨楠已有详细考证,在此无须赘述。有待讨论的是人物改写及情节虚构对于电影“言志”的作用。前揭论及,在“诗化”叙事机制运作下,电影筛选过滤文献记述,以美善的高蹈标准重构丁若铨人格及黑山社会,但是这种美化改写降低了历史现实的“痛感”和“矛盾”,会导致故事内容的去历史化、浪漫化和甜俗化。从这种角度看,对张昌大的人物改写与情节虚构是导演寄托历史批判意识的蓄意而为。它在影片的叙事结构中担当容纳甚至放大“痛感”与“矛盾”的辅助线,与主线的诗化历史幻象形成互文比衬,成为电影“言志”的决定性环节。
对张昌大的人物改写为呈现李氏王朝腐败衰弱的末世景象开辟窗口。通过人物“经历”,观众“目睹”历史现实的疼痛与症候:性理学沦为科举工具而非思想本身,部分官僚与酷吏合谋榨取劳动者财富,苛捐杂税之下民生艰辛却无力抗争,而此时殖民者的坚船利舰已经从旁窥伺。相关情节,包括农民自戕抗税的惨剧,都有真实的历史原型。电影将复杂的历史现实收敛压缩,虚构张昌大怀揣救世理想应举入仕情节,并让他在同残酷现实的对抗中走向失败。人物的典型化使之超出自身意义而成为某种救世道路的象征,张昌大的失败不只是个人的失败,更是“旧思想自我修正必然失败”的具现和例证,也是电影“言志”的故事策略。
丁若铨、张昌大从分歧到同归,构成电影“言志”的环形叙事结构。张昌大的入仕失利验证了丁若铨所逃避的世道之腐朽,丁若铨面对生命终极的泰然喻示着他已经找到安置心灵、拯救世道的思想理路,而张昌大回归黑山则象征失意士人对丁若铨道路的皈依。在诗化的隐逸书写模式下,丁若铨承载导演的人格与价值理想,被塑造为生活纯洁、实学淑世的“真隐士”,焕发人格的光辉。然而,跳出电影营造的诗意幻象看,故事的历史化改编仍然留有悬而未决的难题。丁若铨固然为黑山人的餐桌增添餐食,但他能否帮助人民逃脱剥削的命运获得彻底解放?克罗齐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箴言。由此看来,李濬益导演与丁若铨的跨时空“对话”,却是用后资本主义的疲弱症候曲折地接受了古代隐士的弱德之美,但良善心灵的避世自洁又何尝不是对革故鼎新使命的逃避与背叛。
从历史本事到电影故事,艺术家对庞杂的史料进行筛选过滤、拼接置换,斟酌损益及蓄意虚构间隐含电影作者的风格与观念。李濬益对丁若铨等人物、情节及时空本事的诗化改写,寄寓着导演对历史人物的理解追佩、对边远社会的同情向往和对超俗志向的应和皈依。诗意影像手段与诗化叙事机制相互等衬,二者深度配合共同强化影片冲淡高洁的美学风格。然而,诗化叙事塑造的桃源幻象削弱了历史现实的疼痛与症候,隐逸书写模式一方面赋予流寓士人及其著作纯洁高尚的道德品格,另一方面也使历史矛盾的解决逃避革命话语,这从某种程度上消减了影片的思想洞穿力和提振改造社会生活的价值。《边山》票房失利后,李濬益对边远社会诗意家园的想象延续到《兹山鱼谱》,他对历史本文的诗化接受同时带有心灵净化和精神抚慰的需求。如此不难理解影片对日常饮食不厌其烦的影像细描以及对批判现实的简化悬搁。电影改编在史观层面折射着后现代的价值症候与文化工业规则的濡化规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