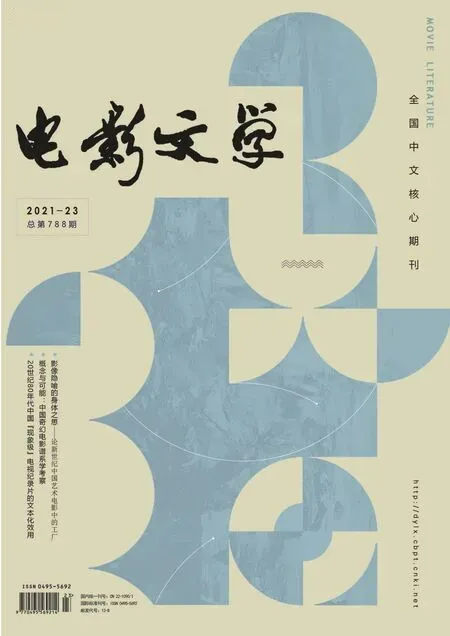人工智能题材电影伦理叙事的创新策略
2021-11-14陈昶洁
陈昶洁
(武汉传媒学院电影与电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1)
人工智能题材电影至今已有93年的发展历史。它的出现不仅吸引了大量著名导演加入创作的队伍中,也将人工智能这一新兴事物成功介绍给观众,俘获了众多粉丝。但即便在创作数量方面稳步上升,近几年获奖及提名的人工智能题材电影却寥寥无几。
与21世纪初相比,当前人工智能题材电影需要的是有思想深度的创新作品,以解决伦理叙事手法同质化或伦理思想表述偏差等创作问题。这既是使人工智能题材电影打破当前伦理叙事缺乏创新瓶颈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塑造人工智能客观形象使其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的一个良好契机。由于伦理叙事涉及故事文本内的符号表意和叙事模式,以及高于文本的叙事话语两个层面,以下将从这两方面分别总结人工智能题材电影中伦理叙事的方法及其创新策略。
一、叙事文本的协调与平衡
伦理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电影的伦理主题需要人物、情节等多重叙事元素合而为一地共同作用,才能更准确地在故事文本中有所体现。创作者应当注意,伦理既不能成为牵绊故事推进的障碍,花费过多的篇幅去阐述,也不能无视它对升华影片主旨的作用。因而在创作过程中,要着重关注与人物形象相关的叙事符号和叙事模式。为了保障人工智能题材电影能够再现时下相对客观的伦理意识,创作者应当选择与之相符的伦理叙事策略,以更好地发挥伦理意识对故事叙事的积极作用。
(一)协调影像叙事的能指与所指
电影通过塑造形色各异的人工智能角色,用以指涉不同的伦理思想。画面中的人工智能符号,不仅是对现代科技的具象临摹,也被赋予了伦理的意涵。这便是结构主义创始人索绪尔提出的符号外延和内涵的差异:符号外延是指语言表述的内容;内涵则是指附加在传播形式上的文化意涵。导演并不能完全依靠影像,将其思想转化为视觉的表达方式,还同时要兼顾画面的符号意涵。换言之,人工智能题材电影不能仅仅刻画人工智能的角色形象,而忽视了背后的伦理意涵;也不能只是给角色贴上人工智能的标签,而轻视了角色外形的塑造工作。
很多人工智能题材电影的口碑存在争议,正是因为没有协调好符号内涵与外延的表述方式,导致故事要么流于表面、过于浅显,要么想表达的思想过于充盈,显得杂乱无章。例如《双子起源》过多的篇幅用于讲述人造人与人工智能的战争;《游戏世界·绝地求生》以人类争夺人工智能的控制权和生产区为核心矛盾,大量充斥着枪战、格斗之类的画面;《疯狂AI之夺命外挂》只讲述了人工智能监禁人类并举办了杀戮游戏,而几乎没有对其性格和精神异化进行描述。这类电影都过于强化镜头的视觉冲击感,大片段地依靠特效镜头和激烈的打斗场面,在表现人工智能的外形和强大功能时,忽视了人工智能这一类符号背后应该承载的伦理意识。对于人工智能角色的情感经历、内心活动等静态场景的叙述较少,使人工智能这一符号外延的意涵略显单薄。
另一种情况则是像2019年由中美共同制作,获得儿童银幕最佳动画电影奖的《未来机器城》。电影开篇,导演试图通过人工智能角色批判校园暴力的现象。安排遭受同类排挤的智能机器人7723与遭受同学冷暴力的女孩苏小麦相遇并成为朋友。故事中段又试图以旁人对这段“畸形”友谊的歧视,表现种族主义或是阶级歧视对个体造成的身心伤害。而故事后半段又演变成女主角与智能机器人携手拯救世界的美好结局,变成对英雄主义的演绎。由此可见,导演想要表达的伦理主题过于庞杂,短短的100分钟无法做到尽善尽美,迫使故事中的每一个独立事件只能点到为止。类似这种多重文化意涵杂糅的主题设置,干扰人工智能角色的显性表征,使其原本作为人工智能的科技属性变得模糊不清。故事主角即便换成外星人、变种人或是克隆人,也都不影响故事整体的叙事。同类型的电影还包括《昆仑仪之超时空狙击》,电影只是通过角色的自我介绍,了解到作为主角助手的铁小猴是一台人工智能机器。后续完全忽视了人工智能角色的科技表征,而过于集中地述说爱情故事,甚至完全忽视了机器与周遭事物的伦理关系。这种类型的故事创作,本质上无异于大众化的爱情片、喜剧片,大大削弱了人工智能题材电影原有的科技感和视觉冲击性。
简而言之,电影中围绕人工智能角色的影像叙事存在着能指与所指的双重意涵。作为故事的核心人物,人工智能既不能只是流于表面、贴标签式的提及,也不能沉溺于对其无限的想象中,而忽视了与影片主题的指意关系。这种疏于考量的人物塑造手法,往往就是造成电影伦理主题浅显或模糊的根本原因。因此,创作者应当让人工智能角色外在形象的描摹与内在精神的刻画相互配合,以便简洁明了地实现影像叙事在电影中的伦理表意功能。
(二)多线叙事彰显伦理观念的现实性
人工智能题材电影可以通过添加角色成长背景之类的剧情,完善人物形象,丰富叙事模式,同时为影片的伦理主题做铺垫。虽然电影往往是利用角色的外貌、性格、行为打造人物形象,但角色的成长背景同样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法之一。创作者可以借此交代人物外貌、性格变化的原因,使其在故事中的行为更具有合理性,成为电影伦理主题的重要体现之一。
一般电影会通过回忆的形式,回溯角色的过往,实现这种跨时空的多线叙事。人工智能题材电影中,这种手法衍变为描述人工智能被创造的原因、程序的设置或是智慧的来源等。这类对人工智能过往描摹的手法,为故事后续的伦理表达做好了铺垫。例如根据日本小说改编的科幻片《阿丽塔:战斗天使》,故事以一台残破的女性智能机器人阿丽塔在垃圾站醒来作为开端,一边回忆一边寻找自己被制造的原因;《银翼杀手2049》的男主角K抽丝剥茧,不断从细微的线索中挖掘有关自己身世的线索;《机械危情》通过回忆式的倒叙手法,让观众理解了艾娃是如何从一个言听计从的机器女孩变成了杀人如麻的战争工具。即便是《终结者》这种动作类电影,充斥着人机两大族群战争的宏大场面,在影片的高潮前,往往也会有善良的智能机器人回忆自己与人类一起躲避战争、相互照料的情节。例如该系列电影第二部中的T-800、第三部中的T-850、第四部中的马库斯。正是这种温情的画面成为它们愿意为人类付出生命代价的重要原因,也逐渐变成该系列电影不可或缺的经典场面之一。因此,电影通过详细刻画人工智能的过去,不仅能够理清智能、自我意识、行为目的的来龙去脉,更是帮助建构和表达人工智能题材电影伦理意识的有效途径。
电影采用多线叙事虽然可以实现跨越时空距离的需求,让过去、现在与未来形成一种对话关系,但稍有不慎也可能会使故事主体情节的叙述变得模糊。即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立体化,交代清楚了故事的前因后果,故事时空的颠倒或跳跃也可能变成观众理解剧情的障碍。这就要求导演对故事整体必须足够熟悉,把控好影片的叙事节奏,并且插入的故事片段也要符合现实逻辑,才能在人物和情节方面进一步深化观众对电影伦理主题的印象。
但多线剧情的安排也有弄巧成拙的情况,例如部分创作者忽视了伦理的现实性。这样的问题体现在近几年的人工智能题材电影中,主要有三类:其一,插入的剧情与伦理表达无关,既缺乏对人物背景的交代,也使故事变得冗杂。如《火星追击》《黄金十二宫》《智能天使》等影片都未曾交代人工智能的创造目的或智慧来源。这些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都是凭空出现的。其二,插入的剧情违背现实逻辑,反而降低了伦理主题的现实意义。以《硬盘少女》《双子起源》《智能危姬》为代表的一些电影,将人工智能失控的原因归结于一场意外,例如实验室爆炸、机器内部线路的短路等。甚至《机器男友》通过仙女施法的方式,赋予机器人自我意识,完全脱离或违背了现实的逻辑和认知。其三,插入式剧情所体现的是陈旧或错误的伦理观。如《天堂计划》《超级APP》《机械娇娃》等电影,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自主学习、自动更新程序设置不断提升自身智力,最终超越人类文明、摆脱社会束缚。但英国人工智能学者尼克·博斯特罗姆表示:强人工智能只能模仿人类的推理、规划、联想等行为;能够自我更改程序、超越人类认知的智能机器人,以目前的科研技术水平及发展趋势,百年内都不会出现。这种人物的塑造手法或情节设置显然是对人工智能的妖魔化,违背了当下遵循客观公正性的现代科技伦理观。
当然,多线叙事也并不提倡构造一种超现实的伦理观,规划现实伦理的改进路径。因为伦理本身具有一定的时代滞后性,其形成过程需要众多社会成员的参与、尝试和认同。并且伦理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地被改变,容易落后于社会时代的发展。所以伦理思想越是超前,对当前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就越低。往往是适应当前社会的主流伦理观,更能够给予观众反思空间,提高影片的思想深度。
所以,人工智能题材电影在创作时,应当多从现实的角度设计人工智能的创造与升级、失控与暴乱,让跳跃性的多线叙事成为影片对现实伦理影射的铺垫。忽视人工智能角色的过往,对其成长和教化过程避而不谈,或是以超现实的虚幻手法拟定人工智能角色的成长和变化,都会大大削弱电影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合理运用多线叙事的手法,以客观的视角交代人工智能的成长经历,才能够更好地凸显影片伦理主题的现实意义。
(三)开放叙事呼应伦理诉求的动态性
任何故事文本都应该以平衡和守序的状态作为结局,来完成完整的叙事。这是茨维坦·托多洛夫对叙事作品结构进行分析和研究所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所有故事的叙述其实只有两大类:避免惩罚型与转变型,并提出了故事的平衡公式。前者是从原本的和谐宁静,到打破禁忌、事态失衡,最终形成新平衡的完整过渡。后者则是跳过最初和平的状态,直接从动荡的局面展开叙述,由主角的行动让事态走向平衡。
人工智能题材电影故事文本的叙事模式,也分为上述两种。避免惩罚型的叙事模式:由人工智能这个新社会成员的加入打破原有的社会平衡,让正反主角之间的对抗或协调形成制衡,最终在故事结局建构新的伦理体系,批判传统伦理观的不足。另一种转变型的叙事模式,则通过无序与有序状态的对比,从而强调伦理道德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功效。
人工智能题材电影都通过这种叙事模式,宣扬了伦理的牵制性和约束功能。但伦理并非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一种动态的制度。它会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不断改善其思想内核,为人类创造更舒适和谐的生存环境。许多获奖的人工智能题材电影就透露着伦理的动态性。从影片开始的人机矛盾,衍变成结尾接纳人工智能的新型社会伦理观,描绘了一幅幅和谐的人机关系或是人工智能自我认同的美好愿景。例如以《机器纪元》《机械危情》《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影片结局,都是善良的人类与人工智能达成和解、相互体谅,共享生存资源与空间。
即便是因失控而被销毁或是为了拯救人类而牺牲的人工智能,影片也以开放式结局的形式,暗示人工智能力量的暗潮涌动。这种开放式结局指的是,故事的主要矛盾得到解决,达成新的平衡,但人物命运依旧存在诸多被改变的可能。例如《魔种》《黑客帝国》《超能陆战队》这类影片,导演以一种开放式结局的形式告诉观众:即便人工智能变成人类的心腹之患,人类也不会停滞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和改进。例如《魔种》的结局是智能电脑被炸毁,但它留下自己的电子人后代;《终结者》每一部虽然都以人类打败智能系统天网作为结局,但最后都会以穿越未来的镜头给出暗示,天网系统通过电缆传输自己的意识成功躲避爆炸,人类与人工智能在未来的战争依旧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到来得或迟或早;《超能陆战队》的结局虽然是智能机器人大白牺牲,但人类主角通过遗留的智能芯片,为其重塑身躯获得新生。因而人工智能角色的灭亡,并不意味着技术研发的停滞将带来伦理意识的固化。
反观在一些口碑存在争议的电影里,伦理意识不仅没有动态性,反而表现出思想倒退的特点。例如《硬盘少女》中的机器人小八为了拯救人类而牺牲;《疯狂AI之夺命外挂》中邪恶的智能电脑被程序员陈奇炸毁,并终止了人工智能的研究项目。这些电影都是以人工智能的消亡、人类社会再度恢复往日的秩序作为结局,表达的是批判和抵触人工智能出现和发展的伦理主题。甚至早期的国产影片《错位》和《玛德2号》在片尾揭示,人工智能只是人类的一场梦,是虚无缥缈的事物。这些影片从失衡到平衡的叙事模式,强调的都是坚守过去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伦理意识。但人工智能融入社会早已经是势不可挡的趋势,否决甚至拒绝它们的电影主题,是伦理意识的倒退。优秀的人工智能题材电影应当倡导接纳人工智能,思考人类与之共生的伦理思想,表现伦理的动态特征。
当然不排除部分电影采用开放式结局只是一种出于开发IP的商业手段。但无可非议的是,开放式结局的叙事手法表现出了伦理随着社会进步不断发展变化的流动性。而现实的伦理也会伴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使个人和群体调整自己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具有显著的历时性特质。所以电影不能只是强调恪守当下的伦理秩序,而不去探寻与想象未来社会的人文景观。这样会造成电影所传递的伦理意识缺乏动态性的特点。
二、叙事主题的和谐与共赢
除了故事文本可以表达创作者的伦理主题,叙事话语同样在以一种隐喻的形式向观众传递某种特定的伦理思想。导演创作电影时不仅要关注人工智能角色的形象塑造和情节设置,也要分析影片话语层面所喻示的伦理意识是否适应当下的社会语境。纵观当前的社会环境,各国都正朝着文化融合的大方向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就要求伦理叙事的创新策略要从并行不悖的视角去尝试和探寻,减少二元对立的传统叙事思路。
(一)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的互补
伦理作为社会人的一种群体意识,需要获得一定基数人群的认可,才能将其推广施行。个体在社会活动中表现的行为规律或认知,并不能称为伦理;将伦理简单理解为社会关系,而忽视行为主体也是不尽全面的。伦理应该是:关系双方作为自觉主体,本着“理应如此”的认知,相互对待的一种关系。换言之,伦理意识的建构既要求有行为主体和客体的参与,也必须获得社会群体认可,这两者条件缺一不可。
若要在电影话语层面表现伦理的普世性,可以结合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两种叙事手法。所谓宏大叙事是以抽象的群体为基础,而私人叙事以个体经验为基础,这是文艺创作中两种不同的叙事策略。宏大叙事的创作手法在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频频可见。它是以题材重大、风格宏伟的史诗作为创作背景,从群体的视野回溯这一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后续造成的影响。当然,宏大叙事并不意味着抛弃对个体角色的情感描绘。它可以与私人叙事相结合,让故事从个体情感最终上升到社会历史层面,强调时空的大背景下的一种群体记忆,也更能表现伦理对个体成长的影响。
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相融合的手法,使电影更能表现人工智能这种新事物对整个社会、生态圈的影响,从而将其伦理问题提升到人人自危的层面。例如《终结者》《银翼杀手》系列电影,虽然聚焦的是人类个体与人工智能个体的斗争,但也在故事中穿插了不少战争的宏大场面,交代了人类与人工智能族群爆发冲突的社会背景。又或是《我,机器人》里机器人桑尼奋不顾身地保护人类,证明了人工智能对待人类的一片赤诚,不该换来人类的歧视;《人工智能》中机器男孩大卫真心诚意地帮助并告诉人们,人工智能也渴望并值得被爱。这类影片对人工智能角色个体的形象刻画、情感描述,最终都会升华至对整个社会历史层面的影响。即便是《鹰眼》《铁皮人》等影片中,铁皮人、鹰眼只是有着强大能力的人工智能个体,但也正是因为其过人的智慧或是无可匹敌的力量,使其能够仅凭一己之力,撼动现有的社会体制,将电影的主题拔高至地球危机、人类命运的宏观层面。
部分人工智能题材电影就是因为没有涉及宏大叙事的手法,过于集中地使用私人叙事,造成了伦理叙事的狭隘。例如《虚拟情人》《硬盘少女》《机器男友》《我的机器女友未成年》《我的男友不是人》等影片。围绕这类单一的角色,故事讲述的大多是以人工智能来突破世俗的眼光,与人类相恋的爱情故事。电影名称就直指以爱情为核心的叙事主题。看似这种打破世俗的不伦恋情是影片的亮点,实际上这种私人叙事手法的缺陷也非常直观,就是导致故事过于片面地煽情而忽视了伦理表达。人工智能角色在电影故事中只有性别标签的展现,显然没有合理运用其他的身份标签,包括阶级、种族、生态等,浪费了伦理叙事的重要机会。
甚至部分电影过度沉浸于角色的情感中,导致原本的宏大叙事变成了私人叙事,阻碍了伦理主题的表达。例如《我的男友不是人》中,人工智能米可原本是为了净化环境、改变人类灭绝的命运而穿越时空的智能机器人。这种保护整个生态环境的理想,以及对未来人类社会衍变的焦虑,本来已经触及宏大叙事。然而导演过于关注米可与人类女孩的情感走向,而忽视了人工智能净化环境的本职工作。电影到结尾也只字未提环境保护的理念,转而变成对人机爱情的赞颂。这种过于狭隘的叙述视角反而压抑了伦理意识在话语层面展现的机会。
毋庸讳言,只关注个体情感的故事是缺乏伦理普世性的。采用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兼具的手法,既保证电影对人物情感和经历的描述饱满充实,也使故事的叙事话语层与现实伦理形成一种映照关系。这样的电影在激发观众情感共鸣的同时,也更容易引起观众对现实伦理困境的思考。
(二)道义与利益的双赢
中西伦理观截然不同的发展语境,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之间的伦理主张往往天差地别。这种差异性使得东西方人工智能题材电影伦理主题的表达往往相悖而行。
例如中西伦理观对利和义的不同看法,是两者亘古不变的尖锐冲突之一。追溯西方伦理思想史,大多数的道德问题是从利益角度考量,例如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功利主义、快乐主义等。在西方的观点中,伦理是在为个人或集体谋求福利。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东方伦理观看待道德问题时,大多从道义的视角出发,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利和义是儒家学者用于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义是最为高尚的品德,可以指导其他一切行为向善发展;受利益驱使则是小人的行为。简而言之,东西义利之辩的核心差异在于西方合理化对利益的追求,而东方传统观念更欣赏侠义之士。
在西方诸多经典的人工智能题材电影如《终结者》《西部世界》《银翼杀手》中,不难看出其核心冲突就是源于对权力资本的争端。这种对“利”的探讨虽然用作批判霸权政治,但同样也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用来合理化不平等制度的手段。安东尼奥·葛兰西曾提出“文化霸权”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以歧视、排挤等非武装暴力形式打击其他文化群体,以便自居和稳固统治地位。在《心灵之声》《摩登保姆》《机器管家》等电影的结尾处,看似和谐的景象下,其本质却是人工智能归顺人类,对人类制定的社会规则做出妥协。这既不是生态中心主义宣扬的“生物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者期望国家公正与人的公正统一而达到社会平权的愿景。
创作者对利的宣扬,还体现在故事的结局上。不论是西方早期的《铁皮人》,还是2019年的《吾乃母亲》,电影的结局往往是问题会伴随着人类或人工智能其中一方的臣服或妥协得到解决。这或许是西方伦理所认可的,大部分人类群体获得利益是合理且本能的生存需求。但在中国伦理观看来,这种“伦理”恰恰是最“不伦理”的体现。尤其是电影中,人工智能角色还常常被赋予少数族群、弱势群体的象征符号。人类以权力或暴力的形式让另一批族群屈服的类似剧情,实际上是不可取的。在叙事话语层面来看,这类电影传递的主题显然不是“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的东方伦理意识。
中国传统伦理对“义”的诠释,讲究仁义、正义、情义等西方人眼中非理性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这种伦理思想注重和谐局面的落成和维护,强调以集体利益和大局观为重心的求同存异,而非像西方那样主张个性化的张扬。例如《超能女仆》中的机器人Ices与多次包容和信任它的人类一起打败了邪恶科学家;《机器侠》的K-1德明牺牲自己保全人类不受邪恶机器人K-88陈龙的伤害;《爆裂直播之全城追缉》面对绑架犯的威胁,机器人Siry与人类人质做交换让自己身处险境。这类电影赞颂的大多是个体为保全集体利益而做出重大牺牲。但科技存在的意义本该是避免牺牲,尽可能包容个体的差异,提高整体族群的生活质量。
所以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利”和“义”并不再是二元对立的概念。人们既需要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完成一些无意义的重复性的工作,给人们创造“利”的享受,吸引大众支持这项科技;也需要人类以友好协作的态度看待人工智能,让体谅包容等一些代表“义”的正能量的话语广为流传。在电影创作过程中,导演应当避免“利”成为文化霸权的渠道,或是“义”衍变成宣扬无谓的牺牲,在叙事话语层面传递了误导观众的伦理观。只有适当结合中西文化对“利”“义”的不同见解,才是适合当前文化融合语境,让人工智能题材电影突破瓶颈的重要发展思路之一。
(三)人文与科技的共生
人工智能题材电影还可以通过塑造一种全新的人机关系,解决伦理叙事手法趋同的问题。纵观近百年的人工智能题材电影发展史,人类一直以龃龉难入的态度看待人工智能。人机协作的故事大概在2010年后才开始出现。
这主要是因为人类与人工智能处理信息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迥然相异,在行为目的和方式上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人工智能主要依据数据和运算,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而多愁善感的人类有着丰富的情绪,看待事物会掺杂情感因素。两者以不同的方式为人处世,往往因此产生意见分歧而爆发冲突。即便是电影中,部分人工智能产生自我意识,获得了生物体本能的情感,往往也会因为缺乏社会系统的教化显得莽撞或自私。对于这种行为方式表现出“异己”性的族群,让人类长此以往秉持着一种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造成人类与人工智能以针锋相对的关系持续了80多年。
近年来推出的人工智能题材电影,虽然不乏创意的想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影片依旧选择将人类与人工智能推向了对立面,构建二元对立关系。这种叙事结构其实违背了现实科技伦理发展时所需要的人文关怀。而构建一种新的人机协作关系,反而是适应现代伦理思想的叙事话语。
人工智能伦理在其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早已演变成一种大众伦理,与人类社会是不可分割的。人工智能不同于克隆技术、核武器、纳米技术等先进的科技,后者只有少部分专业科研人员才明白其操作原理,并能够切实地接触到相应的设备。但人工智能早已在现代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被普及,如智能通信、智能家居等设备。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建设,不仅涉及科研人员的创造目的、研发手段,更需要关注到的是大众的营销渠道、使用规范等。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人工智能的伦理建设离不开人文关怀的本质。
当前研究显示:有关人工智能的伦理建设,应当是建立人道主义、功利主义、生态原则等多重伦理意识的复式结构。当前的人工智能电影大多缺乏这种兼顾多重人文性与科技感的伦理思维。这种片面的叙事方式,导致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否认科技,导致影片主题过于夸大人类的力量。例如2020年美国电影《吾乃母亲》、日本电影《麻雀放浪记》、2019年国产片《流浪地球》等,都存在人工智能不通人性、不近人情,最终败给人类智慧的故事情节。其二是过度夸张科技的力量,贬低人类的价值。例如国产网络电影《蟑潮》《天堂计划》《黄金十二宫》等,还在模仿20世纪中期的好莱坞,塑造一批被妖魔化的人工智能形象。这些角色显然已经不符合当下的主流科技伦理观了。随着科技文明的进步,人们应该正确认知“人文”与“科技”的关系。电影创作者不应该刻意塑造对立面,造成观众的伦理认知偏差;而是应该尝试建构新时代的人机协作共生关系,与时俱进地探讨人文与科技共同发展的新道路。
未来人工智能题材电影的发展趋势,不应该一再简单地以人类与人工智能的矛盾为故事的核心冲突。创作者更应该站在宏观视角,想象和缔造人类与人工智能可以相互照应,共同维护地球生态平衡的美好愿景;更多地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以前瞻性的视角看待智能科技可能对周遭环境造成的影响或是未来可能遭遇的伦理困境。这样也能更好地促进人工智能融入现代社会,使其成为让大众接纳的事物。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题材电影发展至今,其优秀作品的数量不在少数。在伦理叙事方面,它们所创造的手法值得电影创作者们学习。例如塑造人工智能角色时所使用的丰富的电影符号、多线叙事和开放叙事等。但人工智能题材电影也不能因此就停滞不前。在掇菁撷华的同时,也要尝试融合多元文化、结合不同叙事手法的方式,例如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并用、道义与利益叙事话语相辅相成以及结合不同伦理文化与科技表征的叙事话语,宣扬新时代下和谐的人机关系等。相信在学习和坚守的过程中,人工智能题材电影创作者也一定会努力超越前人,制作出更多更为杰出的影视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