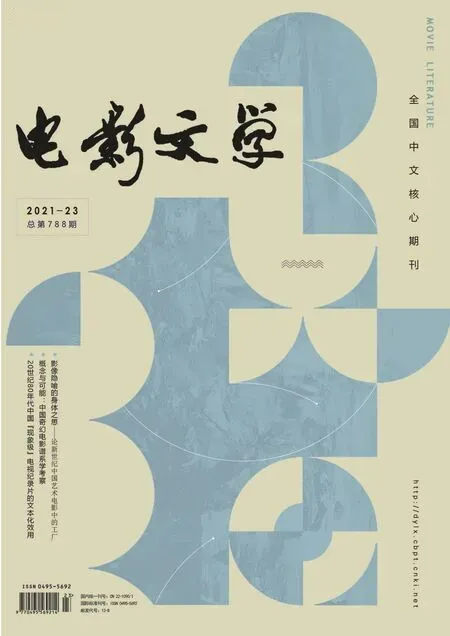国产纪录片中“匠人”形象的塑造策略
2021-11-14李诺
李 诺
(长春人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近十年来,随着群众观影水平的提高,观众对纪录片审美趣味的变化,纪录片也逐渐呈现出多种类、多面貌、多层次、多样态的特点,特别是一些以呈现我国各行各业专业的真实状态,记录人们现实生活为主题的纪录片跃上屏幕,成为一时焦点,具体如《人间世》以医院为拍摄场景,从医护、病患、家属多个向度,纵深地展现了当下现实里个体小人物的命运;《人生第一次》旨在通过蹲守拍摄,观察不同人群在人生重要节点的“第一次”,串联起当代中国人一生的图景;《巡逻现场实录》则是借由民警巡逻出警的日常,展现当代社会中随处发生的小摩擦和人与人之间不经意间的温情等。
在这些纪录片中,“匠人”是得到较多刻画的群体。影片中多次出现了普通产业工人、专业技术人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详细展示了他们生活、工作、学习的多种面貌,实际上是在旨在借由对这些人物的刻画,重塑一种对特殊文化形象符号的认知。工匠们或展示的不仅仅是工作的内容,更多的是在此层面上的个体精神。如《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就展现故宫文物修补过程中,工匠们全身心投入的状态以及工匠们对文物修复工作的热忱,《大国工匠》则将焦点聚焦于为中国的国防科技、民生产业奋斗的工程师,以及他们在工作中无限探索的精神,并通过这些记录,向观众揭示当代中国国富民强的精神依托。在这些以“匠人”为题材的纪录片里,始终体现了一种切合当代中国社会的积极价值观,一种专注的、奉献的、忘我的时代精神,匠人精神体现出的追求极致、奉献自我、高度专注的品质,正是目前消费社会普遍缺乏的精神品质。本研究尝试梳理我国近些年纪录片中“匠人”形象的发展脉络,以《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片中所呈现的匠人精神与匠人特质作为分析基底,并在比较视野下对比中日纪录片中匠人精神的差异,试图探讨中国纪录片在近年来孜孜不倦描绘“匠人”的意义。
一、匠人精神与期待视野:国产纪录片中前匠人阶段
近些年出现的中国纪录片大体上保持着一种“小人物记录大时代”的特点。从《舌尖上的中国》开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纪录片叙事特点就已经逐步形成,《舌尖上的中国》详细描绘了中国饮食文化巍巍几千年历史,借由展示在各个地方形成的特色菜肴,见微知著地呈现了美食背后中国各个地区的风俗特色、历史文化。《舌尖上的中国》章丘铁锅一节中,导演将镜头对准坚持用手工小锤敲击制作铁锅的铁匠,并且将铁匠们对工艺传承的坚守和对职业身份认同的自豪感,作为本章的主旨,《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引发了国内消费者购买手工铁锅的热潮,这种热潮,实质上是观众们对返璞归真的匠人精神和“一生只做一件事”的生活态度的认可。自此以后生活中的平凡人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国产纪录片之中。
《舌尖上的中国》之后,国产纪录片一改过去宏观视点下的大格局、大时代、大变迁为拍摄主体的纪录片传统,《河西走廊》《话说运河》《唐蕃古道》这一类以自然风景、民族风情、历史传说等题材的纪录片明显地减少了,转而开始将镜头对准普通市民的生活。美食纪录片一时间出现了爆炸式发展,《寻味顺德》《味道中山》《人生一串》《一城一味》等就是这一阶段诞生的产物。这些纪录片都着重于地方饮食文化的刻画,其展现的方式与《舌尖上的中国》不乏雷同之处,引发的观众讨论热度也不能与《舌尖上的中国》相提并论,形成这样的差异原因,还是这一类纪录片同质化过重、只留有对具体事物的记录,缺乏对现象背后根源因素的探查,缺乏对美食背后人文精神的深层次挖掘。《寻味顺德》尝试将顺德的知名小吃与当地相对知名的店铺做结合,但却引发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形成这样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影片缺少了对工艺、工匠的背后故事的探索和挖掘,展现的却是消费社会逻辑下,营销、网红、品牌、资本对工艺传承的傲慢。
《舌尖上的中国》不仅仅引发了观众对中国各地风土口味的兴趣,更大层面上,《舌尖上的中国》引发的是中国人对业已失去的工艺、工匠精神的追忆和探索。在《舌尖上的中国》后,以工匠精神著称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横空出世,实际上突破了过去纪录片过分注重高知名度、有悠久历史的大事件,转而开始注重“物品—人—精神”的逻辑链条,并根据人物的特点,人物或器物所传承的精神力量当作重点刻画的内容。《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成功,也反映出中国纪录片将“匠人”文化和精神推向社会所收到的关注和认可。
二、时代精神的弘扬:对“匠人”身份视野的确认与传达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一部围绕着故宫文物修缮专家们工作生活展开拍摄的纪录片。本片重点记录故宫书画、青铜器、宫廷钟表、木器、陶瓷、漆器、百宝镶嵌、宫廷织绣等领域的稀世珍奇文物的修复过程和修复者的生活。《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展现修复工艺时,往往是多线并行的,以故宫中馆藏的稀世珍宝为经纬,以修复作品中小组成员的配合和对工艺的解说为血肉,以对作品价值的肯定,对修复后作品效果的展示作为总结,以修复师在修复工作中展现的专业技能、专业精神、对职业身份的认可作为影片情感升华。四个方面的融合对影片的制作缺一不可。在纪录片第一部分中,可以清晰看到形成叙事链条的三重故事套叠,第一重是以王津为修复专家的钟表修复工作的进程;第二重则是修复唐三彩马的进程;第三重则是以师傅带徒弟的传统视野,展现故宫修复工匠中年青一代状态的内容,从这三层套叠,基本上呈现了时间、空间、历史三重的交汇,工匠们技艺的磨砺、对传统修复工艺的集成以及对后来修复者的培养融汇在这三重结构之中,形成了复杂的、多面的叙事效果。故宫宝物的修复技术超越古今,实现了一种微妙的、持续性的继承,而故宫中的文物同样如此,钟表、字画、陶器等等宝物以“物”的实际存在,微妙实现了历史的“虚”的传承。在故宫国宝的面前,一代一代的故宫修复工作者又成为与穿越历史、亘古不变的“物”的参差对照。这种三重套叠的叙事模式,显然是一种对流媒体与互联网的媒介表现方式的改造和利用,而这种颇具古典美和形式美的叙事样态,又进一步与故宫珍宝修复的主题烘托,形成了“一唱三叹”的格局。
《我在故宫修文物》真正的核心并不是故宫的稀世珍宝,而是修复者们的职业生涯与职业背后对修复工作高度精神认同的个人信仰。因此,人又是时间、器物三重叙事中,最为主要、最为核心的对象。在影片展现陶瓷组专家王五胜时,最为完整和具体。王五胜直到影片第一部分中段才出现,旁白介绍了他的身份和职业路径,他从青铜组转来,帮助陶瓷组修复。影片详细介绍了修复唐三彩马的各个过程。马缺失的马尾、各个小组对马尾形状展开的讨论、王五胜借助展览素材,对唐三彩马的修复做出进一步的计划等,每个片段都展现出王五胜对文物修复工作的认真态度。《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创设性在于它并不拘泥于这些工作内容,而是尝试从情感层面唤醒观众对王五胜工匠精神的情感认同,王五胜在从展览处往回走时,路过故宫宫殿拍照,记录故宫变化的行为,同时也感慨着退休后能够这样近距离观看故宫的机会不多了,片段中包含着王五胜对故宫的依恋,也包含着对修复工作的不舍,深深唤起观众对工作价值、乃至于在工作中实现个人抱负的理想思索。《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素材叙事目的非常明确,它借由王五胜等专家的个人记录,呈现出一个专注于自身工作的人,全身心地投入这份工作,服从组织人员的调配、不断钻研修复技术的各个方面,这种不计代价、不计成本的自我探索,实质上就是中国工匠在千年中师徒传承的对于技艺和职业的尊重和信仰。
在第一部分的末尾,旁白将修复师与文物的关系总结为“在修复中与文物对话、交流、感知古今”。实际上这已经超越了传统对工作的定义,而将修复工作提升到与个人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人生理想相谐的地位。《我在故宫修文物》通过影像化,将承载与特定环境的匠人状态,完全展示给观众,将这种传承千年的对技艺的专注,立体化、全方位地呈现。《我在故宫修文物》中蕴含着多组人物、事物的参差对照,既有古今历史之间的对比,也有国宝与国宝间的对比,同样还有现代职业的从业者与承载古代匠人精神的修复者们的对比,正是这种对比,升华了影片的格调,弘扬匠人的精神与品格,对当前时代所欠缺的精神内涵做出了感召。
三、对“工匠”身份的探索:比较视野下本土“匠人”精神的追寻
国产纪录片对匠人形象的描绘,日本和欧洲地区的“匠人”特征做出了区隔,这一点也是《我在故宫修文物》于目前国产纪录片中对匠人形象描绘最为特殊的一点。从“匠人”一词在网络媒介上发酵的始末,便不难看到,在中文互联网上对匠人的推崇最开始来自日本。《美之壶》《寿司之神》《大渡海》等片中,都细细刻画了日本“职人”肩负责任,向职业生涯高峰攀登的全部路径。一生只做一件事,一定意义上就是互联网文化接受者对“匠人”,对工匠精神的个人定义。
《我在故宫修文物》与日本职人纪录片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们都将镜头聚焦于职业匠人自身,但《我在故宫修文物》叙事和展现的内容往往是多维的,并不像日本职人纪录片那样,将职人掌握的技艺神话,《我在故宫修文物》并不注重“造神”,而是旨在重现那些生活中的人,如钟表修复组专家王津对钟表修复事业的专注和热爱,源自对故宫钟表修复手艺的传承和对这一份职业深层次的认可,而不是受到某些特定的职业神话的感召。电影中无数次提到“故宫拥有的西式钟表储量巨大,光凭钟表组现在的规模,完成三千多座钟表的修复是不可能的”,生而有涯而职业探索无涯的喟叹,实质上体现的是中国工匠对职业的专注和对事业的奉献,这和讲求极致的日本职人是有着巨大差异的。日本的工匠职人,他们的职业路径和技艺传承往往指向历史和自我两个向度。传承家族事业或继承濒临失传的绝技是其历史向度,将技艺不断磨炼,使自己成为本领域极致、顶尖的专家,成为某某职业之“神”,则是其自我向度。中国纪录片工匠们对技艺的追求则是多向度的展示,传承技艺的工匠们既承载历史的责任,同样他们对工作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产生着认可;他们既在自我层面上追求技艺的不断提升,又愿意与其他匠人通力合作,使作品的效果与呈现达到完美。
中国匠人与日本职人的两重状态,同样也是中日两国文化底蕴的差异。中国纪录片对匠人们的如实记录,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展现了文化底蕴之间的差异。《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后,又推出了《大国工匠》《我在故宫六百年》等影片,中国通过这些群像式的人物展示当代中国匠人的精神风貌,展示传承数千年手艺的匠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个人风骨。国产纪录片对匠人的记录显然也必将会影响物质时代的人们对于“物”、对于“人”在空间尺度、在时间尺度所处的位置的思考,也会从思想层面、精神层面引发人们对当代匠人价值的思索,这或许也就是国产纪录片在近年来孜孜不倦描绘“匠人”的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