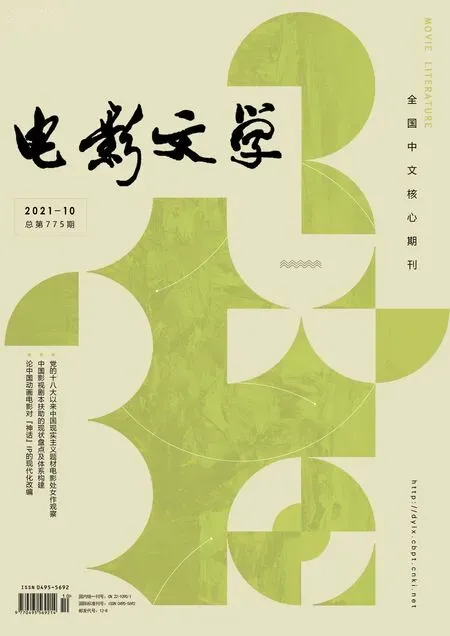档案、空间与身体:奉俊昊电影中的记忆
2021-11-14王灿
王 灿
(武汉轻工大学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23)
电影是一种共时与历时的集体创作,观众在观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限于导演所设置的镜头,也随着导演对剧情的走向而框限在一个被建构的文本里。然而,观众要如何在观看影像的同时唤起自身的记忆,或对一种不曾经历过的事件产生共鸣?韩国著名导演奉俊昊利用了空间、档案唤回过往熟悉的记忆,使其成为某种可见、可形塑的存在,通过影像的再现,重新展现一段新的记忆。电影的语言建立在电影创作者与观众共享的符码上,电影文本不再只是一种影像生产与解读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是观众和作者自身解读与共同合作的作品,因此影片成为一种开放性文本。
一、记忆图腾:档案与媒体
历史记忆如何被重塑?集体记忆要如何被唤醒?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中认为,人类的记忆在集体情景中才能发挥,其情景可以由重大的社会性纪念日唤起,也可以由家庭或一群人对过去重大事件的述说唤起。《汉江怪物》片头在太平间倾倒化学物料的场景,是映射2000年韩国环境监视团体所揭露的一个真实事件。虽然奉俊昊利用这一事件去创造一个虚构、玩笑式的故事,但它的存在在这里也是作为一个提醒过去的事件如何用一个不可预知的方式重返并影响到现在。在电影前段,怪物爬上陆地造成一场大规模的伤害,在之后集体葬礼的大厅现场里,我们看到一片混乱场景:主角们哭喊、打架、摔倒,在这些嘈杂声的背面,广播声呼叫着违停车辆的车牌,请车主将车移开。针对这一段混乱、喜剧与悲伤交错的画面,奉俊昊说道:“我想做一组连续镜头,包含悲伤、幽默、古怪以及一种超现实的怪异感。我认为这就是韩国的现实,韩国已经发生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超现实灾难。”奉俊昊对这一场景的安排,无非是想唤起许多过往韩国人所熟悉的创伤记忆。如:1994 年圣水大桥的倒塌、1995 年三丰百货倒塌事故、2002年两名韩国女学生遭美国坦克车辗毙等。而《杀人回忆》则是通过警察调查无果的故事,将悲痛的对象指向死亡的受害女性,同时也指向其时代本身,使华城这个地区成为一个韩国人民的记忆之场。
韩国影评人全钟铉在评析《杀人回忆》里提及:华城连环杀人事件的“回忆”作为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影片试图通过历史事件的再现,重构与重探一个历史性档案、一段当代历史的可能。影片为记忆建立档案,其中包含了回忆的排斥与遗忘的运作,然而,历史的记忆要如何重现或再现于影像中?奉俊昊的影片里,利用了“档案物品”的建构重现历史的当下,并在剧情中成为对同时代政治、社会的反思,物品成为回溯记忆的媒介,也成了韩国意象的表征。
(一)档案文件:历史记忆与再现
集体记忆指向时间维度,聚焦于集体层面上的过去,重视记忆的传承延续与发展变化,关注群体记忆如何被选择与建构。《杀人回忆》以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背景设置,随着案件的调查发展可能涉及某种历史研究。影片中侦探故事的过程成了一个失败的历史研究模式,而警察也就成了失败的历史学家。因此,虽然影片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案件,但它同时也打破了历史记忆的可能性。尽管影片提供了类型的骨架,并融入真实故事,随着调查的失败,类型框架正逐渐被拆解,而遵循侦探叙事的动力也逐渐消散。全钟铉提到,影片的最后,暴力犯罪不再作为创伤的替代品,而是作为怀旧的对象,不仅因为谋杀本身以某种方式回溯,并因为它们标志着过去的调查发现和历史记忆似乎是可能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档案热》(Archive
Fever:A
Freudian
Impressio
,1996)一书中指出,虽然档案无法让我们回到真实过去的当下,却能给予我们 “碰触过去当下记忆的可能性”。在《杀人回忆》里,充斥着档案、成堆的文件、照片以及在调查过程中所寻找出的各种证据,奉俊昊将各种“档案”加入剧情中,以“历史证据”去重构“新的记忆”。在《杀人回忆》电影的开头,主人公朴斗满在排水沟下发现第一位受害者时,画面所浮现出的日期是1986 年10月23日。电影最后,警察曹探员在执行截肢手术之前,朴斗满代替他的家人签署手术同意书,镜头捕捉了同意书内容,其日期是1987年10月20日。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奉俊昊在电影中利用案件调查的时间顺序,将各种文件、报纸用特写来取代时代的写实性,以景框来成为观众的阅读文本。在一连串的调查与失败的循环中,文件日期的显现也提醒了观众一个事实:从第一个案件开始到结束,显示出调查案件的证据缺乏与破案失败。
虽然在电影里不能完整地提供可靠的调查事实,但在影片中的日期通过新闻、媒体等影像的呈现提供了时代的规律性,将过去已经不可挽回的记忆重新存档。在警察局长第一次出现的画面中,镜头拍摄了局长手上的《朝鲜日报》大篇幅报道了华城的杀人案件,凸显出这一偏远乡村的事件已成为全国所关注的焦点,而报纸上方也显示出日期,是在案件发生近一年之后,案件陷入胶着,而警察的调查似乎没有任何进展,此时的时间呈现似乎更凸显了警察的无能。本内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从共同的语言与民族的建立的关系,进一步解释了印刷技术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是促成了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特别是报纸,因为当原本尚无关联的人,由于阅读了同一份报纸、看见了相同的内容,便开始关注其所提供的资讯,开始产生同样阅读的彼此是共同体的想象。他指称报纸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也就是说阅读报纸就如同仪式般,在不同地点被同时的阅读、消费进行着,产生一种“共时性”的认同。观众通过镜头看着影片中局长看报纸的模样,当镜头切换至报纸内容时,观众成了最直接的阅读者,报纸的出现提供了“想象共同体”一种再现的技术,使得观看影片/报纸的当下,观众会认为自己身处在同样的时空背景里。
此外,录音也成为另一种媒介、一段口述历史的物品,录音带成了一件被记录下来的历史档案。女警前往询问案件受害幸存者并使用录音器材将此对话过程记录下来,镜头特写到录音机,缓缓转动的录音机成了凶手的象征,幸存者用颤抖、惶恐的声音缓缓叙说案发的过程,直到录音机停止,案件叙说结束,幸存者如解脱般转头看向窗外。录音机与角色话语的交织形构成存在于影片的档案,记录了口述的历史当下,而角色所说的“我故意不去看”“如果我看到他,他一定会杀我”两句话,不仅是陈述回忆过往当下对凶手的恐惧,对应于历史背景,“他”也成了被投射到20世纪80年代肃穆社会的氛围下韩国人民的恐惧样态。在此,录音带不仅成了新建立的档案,而通过镜头的特写、角色的述说配合着录音机转动的画面,如同历史档案播放的当下,辅助了过去记忆的重返。当镜头切换到录音机录制结束停止的当下,我们回到了影片叙事的当下时间,这段声音档案成了影片所记录的档案。
奉俊昊利用档案记录呈现的方式,以反向思考批判了历史的真实性,尤其是案件的20世纪80年代背景,时代的历史是通过口述与文字所记载而得知并流传,对于历史记录抱以“真实”而客观的想法。然而,“历史总是通过记录者的想法被折射”。也就是说,档案或是历史性影像在影片中成为导演诠释下的物品,比起观众、角色本身的主体记忆,只是某种事物遗留下的物质性痕迹,虽然容易引起观看对象的诠释再现,但又因为其物质性的痕迹与历史的联结,反而让观众感受到被意识形态建构的痕迹,在接收的同时也可能存在不同时空背景下被无限翻转、再解释的可能。
(二)再现的记忆:媒体与相片
媒体作为现代化进程中重要发展的一环,在数码技术的进步下,社会充斥了手机、监视器、相机等可摄影的机械,而被记录的影像成了一种历史的档案。有趣的是,奉俊昊的影片里看不见韩国近年来的社会高度发展景象,而存在影片中的现代化科技产物,在电影里最终却也未能破案。在《杀人回忆》里,最重要的DNA证据,韩国当时并没有相关的检测仪器,必须送往美国,但最终却也未能成为破案关键;《汉江怪物》中,主人公弟弟朴南日通过GPS定位系统找到侄女贤书所在地,但最终贤书仍死于怪物之手;《母亲》中母亲找寻破案关键证物的科技产物(手机),然而,却也无法成为辩证的佐证;而以现代社会作为背景的《绑架门口狗》,却也因为人性的贪婪,最终“现代人”褪去其外衣,回到如动物般的野蛮、原始本性;在《潮流自杀》短片中,奉俊昊以监视器的画面构成一个故事,将现代社会下的潜在问题显露出来。通过监视器影像我们可以看到一名原先努力工作的男子,面临挫折而导致他走向抢劫、杀人一途。监视影像的呈现如现场直播般,我们观看着一个人的遭遇,这是存在于现实社会中,亦是我们周遭的人。
在奉俊昊的影片中,“肖像照片”成了重要的物品,而这些摄影相片也都成了叙事附加的重要影像。摄影的真实性各有其时代意义,对于摄影肖像的呈现,透过物质性的留存,档案才能成为建立集体记忆的根本。中国台湾学者林志明指出:“摄影在社会体制及社会用途中的变化,摄影肖像作为一个形式类型,其变化轨迹主要是由公众性领域朝向私人领域的过程……摄影肖像的历史从一个指认功能(identifying)走向认同功能(identification)。”“摄影肖像最早是被用于警察拍摄犯人的肖像照片。其大量的犯人照片变成一个巨大的档案……在指认功能的过渡中,它代表的是社会身份控制过程中视觉成分的整合。”档案作为一种历史再现的科学证理,而照片在影片中成为一段捕捉摄影当下的时间残存。
假设在《杀人回忆》中的肖像是一种传统的指认工具,到了现代发达的摄影技术,照片被数字化,可以更精确地看到细致的细节,可以被放大、修复,照片的真实性引发了质疑。在《母亲》里,伴随数字技术的进步,照片可以再制、再修饰,将丑陋的细节遮蔽。当照相馆老板娘回想起被谋杀的女孩想将她手机的照片冲印时,剧情开始另一个叙事转折与伤痛的循环。
回到初始的肖像功能,历经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指认功能依然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作用。然而,借由数码的修复,指认功能的真实性产生矛盾,更能扭转成造假的工具。《母亲》中被杀害的女孩手机的照片,成为潜在的报复和勒索的工具,在女孩生前,这些照片是她的伤痛的回忆记录。死后,替代成母亲调查凶手的指认证据,更是母子成为共犯的工具。在影片中,手机成了一个有趣的物品。相对《杀人回忆》的案件调查方式,《母亲》展现了一种科技进步时代,使得调查方式多元甚至更容易处理,而象征现代产物的手机更是人手一个,一般民众也能当起侦探或创造一则新闻话题。进步的时代使得社会结构被改变,也就凸显出其中所隐含的罪恶愈趋增多。因此,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科技如何变成暴力物品或共谋的一部分。
二、隐喻的场域:景观与空间
电影中的许多物品,包含场景、角色与物质性的物品等,在影像中不仅作为叙事的一环,亦是作为时代产物下的变革痕迹,尤以场所、景观作为塑造时代氛围的主要要素,场景不仅作为记录的物品,同时代表了社会与文化空间转变。特定的空间和地理形势都与文化的维持关系密切。这些文化还不只牵涉明显可见的象征,也涉及了人群生活的方式。电影空间场域的建构对于电影叙事的构成在于叙事的表达方式,依照叙事的结构安排情节、人物特性、组织对白、建构冲突等,而空间性的视觉结构将影像、剧情等要素之间的关系重新调整,成为叙事背后的逻辑与寓意。
在奉俊昊的影片里,景观的镜头有一定分量的存在,这些景观都是已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仓促进度所重创:韩国迅速萎缩的自然景观,如山岭、河流、农地、蓝天、森林等,这些经常占据了奉俊昊电影的想象,构成了他电影叙事中的重要元素。尤其在《杀人回忆》与《母亲》中的非都市场景占有重要的位置,其中《杀人回忆》更是奉俊昊努力去重现20世纪80年代韩国尚未现代化、发展相对落后的乡村景观的结果。在现代化背景的偏远地区,奉俊昊采用广角镜头去描绘整个城镇或乡村的景观。为能使时代的氛围呈现于镜头前,并与叙事内容相融合,奉俊昊采取了时代场域与现代化空间作为记忆再现的空间,他试图通过这些景观与空间的呈现,从中显露其背后的象征寓意。
(一)现代化的工业景观
以20世纪80年代作为叙事背景的《杀人回忆》,除了揭示军人政府独裁期间的韩国社会暴力,同时通过场景的呈现,巧妙地暗示韩国迈向经济成长与现代化付出高昂社会成本的代价。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虽然呈现出一个先进的现代化进程,然而社会不公与专制现象蔓延、恶化。这时期的电影开始出现反现代、反西化的民众群体与意识,不见现代化光明的一面,更多凸显出现代化背后的不堪样态,电影成了创作者意识形态斗争的宣泄。如朴光洙的《黑色共和国》,凸显20世纪90年代前后韩国劳动市场的现实状况;《美丽青年全泰一》,则通过处在狭小工厂空间的女工情景,利用过去和现在互动的结构,反省了劳工的境况。
广义来说,现代化在实质上是西化的进程,是18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工业背景下建立理性、共和的文化,创造一个“进步的世界”。但比起西方人民而言,非西方的人民对现代化产生的矛盾感在于“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这一事实带来复杂的影响,比起表面的现代化发展更令人困惑。而对韩国人来说,可能更相信现代化即是认同“西化”。在种种尚未适应的变革环境下,出现了资本家与劳工、统治和反抗、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过去与现在的矛盾对立。
1988年汉城奥运之前,国家把当地社区夷为平地的“美化活动”后,政府对居民的唯一补偿就是汉江摊贩的经营权,从《汉江怪物》主人公朴氏一家的生活与工作中就可见到历史痕迹。背景为现代城市的《汉江怪物》,镜头却集中在主人公朴江斗一家的狭小店铺以及汉江下的下水道,现代化的城市景观几乎没有出现在影片内,唯一出现的城市景象,是在朴氏一家各自逃离分散后,我们看到站在马路边的民众,各个戴着口罩抬头看着电视墙上的新闻,接着随着公车的经过镜头转换到坐在公车上的朴南日,随着他的视线我们看到了窗外耸立在夜晚的大楼,接着在别有目的的友人“帮助”下进入大楼内。奉俊昊说道:“在拯救贤书未果、朴江斗的父亲死去后,我想我们得到了无助的感觉。当他们分散后每个人都受到考验。这是我们第一次从汉江脱逃,我们突然看到市中心,南日的出现像个犯人似的在奔跑。当他戴着口罩走到城市后街,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氛围展开,仿佛刚刚发生的事件是不存在的。”奉俊昊短暂地将城市景观呈现,但朴南日最终只能靠自己,并狼狈地逃离大楼,再度回到汉江下水道。在此,汉江就如一个“收容”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人的场所,令人联想起“汉江奇迹”,虽然带动了韩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却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如汉江的环境被破坏,其代价是造成了一只怪物的诞生;首尔虽然从废墟中发展成为现代大都会,但汉江也成了现代化的牺牲品。
将时间拉回到20世纪80年代,《杀人回忆》的背景正是韩国社会转型的时代,我们看到影片中的乡村地区逐渐有了工业化的痕迹,如广大的采石场与嫌疑犯朴贤奎所工作的工厂。农业村落与工业建物构成了对比强烈的地景。这些地区本身与其时代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地居民开始脱下农装、穿上工作服进入工厂工作,从农民变成劳工。这样的工作转向意味着整个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化的进程,使韩国步入转型而有越来越多人成为劳工。在资本胜利的传说底下,是以劳动来支撑现代的工业都市。
在一场三位警察追逐自慰男子到采石场的场景,一个长镜头将夜间宽广、巨大的采石场呈现:粗糙、灰白的空间,数以百计的工人穿着同样的黑色衣服在采石场穿梭、劳动,这些劳工成了无特征的无名个体,如无身份的群像展示。冷漠、机械式的动作氛围充斥于工地,大量的灯光照射群体、灰白的石壁将工人包围。这幕场景以群体景象的劳动来凸显社会转型所形成的氛围,进而与悠缓的农村印象形成对比。在经典论述中,马克思提出人的身体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中,被异化成机器,失去了人的主体性、控制权;而在精神分析的探讨中,经常将人对身体的认同看作是人建构自我的关键要素。人物身体是构筑电影中角色主体特性与不同背景下所产生的相异形体,这种空间与人物的隐喻关系,就如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所描述的,当越来越多人被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越来越多令人厌恶和攻击变得越加野蛮、冷漠,每个人变得极度无情,或是变得歇斯底里。如《汉江怪物》中与怪物曾经接触的人们,被认为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疾病,而被强迫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甚至进行“消毒”。
由于现代化,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人们在工业化的环境中工作,使用先进的技术,居住在城市或郊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巨大变化愈趋复杂。但在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必然存在各种事物的矛盾与冲突,奉俊昊以现代化的工业景象,将案件、时代氛围做一个巧妙的联结,同时也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消极影响,如对政府的不信任、重视利益与发展所带来的阶级界限、环境被破坏的危机、人性因环境变迁所产生的影响等,伴随因其产生的各种矛盾,在某些部分上可能否定了现代化所带来的成果。
(二)光明背后:地下的黑色空间
对奉俊昊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华城,在《杀人回忆》里揭露了现代化发展的不足与警察部门的束手无策,在这种时空空间的架构下,人们的死亡成为一种无可避免的状态,悲伤的历史叙事只能以失败告终。在《杀人回忆》中的谋杀和死亡的发生,不仅是因为一个未知的凶手,更广泛地说是由于空间和时间的影响。因此,隐喻的影像在片中展现出一个国家的失败,更借由一个“黑色空间”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荒废、破旧的排水道与隧道的黑色形态。在电影的第一个场景中,一具女性尸体被丢弃在稻田筑堤旁的排水道中,借由镜面反射光线才看出身体已腐烂并被无数的蚂蚁覆盖。这样的影像在电影后半段再次出现:时间来到2003年,当朴斗满已卸下警察身份而再次回到电影第一个案发现场,当他再次往排水道中望去,里面没有尸体,镜头缓缓推进、往排水道另一端前进,如火车隧道中,望向过往,重新找寻那段无法抹去的挫败记忆。
情节告知故事行为者相关的环境、所处位置和行动路径,将有利于我们对故事空间的建构。这些影像赋予了空间新的寓意,透过叙事情境与角色的反面行为来构成强烈的对比性,让叙事情境塑造成一股不安定感,成为潜在的破坏与威胁。在形塑历史剧变中的现代世界,存有许多清晰可见的景象,包括原野、农村、郊区、工业城市。而电影中所描绘出都市对自然的依赖性以及生态的破坏(森林、河流),运用剪接与镜头的连接,构成多层次的空间意义,如工厂、巨大采石场成了国家权力的权威象征,现代化的痕迹在场域的隐喻中受到另一面的冲击和改变。而在现代城市里,怪物的诞生是恐怖的重生,它显现了人与自然、自然与工业之间不再加以区分,当工业从自然中提取原生物料,然后再将其垃圾投入自然中,这种循环的方式掩盖了人类、自然和工业各自独立的存在,怪物的出现揭示了现代化背后的复杂结构,汉江的纯粹被转化成矛盾与暧昧的存在。“黑色空间”调和了奉俊昊对于过去与现代的韩国历史观点,这些工业化、城市破败的景象在犯罪、惊悚、神秘、恐怖、喜剧等元素里,利用类型化的叙事,重新设置出另一面的记忆再现与情感。
三、历史伤痕:有缺陷的身体
在迎来21世纪后,韩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借由影像来批判现代化、工业化、社会动荡与民主抗争的电影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后的科技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矛盾与金钱至上的资本社会。如奉俊昊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寄生虫》,表现韩国现代社会变化不定的样貌,后工业社会的生活是憔悴、繁乱和迷惑,不同阶层之间充满分崩离析的症候,影片对现代性和不平等阶层的抨击,更准确的是冷嘲热讽,对现代化强而有力的反话语。
奉俊昊的影片中几乎都会存在一个“智能障碍”的角色,不管是《杀人回忆》的白光浩、《汉江怪物》的朴江斗、《母亲》的泰宇还是《寄生虫》的基宇和前任女管家丈夫,这些角色缺陷的身体状态不仅成为易于被顶罪与诬陷的身份,更是剧情中隐藏的灵魂人物。
《杀人回忆》中被当作案件嫌疑犯的白光浩,从其脸面的烧伤痕、唯唯诺诺的说话方式以及总是微微驼背的身体,让人对他产生同情弱者的心态。在影片里,他是个手无寸铁、被警察殴打的平民,似乎在权力底下,他只能乖乖地承受。最后,他第一次起身反抗,是拿着木条朝向殴打大学生的曹探员,并使他的殴打结束。在两位警察拿着朴贤奎的照片要白光浩确认凶手长相时,白光浩睁着眼看似仔细地观看,却又像并未聚焦于此,而后将视线移开照片,缓缓地说出:“你知道那有多热吗?你知道那火多吓人吗?”“在我小的时候,那个人把我丢到火里。”白光浩转向旁边,镜头随着视线移转,白光浩的父亲从远处跑了过来。在这里,我们可以得知其脸部烧伤的来由,而在说话的同时,父亲的出现似乎暗示着这场火与他有关。然而,我们无法进一步知道这场火的来龙去脉。白光浩突然吹着哨子跑向了火车,并对着跑向他的朴斗满用柔弱的语气叫他离开,下一秒,白光浩遭火车撞上身亡。白光浩的死亡代表了两件事的终结:奸杀案件与军事时代。唯一看过凶手面貌的白光浩,对他来说看到犯罪过程或凶手是谁并不重要,因为身处那样的时代,就像习以为常的事情,是个暴力者与受害者每日共处的情形。当他第一次起身攻击暴力者(曹探员)的时候,结束了专制的政治,而他也如同对抗军队而牺牲的民众般,与那个时代一同共生、共灭,却也是一个时代真相的消失。他站在铁轨上吹着哨子警示朴斗满不要接近的行为,或也暗示着新一场反抗将起。
与白光浩相似的身体状态,亦出现在《母亲》的角色里。两部电影皆以“智力障碍”的角色作为剧情中的重要人物,但在《母亲》中的泰宇却与唯唯诺诺的白光浩相反,泰宇是个充满自信的角色,却也相对冷血,在犯下杀人案后,仍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与白光浩相同的是,泰宇回忆的过去也是被伤害的过往,白光浩选择埋藏真相,泰宇则直白地揭露事实。在此,泰宇缺陷的身体状态缘由明朗,以坚定的眼神与话语将这股罪恶嫁接到极力隐瞒事实的母亲身上,至此,两人成了共生、共谋的犯罪者。母亲弱小、年迈的身体在电影里几乎身处一个充斥阴暗的空间,不管是充斥药材的店铺还是与泰宇的居住地,这些黑暗空间被塑造成母亲的基本生存空间以及他们那些人最后生活的事实。而在电影最后,其辽阔的草原风景与前面狭窄、封闭的空间形成巨大的反差,母亲的身形如倒影般虚幻,不复存在。母亲为拯救自己的儿子离开罪恶,却使自己愈趋身陷到如人间地狱的生活。
而《汉江怪物》中的朴江斗,是白光浩与泰宇的综合体。朴江斗在影片中是一个父亲的角色,但与《母亲》中的母亲形象又不同,其呈现的是一个无能、无知、懒惰的角色,像是韩国一个后工业时代的韩国人物形象,不仅牵错女儿贤书的手导致贤书被怪物抓走,并错算子弹数量让父亲死亡,还成为国家实验团队研究怪物感染的实验对象,抽血、解剖、植入,他被当成一个实验物体而不是一个人类。达西·帕奎特(Darcy Paquet)认为《汉江怪物》中的每一个角色可以被看作是代表过去十年不同的韩国历史样貌:朴江斗作为大家长,一个朴实、维护家庭的20世纪60年代的家长,在贫穷的生活中努力地养育自己的家庭;江斗,一个精神上出现创伤的中年男子,在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下被迫害的人;南日,在20世纪80年代,参与学生街头运动丢掷汽油弹的经验者;南珠,20世纪90年代,缺乏信心而无法展现自己实力的射箭选手;贤书,一个21世纪10年代勤奋、聪明的中学生。这些角色被放到大时代的隐喻下,朴氏三兄妹的表现成了奉俊昊真正的想象实践,代表韩国真正的草根人民。当三兄妹的父亲被怪物杀害后,他们不再如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期间,朴光洙和张善宇等老一辈导演所回应的历史:以严肃、审慎的忧郁姿态来面对创伤、历史浩劫、国家与家族的丧失。
这些有着“缺陷”身体的角色,在影片中是一个时代、社会缩影的象征,在奉俊昊的影像里,缺陷的角色更接近现实的人物,一种在社会背后不易外显的迫害、创伤。身为新一代导演的奉俊昊,摆脱了身陷痛苦的现实,在电影里刻意避免与现实做直接的对抗,而是借由这些角色,将其身体作为一个重构集体记忆的影像,让其身体成了人民的行为事件,去回应在现代语境下的历史记忆。
结 语
依循哈布瓦赫的说法,集体记忆一种是用来重建对过去的意象的工具,来传承、延续或发展,是建构群体认同、文化凝聚与个人对社会的体验,与个人相比更为广大的力量。档案作为历史记录的物品,奉俊昊利用再造的档案重新唤起过去的记忆;同时,这些因应时代的重显而被制造的档案,也成为影片拍摄当下的档案。这种暧昧的形塑不仅通过时间日期试图让档案重返过往,并使得影片本身成为被记录的档案,就如德里达所论述,档案的建构具有遗忘、解消、摧毁的死亡驱力。奉俊昊借由档案的创建来召回暂时被大众遗忘的记忆,再以这种非真实的档案来销毁受到过去掌权者所建立的记忆。
在空间的建构模式也是相同的。电影的场景不仅记录当下的样态,同时又显示社会过去与现代之间转变的痕迹,特定的空间和地理形势都与文化的维持着密切关系,同时也涉及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通过导演的配置,客观的空间就成了被诠释成不同样态的场域。电影的空间建构对于电影叙事构成的挑战并不在叙事本身,而在于叙事的表达方式,通过情节的安排、角色人物的塑造、角色对白话语以及建构戏剧冲突来接合电影的完整性。因此,空间就成了视觉建构的重要元素,不同的空间结构将重新调整与解释其意义,并且企图去重新将过往记忆纳入当下的空间。在追溯某种记忆的空间场域中,人物成了赋予空间解释的重要角色。前文曾提及,奉俊昊将人民的生活景象来形构成一个时代的显影,因此空间与人物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若以个体来论述,人物自身的身体状态就成了另一种记忆表现。身处韩国时空背景的人物,其不可避免地成为某种历史的隐喻借代。
奉俊昊让身体或生理上带有缺陷的人物出现在他的每一部影片中,成为奉俊昊某种角色形构的特色,这些身体缺陷的人物贯穿了影片的叙事走向与关键,体现了属于韩国历史的具体化。韩国学者徐南同认为,因为地缘政治与历史关系,韩国的民族特性建构在“恨”之上:“韩国人从日本殖民统治、毁灭分裂的朝鲜战争和战后严重依赖外援的精神状态中恢复过来后日益觉醒的自我意识和自尊。”这种民族特性被建构在身体缺陷的角色身上,奉俊昊将其纳入时代之中,让人物在过程中回忆,显露出历史记忆与时间的关系、遗忘与记忆的关系、现实与记忆的关系等,重构与反思大时代之下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