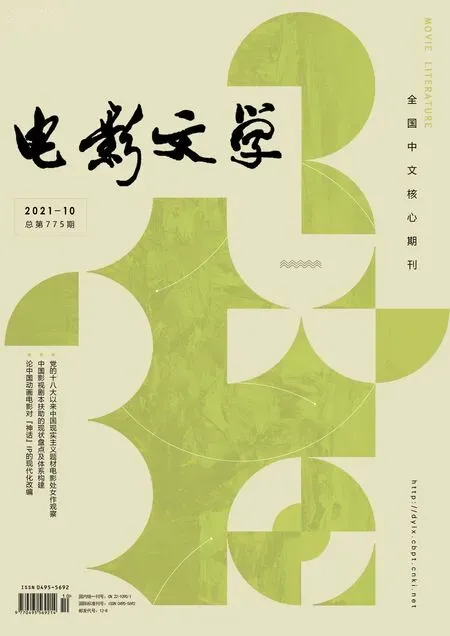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城市电影的“时间错位”
2021-11-14刘建状
刘建状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中国城市电影的发展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相一致的。20世纪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现代化都市,城市电影的发展迎来的第一次高峰。在中国电影史上,意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构成了一个特定的电影文化和城市文化能指。改革开放后,伴随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电影也在90年代迎来了第二次发展的高峰。第五代导演的“回城”意味着中国电影创作理念的变化,从对“历史寓言”的钟爱转移到对当下社会的关注;“城市一代”第六代导演的崛起则从电影制作的根源上激活了城市电影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涌现出一批经典的城市电影,如黄建新的《站直喽,别趴下》、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张扬的《爱情麻辣烫》《洗澡》、张元的《过年回家》、管虎的《上车,走吧》、宁瀛的《夏日暖洋洋》、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张一白的《开往春天的地铁》、路学长的《卡拉是条狗》、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陈凯歌的《搜索》、娄烨的《浮城谜事》等。90年代后,城市电影开始关注都市民众在城市化和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生存问题,关照人的情感状态和精神世界,构成了关于“城市想象”的关键部分。
“时间错位”是指城市人物在快速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内在矛盾。这里的时间概念并不是电影叙事层面的,而是一种“心理时间”。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将时间分为两种:一种是钟表度量的物理性时间,他称之为“空间的时间”;另一种是主观化的被体验的时间,即“心理时间”。柏格森将两种时间对比,认为“心理时间”才是真实的时间。“心理时间”指代了90年代后城市电影中主体人物的精神内在,而“时间错位”则将这种内在具化为在面对飞速变化的时代时所出现的复杂的内在矛盾。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被改变,铺天盖地的现代文明和流行文化不断冲击着传统思想与固有认知,传统的社会关系正在潜移默化中重组,人们的自然的时间被打碎,处于物质和精神、历史和当下、传统和现代的矛盾中。
一、空间巨变:一种时间的解构
空间承载了时间的流动,时间赋予了空间应有的意义,而城市空间的巨变则带有强烈的“时间解构”色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走在超速现代化的路上,成为一个建构和摧毁同时并存的空间。所谓建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起步于90年代;所谓摧毁,则指向了都市民众受到的强烈刺激。90年代后的中国城市电影将镜头对准了正在发生质变的现代城市,城市中的各类空间正处于不断的改造、拆除和更替中。伴随这种空间的剧烈变化,作为城市主体的人物,尤其是普通民众为核心的群体,出现了心理和精神的不适。原有的生活常态被打破,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格格不入,进而在精神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怀旧、抗拒甚至是错乱。事实上,电影中所表现的这种内在矛盾本身是人物所处的客观时间和心理时间的不对称,是“时间错位”的一种表征。
空间巨变最直观地体现在了城市拆迁上,而看似只涉及空间改造的拆迁,却是一种带有暴力元素的“时间解构”。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拆迁成了一个永远保持热度的话题。拆迁最直观地改变了城市的景观,它让高档社区和繁华的商业街比比皆是,也让人们曾经熟悉的胡同、弄堂和院落等传统城市景观逐渐消失。事实上,拆迁所带来的空间巨变,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更是对原有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瓦解,甚至是从精神上影响了人物对于世界的认知。
陈凯歌于2002年拍摄的电影短片《百花深处》就是在表现拆迁背景下,空间巨变所导致的精神问题。电影中冯先生的“疯癫”形象其实是“时间错位”的一种表现。老北京人寻找着自己曾经的家园,搬家公司的人在利益的驱使下,陪同冯先生上演了一出“无实物搬家”,看似滑稽,却令人心生悲凉。名为“百花深处”的胡同在电影中成为一种情感符号,它不仅代表了冯先生记忆中的家,也代表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消失的老北京文化,更是以一片废墟指认了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人物所出现的内在矛盾。由此而言,电影中的那棵老槐树成了一种情感寄托,它和从废墟中挖出的铃铛一样,都指出了冯先生“疯”的根源。“疯”成为一个语义丰富的所指,指向了空间巨变给城市人物所带来的精神冲击,指向了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被忽视的疼痛。生活常态被打破,身处现代城市中却无法找到身份的认同,进而成为一个游离于自我和外界之间的矛盾体。
电影《过年回家》中,主人公陶兰在服刑多年后的一次回家探亲中,因拆迁而找不到自己的家,从而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中。造成精神冲击的不仅是与世隔绝的十几年牢狱生活,更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空间巨变所引起的情感不适。当然,所谓空间的巨变也包含了人物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进入一个陌生的反差极大的空间里。黄建新导演的电影《站直喽,别趴下》中,作家高文乔迁新居后与邻居产生了种种矛盾,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被夹在“政治”和“经济”的“协商”中,最终难逃再次搬家的命运,事实上,作家高文的经历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时代语境。
城市空间的背后其实还包含人的生活轨迹和记忆,当城市的旧建筑拆掉,被新建筑取而代之,改变或变迁的不仅是城市的外观,底层城市居民的记忆也跟着不复存在了。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空间变化所打破的生活常态,以及产生的“时间错位”往往是不可逆的。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城市电影常常通过“怀旧空间”的建构来去缓解这种空间巨变所带来的疼痛和错位。如张扬电影《洗澡》所描绘的大众浴池,“清水池”不仅承载了老北京人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也治愈了城市人物的种种焦虑。电影《老炮儿》中对于北京胡同生态的描写,“六爷”的形象虽然带有悲情色彩,但人物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也为处于内在矛盾的群体做了精神表率。
二、文化扩张:一种浪漫的想象
毋庸置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姑妄称之为“大众文化”的通俗、流行文化以愈加有力而有效的方式参与了对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构造过程。同样,90年代后的中国城市电影所建构的多元的城市想象中,也包含了对大众文化扩张的准确表述。以底层生态为主要群体的人物,在面对城市开放过程中不断涌入的流行文化时,产生了一种近乎着迷的浪漫想象,并因此出现了“时间错位”的表征。
大众文化的扩张引导着流行音乐、电影电视文化、广告文化、网络文化的广泛传播,从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渐在思想和精神中生根发芽。大众文化的扩张过程中,多种媒介的文化元素共同建构了一个充满浪漫想象的“外界”,并与人物自身所处的现实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条源于自我内在的鸿沟出现了。“山的那边是什么”,这个带有哲学意味的命题,不断提醒着人们对于外界的追求和想象,但也同样放大了人们的现实处境与无奈,极具内在矛盾的个体也由此而生,既是豪情壮志的,也是无奈悲情的。
贾樟柯2006年导演的电影《三峡好人》,以世纪工程三峡大坝的建设所引发的大规模移民为背景,以两个山西人的寻找为线索,传递出现代文明洗礼下中国底层生态以及情感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电影中两个长江岸边土生土长的少年,一个喜欢在江边歌唱,一个沉浸在电影《英雄本色》的江湖中,他们都成为大众文化扩张中的产生内在矛盾的个体。拆迁过后的废墟里和因为移民而变得格外繁忙的河道上,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孩重复唱着《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作为2004年极具代表性的两首流行音乐,本身是流行文化在现代社会传播的一种缩影。即使是一个偏远的县城,一个拆迁过后的废墟,一个青春懵懂的孩子,都在接受着关于流行文化的洗礼。歌唱中他面无表情,甚至有些不安,歌唱变成了一种仪式,一种在“历史环境”下简陋的成长仪式。此刻,“时间错位”表现为一种成长的迷茫、恐惧和对未来的无知。由此而言,城市化带来的绝对不只是现代化美好的前景,更多的是成长过程中的阵痛、迷惘,有时甚至是绝望。自称“小马哥”的社会青年对电影《英雄本色》中周润发所饰演的“小马哥”有着强烈的崇拜,香港电影所缔造的“江湖”,成为这个普通青年的幻想。当“小马哥”的尸体从废墟中被挖出时,这场现代文明洗礼下的一个“悲情”人物也在“时间错位”中退场了。“再见移民”的巨大标语下,开启了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固有的生活习惯与不断涌入的外来文化,近千年的小城正在经历着一场关于古老和现代的对抗,带出的却是现代文明洗礼下中国底层的生态,以及他各自笃定执着的情感和价值观念。
事实上,在大众文化的扩张中,以青少年为主要群体的人物更容易出现这种“时间错位”。青少年群体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使得青少年群体时期是认同形成的过渡和关键时期。比起其他年龄群体更容易和渴望接受大众文化的影响。在电影《任逍遥》中,山西大同的两个失业工人的孩子,在那个社会经济转向以及卡拉OK和酒吧等娱乐中心大量涌现的年代,出现了价值观念的矛盾。抽奖获得的美元,被讨论和模仿的电影《低俗小说》,被传唱的流行歌曲《任逍遥》,这些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时代气息夹杂着北京奥运会和世贸组织的新闻,共同构建了一个新的世界。只不过这个“世界”与两个青年离得那么近,又那么远。事实上,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生活,甚至是自以为身处的江湖世界,不过是流行文化下的浪漫想象,是大众文化扩张过程中承载于个体内心矛盾上的“时间错位”。
贾樟柯将《三峡好人》的英文名字定为“Still Life”,静物本身也是一种承载于物质上的时间概念,它代表的是周围环境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人们很难不产生心灵的促动。贾樟柯曾这样描述他在拍摄《海上传奇》时的感受:江的这岸是一个小镇,江的那边就是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小镇上人会经常看到无数的货轮在海上行驶,载满了汽车,载满了城市中所需要的各种物质。面对这些,他们会不会去想,自己何时能买得起,自己何时能够去往那里。其实,“时间错位”就在这样一次目睹和思考中开始了。
三、身份转换:寻找新的身份认同
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所带来的不仅是城市空间的巨变与大众文化的扩张,也引起了城市人物身份的再造与转换。“身份”(identity)的原有语义首先是指向内在的统一、协调及其持续。但是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物“身份”开始有了一种不确定性,随之而来的是“身份”问题所产生的一系列焦虑。这种焦虑在90年代后的城市电影中表现得格外明显,不仅涉及个体的生存和某个群体的命运,更与不断调整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并且,身份转变所带来的这种焦虑,也伴随着主体人物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逐渐演变为一种强烈的内在矛盾。
身份转换常常是被动和不可逆的,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有些群体常常走向一种带有时间色彩的“历史边缘”。电影《钢的琴》将镜头对准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讲述了一段国企改革背景下工人阶级“身份再造”的故事。电影中的每个主人公都在市场经济到来的浪潮中寻找着自己新的“身份”。这种身份的转换不仅是工人阶级脱离集体神话的过程,也是以个体身份回归社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重新寻找自我价值的过程。虽然《钢的琴》以一种乐观的态度讲完了这个“回炉重造”的故事,但电影中人物面临的所有处境都在述说一种“心理不适”。坚守着工人阶级最后的尊严,对周围的一切感到不屑;保持着“劳动最光荣”的价值观念,在废弃的厂房中发挥余热。《钢的琴》中所表现的这种带有群体符号和阶级意识的身份转换,是全球化语境下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经济体制转变,这其中的阵痛体现在工人阶级身上的时候,是一种身份转换的巨大落差所产生的内在矛盾。
身份转换也会以人物主动的选择为开端,出于对未来狂热的追求,却在新的环境和身份中感到不适。城市化的进程中使得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员,他们在城市中被赋予了新的身份符号。电影《上车,走吧!》,两个农村青年到北京做起了小巴车的生意,他们阅读城市,体验城市;他们在城市中遭遇竞争,在城市中偶遇女性,他们成为新的“都市漫游者”。电影《十七岁的单车》中,农村进城打工的少年小贵成为一名邮递员,在北京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新时代的骆驼祥子”。电影《开往春天的地铁》将视角锁定在了都市人的情感问题,主人公建斌和小慧在北京闯荡七年后,也迎来了失业和情感的双重危机。由此而言,即使是主动性的身份转换,也常常会出现一些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在城市中的失意、疼痛和迷茫。
随着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和城市身份的破坏与重建,“都市一代”带着独立电影的徽章横空出世。他们将自身的经历转化为影像的表达,即使作品中带着浓郁的悲情色彩,但终究是对社会的一种关照。90年代后的中国城市电影,捕捉到了都市民众在不同语境下的身份转变过程,这个过程同样是中国城市化的过程,经济转型以及文化开放的过程。全球化和城市化是社会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的必然阶段,存在疼痛,却走向美好;“身份转变”是人物在时代浪潮中的必然经历,存在焦虑,但向往未来。
结 语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城市电影中所表现出的“时间错位”,是城市空间改造过程中的失落和失意,是大众文化扩张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交融,是长期形成的个人身份和社会关系被打破后的不安与不适。城市和社会的发展永远是带着矛盾进行的,在无可避免的大环境中,城市电影不断关注城市中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而所谓的“时间错位”也仅仅是暂时性的,它会因为不可逆的自然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会在伟大的个体生命的适应中逐渐缓和,也会在中国城市和社会的不断关照中而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