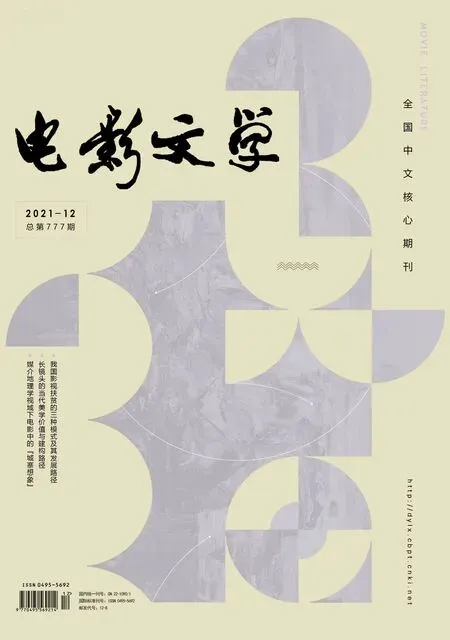试析《隐形人》的“感知受限”范式
2021-11-13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张 娟(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在环球影业放弃将《隐形人》纳入其“暗黑宇宙”后,这部由雷·沃纳尔执导的电影便成为一部将视角主要置于女主人公身上的小成本惊悚电影,也正是在这一转变中,近年来在惊悚电影中频频出现的“感知受限”范式得以大放异彩。
一、科幻概念与悬念设置
一般来说,人作为生命体,拥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与触觉“五感”,通过眼耳口鼻等感官,与外部世界进行多方面接触,是人类获取安全感的保障之一。在电影艺术中,视觉与听觉无疑就是观众接受信息,完成审美活动的重要途径。而所谓感知受限,即人的感官被限制或破坏,或是人与外界环境的各类刺激相隔绝,如让人对光、声音等的刺激麻木化甚至感知彻底消失。科学研究早已证明,当感知受限存在一定时间后,人就有可能陷入生理与精神上的双重不稳定,如产生幻觉等。
惊悚电影作为类型片拥有较为固定的叙事模式:即主人公置身于/走向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随后主人公想尽办法,克服重重阻碍从这一环境中脱离,主人公能否成功脱逃,怎样脱逃便是电影最大的悬念。而在“感知受限”范式中,主人公的困厄与危险,乃至命运的转机很大程度上便来自感知的缺失。这种缺失有可能是主动的,如在《寂静之地》中,保持安静是人们在怪物入侵后生存的第一法则,人们不得不为自己打造了毫无声响的生存环境,这也导致了主人公们难以在生死关头前保持有效的沟通;感知缺失也有可能是被动的,如《无声夜》中麦蒂,《寂静之地》中瑞根的耳聋,《盲女惊魂记》中苏茜的眼盲等,人物的步步惊心都源于其自身难以克服的残障;或是如《屏住呼吸》中,三个小偷误入了盲人老兵黑暗的屋子。而《隐形人》则另辟蹊径,进行了一次科幻与惊悚类型糅合的尝试,以隐形衣这一概念决定了全片的结构动力。
在电影中,男主人公阿德里安是知名光学专家,他研发了隐形衣技术,即衣服上遍布无数微型摄像头与放映机,能够全角度即时转化周围环境的图像,在周围的人看来,穿上隐形衣的人便是“不存在”的,他们的视觉器官并未被损害却被欺骗了,就辨别穿隐形衣者这一目标而言,旁人的视觉是被限制的。相对于《关灯后》中,戴安娜的“女鬼”设定,《隐形人》的这一科幻概念由于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对于观众而言既新异,又具有合理性。更重要的是,电影的两大悬念被制造了出来。一开始观众并不知道阿德里安发明了隐形衣,于是当阿德里安的女友塞西莉亚好不容易逃到好友家中,却总是隐隐感觉阿德里安依然存在于自己身边时,塞西莉亚究竟是不是疑神疑鬼,阿德里安的“自杀”究竟是真是假,就成为第一个悬念。而第二个悬念则是当塞西莉亚发现了隐形衣,知道了阿德里安的诡计后,如何从“我在明敌在暗”的困境中脱离出来。
以第一个悬念来说,长期生活在一个人造成的梦魇中,即使在离开他后,依然出于根深蒂固的恐惧而感到对方对自己的凝视,或是感知到目光无法看到之物,而无法辨析其是不是心理暗示等,都是符合观众日常生活经验,能够充分调动观众关切心理的。而在这一悬念破解后,由于观众得知,阿德里安是隐形衣这一尖端技术的掌握者,同时塞西莉亚的应对手段(如在地上撒粉,向可疑的方向泼油漆等)随着阿德里安对她的嫁祸,塞西莉亚被关入精神病院中而失效,塞西莉亚要夺回自由与清白无疑是难上加难。观众便在对第二个悬念的关注中,积极参与进叙事中,获得一种思维与情绪上的满足感。
二、感知缺失与互动效应
惊悚电影要想达成预定的效果,必须要让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即与观众形成互动效应。而观众与电影中角色的互动又分为直观层面、联想层面、心理层面三个逐次递进的范畴。在《隐形人》中,绝大部分的叙事情境是由塞西莉亚的角度生成的,观众也就和塞西莉亚一起被置于由隐形衣制造出的视觉困境中,体悟到塞西莉亚在具体情境中的感性观念立场。这样一来,一种强烈的互动效应便产生了。
在第一个层面,即直观层面上,观众和塞西莉亚一样,在确知阿德里安就在自己身边,并凝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时,完全看不见阿德里安,也无法向其他人指证阿德里安的存在,陷入极度被动中,焦躁不已。在塞西莉亚住进黑人警察朋友詹姆斯的家中,以为自己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后不久,就收到了不少来自阿德里安的“提示”。如在她试图抽动一块毛毯时,能感到毛毯被绊在地毯上,似乎有人在轻轻踩着,而当她迅速用力一抽时,那个踩毛毯的力量马上消失了;在塞西莉亚将姐姐艾米莉约到玉兰餐厅,试图将一切向艾米莉解释清楚时,艾米莉却突然被一把刀割喉,倒在血泊中,而这把刀马上被塞进了塞西莉亚的手里。在旁观者,如詹姆斯、西德妮,以及玉兰餐厅的其他食客看来,现场并没有阿德里安的存在。而塞西莉亚无论是对面前的空气大吼大叫,转动身体挥舞双手,还是歇斯底里地对其他人辩解,都不能逼迫阿德里安现身,观众也完全无法确定阿德里安的方位和下一步动作。
在第二个层面上,即联想层面上,随着视觉范围内获得信息的有限,人们会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积极寻求更多的信息,也即展开想象。此时,电影在视听元素上的“减法”也就变为了“加法”,残缺反而指向了丰富与完整。如当塞西莉亚猜测阿德里安有可能藏身于詹姆斯家的阁楼上时,钻入阁楼寻找证据,隐隐听到阁楼入口有响动,当她战战兢兢地从狭小的入口低头看梯子时,尽管梯子上什么都没有,但是观众能和塞西莉亚一起想象得到,此时阿德里安就在梯子附近,或是准备抽走梯子困住塞西莉亚,或是准备登着梯子上阁楼加害塞西莉亚。类似的,当观众看到艾米莉收到来自塞西莉亚的辱骂邮件,看到塞西莉亚用于面试的材料不翼而飞时,都能想象出阿德里安在夜里翻动塞西莉亚的笔记本电脑、公文包等使人不寒而栗的场景。《蒙上你的眼》等惊悚电影都是如此,电影不是诉诸感官,而是对观众进行心理暗示,不直接为观众制造令人不适与恶心的客体,而是让观众自行对恐惧根源进行想象,自行扩大摄影机的画框边界。这也正是惊悚(Thriller)电影区别于被称为“血浆电影”的恐怖(Horror)电影之处。
而当观众探寻人物动机时,观众与塞西莉亚的共鸣也就达到了第三个层面,即心理层面。在电影中,阿德里安是一个极为擅长精神控制(Mind Control)之人。所谓精神控制,即“用一种特殊方法打碎人的固有信念,改造形成一种新的观念。其机理是建立在条件反射理论上,通过控制一系列变量,使用种种强化方法,对人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给予持续性的影响和控制,使之服从操纵者的意愿,达到归心顺意,建立新观念并形成心理定势的过程”。电影中的塞西莉亚,以及阿德里安的律师哥哥汤姆都是被其精神控制者。塞西莉亚不断被阿德里安以或软和硬的话术洗脑,在长期同居时住在到处是摄像头的屋子里,汤姆甚至在阿德里安的操控下穿上隐形衣成为阿德里安的替死鬼。正是这种无孔不入的精神控制,让电影始于塞西莉亚给阿德里安下药后仓皇逃走。在现实生活中,隐形衣并没有得到普及,但是精神控制却是广泛存在,而由于取证困难,加害者往往能逃脱法律制裁及道德谴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隐形人”。至此,观众完全能理解塞西莉亚的暴躁、害怕、仇恨等心态,对隐形人的恐惧也达到了最大值。
三、信息差与惊悚效果
除了让观众充分代入到塞西莉亚的立场外,《隐形人》中还有少量镜头是特意从阿德里安视角设计的。这样一来,信息差便出现了。正如希区柯克在“炸弹比喻”中指出的:“……炸弹在桌子底下,观众知道这一点,我们设想,观众看到了——就算是无政府主义者放在那里的。观众知道炸弹将在一点爆炸,现在是十二点五十五分,钟表是可以看见的。同样索然无味的谈话突然变得有趣了,因此观众参与了这场戏。他们想要向银幕呼喊:别再废话了,桌子底下有个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观众知道炸弹及爆炸时间的存在,而将要被炸死者却被蒙在鼓里,毫无逃跑的意识,这便是电影中用以制造忐忑、焦急、惊悚情绪的信息差。
在“感知受限”范式中,信息差来自观众的全知视角以及当事人感官被影响后的限知视角。如当塞西莉亚以为阿德里安死去,并给自己留下了巨额遗产后,与詹姆斯父女心情完全放松,在客厅里打枕头大战。此时,雷·沃纳尔便采用了阿德里安的主观视点:三人欢快打闹的场景距离观众较远,并且为门框、墙壁等部分遮挡,显然有第四个人正在另一个房间中的墙边看着这一幕。类似的还有如西德妮和塞西莉亚在晚上在一张床上各自蜷曲着睡觉的画面,镜头此时也代替的是阿德里安的视点,躲藏在詹姆斯家阁楼的他在夜间下来除了用塞西莉亚的电脑写邮件和偷走她公文包的东西之外,还掀开塞西莉亚的被子,用开了闪光灯的手机拍摄了她和西德妮睡觉的样子,这实际上是一种弥散性的暴力窥视,尽管阿德里安没造成实质性伤害,但观众已备感不适和紧张。最具张力的莫过于塞西莉亚从医院回来,在詹姆斯家洗澡的一幕,雷·沃纳尔先以低机位缓缓推进的移动镜头暗示了阿德里安向浴室的靠近,之后塞西莉亚淋浴、擦拭的景象,观众可以理解为都是阿德里安眼中看到的景象。阿德里安与塞西莉亚如此近在咫尺,塞西莉亚却并未察觉(这次洗浴与电影中塞西莉亚第二次进入浴室,即在精神病院的浴室中故意自杀,吸引阿德里安现身形成对比),观众接收到了这些危险信号,却无法通知塞西莉亚,只能被束手无策的无奈感折磨。
除了显而易见的隐形人视角外,雷·沃纳尔还在电影中加入了大量空镜头。如阿德里安海边豪宅光线阴暗,装修与家具都是冷色调,毫无温馨可言的内景,塞西莉亚在精神病院中的病房,向着詹姆斯的房子步步接近的移动镜头,夜里詹姆斯家内景摇镜头等,这些都可以视为阿德里安眼中的画面,它们透露出了阿德里安跟踪去了不同地点的塞西莉亚的信息,限制、阻碍他人感知者却可以肆无忌惮地观察一切。
正是在这种一次次信息差的制造中,观众对心理扭曲又一直居于优势地位的阿德里安充满恐惧与反感,塞西莉亚最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地借助隐形衣和摄像头伪造了阿德里安的“自杀”,才让观众感到如释重负。
在《隐形人》中,隐形衣的科幻概念让男主人公阿德里安实现隐身,对于女主人公及观众而言,他们的视觉被部分剥夺了。但是这种加害者的“无形”反而实现了为恐惧“赋形”:在塞西莉亚视角下,观众能够充分理解她看不见,摸不着,孤立无援,有冤无处诉的恐惧与悲愤,被引导着成为塞西莉亚挣扎逃离的同路人,而在阿德里安的窥伺视角下,观众又能拥有与塞西莉亚之间的信息差,电影的惊悚效果由此形成。可以说,《隐形人》让人们注意到,当惊悚电影创作者需要在小成本的框架内闪转腾挪时,“感知受限”范式无疑是值得考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