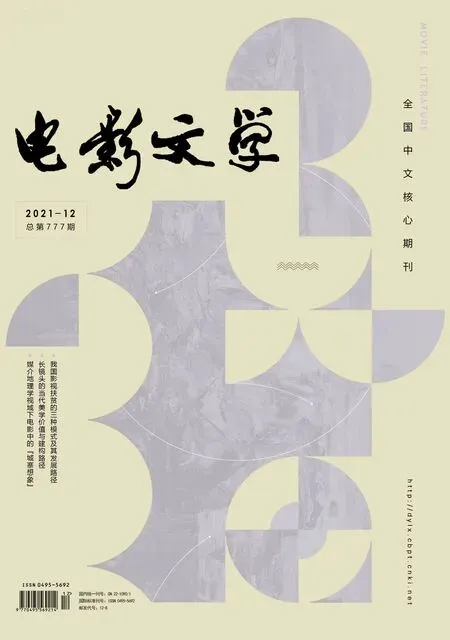传统与现代的撕裂与融合
2021-11-13朱天寒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蔡 颂 朱天寒(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在电影商业化的浪潮中,万玛才旦和他的藏族电影因题材和拍摄风格的迥异而显得独树一帜。电影《气球》作为其执导的最新剧情电影,延续了其作品脱离宏大叙事框架,着眼小人物命运变迁的叙事习惯。从一群藏族百姓的生活视角出发,用时代的目光对这片土地上发生着的一切进行审视,展现在大时代滚滚潮流下藏民的精神变迁。
一、父权制度的解体与女性意识的萌发
在电影《气球》中,导演以藏在白色气球(避孕套)后孩子的主观视角作为开场,以飘向蓝色天空的红色气球作为结尾。这两种颜色气球的首尾呼应,暗含了一种万物的轮回新生之意。结合电影主题而言,这象征着藏族传统父权制度的衰败与终结以及藏族女性个体意识的萌发与觉醒。
与以往万玛才旦导演的作品不同,《气球》中的女性视角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这种充分并不局限于对电影中女性行为动作与自身话语表达的关注上,更重要的是将女性放置在了电影段落叙事的核心位置上。在电影后半段的叙事里,矛盾与冲突的焦点集中于卓玛对于自身生育与否的选择上,而这种选择直接主宰了剧中所有他者自身情感的起伏与行为动作。
在电影中,达杰与上师那段关于爷爷转世的话给卓嘎的生孕赋予了极强的神圣性,但两者都未给予生育的“主体”——藏族女性基本的理解与尊重。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生育的女性并非一个拥有着独立意识与身体掌控的“个体”,其存在的意义更多是一种生育的“载体”,母亲与即将生育出的孩子之间也并非纯粹原始的骨肉关系,它代表着的是灵魂的轮回与新生。这种”载体”的身份以及母子之间的复杂联系使得卓嘎自身彻底沦为了父权制度下的生育工具。她本能地抵触与反抗这种不公与侮辱,但换来的却是父权制度下达杰冰冷的一巴掌。也许卓嘎并不能明确自身在这种制度下被赋予的价值符号,但这并不影响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对于自身身份与处境的感知,也正是这份感知让她最终选择了脱离自己家庭的枷锁,去追寻内心的安宁。在电影里,为了进一步表现藏族传统父权制度对于女性的生育压迫,导演选择了将达杰家的羊群作为电影中人物暗示的意象。作为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达杰必须确保羊群的繁衍与壮大。他向自己的朋友借来了一只“种羊”,尖锐修长的犄角、茂盛的胡须以及两颗硕大臃肿的睾丸都体现出了它“能力”的强大。当达杰骑乘着这只威武雄壮的“公羊”跳跃进母羊的圈栏之时,“种羊”与达杰之间便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内在关联,他们都是这片天空下的“强者”,他们倚仗着强大的“能力”统领着自己的“羊群”。与之相对的是圈内四处奔散,低声呜咽的母羊,面对雄性贪婪的审视,只能在圈内躲藏却无力逃出这片被禁锢的天地。同时在这片母羊群里,不能生育的母羊将彻底丧失自己生存的价值,迎来的只有被屠宰的命运。这种羊与人之间命运的隐喻,暗示了父权制度下女性个体的生存困境,即对于自身生孕能力的不可掌控以及放弃乃至丧失生孕能力后可能迎来的斥责与惩罚。
在古老父权制度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卓嘎的大儿子江洋以及两个小儿子都成为其无意识的帮凶。纵然江洋已经接受了现代化的教育,但他依旧被传统的父权制度所挟持而无法对女性的自由、平等的权利做出理解与尊重。而正是这种尊重的缺乏给卓嘎带来了沉重的压迫感与背离感,促使她自身女性意识得到了真正的觉醒。在电影中真正对女性抱有同情与怜悯的男性只有江洋的老师德本加,他送给香曲卓玛的书名为《气球》,这与电影片名相呼应,也暗示了其作为导演个人意识在电影中映射的身份。他与香曲卓玛感情的破裂,使得香曲卓玛选择出家为尼。他对于香曲卓玛这种看似放下实则难以割舍的选择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才会将自己的作品《气球》送给她。正如电影的主题一样,他寄希望于香曲卓玛能够理解自身被束缚处境,只有真正放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解脱与自由。但遗憾的是,他的书被卓嘎烧毁,他去寻找香曲卓玛而又被卓嘎劝退。所以当卓嘎自身女性意识觉醒,决定暂别自己的家庭时,选择了一条与自己妹妹香曲卓玛相同的路——归宿宗教的信仰。这何尝不又是一种轮回?妹妹的悲剧在姐姐的身上重现,每个人看似放下却又都从未放下。真正的女性个体意识觉醒,脱离父权制度束缚的道路就如藏地这些崎岖的小道般,漫长而遥远。
二、古老风俗的没落与科学文明的兴起
万玛才旦作为一名在藏地土生土长的藏族人,佛教给他带来的烙印早已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骨子里。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浓厚的藏传佛教元素,以及诸多关于佛教文化的反思与辨析。宗教对于万玛才旦而言是他观察藏区这片土地上人们生存发展的一个窗口,在这个窗口里,万玛才旦见证着千年来藏族人生活与精神的传承与变迁。
在电影《气球》中,佛教文化对于普通藏民生活影响的痕迹随处可见,如:身穿红色僧服的尼姑香曲卓玛、僧人们对于逝者的祭奠、上师的对于灵魂的预言等宗教元素贯穿在达杰一家的日常生活之中,展现了其神秘、圣洁的特征。在这些元素之中,“轮回”作为藏族的一种古老文化,代表了肉体的消逝与灵魂的重生,象征着万物的初生,也象征着万物的终结。电影中江洋作为奶奶的转世一直在父亲与爷爷心中有着一种特殊的地位和情感倾注,而代表着“转世”身份的印记——背后的黑痣更先天带有神圣、福气的意蕴。但当这种“神圣”的印记在导演勾勒出的幻境中被两个幼小的孩子如同一枚贴纸般轻松取下,这种“神圣”便被彻底地破坏与解构,这给予了电影浓厚的反叛色彩,暗示了人们对于自身传统“信仰”的背离,也为卓嘎未来对于自身命运的选择做好了铺垫。虽然这种幻境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全新的世界,但在真正的现实生活里,宗教对人的影响确如附骨之疽般难以摆脱。由于上师对于达杰与卓嘎孩子的预言,使得这个家庭在孩子诞生与否的选择上产生激烈的冲突。受爷爷佛教“转世”理念熏陶的达杰父子三人坚定地希望孩子的诞生,遁入空门的妹妹香曲卓玛也认为这是前世积缘才有的“福报”,卓嘎就如同医院窗外那只被束缚住的母羊一般被宗教信仰这根绳子死死地拴在了这片土地上而无力反抗。同样被束缚着的还有作为丈夫的达杰。贫瘠的生活让他的理智无力再去接受一个新生孩子的负担。但在宗教信仰这个庞然大物的裹挟下,他沉默着放弃了思考与抵抗,让自己的妻子在家庭中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在这片被宗教信仰笼罩着的土地上,仍有一束光芒照耀到了卓嘎,那就是周措医生。这是一位接受过现代教育,有着崭新思想的独立女性。她从不避讳性、生孕这些传统禁忌的话题,但对于卓嘎心中的“羞涩”又保持着一份尊重。也是她告诉卓嘎,女性不是为了生孩子才来世上的。这份真正的尊重与理解给予了困境中的卓嘎以巨大的力量,这股力量让她足以突破宗教信仰的困缚与家人的逼迫,遵循着自己的内心做出选择。
在《气球》中,白色气球(避孕套)这一重要的意象就是科学与文明的象征。正是它的出现让这片土地上的藏族女性脱离了“生孕机器”的宿命,它让女性第一次拥有了选择是否生孕的权利。但这股力量不够强大,还不能完全改变藏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但至少我们在卓玛身上已经看到了那弥漫在黑暗森林之中的“星星之火”,这颗代表着科学、文明的火种正在积蓄力量缓缓地燃烧,那形成燎原之势席卷天地的一日终将降临这片古老的土地。
三、过去未来的撕裂与传统现代的融合
撕裂与融合一直是导演万玛才旦电影中不变的主题,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善良却又虔诚的藏民,如电影《静静的嘛呢石》中的索巴大叔作为村中唯一可以雕刻嘛呢石的工匠,却固执地选择在清贫的坚守中逝去,只为到达那一片心中的净土;电影《老狗》中的老人面对狗贩子的纠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藏獒,用死亡去维护“神犬”的尊严。面对着滚滚而来的时代潮流,他们选择了逆流而上,坚守在传统文明的礁石上,顽固而坚韧地捍卫自己的信仰。
在电影《气球》里,达杰的父亲作为传统文明的捍卫者,他顽固且保守。当他面对电视中关于试管婴儿的讲述时,感到惶恐而又绝望,这种对于传统生育理念的冲击,使他固化的思想世界感受到了世界末日般的恐惧。在达杰父亲的话语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万玛才旦电影中老一辈藏族人民身上过去与未来的撕裂感,他们的肉体生活在现代的文明下,但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却仍活在那个逝去的时光中。他们恐惧而迷茫,他们拒绝接受新事物的产生与发展,时刻幻想着回归到被宗教信仰裹挟的时代里。这种撕裂感同样也表现在了《气球》里达杰和三个孩子的身上,他们不像爷爷那样固化而古板,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传统社会伦理的冲击,能够保持着一种客观而冷静的态度。但这种客观与冷静却又在面对卓嘎选择放弃肚中的孩子时消失殆尽,这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思想层面的冲突斗争来源于自己的真实生活,远比电视中看到的有更强的冲击力与复杂性。另一方面,传统宗教信仰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思考惯性,使得他们无法真正遵循科学带给他们的理智感。他们虽不像达杰的父亲般处于过去与未来、肉体与精神完全的撕裂之中,但他们的思想也未真正像电影中的周措大夫一样皈依于科学与文明,这种思想上的杂糅使他们常常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并在这种困境中无法自拔。
现代文明的吸纳与传统文明的继承之间往往会被人们认为存在着无可融合的鸿沟,新思想的诞生仿佛必然代表着旧思想的湮灭。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种言论有其正确的一面,文明与文明的斗争一向冷酷且残忍,正如万玛才旦在访谈中所提及的“一种文字或文化的消失其实是很快的。虽然信仰力量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但面对着多元文化的挑战与夹击,它有时也显得极为脆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人类历史上,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斗争,更多的是以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融合所结束的。正如电影中江洋一样,作为新一代藏民的缩影,他同时接受着传统宗教信仰的洗礼与现代教育的培养,这两者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种奇妙的融合。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对于藏族文明未来的一种希望与期盼,在传统与现代交融中长大的他一定会有着比父辈更加科学文明的思想与理念。到那时,他也就会真正读懂德本加老师送出的那本《气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