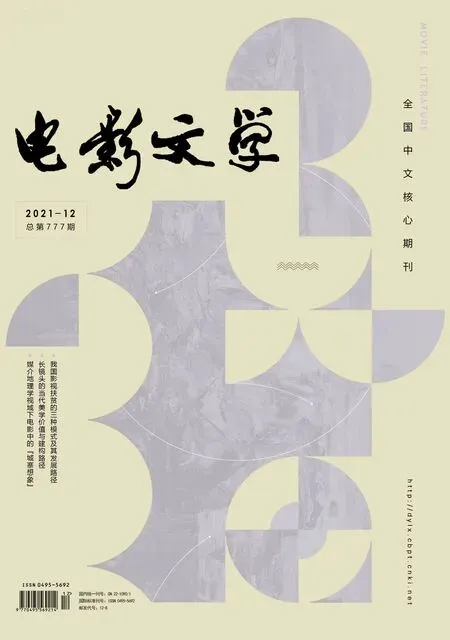赵德胤电影中离乡文化景观研究
2021-11-13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文学院福建漳州363000
鲁 政(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赵德胤导演早期电影以归乡三部曲《归来的人》《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冰毒》而出名。而后拍摄的《再见瓦城》获得第73届威尼斯影展欧洲电影联盟大奖最佳影片、第58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继而跃升成台湾知名年轻导演。赵德胤导演的电影画面朴素,情感真挚。他用长镜头将新一代华人的离乡经历以接近纪录片的方式呈现出来,体现了赵德胤导演在电影自我表达上的无遮蔽性。电影以边缘底层华人为描述对象,把跨国谋生作为叙事重点,悲剧命运作为故事终点。拼命挣扎的历程和空欢喜式结局,既写照了缅甸一代年轻人的现实困境,又勾勒出离乡人对理想追求的虚幻性。
赵德胤出生于缅甸腊戌。早年赵德胤的曾祖父因抗日从南京来到云南,后国内战乱,家族中祖父一支从云南边境迁往缅甸。此后,他们一家生活在腊戌。腊戌是缅甸北部华人居住较集中的地方,经济相对落后。毒品制售和越境谋生是当地许多人摆脱现状的主要方式,其影响了腊戌几代人生存状态。赵德胤一家中,哥哥姐姐们以及自己先后离开缅甸。大姐偷渡到泰国,之后二哥也到了泰国,赵德胤则通过考试的方式来到台湾。兄弟姐妹及亲友的离乡境遇汇聚而成的离散经验,为赵德胤离乡题材电影提供了叙事上的共情。电影主人公以缅甸腊戌为出发原点的离乡人,他们或者离开家乡,或者即将离开,以及离乡后归来。赵德胤通过探索离乡的艰辛与挣扎、失望与痛苦、徘徊与努力,用具有象征性的符号,勾勒出一幅海外边缘华人离散的社会景观。
一、家园告别下离乡影音
赵德胤的电影中,交通工具反复出现,成为影像中主要离乡表意符号,它连接家乡与他乡的地理空间。飞机、长途客车以及摩托车等系列交通运输工具,是主人公离开家乡的载体,也是导演赵德胤返回家乡的记忆。电影中交通工具的着重刻画构成赵德胤离乡题材影片的共同特色。橡皮船、小卡车、三轮车、摩托车等较为落后的交通工具,承载起电影的离乡情结,既突出缅甸不发达的落后经济,也反映出年轻的一代人离开家乡体受的艰难。尽管艰难,他们不放弃改变生活状态的执念,以及憧憬美好生活的愿望。导演不遗余力地聚焦交通工具同命运进行斗争,用以换取更好的生存空间,用长镜头叙事手法演示跨境者们的别离困境。
电影《冰毒》里,被拐卖到中国的女主人公三妹因奔丧回到家乡缅甸。在中国生活不如意的她想在家乡做点赚钱的生意,最终走上了贩毒道路。男主人公阿洪的父亲为了让儿子生活下去,不惜卖掉家里的耕牛,为他换来一辆摩托车。父亲希望阿洪能够通过载客换来收入,以此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可是儿子阿洪却为利所诱,在偶遇的客人三妹劝说下,与三妹一起做起了运毒生意,幻想用快速的方法实现致富路。两个人最终在一次贩毒中被警察控制。看到三妹被包围后,男主人公阿洪仓皇而逃。影像中赵德胤用三段长镜头诠释阿洪一路逃跑的状态。长时间的镜头跟拍所呈现的恐慌与无措,与其说是逃跑的心态展示,不如说代表了从中国跨境返回缅甸的三妹——作为社会底层人物代表,因为生活所迫,在毫无安全感的生存状态下共同表现出的无助感。三妹被围捕时她双脚撑在墙上,竭尽全力地想挣脱警察,可是无论如何她还是没有摆脱代表权力的大手。交通工具摩托车本来承载着主人公共同谋划致富的梦想,结果成了毁掉他们各自生活的噩梦。在《穷人》里,人贩子三妹一伙人靠边境贩卖人口为生,凭借摩托车这类灵活的交通工具在边境运送“猎物”。在一次运送缅甸女孩儿回中转站的途中,女孩儿借上厕所时逃走。人贩子三妹等人发现并追回后,导演将镜头对准摩托车进行了长达80余秒的无间断跟踪拍摄,将交通工具与人的命运绑在一起。三个人一起坐在一辆摩托车上在荒野中奔驰,随着边境的路线的颠簸而不断地起伏。女孩儿最终没有逃离掉被贩卖的命运。而2016年上映的电影《再见瓦城》,主人公莲青从缅甸边境偷渡到泰国,乘坐手划橡皮艇到河对岸。导演再次将长镜头对准皮划艇,超过120秒的超长时间聚焦在看似平淡无奇的离乡路,蕴含着从一个国家偷渡到另外一个国家,偷渡人所经受的险阻与煎熬。
交通工具在赵德胤电影里不仅将主人公生活艰难的画面尽情呈现,也体现出交通工具作为跨境实现梦想的现实凭借,寄托着众多像电影主人公一样的人在各种法律边缘的辗转挣扎。在一贫如洗的生存环境里,他们渴望改变,幻想通过某种方式改善自己。这种挣扎的理想凸显了现时代缅甸年轻人争取美好生活的可贵性。虽然他们对彼岸的幻想是乌托邦式的寄托,但简单而又有效的交通工具是他们实现流动、打开理想边界的钥匙,成为他们在缅甸与中国、缅甸与泰国边境之间跨境的最便捷的一种方式。就电影表现手法而言,交通工具是众多符号里抽离出来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代表,它负载着离乡人地理空间的串联,构架起离散社群转换现实贫穷与虚幻美好之间的桥梁,成为寻求踏入另一个不同生活空间的重要渠道。
二、跨境谋生中的身份想象
2011年赵德胤获得台湾身份,实现其海外身份的再造。此后他的电影也以台湾电影的名义走上国际舞台。获得身份认同是许多跨境离乡社群的追求。然而,尽管导演获得了台湾新的身份,但他的电影并没有给任何主人公以完满的身份作为结局。对离乡社群来说,身份认证是很多离开缅甸去往境外人奋斗的目标。赵德胤把这种奋斗塑造成了乌托邦般的想象。电影里,身份再造与其说是跨境社群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如说是以期待为名义,透过影视媒介再造了一个悲剧现场,主人公在现场体验了对寻找新自我所付出的代价。
黄钟军、费园发表的一篇《消费视域下的多重身份焦虑——论〈再见瓦城〉的身份求证与告别》文章中,将《再见瓦城》里女主人公莲青在泰国获得的身份认证表述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工作身份、识别身份与证明身份,即工作编号代码、出生地身份证明和泰国正式身份。这样分类与女主人公偷渡到泰国的生活经历相衔接。莲青到达泰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没有名字只有工人编号的工作,编号上的数字代表着她的存在,这给她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随后她用尽一切办法高价购买身份证明,以及最后她用身体作为交换,获得一个叫“美依高悠”的泰国合法身份。这是赵德胤为主人公身份再造最接近圆满的一次。她在泰国经历了工作的挣扎、金钱的欺骗以及身体上的付出,换来身份再造上的成功。可是导演并没有以此作为主人公命运结局。相反,莲青的正式身份没有改变她在泰国的命运。当她还沉浸在幻想美好未来生活时,一个睡梦未醒的清晨,男友悄悄潜入房间将其杀死。身份证明演化成一张盖着尸体的遮脸布,将她盖在了异国他乡。《穷人》中,女主人公三妹为了获得台湾身份证,情愿受制于人贩集团。她为集团工作很多年,迟迟不见集团为其兑现办理台湾身份的承诺。打电话给大哥电话打不通,打给同行阿丰想了解一下情况也毫无收获。她一边为大哥做人口贩卖的生意一边等待身份证确认的消息。三年过去,毫无结果。剧情结尾处,三妹在众人面前最终控制不住落下眼泪,不得不面对身份想象换来的空结局。
获得身份认同是跨境社群的集体期待,也是他们的共同焦虑。赵德胤塑造的焦虑不仅反映在现时代年轻人身上,在迁居缅甸更早的一代华人中,也同样存在着身份焦虑问题。在赵德胤出生地腊戌,缅甸政府军于1982年颁布相关法律就言明:“唯有在1823年之前定居于此的民族才能享有完整的公民权。”也就是说,从中国云南迁居到腊戌的祖辈一代就没有获得过正式的缅甸身份,也没有得到缅甸社会各方面的认可。身份焦虑一直伴随他们并且延续下来,一直到现在的年轻一代人身上。赵德胤16岁去台湾读书时,为了获得去台湾的护照,全家人花了一年时间筹钱和奔走,仅在当局获得一年有效期签证。等他再次与缅甸家人团聚已经相隔十年。从祖辈的身份认证遗落到新时代年轻人自我身份的探寻,长期缺少社会承认带来的安全感缺失,让赵德胤在他电影里将身份证明的获取,演变成表达海外离散社群奋斗争取的标志性事件。身份证明已然内化成他们追求“成为自己”的一个重要认同符号。
此外,赵德胤还试图探索海外离乡社群再次返乡时,家乡对他们身份的再次理解。在《归来的人》里,归来人的海外身份在家乡变成他们的光环。主人公兴洪从台湾打工回到家乡。尽管在台湾他只是一个底层务工人员。可是回到家乡,由于自己归国人士的身份,他摇身一变成为家乡“知名人士”。从这个细微的变化可见,对于长期缺少社会存在感以及得不到社会认同的社群来说,身份获取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位“成功人士”回到家乡后的待遇直接刺激了更多年轻人产生获得国外身份的想象。在《归来的人》里,一群年轻人没有出国就开始幻想自己有钱的样子,他们在聚会中甚至瞧不起美国,想着去欧洲,去法国,一头扎进他们幻想的世界。学者李有成认为对离散社群而言,即使是个人的想象往往也隐含着集体的意志与意义。然而幻想毕竟不能成为现实。当离乡的一批人返回家乡之后,以兴洪为代表的年轻人,仍然还在为谋生发愁。海外身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最后仅成为一个饱含离乡心酸的假想物,变成只有象征意义的一个空头符号。《穷人》里三妹最终没有获得台湾身份;《再见瓦城》里莲青最后搭上了自己的生命;而《归来的人》中,兴洪镀了一层海外回国的身份,最后也只是在家乡做了一个工人。身份认同带来的焦虑没有因为跨国离乡而化解,反而成为离散社群更为恒久的认同想象。
三、国别叙事与语言裹挟
赵德胤离乡题材电影着重边境叙事。电影镜头与边境环境保持密切关系。由边境叙事演化的国别叙事是电影另一个符号设置。电影涉及跨国(地区)大环境,如《归乡的人》,寄托的背景为台湾;《再见瓦城》故事发生于泰国。涉及边境叙事场所,如《冰毒》地点发生在中缅边境,《穷人》发生在泰缅边境。边境作为具有争议的模糊地带,即是偷渡的人跨越边境生成幻想的空间,也是离乡人寻求身份认同的一个隐喻。在空间有限的边境空白地带中,饱含偷渡的人对解救自我的期待与重新塑造自我的愿望。主人公莲青通过皮划艇划到河对岸被摩托车带走;三妹宁愿怀揣冰毒铤而走险也不愿意与丈夫孩子在家生活;人贩带着要过境的人在边境线辗转倒手。这些跨境谋生背景下的叙事隐含主人公们在解救自我中冒险与挣扎,他们期待通过寻找边境之外的一种空间,创造一个离乡之后的新自我。
赵德胤电影叙事里的国别转换,包含以国界为界限的“一侧是离开”与“另一侧是来到”的复杂感情。这种感情充满对原始家国观念的冲击。跨境界限一侧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旧家退守到记忆,另一侧则是以社会关系为纽带的新“家”渐渐走进现实。寻找境外身份认同的群体,由于长时间的海外漂泊,传统上家的观念在长久海外生活中产生认知上的转变——从作为族群生活的共同体逐渐变成只存在于脑海里的共同体,最后家的实体化成仅剩一个伴有思念的想象空间,失去固有的实体具象。故土久别让原始家的实体感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模糊的家的文化符号意象。跨境群体的离散最终连自己的家都成为想象的存在,家只能生活在群体记忆和想象中,这是导演赵德胤表达出离乡社群的生存遗憾。正如他获得台湾身份后面对镜头时说,在缅甸,我是异乡人;在台湾,我也是异乡人。身份认同的去疆域化正逐渐成为全球离散文化探讨的新领域。
语言是作为跨境社群的另一个离散符号。语言作为文化资源,其集中表现在语言群体的认同功能方面。在近代史里,中缅边境一直是人员互动较多的区域。赵德胤描述缅甸人,聚焦的重点是背井离乡的华人,他们是从祖国迁居至缅甸的移民。长达近百年的文化异质化与地方化的影响,这些移居的华人已经具备了融合当地生活的许多特性。他们保留着的具有汉语特性的语言表达系统,是证明具有迁居史的证据。尽管许多人目前已经持用中音缅甸语,语言表达系统已经融合当地部分语言。但是电影里存留下来的具有汉语主体性的语言特色,给了电影表达离乡主题以活力,缅甸华语的使用成为电影主人公在生疏世界里唯一与家乡相关联的符号。
缅甸华语作为赵德胤电影中主要语言符号,它界定了电影主角民族文化的亲缘关系,也体现了作为一支海外华人离散社群的文化特征。华语在彼此交融的边界范围具有意义上的创造性。与传统由血缘连接而成的亲缘关系不同,缅甸华语是由迁徙与群居形成的具有地理空间聚集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除了本有华语语言作为基础成分之外,新实体已经内含不同区域文化的异质融合。海外离散华人的话语体现了离乡带来的多元文化特征,它见证了海外华人离散的历史。
缅甸华人长期生活于缅甸社会边缘,无论地理位置边缘还是政治边缘,边缘性的特征给他们带来不利的发展环境。加上区域经济处境较差,他们成为一个为谋生而付出巨大努力的群体。迁徙因此才成为他们求生的手段。他们的身份既是华人也是缅甸人,同时又是为了生活需要不断跨地域行走的离乡人。祖辈离开中国与数十年后后辈离开缅甸构成了缅甸华人的双重离乡,他们的身上承载着沉重的迁移包袱。新时代离乡的年轻人,他们既没有完全忘却汉语、也没有全面接受缅语。语言是他们成为异乡人的记印,也是他们离乡的证明。电影采用缅甸华语作为电影主体语言,是在向外界展示身处缅甸社会边缘的一代海外人,他们求生过程中带着浓厚的离乡情感。在表层多元文化融合之下,肌质里流露着的是因他们移居而被迫成为他乡文化接收者。他们是社会迁移史中的背负者,又是迫于不同语言环境而无法正常使用母语的受害人。语言的历史文化动能,丰富了赵德胤导演的电影表达。在赵德胤的离乡文化叙事中,华语尽管已经是被裹挟的语言,无法在主人公生活的主流社会广泛使用,但是它充满能量地参与了离散文化书写。几代人连环的迁移与国别跨动中,华语作为被继承的境外华人社群文化根性,串联着海外华人背井离乡的离散景观。
四、共情语境里的离散景观
赵德胤在一次采访中曾说:“其实一个人,如果离开你的家乡,或离开你过去比较亲密的东西,你可能就一辈子,再也回不到原点了。”出生于普通家庭的赵德胤,父亲是个没有执照的中医,母亲靠在家卖小吃补贴家用。为生活母亲曾不惜贩运毒品以换取粮食。被抓到后,为了救母亲,大哥被迫离家去玉石场打工,此后多年再没有消息;家境愈发困难之际,大姐也无奈地走上偷渡之路。赵德胤的电影与他的家庭经历在感情上保持着朴质的一致性。除了2019年新作《灼人的秘密》之外,其他长片剧情主人公几乎都与身边的人事相关。电影以缅甸为散射点,地理空间发散到境外多个地区。赵德胤是台湾电影导演中为数不多的以乡亲离散为叙事背景的华裔导演。
2011年到2016年,经过六年的电影制作与演绎,赵德胤的电影逐渐形成一种表现社会离散者生存状态的文化景观。电影景观是电影实践中的一种镜语范式。离散景观则是在镜语范式中延伸开来的社会景观。赵德胤的电影表达了对社会离散社群生存状态的关注。他构建的社会景观塑造了许多用于表达离乡情节的符号,这些符号从有形到无形,他用简单的写实主义手法凝聚自己的情感,还原真实的欲望。赵德胤曾说,《再见瓦城》的前半部分是他大姐早期偷渡到泰国的故事;《冰毒》讲述的是他出生地发生的故事;而《穷人》里众多情节都是提取生活里的片段加以转化。赵德胤这种介于真实与非真实的电影,提升了观众对电影感受的真实性,也让电影在现实环境里游走变得更加细腻。在缅甸尚不允许拍摄相关题材的环境下,赵德胤从一部朋友的DV开始,完成他的第一部长片《归来的人》拍摄。赵德胤在一次接受何俊穆题为《在拍片之中我们发现了一种自由》采访时说:“《归来的人》是普世性的、流浪的、移动的。”他说他的电影一直在探讨空间的距离感、人移动的距离感,以及在这个距离感下发生的事情。这种强调以距离感方式带来的社会景观,恰好解释了他所描绘自己以及社会离散社群的宿命——对底层离散社群生存命题的探讨。《冰毒》柏林首映时他接受采访说,通常一个政权或大时代的改变,会有很多人的生活在过渡期里比改变前还辛苦。赵德胤很好地理解了这种因为环境改变所带来的社会冲突。他塑造的以缅甸为背景的离散社群是社会转型中的产物。这也是前辈侯孝贤与李安导演教导他拍摄“要有生活感情”的一种尝试。他真实的生活情感与他朴实的拍摄风格不谋而合,转化成他拍摄多部离乡电影的情感基石。
赵德胤将人生经历共置在他离乡题材电影之中,他运用简约的影像绘制出底层海外华人离散生活的景观——一个分散在世界各地同时又相互关联的社会景观。赵德胤电影里的景观,反映了以缅甸为地理背景的海外华人形成的一种群体离散现象,并由此连接而成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虽然与原乡已经产生了裂痕,但正是这种断裂感勾勒了赵德胤电影社会景观的独特模样。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指出,“在真实的世界变成纯粹的影像之时,纯粹影像就变成真实的存在。这是赵德胤导演的电影价值所在。
结 语
赵德胤导演是台湾电影界后起之秀,其电影在近十年大放异彩,频频亮相国际视野。他的早期电影多以离乡谋生为主要题材,蕴含着赵德胤作为离乡的一代人在高速且多元的社会中对跨国流动群体生态的探索与关注。他将个人的离乡情感置于拍摄的电影之中,形成导演与作品的互文性。他成功地运用交通与边境相关联的符号意象,在介于真实与虚幻间构建了一幅以缅甸为背景的离散景观。作为缅甸华裔导演,他以独特的视角获得台湾电影界的认可,也为台湾电影的发展做出了一份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