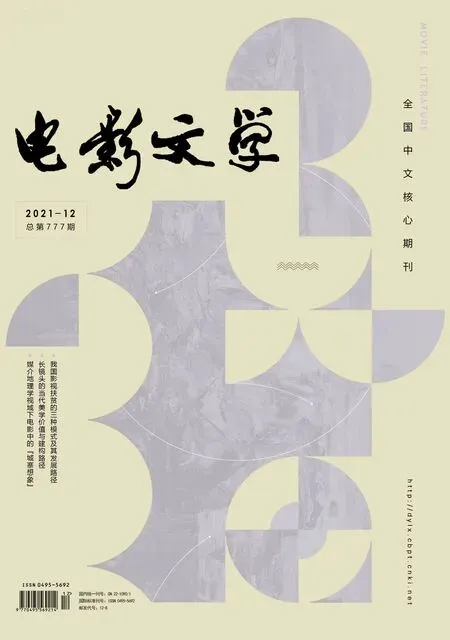反叛的与反叛失败的:论路阳电影中世界观的构建与表意
2021-11-13郭建鹏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郭建鹏(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路阳凭借着2010年上映的《盲人电影院》一举夺得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最受观众欢迎大奖,2011年中国金鸡电影节最佳导演处女作奖两项大奖。路阳也自此走近中国观众的视野,2014年的《绣春刀》、2017年的《绣春刀2》以及2021年春节上映的《刺杀小说家》都展示了路阳在动作类商业片中相对独立的电影作者倾向。从风格上看,路阳所执导的影片以一以贯之的“反叛”意识和中国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的反叛呈现出显著的气质差异。中国第五代导演如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陈凯歌的《黄土地》,主角的反叛是建立在对命运不屈服的层面的,是不妥协的反叛,当个人意志在时代环境中无法得到尊重或实现时,主角们宁肯选择死,并借生命的消逝来作为个人意志的声明。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如王小帅《冬春的故事》、张元的《北京杂种》里,主角们的反叛则成了一种“无因的反叛”,他们对生活感到不满,对突如其来的自由感到迷惘,于是他们的反叛便更像是一种自我的声明,通过反叛(破坏)的行为,证明自我意志的存在。
路阳电影中的反叛则是夹在前两者之间的反叛。主角们或多或少都遭遇了环境的压制,对自己的工作、社会地位、命运感到不满,但是他们常常又是忍耐的、充满着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活哲学。路阳电影中的主角们对潜意识中的欲望更多是趋向于一种“既不放弃,也不寻找”的自然主义观念。在这层预设的背景下,陈语、沈炼、路空文等时代各异的角色就呈现出统一的当代气质,他们的反叛呈现出一种灰色调的失意,反叛的收获更多是顾影自怜式的自我实现。
一、反叛的因由:个体对环境的不接纳与不信任
在常见的国产电影中,反叛的行为经常是外部压力造成的结果。如《狗十三》中,少女丢失了宠物小狗,随后才引发了一系列与父亲和家庭冲突;如《过春天》中,主角想要逃避日渐窒息的周身环境,因此选择了早恋、走私手机作为其反叛的路径。但是在路阳的电影里,往往很难看到单纯由外界环境或是外界压力引发的反叛。不论是陈语、沈炼,还是路空文,他们身上往往有着一以贯之的反叛气质,尽管他们中甚至有现状环境的维护者,但是他们对世界的不信任、对周遭事物的失望以及迫于某种无奈不得不做出的妥协,显得他们与其他人格格不入。
这也是路阳电影始终不脱少年气的原因所在。电影中往往很少出现“成长型”的角色,角色从传统故事片中的成长路径逃逸了,从而转换成了一种先验性的抉择。如《绣春刀2》中的沈炼一出场就已经是一个老练的军人,一个深谙北镇抚司安身立命之道的锦衣卫。但是事实上,经验的成熟性并没有带来精神上的安宁,角色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接受着身份环境与精神倾向的碾压与拉扯。沈炼在影片开场时的精神形象,恰如汉斯-格奥尔格·梅勒尝试在《游心之路》中,对中国老庄中混沌初辟状态所做出的描述:“一切都是既是非是,既可非可的‘真实假装’。”沈炼浑浑噩噩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下显然暗示了后续他变化的可能,也同样标志着影片起初,他精神状况更像是处在混沌初开,尚未长成的“童蒙”阶段。
这种精神上的混沌和“既是非是,既可非可”在《刺杀小说家》中,被进一步提纯和放大,成了一种接近与影片内核的象征和解释。路空文在影片的现实世界里,是写作八年却一事无成的小说家,他对周遭一切现实事物都不再关心,甚至对远道而来准备杀害他的关宁也处于“知与未知”的混沌状态,他对于现实的关注点全部浓缩进了小说里,从而召唤了一个更加接近理想精神的幻想世界。
在路空文、沈炼等角色身上,主角充满着对环境的不认同而产生的巨大的危机感和不确信感。在这种精神危机的状态下,用以自卫或杀人的武器则成了最好的表现符号。沈炼与丁白缨比试后,原本其使用的绣春刀折断,沈炼取出曾经是锦衣卫的父亲留下的绣春刀迎战;路空文在小说世界中,同样延续了沈炼的情节——少年空文失去了姐姐留下的刀和旅途上与其共生的“铠甲”所使用的刀,转而通过拔下了父亲过去刺进赤发鬼眉心的刀,从而实现了除魔的任务。刀作为符号的譬喻,暗示着角色的精神意志。沈炼最终决定使用父亲的刀,暗喻了沈炼对丁白缨、陆文昭等人态度的转换(从明哲保身到愿意为其偷盗东厂篡位的证据),承担起作为社会个体,为其他生灵谋求公平和正义的责任;少年空文最终拔下了父亲的刀,同样也暗示着其内心正视了父亲遇害的真相,不再将小说视其唯一的宣泄口,他可以与李沐面对面,揭露现实中赤发鬼的恶行。
二、反叛的路径:对结构和规则的否定与破坏
《绣春刀》和《刺杀小说家》在上映后都曾被观众诟病其情节的断裂和生硬,因此在分析其影片反叛路径之前,首先应该论析影片的情节是否与表达目的的需求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绣春刀1》中,沈炼的反叛的表因是为了周妙彤——他始终心怀愧疚的情人。《绣春刀2》依旧延续了这层表因——他要拯救他欣赏并逐渐产生情愫的画家北斋。和其他类型片一样,美好的女性角色常常暗示着主角人性的复苏,女性承载者主人公对寻常普通生活的希望。然而实际却并非如此,这一特点在《刺杀小说家》中更为显见,幻想世界中的少年空文为了给姐姐报仇,才决定刺杀赤发鬼。姐姐的死亡看上去成了一切决策的基本点,但是反观影片的类型结构来看,姐姐的死亡只是少年空文做出决定的最后一个因素,姐姐代表着的是他对尘世的一切寄托,电影中路空文旁白道:“因为他(空文)知道,如果不为姐姐报仇,活着便没什么意思。”失去姐姐,也就代表着与现实的连接脱节,人将在精神世界彻底迷失,丧失了生存的意义和可能。
在解答了这一前提之后,再重新回到叙事的原点,就可以看到,角色们的反叛首先来自世界的辜负。沈炼勤勤恳恳、明哲保身之后,其生存空间仍然被不断出现的侵入的外部环境干扰,他因为命令参与抓捕东林党官员的行动,最后导致了周妙彤被发配为官妓;少年空文不想杀任何人,结果却一直被赤发鬼派来的亲兵不断追杀,直到唯一的亲人死亡。由此可见,他们的反叛往往是在丧失了希望和生存空间之后,不得不以生命做出的声明,因此他们的反叛,在起初便显得动摇而脆弱。沈炼迟迟无法决定要不要为结拜的大哥和三弟摆脱麻烦;少年空文在白翰坊与红衣武士的一战孱弱得几近可笑,逃到无处可逃,才与之一战。这仍然证明了他们作为“顺民”的身份与对环境结构的内在认同。
然而,反叛也就在这一刻发生了。作为“顺民”他们的破坏也更隐蔽、更持久。《绣春刀》中,沈炼作为维护明朝统治锦衣卫组织的一分子,直接参与了对系统的内生性机制的破坏,揭破了时代的荒谬。《刺杀小说家》中,路空文借助着小说,将父亲被害的真相与李沐的邪恶藏在真真假假的玄谈之中。写小说看似是无意义的,但“只要相信,就能实现”。超能力在现实中边界的模糊也暗示着这种低调的反抗与不配合对系统的破坏,李沐在路空文写到赤发鬼受伤后,生命力的流失,如果说是超能力的显现,不如说是导演对世道人心的美好愿望。《刺杀小说家》的原作者双雪涛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他小说的主角,实际与他生活环境中的人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或多或少都能算得上是“顺民中的叛徒”。这样的批语实际上也可以用在路阳电影的主角身上,顺应和忍耐并没有使得世界变得更好,于是理想主义者们纷纷成为与世界背道而驰的“叛徒”,成为破坏系统的分子,然而作为一个物质主义甚嚣尘上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这些角色的命运实质上在故事起点就已经被说明和决定了。
三、反叛的实现与失败:理想主义者的无声言说
路阳电影中的人物始终秉持强烈的内倾性,敦促他们改变和反抗的压力来自内部。而他们反抗的手段,则颇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气息,偶尔甚至使得整部电影显示出黑色幽默的气质。沈炼懂得为了保一身官服而对一些事情装聋作哑,乃至于成为制度规则下的一把屠刀;陈语一边厌恶着光鲜亮丽但虚伪和无价值的高薪职业,一边却为了和女朋友继续保持关系,即便住进了老高逼仄的老胡同房子,也不肯放弃求职;路空文对俗世评价并不在意,却仍然对“啃老”的行为心中有愧,甚至觉得“这样死了也好”。
两部《绣春刀》的结局中无时不展示着一种惆怅的幻灭情绪,不论是弄权上位的信王随手划掉了沈炼死刑的名字,还是沈炼和丁修斩杀勾结女真人呼喊着“毕巴拉赵尽忠”的叛徒,都显得像是命运随意摆动的结果,人们在命运的枪口下侥幸逃生。在东方世界观的故事的主角像是一则缺了结尾的寓言,因为主角们自身不动声色的犬儒与观察,才使得他们对于周遭变化显得格外格格不入。《刺杀小说家》的幻想世界则佐证了这一观点,少年空文第一次走进皇都城后,身陷了一场巨大的狂欢。在少年空文提问前,观众和主角一样,潜意识将这种狂欢的非日常景象看成是节日,直到观众和少年空文一起看到了普通人冲杀抢夺的景象时,才为那层无意识的狂欢而感到恐惧。
《刺杀小说家》和《绣春刀》都缺乏一个绝对的英雄,主角们或隐微地认同大义,但缺乏将自己看成是正义使者去拯救他人于水火的自觉。因此角色的反抗是“了结私仇”与“主持正义”在暧昧地带的摇摆。这一类角色的奋起冒险,与生活在现实中的普通人相比,更具有了某种理想主义色彩,和主角的人格品质无限接近的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压抑欲望的实现。沈炼因为无法忍受制度对人性的残害,握起了刀,成了“反贼”;关宁则跳脱了李沐制造的陷阱,遵循了善良本性,发现了更大的秘密与黑幕。此时,观众在日常生活中所被压抑的情感也得以释放,从某种程度上,和银幕中的主角们一起获得了解放的喘息。这或许也解释了《刺杀小说家》和《绣春刀》系列上映后口碑两极分化的根源——电影强烈的理想主义气质隔绝了一部分真正理性为王的现实主义观众们,它无法向期待剧情自圆其说、精彩反转的观众们提供答案。事实上,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答案,体验和观看本身就是故事的核心。主角也不再是银幕上的那几位,随着情感的谐振,故事的参与者已经拓展到了观众自身。
《刺杀小说家》的宣传材料中,“只要相信,就会实现”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宣传语。这或许也是现阶段路阳电影最大的特点,作为理想主义气质浓郁的导演,其作品独立与叛逆气质,都将成为当代中国本土电影难以忽视的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