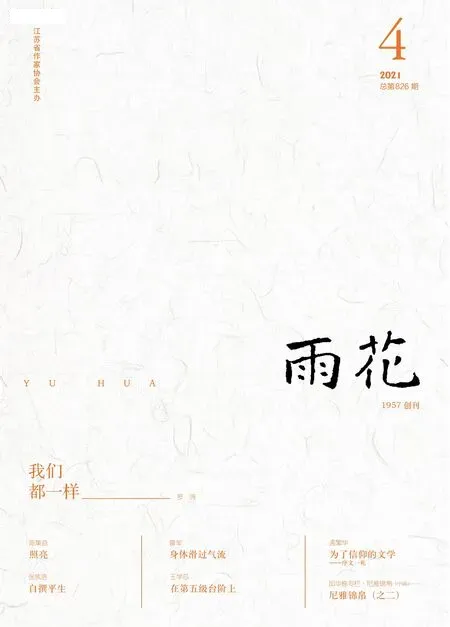草木有情
2021-11-13
桃花难画
有人说:“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
远方的木子妹妹发消息来,说是想看慈溪的桃花。我拒绝了她。不是拒绝她来,而是拒绝她的看桃花之邀。
慈溪最绚丽最有名的桃花,宣传最广的大抵要算古窑浦桃林的花了。早些年作协采风时,我去过一次。成片的桃林,规整,统一。高度、姿态、长势、朝向,看不出哪株是哪株,任意走到一棵桃树前,都是一样的模样。
花是鲜艳的红,春风里,映着蓝的天,但树下没有绿草如茵,只有整洁的泥地,偶尔泛起一抹绿,也似乎带着点负罪感。
也不静。攒动的人头,走过来,走过去。倒也有流水,浅浅的沟渠,落花无意,流水亦无心。
我说,不如去山里吧,春色也该满山头了。五磊寺的那条山道我惦记已久——我心心念念山道旁的木香子,该开满枝头了。
阳光很好,照在树上,那些嫩芽都闪着亮光。春天,本来就该是欣欣然的模样。一路的木香子,开着小黄花,也不拘谨,很放肆地长。它们把枝条伸到了路边,任谁都能攀折得到。还有白的蛇莓花,粉的映山红。辛夷到了山间,便不能叫辛夷了,该叫玉兰,高大硕壮,少了些许柔弱与诗意。它有点霸道,有点倔强,被其他的树围绕着,尽是山野味道。
于转角处,我看到了一树桃花。淡粉,并不明艳。初以为是樱花,长在低低的山腰处,居然有点出尘的况味。
难得见到这么静的桃树,一树的花,开得正是繁茂,居然没有喧嚣之感。这大概就是胡兰成见过的桃树,山野之间,遗世独立。满山的新绿,反而映衬得它愈发安静。仿佛,潺潺的流水,啾啾的鸟鸣,都与它无关。只有风过的时候,它会叹下三两片花瓣。落在溪水上,一只小虾依旧在水里,纹丝不动。
见过了规整的桃树,此处逢着它,居然有些小小的不适。它的肆意,它的浅淡,它的静谧,让人有恍惚之感,这究竟隔了多少时光?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桃花大抵都是它的模样。房前屋后,乡野田间,只一两株,少有成片栽种。它们的枝条,爱怎么长就怎么长,爱朝哪个方向就朝哪个方向。它们亦不似现在这般鲜艳,都是浅浅淡淡的粉。花开繁茂的时候,叶子也开始慢慢探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它们也静。桃李不言,说的就是它们。它们少有伙伴,开花,抽枝,结果,从不扎堆。
这份静是什么时候消失不见的,我已然不记得了。如同很多消失不见的人与物,似乎,就那么慢慢地前行着,走远了,从来不曾有过回望。似乎,这一切就该是如此的轮回,于这久长的时光里。一如童年的河流,芦苇地,以及一些旧友。
桃花难画,因要画它的静。这是胡兰成的话。他看到的是百年前的桃。而我,于今日之时站在桃树下,且迈不开脚步。我知道,心头这支笔,终究是画不出、写不出这样的桃,这样的静来。
无尽夏
绣球花开的季节,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外婆。外婆喜欢绣球花,她把绣球种满整个院子。谷雨后,绣球疯长,肆意开放。深邃的蔚蓝,粉粉的紫,簇拥着,赫然揭开夏的序曲。
外婆养的品种叫“无尽夏”。
夏天,我喜欢在外婆的小庭院里嗒嗒走着。外婆说,剪几枝绣球带回去吧!我总下不了手,它们开在那里,就像一种完整而固有的存在,就像云在天上,就像羊在草间。当然,最后的最后,我依旧会装出很稀罕的样子,剪几枝绣球带回家。
有一次,我剪了几枝,插在母亲陪嫁的青花瓷罐里,那绣球,美得把自己给吓了一跳。我拍了照片,带给外婆看。那是初夏的黄昏,绣球掩映的小院宁静安详,外婆把手机举得很远,她一直在笑,好像在看别人家的花……
这些情景,一晃已过去十年,而外婆离开也已经四年有余。最近两年,花友间突然流行起绣球花来,品种繁多,色彩缤纷,有的婉约,有的圣洁,有的清新,有的浓烈,姹紫嫣红。
时间也真是奇怪的存在,它总是猝不及防地激起血液里一丝一缕的传承。外婆离开后,我居然开始对花痴迷,于是我更加想念外婆,想念她的绣球。去年,我买了很多很多绣球装点阳台。你可以想象,小小的阳台挤满各色绣球的景象,花团锦簇,仿佛外婆的小院。
没想到,在外婆手中极其好养的绣球,到我这儿居然娇气起来,它们三三两两地生病,任我喷药施肥都无济于事,望着满阳台枯枝残叶,我知道,我把一个梦丢了。
外婆走后第二年,我去看过那片无尽夏。它们依旧枝叶繁茂,仿佛外婆依旧还在那里行走、忙碌。隔着一扇紧锁的铁门,我的泪怎么都止不住。
我很想我的外婆,想那一个个有她、有绣球的夏日。
文字,真的是一种神奇的介质。这些由点、横、勾、撇、捺组成的符号,怎么就能承载起每个人心头的喜怒哀乐,随着阅历和经验,生发出不同的情愫呢?
记得第一次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是在我的中学时代。老师在讲台上朗声诵读,居然有哽咽之声,我在底下捂着嘴使劲憋住笑,为文中父亲的臃肿和笨拙。“不过是几个橘子”,我在心里嘀咕。然,当我在而立之年经历丧父之痛后,再读《背影》,一字一句,生生敲到心底。一时怅然。
我们追着时光,用文字记录这世间的温暖与美好,记录一场场欢愉,一次次离别。此时,我正用它们来记录我的外婆,和外婆栽下的绣球花。
是的,外婆的绣球一直开在我的心里。每年春季的时候,它们和思念一起疯长。我心里想着,没了外婆的照料,它们可还会开花?
今年,我租了一个房子,有个很小的院子可以栽种花草。我想起外婆的绣球,想着掘一株拿回家种——那绣球上面,有着外婆的气息,有着外婆的身影。
舅舅不在家,推开门,满眼的绿。它们依旧开得葱郁而从容。旧年的花,谢了,舅舅并未剪下来,它们依旧长在枝头,枯了。我拿出剪子,一朵一朵地剪。若外婆在,那应该是她旧年花谢时就会干的活。
绣球又高出了不少,根系缠绕,终究无处下手。最后,我只拿了一枝错剪的枝条回家。那鲜嫩的枝条,我舍不得将它孤零零地扔在地上。
折返时,在门外河边遇到两位婆婆,她们欣喜地喊着母亲的名字,然后,她们看到了我。她们大概忘记了我的名字,只能用我母亲的名字作为前缀喊着我。她们很兴奋,露出孩童一般的笑,为自己还能认出我来——那个三十几年前在这条河道边奔来跑去的女孩,俨然有了中年的模样,可她们依旧能穿过时光一眼认出来!得到我的确认,她们更欣喜。她们拉着我的手,问我的近况,一如三十多年前,她们追着我的背影问我外婆有没有睡午觉,问我又要去哪里捉知了。
我问阿婆高寿,她掰着指头示意着,八十九啦!我笑着夸她身体硬朗,阿婆亦哈哈大笑着。这一瞬间,我突然很想外婆:要是外婆还在,可不会这么大声地笑——外婆是个极其内敛的人。
外婆走后,我很少再去外婆家,那些和外婆同辈的老人,也都渐渐走向另一个世界。这两位婆婆,也许是村里最后认得我的婆婆了。她们拉着我的手,和我说着旧年的事。那时多好啊,还是这一条小河,我沿着河岸走过来走过去,记忆里的河要宽得多深得多了,没有茂密的迎春花,但是有高大的楝树,夏天,无数只知了在枝头大声歌唱。可一转眼,河变浅了,变窄了,那位傍晚喊我回家吃饭的外婆,我再也寻不着了。
我和婆婆们道了别,走了一段路,忍不住转过身给她们拍了一张照片。距离太远,照片很模糊,模糊得如同那些远走的记忆。
妈妈和我小侄子在我前方的小巷道走着,那是妈妈的老家。也许若干年后,这条小巷子也会渐渐消失在时光里,那时,外婆的无尽夏,是否还会长长久久地开着?
枇杷树下
好几次,几个老友聚在一道时,总会念叨起外公外婆,念叨起外婆门前那棵枇杷树。
一晃,又是三五年的光景了。时光轻轻悄悄地走,春华秋实,周而复始;它无声无息,带走我们的心头挚爱。你看,斜阳照进白壁,照进壁上人的容颜与白发;它隔阻阴阳,拉开生与死的距离。
我不知道那株枇杷树是何时栽种的。童年的时候,那是泡桐树的领地,泡桐高大粗壮,每逢春日,桐花开了,仿佛一片紫霞罩在头顶。树下,鸡儿笃定地走着,时而朝着树根啄上几下。我从来不曾见过它们啄出一条虫子来,但它们依旧乐此不疲,不见停歇。
后来,这排平房都拆了,改建为两层的楼房。泡桐树的砍伐与倾倒的过程,我也未曾亲眼看见。那块泥地,被浇上了水泥。平整的水泥地的一侧,留了一块四方的花坛,大概那时,就有了这株枇杷树。
有了这株枇杷树,我愈发感觉到外婆的偏心。年年枇杷成熟的季节,隔三岔五,舅舅都会摘下一篮子枇杷。外婆喜欢给这些枇杷分类,最大最黄的,放到购物袋里,打好结,谁都不能碰。剩下的,舅舅和阿姨才能吃。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外婆就开始给我打电话,喊我过去吃枇杷。
每每去时,外公总会在路边等我,拄着拐杖,却又站得极其挺拔。外公长得清秀,他满头的银发和温和的脸庞是那个季节最和煦的风,在我转入村口的第一时间迎着面扑来。外公不爱高声说话,他总是微笑。他微笑着看我下车,微笑着跟在我身后,微笑着看我走进院墙,然后,他就走进房间,有时看报,有时翻牌。外公其实知道,等我进了家门见到外婆,他是插不上话的。
我和外婆坐在一起,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我们的交谈地随着季节转换。春雷过后,我们蹲在屋前的竹林里说话,外婆挖着小笋,我帮她找新冒出来的笋尖;月季和绣球开的时候,我们坐在屋檐下说话,正前方就是成片的花朵,有时还能闻到淡淡的花香;枇杷成熟的季节,我们自然就在枇杷树下说话。这个时候,外婆总是围着枇杷树看上几圈,招呼我摘下她够不着的枇杷。我自是不闲着,一边摘着枇杷,一边剥开往嘴里送。此时的枇杷最为鲜嫩,我常常一口气能吃上好几个。吃得快撑了,外婆还是会不时送上几个,说这个甜,你再吃一个。如此这般,常常到我嚷嚷着真吃不下了,外婆才心满意足地收了手。回家时,那一包打了结的购物袋,自然都是塞给我的。外婆似乎总觉得不够,总是想着搬把凳子再上去添几个。我于是急急地劝着,向她保证过几日再来拿,她才肯作罢。
次次如此。年年如此。外婆家最甜最大的枇杷,是我的专属品。
那一年,枇杷又熟了。微风和煦,我邀了几位老友一起去吃枇杷。转入村口的小道,外公依旧早早等在路边,他的头发更白了,拄杖的身影已不再那么挺拔,那年的外公,已到耄耋之年。外公一如往常那般,微笑着把我们迎进门。
一树累累的果实令人欣喜,我们把竹椅搬于树下,有人攀折,有人吟诗。我躲着阳光,剥着新采的枇杷。外公站在一边,只是微笑,并不言语。经历过一场脑溢血后,外公对物件与往事的记忆越来越差,以至于很多时候他拒绝开口。但他依旧慈祥而亲和,他笑盈盈地递上篮子,然后,静静地看着热热闹闹的我们。
那日的风儿真好啊,衣襟上都是枇杷的香甜味道。那日的外公一直没有言语,天空高远,外公的白发映在碧蓝的天空下,绣球花呼啦呼啦开着。
那年,意犹未尽的我们于这棵枇杷树下约定,一年一期,一期一会。然,我们于树下做的约定,偏偏忘记告诉年迈的外公。
外公是在次年夏天摔倒在枇杷树边的。毫无征兆。在昏迷半个月后,去了天国。那是九月,枇杷树上已然无果,叶子还顶着初秋的骄阳,片片挺立。
外公去世后,那棵枇杷树渐有萎靡之态,花亦开得萧条。外婆说,许是营养不够,土地薄了。至寒冬,看它瑟瑟落叶,竟无半点起色。心头郁郁,遂想起各种约定,恍然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