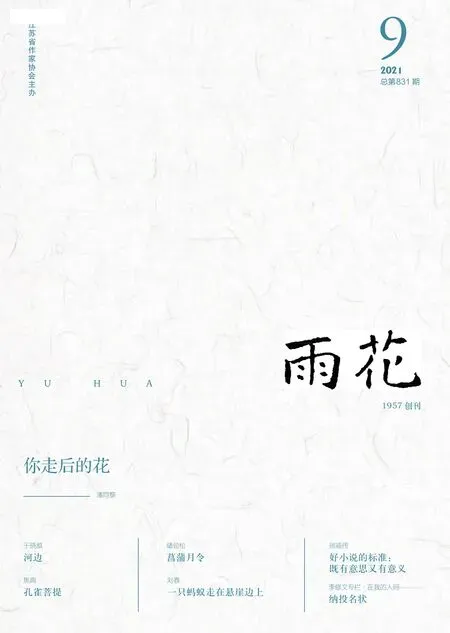野鹿荡:暗夜星空
2021-11-13姜桦
姜 桦
川东闸口南侧的一片宽阔的芦苇场,因为濒临世界上最大的麋鹿野放区,茂盛的苇丛里时常有野鹿、牙獐、柴狗、野兔等动物出没,故名“野鹿荡”。四月,天气清明,大地升温,一群有头无脸的虫子从草根下钻出来,爬过那一片片新鲜的树叶。被泥土抬高的野鹿荡的“麋鹤营”中,几头雄性麋鹿屏住呼吸,颤抖的犄角直挺挺地钉在地上,睫毛上挂满了青草种子,一股浓烈的欲望,伴随着扑朔迷离的眼神,正渗入春天的深处。
以一条宽阔的复堆河为界,与“麋鹤营”隔着一道河堤,野鹿荡东边一片更大的区域属于野生麋鹿的活动范围,通常被称作“麋鹿野放区”。早些年,这片野放区仅仅是指川东闸口到梁垛河口的一片芦苇滩和沼泽地,如今,随着野生麋鹿在响水灌河口以及东台条子泥滩涂相继被发现,盐城沿海从南到北数百公里的海岸线,几乎都成了野生麋鹿的生活区。只是,作为麋鹿活动的核心区域,“麋鹤营”和野鹿荡的地位一直不曾改变,有时候,在这个区域聚居的麋鹿会达到近千头。
大地在不同季节里捧出的一束束野花,仿佛一封封写给远方的质朴而亲密的信。十月,滩涂上的风从麋鹿野放区一路吹过,一直吹向野鹿荡,站在那一条条高高的老木船上,水波晃动着一群群麋鹿的倒影。深冬的滩涂大地天寒地冻。正是麋鹿脱角的季节。夜晚,一轮月亮从野鹿荡里升起来,圆圆的月亮被勾出一道白色的霜边。大野安静,一只只鹿角从半空中脱落,也有走着走着就掉了的,但是都会在坚硬的滩涂地上留下空空的回响,那“咔吧咔吧”的声音很远就可以听到。这样的情景是独特的,但你且不急着去管它,等到翌日清晨,一片耀眼的阳光照耀着那片坚硬霜白的滩涂,那块空旷的土地上留下的一只只鹿角一律平稳倒置,犹如一只只坚定有力的手掌紧抓着这一片滩涂。围绕着那一只只巨大的鹿角,滩涂地上布满了麋鹿新鲜的蹄花,一只又一只,一圈又一圈,那是一只只麋鹿围绕着刚刚脱落的鹿角向大地致敬,也是它们就着清冷的月光写给滩涂大地的秘密经文。
四月末,堆满滩涂的油菜花结出了饱满的籽粒,稍晚一些,白色的洋槐花又会在头顶上盛开。紧挨着野鹿荡,一条海堤公路由远及近。这条路是从附近的一座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国有林场走出来的。道路两旁,到处是蒲公英、狗尾草和野蔷薇。偶尔会遇见一群野山羊和海仔牛,一个个健壮肥硕,它们身披露水,似乎一夜未归,让你怀疑它们是不是原本就没有主人。身边不时有赶海的人们骑着摩托车经过,都是一些赶往海边小取的人,有本港人,也有外地的,连云港人、南通人、山东人、浙江人,甚至是河南人和福建人。他们凌晨三点多就出门了。一个多小时后,当海水退去,一片巨大的海滩从海水里裸露出来,一波又一波赶海人,他们用随身携带的长长的竹钩在滩涂上左勾右刨,东奔西跑中就将一只只海蛏和文蛤捉进自己的鱼篓里。追逐着浅浅的潮水,这样的劳作一般会从上午一直持续到晌午,在下一个潮汛到来之前,这些赶海人会撤出滩涂。傍晚时分,他们带着满满的收获退回到岸上。装满鱼获的蛇皮口袋一般都是扛在肩上,鱼篓则会放在滩涂上一路拖着往前走。这活计看似简单实则极其消耗体力,因为刚刚退潮的滩涂上,那潮湿的淤泥总是充满了阻力。为了减少这种阻力,赶海人会在鱼篓底下放上一块特制的木板,薄薄的,前面高高翘起,像拱起的船头,又像一只飞扬的雪橇。当然,拖鱼拉货这些活儿基本都是男人们的事,跟在后面的女人,腿上身上沾满了点点泥斑,在春天的风中,那些飘动的头巾五颜六色,依旧被裹得严严实实。这时的野鹿荡更像一个巨大的芦苇城堡,一直跟随在他们的身旁。
走进野鹿荡最好的季节还是在初夏,五月。清晨五点,你起床,跟着一块很有些年代感的木质门牌,走出一条条被风雨剥蚀的已经成了客栈的古船。徒步向前,去往野外。宁静的野鹿荡里,青苇环绕的湖面被一层薄薄的晨雾笼罩着,时而有鱼儿跃起,时而有宿鸟飞过。一轮初升的太阳浮出水面,红彤彤的,美轮美奂。越往前走,芦苇越深。随着云雾逐步散去,一片巨大的草原在滩涂上铺开,那是野鹿荡最核心的部分,已经快到了“麋鹤营”。最早发现这片海边大草原的是摄影师老宋(我们更习惯叫他从然)。2013年深秋,我和老宋一起去滩涂采风。车子开上川东河大桥,迎着川东闸口的方向,老宋从航拍器里意外地发现了这片系着金色腰带的红滩涂,那是一大片盐蒿草滩和大米草滩。棕红的大地火焰喷薄,川东闸口方向,一座座巨大的风电塔伸向蓝天,转动的叶轮要将天空的白云一片片绞碎。
一次贸然又意外的闯入,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惊喜。穿行于这片海滨滩涂,仿佛行走在辽阔的北方大草原。几十年的滩涂湿地田野考察中,我曾经在响水陈家港的灌河口和东台弶港的围垦区多次见过盐蒿草滩,却不知道在川东闸口也有这样一片神秘之地。航拍的小飞机在天空转了一圈又一圈,老宋拍了一张又一张滩涂草原的照片,我则为这些图片配上新写的诗,然后在本地的一家报纸以专栏形式推出。
这一组滩涂草原的诗我前后写了近二十首。报纸连续刊载了十多期,有几期还特意印在了封面。
记得有一首《黑蓑衣的雨》:
林中密布穿着黑色蓑衣的雨滴
赶往五月的路上,随着一阵风
那些蝴蝶、蜜蜂和鸟鸣
跌落成身底下星星点点的油菜花田
一丛丛菖蒲站在水边,我知道
它们喉咙里的饥渴。疾飞的鸟划过雨水
它们的身体,翅膀,长长的腿脚和喙
而我最疑惑的是那些树,枝干灼烫
它们藏于内心的绿色,是否要等到
油菜花开满了,才会彻底说出!
十多年来,这片美丽到惊心的滩涂草原无数次在我的梦中出现,我和老宋也一次次重回野鹿荡,重新走进这片海滨草原。我们还策划了一个个和滩涂相关的采风活动,有几次,我们甚至将朗诵会开到了滩涂上。在高可没膝的红草地和大米草滩上铺下一张巨大的塑料布,一行二十多人,大家或立,或蹲,或卧,或者干脆躺在干净的草地上,一边看着那片湛蓝的天空,一边高声朗诵自己新写的诗。白云飘舞,飞鸟诵唱,天远地偏,万物皆忘。太阳落下,红色的盐蒿草被夕阳抱回家去,我们在一大片空地上燃起篝火,在欢快的舞蹈和歌声中彻夜狂欢,那样的时刻,沉醉于诗歌中的我们,乃是整个世界的中心。
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们有幸结识了这片野鹿荡的主人——地方史研究专家马连义。头发有些花白的老马是一个典型的自然环保主义者。20世纪70年代,他曾在西藏的阿里地区工作生活多年。80年代调回江苏老家后,在当时的县委宣传部做了两年多的副部长,但是很快老马便弃官,非要到海边滩涂去做一名义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老马一次次只身深入黄海滩涂的农场、林场和麋鹿野放区,跟踪那一只只野生麋鹿,进行黄海湿地麋鹿生态和滩涂文化的田野调查。十多年间,他精心撰写的一本厚厚的《麋鹿本纪》成为他有关麋鹿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一组为祭奠从英国乌邦寺回归祖国的三十九头麋鹿而创作的“十四行诗”,迄今也一直都是中华麋鹿园的“镇园之宝”。
从2009年春天开始,为了更好地研究野生麋鹿种群保护和生物遗民的历史,老马将目光转向了麋鹿野放区以外一处更为偏僻的滩涂地,也就是今天的野鹿荡。据老马和一群志愿者考证,大约一万年前,靠近川东闸口的一大片野芦荡,包括东台的新曹农场、蹲门口(野鹿荡下游三公里)、巴斗村一直到弶港一带,都是古长江的入海口。江河东流,大船出港,小船靠岸,彼时的长江入海口水道宽阔,一片巨大的河口三角洲,两岸居住着一个远古的移民部落。在这里,他们打鱼、捕猎、晒盐,看着那野草蓬勃生长,与身边的芦苇菖蒲、灰鹤苍鹭一起,见证了一片滩涂海岸的千年沧桑。
千百年河流冲击,最终造成了长江口的不断南移,这条老河口也变成了一片更大的滩涂地。老马出生在大丰裕华,是典型的本场(本地)人。一百多年前,民国实业家张謇组织大批移民从南通北上盐城,带着上万名启(东)海(门)移民在荒凉的苏北海边滩涂废灶兴垦。作为一个自然生态作家,老马对这一段移民的历史情有独钟,从骨子里认定可以在这片滩涂地上找到更多祖先的足迹。整整两年时间,老马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起早贪黑,不辞辛劳,从南到北,踏遍了沿海地区上百公里的滩涂,从干涸的淤滩上拉来九条一百多年以前著名实业家张謇兴办“大丰公司”时留下的古老沉船,还将搁浅在海滩的晚清和民国初期的几十只铁锚也运到了这里,最终在麋鹿野放区附近,这片芦苇丛生的三角地上,建起了一座生物移民所,并将这片蛮荒的土地命名为“野鹿荡”。起初,老马试图将野鹿荡建成一座专门研究移民史的半开放的工作场所,同时兼及旅游和湿地文化传播,只是事情一波三折,整个过程并不顺利。但是无论如何,因为一个人的努力,一块原本荒寂无人的亘古荒原,最终成为了一片面积宽阔、芦苇环绕的野鹿荡,成为了一处历史文化遗产。站在滩涂,面朝大海,头顶着暗夜星空,野鹿荡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讲述着一个个生物移民和滩涂变迁的故事。
六月,面向大海的滩涂晨光熹微。挂满露水的野鹿荡,一群高大壮硕的雄性麋鹿将颤抖的鹿角猛然抬起,一场充满魅惑的鹿王争霸战拉开了序幕。
电视正在直播——
春天,野鹿荡的水位被一棵棵新生的芦苇所提高,滩涂大地上花木生
发,槐花飘香,成年麋鹿开始进入发情期。在这个生动的季节里,每一头业已成年的雌性麋鹿身上,都会自内而外、从下而上地散发出一种神秘而特别的气味,即便是没有风,这种气味也会稳定地震颤在空气中,并且沿水平方向朝着四面八方的灌木和草丛间弥漫。
鹿王争霸战说到底就是一只只雄鹿为了争夺嫔妃而展开的角力与较量。开阔的滩涂上,尖锐的鹿角挑起的泥土四处飞散。陶醉于某种浓烈的气味,一群雄鹿渐渐靠向另一群雄鹿。一场充满激情的鹿王争霸战,使得整个城市也跟着荷尔蒙上升。你看,大街上的人们脸上都是红扑扑的。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这样一次即将开始的充满激情的狂欢。
麋鹿争霸的滩涂,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力量的竞技场。电视直播的镜头紧跟着那一群行进中的麋鹿在不停调整着角度。那些雄鹿大口呼吸着雌鹿身上散发出的独特气味,然后屏住呼吸,沉默良久,再舒缓地呼出。而游动机位则给到了那些雌鹿,它们健壮,美貌,站在远处静静地观赏,粗大潮湿的尾巴扬起又落下,神态专注又如醉如痴。
随着体内的荷尔蒙的骤然增多,竞技场上,那些仰头长啸的雄鹿紧张而忙乱。成年雄鹿会突然开始装扮自己,它们往身上涂抹泥浆,用尖锐阔大的双角,挑起地上的泥土和青草、树枝作为装饰,分泌出的液体,也被随意涂抹于高大的树干之上。伴随着身边的草浪,平时看似散淡的雄鹿们突然变得性情暴躁,并且发出一阵阵响亮而怪异的叫声——显然,雄鹿们希望以自己的吼声来震慑住对方,更希望由此博得远处的雌鹿们的青睐。
偌大的滩涂上聚集着一头头雄鹿,他们站在野鹿荡或者麋鹿野放区的纵深处,一双双眼睛看似眯成了一条缝,却是一刻不停地紧盯着那片即将成为竞技场的空旷滩涂,紧盯着迎面而来的一个个对手。
一头雄鹿开始缓步走向一头雌鹿。即便只有短短二三十米的距离,这段旅程也几乎需要耗尽它们全部的体力。因为,在抵达雌鹿的过程当中,几乎每一头身强力壮的雄鹿都要经过一场激烈角逐和生死决斗。
鹿王争霸战,这是麋鹿家族为了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最壮观的充满血腥的战斗。
两头体魄健壮的雄鹿走进了画面,双方是那样的激情四射,又那么虎视眈眈。
啊,你看,它们沉默,它们不说话,它们不打招呼,就这样猛然冲向了对方!平时的空旷地带,瞬时成了一只只麋鹿之间争夺鹿王的战场。
一边是一头头雄鹿为了夺取鹿王打得不可开交,一边是大群的雌鹿站在远处静静观望。是的,那些身体里
散发着特殊气味的雌鹿,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场战斗。此时此刻,它们的眼睛里写满了渴望,它们希望有一头最为健壮有力的雄鹿力克群雄,尽快脱颖而出。而那头最终胜出的雄鹿,将是它们最伟大的“王”。
鹿王争霸,是一群麋鹿为了夺取交配权所进行的鏖战。事实上,雄鹿之间为了争夺嫔妃而展开的角逐并非人们描述得这么有趣。那些摄影师们偶然捕捉到的所谓鹿王争霸的场景,从未在直播现场的镜头中重现过。根据来自国外的一份资料显示,雄鹿之间为争夺配偶的角斗相对温和,并无激烈的冲撞和大范围的移动,角斗的时间一般也不超过十分钟,失败者只是掉头走开,胜利者一般不再追逐,很少发生鹿与鹿之间相互伤害致残的现象。一头雄鹿占群之后,若遇其他雄鹿窥视母鹿,占群的雄鹿仅会用吼叫和小幅度的追逐赶走对方。
让许多人津津乐道的麋鹿争霸战,说到底只是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楔子。从野放区到野鹿荡,麋鹿家族的上千头麋鹿似乎并不关心这些。它们或跪或卧在高高的堆堤或者浅浅的沼泽里,一边安静地啃食着水边的青草,一边抬起头看一看透明的蓝天,安然自在,气定神闲。
那些胜利者和失败者很快都将再次回到野鹿荡,再次回到麋鹿野放区,回到属于麋鹿、飞鸟和风声的滩涂大地——那绿色无边的草原。
对麋鹿争霸的观察与描述,同样体现出东西方人精神、文化和世界观的差异。
绿色在弥漫,一直弥漫到秋天——秋天,巨大的滩涂正被火红的盐蒿草覆盖。紧接着,那血一般殷红的盐蒿草又将被大米草吞没。
大米草(学名:Spartina anglica Hubb),一种多年生直立草本植物,原产于欧洲,生于潮水能经常到达的海滩沼泽中。因为耐淹、耐盐、耐淤,可以在海滩上形成稠密的群落。
在中国东部黄海海岸地区,大米草的引进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初只是为了挡潮消浪、保滩护堤,但是没想到这种植物繁殖极快,几年就能把整个滩涂上的其他植物吞噬得一干二净,往往去年还生长在海边的一大片盐蒿草,今年已经被大米草吞噬了大半。在野鹿荡附近,包括更远一些的条子泥海滩,我们带着满腔希望寻找的红滩涂,仅仅几个月就没有了踪影。
但是,这片安静的海滩还在。在一片开阔宁静的天空下,在奔跑着成群麋鹿、留宿着无数飞鸟的野鹿荡,今夜,我们的头顶停留着一片世界上最黑暗也最宁静的夜空。
刚刚被命名的“黄海野鹿荡·中华暗夜星空保护地”,是继黄渤海湿地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之后,人类与大自然又一次成功建立契约。盐城黄海野鹿荡,这是中国继西藏阿里、那曲之后第三个暗夜星空保护地,也是中国沿海地区从南到北第一个暗夜星空保护地。面积逾万亩的野鹿荡和更大范围的麋鹿野放区,平时人迹罕至,数十万株茵陈草迎风生长,香味扑鼻,每到夜晚,虫鸣如潮,浩瀚的天空繁星闪烁。在野鹿荡这片面积26 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因为没有光污染,平均每年可观察星空238 天,夏夜银河、冬季猎户星座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可触,而白茅岛上的茵陈草引来的繁星般的萤火虫飞来飞去,闪闪烁烁,和天上的星海遥相呼应,散发着圣洁之光。“黄海西岸一古船,繁花野草满天星。”在以条子泥为核心的黄海滩涂湿地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之后,野鹿荡的万亩草原又成为无数天文爱好者追逐暗夜星空的最佳去处,于是,在追逐滩涂候鸟的队伍之后,一群又一群人来到了这里,来到了静静的野鹿荡。太阳落下,夜幕低垂,大地宁静,星空喁喁,大家在此静坐相依,抬头遥望星空万物,以手中的镜头记录下头顶的深邃星空,一起分享这独特的、能够看见浩瀚星空又能听见彼此心跳的野鹿荡之“夜”。
滩涂浩大,海生烟波。生活在大海边,大自然赐予我们不断生长的滩涂地,天空之镜般的野鹿荡。不灭的星光下,更多的志愿者加入了野鹿荡的保护队伍,追随高高举起的芦苇穗絮,将目光一直送向头顶的浩瀚天空。大海边的暗夜星空,像一篇古老的神话,更是一首连着天际的大地歌谣。
自然保护主义者马连义还徒步行走在滩涂上。他和他的团队在野鹿荡的田野调查工作已经进行了整整十五年,记录下的野草种子已经达到四百八十五种,发现的鸟类也已超过了三百多种。
摄影师老宋还在滩涂上跋涉。经风历雨,饮霜宿露,一遍一遍走向大海,走向滩涂上的野鹿荡,他的那辆装满器材的车子几乎就是一辆滩涂直通车。河流沧海,火焰滩涂,浅沟深壑,头顶红冠的丹顶鹤,“四不像”的麋鹿,一直都是他镜头中的主角。
而我,面对滩涂,面对野鹿荡,抬头仰望头顶广阔的星空,遥想着千百年前那些居住在长江口的移民部落,追忆那片滩涂大地的前世今生,以及一首诗歌的来历和去处,我发现,身边的野鹿荡,那艘古旧的船头上,不知何时,多了几架天文望远镜。
“暗夜”汹涌,我们在这里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