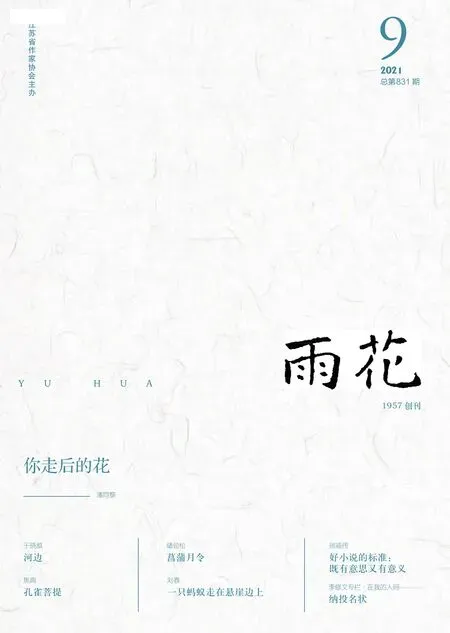我们的荒凉
2021-11-13连亭
连 亭
父性的故乡
我惊讶地发现,人们对故乡的回忆,总是母性的;几乎所有对故乡的文字描述,都把故乡比作母亲而非父亲。
我也不例外,想起故乡最先闯入脑海的也是生育我的母亲。
母亲是在一座年代久远的山村小瓦房生下我的。小瓦房是家族大宅中很不起眼的一间,也唯有这一间是属于父亲的,其他房屋则分属不同的族人。
这间小瓦房里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是那个年代山村唯一的一台电视,作为母亲的嫁妆出现在山村。母亲挺着大肚子整理家务时,电视里频频出现的是邓小平挥手致意的身影。母亲说,电视里的他讲话带四川口音。
这个讲话带四川口音的老人发表南方谈话的那一年,我出生了。那是岁末,南方的湿气加剧了冬天的寒冷。母亲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裹紧的被子上加盖了几件厚衣服,身子仍暖和不起来。
她的脑神经被寒气绷成一根弦,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日出时分,疼痛第一次席卷她,她应对的方式就是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那必然降临的时刻。
我在她疼痛的顶点来到了人世,从此用她给予我的生命,开始学着认识和接受整个村子,以及村子里的每一种痛苦和每一种希望。
在门前的小路上学走路时,我总能看到房屋旁边的一棵树,树上最浓密的几条树枝举着一个鸟窝,几张绒黄色的鸟嘴时不时地从窝边探出来。外出归来的大鸟,频繁而又细致地往这些黄嘴巴里喂虫子。这个画面深深印入我的脑海,并且在记忆中一次次盲目而又顽强地再现。
印象里,母亲总比父亲亲切。她以坚强的意志和非凡的耐力呵护我们的成长。而回想起来,父亲在孩子的成长岁月中总是缺失的。在我两岁半到十岁期间,他把我寄养在码头。我十岁时,他以哄骗的方式把我从码头带走后,也并没有填上他在我生命中的空缺。
他经常去遥远的地方,有时是西边的矿场,有时是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建筑工地。我和妹妹总是一连几个月都见不到他。奇怪的是,我们对此并没有太大的感觉,有时他离开很多天了我们才发现他不在家。
没有人对我们说过他为什么不在家,母亲只偶尔念叨他什么时候会回来,通常是过年或者中元节,而我们对此并不十分期盼,我们早已习惯他不在家。
我们并不清楚,父亲到底爱不爱我们。似乎对他而言,家只是一个过年的地方,而我们只是他心烦时所呵斥的对象。
他总是冷不丁地叫住我,粗哑地问道:“你又上哪儿野去了?”我被迫低头站在他跟前,紧张和难堪使我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只好拼命用手摩挲衣角。紧接着他咕哝着说:“大了就该懂事,整天到处野,不像话。”
母亲为了护我,就会在一旁解释,说我上哪干活去了(多数情况事实也是如此)。这些解释却并不能使父亲满意,他会加强语气说:“你总是惯着她们!”
远嫁北方之前,我再一次回到了小山村。我先是坐火车,接着是大巴,然后是中巴,最后是三轮摩托车。山从眼前不断划过,最后是父亲的身影出现在路口,如同上学期间寒暑假我从学校归来时一样。
这一年他五十岁,头发已经花白,手在干重活时会突然麻痹。他骑电动车把我从路口载回家。我坐在他背后,他黑白参差的头发就在我眼前飞动。
我们都清楚这一次我回来意味着什么。在家等待婚礼时,我们很少说话,总怕触及某种东西。
我们都记得,高考前夕我们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成绩一向优异的我,分数只比一本线高出二十多分。这些年我的挣扎与努力,都和这一次争吵有关。我不得不认命,又有所不甘,于是开始另辟一条路。前路艰难而孤独,很多年来我都以为自己是独自前行。
我想,如果非要寻找他也关心我们的证据的话,就只有他对我们的成绩单的重视了。由于没能上学的缺憾,他对“学习”几乎是敬畏的。虽然半文盲的他,有时会因为自尊心而故作瞧不起读书人的样子,但心底其实对读书十分向往。他甚至坚信,读书是划破贫穷的一道光。
每当我们带着奖状回家,他都郑重地把它们贴到墙上,在亲友们面前也从不掩饰他的自豪。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他看重成绩单是为了满足这份虚荣心。穷得发赤的他,也实在没什么别的可骄傲的了。
为此,他总是催促我们坐到书桌前,连除夕夜也不例外。相比之下,母亲很少强迫我们。或许,母亲更希望女孩子能帮家里洗衣做饭、耘田绩麻。
在因缺钱而赊欠学费的年月,父亲的脾气变得很暴躁,总是无端冲我发火。我们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我心里已把他称为“暴君”了。
高考那年,码头的外公过世了。那是从小抚养我的外公啊!没有人把消息告诉寄宿在学校的我。事实上,父亲是故意让所有人瞒着我的。
然而,在一个不太适合的时机,我从一个小孩嘴里听到了此事。我的泪水流了下来,眼睛哭肿了,脑袋也发胀。
他骂我,强迫我把眼泪收回去。我们吵了起来。
我不出意外地考砸了。他的狂怒可想而知,尤其是亲友向他询问我有没有考上北大时,他总是以讽刺我的“谦辞”来掩饰他的难堪:“别说北大了,连最末的都够不上。”
填报志愿当天,我们又吵了一架。我决心不再听他的话,就连填报志愿也带着几分赌气。我只报了一所学校,而且是学费最便宜的师范大学。
我不想被录取,我心里已不想上学了。那个一生中最长的暑假里,我跟在父亲身后去了工地。我在那里搬砖,搅拌沙子和水泥。我跟他说:“除非你变得有钱,否则休想管我。”他在水泥的飞尘中沉着脸说:“你记住你说的。”
临近开学,他没在家,也没去工地。最后一天,他托人叫我去公路边的一个林场找他。我见到他时,他的头发和胡子都长长了,打着补丁的迷彩服被汗水和污渍浸得又黑又黄。
那天,他没让我干活,而是快速地递给我一张银行卡,叫我回去好好上学,说完就爬上了一辆开往林场深处的拖拉机。
拖拉机扬起路尘,我的心里涌起一股刺痛和酸涩,眼泪不争气地湿了满脸。
我带着他给我的钱坐火车去大学报到,完成了四年学业,然后被保送到一所985 高校读研究生,再后来走上了写作之路。
对此,父亲应该是心有遗憾的。我想,他始终对我没能去北京上大学耿耿于怀吧。这几年,无论我取得多大的成就,获得多大的奖,他都没有说过一句肯定的话,也没有在人前显露半分喜气。
我跟他说我要嫁人了。他不置可否。我以为他对男友不满意,只是碍于情面没有明说。婚期接近,母亲替我四处张罗,他像不知道此事般整天在地里瞎忙活。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他在屋里偷偷试衣服,才知道他特地定制了一套西装。他站在镜子前,笨拙地穿上平生第一套西装,仔细地扣上扣子,扯平衣角,然后曲起手臂,认真地练习婚礼仪式上父亲带新娘进场的走路姿势。
他手腕上的疤痕在白色袖口的映衬下十分触目,那是那年在林场砍树时留下的。婚礼当天,他用这只手把我送到新郎面前,然后看着我登上开往北方的火车。
车子渐渐走远,他忽然把手高高地扬起,看上去像是要托举什么东西。
他托举什么呢?那些年,由于他经常不在家或者过于严厉,我从没留意,也不曾看清。
这一刻我突然发现,他这个托举的姿势已经很多年了。他一如既往地在风雨中奋力地伸长手臂,就是为了把我送到比他更高的地方。一如当年站在尘土飞扬的拖拉机上,他把手高高地扬起,叫我回去上学。
他的每一根白发都是我的过去啊。我再一次望见门前的那棵树,它曾经也托举过一窝伴我学走路的雏鸟。雏鸟早已长大飞走,并且不知繁衍了几代。越飞越高的鸟儿,能低下头来看看托举它的大树吗?能在春天唱一支歌献给喂养它的大鸟吗?
无论是树还是鸟,它们都不曾在意吧。越走越远的孩子,知道父亲的爱和不舍吗?知道父亲也会像外公一样老去、不在吗?
当年,父亲把我从码头带走时,外公是舍不得的,但他没有使用他的权利留下我。他只是摸着我的头说:“有空就回来看外公。不用太勤,上学要紧。也不要太久,太久恐怕就见不到我喽。”说完他转身沿着土路向瓦屋走去。他佝偻的脊背上,似乎背着我的整个童年。
多年后,父亲也对我说了类似的话:“有空就回家看看,不用太勤,工作要紧。也不要太久,太久你妈会想你。”我忍不住久久地抱住父亲,告诉他我会常回家看他。
如今我在北方写下“故乡”两个字时,父亲的形象变得鲜明起来,时而离母亲很远,时而与母亲合成一个影子,共同组成故乡的概念。
从此,除了母性的故乡,我多了一个父性的故乡。
我们的荒凉
我并不是在黔江出生,但所有的童年记忆都在黔江畔。在那里,我从两岁半长到十岁,生活由河水、鱼虾、船只、瓦房、稻田组成。
在世人眼中,它贫穷、边缘、封闭,是一块被遗忘的蛮荒之地,充满野草蔓延的荒凉。我年轻的生命,不是对抗这种荒凉,就是和它一起荒凉。
有一次,我在码头看到落日跌下山头,没有一条船的水面风急浪高,心头陡然浮起莫名的意绪。我开始盼望长大,急于拓宽生活的边界,心中灌满向前的声音。
而外婆总是一边在灶台忙活,一边念叨身在广东的舅舅。她祈求各种神灵关照她的孩子,灶王爷、关老爷、老天爷、庙娘娘以及其他有名无名的神灵,都无数次地聆听过她简单又乏味的祷告。
相比于躁动的后辈,外婆是静止的。她不知道码头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若不是舅舅跑到了外面,她也不会关心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圩日,她拎上一大袋自种的辣椒到码头,找一块临江的空地摊开,等过往的船夫来买。有时一天都没有人来买,天快黑时她就把辣椒装进袋子拎回家,连夜捣碎制成辣椒酱,再用罐子密封好,叫我找人寄给远方的舅舅。有时她刚到码头,就碰到一拨人从船上下来,一口气买完她所有的辣椒。零碎钞票在她的布袋里渐渐多起来,攒够数后她就拿去买盐和止痛药片。
她以为挣钱就是这个样子的,只要拿货候在岸边,等别人拿钱来换就行。所以她感到奇怪,儿孙们为什么跑那么远,而且一去就是一两年不回来?
守在岸边的外婆,有时目光会跟随船只顺流而下。沿河废弃的码头,以孤冷的姿态提示往日的繁华。芦花斜阳,风枝水鸟,稀疏的桨声点明水运的衰落。
在漕运码头衰老的遗迹里,我的脑海会闪现出世界的这一角与世界的轮廓。我坚信这一角之外的影像,就是世界的轮廓,尽管我的视野所见还只是这一角。事情或许就糟糕在这一点,我笃定,蠢蠢欲动,又幼稚至极。
很显然,自从水运衰落后,曾经声闻海内的码头,已步入被世人遗忘的境地。这种境地和日益变化的外界是不一样的,尤其和城里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仍希冀,我们的家园是世界的一部分,而非边缘,不是陪衬。
我们渴望再续时代磅礴的图景,在这个图景里,我们是我们,又不只是我们。然而,尽管河流之水无所不达,山之外的一切却皆为梦境。我们的想象带着我们在混沌中飞扬,我们所借住的形体却始终停泊在山旮旯中。
我们的生息歌哭,生老病死,在世界的一隅静默地持续。宽阔的江面偶尔驶过开往广东的货轮,更多的时候只有摇晃的木船和孤独的渔夫。我记得那些寂寞的货轮,是因为我在河边洗衣服时,它们掀起的大浪经常卷走手边的衣裳。而在另一种时候,它们会吸走没能和我一同长大的小孩。悲伤的农妇自杀,也喜欢选择白浪翻滚的时候,那样她们死后的躯壳就会被冲得很远,再也不用返回码头。
在码头的我们,是真实的,也是虚妄的。
我们不愿说服自己去爱别的东西,恐惧与困惑迫使我们只爱我们的码头、河流、船只、粮食与亲人。我们狭隘、固执,多数时候这能使我们免于被诱惑、被左右而陷入危险。我们深深地知道,相信一根柴火比相信陌生人的长篇大论更可靠。
尽管如此,码头还是灾难不断。而且,码头的灾难不是虚幻的,总有实物对应,水对应洪涝,风对应台风,阳光对应旱灾……总之,一切事物都有两副嘴脸,今天是美好的,明天变脸了就是灾难。
被灾难洗礼过的我们,不去谈论似是而非的东西,因为我们的世界不是由别处的事物构造,而是由周遭的事物组成:河流、船只、石岸、沙土、山岭、草木、田地、庄稼……具体的事物总是占据我们的心,有时我们的悲伤因为过于具体,变得轮廓浩大、面目模糊……
我们终究成为了这样的人:有着坚忍的好脾气。这好脾气常常给人一种好欺负的错觉,事实上我们是百折不挠、寸土不让的。
我们练就这脾气,只是为了遇到困境时,能够在守住根基和底线的前提下,做出一些退让,以便适应环境和承受生命的重负。
这很像树,当强风吹来,它们顺势弯下身子,减轻风所带来的损失,不管摇撼得多厉害,也不离开脚下的土地半步。而风超越生命的极限时,它们也会慷慨赴死,绝不犹豫半分。
然而,我们的脾气并不能阻止码头的衰落与荒凉,犹如岸石不能阻止流水奔向大海。
码头的每一个人,都熟悉那块高耸的岸石,它犹如巨蟒盘踞在水边。对于我们,这块探向深水的岸石,是起点,也是终点。船舶在这里起航,岸上的路却就此中断。于是,它成了人心的据点,码头人的目光在这里延展,也在这里终结。
一些偶尔通过地图缝隙寻到此处的游客,也注意到它对于这片土地的特殊含义。他们站在岸石的最高处眺望,发现延伸十里的峡谷风光醉心迷人,于是他们请求在岸边缝补渔网的外公用木船载他们游江。
他们通常一身名贵的衣服,眼睛罩在墨镜下,脖子上挂着照相机。他们见过无数的美景,到了此处仍不禁赞叹,甚至说起羡慕远离尘世的桃源和渔夫的话来。满目的荒凉,到了他们眼里,也成了一种时间镌刻的情调。
外公把船靠在石岸边,在船板上铺好报纸,以免留在上面的鱼鳞血迹弄脏客人的衣服。船缓慢而平稳地前行,游客兴奋极了,一会儿纵情呼喊,一会儿疯狂拍照,有时还把手伸出船外,撩动如梦似幻的河水。外公则提醒他们小心避开水上的漩涡,漩涡过来时千万不要伸出手。
我到河边喊外公回家时,往往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只听见外公沧桑浑厚的歌声远远近近地传来。我找一块干净的岸石坐下,对着无尽的流水和苍茫的码头,等待外公泊船。
水手的号子、渔夫的渔歌、沿岸的山歌,外公都会唱,也只有他们那一辈人才会唱了。这是靠水吃水的一代人的记忆。他们后辈的记忆,已转由城里的高楼和流水线填充。
欣赏着醉人的景致和野趣十足的歌谣,游客们时而欢呼,时而鼓掌,有的还打开录音设备录下来,带回城里供日后回味,或者传播给更多的人听。多年后,我走在一条异乡的小巷,听到二手音像店的旧磁带传出苍凉的乡音,总以为是外公在唱歌。
日落西山,游客兴尽而返。外公掉转船头,自顾自地唱起挽歌,悠长深沉的调子,伴着他的船停靠在宁谧的码头。我走上前去,帮他把船缆牢牢拴在木桩上。
我那时总以为,码头的日子会无尽地延续下去,我将在码头无拘无束地帮外婆捡柴火,帮外公拾掇鱼虾。十岁那年,外公一下子老了许多。他在帮邻居修葺房子时,脚被跌落的石块砸伤,此后常年浮肿,连鞋也穿不进。外公再也划不动笨重的船桨了。而后,外婆的灰白头发渐渐雪白。最后,三个人的瓦屋,只剩下外婆一个人。
与此同时,每年都有新的一批年轻人离开码头。他们投身外省的工厂,只在过年时才回来。舅舅是在我三岁时下广东的,和别人不同的是,他从没有寄钱回家。他的钱都花在了酒友和姑娘身上。
我十岁那年的冬天,父亲突然出现把我带走。由于匆忙,除了身上穿的衣物,我什么也没拿,就连学籍、课本、作业本都落在了村子里,更别提与小伙伴们告别了,这些年他们想过我吗?
这一离开,我的生活就剥离了码头。河边的瓦屋越发荒凉了,外婆在岸石上遥望河川时,眼里也多了一份思念。
想来真是荒诞,我曾经盼望离开,真正离开后,却又万般怀念。我的思念与日俱增,如同码头在日益荒凉。
再后来,外公去世了,独留外婆在河边守着我们共同生活过的瓦屋。日渐苍老的外婆,不愿意离开故土,也不肯要我们的钱,只靠微薄的养老金度日。每念及此,我内心十分苦涩。
无论是寒风怒号的冬天,还是洪水滔天的夏季,她一个人站在窗前或门前,望着空阔的码头和大江,长风把她的白发吹得凌乱。
一些清冷的早晨,通往码头的小路,响起脚步声或说话声,睡眠不深的她就会被吵醒。她像往年一样披衣起床,却发现没有一个声音是走向她的。
她的儿孙都到外地去了。而外公的坟头,就在一公里外的林子里,长满野草和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