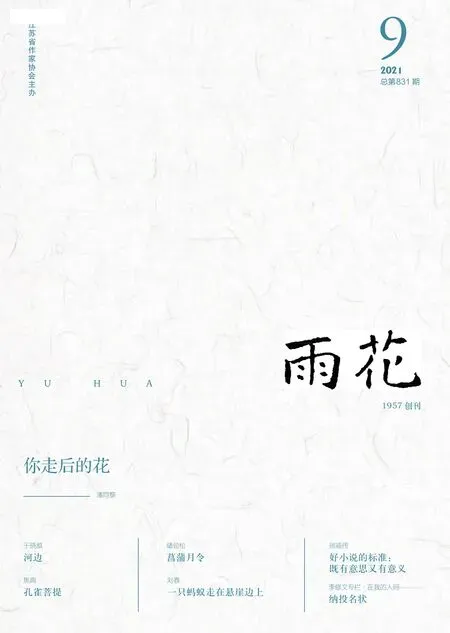燃烧的火焰
2021-11-13周齐林
周齐林
1
深冬时节,晨雾笼罩着村庄,睡眼惺忪的我匆匆走在铺满鹅卵石的小路上,往几里外的学校赶去。走出家门几百米远,在紧邻池塘的三岔路口,我隐约看见广阔无垠的池塘边有一团火。三条小路在这里交汇,而后又蜿蜒着伸向远方。通红的火昭示着一个村里人的离去。夜色还未完全散去,弥漫着死亡气息的火让我适才平静如水的心忽然恐慌起来。这是通往学校的必经之路,我必须跨过这团火。
穿过稀薄的晨雾,慢慢往前靠近,火的样子愈来愈清晰。火越烧越旺,爆裂的响声在我耳畔响起。在走近火的那一刻,我忐忑的心忽然安静了,火营造出的肃穆庄严感在我心底弥漫开来。久久地盯着燃烧的火焰,我仿佛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在火里舞蹈着。百年来,每当村里有人过世,他在世时睡过的稻草席就会被搬到池塘边的三岔路口点燃,直至燃烧成灰烬。睡过的床板会搬到“哗哗”流淌的禾水河里浸泡。不远处一声悲戚的鸟鸣让我从遥远的思绪中抽离出来。再次瞥了一眼燃烧的火焰,恐慌迅速袭来,我拔腿往学校跑去。早自习结束后,我回家吃饭,经过池塘时,看见灰旧的稻草垫已燃烧成灰烬,零星沾染着晨露。水波荡漾的池塘边,宏德叔正挎着竹篮子,手握镰刀在割猪草。目光相迎的刹那,他咧嘴朝我微微一笑。
回到家,刚踏进门槛,母亲告诉我村里的铁匠去世了。她叮嘱我下午放学直接去铁匠叔家吃流水席。
彼时,年幼的我懵懂不知。五年后,屋外寒风呼啸,我年近八旬的玛奇奶弓着身子如一尾虾般去菜园子里浇菜时,不小心摔倒在地,骨头发出“嘎吱嘎吱”破碎的声音,从此卧床不起。两个月后,玛奇奶安详地闭上了眼睛。玛奇奶去世的那天清晨,我看见年近五旬的宏德叔扛着玛奇奶睡过的稻草席,一步步走到水波荡漾的池塘边,走到那个熟悉的三岔路口。万物凋零,路旁的树木光秃秃的,田野一片肃杀。
晒干的稻草编织而成的草席,弥漫着泥土的气息。稻草护佑着人的一生,它帮人抵御饥饿和寒冷。玛奇奶睡了多年的稻草席是她亲手编织而成的。稻草是她从种植了多年的稻田里一根根挑出来的。那些在烈日的暴晒下,变得柔软、充满韧劲的稻草成了她的首选。宏德叔把沾染着岁月尘埃的稻草席放在脚下,望着一望无垠的水波,从裤兜里掏出一根劣质香烟,缓缓点上,神色凝重。我看见因为过度劳累而鬓边发白的宏德叔贪婪地吸了一口烟,而后蹲下,掏出打火机,把稻草席点燃。一阵晨风袭来,火舌贪婪地吞噬着干燥的稻草席。火寂静地燃烧着,一旁寂静的水倒映出宏德叔疲惫的身影。
邻近池塘的三岔路口是生与死的路标。一辈子从未离开过村庄的村里人对村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了如指掌,他们在村庄里行走自如,永不会迷路。在村里人眼里,三岔路口是人世通往彼岸的路标,燃烧的稻草温暖他们前行的路,有了这个路标,逝去的亲人归来就有了方向,出走也不会迷路。
记忆中的那天,深冬温柔的阳光抚摸着大地上的一草一木。祖屋里人影憧憧,在宏德叔的吩咐下,我颤抖着双手,心底颇有排斥地把玛奇奶睡过的一块块床板叠在一起,而后扛在肩上,步履匆匆地朝禾水河岸走去。扛着一块块床板,仿佛扛着玛奇奶枯槁的身躯。我加快步子,急于摆脱它们。在即将抵达岸边时,我忽然疾步跑到岸边,一把把肩上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床板摔到了禾水河里。一块块床板撞击在一旁的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有一块拦腰断成两半,其余的都顺利落入水中。床板断裂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仿佛玛奇奶摔倒时骨头碰撞在一起发出的“嘎吱”声。我不敢把一块床板断裂的事实告诉宏德叔,只能偷偷把它们扔到了水中央。看着断成两段顺水而下越流越远的床板,我脑海里浮现出玛奇奶的身影,心底忽然隐隐感到一丝恐慌和内疚。
午后,我看见宏德叔把禾水河边浸泡了一个上午的床板搬回到祖屋前的那块打扫干净的空地上。在烈日的暴晒下,湿淋淋的床板很快晒干了。那一晚,我做了一个噩梦,睡梦中有人忽然把我推进无边的深渊里。我拍打着双手,使劲挣扎时,玛奇奶忽然出现在我眼前。“你为什么摔断我睡了这么多年的床板?”玛奇奶质问我,她面容模糊。我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在即将被深渊吞噬的那一刻,梦戛然而止。我大汗淋漓地醒过来,望着窗外如水的月色发呆。
薄暮时分,我看见宏得叔在院落中央架好干柴,而后擦亮火柴,点燃。在夜风的吹拂下,火越烧越大。玛奇奶生前的贴身衣物被宏德叔一件件扔进了熊熊燃烧的大火中。他一边烧,一边念念有词,像是在为渐行渐远的玛奇奶祈福。在故乡,每个人离去后,亲人们都要在他出殡前,把他生前的衣物、稻草席以及睡了一辈子的床板在特定的地方烧给正奔赴在黄泉路上的亲人。他们担心亲人在那边饥寒交迫,流落街头。
次日,刺眼的阳光下,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沿马路而下。玛奇奶葬在离村庄三里地的涌口。涌口,是祖辈的栖息地。山间的清泉从石头上滑过,沿着窄窄的小溪,流到山脚下,在山脚的土井里汇合。溢出井边的水在附近不停打转,在时间长久的腐蚀下,形成一个大水塘。鲜活的生命在时间的过滤下只剩下记忆的骨殖,在发黄的族谱上,白纸黑字,我看到了祖辈的足迹。道光癸卯年间,天祖父路过涌口,见这里青山环抱,泉水清澈,成群的鸭子自由地嬉戏,顿觉是风水宝地,迅疾在这里置下两亩地,以作百年后的归宿。宏德叔与我家同宗,他的祖辈也埋葬在此。天祖父曾经开着一家名为“泉水塘”的药店,在文竹村方圆十里都颇为有名,他乐善好施,每遇大旱便施粥舍米,周济穷人。每有穷苦人家过来抓药,他只收半价的药钱,再送对方一小包红糖。先辈生活上的富足映衬出儿辈的落魄和窘困。
一个月后,这些床板放置在宏德叔自己睡的那张床上。他天天睡在上面。床板断裂的事,我未曾向任何人吐露,它成了我的秘密。时间流逝,年少时莽撞扔床板入河的点滴内疚慢慢生根发芽,在我心底变成一种挥之不去的罪恶感。清明时节,我总会在玛奇奶的坟墓前插上三根香,默默鞠躬,为自己年幼时的鲁莽和不敬致歉。
2
死亡的巨石砸入村庄这口寂静的深井里,惊起阵阵浪花,迅疾复归于平静。
玛奇奶的生命之火已经熄灭,属于宏德叔的生命之火依旧熊熊燃烧着。日复一日的劳动造就了宏德叔高大结实的身板。玛奇奶下葬后,宏德叔又恢复了他忙碌的生活节奏。年近五旬的宏德叔正值壮年,仿佛一团正在熊熊燃烧的大火。炽热的火烘烤着生命的阵阵寒意,寒意不断入侵,却一次次被生命之火吞噬。
夜幕缓缓降临,村庄被一股稀薄的白笼罩着。
黄昏,晚霞染红了半边天,村庄里炊烟袅袅,锅碗瓢盆撞击在一起发出的声音仿佛夜的序曲。只有夜幕降临时,忙碌了一天的宏德叔才是悠闲的。我们一群小伙伴围着宏德叔。宏德叔变魔术般,从裤兜里掏出各种各样山上的野果子分给我们吃,乌米饭、火棘果、五味子、拐枣等,我们吃得津津有味。这些带着山野气息的果子是宏德叔上山砍柴时采摘的。
宏德叔每天像陀螺般飞速旋转着。他喂猪、放牛,赶着一百多只水鸭在水田里奔跑。他养了四头黄牛、八头猪、三十多只鸡以及一群水鸭子。饲养这些家禽需要大量的柴火与猪草。他细心呵护着这些家禽,像是呵护这个家庭的命运,他把大半的时间花在了砍柴与割猪草上。
卑贱的草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草,在禾水河的滋润下,匍匐在村庄的各个角落,它们低调,卑微,不张扬。村子中央那个水波荡漾的大池塘边是青翠欲滴的菜园子。池塘的浅水边长满了各种嫩绿的草。马齿苋、鱼腥草、车前草,这些弥漫着中药气息的草成了猪和牛最喜欢咀嚼的食物。有几次清晨,挎着篮子割猪草的我与同样来割猪草的宏德叔迎面相遇,翠绿的猪草已经盛满了他的竹篮。池塘边的各类草儿割了又长,长了又割,一夜之间又长回当初的模样,仿佛带着某种魔力。
一根根干柴在细小火柴的点燃下迅速燃烧,发出噼啪的响声。宏德叔用一根根柴火引燃生活的激情。
天微微亮,宏德叔就起床了。擦亮的火柴迅疾点燃灶台里的松针,柴在幽暗中发出窸窣爆裂的响声,仿佛清晨的序曲。他把三四个红薯扔进火堆里,不久,一股诱人的香味弥漫在屋子里。随着“嘎吱”一声响,沉重的木门被拉开,黑夜中露出一张模糊的脸。猪食和牛食煮熟煮透后,宏德叔就拿着扁担出发了,红薯、馒头等干粮放在白色饭盒里,拴在扁担的一头,他裤腰的行军壶里装着一斤烧酒。走进浓浓的晨雾里,瞬间不见人影,只听见他的咳嗽声。
出了家门,左拐,上了那条黄泥路,一直往前走六七里,就到了涌口。那条通往山间的小路满是宏德叔的足迹,蛇一般蜿蜒曲折的小路像极了他一生的命运。
过了涌口,再往右拐,一直往前走,就是文竹林场了。林场的房屋后面是一望无垠的山野,山上种满了密密麻麻的茶子树。初春时节,茶子树开满了茶花,远远望去,白茫茫一片,闪烁着一股灼人的白。林场的人大都认识宏德叔。林场有一口不大不小的池塘,草鱼、鲫鱼在水中游来游去。几十头猪和牛分布在林场的猪圈和牛圈里。林场周边种满了桃树,初春时分,红艳艳的桃花格外耀眼。
每次靠近林场,那些旧时光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阴霾吞噬了头顶的阳光。20世纪60年代,成绩优异的他日夜在为高考准备时,作为知识青年,他被下放到离故乡文竹比较近的林场。在林场,像是要发泄内心的苦闷,宏德叔一头扎进了无边的农活里。他是干活的能手,给农作物锄草,给果树喷药,插秧,收割稻谷,样样拿手。他不再是文弱的书生,肤色变得黝黑,弥漫着大地的色泽,干农活时紧握镰刀的他有如神明附身,整个人仿佛脱胎换骨一般,无比娴熟。
闲下来时,他最喜欢去十几里外的深山老林里砍柴。林场鸡鸭成群,猪牛成圈,几十个工人一日三餐的伙食都需要用到大量的柴火。他被林场派去山间砍柴。他酷爱砍柴,走在寂静的山林里,山风在耳边呼啸,静听着风的声音,他苦闷的内心在山野间得到了抚慰和释放。山间摇曳的花朵、清脆的鸟鸣、哗哗作响的树叶、淙淙流淌的水声,都让他的心变得无比安静。农场的生活经历给了他不一样的生命感受。
很快,一个电话改变了宏德叔的命运:因为在林场工作突出,他被调到县城新建的化肥厂做工人。接到通知的那一刻,宏德叔沉寂多年的心被点燃了,一团无形的火在心间燃烧起来。在通往县城的路上,温暖的阳光透过车窗落进眼底,他感到一股久违的温暖。然而上班不到一周,一个电话,他就被退回了林场。他的名额被村委会的人的亲戚给挤掉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从县城回到林场的,面对同事们好奇和不解的眼神,他选择了沉默。内心深处那团好不容易燃烧起来的火瞬间就熄灭了。他经常借酒浇愁,砍柴时腰间挎着一壶自酿的米酒进山,喝醉了便躺在落叶堆积的山顶酣睡,温暖的阳光落在他粗糙的脸上。酒醒之后已是薄暮时分。稀薄的夜色里,他挑着一担近一百五十斤的柴火,在山间的小路上健步如飞。
3
宏德叔踽踽独行在山间小路上的身影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睡意未消的我默默跟在宏德叔身后。晨雾弥漫村庄,仿若仙境。长途跋涉,抵达山间时,太阳正探出头。我们早已浑身湿透,山风呼啸,树叶哗哗作响,风裹着丝丝寒意由远及近袭来。站在山顶,山下村庄的一景一物尽在眼底,炊烟袅袅,农妇在禾水河边浣洗衣服,幼童牵着水牛缓缓朝田间走去。我蹲在一块鹅卵石上喘息的片刻,看见父亲和宏德叔各自拿出腰间挂着的酒壶,而后扬起头,喝了一口家里自酿的烧酒暖身。锋利的柴刀在晨曦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宏德叔手持柴刀走进了荆棘丛中。
杉木、樟木、楠木、桃树、梨树、松树密密麻麻、疏密有间地分布在山间的各个角落。这些是村里的保护树木,不能随意砍伐。他们把目标放在了枯枝干柴上。干柴轻,易燃,耐烧,适合做柴火。山间遍植着松树,松树割裂的伤口流出的松脂沿着树干流到挂在树半腰的白色塑料袋子里。我曾见过割松油的人拿着一柄磨得闪闪发光的弯刀,一刀刀朝松树砍去。刀落在树身上,树震颤着,松叶簌簌而下。树的震颤声仿佛垂死挣扎时发出的最后呼救。山上的松木害上了一种罕见的松毛虫病,林场的人也束手无策,枯死了一大片。父亲用砍伐回来的松木做衣柜、做床板,卖给即将嫁女儿的乡里人。
时歇时停,日头慢慢往上移,柔和的光线变得毒辣,细密的汗珠爬满额头,砍完柴已近中午。宏德叔通常会把带来的红薯和馒头当作午饭,塑料瓶里装着从山脚下打上来的清泉水。树叶落了厚厚的一地,弥漫着腐朽的气息,饭后,我们躺在厚厚的叶子上休憩。阳光透过叶的缝隙落在身上,阵阵凉风不时袭来,疲惫仿佛长了脚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午睡醒来,阳光正烈,宏德叔缓缓抽完一根烟,默不吭声,仿佛深陷在无边的思绪里。抽完烟,挑着一百三十斤重的干柴下山。走在山野间的小路上,肩上的扁担伴随着均匀的步履上下震颤着。他不时坐在山间的石头上喘息片刻。两个小时后,当他把弥漫着山野气息的柴火放在院落里时,他已浑身湿透。宏德叔深谙山间一草一木的作用,他用捡回来的松针引火,一簇簇细小微弱的火苗慢慢起死回生,迅速摆脱奄奄一息的状态,转眼间就变成了大火。他用松油做成松油灯,放在院落的长柜子上,上面放着玛奇奶的遗像。夜风袭来,松油灯左右摇曳着,玛奇奶的面孔在夜色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宏德叔把松油灯放在睡觉的房间里,起夜时就擦亮火柴点燃,一路提着它。忽明忽暗的松油灯让院落里的夜色弥漫着一股神秘的山野气息。他会请我父亲帮忙,把一些从山上捡回来的上好的木头做成衣柜、床头柜、饭桌等家具。山的气息就这样融化在房间里的一桌一椅间。
秋去冬来,寒风乍起时,宏德叔又忙碌起来。他在山脚下的斜坡上挖一个简易的炭窑,把一根根劈好的柴放入炭窑中。年幼的我站在一旁看着宏德叔忙碌的样子,几近痴迷。燃烧的火焰映衬出他眼底的光。浓浓黑烟通过炭窑上端的几个孔冒出来,朝天际飘去。当炭火的烟量渐渐变得稀少,缝隙里冒出的烟颜色发青透亮,宏德叔开始封窑,他乌黑的脸上露出兴奋愉悦的表情,眼底满是期许。宏德叔烧制的木炭耐烧、经用、无烟。他把烧制好的木炭拿到墟上去卖,在众人的夸赞声里,他如沐春风。一个冬季下来,宏德叔能烧近千斤木炭。腊月时分,他们一家围坐在炭火旁烤红薯。不远处的厨房里,燃烧的柴火,火焰通红,煮熟的猪食冒出的阵阵热气,把锅盖不断顶起来。这一幕长久地回荡在我的脑海里,多年后的今天依旧清晰如昨。
4
时光从手指缝间溜走,随着枯黄的落叶坠落在地。随着三个儿子娶妻生子,宏德叔慢慢苍老下来。过度的劳累让他的腰弯曲成一张弓。
炊烟是一个乡村的符号。没有炊烟的村庄不是一个真正的村庄。当村里人过起便捷的现代生活,柴火慢慢绝迹,一个乡村的炊烟便越来越少。宏德叔一辈子都在制造炊烟。当村里的炊烟渐渐消失,宏德叔家屋顶的炊烟便凸显出来。站在山顶,能清晰地看见缕缕炊烟透过瓦片的缝隙缓缓朝天际飘去。
炊烟的存在,暗喻着一个人对古老生活方式的坚守。科技的飞速进步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便利。宏德叔依旧踽踽独行在山间小路上。他时常选择夏天快结束时或者深秋时节,频繁地上山砍柴。作为资深的砍柴工,他深谙山林的秘密。盛夏时节,烈日的暴晒下,木材的水分蒸发,变得很轻。秋收时,经过一年的风雨侵袭,枯木很多。这两个时节是上山砍柴的最佳时节。竖耳倾听,他仿佛听见季节的召唤声,来自山间树木体内细微的爆裂声。这种声音他如此熟悉,仿佛多年前的黄昏,年迈的玛奇奶摔倒在地,身子骨落在坚硬的石头上,发出的“嘎吱嘎吱”的破碎之声音。他循声赶来,迅速把摔得鼻青脸肿的玛奇奶抱起。玛奇奶已经轻得像一把晒干的稻草。
他对柴火的过度依赖,让习惯了都市生活的儿孙们产生了极强的排斥心理,以至于到最后纷纷远离,自立门户。盛夏,屋外烈日高悬,他弓着身子蹲在灶台旁烧火做饭。厨房里异常闷热,柴火燃烧的浓烟弥漫在整个房间。他从烟雾里走出来,露出一张大汗淋漓的脸。待烟散去,厨房的轮廓复归于清晰,阵阵凉风袭来,他正躬身坐在灶台旁的小凳子上,盯着燃烧的火焰默默抽烟。适才厨房的闷热映衬出此刻阵阵凉风的舒适。
显然,他对柴火的依赖没有随着自己身体的日渐苍老减轻,反而变得愈加浓重起来。他依然隔三差五去几十里路外的山上砍柴,只是每次背回来的柴火由当初的一百三四十斤变成了七八十斤。沉重的木柴压在他日渐衰老的肩膀上,他步履维艰。但弥漫着山野气息的柴已融入他的生命里,他不甘心放弃。
一次上山砍柴,准备下山的途中,天空忽然乌云密布,随之下起了瓢泼大雨。他挑着柴火趁雨水还没降临之前,疾步走到山间的亭子里。到亭子里刚坐下,漫天的雨就下起来,一双无形的巨手把密集的雨珠织成一道细密的雨帘,山野间顿时一片迷蒙。雨雾笼罩着山川与河流。骤雨初歇时,宏德叔挑着木柴又上路了。走到半山腰,他踩在湿润的泥土上,双脚打滑,一个趔趄,整个人摔了个底朝天。一根木柴锋利的一端险些戳进他右眼中。他的额头磕在被草丛覆盖的一块石头上,瞬时渗出鲜血来。他忍着疼痛,咬牙把柴火慢慢往回挑。那些欢愉的时光浮现在他脑海里,他挑着沉重的木柴在山间的小路上疾步如飞。村里人看着他矫健的身子心底暗暗佩服。他挑着柴,在稀薄的夜色中回到家里。夜色暂时掩盖了他额上的伤口,但在屋内昏黄灯光的映射下,他的老伴还是发现了。老伴进屋拿来红花油,默默给他涂抹上。饭后,他默默进了房间。这一夜,在林场上班时的那些时光又浮现在他的梦境里。
歇息调整了一段时间,不顾家人的劝阻,宏德叔在晨曦中又上山砍柴了,这里有他熟悉的一草一木,有他的山野和清风,还有他远去的青春时光。
5
一棵棵鲜活的树移植到异乡的马路上,在暴雨、台风中,在烈日的炙烤下,有的伤痕累累,有的被连根拔起弃之一旁,有的变成一根细长的干柴,等待着最后一团火的燃烧。
更多的火焰熄灭在异乡的路上。宏德叔无法预料,他多年来小心翼翼呵护的那一团团生命之火,会瞬间熄灭在异乡的路上。
宏德叔的小儿子昌海比我大十岁,那一年在深圳一个五金厂工作时,与一个1988年生的小伙子发生口角。本以为这件小事已经过去,没想到次日下班后,这个小伙子找来同在工厂上班的父亲找他算账。三个人围在一起还没说几句,很快就厮打在一起。昌海被打得肾脏破裂,造成肾脏急性衰竭。经过七天七夜的抢救,还是束手无策,昌海的生命只剩下一丝微弱的喘息。宏德叔和大儿子连夜赶到深圳,雇上一辆急救车,把只剩下微弱呼吸的小儿子从深圳拉回了老家。要死也不能死在外面,不能成为孤魂野鬼。昌海奄奄一息,他哥哥匆忙跑到附近一百米的镇中心小学,把昌海正在上一年级的女儿叫回家。昌海的女儿小银子跑进屋,看着奄奄一息的昌海,惊恐地叫了一声“爸爸”,昌海嗫嚅着嘴,扭过头看了女儿一眼,吐出一口血来,头慢慢耷拉了下去。
昌海睡了多年的稻草席早已换成席梦思床垫,衣柜里存放着的一件件衣服已沾满细小的灰尘。这些曾经弥漫着他的气息的衣服早已过时,每次到年根,他都会带几件弥漫着城市气息的衣服从异乡归来。衣柜成了摆设。柔软的席梦思床垫只能供他睡几天。
众人深陷在悲伤中时,宏德叔转遍了小镇上的集市,才在一个偏僻的小店里买回来一张稻草席。透过人群的缝隙,我看见年过六旬的宏德叔把昌海抱到了稻草席上。众人眼里可有可无的稻草席,在宏德叔眼里却不可或缺。这是贴身之物。席子,意味着一席之地。我慢慢理解宏德叔坚持烧一床昌海睡过的稻草席的意义。他期望这个比自己先走的儿子在世界的另一端能有自己安睡的地方。
不知从何时起,池塘边燃烧的草席,禾水河里浸泡的床板,这些村里曾经流行的丧葬习俗渐渐消失。曾经清澈无比的广阔池塘已经填成平地,曾经水波荡漾的禾水河已经污浊不堪。城市的气息无孔不入,村里人用来垫床板的不再是草席,而是带着工业气息的席梦思床垫。
晒干的稻草堆积在宽敞的稻田里,深秋时节,在火的点燃下,稻草迅速烧为灰烬。面对一亩亩撂荒的土地,村里人不再像几十年前那般把一捆捆湿漉漉的弥漫着晨露的稻草置放于烈日下暴晒,而是捆成一捆捆,再垒成碉堡状,等待深秋结束时开着大卡车的司机来收购。晒干的稻草可以做成草席、草帘等草类制品。
村里那块几十年来带着浓重隐喻色彩的三岔路口,也被一栋栋的洋房淹没,无迹可寻。那些疾病缠身,像一颗钉子般留守在村子里的老人,在孤寂中煎熬着。他们的儿子与儿媳常年在外讨生活,儿子与儿媳曾经睡着的床铺早已落满灰尘。草席在村里的三岔路口燃烧时的图景,我只能在记忆的深井里打捞。
年幼时的情景再次重现,夜深了,我跟在宏德叔身后,来到村口马路边的三岔路口。远处的灯火在夜风的吹拂下左右摇曳,月光洒落在路面上,泛着白光。宏德叔把还是九成新的稻草席摆放在三岔路口的空地上,月光映射出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掏出打火机,稻草席在暗夜里迅速燃烧起来,火蛇吞吐着芯子,火焰随着夜风微微摇摆着。宏德叔从一旁拾起一根树枝,不停地敲打在路面上,嘴里念念有词,他的手微微颤抖着,面无表情。面向燃烧的稻草席,我和宏德叔深深地鞠了三躬,而后又跪拜在地,磕了三个响头。
转身离去的刹那,燃烧的稻草席很快变为灰烬。亮光复归于黑暗。一辆汽车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的刹那,司机探出头满是疑惑地瞥了我们一眼。
三岔路口多了车流的喧嚣,少了往日的安静与河流的相伴。
这一年年底,父亲正在深圳世界之窗的一个工地上做木工,我陪着母亲在省城南昌的人民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复查身体。在弥漫着福尔马林气息的走廊上,看着从门诊室走出来的母亲脸上舒展的笑容,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身患子宫内膜癌的母亲终于走出了死亡的阴影。薄暮时分,我和母亲回到了村子里。清澈的天空显得空旷悠远,晚风带着一丝凉意。母亲坐在院落的老板凳上休息。这个板凳是父亲十多年前用宏德叔从山上砍下的木头做成的。来不及生炉子,我在院落里劈柴,而后生火煮饭,看着缕缕升起的炊烟缓缓朝天际飘去,看着母亲平静的面容,一股重生之感忽然在心底流淌开来。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缕炊烟,缕缕炊烟在流逝的时光中,在我心底呈现出复杂的意义。
6
生老病死的圆圈,优美的弧度,首尾咬合,这是亘古未变的宿命,世人无法逃出。时光飞逝,2017年年底,一天晚上,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宏德叔被查出肝癌晚期的消息。回到家,我提着一箱牛奶和苹果去看望病中的宏德叔。疾病的侵袭下,曾经身强体壮的宏德叔瘦得变了形,他颧骨突出,肩胛骨深深地凹陷下去,打皱的皮肤牵扯着一身的骨头。疼痛不时向他袭来,他一只手捂着右腹部,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床头柜上的那碗米饭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一只苍蝇在半空中飞舞着。曾经的宏德叔砍柴归来一口气能吃下三碗饭,一粒粒白米饭迅速被征服,吞入口中,化成他的精气神。现在,躺在碗中的米饭一直在等待着被宏德叔吞入口中,却迟迟得不到回应。一粒米饭从口到喉咙的距离曾经近在咫尺,如今却遥不可及。疾病让一切事物变得模糊、遥远起来。
宏德叔睡在老屋最里间的暗房里,一阵风透过窗户吹进来,案上放着的那盏松油灯左右摇曳着。从山间的松树上捡回来的松脂油,他依然使用着。松油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熟悉的气味让他仿佛回到了广阔的山林。一生的时光在他眼前一闪而过。看着在夜风中摇曳的松油灯,他仿佛看见了自己即将熄灭的生命。
他渐渐老得像一根枯萎的柴,在疾病的折磨下,身体变得越来越轻。就像当年每次上山砍柴时,他总会先选择枯柴。年尾时分,树木经过四季的轮回和一年的暴晒,体内的水分慢慢干涸,木柴变轻变脆。枯柴易燃,容易被火吞噬。就像年迈步入寒冬的生命,骨头变得疏松,肉身变轻,轻易就会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生命的火焰在经过一世的燃烧后,慢慢趋向终点。
“宏德叔怕是没几天日子了。”黄昏,村里人聚集在村后的那块空地上议论纷纷,一生卑微如草、沉默寡言的宏德叔成了村里人关注的焦点,一个人的死惊醒了沉睡的村庄。
“宏德的病都是累出来的,可怜呢!”住在宏德叔隔壁的老人说道。
“砍那么多柴干吗?现在人死了,柴还没烧完。哎!”村里的木头叔说道。
次年夏天,宏德叔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在剧烈的疼痛中闭上了眼睛。临近生命的终点,宏德叔不停地咳血。
宏德叔临死前的场景从春兰婶口中吐出来,仿佛一块巨石,砸入寂静的湖里,惊起阵阵巨浪。春兰婶在我们那个巴掌大的村里因为乐善好施而颇有威信。
宏德叔临死前那一分钟一直努力张着嘴看着他的大儿子春春。春春知道他还有话说,俯身细听。“柴——柴。”气息渐弱的宏德叔用瘦骨嶙峋的手指了指天花板,使出口中的最后一口气说道。宏德叔的气息愈来愈弱,他躺在大儿子春春的怀抱里。有那么几分钟,他一动不动,正当家人以为他已经离去时,他忽然又艰难地睁开眼,对春春说道,等龙龙满月时,烧那些柴。宏德叔的最后一句话永远停在了“柴”这个字上。他艰难地说出这句话,而后在胸口一阵剧烈地起伏后,闭上了双眼。
“宏德叔临死还在惦记着他砍的那些柴,惦记着他刚出生不久的孙子龙龙啊。”春兰婶感叹着。
看着亲人们把宏德叔从床上抱进漆黑的棺木里,我又看见了那一块块熟悉的床板,那是玛奇奶睡过的床板。十多年过去,在时间的浸润下,这些床板弥漫着灰旧的色泽。床板上铺着的稻草席已经破旧不堪,有几处磨损成洞。这是一张睡了许多年的稻草席,宏德叔一直坚持着没把它换掉。
薄暮时分,我看见宏德叔的大儿子春春抱着这张破旧的稻草席来到了马路边的三岔路口。春春没有用打火机点燃草席,他手里攥着宏德叔生前一直用的火柴。“扑哧”一声,灰旧的稻草席瞬间被点燃,很快就烧为灰烬。
“要是能在池塘边烧就好了。我爸他喜欢水,以前经常去池塘边割猪草。”春春叹息了一声,如水的月光映射出他那张疲惫忧伤的脸。
按照村里的习俗,宏德叔的葬礼摆了三天的酒席。丧宴用的都是宏德叔生前砍回来的柴火。我站在门槛前,望着院落里的一堆堆木柴发呆。在宏德叔大儿子的要求下,亲朋好友把宏德叔生前在山上砍的部分柴火从暗房里搬了出来。柴火堆满了大半个院子。喧闹的酒宴映衬出死者的孤寂,一边是生者大快朵颐的狂欢,一边是死者家属的悲伤与痛苦,命运呈现出荒诞的一面。
丧乐弥漫在房间里,宏德叔静静地躺在一副宽大的楠木棺材里。这是他大儿子花了近五千块钱购置回来的。
夜,黑色幕布般降临大地,饭后,村里人渐渐散去,远处近处的灯火渐次亮起。与宏德叔相熟的人还停留在院落里。我跟着父亲和母亲围坐在院落那团燃烧的柴火前,脑海里浮现出曾经和宏德叔上山砍柴的情景。宏德叔挑着一百多斤的干柴一摇一晃地行走在山间小路上,背影忽远忽近,模糊而又清晰。
夜深了,带着些许凉意,村庄深陷在一股巨大的寂静中。宏德叔的大儿子春春把两根拳头粗的木柴投入火中,奄奄一息的火又重新熊熊燃烧起来,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仿佛在为宏德叔送行。按照村里固有的习俗,春春把宏德叔生前穿过的衣服一件件扔进火中。打着补丁的衣服迅速被火吞噬。
次日,在县城位于后山的殡仪馆,三号炉的火化工面无表情地把宏德叔推进了火化炉中。宏德叔双眼紧闭,嘴巴微张,仿佛睡着了一般。推进火炉的刹那,宏德婶忽然拉住宏德叔的腿,又撕心裂肺地哭起来。众人掰开了宏德婶的手。很快,我看看火化工娴熟地按了下按钮,熊熊燃烧的火焰瞬间就把宏德叔吞噬了。屋外的烟囱里冒出阵阵白烟,缓缓朝天际飘去,仿佛宏德叔生前制造了一辈子的炊烟。
火化到中途,透过那块小玻璃窗,我看见火化工用长长的钳子翻转着宏德叔已经火化过半的身体。这一幕让我的心头一紧,我迅速退了出来,怔怔地望着湛蓝的天空。又过了半个小时,火化工推出一铁盘冒着阵阵热气的骨灰。宏德叔化为了灰烬。
一棵在凉风中“哗哗”作响的树,如此鲜活,它终究要变成柴,燃烧成烈焰,变为灰烬。每一个过程都弥漫着生命的挣扎与抵抗。
人何尝不是一根柴。
这年年底,多年未见雪的故乡下起了大雪。雪,纷纷扬扬,在半空中飞舞着。看着雪,我脑海里又浮现出多年前的薄暮时分,窗外雪花纷飞,宏德叔一家围坐在柴火旁,一边烤火一边吃猪肉炖黄豆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