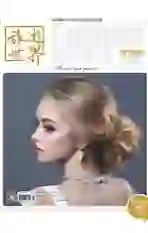苗银,穿着身上的苗族符号
2021-11-12雷虎
雷虎
提到苗族,每个人眼前都立马会浮现出一幅景象:美丽的苗族姑娘身着盛装款款走来,别在五彩苗服的银饰叮叮作响。华贵的银饰反射着太阳的光亮,让光彩夺目的苗女宛如鲜花盛放。
在众人眼中,苗族是个美丽而神秘的民族,而民众对于苗族的第一印象,则来源于那些佩戴在苗女身上的银饰。以往,在苗人生活中。苗银集巫术的神秘和货币的实用为一体,而如今,苗银则已经变成苗族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变成穿戴在身上的苗族文化符号。
在新时期,苗银已经自我调整,找到了新的自我定位。而那些曾经是苗寨标配的苗银银匠呢?在机械化和城镇化双重“围剿”下,他们该何去何从?
消失的苗寨和隐身的银匠
行走在凤凰古城街头,看着那些顶着苗族银饰扮苗女的姑娘,同行的摄影师也沦陷了。虽说明知道沱江边出租的苗服和苗银风格属于贵系(贵州)苗族,但是依然租来扮苗女。
“为什么凤凰本地的苗服和苗银都是现成的,凤凰人却舍近求远用贵州苗饰来充数}”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坐上了乡村巴士,前往凤凰县城19公里外的山江镇寻找答案,因为山江镇是凤凰最大两个苗族聚居地之一(另一处为腊尔山镇)。这里,是湘西末代苗王龙云飞的发迹地,有集苗族民居精华的“苗王府”。更重要的是,这里减着湘西苗银世家麻氏家族的最后传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苗银项目传承人麻茂庭。
车出凤凰县城后就一直在山里蜿蜒前行,随着时间的推进,路两旁的“苗味”渐浓:路边的村寨渐渐出现了青砖灰瓦的老屋,坐在屋门口晒太阳的老妇身着苗衣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车辆在一个小镇的叉路口停下,车上的人全部下车了,但是我却不肯走,直到司机提醒我三江镇到了,我才不情愿的收拾行李下来。因为眼前的景象与我心中想象的“凤凰最后的苗寨”相去太远——钢筋混凝土堆砌起的高楼沿山而建,两条狭窄的街道如蛇一般在水泥森林中游走,而我现在就站在这两条路交汇的丁字路口,眼前的景象与汉地的小镇没有任何区别。我不甘心,沿着两条路溯源,我心存幻想,但我的希望再一次破灭,我沿着两条路甚至走出山江镇了,路两边的景象依然和眼前一样——虽然这里是湘西最大的苗族聚居地,99.9%的居民都是苗族,但是苗寨消失了。唯一让我感觉有一丝苗味的,是我看到了唯一一家苗银店——“麻茂庭苗银铺”,但是银铺已近关门,从里面的陈设看来,这银铺已经很久没有开张了。
看到关门已久的麻氏银铺,摄影师慌了:“那打苗银的银匠不会已经不干了吧}”带着同样的疑问,我拨了银匠麻茂庭的电话。麻茂庭的回答让我悬着的心落地了:“我正在打银,没空去接你,你自己过来吧。下车后你看到旁边有个小巷,穿过小巷隔着稻田看到山坡上的苗家就是我家了!”
我在麻茂庭的指引下穿過狭窄的小巷。小巷并不幽长,行过十几米就到了尽头。小巷的尽头是一片新月型的稻田。稻田的尽头是一座矮山,有几栋青砖灰瓦的苗居隐藏在稀稀拉拉的树丛中——这儿便是银匠麻茂庭的“藏身地”了。
手艺家族和苗家村寨
从田埂边上的水泥路绕到矮山边上,矮山上的民居倒还有几分山寨气象:沿着山脚用石块砌起高墙,几户民居就立在石墙之上。石墙只留有一条石阶上山,石阶旁边有一不知名的古树,古树下坐着一位身着苗服的佝偻老人。见到有生人走近,一条黄狗从石墙上探出头狂吠,吠过之后还觉得不过瘾,于是站在石阶上方和我们对峙。颇有“一狗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我们向老人打听麻茂庭家地址,但是老人似乎听不懂普通话,于是我指了指老人手上的银手镯,做了个抡锤打银模样。这时老人才回过神来,指了指山寨最靠边的那一栋民宅。
我们踏上三级石阶,推开了麻茂庭家院子虚掩的门。进门后是一个别致的小院,地上铺了一地的枯叶,有两个小孩在院子里嬉戏。院子里有持续而有节奏的“咚咚”声回荡,想必那就是麻银匠在打银了。
银匠家是一栋外面用砖头砌、里边用木头衬的传统苗居,和传统的徽州民宅有几分相似。打银声从房子的角落传出:那是在房子楼梯拐角处,一位清瘦的老人一手拿着火钳,一手抡着铁锤正在作业,嘴上叼着的烟随着老人的呼吸一明一暗。老人看到我们之后示意我们坐下,自己把手上的银器打完后,洗了把手后径直上楼拎了一个红布包下楼。老人把红布包往八仙桌上一摊开,整个屋子立马“蓬荜生辉”了:各式各样的银戒指、手镯、头饰一下子让这偏远苗居变成四十个大盗的藏金洞。
麻茂庭说,他只是个打银匠,自己并没什么故事可讲。如果说真要讲故事,那就得从这个村庄和这些老银饰的历史说起:
麻茂庭家是湘西有名的苗银世家,麻家的苗银传到麻茂庭手上,已经是第五代了。麻家打银的历史,应该从麻茂庭爷爷的曾祖父说起。麻茂庭点燃一支烟后进入了回忆模式:“那应该是清朝中期的事情了!”
这一年,凤凰县三江镇来了一位挑着货架的游方银匠。那时,正好麻家要为将要出嫁的女儿准备嫁妆,就让游方银匠在麻家住下了。没想到银匠人技艺精湛,为麻家打出的银饰不仅让麻家人眼前一亮,更让整个山江镇的村民垂涎。苗民纷纷效仿麻家让银匠为将出阁的女儿打银嫁妆。于是,原本只准备在麻家住三个月的银匠竟然在麻家住了整整三年之久。因为麻家人对银匠非常照顾,银匠作为回报就收了麻家主人的儿子为徒。
在为全山江镇的苗民打造了银器后,银匠继续挑着货架游方去了。而麻家人却在山江镇坚守下来,农忙时封炉,农闲时操锤。最开始,麻家只为山江镇的苗民打制嫁装,慢慢地因为麻家人打制的银器精美绝伦。麻银匠的名气越来越大,周边苗寨的苗民也慕名而来,甚至有人以订制银器之名来偷师。但麻家人并不守旧,有人来学习打银,麻氏就欣然相授予,久而久之,山江镇慢慢成为了湘西的银器之乡。
麻家从事苗银制作的人多了,山江镇的市场容量不够大,有的族人就迁往附近的州县。最终,山江镇麻氏银匠的名号开始在周边的泸溪、古丈、吉首、花垣、辰溪等州县流传,麻氏家族也慢慢发展成湘西地区最大的银匠流派之一。
物质故乡和精神家园
一根烟抽完,苗银家庭的历史也从清代穿越到了现代。
“这就是银匠的现在了,全镇人都住上新楼房,但我房子还是结婚时起的木头房!”麻茂庭指了指自家的老木头房子,又指了指镇上那些新盖的高楼自嘲。以前银匠是苗寨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但如今,苗银艺人已经跟不上苗寨发展的节拍。
以前,银饰是苗族居家旅行必备神器,苗族订亲,头饰,披肩再穷也先送半套,另半套过门时必须付清。上世纪90年代,山江镇汉化的苗族开始拒绝银饰做彩礼:“我们已经汉化,不兴戴银了,直接送钱好了。”
因此,大批银匠失业,麻茂庭五兄弟,四个改行了。教徒十五人,十四个不沾银了。还好,麻茂庭手艺闻名乡里,虽说汉化凶猛,但山沟里还苗风犹存,麻茂庭一年还能接几单生意。在麻茂庭扛不住也准备放弃传了三百年的祖传手艺时,旅游兴起了,非遗评选也来锦上添花,他的银匠生涯柳岸花明了。他成为全国第一批国家级苗银传承人(湖南第一个,全国仅有的两个)。升级为国家级,名气大了,订单多了,却也画地为牢了——别家可以用白铜做银器,自己的银只能是纯的。
我们提出要拍摄苗银制作工艺,麻茂庭说不急,他带我们来到矮山上的苗寨,说只有我们看懂了这个“苗风遗存”的村庄才能更好的理解苗银。
他抚摸着村庄那青石垒砌的石墙说,湘西向来多土匪,因而传统的苗寨大多依山而建,都有自己的防御工程,而这石墙便是村子的“城墙”;又指石墙上那唯一的台阶说,这便是村寨的寨门。而寨门前那棵已空心的老树,则是土匪攻寨火攻时的杰作。
最终,麻茂庭在寨子的最高处停下了。村子的最高处是两处建筑,一处是一间已经坍塌的老屋,一处是类似烽火台一样的石头房。麻茂庭叼着烟和石头房相对无言。原来,这石头房子是苗寨的堡垒。而这老屋,正是麻氏银匠的祖宅。
以前,当土匪来了,村民们会把村里的贵重物品放在这堡垒中,然后在堡垒中做最后抵抗直至救兵到来。而银匠的家族作为寨子里贵重物品最多,威望最高的家族,他们理所当然选择了靠近堡垒这全村最安全的地方。
其实,苗族之所以有如此重的银饰情结,正是因为苗族从来都缺乏安全感,因而“安全”一直是苗族人追求的方向。苗族人起源于中原,但卻被迫迁徙到湘西、贵州、广西、云南等多山之地。这些地方是毒虫、瘴气多发之所,因此苗族很自然地对有鉴毒功能的银情有独钟。再加上苗地多战乱,战乱起时只能挑细软值钱的逃,而既能当饰品又能做传家宝的银器成了最好的选择。
参观完苗寨,我们也读懂了苗人和苗银的关系,麻茂庭这才回到自己的作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苗银匠人分为游方银匠和定点银匠两种,教麻家打银的银匠属于前者,麻茂庭属于后者。对于麻茂庭来说,山江镇这个名为黄茅坪的村庄,既是麻茂庭作为苗族人物质形态上的故乡,也是他作为手艺人精神意义上的家园,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
打银的艺人和看表演的猫
麻茂庭每天的生活都是从上午十点开始的。
他首先在熔炉中生起木炭,随着“呼呼”的拉风箱声响起,熔炉中很快就燃起青色的火焰。这时麻茂庭从炉子上拿起一个酒盅大小的铁杯,往铁杯中倒入些许平时做银饰的边角料后,把铁杯放进木炭中。这一步叫熔银,任何一种精美的银器,都是银在烈火中熔化后锻造而成的。
熔银是个漫长的过程。麻茂庭先用火钳夹了块木炭点了根烟,然后边悠闲的抽着烟边缓缓的拉着风箱。看到熔炉中的木炭燃起,一只黄猫鬼使神差地跳到炉上。于是一人一猫你瞪着我,我看着你,相对无言。你拉你的风箱,我烤我的炉火。
当铁杯中的碎银慢慢化成了红色的银浆时,麻茂庭从炉边的窗台上拿起一只空心的铁棍,铁棍的一头含进嘴中,一头插入银浆。看到这情景,趴在炉火上的猫立马从炉台上纵身一跃,跳到了熔炉边的木楼梯上。与此同时,铁匠憋足气后对着铁棍猛吹了一口气。瞬间,一串串火星从熔炉中冒出来并在空中四散飞舞,宛如银浆中减着一条金鱼一口气吐出了无数气泡。其实,飞舞的每一个火星都是碎银中隐藏的杂质——这个过程叫去杂,目的是把银浆中的杂质吹走。
在连续吹了三四口气后,银浆中的杂质就被去得差不多了。这时麻茂庭取来一个铸铁凹糟放在熔炉边,从煤油灯里往凹糟中倒入些许煤油后,用火钳夹起炉中的铁杯把滚烫的银水倒入凹槽中,当银水入槽后和槽中的煤油接触后立马燃起雄雄的火焰。此时猫正站在熔炉边的楼梯上炯炯有神地看着银匠,想必这猫正在做着白日梦,把眼前的银匠当厨师,正端着着火的菜锅烹调美味的烤鱼吧!
当火灭后,银匠用火钳把凹糟反扣在炉台上。掀开凹糟,一根细长的银条就出现在眼前了。银匠用火钳把凹糟放在地上后,就立马换手用左手架住银条,把银条转移到炉子边的木桩上,右手抡起一把铁锤开始敲打。每敲打一下就把银条翻个面。不知敲打这多少锤,翻过多少面,最终一尺来长的银条硬是被敲成了一根一米多长的银线,到此锻银工序就完成了。
这时银匠把火钳一丢,铁锤一放,爬上一米来高的马凳。马凳上有一排大小不一的小圆孔。银匠先是把银线穿进最粗的圆孔中,用一只铁钳紧紧夹住银线的一头后使劲往上拉,当银线从圆孔穿出后,银线就从不规则的扁线变成了规则的圆线。这个过程叫拉丝,目的是把银线拉成易于加工的圆银线。拉丝是分阶段进行的,先把扁线拉成圆线,再换不同直径的小孔,把粗丝拉成细丝。今天银匠要做的是银丝戒指,要求的银丝直径很细,因而银匠拉完大孔后换中孔,拉完中孔后换小孔,再换细孔……拉丝是个辛苦活,大冬天的居然把银匠拉得满头大汗,也把暗淡无光的银线拉得光彩夺目。
拉完丝就进入了苗银制作最重要的工序——吹烧。银匠先剪取了一小段银丝,用钳子把银丝卷成戒指模样后。点燃了一盏油灯,拿出一只细小的铁管,铁管一头衔在嘴里,另一头放入油灯火焰中。与此同时,用钳子夹住戒指放在油灯火焰前方。只见银匠深吸了一口气后让气流从细铁管中喷出,喷出的气流通过油灯火焰后,把豆大的火焰吹成了一条火舌,覆盖住了整个戒指。于是,银匠就用嘴衔铁管,用他呼吸之间产生的火舌炙烤银戒。时间整整持续了四五分钟,银匠整整吹烧了上百息,戒指终于从银变红。看到戒指变红,银匠赶紧停止吹烧。顾不得戒指滚烫,拿起镊子,夹起桌面上一朵朵细小的银花往戒指上粘。待戒指上熔化的银水粘住九朵银花后。银戒又用火钳夹起带银花的戒指放在油灯前开始了新一轮的吹烧。又是一百次呼吸之间,银花和戒指一起变得通红,表皮变成部分银浆后彼此牢牢的焊接在一起。
再经过擦洗和抛光等环节后,一枚小小的银戒才宣告结束。这时银匠又点燃了一根烟把银戒放入手中仔细端详,仿佛那是一枚求婚时要送出的信物。感觉银戒没有瑕疵了,银匠才缓缓走到八仙桌前,把新出炉的戒指往那银器堆里一放,那银戒就如一朵浪花没入海洋之中。
正在這时,麻茂庭的妻子从外面赶回来,麻茂庭立马从八仙桌上的银器堆里拿出刚打好的银戒递到妻子手上:“刚打好的戒指,你看合不合适!”妻子把戒指戴在手上左瞧右看后用我们听不懂的乡音和丈夫交流了很久,听口气像是批评中夹杂着表扬。麻茂庭听后若有所失,拿着银戒指返回工作台开始回炉——不仅仅是这枚戒指,这八仙桌上满足苗家生活的各式各样的银器,要想出厂,都得经过妻子这最严厉的“质检员”。
在没见银匠妻子之前,我认为最美的苗银因匠人的烈火与锤打而催生。这时我才明白,妻子“歹毒”的眼神才是苗银诞生最不可或缺的元素。
银匠妻子回家的目的是告诉麻茂庭,有人需要新盖房子,需要水泥砖。她是回来催麻茂庭把手上的银器活停一下,去生产水泥砖的——如今银器生意不好做,麻茂庭不得不另谋出路。
其实,麻茂庭的举动并不出格,他遵循了从古以来苗族银匠的传统——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职业的苗族银匠。所有的银匠都是在农忙时封炉,农闲时开锤。但不同的是,古时银匠开锤,是因为苗银是苗家穿在身上的符号,而银匠是用铁锤记录历史;如今银匠封炉,只因苗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消失的步伐迈得太快,年迈的银匠角色一时半会儿转变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