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交”与异类婚姻谭之关系*
2021-11-12孙瑾
孙 瑾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魏晋志怪小说中关于人与异类交接的故事,与唐以后的传奇、白话小说中的异类婚故事(异类婚姻谭)大有关系。志怪小说大抵记录民间口耳相传的怪闻,唐传奇之后才有了比较明确的文学创作意图,人与异类交接的怪闻便成了异类婚姻谭的主要原型。近年来有不少研究以故事类型及母题为线索,讨论文人作品中的异类婚姻谭对民间故事的继承,[1][2]而关于异类婚母题的起源问题,多以文化意识层面的探讨为主。[3][4]但魏晋志怪中记录的民间口传故事,亦即民间文艺,归根结底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钟敬文先生提到民间文艺“是社会的人们之现实生活的精神反映的产物”,[5](P13)认为民间文艺的起源问题“不能不从那主要的社会生活去找寻正确的原因”。[5](P10)目前在关于异类婚母题起源的研究中,对民众社会生活方面的探索还比较少见。本文拟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疾病发生的角度出发,分析特定疾病在异类婚母题的产生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一、魏晋以后异类婚母题之起源的研究背景
对于魏晋以后异类婚母题兴起的原因,有外国传来之说,即认为人兽通婚源自印度佛经故事母题。[6]或者将之归因于魏晋时期特有的文化变动,如动物崇拜思想衰弱,各民族文化交融,儒释道思想共同影响等。[3](P53)叶庆炳先生认为,六朝志怪中人与异类交接的故事是中国爱情小说之兴起,也就是说,从民众的精神文化层面分析,主张异类婚主题的产生源于当时民众表达爱情的渴望,并认为这些故事是“幻想,虚构而非事实”。范金兰援引此说,将此类故事的起源总结为人们想要纾解压抑情欲的欲望。[7](P28-29)日本学者富永一登也将之归结为人类对性的欲求和幻想。[8](P206)将异类婚姻谭产生的源头归结为古代民众对性的幻想,这样的观点虽说有一定道理,但无疑是将文化形成之过程过度简化(1)Kleinman从人类学角度来批判当今对疾病医疗概念的过度简化,提议从文化整体论的角度来思考。参考此处一方面是因为本文讨论文学主题的出发点即是疾病文化,一方面也是主张从文化整体论的角度考虑异类婚母题形成过程中涉及的因素。的结果。[9](P24-35)这种结论就好像是说古人仅凭内在的性欲冲动与空想就能够虚构出这些传说故事一样。
尤其要考虑到,早期的异类交接故事并非出于文学创造,而是对地方民间传闻的记录,仔细考察六朝志怪,就会发现这些民间传闻的最初往往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也就是说,民间必然是先发生了某件特定的事件,当时民众在理解该事件的时候联想到了人与异类的交接。当这样的联想被社会普遍接受,就会产生所谓的“共同幻想”,[8](P206)当再次发生相似或仅仅是具有相关要素的事件时,民众就会将该事件与此联系起来。笔者更倾向于用“集体意识”,[10](P288)或者说大众意识进行概括与解释。这一概念更侧重从集体大众角度把握与理解某类事件。这种理解方式在社会上普遍流行之后,大众意识便渐渐能够脱离客观发生的事件本身,以“意识”的形式独立流传。也就是说,即便出现不相关事件,民众也有可能将二者关联起来;或者,根本没有任何事件发生,民众仅仅是靠着这样的意识,就能够创造出类似的故事。
因此,民间传闻产生的最初至少要涉及到特定客观事件的发生,以及民众对此事件的联想这两个方面。在此阶段,我们可以说促使民众产生“人与异类交接”这种联想的原因,或许与先行研究提到的“性的欲求与幻想”有关。而客观发生在生活中的事件本身,则是促成这种联想的必要前提。意识的产生应当是与客观世界相关联的。在讨论异类婚母题的起源时,只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精神意识层面的“性幻想”,是对文化形成过程之复杂性的过度简化,其中尤其忽视了大众的社会生活在文学主题产生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笔者近年来致力于古代疾病医疗与民间文学之关联的研究,发现志怪小说中某些人与异类交接的故事(以下简称“异类交接故事”)实际源于当时的一种疾病。其中对异类与人交接的联想其实与这种疾病的症状密切相关;而男性与女性之异类婚故事的差异也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疾病患者的性别群体区分相对应。
二、鬼交之病的特征和病理解释
这种疾病在医书中被称为“与鬼交通”和“梦与鬼交通”。也有称“鬼”为“鬼魅”“鬼神”或“邪物”等,总之是指非人的异类。“交通”又可用“交”“通”“交接”等近义词来表达。这类疾病被统称为“鬼交”之病。
需要注意的是,“与鬼交通”“梦与鬼交通”等说法,在汉朝以前的医学类文献中几乎不可见,目前主要见于六朝以后的医书。并不是说这样的疾病在六朝以前不存在,而是说直至六朝以后才开始普遍被称为“与鬼交通”“梦与鬼交通”等,实际上《黄帝内经》将与之相似的病症归类为“狂”。[11](P16)再往前追溯,目前可见的战国时期医学类文献中并没有与此相关的记载,倒是睡虎地秦简中的占卜文章《日书·诘》中的“鬼恒从人女,与居,曰:‘上帝子下游’”应该与此病症相关。[12](P133)[13](P65)《日书·诘》主要记载当时鬼、神、妖、怪对人民的侵扰以及防治方法,可见当时的民众对这类病症可能还未形成固定的名称。
成书于隋朝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古典医学史上最初的病理学、病因学及病态学专论全书,对六朝为止的各种疾病进行了汇总分类,并一一记叙了其病因、症候等相关的经验理论。其疾病分类法和病学基本理论,成为《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唐朝的医学全书,以及《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部分宋朝医学全书的依据标准。[14](P387-412)因此,虽然在其他六朝医书中对这种疾病也有零散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首先通过《诸病源候论》来了解六朝以及唐以后很长时期内对这种疾病的普遍认知。
(一)关于“与鬼交通”和“梦与鬼交通”问题。《诸病源候论》(2)本文写稿时参考筱原孝市等编《宋版诸病源候论》,修稿时条件所限仅入手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周学海本,参考文献著录及页码皆从后者,引用之处若二版本间有差异则以脚注说明。共有五十卷,其中三十七至四十四卷皆为妇人疾病,卷四十《妇人杂病诸候四》中收录了五十个病候条目,第四和第五条便是“与鬼交通候”和“梦与鬼交通候”。
与鬼交通候……然妇人与鬼交通者,脏腑虚,神守弱,故鬼气得病之也。其状不欲见人,如有对忤,独言笑,或时悲泣……
梦与鬼交通候夫脏虚者喜梦。妇人梦与鬼交,亦由腑脏气弱,神守虚衰,故乗虚因梦与鬼交通也。[15](P214)
由上述引文可以得知的第一点是,鬼交之病有“与鬼交通”和“梦与鬼交通”两种情况,二者的初始病因相同,都是因为患者脏腑虚弱以及脏腑的神守虚衰。不同的是“与鬼交通”发生在患者醒着的时候,外部鬼气因内部正气虚弱得以乘虚侵入,破坏了内部机制的平衡,从而使患者得了“与鬼交通”的病症。症状具体表现为不愿见人,喜欢独处;独处时会做出仿佛在跟谁对峙的举动;自言自语;情绪波动异常,不明缘由地笑或悲伤哭泣。而“梦与鬼交通”则发生在患者的梦中,患者因为自身正气虚衰而在梦中与鬼交通。此处没有具体描述梦与鬼交通的症状,但可想而知,梦见与鬼交通本身就被当作是一种症状。另外,《肘后备急方》(3)葛洪撰,陶弘景增补,杨用道附广《葛仙翁肘后備急方》,本文原则上不使用附广内容。中还提到患者精神恍惚的情况:
治女人与邪物交通独言独笑悲思恍惚者……
若男女喜梦与鬼通致恍惚者,锯截鹿角屑酒服三指撮,日三。[16](P11)
《肘后备急方》中“与鬼(邪物)交通”和“梦与鬼通”也被放在一起。对前者症状的描述大体与《诸病源候论》相近,但额外提及了患者精神恍惚的状态。对“梦与鬼通”患者的病状也提到了“恍惚”。成书于南朝的《小品方》中有“男梦见女,女梦见男,悲愁忧恚,怒喜无常”,这条收录在《医心方》卷廿一的“治妇人鬼交方第卅”这一条目中。[17](P440)虽然表述中未涉及“鬼交”,但其中的“男梦见女,女梦见男”实际等同于“梦与鬼交通”。因此,此类症状才会被《医心方》收录在专门治疗鬼交的条目中。由此可知,“梦与鬼交”的患者也可能同时出现悲伤、忧郁、怨愤、喜怒无常等情绪异常的症状。
综合以上症状描述,“与鬼交通”和“梦与鬼交通”恐怕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病症。前者以现代医学来看是一种会出现幻视或幻听,以至于行为举止怪异失常的精神疾病。对当时的民众来讲,这种病症即显示了某些“异类”的存在,它可以为患者所看见、听见,其他人却看不见摸不着。按照《诸病源候论》和《肘后备急方》的描述方式,不难想象当时是如何理解该病症的:患者喜欢一人独处,独处时却好像在与“某人”相处,自言自语地与“此人”说话,有时又与“此人”冲撞对峙,相处过程中时而欢愉时而悲伤,平时则精神不济意识恍惚。而“梦与鬼交通”的患者一般没有如此外放的怪异行为,其症状主要为梦见自己与异类交通,醒着的时候精神恍惚,部分患者伴随有情绪不稳定。
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现代人或许习惯将“梦”与“现实”对立,但对古人来说“梦”在许多时候并不意味着虚妄,它与“醒”仅仅代表着生活中的不同时间段。因此,“与鬼交通”和“梦与鬼交通”尽管表现为不同病症,却因为都涉及到与鬼交通这一内容,对古人来说就是很相近的两个疾病,或者说是属于同一类疾病的两种不同情况,其区别仅仅在于与鬼交通发生在患者醒时还是梦时。
由上引《诸病源候论》可以得知的第二点是,鬼交在最初是一种以妇女为主要患者的疾病。“与鬼交通候”和“梦与鬼交通候”作为病候条目被列于妇人杂病的分类中,便是一种明证。
从《肘后备急方》的引文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倾向。《肘后备急方》的记叙体裁一般为“治+(某病症)者+(治疗方法)”。上述引文即为“治+女人与邪物交通独言独笑悲思恍惚者+(治疗方法)”,笔者引用时省略了原文中详细记叙的三种治疗方法。而其后的“男女喜梦与鬼通”开头用“若”字来表示附加情况,且只用十数字极简地记录了一个病方。可见《肘后备急方》的这一内容原本主要是讲“治女人与邪物交通”,末尾的“若男女喜梦与鬼通”则是对附加情况的补充。另外,此处对与患者交通的对象,前者用“邪物”,后者则用“鬼”来表达。与人交通的异类被称为“物”的例子,有《论衡》卷二十二《订鬼》中的“人之受气有与物同精者,则其物与之交”,[18](P935)而南北朝以后主要被称为“鬼”“鬼魅”“鬼神”。综上可以推知,“治女人与邪物交通……”部分的内容应为东晋葛洪所著,而最末的那句“若男女喜梦与鬼通……”则是南朝齐梁年间陶弘景的增补。(4)关于《肘后备急方》引文的时代问题,笔者将在其他论文中详述。由此推断,被称为鬼交的病在初期主要是妇人所患的精神异常的疾病,即“与鬼(邪物)交通”。
而“梦与鬼交通”在早期,如东汉医书《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亦即今传《金匮要略》中被记载为“男子失精,女子梦交”。[19](P53)这个“女子梦交”大体对应后来的“妇人梦与鬼交”,只不过当时还未将女子梦交的对象称为“鬼”。应该是后来有了“与鬼交”这样的说法,才渐渐将“梦交”也称为“梦与鬼交”。相比较而言,“梦交”的重点仍止于梦见交通这一现象,而“梦与鬼交”除了梦见交通的现象,还强调了作为交通对象的“鬼”,这种病症描述的差异反映到治疗方法上,后者往往就会涉及“驱鬼”的要素。“男子失精”应该对应“梦与鬼交,遗精白浊”“男子夜梦鬼交泄精”等,[20](P292)[21](P274)就是说男子的“梦交”伴随着遗精的症状。
《诸病源候论》卷八“伤寒梦泄精候”条目也涉及到男子梦交:“邪气乘于肾,则阴气虚,阴气虚则梦交通。肾藏精,今肾虚不能制于精,故因梦而泄。”[15](P51)如此例所示,男子梦交通的症状描述中没有提及交通对象的“鬼”,而仅仅示意了梦中交通以致泄精的这种现象,与《金匮要略》中的“男子失精”相对应。此外,男子的梦交通也没有像 “梦与鬼交通”那样,被列为固定的病候条目。《诸病源候论》将“与鬼交通”和“梦与鬼交通”作为病候条目并列于“妇人杂病诸候”之中,正是因为鬼交之病作为妇人疾病的印象在当时更为普遍。
(二)基于“气”的病理解释。古人将这种病描述为“与鬼交通”时,其背后究竟是如何思考的?弄清这样的内容,是理解鬼交之病与异类交接故事乃至异类婚姻谭之间密切关联的关键之一。
上引《诸病源候论》“与鬼交通候”对其开头部分有一段省略,现将省略部分列出:
人禀五行秀气而生,承五藏神气而养,若阴阳调和则藏府强盛,风邪鬼魅不能伤之,若摄卫失节而血气虚衰则风邪乘其虚,鬼干其正。然妇人与鬼交通者,脏腑虚、神守弱,故鬼气得病之也。[15](P214)
大意是:人禀受天地五行之秀气而生,承转五脏神气而得以延养生命。若身体内部之气阴阳平衡,脏腑强盛,那么外部的风邪鬼魅便无法侵害;若保养失当以致内部气的平衡崩溃,血气衰弱,就会被外部的风邪鬼魅乘虚干扰。而妇人的“与鬼交通”,正是因为脏腑神之正气虚弱,外部鬼气得以侵入干扰使其生病。
这种基于“气”的病因解释在《论衡·订鬼》中也有近似表述:“人之受气有与物同精者,则其物与之交。及病,精气衰劣也,则来犯凌之矣。”[18](P935)“物”便是指异类。此段叙述了“物与人交”的原理:万物皆禀受自然之气而生,摄取自然之气转化为各自的精气以维持生命。假如某人承接的自然之气与某物承接的恰好同质,那么此人的精气与此物的精气本身就具有连续性,可以互相连接勾通。当人生病以至精气变得衰弱时,与之同质的物的精气相对而言就变得更强大,从而侵入人的气的领域并压制人的精气。
虽然“气”的用词略有异同,但从病理解释根底上的气的理论来看,《论衡》与《诸病源候论》非常接近,都是讲人体内部之气衰弱,以致外部鬼气(物之精气)得以侵凌,破坏了内部气的运转机制。《论衡》接下来又举了具体病状:“俗间与物交者,见鬼之来也……”[18](P935)也就是说,“与物交”的患者出现幻视,能看见鬼的到来。这种幻视与前面分析的“与鬼交通”者出现幻视或幻听,以至于自言自语仿佛在与谁交流的病症是相通的。
因此,《论衡》的“物与之交”与《诸病源候论》的“与鬼交通”基本可推断为同一类病症。《论衡》收集的是东汉当时民间的俗说。虽然对异类的称法不同,但可知这类病症被称为“人与异类交通”的现象在东汉时就已存在,只不过是在六朝以后才广泛出现在医学类文献中。
再回头思考《论衡》对“与物交”以及《诸病源候论》对“与鬼交通”病因的说明。以气的医学理论来看,所谓鬼交应该是指鬼气与人气的相交。得以侵入人的气场的鬼气,一方面与人气交合在一起,一方面因为强盛于人气而出现了压制的局面。据此思路,患者自言自语好像在与谁对峙的现象其实可以理解为,两个气在患者的体内争夺对身体的控制权。另外,如果鬼气完全压制住人本身的精气,也就是说,鬼气完全取得了对患者身体的支配,患者的行为就会变得像是被鬼控制。如“或歌或哭,为鬼所乱”“或歌如鬼所使”等。[22](P282)[23](P750)
(三)房中派的解释。基于“气”的病理解释并非成为唯一定论,六朝至唐期间医学界对鬼交的讨论非常活跃,相关说法层出不穷。其中颇具影响,且与异类交接故事及婚姻谭等密切关联的是房中派的论说。
六朝时期的养生房中家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房中说,一方面也给房中术内容注入了一些新鲜要素。鬼交之病便是其中之一。首先来看《医心方》卷廿一的“治妇人鬼交方第卅”对《玉房秘诀》的引用:
《玉房秘诀》云:采女曰:何以有鬼交之病。彭祖曰:由于阴阳不交,情欲深重,即鬼魅假像与之交通。与之交通之道,其有胜于人,久则迷惑,讳而隠之,不肯告人,自以为佳,故至独死,而莫之知也。[17](P440)
这一段以采女和彭祖对话的形式阐述了鬼交的病理:患者因长期没有性生活而欲望强烈,使鬼魅得以乘隙幻化人形与其交通。又因为鬼魅所带来的性体验远胜于人类,患者受到迷惑,不愿将实情告知旁人,自以为美而沉溺其中,逐渐病死却无人知晓原因。
彭祖这一人物虽然在马王堆出土的房中资料里已有现身,但不过数言而已。且彭祖在当时并非像容成子那样是房中代表人物,是从葛洪的《抱朴子》《神仙传》开始才以因房中术而得道的形象活跃于房中术的论说之中。[24](P85)因而引用自《玉房秘诀》的这段言论不太可能早于葛洪的时代。
根据上引《玉房秘诀》,鬼交的根本原因在于“阴阳不交”。其实,“阴阳不交”有弊的房中观点自古以来即有,比如葛洪《抱朴子内篇》中有“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25](P4)大意是:男女若长久独处而无性生活,阴阳二气不得交互,体内的气便会滞塞,以致经常生病,寿命也会缩短。不过,葛洪及其以前的房中论说,尚未将阴阳不交与鬼交的病症关联起来。将鬼交病因解释为阴阳不交是六朝往后才有的现象。
《医心方》卷廿八的“断鬼交第廿五”再次引用了《玉房秘诀》对鬼交的阐释,其中提到此病是“怨旷之气,为邪所凌”。[17](P594)所谓“怨旷”与《抱朴子内篇》中的“幽闭怨旷”一样,意指长久独居而无交接对象的状态,亦即“阴阳不交”。但《抱朴子内篇》与《玉房秘诀》的不同在于,前者认为“阴阳不交”导致内部之气的闭塞从而使患者生病,而后者则认为“阴阳不交”招致外部邪气侵凌内部的“怨旷之气”,因而形成了鬼交之病。有趣的是,外部邪气侵凌内部之气的想法,正与前述《诸病源候论》等对鬼交的阐释相符合。可以说,《玉房秘诀》对鬼交之病的解释,即是将这个气的理论与“阴阳不交”有弊的房中理论相结合,将外部邪气解释为幻化人形的鬼魅,将外部邪气与患者之气的相交解释为阴阳之交接。
此外,卷廿八的“至理第一”中还有一条对孙思邈《千金方》的引用:
《千金方》云: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若孤独而思交接,损人寿,生百病。又鬼魅因之共交,精损一当百。(5)高文柱注释本作“又鬼魅与之共交精,损一而百”,本文对照《养性延命录》的引文,将原文断句为“又鬼魅与之共交,精损一当百”。[17](P580)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很自然地将“男女阴阳不交导致生病”与“男女阴阳不交导致鬼交之病”连接在一起。《备急千金要方》(6)宋·林亿等校正的《千金方》题名为《备急千金要方》。本文为方便区分以《千金方》为宋校正以前的版本或统称,经过校正的版本则特称为《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房中补益第八”中又有如下内容:

划线部分与《千金方》的引用略有重复。而《千金方》和《备急千金要方》的这两段内容其实在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中都可以看见:
采女问彭祖曰……彭祖曰:不然。男不欲无女,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神劳则损寿……有强郁闭之,难持易失,使人漏精尿浊,以致鬼交之病。……凡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若孤独而思交接者,损人寿生百病,鬼魅因之共交,失精而一当百。[27](P9)
如文所示,这段文章原亦采用采女与彭祖对话的形式。上面提到彭祖主要是在葛洪之后才作为房中家代表流行起来。当时不免有借彭祖之名撰写文献的现象。《养性延命录》的这段文章据先行研究应出自《彭祖养性经》或《彭祖养生经》,[28](P51)[29](P19)两种皆初见于北周《玄都观经目》中,被认为是托彭祖名而造。[30](P444)这段文章非常客观地展示了古代房中术以男性立场为主的特征,虽提到了男女皆不可“绝阴阳”,但对阴阳不交引起鬼交之病的叙述仍旧侧重于男性患者,尤其是将精液的异常排泄与此病关联,强调与鬼交通比正常的性交接要损失更多的精液,从而导致生病乃至寿命缩短。像这样,将精液与男性生命直接关联起来,提倡通过减少排泄精液以及“还精”等方法来延年益寿是房中术自古以来不变的主题。
以上列举了六朝及唐期间房中术相关记载中关于鬼交的说明。当时社会上对鬼交之病的关注度比较高,房中派把“阴阳不交”有弊的房中理论与此病关联起来,首次明确地将“与鬼交通”阐释为人与异类的性交接。尤其是男性的鬼交,因为涉及到梦遗等精液异常排泄的症状,更成为房中派议论的重点。这种议论后来被纳入唐朝的医学全书《千金方》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这类病症的认知方式。另一方面,由于古代对房中术的讨论主要以男性视角为主,这种讨论扩展了民众对男性鬼交概念的认知。
三、异类交接故事与鬼交之病的关系
很多异类交接故事中会提到当事人生病的状况,这种病一般被称为“魅”“邪魅”等。
先看《太平广记》中的一个例子:
……县令有女为精邪所魅,医疗不効。乃投奉治之……奉然之,即召得一白鼍……奉使侍者斩之,女病即愈。(《董奉》,出《神仙传》)[31](P68)
这是六朝志怪中被认为是异类婚姻谭原型的典型事例,讲妇女被异类魅惑而病,术士来为其治理,最后发现是白鼍作怪。关于“为精邪所魅”可参考《诸病源候论》卷二的“鬼魅候”:“凡人有为鬼物所魅,则好悲而心自动;或心乱如醉,狂言惊怖,向壁悲啼,梦寤喜魇;或与鬼神交通……此魅之所持也。”[15](P13)所谓“魅之所持”可理解为“凭附”,患者的自我心神意识变得模糊甚或丧失,行为举止像是受到鬼魅把持一样,情绪也异于常人。在这种情况下,患者有可能会发生“与鬼交通”。“向壁悲啼”的症状描述中隐含着患者不愿与人交流的意思。另外“心乱如醉”“狂言”等症状也与上文讨论的“与鬼交通”非常接近。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为魅所持”的各种症状之中,那些使民众理解为患者与鬼魅有所交通的症状,人们就称之为“与鬼交通”。与此相对应的有《太平广记》中的另一则记录:
……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姘净,着赤衣,自云家在侧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輙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茎。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焉。(《鲜卑女》, 出《异苑》)[31](P130)
这个“为赤苋所魅”的女性每日黄昏时装束打扮,家人看到她用手指环绕着赤苋草,这一细节应该是在说患者具有幻觉的症状,在接触旁人看不到的异类。而前面提到她看见一个容貌美丽的男子,如果确为患者自述而非传说过程中添加,无疑也是在暗示患者具有幻视的症状。另外,异常的歌唱行为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与鬼交通”的症状,前文列举的“或歌或哭”“歌如鬼使”等便是其例。
(一)“魅”疾患者以女性为主。有趣的是,小说中的“魅”疾患者也是以女性为主的。本文将《太平广记》中与女性“魅”疾相关的事例分为A、B两组,A组13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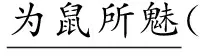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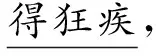
B组5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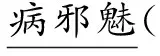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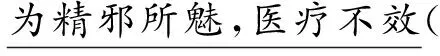


A组事例皆明确述及患病女性与异类交接或婚姻的情形。B组几例的叙事主线都是“妇人被魅惑而生病,术士发现并解决了作怪的异类”,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异类交接的情节,但只要将之与后世的异类婚姻谭做对比,便可以判断,这些事例大抵可以看做是异类交接故事比较初始的形态,或者说是与之相关的事件。
男性的“魅”疾在《太平广记》中有两例:
所记皆唐时事,且事例中的异类皆为狐。另有“后被病……神魂不足,往往狂语,或笑哭不可禁”(《裴少尹》,出《宣室志》),[31](P350)一条亦为妖狐作怪,其中提及男子症状颇似“妇人与鬼交通”,但内容与异类交接的主题并无关系。唐朝时出现男性“魅”疾的异类交接事例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狐魅流行的影响。[8](P270)
以上,无论从症状内容,还是从妇人为主要患者群体的特征来看,异类交接故事及婚姻谭之中常见的“魅”疾,应当正是当时医学文献中记录的“与鬼交通”。
(二)房中思想在男性异类交接故事中的体现。六朝的以男性为主角的异类交接故事,很少涉及这些男性的身心状况。大多不过是男子与幻化成女子的异类相遇交往,再因某契机发现真相而破局。仅有一则故事提到了男性身体消瘦病弱的情状:“太元末,徐寂之尝野行,见一女子操荷举手麾寂之,寂之悦而延住。此后来往如旧,寂之便患瘦瘠……”(《徐寂之》,出《异苑》)[31](P306)
唐传奇中有一则讲述凡男与女仙交通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鬼魅之近人也,无不羸病损瘦。今义起平安无恙而与神人饮燕寝处,纵情兼欲,岂不异哉(《成公智琼》,出《墉城集仙录》)。”[31](P307)当时普遍认为与鬼神交通的人身体会有所损耗,出现赢瘦病弱的症状。因此该事例中男子与所谓女仙交通却依旧平安无恙的情况反而令作者感到讶异。
《墉城集仙录》中的这个观点与养生医学中的房中思想非常有关。上文论及男子鬼交往往伴随有精液的异常排泄,而精液的异常排泄,又多伴随患者身体虚弱的症状,如“梦与鬼交通,去精惊恐虚乏”“鬼交精出,病人虚而多热”等。[21](P836)[26](P511)笔者在调查宋代医疗民俗文化的时候,曾经对《夷坚志》中男性与异类交通的事例做了收集,涉及男性病状的有35例,其中31例都明确提到了男性患者具有赢瘦、憔悴、虚弱无力、疲劳感、脸色差等身体虚弱的症状,且这些症状在记事中往往成为引导人们揭破男子与异类交接之真相的关键。[13](P49)可见在当时,男性与鬼交通导致生命损耗的想法已深入人心,而生命损耗的背后原理便在于患者精液的损失。
《夷坚志》中有几则事例尤为相关,此处略举丁志卷第二十《黄资深》的事例:名为黄资深的男子寄居某家时,与一只化成女子的母狗交通并患病虚弱。某家子弟发现后将母狗杀死,“剖其腹,似有孕,一物如皮球,膜里皆精液,疑结如乳。即煮熟之,加盐酰,托为野物以啖黄……所患瘵疾亦愈”。[32](P701)也就是说将母狗腹中被认为是患者精液的东西取出给患者服用,他的病便治愈了。
这则事例非常巧妙地反映了异类交接故事中的房中思想:一是与男性交通的异类会摄取男性的精液,而男性因此患病,这一想法可见于六朝的房中文献;二是将遗失的精液给男性食用本身与房中派的“还精”思想相关,也与宋朝当时道士的房中术实践活动有关。(7)关于这两点,笔者将在其他论文中详述。
四、结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与异类交接故事及婚姻谭相关的古代疾病——鬼交。首先详细论述了鬼交之病的三个方面:1、鬼交分为“与鬼交通”和“梦与鬼交通”两种情况,各自的症状特征不同;2、鬼交之病早期以妇人为主要病患群体;3、房中派对该病的阐释扩展了人们对男性鬼交之病的认知。继而通过对比分析可知,异类交接故事及婚姻谭中女性所患的“魅”疾正是医书中记载的“与鬼交通”之病。而后来的男性异类交接故事及婚姻谭中开始频繁提及男性身体虚弱的症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房中派对鬼交阐释的影响。
因而,鬼交之病可以说是相当一部分异类交接故事产生的要因。一方面,民众将鬼交之病的发病症状理解为患者与异类交通;另一方面,房中派对该病的解释被纳入医学文献之中,从而广泛影响了民众对男性鬼交之病的认知,这种认知随后又体现在异类交接故事及婚姻谭的记叙之中。
促成异类婚母题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因素自然是复杂的,本文仅从疾病发生的角度分析了鬼交一病在这种文学题材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知道了异类婚姻谭的起源绝非仅仅是“人类对性的幻想”。因而得知,在研究某个文学主题之产生与发展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多层面考察,从文化整体论的角度来分析讨论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