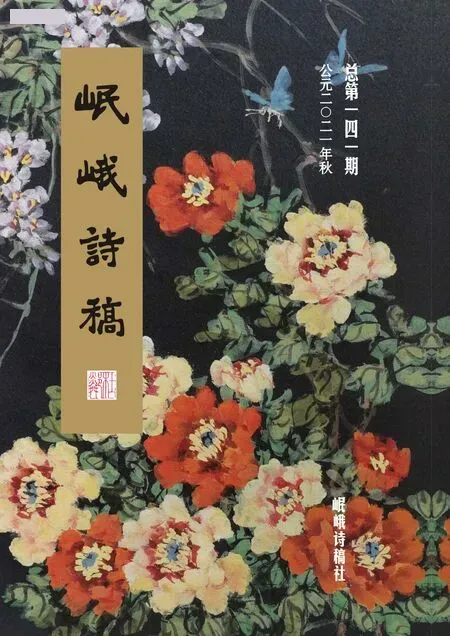《三声集》序
2021-11-12周啸天
周啸天
《九歌·少司命》云:『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二〇一四年因四川省政协主席陶武先之介绍,认识了刘道平同志。道平同志阅历丰富,廉洁自律,性情爽朗,谈吐大方,毫无官气。与之相处,实人生乐事。
其时道平正热衷习诗问道。孔子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一不小心,我便成了『三人』中的一人。道平有一句口头禅:『我这个学生,是不好教的。』一则因为他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二则因为他要和老师抬杠。话说回来,若要对道平学诗下一评语,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三好』。
一是『好写』。清人钱泳说:『凡事做则会,不做则安能会耶?』道平勤于写作,几乎遇事入咏,每日不可无诗。怎样才能动笔呢,依我看,起码得有好句。『立片言以据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好诗是靠好句撑起来的。苏轼的《惠崇春江晓景(一作晚景)》,是靠『春江水暖鸭先知』撑起来的。许浑的《咸阳城东楼》,是靠『山风欲来风满楼』撑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一句,就不要写七绝;如果没有这一联,就不要写七律。写了也白写。道平同志是懂这个道理的,每作一诗,必先得句。例如《咏竹》:
拔节青山入翠微,虚心惯见白云飞。一朝截作短长笛,便喜人间横竖吹。
这首诗的三四句便是好句。这里的『吹』字双关,既是『吹笛子』的『吹』,又是『吹捧』的『吹』;『横竖』亦双关,既是横笛、竖笛的『横竖』,又是反正。此联本非对仗,却给人以工对的感觉,措语之妙也。全诗针砭人性的弱点,意既到位,语亦随之。这样的诗,不会不传。读者忍不住传,写了便不白写。或谓一二句『拔节』『虚心』落套,但这一二句的落套,是为了三四句的不落套。所以必须如此。
自诗经、楚辞以来,传统诗词特重比兴手法,苏轼说:『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道平同志也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不会一味模山范水,不会止于合辙押韵,例如《高压锅》:
一阀千钧头上重,天旋地转口难封。若无舒缓盈胸气,便付安危儿戏中。
咏物诗要做好,不能止于咏物。白居易说诗要『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但若直接把这个道理说出来,则不是诗。诗须有联想,须有意象。『高压锅』便是作者因联想而寻得的一个意象。高压锅重要的设计是其头上之『一阀』,重量虽轻,作用极大,谓之『千钧』亦宜。其妙用在于适当出气,使锅里的压力,保持在一个安全的度上。不准出气,可能酿成重大事故。三四点到为止,有举重若轻之妙。
有人说,诗不是写好的,而是改好的,有时是别人改好的。王之涣的『黄沙直上白云间』,是被传抄者抄成『黄河远上白云间』的,竟成名句。李白《静夜思》的『举头望山月』被明代赵宦光改作『举头望明月』,『床前看月光』被清代沈德潜改作『床前明月光』,《唐诗三百首》一并予以采纳,遂成通行版本。晏殊《浣溪沙》『似曾相识燕归来』,是出于下属王琪的建议,用来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竟为千古名联。毛泽东的『原驰蜡象』,『蜡』原作『腊』,是臧克家建议改的。凡此种种,并没有产生著作权纠纷。《论语·子罕》云:『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就是说,人不要先入为主,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固执己见。道平深知这个道理,与人酌诗,往往从善如流。例如《都江堰》:
千秋郡守盛名传,浅作长堤深凿滩。鱼嘴争流何太急,向前一步自然宽。
这首诗写到第三句,诗情达到高潮,如足球在球门附近滚来滚去,就差临门一脚。末句『向前一步自然宽』便是临门一脚,进球得分。而这句诗,是与友人商榷的结果。
二是『好读』。人的写作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人的写作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阅读受用的结果。故我对学生说:『读也,写在其中矣。』『读到什么份上,写到什么份上。』
当代人有一个误区,就是常将传统诗词等同于近体诗词,以为跨进格律这道门坎,就算会写。殊不知格律这个门坎很低很低,聪明人说,平仄问题只须半天就可以解决,而语言问题十年不一定过得了关。不懂这个道理的人,每日指物作诗,尽心安排平仄,追求到了拗救,逢人就说:『我已经写了几千首了。』遇到这种事,我只能善意地规劝:『几千首够了,数量超过白居易了。暂时不用再写,花点工夫来读吧。』
与诗词写作直接相关,须读古今诗词的选集、别集和总集,以及历代的诗话词话著作;其次须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以及文艺理论著作;其次须读古今中外人文科学名著;其次须读形形色色的奇书、杂著(曹雪芹连制作风筝的书都读)。人生最怕心胸狭隘,与人无趣。阅读,可以造就心怀悲悯的人,腹笥甚广的人,有趣的人,诗性的人。
道平同志生在一书难求的年代,却嗜读如命,饥不择食。阅读所及,至于风水宅经,麻衣相术。后有机会上党校,在老师指导下系统阅读中外政治理论、文史哲名著,读书逐渐有了系统。他好学善思,成绩优异,经常名列前茅。学诗以来,得武先同志惠赠书两大袋,对诗词理论知识进行了恶补。腹有诗书,进步甚快。
第三是『好谈』。朱光潜说,要精通一门学问,最好写一本有关该学问的书。讲谈的作用,也是一样。必须对所学了如指掌,方能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苏东坡说:『诗三分,诵七分。』在我看来,一个人能记诵古人的名篇,却不能记诵自己写出的诗句,肯定是语感出了问题,用记性不好来替自己缓颊,是怎样也说不过去的。道平同志以文会友,言必称诗,每自诵近作,逸兴遄飞,任人评弹。谈读书心得,辄得其要旨;道写作经验,则如数家珍。常将朋友的聚会,无形中弄成雅集,如坐公益论坛,与会者无不称善。
综上『三好』,成就了道平的诗词,也成就了诗人刘道平。这本诗选,是作者近年之作,几经删汰而成。定名『三声』,取『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义也。诗词最忌公共之言,反之,最喜独到语、未经人道语。主旋律题材之所以难写好,就在易落公共之言,成为『老干体』。道平则不然,如写《访贫》:
泥径孤村冒雨行,打工人去暗心惊。几多触目几多叹,一半拋荒一半耕。孙傍柴门呼客到,翁停竹帚带愁迎。脱贫事业谈何易,不觉东山新月升。
蜀中诗家郭定乾点评:贫困村之所以贫困,多半是受地理环境的限制,比如土地贫瘠、缺水、道路不通等,在这种环境中靠农业生产来维持温饱已属不易,倘遇自然灾害,种庄稼就是赔本生意,因此就有大量的贫困村男女青壮入城打工挣钱。留守农村的就只有老人和孩子。由于缺乏劳动力,原有的熟地也只能『一半抛荒一半耕』了。诗中的『泥径』,意指道路艰难。『孤村』,意指环境偏远。『柴门』,照应『贫』。颈联形象生动,很有画意。在整个访贫过程中作者没有一句冠冕堂皇的慰问语或鼓励语,而更多的只是叹息,这样,我们反觉得它真。因为『脱贫事业谈何易』。诗以景语作结,尤觉饶有馀味。作者是一位老干部,但诗中无一句『老干体』语,难得!
总之,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诗。谓予不信,请读《三声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