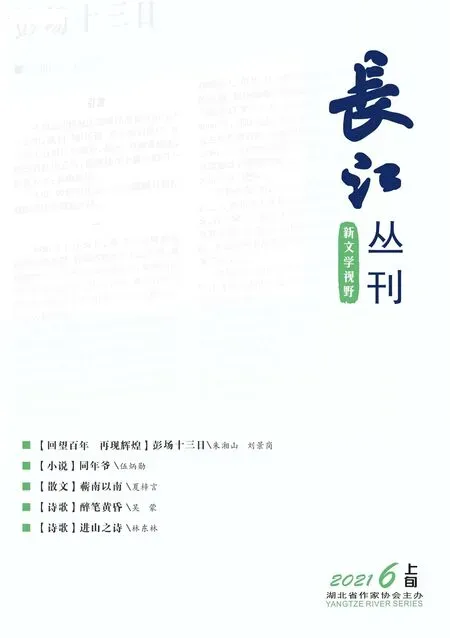同年爷
2021-11-12伍炳勋
■ 伍炳勋
不是和父亲同年生就可以叫同年爷,同年生加上关系好,才能叫同年爷。第一次见同年爷神屌,是在他的黑屋子里。那年我十七岁,念高二,大学不招生,还差一年就念书念到头了,“幸福在哪里”这个问题日夜萦迴,剪不断,理还乱。那年月,最好的出路是当兵吃粮,可自己头上长铜钱疮,手上长“鱼刺”,据说这两种病都是禁忌,便愁。高三一年无须应考,心思就都放在跳“农门”上,整天唉声叹气。父亲不忍,说,带你问问同年爷。
同年爷直挺挺地躺在一间两进的里间,门是虚掩的,推开房门,阳光跑在头里引路,才堪堪看得清乌七抹黑的里间门,推开里间门,阳光没法拐弯,墨黑墨黑,偏生同年爷还穿着一身黑。要不是父亲吊起喉咙大喝一声“老同”,同年爷“嗯”了一声,谁也不晓得这里会有活物。
同年爷只穿两种颜色的衣裤,一是黑,二是白,要么全黑,要么全白,从不混搭,说是这两种颜色上通天堂下通地狱,左通鬼右通神,说这个道理是他儿子告诉他的。要不他也不晓得,他说他狗屁不懂,他儿子天上地下的事,事事通。
有事快说。同年爷幽幽的声音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你莫做起这个卵样子,我带了油炸糯米粑的,父亲说,二牛想当兵,却长了“鱼刺”和铜钱疮。整天茶不思饭不想的。我望到急。
我看看我崽去南岳开会去了么。同年爷侧转刚刚侧过来面朝父亲说话的身子,重又平躺,闭眼,说,崽呀,去你同年爷屋里看看,你二牛老弟的鱼刺和铜钱疮治得好么,会影响到他明年当兵么。许是同年爷的儿子并没去南岳开会,同年爷眼一闭足足闭了十来分钟。父亲和我大气不敢出,屋子里只有同年爷“呼呼”出气的声音。
父亲性急,耐不住性子老听同年爷呼呼。瞅准了同年爷紧闭的眼睛第一次忽闪的当口大声喝问,你儿子还没回来?你怕动飞?同年爷十分不满,就你敢在我面前惊弓拌弓,打雷的一样,吓跑我屋崽,我扔你下钟潭。同年爷屋面前有条河,叫小龙江,小龙江一个最深的潭,叫钟潭。我要不是要求你办事,早把你扔钟潭了。父亲的声音一下爬高了几十丈。快说快说,我崽二牛的事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我崽说了,你家灶堂里有块三角石,回去刨出来扔了。再烧点草灰拌上桐油涂铜钱疮。鱼刺自己会脱。
那二牛能当上兵么?父亲最关心的事就是这个,同年爷“腾”一下坐起来,别个来都捉鸡送鱼打红包,你就几个糯米糍粑打发,我给你管得那多!同年爷也是惊弓拌弓,包你治好二牛的病就封了顶心毛了,你还问起那多。父亲说,卵大的脾气,我走。脚还没跨过门槛,床上又呼呼地拉风箱一样。
同年爷的儿子生的蹊跷,死的也蹊跷。说是哄爷崽正好。民国三十二年春上,某一天久雨放晴,村前晒谷坪好多老头老娘都脱了棉衣,捉虱子的时候,不知从哪里来了个长胡子长头发后脑壳耸个大发结的道士。道士一来就冲着同年爷叫道,恭喜啊恭喜。同年爷正痴痴地看郎寡妇捉虱。我人一个卵一条,有狗卵子喜啰,你怕是讲癫话?道士嘿嘿笑,讨婆娘生崽算喜么?算。可婆娘在哪?没婆娘崽又从哪个岩洞出来?婆娘,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不过你得修个阴德。修阴德?对,小龙江年年发大水,淹死无数生灵,卷走无数庄稼,搞得满院子人妻离子散,你也讨不到婆娘。倒是。你还能制住洪水?能。只要在这里修座庙,镇住洪水,满院子人有了好日子,你也能成家立业。
同年爷半信半疑,同年爷宁愿信其有。别的不说,光是上半夜子时,下半夜卯时的煎熬就捱不住,下面一闹脾气,上头就憋得鼻青脸肿,一张木架子床遭尽了罪生生要散架了。要不刚才也不会鼓起死鱼眼看寡妇。
寡妇蛮丑,陡颧骨爆牙齿,缺油荤的枯黄头发长在前砸金后砸银的扁脑壳上,脑壳就像死透的棕树蔸蔸。丑不打紧,安排眼睛受受委屈也就过去了。还克夫,嫁到院子里没三天,天天在小龙江浪里打滚捞鱼捉虾的丈夫,被一揝丝草缠了脚就闷死了。可她终归是个女人,是女人就有一个坑,一个萝卜要个坑,同年爷的萝卜没坑可放,克夫啊丑啊都不是事,一辈子没碰过女人才是事,大事,哪天死了卵都不值。
道士指明了前进方向,同年爷心中也有了远大理想,为了婆娘崽和卵快活,修庙干活生生把自己做卵累,出门进屋两头黑,两三百斤的杂木筒子嗨咗一声扛起当野猪跑。屋里穷没得饱饭呷,就把腰间那块粗布洗澡巾做死的往紧里勒。那些日子,院子里打了喊,个个说,神屌发了么子癫,明明懒得蛇钻屁眼不挪屁股一个人,如今勤快到没卵谱。
庙建好,菩萨上任的那一天,同年爷直奔寡妇家,寡妇早把同年爷的勤快和多情看在眼里,何况早就渴得爬墙壁了,何况男没娶女待嫁。干柴烈火一对眼,直接就搂上了床。办完事,同年爷道,道士说了我能得崽。寡妇板起脸,你就是为了崽才撩骚咹?同年爷不解风情,深陷在自己的思路里。昨晚上庙里菩萨给我送梦来,说我修庙有功,让他的书童下凡做我崽。今天这一炮中靶,你就能做菩萨他娘了。明明只是菩萨书童。寡妇不屑地撇了一眼同年爷。同年爷却打尿颤颤,他把寡妇的嗔怨当作刚刚孵崽的余韵了。
同年爷说过,父亲难长寿,但不会欠床债,说死就死,风吹灯灭一样。父亲不服,说,讲卵话哩,哪个不晓得,像我这样点得火燃的爆脾气,有几个欠床债的?同年爷就骂,你以为我讲的?是我崽讲的,我崽是菩萨!菩萨!!菩萨你不信?
同年爷的崽又变菩萨了。民国三十八年,变了天。院子里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个读书伢子,先是每天见人总哼两句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后来就说那庙占地方不如拆了,说头次,院子里人都伸长舌头像吊颈鬼。读书伢子缩起颈脖瞪圆眼,你们属狗的,呷屎不记坨数?个个伤风感冒无名肿毒往庙里跑菩萨给治好了?女人“百日痨”,男人“梅毒”菩萨给治好了?每一年春、夏小龙江的洪涝菩萨镇住了?同年爷一拍脑壳,嗯在理。捊起袖子就干。
拆庙,同年爷冲在头里。谁晓得,菩萨大约是两天打渔三天晒网的那种,治病抗洪无能,保自己衣食住行够神通。放倒庙廊柱那天夜里,同年爷刚躺平闭眼,菩萨就气愤地朝他发飚,修庙你买力,拆庙又带头,我的书童还帮你续香火?同年爷弹簧一样蹦起三尺高,嘴里叨叨何得了何得了。寡妇一脸懵懂,发神经啊你,么子何得了?同年爷伸长颈子瞅脚头熟睡的崽,崽吐纳均匀,一颗出窍的心又回到胸腔里。他连拍了三下胸口,冲寡妇吼,没事,咋唬条卵!臭婆娘家家。庙夷为平地的那天,天雨浩浩,洪水荡荡,寡妇扛个抓网,带七岁的崽去江边田坝捞鱼虾,一去就再没回来。院子里有人看到,寡妇捞到一个足有两三斤重的脚鱼,狂喜,喊崽快来看,崽一脚滑进江里,寡妇跟着蹦下去,结果娘崽却没了踪影。
同年爷没有哭,父亲跑十里山路回到院子里的时候,他两手一摊,老同你再看看我的相,我是不是天生孤寡啊。昨天还有婆娘有崽,今天就又回到了民国三十二年。同年爷晓得我父亲有一本皱皮卷角的草纸印的《柳庄相法》。父亲就抱着同年爷哭,同年爷也哭,父亲眼泪放坝水一样,同年爷却干嚎。父亲突然止住哭,一根手指戳到同年爷面门上,你看你,你就不是肉做的身子,是铁打的,屋里一天死两个,你都没掉一滴泪。就凭这,你不孤寡谁孤寡!还有,你自己去看,父亲起身突突突走到洗脸架子上拿下一小片镜子,硬塞进同年爷手里。你山根(鼻梁与印堂交界处)尖细,鼻梁刮瘦无肉,泪堂(下眼睑处)杂纹遍布,人中短浅,还长颗黑色恶痣,喉结凸突,长张吹火嘴。你不孤寡谁孤寡?父亲讲得要多直有多直。他太没分寸,同年爷孤寡,好歹还开过女人荤养过崽;父亲那时还卵打叮当黄花崽呢。同年爷却不生气,只淡淡地问,你呢。末了又说,这就好,迟孤寡不如早孤寡,反正孤寡命,婆娘是哄郎婆娘,崽是哄爷崽。父亲就又抱紧了同年爷哭。
这一年同年爷和父亲都是三十岁,从此,一直到六十岁,同年爷寂寂无事。其间也有人给他介绍过对象,可大多都怕死在他手里。一个克死男人的寡妇,一个菩萨下凡的崽都被他克死了,还有谁能抗得过他?只有一个不怕死的,大概是没男人干久了,淫壮怂人胆,对象时给他送了一脉妩媚,从女人家回来,同年爷特意杀只鸡,一锅炖了,也没起锅,抓一双筷子三个碗,一边夹鸡肉一边叨叨,自己一坨婆娘一坨崽一坨,自己一坨婆娘一坨崽一坨……一锅鸡肉夹完了。看看三个碗每个都不够小半碗。苦笑,摇头,再把鸡肉全部垒进一个碗,鸡肉立刻就堆出山尖尖。同年爷哈哈大笑。说,反正也尝过味了,还找个跟我抢鸡呷的打鬼噢。
同年爷六十岁这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甲子生日这天,他杀了一条养了两年的壮猪,邀请院子里所有户主和七大姑八大姨所有亲朋,在院子大会场摆了整整十桌。菜就两样:杀猪肉、大白菜,酒是去年的重阳老窖。宾客呷得满口流油的时候,同年爷走到每个人身边原封不动地退还了贺寿礼金。然后回到首席寿星佬的位置上,云淡风轻地放了一个“风”——我神屌为什么叫神屌?我神屌为什么今天大寿请客却不收大家礼金?跟你们说,昨天晚上,我那菩萨身份的短命鬼崽,给我送梦,说我辛苦养他七年,如今我老了,他要报我养育之恩了。包我往后的日子呷好喝好还脚不沾泥手不落水。哈哈。打完哈哈,同年爷又特意强调,今天就是借个机会给大家报喜,断断没有收大家礼金的道理。
一众亲朋好友,直听得云里雾里。有信的,有不信的。信的不信的都做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喇叭,神屌死去三十年的崽要回来为神屌养老,消息一时间传遍大江(小龙江)南北,乡村上下。
而我父亲,是同年爷最虔诚的信徒。
只可惜,父亲命不济,和同年爷同年生,却火急火燎地在同年爷打屁吹得火燃的鼎盛时期赶向了另一对父母的怀抱。父亲带我见过同年爷之后,兴高采烈。我听同年爷的话听得垂头丧气,可在父亲耳里,听到的却好像是我已经穿上了绿军装。他拼命地上山打桐籽捡桐籽再挑上桐籽去油榨里(榨油作坊)换桐油。再选晒得最燥的稻草烧成灰,兑好桐油,在我出门上学时给我擦一次,放学回来一进屋擦一次,晚上睡觉前又擦一次。直擦到头皮像锅底,乌七抹黑。我怕同学笑话,父亲说,你还没摸过锄头扶过犁,不晓得养工的辛苦,当兵吃粮才是最重要的,人家要笑,你当耳边风,月大多笑一天,月小少笑一天,关你卵事。
可是父亲再上山捡桐籽的时候出事了。本来先换来的桐油擦一百个铜钱疮脑壳都够,但桐油还有很多用处,最重要的是能卖钱。父亲就把捡桐籽当做每天十分工八厘钱之外的生钱门道来做。每天做完队里的叫工,就往山上爬。山里的野生桐树万千,桐籽捡也捡不完,捡起上瘾。结果一颗桐籽纳了父亲的命。一天夕阳将将滑进山岫的时候,父亲背起一背篓桐籽打算回家,在一个坡上踩着那颗桐籽,身子一斜便就地扑倒。篓里的桐籽天女散花似地纷纷滚落,全都变成父亲身下的滚筒,载着父亲的身子一路从山坡滚到山脚。父亲爬起来拍拍身上柴渣泥土,啧啧啧地可惜滚得遍地皆是的桐籽。父亲回到家说浑身无力,脑壳发眩。娘一急就让我请来镇上的医生,医生说营养不良贫血,给打了一大针筒葡萄糖。大姐姐一看父亲黄胆上脸没血色,就近去问仙娘,仙娘说父亲夜晚下河打鱼被钟潭的岩仙捉起了,要收魂。二姐姐说问了风水先生,是屋门口那棵老脱皮的桃树作的妖,桃之夭夭,不利户主寿命,强烈要求把桃树砍了,我心里暗暗叫苦,那还去哪里吃又乌又红蜜蜜甜的桃子啊。最后娘拍板,请仙娘招魂,请医生打针,等桃子下树再砍桃树。哪晓得什么都没来得及做,第二天天麻麻亮就出事了。由于家里人口多,我和父亲睡在不足六平方米的后堂,鸡叫三遍,父亲就一遍又一遍地叫我起床自己做饭呷了去读书,我乖乖地穿衣起床,出后堂门转出茶饭屋,抓一把刨花划根火柴点燃,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不过一分钟。我离开后堂的时候父亲还一动不动躺床上,可刨花点燃,父亲已经在正屋右侧百米开外的牛栏方向叫我了。更奇怪的是,父亲一声叫传到火堂,分明熊熊燃烧的火熖刀砍一样瞬间熄灭。我不由一惊,条件反射似地狠擂墙壁喊哥哥快起床。少顷,隔壁吱呀一声,哥哥推门而出,我立马奔过去跟上哥哥。我们走到父亲身边的时候,哥哥提着的煤油灯照见父亲光着脚双手抓着牛栏枋站在离茅厕二米远的地方,他很从容很平淡地对我说,我的鞋在那里,顺着父亲的手望去,父亲的两只鞋分别散落在茅桶的左右两边,我来不及设想,刚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只顾弓身去捡鞋的时候,一只手提灯,一只手扶着父亲的哥哥突然凄厉的叫了一声父亲,我猛然抬头,瞥见父亲嘴一咧,喉头一抽,头一丢,身子就软软地往下塌,我飞一样冲过去,紧紧抱着父亲,失声大叫父亲父亲……父亲勾着头,在两个儿子的拥抱下,静静地闭上双眼。
我和哥哥刚刚把父亲抱进堂屋,铺好垫被,让父亲平躺上去,门外就有堪堪十几声鞭炮炸响,一身黑的同年爷来了!我们兄弟姐妹五六个,慌忙跪地迎接。同年爷没理我们,径直走到父亲面前,呆立半晌,说,冇光眼,冇张嘴,你还死得蛮心安理得嘛。娘卖X的,光棍打到四十几,讨个二锅头(我娘嫁给我父亲时是二婚)还寡死味,得空就日日日,没几年就日出五六个,你以为肉是铁打的累不垮啊,活该!“该”字没落地,一只脚就弹离地面,快要触到父亲身体的时候,却全身软了下去,伏在父亲身上,嚎了起来:老同啊,你个无情无义的,一身轻快走了,叫我找个吵架的都找不到了啊!
没了父亲的家立刻变得艰难困苦。好在高中毕业务农两年的哥哥获得了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的机会。那时候真心是尊师重教的,全劳力每天十分工分,得除去下雨、病事假。而民办教师不仅每天12分,休假白休,每月硬梆梆360分工分,还发五块钱生活补贴。哥哥的职业变化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家庭困难,但并不能完全弥补丧父的损失。因此我十分纠结,一面学着父亲的样子按时往自己脑壳上涂桐油草灰,一面不停地向娘和哥哥提出辍学务农算了。其实提这样请求的时候,心里又巴望着娘和哥哥能坚定地驳回我的请求。事实上她们的确一次又一次地这么做了。当我获得继续学习的机会了,眼看着娘和哥哥陀螺一样忙碌的身影,我又禁不住心里发酸疼痛,上课不在状态,心不在焉地用钢笔尖去戳长在食指背面那个最大的鱼刺。乡里有个说法,鱼刺有公有母,母鱼刺死了,所有鱼刺就会自然消失。真能戳中母的就好了!怀着强烈的侥幸心里,我对食指背部的鱼刺一如怀着杀父之仇一样,不顾疼痛,推着金属笔尖狠狠地往深处戳,戳到有两三个毫米深了,就用另一只手压迫墨胆往里挤墨汁。心里指望墨汁是能除百病的灵药或者见人杀人见鬼杀鬼的毒药。我这样纯属瞎胡闹的做法,竟然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在当年征兵体检之前,鱼刺没了,铜钱疮也没了。我十分顺利地实现了当兵吃粮的愿望。临入伍前,我背着娘和哥哥,幻想着依然是父亲牵着我的手,跨过两重门槛,来到一屋黑又一身黑的同年爷床前,瞌了几个咚咚响的响头。然后冲同年爷说,我不想再回院子里养工,想当干部,你让菩萨哥哥保佑我好么?同年爷嘿嘿冷笑,丑丑娘卖B的,三寸钉高四两重,心倒不小,还想当干部啊。也是,那一年征兵身高标准156厘米,体重标准90市斤。我只有155厘米高,89市斤重,能被批准入伍已经是奇迹了,当军官的希望实在十分渺茫。但同年爷的态度,让我反感,在心里恨恨地骂了句“狗眼看人低”!愤愤然头也不回走了。出得屋内,身后传来幽幽的一句“闯狗屎运出息了莫黄眼珠!”像空山回音,像鬼叫。
同年爷上八十,再不回去就要让人指背皮了。
离开院子快二十年了。我出门当兵的第二年,哥哥民办转公办,把母亲带进城,姐姐们相继出嫁成了家。二十年没回院子,自然没见过同年爷。关于同年爷的事倒知道一些,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第一件,同年爷钱多,多少?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穿的内裤都缝上硕大的布袋,钱全都装在里面,他平躺的时候,耻骨一带总是鼓鼓囊囊,分不清是鸟大还是钱多。越是分不清越想分清,于是所有去他床前问事的,都会在他平躺着灵魂出窍会崽的时候,总会悄悄地盯他的裤包。吃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鸡、肉、鱼、蛋不在话下,红薯、芋头、粟米、春香、蕨根堆烂一屋。听娘说,我换上军装戴上大红花的当天,同年爷就打发人把我娘叫去,说了两句话,一句,从今天起,隔两天来拿一次呷的,喜欢什么拿什么,缺什么拿什么。二句,等我死了,你矮子崽出息了,叫他每年清明到我坟头踢一脚。第二件,前不久同年爷大病一场,总有七、八天没吃没喝闭门谢客,大约第八天的晚上,家里养的一条过年猪破栏而出,走得不知去向,近邻远亲纷纷自告奋勇要帮助找猪,他少见的咚一下挺尸一样坐起,你们想要我早死?找找找,找条卵啊。全场愣成死水,总有分把钟,终有一位聪明点的一拍脑壳,说,原来如此哦,大家快散了吧。祝神屌长命百岁。
同年爷80寿宴最大亮点,就是同年爷出奇地亢奋,虽然身体也有久病初愈的痕迹,比如面带菜色,比如气短音虚,但这些都掩饰不住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强烈自信。在心里,同年爷于我,就是汇仁肾宝,他好我也好。作别前,我说,好多年没来看你,一会就又要走,这一走,又不知要过多少年才能见面了。不过见不见面,我心里都是惦着你的,我不会做黄眼珠。同年爷哈哈大笑,你会来找我的。我惊奇的发现,此时同年爷的音容,“人”气十足,不像他平躺在黑屋床上那时,有“鬼”气,我一直怀疑,世界上如果有阳间阴间之分,同年爷的黑屋和平躺的同年爷,正是阴阳的接点,人鬼的混交。
同年爷还真有点“神”,八年后的一天,哥哥千里迢迢而来。好稀奇啊哥你可是从没来过的啊。还不是有事!你的事,大事。我的事,还大事?你莫吓我。
哥哥前几天梦见父亲,八百里加急似地对他说,有人要杀你弟弟,你快点去部队告诉他。其时逢双抢,哥哥打谷插秧忙不赢,暂时顾不上我。捱了两天没动。第三天晚上,父亲又来了,见面就凶巴巴地恶骂,你个没心肝的,我不在了,就该你管弟弟,明天你再不去,有你好看的。可双抢没扫尾,像哥哥那样的“半边户”,一家人不妇便幼,双抢如何离得了他?结果这一天就开始屙血。第二天又屙。哥哥被吓得一收工就往同年爷黑屋子里钻。把情况一摆,同年爷就板起脸来,快去快去,把矮子叫回来。哥哥扯起脚杆就跑。
好蹊跷啊哥说,你一累痔疮就发作,这有么子蹊跷!你得罪谁了嘛?我谁也没得罪,上好!那你不回去?同年爷的话你也不听?说实话,听哥哥讲故事的时候,我胸口凉了一下,背脊麻了一下,先凉后麻,又麻又凉。大概是父亲和同年爷都想我了。回去吧,正好刚搞完野营拉练,有几天轮休。
这一回太阳从西边出,同年爷双手拄着拐棍站在屋门口迎我。和同年爷两双手握在一起的霎那,天刚好断黑,屋里的灯火烛光显得格外明亮。今晚得在我屋呆一晚,我给你垒高台,追魂,同年爷说。屋里的场面让人震撼。中堂神龛两边挂满了道行莫测的菩萨,文殊、观世音、普贤、地藏,全是鬼中领袖,阴曹王候。菩萨脚下,一排四个红彤彤袈裟和尚。同年爷吩咐我和哥哥一旁坐下后,他打着拐棍一踮一瘸地走到袈裟的中间,一身黑立即显出不可撼动的威权。神龛下方的桌案上,红烛、檀香、鸡、肉、鱼三牲和酒,依次排列。同年爷轻咳了一声,正要开口,突然想起还没把双拐支在腋下。支好了,他说,香烛点好了,三牲供上了,各位菩萨请呷,大菩萨呷多的,小菩萨呷少的。“扑哧”,听着同年爷毫无专业素养的大白话祷词,我禁不住笑喷。早就听说同年爷是道中另类,亲眼看到奇葩如此却是头回。
垒高台并非真要垒台,它只是一场法事的名称。由红袈裟当中的一位主持。我问哥哥,同年爷怎么不亲自主持?那可是要颂许多经文的,一场法事下来,费时一个多时辰,除了中间敲点锣鼓吹点锁呐,就剩颂经了。同年爷没念过书,经文认得他他认不得经文,怎么主持啊。“咳咳”正嚼着同年爷的长舌,同年爷却拢来了,我赶忙拖条二人櫈,扶同年爷坐下,我陪着。劳同年爷辛苦。你真心还是假意?当然真心。哼,矮子矮一肚子拐。你信我这一套?我不信,不好意思啊同年爷。我就知道!可是你还是回来了。因为是同年爷召唤啊。还有你那短命鬼父亲呢。“咳咳”这老不死的,谁能当人崽的面骂人父亲短命鬼?糟老头子坏得很!同年爷对你家好么?好,同年爷对你好么?好得很。同年爷求你个事你会做么?……做。我心里打鼓,同年爷打什么鬼主意呢?帮我去把猪栏打开,你知道的,上八十那场大病,丢了一条猪,到如今我又活了八年,这八年我年年喂猪、放猪,那些猪比猪还猪,在外面摆盆潲也不肯迈出栏半步。同年爷用肘碰碰我,你是有身份的人,和我八字又合,可以加持我的命运。这可是我崽说的。我去,同年爷欢喜得什么似的,赶紧让人提盏斋灯跟着我。一路走我一路在心中默念,保佑同年爷长命百岁,保佑同年爷长命百岁。保佑……一边取猪栏枋,还一边念叨。可是,栏里那条跟同年爷一样全黑的壮猪,只一个劲嗷嗷地后退。退到最里的墙边便只剩下嗷嗷,脚是再不肯移动分毫了。
我十分难过,更是尴尬。怎么跟同年爷复命啊。
回头走,灯芒照耀下,屋后门那儿,一个蹒跚的身影,在缓缓地向屋里挪动。那头,比平时低了许多。很明显,一切他都看在眼里。
进后门就是同年爷平素平躺着和崽约会的地方。同年爷一言不发,极其平静地从橱子深处取出一厚叠崭新的衣裤。是寿衣。他当着我的面,脱得一身精光,又穿上里三层外三层的寿衣,里白、外黑混搭,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这么穿,穿齐崭了,脱掉鞋,上床平躺好,说,矮子,感谢你那么远回来为我送终。
在我小的时候,满院子都传,同年爷穿开裆裤的时候,许多人都亲眼看到,他的小鸡是弯的,像镰刀一样弯,一个精通相术的人说,这个人千百年前或许是个神,这一生即使是人,会生神崽,会是离神最近的那个人。
早上八点,第一束阳光射进同年爷屋里的时候,同年爷咽了气。
人无长生,包括我最亲的这个叫做神屌的人。只有土地,在你我脚下,长生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