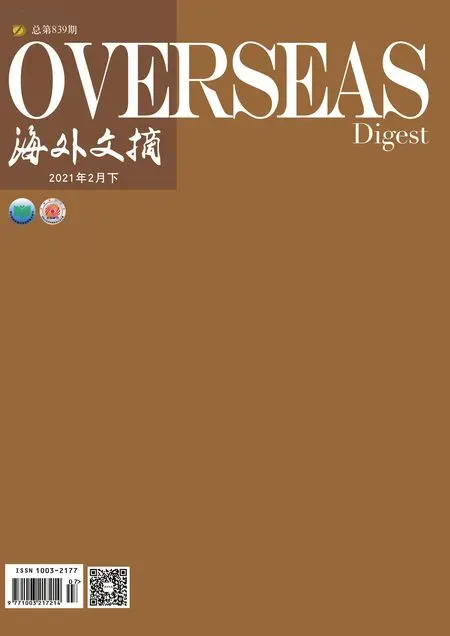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解读莎士比亚悲剧作品的艺术特点
2021-11-12唐澜心
唐澜心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成都 610066)
威 廉·莎 士 比 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诗人,现存剧本38部、长诗两首、十四行诗154首。《罗密欧与朱丽叶》是1595年创作的一部早期悲剧(喜剧创作高峰后,悲剧创作伊始的独家创作),但是“洋溢着喜剧精神”。创作背景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后期英国新旧国王即将交替,社会动荡性日益凸显,矛盾日益加剧,各种权势日益纠葛,承载着较为复杂的过渡性特征。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因此,从语言描写、情节构思、人物塑造、主旨表达四个方面展开分析便更有理据性。
1 语言描写:风格错杂,诗意流淌
1.1 诗一样的语言
《罗密欧与朱丽叶》有着“诗一样的语言”。黄奕采认为这部作品“有纯洁高雅、美丽动情的诗化语言。特别是那些巧用修辞、切情切境的诗化语言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极大地提升了文学品位。”郑媛眉认为十四行诗的格式在作品中十分典型,并且朱罗二人各自的独白、对白也颇有鲜明的“诗歌化”特征。
在句式结构层面,多用短句、散句。灵动短小,但蕴含丰富;疏疏落落,但形散神聚。正是在短小、简洁、精悍的语词之间,才最能肆意和轻松地直接倾吐悲愤之情,塑造出悲剧的鲜明特色。比如“名为睡眠,实则是永远的清醒!”“所以,你要像封面把他的一切分享,你拥有他,你自己绝不会缩小分量。在音韵节律方面,韵脚和谐,极具音乐美。这种形式美最能让人沉浸其中,深度感知作品的情感意蕴,从一句又一句的深情中欣赏美,进而也最大限度地品尝所有苦涩滋味。比如,“唉!这就是爱情误入迷津,愁肠百结重压在我心庭,蒙你感同身受,你的悲情。”在修辞表达层面,主要采用比喻、双关、拟人手法,将一些抽象的、不可理解的情感具体化,含蓄地将悲苦潜隐而换一种形式艺术化的存在。比如“我陷落了,爱的担子重若山丘”,又如很多意象被“符号化”以暗示二人的感情和命运,在故事开篇的诗句中出现的“star-cross dlovers”将二人比喻成“终将要陨落的双子星”,很是引人动容。
1.2 典雅与世俗化并存
这部悲剧在语言上还拥有错杂与极端化的质感,即“同时保留了平民化和宫廷化相结合的语言风格。”罗密欧、朱丽叶、劳伦斯神父等人的语言典雅色彩浓重,每次开口都有一种豪奢精致的高雅既视感。如“你纵使给我引见一位绝世佳人,她的美只是对我把另一个更美者提醒,此外还有何用处于我可心?再见,你不能教给我忘情的本领。”而与之相反的是奶妈、葛雷古利、桑泼生等人,语言粗俗,多用下流语词、性暗示隐语、随意的日常用语,如“我敢发誓,以我十二岁童贞做抵押:我真叫过她。嘿,小绵羊!嘿,小骚货!”“那当然,那样的话,咱们跟没饭吃(煤贩子)一样倒霉。”“蒙太古家里的狗就会让我冲动起来。”“正在和湿里吧唧的黑夜厮混”。尤其在对白体中,这种与典雅风格形成的反差、冲突尤为剧烈和夸张。
因此,“这种‘参差不齐’使得戏剧在表演或者被阅读的过程中,都能够产生‘戏剧式’的效果。”进而使我们可敏锐地捕捉到——作者通过语言风格的内部差异,隐约寄托对当时不同群体的怜悯与同情之笔法。因为粗俗语言背后或有诙谐或有毒辣,典雅语言背后或有掩饰或有逆反,但都间接折射出了人内心的空虚浮躁、混乱压抑。
2 情节构思:宿命导向,节奏跳跃
2.1 宿命导向,天意为先
整部作品从头到尾都有一种鲜明的宿命导向。从朱罗二人上场开始,作者就采用隐喻手法,把二人比作终将要陨落的双子星,将其最终命运巧妙地和盘托出。如“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情感进行的过程中,两个人在舞会上(平地)相遇,阳台上(半空)的两次幽会以及最终在墓中(地底)的殉情,非常严谨地符合了这对双子星命运中‘相遇—升起—陨落’的呼应。”
另外,劳伦斯神父谶语的暗示性与前后态度的转变鲜明地反衬出了他内心的激烈斗争——命运掌控论与宿命论的博弈,而最终的结局宣告了前者的破产。他虽早以理性之眼观瞻二人情感动向,做出了准确预判,极力反对二人在一起,却最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二人的情感牵线搭桥。可见,情节层层冲突的节节铺设不过是换来了更有力的宿命论召唤,如此抗争得愈激烈,如是‘悲剧”得愈彻底。
2.2 节奏跳跃,迅速推进
首先在幕与幕之间,这种节奏的跳跃性最为显著。因为地点改变、人物洗牌,从上一幕一句仿佛还没说完的对白亦或是情节就直接跳跃到另一个时间点或另一个事件。笔者在阅读第二、三幕时,体验尤为深刻。第二幕还在讲述劳伦斯神父告诫朱罗二人必须完婚才能在一起,下一幕就直接跳到一个闹市去了,故笔者一度以为神父的话还未说完。其次在场与场之间,这种切换也有点令人应接不暇。比如第一幕的第四场和第五场。第四场还在描写罗与迈谈论梦境的事宜,接下来笔锋一转就到了凯普莱特家的厅堂里,两人之间的对话还在笔者耳边萦绕,一下子就跳到仆人分工忙碌的对白,实在让人难以迅速反应过来。
《罗密欧与朱丽叶》“对于故事的叙述常常省去繁冗的细节而直击故事发展的关键情节。在艺术性上而言,这样的故事叙述方式使得戏剧的矛盾冲突更为紧凑,利于增添故事情节的张力。”正是在快速推进、节奏跳跃的情节中才能更加集中戏剧矛盾,给人造成心灵上的冲击,彰显强烈的悲剧意义。
2.3 喜剧情节,反衬悲情
“从莎士比亚所创作的悲剧来看,其打破了传统悲剧的故事情节,安排了大量喜剧情节。”一是少女怀春时的夸张抒情渲染喜剧性,比如朱丽叶在见了罗密欧之后独白:“啊,罗密欧,罗密欧!为何是这名称?快否认你的父姓,抛弃你的本名;你纵然不肯,但只消发誓做我的爱人,我便从此改变这凯普莱特之姓。”二是借助奶妈与朱丽叶闲聊的幽默情节——“嫁期问题!假如我不是你唯一的奶的妈,我一定要说你的聪明是从奶头上吸来的”来反衬女主人公内心对奶妈前言后语不一致的怀疑与失望。
所谓“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莎士比亚不是把这些喜剧情节作为单纯的调味佐料,更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约翰逊认为,“不能否认混合体的戏剧可能给人以悲剧或喜剧的全部教导,因为它在交替表演中把二者都包括在内,而且较二者之一更接近生活的面貌。”因此,通过一定的喜剧情节的构建,才完成了对一体多面的人生本质的探讨;才能更进一步地彰显出悲剧气氛、结构和故事情节的完整性;才能更好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性。此类喜剧情节在很大程度上非但不会影响观众的观赏情绪,而且还使得悲剧的悲凉气氛更加凝重、可悲,加大了它的凄惨氛围,所以获得了更好的戏剧观赏效果。
3 人物塑造:痴狂显著,矛盾突出
在这部作品的人物塑造上,作者较为成功地把人物本身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人物都具有一个共性——趋向痴狂,越发显著;矛盾显露,越发突出。痴狂和矛盾这两种特点集中表现在情感领域和行为领域。
在情感方面,朱丽叶对罗密欧的情感不是一直稳定的,而是在痴与狂的边缘打转。她一开始对罗密欧就有一种超越一切的炽爱,但是在罗密欧杀了自己的表哥之后,很明显她动摇得很剧烈,甚至有种极致的仇视感。如由“暴君装风流倜傥!魔鬼扮天使形象!黑鸦披白鸽丰羽,恶狼似温驯羔羊!道貌岸然的外表掩盖着灵魂的肮脏!看上去有模有样,骨子里丑恶荒唐。”这样一段恶毒的讽刺突然变为“他既是我夫君,我岂能恶言诽谤?足见其内心冲突矛盾。而罗密欧也是如此,他从痴迷于罗瑟琳那么多年突然转而喜欢上朱丽叶,变化实在迅疾,体现出痴、疯、狂的特点,由“几何时你还对罗瑟琳一往情深,今日忽弃如敝屣?年少者之爱情非珍藏于心底,而只寄托于眼睛。圣母马利亚在上!”可见。在行为领域,神甫虽已意识到“狂暴的快乐常常有狂暴的结局”,却仍然为年轻的恋人秘密举行婚礼;帕里斯虽然最后可坐收渔翁之利,但他利令智昏地与罗密欧决一死战。这些矛盾着实令人焦灼和感叹,同时也让人从中自然而然地生出一份低落与审视的心情,去静静的、反复的体会这些人物身上的悲剧色彩。
4 主旨表达:人文色彩,理性观照
在这部悲剧中,既充盈着一种人文主义色彩,也充斥着理性和审判精神。在人文主义色彩的烘托上,该作品从语言表达和人物塑造的角度出发,将主人公的爱与情,自主与斗争凸显得十分具体。莎翁悲剧具有独特的魅力,揭示了心灵内在化的趋势,诚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在现实的冲突与理想的幻灭中营造出一种极致的矛盾,在矛盾中郁结作者对人文主义的呐喊与追求。比如,其中涵盖了两代人的代际冲突。朱罗二人皆受老一代顽固思想的阻碍,乃至造成了二人最后的殉情结局。因此,作者充分肯定了朱丽叶与罗密欧之间自由的恋爱模式,冲破一切阻隔仍旧要在一起的,冲锋陷阵式的纯爱风格。尤其是朱丽叶,“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理想中的新女性,在她身上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新的恋爱观。他们所经受的那种感情不是普通的人的感情,而是精神的巨大冲动。”
李伟民认为这部作品“并没有对于人性的深刻的解剖,只是真挚地道出了全世界青年男女的心声。”在笔者看来,这部作品同时也在抒发人文主义基础之上存在的许多理性观照部分。如在前文中出现的“名为睡眠,实则是永远的清醒!”“狂暴的快乐常常有狂暴的结局”“还有何辞可喻?最疯狂却又最审慎,苦,苦到喉哽;甜,甜到钻心。”等,这一系列短小的句子都蕴含了强大的启示性与哲理性意义。又如在结尾,亲王说道“天帝假手于爱,让你们痛断肝肠。我因姑息放纵了你们多年的争执,也痛失双亲:人人落得惩罚下场。”这段话其实深层地揭示了作品在爱的宣扬中沉淀下来的静谧感——人对自我的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觉察与反省。这其中充满着肃穆与庄严,宛若星河一般缓缓流淌进所有人的心灵,一步一步地引导着人们颖悟悲剧的根源,我们日后应该如何去改变以去汲取两个年轻人之死所带来的教训。
5 结语
纵观上文,《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它完美地展现了悲喜剧的中间状态,与此同时也延续了依然十分明显的悲剧性意味与倾向。具体来说,它有一种“反”“逆”的精神,体现在其语言描写诗意化、典雅化也世俗化;其情节构思充满宿命性、跳跃性也以喜称悲;其人物塑造洋溢痴狂性、矛盾性;其主旨表达寓寄人文性、哲理性。正所谓处处有痴狂流涡,处处也有静谧星河。一言以蔽之,我们不能忽视这部作品之于莎士比亚悲剧艺术特点之探讨的重要地位与鲜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