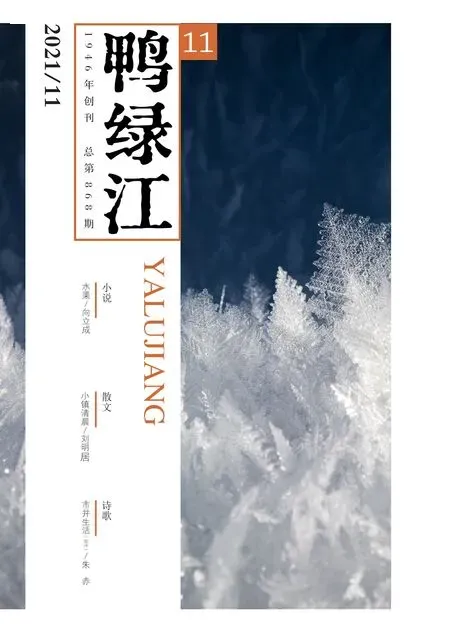看电影
2021-11-11山汉
山 汉
提起看电影,想必现在根本不是什么值得人们稀奇的新鲜事了,也根本不再是什么能够吊足人们的胃口、令人们会从灵魂深处生发出来一种迫切渴望享受的精神企求了。因为如今人们看电影就像天天吃大米白面的一样,早已成了家家户户的家常便饭了。
而就电影本身来说,之所以能够迎来今天这样被广泛普及到家家户户的可喜局面,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健步走向世界之后,不但快速解决了老百姓穿衣吃饭的温饱问题,而且也使人们的精神文明享受与物质文明享受得到了同步的全方位、多渠道、多层面的提高。一句话,如今人们几乎谁也不再缺电影看了。
但是在我们这些从大山深沟中走出来的人的记忆中,那时候的电影就是一个稀缺物中的稀缺物,人们是很难与其谋面的。尤其是地处荒僻的山乡民众,常常一年半载也很难看上一场电影。因此,当年我和我的那些小伙伴,为了一饱眼福,曾结伙搭伴,三五成群,不惜黑天夜半,长途跋涉,往返跑上十几二十里的路程,去看一场电影。
听大人们说,那时候我们子洲县还没有电影放映队,人们看电影全靠邻县绥德的电影队跨县来放映。还说绥德的电影队当时好像分三个放映队,这三个放映队在一年四季中要马不停蹄地赶着骡子,驮着老式的16毫米放映机,和四个好后生抬着也感到吃力的笨重的老式发电机,翻山越岭,走乡串村,依次对两县一千多个行政村进行电影放映宣传。有时一晚上还要跑两个村子放映,就是一个村子刚放过之后,连夜就又要到另一个村里去放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放映宣传任务的完成。但有时因刮大风、下大雨等情况,一年的宣传任务还是难以完成。这样一来,那些边远的小村庄的村民,自然就看不上电影了。
当时,我们那些碎脑娃娃只要听到那些消息灵通的大人说,我们村里什么时候要放电影了,或者说在就近三五里、八九十来里路的哪个村庄,啥时候要放电影了,就意味着我们村里也很快就要放电影了。而只要这消息得到有头有脸的人确认,我们那小小的心脏就都跳动得更加欢快有力了。于是,我们常常会激动地聚一起,一边共同回味和嚷吵着之前看过的那些电影,一边又竞相猜测着,这次究竟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电影。
如此,我们一天天地掰着指头计算,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终于盼来了电影放映队走进我们村里的一天,我们便兴奋地欢呼雀跃,仰天长啸,并不忘奔走相告,好像比过年还要激动和开心。
但可笑的是,当时我们好多娃娃,甚至一些大人们,竟然谁都不懂得那影幕叫作影幕,发电叫作发电,放映员叫作放映员。也不知是从谁开始叫的,大家就鹦鹉学舌似的都跟着管那影幕叫作亮子,管发电叫作磨电,而管那放映员又叫作耍电影的。但无论叫什么,都无所谓,关键是我们都能够听懂。
那时,我们村里放电影常被大队安排在沟岔上,也就是村口侧一座神庙前的一块宽阔而平坦的空地上。所以,每当太阳还没有落山,那雪亮的影幕被那耍电影的挂在神庙的门面前时,满村子的娃娃就像过节一般,在那东面山上和西面山上的一处处农家院落的硷畔前、坡坬上,蹦蹦跳跳,大喊大叫,“喔——哎——亮子挂起来了!喔——哎——就要磨电了!就要耍电影了!”那喊叫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直冲云霄。
于是,有好些孩子甚至连晚饭也顾不得吃,就火急火燎地跑到沟岔上,将一块块石头或者砖头,像蚂蚁搬家似的,搬在那神庙前的空地上,为自己和家里的兄弟姐妹率先抢占那观看电影的最佳位置,垒好一个个座位。
在耍电影的开始调试镜头焦距的时候,一些胆大调皮的捣蛋鬼,又时不时地故意站起身来,摆出各种姿势,或者用双手做出各种动物造型,借助镜头上的强光,将那影像投射在雪亮的银幕上玩耍,常常引来大家开心快乐的一阵阵欢笑声。
耍电影的在正式放映前,总要播放一些幻灯宣传片,即由一人放幻灯,一人则打着莲花落,向观众进行说唱宣传。那幻灯都是图文并茂,内容大多是上面的路线、政策、方针什么的,还有英雄模范人物故事等的宣传。等到将近半小时的幻灯宣传结束之后,焦急的人们才能够正儿八经地看上那要放的电影。
我最早看电影大约是五六岁的时候。现在我还记得,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南征北战》。之后,随着一年年长大,我又陆续看到《英雄虎胆》《平原游击队》《沙漠追匪记》《刘三姐》《洪湖赤卫队》《兵临城下》《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等。这些拍摄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影片,估计现在年龄稍大一点的人都看过,基本是枪林弹雨炮火连天的战争片。而这正合我们的心意,因为我们就爱看这样的打仗电影,就觉得看打仗电影特别兴奋,也特别过瘾。尤其当我们看到《南征北战》中那个胖墩墩的战士李进,在英勇负伤后,还连滚带爬地炸掉了敌人的坦克;《英雄儿女》中身负重伤的王成,毅然双手紧捂爆破筒,纵身怒目高呼“向我开炮”的时候,我们被一次次感动得热血沸腾,热泪涌流……
当时,农村放电影少不说,关键是片源也少得可怜,几年时间,也就只能看到那么几部老片子。可是就这样,到了后来,在我们所看过的那些电影中,也就只能看到“三战”了。而再能看到的,基本是八个样板戏了。因此,单单是“三战”,那时候我们不知看了多少遍。所以直至现在,我们不但依然能够完整地唱出这些电影的插曲来,而且还能够一字不差地说出其中的某些经典台词来。比如,某某为大家正愁无法解决的问题,忽然脑洞大开地想出了一个什么好点子的时候,有人马上就会暗笑着伸出大拇指夸赞说“高,实在是高”。这话就是出演《地道战》中皇协军司令汤丙会的演员刘江,为出演日军分队长山田的演员王孝忠所拍过的一句经典马屁。由此可见,我们当时对所看的每一部电影,用情多专多深。
那时候,也有一些外国电影被翻译进国门来,其中有朝鲜的一部电影叫《卖花姑娘》,还着实牵动了我国无数观众的心,曾令好多善良的国人感动得流了不少的眼泪。记得我是在1972年隆冬的一个风雪之夜看的这部电影。
那天晚上,天空雪花漫舞,寒风劲吹,但我和我们村里的好多青少年甚至中老年却无惧天气的恶劣,也不怕穿着单薄破旧、挨冻受凉,都大老远地跑到集镇上去了。因为大家都听说那晚镇上要放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而且据说是由什么双头机子放映的35毫米的彩色宽银幕电影,中间根本就不用等待停机换片,而是一气儿就可以看完的。所以,村里凡是爱看电影的人,那晚基本都赶到镇上去看了。
那晚看电影的人很多,直将那集镇街头放电影的一大块空地站了个满满当当,想必周边村庄爱看电影的人都来看了。而电影却放得很迟很迟,因为影片要等30里之外的县城放过之后,才能送到我们镇子上。所以,人们就那样在风雪之中,抱着膀子,跺着双脚,咬着牙把子,聚集在那空地上耐心地等了将近三个小时,电影放映队方才急匆匆地赶来。
于是,风雪中无数观众无不被那从未见过的宽银幕的壮观景象震撼、为之倾倒,很快又随着电影的优美旋律,听着那凄婉动人的“卖花来哟,卖花来哟,朵朵红花多鲜艳;花儿多香,花儿多鲜,美丽的花儿红艳艳”的主题歌,看到卖花姑娘花妮用自己千辛万苦卖花得来的钱,买来药想医治好妈妈,想照顾好被地主婆烫瞎了双眼的妹妹,想努力撑起她们那个破碎不堪的家,又出去寻找哥哥。但妈妈却已去世多时,哥哥又传来已死的噩耗,而孤苦伶仃的妹妹亦被狠心的地主婆以阴魂附体为由,于风雪迷漫中将她扔在了山沟里,等等。这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剧情,无不令人痛断肝肠。适逢天上也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鹅毛大雪,于是,一时间银幕内外,情景交融,凄风烈烈,大雪纷飞。而观众中早已唏嘘不已,人们全都哭得一塌糊涂……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少林寺》《英雄本色》《男儿当自强》等电影在内地相继爆红之后,我们的电影便迅速崛起,并很快走向全新发展的道路。而随着电视机的不断普及,看电影的条件越来越好,国人无论老小,基本上连家门也不用出,手指一按,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看到各式各样的电影,甚至还能看到许多国际大片。20世纪90年代之后,电脑和智能手机以及互联网的逐步繁荣发展,和电视剧的大量出现,使看电影的热度逐渐下降,但是,3D、4D电影的出现,让人们在看电影的整体层次上更上一层楼。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男男女女,牵手相伴,甩手百八十块钱购得两张电影票,就可以轻松地走进那豪华高清影院,去尽情欣赏自己想要欣赏的电影,这是何等从容自在,何等潇洒浪漫啊!
电影虽不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但是从我小时候到现在,通过看电影的经历,即可透视出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轨迹,和祖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发展历程。在物质生活得到很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精神方面的力量,依然需要中华传统文化的文明健康发展和传播,因为除了高新科技,只有传统文化才是我们走向世界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