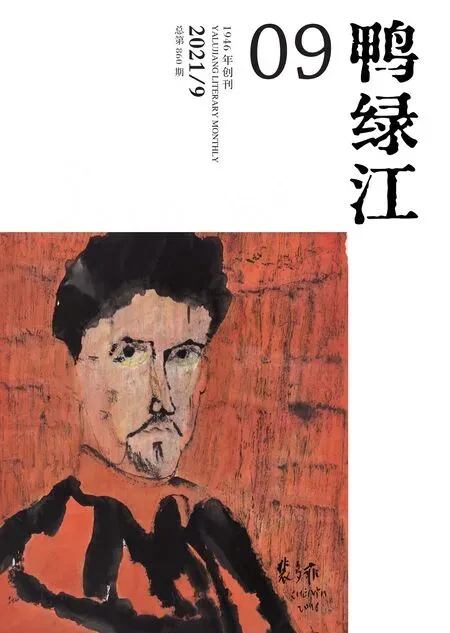自传与公传(节选)
2021-11-11董学仁
董学仁
1979年
因为粮食由国家限量供应,工厂里没有食堂。工人们上下班拎着布兜,里面是大号的铝皮饭盒、中号的铝皮菜盒。车间里有个气锅,能把职工的生米蒸成熟饭。菜是在家就做好的,放在气锅旁边,保持着温暖。
我们的饭量真够大的,都能吃下整整一盒蒸高粱米饭,或者掺了大米的高粱米饭——不那么硬了,口感好一些。我在铁东区铆焊厂的第一年,大家还都是高粱米饭,第二年就开始掺大米了。
我在铁东区铆焊厂的第一年,老工人从家里带来的菜,总是那么几样,炒白菜、煮萝卜、炖土豆,都没有加鸡蛋和肉,所以虽然都坐在一起吃饭,也各吃各的,用不着请别人尝尝自己的菜。到了第二年,商店里卖的猪肉多了,鸡蛋也多了,偶尔出现在大家的菜盒里。
这里说的第二年,就是1979年。
春节过后一个多星期,我家里还有肉吃,这是这些年里从来没有的事。记得我那一天上大头班,带去了一些做菜的原料,绿豆芽、葱丝、香菜,一点盐和凝固的猪油,最重要的是,还有几粒炸熟的猪肉丸子,说是晚饭剩的,其实是我妈没舍得吃,非要我带到工厂去不可。
吃饭时间到了,我开始煮我的丸子豆芽汤:弄来一块烧红的铁板,铝饭盒里盛水煮开,顺序投入猪油、葱丝、丸子、豆芽、盐和香菜。没有几分钟,车间里就飘荡出一片很浓的香气,把吃饭的人全都吸引过来啦。
一些年后,我弄了同样的原料,想做出同样美味的汤,几次实验都不成功。于是我知道了,人世间的有些事情,其实是唯一性的,根本无法复制。
如果说还有复制的办法,也得回到同样的环境:穿一身完全变硬、汗碱层叠的劳动服,蹲在由橘红渐变为暗红的铁板前面,舀起一勺热汤倒入长期营养不足的肠胃。
或许,还要有空中飘浮的沥青微粒。
在那个漫长冬日的夜晚,它可能是那道热汤特殊香气的组成成分。
铁东区铆焊厂那种用沥青润滑轧辊的老轧机,现在,全世界都再也找不到一台。它于20世纪初由德国人制造出来,再由日本企业主买来安装在伪满洲国的工厂。后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还在中国鞍山的铁东区铆焊厂里转动,生产一些热轧薄板与工伤事故。大约我离开那家工厂五年后,那个车间被撤销。那台与人寿命仿佛的老轧机,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死了。
它的活着,就是它不停歇的运转。比起在它前面流汗干活儿的一批批、一代代工人们,它见过更多的事情。如果它是历史,我和许多人只是它的一部分,为了完成它的使命而存在。
我与它在一起的时间两年多,可是并不总在它的身边。
时常把我从轧机前拉走的,有车间工会,也有厂工会,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然后再回来。工会逢年过节搞些应季的宣传,或者有宣传国家政策的临时任务,都会找我去搞个展览橱窗,写些大字标语。这样零零散散的时间加在一起,估计有半年以上。
在那家有五百多人的工厂里,我可能是最好的美工,也可能会写出最好的文字材料,但厂里不会把我调离生产岗位,专职负责宣传事务,那是从工人到干部的一次身份跨越,很难完成。虽然是这样,我还是感谢那些写写画画的工作,让我从疲惫不堪的轧机前脱身,得到一次次休息与调整,不然的话,我的身体可能会垮掉。
有一次,我在厂门左侧画了一幅临摹的宣传画。它画幅很大,高约三米,宽七八米,标题也很长,大约是“团结起来,鼓足干劲,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画面上有十多个人物,挺胸抬头,造型相似,神情呆板,没有性格,像是其中一个人的翻版,只是他们手中道具不同,显示出了他们不同的职业和身份。
本来三四天可以画完,我却有意放慢了速度,画了一个多星期。一是我很享受它的制作过程,这比在轧机前干活儿好多了;二是画得慢一些才不会太差。我先前学的是水粉画,还是第一次用油画颜料制作巨幅人物画呢。
有一次画到最后一块展板,想不出合适的图案了。我就把展板搬到室外一棵柳树旁边,让阳光把柳树枝条的影子投在上面,再用笔和颜料把它描摹出来。
我退后了两步,看展板上的柳树。
那是一棵有三五十年树龄的老树,可能生于中华民国时期,可能生于伪满洲国。如果有一阵风吹过来,它会忘记它的历史、它的幸与不幸,在我的展板上摇摇晃晃。
你有什么可追悔的呢?
你是你的经历与环境的产物,还有,你的性格也是它们决定的呀。有一个童话,穷人家的孩子遇到了王子,换了衣服,换了身份,看起来一步登天,可那也是经历与环境的产物,像抽中了特等奖,不是别的。
如果把我放回到过去的某一段时光,比如说1979年考大学的那段时光,再用力拼一次,我也不能比那时更好,或者更差。
我想考大学,改变我在铁东区铆焊厂的恶劣环境,是在春节前定下来的。同一车间的万兵在前一年考上大学,吉良也考了,分数不够,今年还考,等他考上大学离开,我真就孤单了。万兵与吉良,是那个车间里,我能够相互交流的朋友。
与他们一样,我也想考文科。离开中学校门,一晃七年,再学数理化来不及了,赶不上应届的中学毕业生。还有一点没法与他们相比,他们是高考前的半年里,复习这几年学过的知识,对我来说可不是复习,是把那些考试科目学一遍,几个月学完,时间太紧了,只能考文科。
其实我想考美术学院,可在重开大学的两年里,鞍山只考上一个人。有个消息说,今年考大学的年龄放宽到二十五周岁,而我已经二十四周岁了。
考吧。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
也许,对我来说,有一次机会就够了。
我只有一次机会,与戏剧界人士谈契诃夫戏剧。
是在1979年,我去外地读中文系之前。
那时,辽宁省公布考生成绩和录取分数线在先,考生选择读哪所大学在后。这样做挺好,考生选择不当而落榜的风险就少了。我认识的一名考生分数很高,但不知道各地都有哪些大学,只记得好多年前革命领袖的一句话,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就报了锦州一所大学,许多年以后还在后悔。
我就是在那时认识小顾的。小顾的分数与我的相近,那几天我都去他家里找他,商量怎样填报志愿。后来我们一起去了辽宁师范学院,都读中文系。
我也认识了小顾的父母。顾叔叔很瘦很高,说起话来平静温和,五十多岁了还显得英俊,是我见到的最像知识分子的长辈。建国之初,顾叔叔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出演过一部电影里的人物,更多的时候当场记。后来有些场记出身的人当了电影导演,顾叔叔却离开电影制片厂来到鞍山,偶尔在辅导群众戏剧创作时才有导演身份。但在我坐在他对面时,还不知道他在电影制片厂的经历,我们的话题就没有说到电影。
坐在顾叔叔对面,听他谈上几个小时话剧,是1979年里我最舒适的时光。
我告诉他,我离开中学后学了水粉画,话剧团想调我去画布景,但是没有去成,这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这件事成了我们谈话的起点,顾叔叔接着说,话剧团里的人都有哪些分工,编剧和导演怎样工作,怎样让一部话剧让人看得下去。说到这里,就遇到了理论方面的一些观念。
顾叔叔告诉我,人们都说是苏联的戏剧观念指导中国话剧,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体系,是在俄国时期创造的。接下去他说了这个体系中的一些观点,包括表演、导演、戏剧教学和方法,集合了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己在内的一些戏剧大师的经验。
我有一本书,你可以带回去看。顾叔叔说。
这时我就想起了契诃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了契诃夫的几部话剧,听了顾叔叔的讲解,我觉得这位戏剧大师的某个观念,是从契诃夫戏剧里演绎出来的。我读过契诃夫的小说和几部话剧,书是从西长甸废品收购站里翻出来的,繁体字,竖排版。
在我看来,契诃夫不只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更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为了让顾叔叔同意我的看法,我说到了契诃夫的《海鸥》《樱桃园》《三姊妹》《万尼亚舅舅》,那时我正对契诃夫入迷,剧中人物的有些对白都能复述出来。
《三姊妹》的一个人说:“火车站近了就是不远,远了就是不近。”
《樱桃园》的一个人说:“人类向着地面上允许有的最高的幸福,节节前进。”
还有一部话剧,一个人说:“我不了解您,您不了解我,我们也不了解我们自己。”
《万尼亚舅舅》中的一句话很长:“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活过无数悠长的白日和疲倦的夜晚,我们要耐心忍受命运加给我们的考验,我们会听见天使的歌唱,我们会看见所有人世的罪恶。”
从鞍山去大连,硬座火车四五个小时。车上人不多,有空座。即使是大学新生入学的前后几天,车上也不紧张。这件事想一想就会明白,1979年有接近五百万人考大学,但考上的太少了,大约百分之六,二十八万多人,还不到现在每年考上研究生的一半儿,当然不会把南来北往的火车塞满。
大连站在辽东半岛顶端,火车到这里必须停下来,再往前开就开到海里去了。
迎接我的是海腥味,很浓很香。那香味带着热气,从街边一个个麻袋里冒出来。卖熟贻贝的商贩,接过我递过去的一角钱,从麻袋里盛了冒尖的一大碗熟贻贝,装进大纸袋,送到我手里。大街上很多人像我一样,边走边吃,贻贝壳扔了一地,在脚下咔咔地响,仿佛音乐。
转过街角,一名年轻妇女拦住我,向我要钱。她耸了耸怀里的小男孩,说她和孩子想回哈尔滨,钱丢了。我的衣袋里有钱,七十多元,是我到大学第一个学期的全部费用,数出不到三元钱给她。不能给她更多了,这让我感到一些歉意。
在火车站前转了一圈儿,肚子饿了。
旁边是一家鱼肉馅饺子馆,不算贵,一元五一斤,六角钱能买四两,差不多够我吃的了。又走到旁边那家,我高兴地看见,一碗米饭一盘炒土豆丝只要两角钱。
快要吃饱的时候,我往左右看了几眼。墙角那张桌子,一个小男孩朝我这边笑着,让我觉得愉快和温暖。我看着小男孩有些面熟,直到他妈妈端着饭菜走到他面前,我才想起来,不到半个小时之前我见过这母子二人。他的妈妈买了两盘炒菜,都比我吃的土豆丝贵多了,也不知道节省一点,我掏给他们的那几元钱,只够他们吃两三顿饭的。回哈尔滨的车票钱,他们要来多少?够用了吗?
过了一个多月,再从那家饭店门前走过,我偶然想到,那名年轻妇女可能是个专业乞讨的人,回哈尔滨只是她用来乞讨的借口之一。那个小男孩可能会跟着妈妈,从一个城市乞讨到另一个城市,在流浪中慢慢长大。
有个年轻人在工厂干了四年,然后考上大学。上班那几年,他每年的工资大约四百元,吃饭穿衣,偶尔买书,剩下的钱不多了。上班第三年买了一辆长征牌自行车,第四年离开工厂前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这在1979年可不是小事。城里男青年结婚时,能给女青年送齐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样东西,生活水平就属于中等阶层,等同于国外的中产阶级了。但这个年轻人运气不算好,他的自行车骑了不到一年被小偷偷走,手表戴了一年也被偷走,什么都没剩下。
他想站在街上,把他看不见的小偷狠狠骂一顿,可是他只会一句骂人的话,不够骂一顿的。于是,他连骂一句的兴趣都没了。
你也许猜到了,那个年轻人是我。
在我的回忆里,不止一次地提到西长甸废品收购站,是因为我对它充满了感激。我是那家收购站里不占编制、不拿工资的美工,唯一的酬劳是允许我翻检这里收购来的旧书,想看什么就带回家去。
那些年月,阶级革命的波涛汹涌,大学关门了,图书馆关闭了,出版业严格控制,但我找到了一条通道,与先前的时代连接起来。这通道就是废品收购站里的旧书。
离开中学校门,再走进大学校门,这中间有七年时光,可以读书。
我学会了怎样用比较短的时间,从西长甸废品收购站小山一样堆积的旧书里,挑出有价值的好书,这是一种经验,要看过很多不该看的书才能养成。于是,我在1979年跨进大学校门,首先发现的不是可以看的好书,而是“不该看的坏书”。
记得有句名言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这句话是错误的,只有好书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坏书不是进步的阶梯,而是退步的滑梯,能让人类迅速倒退到愚昧时期,并且比先前所有的愚昧更甚。我记得这句名言是高尔基说的。
在我读大学之前和之后的好长时间里,一直不把教材当成书,但它又确实是书,所以也有好坏之分。我在先前的回忆里,写过这样的观点:人人都有不幸运的时候,有的人甚至一生都不幸运。他们即使读了本科或硕士、博士,也仅仅学到一些知识的皮毛,没有形成自己的学问,甚至没有从狭隘、偏见、歪曲和有害的知识中挣扎出来的本领。他们没有走向正确的方向,对人类的进步没有益处。
我曾经迷恋艾利蒂斯的诗歌。
虽然他在1979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直到八年以后,中国大陆才出版赛弗里斯与艾利蒂斯的诗歌合集。在此空白的时间里,我只能把散见的艾利蒂斯诗歌抄录下来。
1985年春季,我与一位女士旅行结婚去了北京,投宿在诗人王家新的家里。那天晚上,我找到一本民刊《今天》,有赵振开即北岛的一篇小说,还找到一份香港杂志,有黄维梁译的《疯狂的石榴树》。艾利蒂斯的这首诗,我已有了两个中文译本:袁可嘉的,李野光的。同一首诗歌,读到了第三个译本,仍然让我兴奋不已。
当赤身裸体的姑娘们在草地上醒来,
用雪白的手采摘青青的三叶草,
在梦的边缘上游荡,告诉我,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出其不意地把亮光照到她们新编的篮子上,
使她们的名字在鸟儿的歌声中回响,告诉我,
是那疯了的石榴树与多云的天空在较量?
比较我看到的三个译本,这一节还是袁可嘉的译本好。那些词语并不平庸,鲜活和清新,充满了生命感,有我理解的艾利蒂斯的光明和清澈。我还喜欢这个译本的最后一节,读起来很顺畅:
在四月初春的裙子和八月中旬的蝉声中,
告诉我,那个欢跳的她,狂怒的她,诱人的她,
那驱逐一切恶意的黑色的、邪恶的阴影的人儿,
把晕头转向的鸟倾泻于太阳胸脯上的人儿,
告诉我,在万物怀里,在我们最深沉的梦乡里,
展开翅膀的她,就是那疯狂的石榴树吗?
我想知道,对于艾利蒂斯来说,“一切恶意的黑色的、邪恶的阴影”是什么?
任何时候都不是诗人写诗的最好年月,任何地方都不是诗人写诗的最好环境。
艾利蒂斯遇到的也不是,大约是1945年到1959年,他曾经有十多年没有写诗。这像太阳收回它的光线,像木柴怜惜它的燃烧,像膝头受伤的少年,头发剪短了,梦也剪短了。我还想知道,停笔不写的诗人,你在你的时代看见了什么呢?
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诗人有什么用呢?对人类来说,不幸得很,年代一直是贫瘠的。
在离艾利蒂斯很远的地方,年代也很遥远了,我看见我自己,也看见一些年轻人不再写诗。我们在语言上的才华无法安置,我们内心的生活,比写诗过程中的痛苦还要痛苦。我们不再哀叹了,但我们的血无缘无故地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