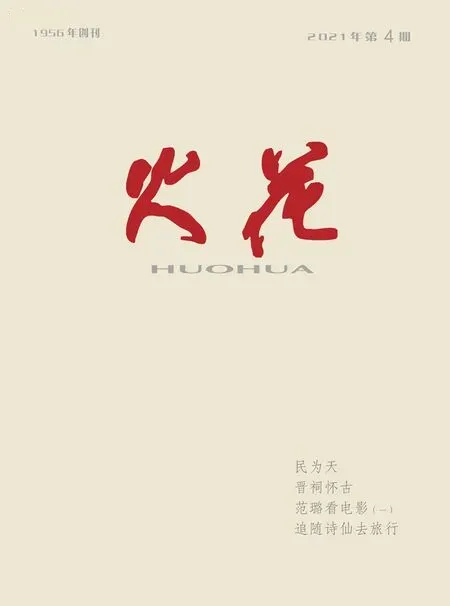五十年代山西作家:在熟悉的土地上耕耘(四)
2021-11-11杨占平
杨占平
李国涛:文笔练达多面手
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山西省作家协会办公和多数作家、编辑居住地。这是一条无出口的巷子,古老而幽静,是太原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之一。这条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平平常常的巷子,却记载着许多历史、文化事件和人物,与山西现当代社会史、文化史紧密联系着。
半个世纪以来,南华门东四条成为山西省文艺工作者的核心聚集地和山西文艺创作的代名词,一大批人从这里起步,走向全国,作家、艺术家数不胜数。这里,产生过无数在广大读者中口口相传的经典作品;这里,更记载着许多山西文艺界的大事件、大活动。在众多名人中,有一位在这里居住了四十多年的编辑家、评论家、小说家、散文家李国涛先生。
出生于1930年的李国涛,是江苏徐州人,1957年8月奉调来山西工作,先做煤炭企业学校教师,1962年进入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当编辑,“文革”后不久调入省作家协会当编辑,1982年至1985年任《山西文学》主编,1988年被选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94年退休。李国涛看似简单的人生历程,却是伴随着中国现当代社会史和文化史上诸多大变革、大事件一路走过来的,他见证了几十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风风雨雨,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曲曲折折的发展过程。
李国涛出生于古都徐州最著名的李家公馆,他曾经说过:“我家前两代都是读书人。那时候他们有闲钱有闲时间又有闲房间,三闲,所以也就买书,买书之外又买字画、碑帖,想当收藏家。在我印象里,好像主要财力都花在砚石上,藏砚。日本人入侵后,我家收藏损失大半。后来人事沧桑,几经变故,到解放后,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一个人的出生不一定决定一生的命运走向,但是,肯定会影响他的文化选择。李国涛后来有过不少从事其它行业的机会,但他坚决选择文化行业,包括做教师,搞研究,当编辑,写文学评论和小说、散文,跟他从小接受的广博厚实的家学是有很大关系的。徐州城里的名门大户,让李国涛终身受用的是那种温良恭俭让、读书为至上、谦逊做真人、保持高尚品格、永远有悲悯情怀的性格。
李国涛的学生时代是在徐州度过的。那是一个新旧体制转换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教育思想转换的时代。传统教育与西方文明教育相互渗透,这对初出茅庐的李国涛来讲,是一个机遇选择。他的态度是既不放弃传统教育的精华,也不排斥西方文明教育的长处,用一个成语“兼容并蓄”来形容那个时候的学生李国涛,是比较贴切的。
从徐州第一中学毕业后的李国涛,没有现在学生毕业可以双向选择职业的自由,那个时候叫做分配工作,根本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组织上让你去哪里工作,你只能服从,不能有任何不满意或不想去的想法。按说,优等生李国涛留在徐州工作是正常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被分配到了山东省泰安的一所煤炭干部学校当教师了。虽然有一百个不情愿,却绝不能表现出来,还得以一种心甘情愿的态度去。
于是,1952年夏天,二十岁出头的李国涛,告别古城徐州,告别李家公馆,只身去了山东省泰安煤炭干部学校任教。在这所职工学校教书、工作对于李国涛来说,特别容易应对。工作之余,他迷上了文学伊甸园,把大量时间都花在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上。读着读着,自然就产生了写作的想法。由于从小读过不少文学方面的著作,逻辑思维清晰,富有理论概括能力,他感觉到自己的写作最适合的是文艺评论。有深厚的功底和充分的准备,1955年,李国涛写出文艺评论稿子《诗爱好者的意见》之后,就投寄到北京最权威的文化类报纸《光明日报》,很快就发表出来了。像李国涛这样不在名牌大学也不在研究机构,只是一家职工干部学校的教师写的稿子能够在《光明日报》这样的全国文化类权威报纸上发表,没有一点真才实学,是绝无可能的。
1957年8月,李国涛被调到山西省西山煤矿学校,继续任教师。他坚持了读书的习惯,写作更是没有放弃。那个时候,山西以赵树理为首,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为骨干的作家群刚刚进入写作黄金时期,优秀作品不断问世。李国涛认真阅读山西作家的作品,选择有艺术特色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发表评论,当时山西省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火花》上,就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评论文章。
“文革”后期,山西省文艺工作室(原山西省文联)成立,同时创办文学杂志《汾水》,这是五十年代《火花》的延续。主政的马烽、西戎等在选调编辑人员时,首先想到五十年代活跃的评论家李国涛。很快,就把他调到编辑部做编辑。这也是李国涛文学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不久,他被任命为编辑部副主任,当时主编是“山药蛋派”骨干作家西戎先生,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是同样从根据地成长起来的评论家郑笃先生。编辑人员都是当时省内有经验的作家和评论家。
进入新时期,文学迎来黄金时代,全国人民都在阅读文学作品,写作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的更是不计其数,不少作者靠一部作品能够改变人生命运。同时,文学刊物大受欢迎,来稿量很多,订阅者也很多,编辑工作非常繁重。但是,李国涛以一种特别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工作,他深知每一位写作者对用心写出的作品都抱有很大期待,自己原来也是作者,明白文学编辑的重要性。因此,他认真读每一篇来稿,认真回复,发现有好稿件会主动联系作者,并推荐给主编。当时的许多山西年轻作家,都对李国涛老师尊重和感谢,因为是他促进了这些年轻作家的成长。
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李国涛的研究与写作也进入辉煌时代,发表了大量文学评论文章与专著,对国内重要作家作品都有涉猎,对山西的老中青作家作品更有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79年11月2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且说“山药蛋”派》一文,引起了全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山西日报》曾开辟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学流派的讨论》专栏,延续了长达近五个月,刊登各类文章四十多篇。讨论主要是围绕以赵树理为旗帜的“山药蛋派”形成、发展过程与艺术风格、特色等问题展开的。此后,“山药蛋派”得到了全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认可,成了文学史上一个有影响的流派。可以说,李国涛为这个流派定了名,定了特色,定了风格,其贡献功不可没。
1982年1月,《汾水》杂志更名为《山西文学》,李国涛被任命为主编。在他担任主编的几年里,扶植年轻作者,培养文学新人,抓重点作家的创作,尤其是在培养山西青年作家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他以编辑部为平台,经常组织中青年作家培训班、笔会、改稿会、采风活动等,对一些重点作家更是全力扶持,帮助他们选择题材,跟踪写作进度,配发评论文章,撰写编稿手记等等,许多后来在山西文坛及至全国文坛影响很大的作家,当年都曾受到李国涛以及《山西文学》编辑部的帮助,应当说,山西文学创作能够“晋军崛起”,李国涛和他领导下的《山西文学》功不可没。
做好《山西文学》编辑工作的同时,李国涛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他一方面结合多年的编稿工作,撰写大量关于山西老作家和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评论文章,像马烽、孙谦、田东照、成一、张石山、李锐、钟道新等人的创作和有影响的作品,他都有中肯、准确的评论;另一方面,他把研究视角放到作品的文体上,写出了一系列有深度、有影响的文章,在国内文坛成为文体研究专家。他结集出版的有:文艺论文集《〈野草〉艺术谈》,收集了关于鲁迅作品等方面的研究文章;《文坛边鼓集》,收集了他关于一些当代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STYLIST——鲁迅研究的新课题》是一部研究专著,STYLIST是英文文体的意思,从文体的角度研究鲁迅,是对鲁迅研究的一种拓展。李国涛的这些评论和研究,都是很有见地很有深度的,不少文章曾经在文学界甚至于整个社会科学界都引起过反响,比如他关于汪曾祺作品文体的研究等,在全国学术界都受到好评。
1989年下半年,李国涛开始以“高岸”的笔名发表小说,几年过来,他写出了十多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两部长篇小说《世界正年轻》《依旧多情》。他虽然过去一直是写评论,但多年当文学杂志主编,并潜心研究小说的文体,所以,写起小说来非常轻松,出手不凡,文笔练达,内涵深刻,让不少多年写小说的作家赞叹不已。他的中短篇小说,多数是以“古城旧事”为主题,表现他的家乡古城徐州的往事。他凭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独到感受,凭着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凭着多年积蓄的艺术素养,写出了古城徐州的文化氛围,写出了旧人旧事的独到风采,把四十年代徐州特有的风情民俗、人情世态渲染得淋漓尽致,构成了一幅浓淡相宜的古城风俗画。
《世界正年轻》以五十年代初期建国不久为大背景,描写了位于东岳泰山脚下的一所学校从筹建、开学到第一学期结束的过程,无非是一些学校如何管理、教师如何教课、学生如何学习等日常琐事,却让读者感到了作品中寓含着的关于历史、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厚重,读出了年轻的世界与沉重的心灵之间的悖论与反差。《依旧多情》则是以独到的艺术表现力直接切入了现实生活,叙述的是一所区级老年大学的办学过程,跟《世界正年轻》的视角差不多,也是写一些琐事,却刻画出了不同人物的复杂心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思考人生的变幻莫测和普通人命运的起伏,具有强烈的现实启迪意义。
写完《依旧多情》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国涛就不再写小说了,转而写起了文化类随笔文章来。他读书很多,但是绝对不乱读,都是读一些文化蕴味浓厚的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古典名篇和外国作家经典著作,不少名家名作中的重要思想,他都能讲述得清清楚楚。他以一种平和、恬淡的心态,把自己的读书感想、生活感受,用充满文化气息的笔触写出来,让读者读得轻松有味,还能学到许多知识。这些文章结集成随笔集《世味如茶》和《目倦集》问世。
概括李国涛先生八十多年的人生与写作经历,虽然没有多少坎坷或者大起大落,却也是走过了两个不同社会体制,体验过大户人家的风范和书香门第的品味,接受过政策对人生道路的强制执行,享受过文学带给他的快乐与烦恼。
董大中:一个人就是个研究所
在山西文学界,董大中的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用著作等身评价也是不为过的。作家成一、李锐、韩石山等人就多次说过:董大中一个人就是个研究所。如此评价,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董大中在赵树理研究、鲁迅研究、高长虹研究、山西作家群研究、董永民间文学研究、孝文化研究、胡适研究等方面,都有建树。
董大中1935年3月出生在万荣县前小准村。祖父和父亲都曾做过教师,在当地农村就是有文化的家庭。因此,他从小接受读书为上的教育理念,特别喜欢读书。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尽管当时是抗日战争年代,他还是进了本村的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按部就班读完小学,顺利地考进县立阎景中学读初中,到二年级时,因为患脑膜炎病,只得退学。没有能系统地读中学、读大学,成为他一生的遗憾。好在那个时候已经解放,医疗条件好转,经过治疗康复后,他应聘到附近一个村办学校当代课教师。
1954年秋天,山西省教育干部训练班(后改名山西省教育学院)面向全省考试招生,董大中抓住机遇,参加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成为该校中文科学员。从此,他离开了万荣县老家,进入省城太原。近二十年的老家生活、求学及教书经历,让董大中深深地浸透到了河东文化氛围中,他后来能够坚持不懈地从事各项研究工作,应当说与从小接受的河东文化有很大关系。
在山西省教育学院学习一年后毕业,由于成绩突出,分配时没有让董大中再回原籍,而是留在太原市教师进修学校(现太原市教育学院)任教。虽然是到了省城做教师,但他功底扎实、态度认真,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在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之余,董大中迷上了文学阅读,尤其喜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大家和赵树理、马烽等山西作家,是他重点关注的,这也为他后来从事这方面研究开始打基础。
1956年,是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全国有许多纪念活动,董大中借这个机遇,开始收集有关鲁迅的资料,并把鲁迅作为研究方向,陆续写出一些文章。不久,他又尝试文学创作,先从写诗歌入手,并有一些诗作见诸于报刊。两年后又涉足文艺评论和杂文写作。
从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结束的二十多年,董大中都在太原市教育系统教书、任职,当然,也得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比如下乡搞“四清”等。最让他难忘的,是曾经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一年,让他亲身感受到了全国最高学府的氛围,接触到许多文化名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没读过大学的遗憾。
虽然这段时期政治大背景变化多端,运动一个接一个,但是,董大中并没有放弃读书和写作,并且撰写文艺评论文章,省城不少报刊上经常刊登他的作品。这样,就引起了省文联和作协的老作家马烽、西戎及其他领导的注意,1979年初,把他调进文学刊物《汾水》编辑部,做评论编辑,正式踏入了文学界。
应当说,这次调动对于董大中来说,既是工作环境的变化,更是从事专门研究的开始。他有多年读书写作经历,尤其是有文艺评论功底,加上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环境,很快就适应了编辑工作要求,对于加强《汾水》杂志的评论分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汾水》改名为《山西文学》,董大中被任命为评论组组长,一年后升任副主编。
进入文学界做编辑以后,董大中的研究也进入新阶段。他结合工作和自己的兴趣,首先是把山西作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研究赵树理及其“山药蛋派”。他对所选择的研究课题非常专注,采取比较传统但也很收效的方法,就是从搜集资料入手,能找到第一手资料的,决不转用别人的。在赵树理研究方面,他沿着赵树理人生与工作及写作的道路,一点一滴找原始材料,跑遍了全国所有可能存有赵树理材料的图书馆、资料室、档案室,经常是带几个面包一壶水,在图书馆一坐一整天,为每个发现而高兴。同时,他也特别注意走访当事人,找到很多跟赵树理相交相处的同事、朋友,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
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董大中勤奋写作,成果频频问世,仅在赵树理研究方面就有著作《赵树理年谱》《赵树理评传》《赵树理论考》《你不知道的赵树理》等;主编有《赵树理全集》(五卷本)和《赵树理研究文集》(三卷本)。可以说,在赵树理研究方面,董大中是国内成果最大最权威的专家;而且,以他为中心,集结了一大批国内外赵树理研究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山西一批青年作家生活积累丰厚,知识准备充分,创作成就突出,在全国文坛闯出一片天地,被称为“晋军崛起”。但是,山西的文艺评论却不能跟创作同步发展,比较滞后。这个问题成为制约山西文学发展的瓶颈之一,也引起省里宣传文艺部门领导的重视,顺应广大作家和评论家的呼声,决定由省作家协会主办一份文艺评论杂志。
省作协党组研究,决定由董大中做主编、蔡润田为副主编,具体创办。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并征求意见后,把刊物定名为《批评家》,得到领导的认可,得到广大作家评论家的赞同。他们从最基础工作做起,找办公室,落实经费,跑印刷厂,选调编辑,外出约稿,于1985年4月,出版了《批评家》创刊号,成为山西文学史上第一份专门的评论杂志,对于推动山西文学创作发展,培养青年评论人才起到了特殊作用,在全国文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做好《批评家》编辑工作的同时,董大中还写了许多关于山西作家作品评论和影视随笔文章,结集为《瓜豆集》和《敲门集》出版;协助北京大学编辑出版了《王瑶文集》,主编了《我的第一篇小说》《抗战文学论文集》《山西文学十五年》等等学术书籍。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他在研究现代文学史时,发现山西籍作家高长虹和“狂飙社”一直被人误解,总是当作鲁迅的对立面出现。他查阅大量资料后,认为要给予高长虹正确的评价,改变过去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偏向。于是,他联系上高长虹原籍盂县有关部门,获得支持后,多方搜集并整理相关材料,主持编辑出版了三卷本的《高长虹文集》、两卷本的《高沐鸿诗文集》,指导编辑出版了两卷本的《高歌作品集》和《高长虹研究文选》;尤其是自己撰写了《孤云野鹤之恋》《鲁迅与高长虹》《高鲁冲突》等专著。他的这些成绩,重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高长虹及其“狂飙社”,具有文学史的重大意义。
1989年底,《批评家》杂志因省里结构性调整,奉命停刊。一份有过很大影响、培养出许多中青年评论家的杂志,留下诸多遗憾、留下诸多话题,结束了使命,也结束了董大中的主编生涯,他转到省作协所属山西文学院,做起了专业作家。这个转变,对于董大中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有了全部时间做研究工作和学术写作。
从九十年代起,董大中把研究方向首先转到大文化上,写出《如何看待“五四”的反传统》等有独到之处的文章。之后,又研究台湾文化名人李敖,先写《李敖评传》,又写《台湾狂人李敖》,出版后,成为大陆研究李敖的重要成果。前几年,为了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董大中又研究考证民间文学董永传说,出版了专著《董永新论》,被国家文化部列入全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此外,他还有大量青年作家作品评论、文艺理论论文、散文、随笔等,散见于全国众多报刊上。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等外国报刊,也曾出版或发表过他的诸多研究著作和文章。2007年,台湾一位学者将他的近五十万字的《鲁迅1925年日记笺释》列入“大陆学者丛书”出版。总起来统计,董大中新时期以来撰写学术性文章和专著在六百万字以上。
概括和总结董大中多年的研究与写作,可以说,他对自己所选择的每一项课题,总是非常投入、非常执着,他认准的事一定要做到。比如《赵树理全集》《高长虹文集》《王瑶文集》这几套很有价值的书籍的编辑出版,他付出了极大精力,是许多研究者难以做到的;他的辛苦、他的韧劲、他实实在在干事业的精神,总会感动人们,使得不少普通人认为难办的事,他能够成功。
具体到每一项课题的研究,他从来都是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特别注意资料的搜集、整理、归类、分析,一定要查阅所有能够查阅到的相关的资料,省内外有关的图书馆、资料室、档案馆,他不知跑了多少次;他在这方面非常舍得投入经费,每一项课题,都要购买大量书籍。用他老伴儿的话说,这么多年他挣的稿费,还不够买书用。多年来,他养成一个习惯,只要在太原,每到周六和周日,肯定会去南宫旧书报刊市场,在那里能够有许多惊喜发现,淘到许多有助于研究和写作的宝贵资料。
一个人等于一个研究所,董大中做到了,在山西文学界他是独特的,在全国文学界像他这样的评论家也不多。无疑,他是值得尊敬的,也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