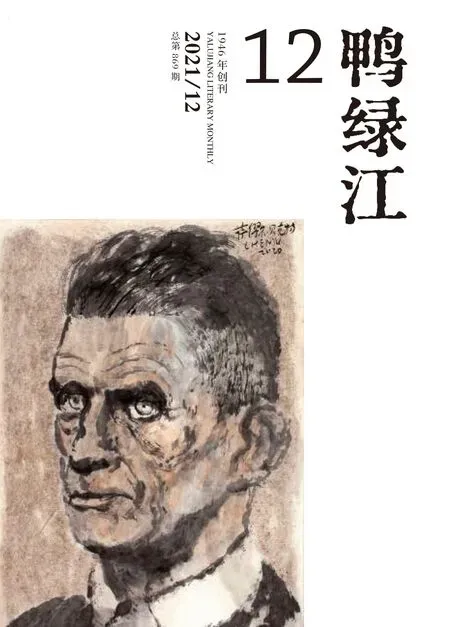人生一半诗一半
——纪念苗强
2021-11-11刘恩波
刘恩波
布罗茨基说到写诗的目的,认为“是为了在大地上留下痕迹”。
苗强留下了一本书——《沉重的睡眠》。若严格地说,是半本。该书是跟漫画家韦尔乔合作完成的。苗强出诗,韦尔乔出漫画。
高岩写的序《两个人,一本书》介绍了他们之间合作的因由,说他们“有着如此相像的精神气质,同样高度的文化修养,同样精绝的表达方式,同样的卡夫卡式的忧郁低回的调子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热烈和阴暗,具象中强烈的抽象感,敏锐的感性背后不可忽略的哲理意味……”
从1964年来到尘世破浪启程,到2004年落下航行的帆,苗强的人生之船过于短暂,不到四十年。但其诗的容量、重量以及强大的气场和冲击力显然成了他短暂生涯的标志性构造,所以我才说苗强是“人生一半诗一半”。
苗强死于脑出血复发,在此之前,他主要完成了两件事,一件是写成一百零二首十四行诗,最后结集为《沉重的睡眠》;另一件是写作长篇小说《朱某本纪》(据说在快要完成的时候,他的生命戛然而止)。后来,这部作品未见任何出版消息,犹如石沉大海。
可以说,苗强此生的光荣,若按照世俗礼仪和文学规格评价,就定格在艾青诗歌奖上。2004年7月中旬,首届艾青诗歌奖评选结果揭晓,在六部获奖作品中,苗强的《沉重的睡眠》以最高票数位列榜首。
颁奖词本身就像深沉、典雅、激荡、飘逸的诗——“苗强诗集《沉重的睡眠》是生命的奇迹,也是诗的奇迹,他在瘫痪和严重失语、失忆后,用诗的语言呼唤感觉,呼唤生命的灵性,以神启般的智慧与世界对话。语言的神骏从时间深处奔驰而来,与他的生命相遇,从而生动地证明语言是感觉方式而不是逻辑方式,是生命美丽的自我发生。他的语言纯净而安恬、质朴而自然。这位富有才华的诗人和青年美学家,以不满四十岁的英年溘然长逝,给中国诗坛留下一部感人肺腑的生命绝唱。”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的终结处有这样发自内心的感喟:“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每每念及此语,不由得悲从中来,苗强的命运和他的诗意王国,以及他的匆促、凄凉而辉煌的人生变奏,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苍天可问,大地永无回声,岁月和记忆甚至湮没了有关苗强的一切。
他留下痕迹了吗?现在的诗坛似乎将他彻底遗忘了。
我想说,诗就是命,命亦是诗。诗理就是命理。好诗未必有好的运气。
命理是按照生辰八字来推导的吗?诗理是按照诗坛的风水排场、地位官爵来排定的吗?苗强在地下无语。我也无语,但我偏偏不甘心,遂渴望以自己微不足道的点滴文字来祭奠一下这位了不起的诗人。在他的诗中,那地火,那甘霖,那眼泪,那浓稠的血,那静夜,那独语,那默默花朵绽放的香气,漫过了流年的栅栏和挤满厚厚灰尘的历史的门窗。
我读着一百零二首诗,带着固有的虔诚、孤寂的痛楚,还有哀歌大地的悲摧之心。
苗强仿佛活了,在我面前叹一口气。他说:“写《朱某本纪》写到最后,就像烈火烹油,来不及收束了,人就掉在死亡的拥抱里。”我说:“兄弟,你早就写完了你的一生,那就是在创作十四行诗的日日夜夜的脉搏跳动中,你的魂灵附着在文字上,变成了生命的响动。嘀嗒,嘀嗒,你的内脏快要成为记录时间消失的钟表的指针和发条了。”
当然,我见过苗强,不多的两三回吧。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住宅小区里,我敲着他的屋门,他出来了,身体明显不便,有一只手很违拗地不听使唤了。但他就用好使的另一只手,为我端茶倒水,我赶紧阻拦,可是他很坚定地做下去。那一次,我们没有谈诗。地球在动,我们会说“地球在动吗?”我们甚至也没来得及谈足球、谈健康、谈生机勃勃的生活和事业、谈童年往事……是的,我们都不善言谈,沉默如一张网,罩住了两具似乎关闭了心灵闸门的年轻的躯体。诗意的沉默就像是购销记忆的呆账。
很对不起老兄啊,现在你的书放在我手里,书脊都有点开裂,还好没有掉页。纸张发黄了,年轮和时光的折痕还在。2002年9月23日,果然是秋天,我是在秋天去看你的。你家窗外的天很蓝,那会儿没有雾霾。有鸽子吗?有爬山虎吗?有蛐蛐叫吗?我不记得了。《沉重的睡眠》,我接到渗透着你手掌温度的书,不自觉地在心里许下祝福,既然死神这次放过了你,那么生活会赐给你新生的希望和更优厚的报偿。
这心愿我把它记录在写给《当代作家评论》的“印象点击”的文字里。在那里,我将你的诗视为里尔克和特拉克尔精魂的再生!你的十四行诗,是汉语诗歌的祭礼,是生命心血的特别馈赠,是真正的诗歌,是美妙的眼睛、呼吸和心跳的奇异组合。我晓得那是上苍的造化和恩赐,因为你为诗歌付出了大半个生命。诗歌是你命运的另一种名称和承命啊!
我在2020年暑气正浓的时节重温《沉重的睡眠》,又一次走进了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天地。必须告诉你,你的伙伴韦尔乔也走了十多年了,你们在那个世界会遇到吧。而我此刻坐在电风扇带来的凉风里,阅读的目光轻轻落到你们的文字和线条中。那是两个年轻的生命会聚在一起的灵性世界。你是不到四十岁走的,尔乔是四十三岁走的,死神跟你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记得在尔乔他身后出版的书里,曾经留下了他生前对于主的虔诚祷告:“主啊,请让我慢点走啊!”
尔乔是个医生,他在处方单和病历本上画过画,就像王小波在五线谱上给李银河写信,那叫深情和有趣,那叫顽皮和快活。据说他爱在画面上涂抹一些拉丁文,以至于有些读者误以为他是个老外。
管他呢,反正你们都谙熟,都青睐中外经典里那些时隐时现的神采和意象、趣味和形貌。尔乔的插图往往像梦游似的,骚动着潜意识里的泥浆和暗潮,就像你的诗歌,往往呈现出更多的属于内心角落的话语流动。
此前,我有段时间在看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在那书里发现这样动人的话:“艺术是个人的行为,是孤寂的个人将孤独与希望融为一体后诞生的孩子。”如此说来,即便你和尔乔的合作,也注定是两个人各自献祭出自己的心意和灵感,然后汇聚熔铸为精神共同体的生命祭坛。“两个人的孤独只是孤独的一半”,这句来自欧阳江河诗里的警语恰恰点醒了人生和艺术交流的内在实质。
隔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再度欣赏两个人如合金一样熔炼出来的书,既像一次发自内心的还愿,也如重新出发到他们远行的起点。有些地方原来忽略了,此番会补上一点蓦然回首中的惊奇和悟性。比如封二和封三的图片,从前没怎么在意,如今越看越觉得那就像是预示两个人终极命运的某种标示。
封二的前景是一个躺着的人,摊开两手,伸开腿脚,看上去就是病了或者处于沉睡中。后景画着许多人的腿部,是来探视,来挽留,还是来告别?封三更抽象,一只手从水面升上去,另一手从空中伸下来,两只手没有交集,但感觉是要拉住对方。两个画面如果对照两位当事人的生前身后,我们会在传递出来的意味里觉察出命运的一丝莫测和诡谲。
现在两位安详地长眠于他们的作品里,比以往更加安详。
毋庸置疑,他们的作品已经超越了时间的障壁,大概也会通往岁月的深处吧。尤其是苗强的诗,属于另类,与同时代大多数诗人处于不同的精神轨道。当然这首先跟他本人的身世命运相关,跟他的疾病相关。
有人说,苗强是个奇迹。但凡了解一些他生命中最大挫折的人,都会为之唏嘘。
收信人的矛盾复杂心理是写信人写信时所适应的某种情境语境。此种情形下,主体之间通过文本有效地契合起来了。
1999年3月31日,35岁的他突发脑出血,出血量达80毫升。开颅手术挽救了他的生命,但手术后的他既不会说话,也不会写字,连记忆也丧失了。医生对他最乐观的诊断是:恢复两三年以后,病人可能会借助手势表达一些简单的意思。谁都没有想到,他在得病一年零八个月之后,却开始了诗歌写作(见高岩《两个人,一本书》)。
里尔克说过一句关于宿命的话:“一切都是时至才能产生。”人们等来了生,等来了挫折和逆境,等来了希望和工作,等来了爱情和亲人,然后也等来了死。苗强等来了脑出血,性命攸关,好在命运之神给了他第二次生。他用自己的102首十四行诗,等来了文学精灵的光临。
十八年前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在自家不远处的小园林里捧着《沉重的睡眠》,那会儿苗强还活着。我一下子感受到了来自精神深渊里的光亮。小园林生长着各式各样的树,有松、柏、丁香、榆、槭、枫……大地的土托举着这些年轮不一的树向着阳光生长。苗强的每一首诗在我眼里也如同不同品类的树木,绽放着各自迥异的芬芳,但它们的材质、断面、根茎依旧是“诗歌”这棵粗壮的老树赐予的成长序列。
2000年11月25日,康复期的苗强写出自己第一首十四行诗。在诗里,他自然而又亲切地称呼自己为“邮差”,是一个“患有怀乡病的人”。
那是个雪天,“天气异常阴暗/没有风/没有人在外面走动/仿佛这个世界/一开始就下着雪/地老天荒/没完没了。”这时,诗人虚构了一个急匆匆上路的邮差的形象,他让这个人去远方告诉另一个人这里下雪的消息,而那个人患有怀乡病。他是许久以前出走的吗?无论怎样,诗人说只要他得知下雪的消息,就会风尘仆仆地往家乡赶。“他的眼睛和我躲在窗后的眼睛一样迷茫”。诗的结尾点出邮差和还乡者都是同一个“我”。换言之,苗强在诗的洗礼中,发现自己原来既是送信人,又是接信者。
也许现实中我们分身乏术,但在诗歌的想象里,一个人的使命感和归属感终于合二为一了,想来那一刻的苗强是幸福的。他当然不会像海子那样大声喊出“幸福说/瞧这个诗人/他比我本人还要幸福!”苗强是不喧嚷的,他在僻静中品味着诗歌的天籁之音,甚至略带羞怯和腼腆。他的深情是内敛的,无须声张。
海子的喊是本真的歌唱,苗强的倾吐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生命灵魂的呢喃。
从第一首诗开始,他精神漫游的特质就已开始呈现。苗强的作品始终没有放射出逼人的、令人感到窒息的灼热的高光,他的出场在诗里如同一个悖论,是在场的不在场,或者说是不在场的在场。这是局外人的冷静打量和审视,有着使者置身于现场的大模大样的庄重感甚或拘束感。比较起来,海子倒像是司仪,可以随意任性地操控诗世界里的任何分子,苗强则是带来消息的人,只是把自己的口信送到精神的一方领地,就算完成了使命而自觉心满意足。换言之,苗强写诗如同写信,他给自己写,给天地写,给世间万物写,给人生写。我在他的诗中,听到了精神的天籁,性灵的低语,还有关乎存在之谜的娓娓弹奏。
这是十四行诗的第九首,最初一读,如遇雷电。“一口棺材收敛着我的语言”,这一句有着残酷的美妙感,是思维的风暴。诗人跟词语的幽灵见了面,而且相谈甚欢。
整首诗是一个人经历巨大生命考验和灵魂撕开一道口子之后的“洞见了某个东西”(海德格尔语)。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上路去体验”才能学会认知和思考,这是真正的诗人该做的事。苗强得了重病,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样的经验是极限经验。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绞刑架上被释放下来的一瞬间,就像史铁生瘫痪然后又得了尿毒症,需要不间断地透析,生命遇到了极刑般的折磨与毁损,这时候人对语言、对文学势必面临脱胎换骨般的吁请、祷告和诉求。
苗强是在无路可走的地方找到了路,是在绝境中掘进。
从前他写过《卡夫卡的疾病》,其中引用了罗兰·巴特的话:“不管怎样,写作就是播下病菌。而人们可以认为这是撒下种子,从而进入种子的普遍循环之中。”苗强的这篇随笔发表于《艺术广角》1998年第4期,那时他尚未得病,却以惊人的发现找到了卡夫卡的心理病症的出发点和去向。他说:“‘病人’卡夫卡用他的‘疾病’营建起的纪念碑,是20世纪最为显眼的文学建筑;我们逗留于它的阴影里,而这浓重的影子仍在向不可知的未来蔓延,似乎一个时代的终结,全看它在哪里结束……”
疾病的隐喻,大概是文学精神必要的组成部分。如同苏珊·桑塔格指出的,“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更是一种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的公民身份,其中一个属于健康王国,另一个属于疾病王国。”卡夫卡作品中的疾病、饥饿、变形和被惩罚,曾是一些人思维脚步驻足打磨的敏感地带,有人甚至认为卡夫卡是遭受了肺结核的折磨才最终形成了天才的敏感,拥有了迥异于常人的发现。
同理可证,苗强突发的疾病,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因祸得福。如果他不得病,肯定没有《沉重的睡眠》的横空出世。当然,另一方面,如果苗强没有对中外经典遗产进行创造性继承、淬炼和研读,即使他得了病,也绝对不会写出这些惊人的十四行诗。
让一个人的肉体成为语言的殉葬品。苗强的诗句后来竟然一语成谶,他死在了他的诗中,他的诗升华了他的死。然而,那个秋天我在小园林里徘徊散步,绝对想不到后来发生的一切。我只是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位新朋友的作品,并禁不住连连叹气:这不就是我想找的诗吗?
我可以说,那些文学的经典铸造了他诗歌风格的骨骼,而他濒临死亡的生命考验与磨砺造就了他精神气象中的血脉、魂魄和肝胆。
《沉重的睡眠》某种程度上也是诗人与自己的文学恩主或者艺术施洗者的深层次的对话。比如他在第四首中,提到了凡·高:“像凡·高燃烧着的丝柏一样/我不幸地被命运选中/雷电把我劈开/把我烧焦/天空中/群星疯狂地涌现/迷失于既定的路途/人们点亮灯盏/却照亮/不会说话的病人平静的灵魂……”那个凡·高,曾经依托向日葵,依托星、月、夜,当然还有丝柏、鸢尾花、麦穗、土地……一同塑造了他的绘画王国。在这诗中,苗强也罕见地燃烧着属于自己的热情能量。他说接受自己的命运,“像接受一个稀有的纪念品”。这诗充满不可遏制的疼痛感和悲怆感,以及罕见的希望。在结尾处,诗人欣慰地将自己想象成一棵高大的云杉,“孤独地生长在人迹罕至之处”。
苗强长得很魁梧,从外形上看,用高大的云杉自拟并不走样。关键是他扎根在孤寂险恶环境里的不屈不挠的意志,让我们看到了更超拔的激情。
直面过生死交界的状态,比一味幻想到底是有骨子里的差别。在第七首十四行诗中,苗强写道:“我死过/这是我唯一可以自夸的”。当然,他庆幸自己没有就此死去,“在没有通晓人生之前,死亡又有什么意义”。他羡慕那些成熟的果实,“心满意足地从树上坠落”,哪怕闷闷地发出不大的声响。可那毕竟属于踏入自然流程的因果序列,没有强加,也没有意外。活着,通晓人生,在苗强眼里,那意味着“具有无限可能”。“比如/我的呼吸有一种隐约的春天气息/来自心房的潮汐使大地冰雪消融”。正是在这种从幻灭和绝境里猛然挣脱出来的惊喜感和苏生意识,让诗人一下子切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无限感怀之中。全诗的尾声写得漂亮极了,“尘世微微闪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阴暗的绞刑架走出/目露晦涩的光芒”。是啊,来自上面的一道特赦令,解脱了这位大师的命运重负和死亡恐怖。而苗强明明知道人生的希望有可能是游移的、荒诞的,但是此刻暂且不管,面对绝望和险境,诗歌的“出场”,使一个写作者在通往语言之路的苦苦跋涉里得以遇见真神!
无论十八年前的阅读还是现在的重温,面对《沉重的睡眠》,就好比在无边的沙漠或者旷野里采到了金矿,这种感觉一直未变。我觉得,那些诗是诗人缺氧后的深呼吸,是用全部身心去透气换气,是走过悬崖峭壁后的重新站定,是从深渊中捞取一颗生命和记忆的珍珠之余飒然的心魂觉醒。
苗强的艺术风格通常是平稳中见机智,深沉中露才思,婉转里显深情。与其说他是特拉克尔式的梦幻般的写作者,不如说他更像里尔克,在思辨、内省、历练和打磨中不断汲取开掘着诗意的生命源泉。
他善于在现实存在的深处找到个性的发光体,进而变成文字的彩练和精神的微雕。他的措辞不论宏大深远还是俏皮优雅,不论凝重庄严还是活泼激荡,看起来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纾解性灵。“书籍是我幸福的刑具/我不停地锻炼/以期能得到减刑”(十四行诗第十二首),“我的家/就像一个钟表匠的家/到处陈列着残酷流逝的时间”(第十三首),“如果有一座雪山/我在其中行走/像一条虫子在爬行/身穿绛红袍子的虫子/我是个痛苦的喇嘛”(第八十八首),“我僵死的右手的骨骼/僵死的神经末梢/如同一条干枯的鱼/搁浅于稿纸铺成的河道”(第六十首)……不同篇章里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属性、外观和内涵,实质可能大相径庭,不过最后归结到一起,却都在入骨传神地拓印、刻写、勾勒、见证着诗人立体人生的某些断面、侧面或者背面,从而让我们捕捉到属于这个人的质感、温度、灵性还有气息的一部分。
好的阅读,应该说是将寂寞还给寂寞,是将诗意还给诗意。或则,“把你的寂寞扩展到广远的地方”。当年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里闪耀过这样的火苗一般的忠告。苗强的诗,注定也是将他的寂寞扩展到广远。
十八年前,在那个清凉的小园林里,当我像寻觅着树叶上的露滴一样一行行地搜读着苗强韧劲十足的诗篇,忽然觉得残缺的生命才有可能意外地圆满,压抑的灵魂才会激发属于生命深处的、真心真意的歌唱。
不久之后,我又去看苗强,把上次从他那里借阅的卡瓦菲斯的诗集归还给他。那时节,我的眼里一片白。下雪了,沈阳的雪应对着节令从不拖延。
苗强照例又端来一杯水,他年轻的面孔一片潮红。是出去踏雪的缘故,还是由于纵情的阅读?记得他曾说过,读好的诗,是会让人掉泪的。但是读卡瓦菲斯,我只是愉悦,并不激动。大师又怎么样呢?没有激动就是没有激动。
苗强听了我的告白,笑了,很温暖。我们在一起依旧没有谈诗,仿佛我们两个人的对面就坐着一位诗神,我们不必说话,只要洗耳恭听。岁月浸润着从前点点滴滴的回忆,此刻想来像是幻觉,也像是错觉。
还是读苗强的诗吧,那些最好的部分,如同目睹了神迹。
她看见一条龙从天上落进村子里/她往那个金光闪耀的方向跑去/那条龙/大概受了伤/吃力地向井边爬去/她站住了/看见受伤的龙在井里喝水/这时有个挑水的男人正向井边走去/她吃了一惊/那条龙气喘吁吁地盘绕在井边/可男人什么也看不见/用辘轳在井里汲水/但是井里已经没有水/男人摇着头回去了/于是就有许多人三三两两来到井边/大家议论纷纷/只有她才知道真正的原因/但她为什么悲伤呢/由于全村人都来过井边/由于他们看不见龙/而龙又奄奄一息/所以他们在龙身上践踏/弄得金色的鳞片到处都是/她无声地哭了。
这是第三十四首,说心里话,直到今天,我也未必彻底搞明白苗强想表达啥。是一种隐喻,一个寓言,一个传说,一场梦境,还是一个迷醉了自己也迷惑了旁人的童话?
要想彻底弄懂其中的意味和蕴藏,即使经过了十八年的沉淀、积蓄和等待,依旧是一道难关。这令我想到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那个经典的开头所预示的——他说乞力马扎罗是一座常年积雪的高山,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在被称为“上帝的庙殿”的西高峰,有一具已经风干的、冻僵的豹子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小说引出故事的口吻,确实有违海明威通常的惯性思路,却带来了新的可能和创意。同样,苗强的一百零二首十四行诗中,这么写的也很少,注定是另类的创作。
后来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就是“幻象”啊,是叶芝用一整本书揭示的人类宗教和艺术的整体起源所在。当然,叶芝的《幻象》实在太深奥了,里面有一些星相学、象征主义玄学的成分,不是圈里人几乎无法接通其信息定位。但是,叶芝笔下呈现言说的诗意、梦境、幽灵、魔幻世界等等,如果用艺术的眼光看,其实就是在表明:人在某个时刻会得到一种特殊的暗示和启示,进入心灵的幻象的感应时空,于是超验之感官表象出现了。
苗强写的那条龙就是幻觉、幻象,是某种精神世界的象征,那个村子的人与这条龙构成了错位而又对位的关系。包括那个汲水的男人,他们看不见气喘吁吁直至奄奄一息的龙,他们需要水,但是井里的水由于龙在井边盘绕而干涸了。龙遇水则生,在民俗系统里,龙和水相伴相生。诗意的龙当然表达了更多的意蕴,妙在诗人没有说透,而隐藏的部分形成了更强烈的气场。那个假托的叙述者“她”,像个先知,又像经历者,抑或见证人。人们在盲目中所做的事给龙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弄得金色的鳞片到处都是”。可问题是,这些人是在无知中犯错至犯下罪过的。诗写到此处就超出了故事表层,进入到思辨的深层,它多少有点像卡夫卡笔下的寓言。卡夫卡写了许多小故事,每一段都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同样,苗强的这首诗也太值得我们费心琢磨了。寓言式的存在,从起点到落点,几乎是人类命运的抛物线。它的超验性和探索性,打破通常思维逻辑陷阱的追求以及梦境般的叹息,都将诗的叙述带到通灵的地带和边际。
好的诗,都是神迹,可遇不可求。海子诗里就有许多神迹,比苗强要多,几乎是脱口而出,破空而来。但苗强的根在大地上,他的浪游和梦游,是一个异乡人的流浪,向往着精神的故乡。他老实的诗多于不老实的诗。他骨子里像个哲人,不过是借用了诗的外壳,像鸟借用了谷粒和稻穗生长出自己展翅翱翔的羽翼一样,游历到天空深处。
第六十一首诗,写了一个人总是夜里磨刀的事,古怪、压抑、有意思。那也是苗强想象力的浪游和翱翔,是出奔和越轨的寻找。
如果一个人总是夜里磨刀/既不是为了/削平果/也不是为了杀人越货/那么他为什么这么锲而不舍地磨这把刀呢/而且他磨刀霍霍/如果我们睡不着/会眺望他家的窗口/他点灯熬油/把他的身影镶嵌在窗口上/直到天亮/才随着夜色一起消失/如果我们不能忍受失眠的痛苦/还有其他的办法/我们邀请窃贼高手/这样他的刀很快到了/我们手里/但是夜里的磨刀声依旧/第二把刀和第三把刀相继偷来/据说/他家没有别的刀了/但是磨刀声依旧/也许真如传言所说/他有一把看不见的刀/不难想象/那该是一把多么锋利的刀。
初读该诗,碰巧是在秋夜里。窗外是唧唧虫鸣,夜雨淅沥,隐约听到隔壁上楼的脚步声,心里悬着一块石头。感觉像是武侠小说的镜头和场景,琢磨起来又不是。像是诡辩游戏,却又分明触摸到那磨刀人的一点心思。总之,苗强的叙述,让夜都亮丽了起来,再也睡不着觉。磨刀霍霍,那鬼神相接的地带,时空不隔,人心不隔。
现代诗越发展,越是高招迭现。
苗强的叙述无疑是高手出招,时隔多年,这样的叙述也依旧如空谷足音。他的细节化处理、虚张声势的手段以及思辨的戏剧性点染,一浪接着一浪,让我们惊心动魄,回味无尽。
“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寻找什么”,海明威的疑问,是文学史上辗转不眠的脚步,回响着探秘者的足音。我伫立在苗强诗中“金色的鳞片到处都是”的那条龙的离奇命运前,伫立在磨刀人原来在磨着一把谁都看不见的刀的诡异存在前,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想问一下,在现代诗人中,又有几人能为我们提供包含如此宽旷的人生、人性的秘密和迷局的作品?
苗强曾经自比为一只蛾蛹,“隐身于黑暗的茧中”。他向往光明,但过度的光明又让他不适应。他写诗,如同一个异乡人归乡,但是脚下的路由于陌生和无助而变得模糊茫然。苗强在寻路,又在迷路,因迷路而失踪。有时候,我们几乎找不到他诗歌的出口。来路依稀可辨,去向杳无踪迹。也许,劫后余生的他更愿意相信今生现实的可珍重、可信赖、可依托。他写过这样的句子:“一切属于光明的东西都完好无损/一切属于向上的东西都欣欣向荣。”(第九十二首)然而,转过命运的拐角,他又无法不逼视“在季节的苦闷期里/痛苦是一种治愈的力量”。“秋风起自何处/吹过疾病的家乡/吹过我/吹过我的铁锹和美酒”,他的《沉重的睡眠》第一百零二首的结尾处如此写道。这既不卑微,也不高昂,既有沉痛的警语,更不乏生命庄严的法相。
经历了开颅手术、失语、失忆,在后来恢复期,他像个小学生一样重新提笔写字,每天读一段《格林童话》和《伊索寓言》。他说起话来很慢很慢,娓娓道来,这是我在现场见证的。如今想来,那就是他写《沉重的睡眠》的节奏,不疾不徐,抑扬顿挫,声声悦耳,字字动心。他飞升了,在汉语无比美妙的组合重构中,他寻找着诗的光亮和梦的远方。
有一年,在某个时节的某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是位女士,她想从我这里借阅苗强的《沉重的睡眠》看看,说市面上买不到了。她的来信口吻很诚挚恳切,让我不能不借给她。那会儿,苗强已经辞别这个世界多年了。我略带疑虑地把书按照地址给她邮过去,我也生怕这本书从此失踪,就像苗强的失踪一样。
我想起他在诗里描绘过一只小松鼠,在校园里,机警地跑过横道,然后钻进草丛里不见了。《沉重的睡眠》大概是我能够见到那只并不存在的小松鼠的唯一方式。我深信,在我阅读的目光深处,在记忆的某个区间,苗强的微笑、呼吸和眼神还会跟我一起翻阅远去的时光和命运。
许多天之后,我终于收到了那本《沉重的睡眠》,还有一封致谢信。
如此说来,这书等于是一架桥。是心灵的秘密通道和沟通信使的驿站。
“作为一个活人/我此时此刻并不存在/我和小松鼠的命运一样/都属于某个超现实主义诗人的某本诗集里。”是的,苗强的生死已经不重要了,他带着他的诗,走向了远方,走向了永远,走向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