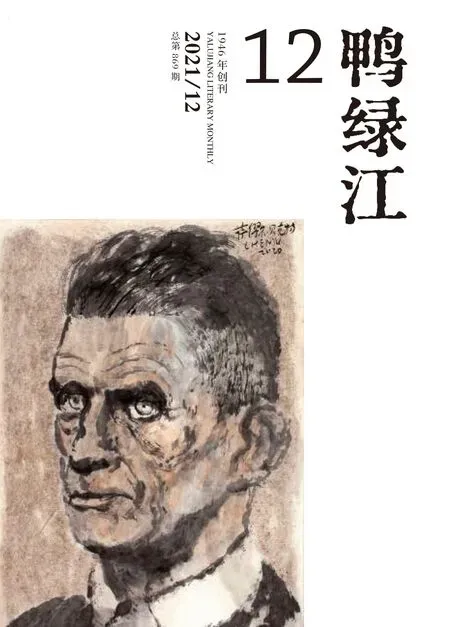荒诞意识与社会风情画的糅合(评论)
——由冯骥才《哈哈镜》想到的
2021-11-11卢桢
卢 桢
提到新时期以来的天津小说,聚焦点大都会集中在冯骥才与蒋子龙身上,一位书写市井小人物传奇,一位谱写工业改革者赞歌,他们共同支撑起新时期的天津文学,并各有侧重地被列入20世纪80年代小说的文学史谱系之中。翻览今天的诸多文学史教材,蒋子龙往往被视为“改革文学”的领军人物,文学史形象较为稳定。相较而言,冯骥才的形象则要丰富得多——由“伤痕”到“反思”的见证人和书写者、寻根文化的自觉探索者、现代小说技法的追溯者、市井文学的初探者,再到文化散文的先行者、民俗传统的守护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断在“激进”与“保守”、“精英”和“民间”之间穿梭,彰显出作家气质中丰富的个性元素,以及不断求变逐新的创作理念。不过,在纷繁热闹的标签背后,文学史实则缺乏对冯骥才创作的总体式评价,其作品中那些稳定的、核心的特质究竟为何?在“俗世传奇”或“津味小说”之外,作家是否还有继续被诠释的空间?或许,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作家创作的原点,从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短篇创作谈起,开启对其文本的再解读。
“文革”结束后,冯骥才写下一系列反思性色彩浓郁的作品,以此跻身文坛。新时期之初,他的写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以城市人的生活百态作为题材,强调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干预,并自觉地将叙述意识和文化意识、社会责任感熔铸一身,由此形成了两种驾轻就熟的写法,如作家所言,正是其初期创作的“两条路子” :一条是从《雕花烟斗》到《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今天接着昨天》《雪夜来客》等等,凭借作家的气质、个性、艺术感觉及审美观念追求人生况味和艺术境界的小说;另一条是从《铺花的歧路》《雾中人》到《走进暴风雨》等等,受直接来自生活的激情所鼓动,被作家言及的“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感驱使”而完成的小说。在这两个向度之外,如何理解我们的民族史和文化史,成为作家创作的又一驱动力。随着中篇小说《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短篇小说《市井人物》等作品问世,冯骥才逐渐摸索出一条地域文化的书写之路。评论界往往对这类作品投入广泛的关注,而对其自谓的“两条路子”上的其他作品普遍缺乏再解读的意识。实际上,冯骥才早期作品中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融含的文化信息非常丰富,新时代的“人”如何找到存在的价值、改革路上“人性”的多维变化、两性情感中的激情与抉择……都蕴含在这一系列作品之中,氤氲着作家观念中的感性气息。从这些作品里,也能捕捉到写作者与彼时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窥测出作家的审美观念与时代主流观念之间的对话渠道。
冯骥才早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有30余篇,其中大部分为短篇小说甚至样式更为精巧的“小小说”。在与《中华读书报》记者的一次对谈中,作家曾回忆到自己早年写过的小小说《哈哈镜》,通篇才五十多字。文本仅有四行,写出不同的人在哈哈镜面前的反应,以此揭示他们各自殊异的性格与观念。可以说,以四行文字构成小说,对写作者而言绝对是一种挑战。1985年,冯骥才写下名为《让心灵先自由》的创作谈,他提出作家只有心灵获得自由,思想才能松绑,等到写作的活力恢复之后,就有可能找到久违的激情。显然,冯骥才收获了这种自由,袖珍体量的《哈哈镜》,既是其短篇小说写作的形式主义实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初期作家普遍持有的激情与创造力。
1982年,《哈哈镜》一文刊登在《鸭绿江》杂志第8期上,并附有《选主席》《胖子和瘦子》《狼牙棒》三个短篇作为“外三篇”。这一系列短小精悍的作品或是勾勒官场丑态,或是抒写时代风尚,抑或讲述民间寓言,且都统合在《哈哈镜》的主题之下。一面哈哈镜,为众生创造了一个极端化的情境,人们可以通过照镜子的方式,发现与日常生活迥异的另面自我,从中投射出世事万象与生活百态。哈哈镜也是变形镜,它能展现出心灵上有霉斑者的各种丑行丑态,给予世人以警醒。看《选主席》这一篇,某单位总共才十个人,却要选出九名主席和副主席,演绎了一场名曰互相谦让、实则争名夺利的闹剧。再看《胖子和瘦子》,简直是作家那篇讽刺“崇洋媚外风”的《BOOK!BOOK!》之翻版,针砭了市民盲目赶时髦的时弊。社会刮起流行“胖子”之风,人们便趋之若鹜,而风潮退去,“瘦子”之风袭来时,毫无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人们又开始追随所谓新的“潮流”。这些人什么风来了就随什么风,以别人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其盲从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东施效颦。再看《狼牙棒》,这是一篇现代寓言故事。赵六曾遭强盗的狼牙棒毒打,后来他自己也成了强盗,手持寒光闪闪、凶厉无比的狼牙棒打劫路人。不难看出,虽然是架空的故事结构,但赵六其人其事距离现实并不遥远,在极左路线下遭受过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人,很有可能在新的环境中成为新一代的“江洋大盗”,甚至会去伤害救过自己命的朋友。文章读到最后,不禁令人生出些许寒意。三篇充满反讽意味的小故事,直击了当时的人文生态,其意义又不断向未来延伸,指向对整体意义上的人性批判与思考,因而在“伤痕”和“反思”的时代文学框架之外,为作品赋予了更开阔的普遍性意义。
在今天的诸多冯骥才文集或是小说选集中,《哈哈镜》和“外三篇”一般被统合在《哈哈镜》的题目之下,相当于原先五十字的小小说又多了三个彼此独立却又在不同向度上反映人性的章节,形成一部“组合体”的小说。《哈哈镜》入木三分地讽刺了那些“假亦当真”的人,而《选主席》等篇目之间仿佛也有一条无形的线索串联着,这些文本都意图打破生活的常态,以“意料之外”的故事反映客观现实。就好比是在读者面前树起一面哈哈镜,通过镜子透视生活表层下的内相。从技法角度言之,冯骥才采用了民间“说书人”的口吻讲述故事,并以荒诞和幽默的因子,推动着情节向前发展。他创造性地吸收了古典笔记体小说、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爱丽丝·默道克、威廉·戈尔登等人的“寓言编撰”小说,多借寓言、民间故事、荒诞传说阐发对当代社会生活并非表面而是更深一层的理解。正如《选主席》中,最后只剩下老牛同志这一名群众,然而生活的辩证法却同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因主席太多,遇事常常争执不下,无奈,各位主席“都来征询老牛的意见,争取这代表‘群众’的老牛最关键的一票”,从而使老牛成为比主席还要举足轻重的人物。一部当代意义上的“官场现形记”跃然纸端,生动地加深了人们对官僚主义作风的了解。文章篇幅虽小,却和《二十万辆菲亚特》《表演扫地》《三十七度正常》等作品一起,构成了冯骥才反思官场文化的系列文本。
很多时候,作家都保持着不动声色、尽量不掺杂主观评论的态势,让故事自由前行,为人们留下了自由思考的宽阔余地。他擅长以平常人之心讲述不平常之事,使读者非常自然地进入作家笔下的一个个传奇空间,进而产生情感的共鸣。单从题目上看,“哈哈镜”自身的属性恰好与冯骥才擅长的夸张变形手法形成互文,他喜欢将事情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置于“意外”的处境之中,“有意把荒诞手法和写实主义的社会风情画糅合一起” ,并以“荒诞”将人性的潜在面相挖掘出来,写出既通俗又脱俗的小说。凭借此般艺术感觉,作家的关注点由“干预生活”过渡到探析灵魂的复杂性,在荒诞的乱象下揭示人性的弱点,直击民族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落后传统和思维模式,以期引起重视和疗救,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对接了现代文学的启蒙传统。《哈哈镜》透射出的荒诞色彩和批判精神,也充分地体现在冯骥才的其他文本序列中,成为冯氏文本的显在标签。
冯骥才小说中的荒诞意味,既是他为自己寻找到的理想表达方式,同时呼应了当时文学界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荒诞文学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初的荒诞派文学主要针对因为社会动乱形成的各种问题,对其进行批判和类似于黑色幽默式的反讽。在宗璞的《我是谁》中,主人公变成了虫子,丧失了对自我原始身份的认知,从而以荒谬的形式展现了那个时代异化的现实和人的悲剧。而谌容的《减去十岁》虚构了一份并不存在的文件,文件中传达了一个小道消息,说因为“文革”耽误了大家十年,所以允许所有人减去十岁。潜藏在这些文本中的时间焦虑感,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冯骥才的《多活一小时》,文中写到天神动了恻隐之心,决定给十个死者延长一小时的生命,看看他们如何利用这短暂又珍贵的时光,十个死者各用一句话依次作答,显露出不同的性格、志趣和境界。作品的内容是荒诞而非真实的,然而作家的叙述口吻又是真诚的,是在用荒诞意识表现严肃的思想主题。像《减去十岁》一样,《多活一小时》隐含了时人“浩劫重生”后的群体性时间焦虑,不同的是,冯骥才利用了微型小说的样式,将这种焦虑感通过一个场景集中塑造,仅仅依靠人物的话语成章,反而达到了直击命门的“短平快”效果。此般寓言性的书写、合乎逻辑的荒诞,延伸了小说言说的可能性及其限度,推动了当时微型小说创作的热潮。
无论是微型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它们的结构相对都比较清晰,不完全依靠情节的起承转合组接全篇,也无法承载信息过大的情感叙述。因此,如何寻找恰切的角度构筑小说的框架,就成为作家们思考的核心问题。大概是少年痴迷绘画的缘故,冯骥才经常谈及文学与绘画的关系,他认为西方绘画力求形似,注重逼真如实地反映生活,而中国画家则不依据眼睛透视,而是依靠心灵(现代美术学上的散点透视)摹拟现实,形成凝聚型的思维模式。如同中国绘画非常重视人物眼神的变化,从中透露风骨,小说创作也应当存有一个聚积着作品全部精神,可以解开艺术堂奥的眼睛。在创作谈《小说的眼睛》中,冯骥才提到他运思《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时,便找到过小说的“眼睛”。那便是高女人去世之后,每逢下雨天气,矮丈夫依旧习惯地“半举着伞”,那伞下却好像空了一大块,任何东西也填补不上。这样的画面出现在作家的脑海中,使他瞬间获得了创作的灵感,并由这个事态化的意象扩充出一篇名作。再如他写《雕花烟斗》时,想到的是唐教授得知老花农至死还叼着自己随意赠送的烟斗而唏嘘感叹这样一个“事态”。当他写《酒的魔力》时,首先映入脑海的便是老首长酒后恣意纵情的模样。可见,熟稔绘画技巧的冯骥才早已习惯了形象思维的方式,包括小说的想象与联想,都始终伴随着一幅幅画面的展开,他的小说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那些独特又具体的画面。而在作家动笔之前,当他找到了这些鲜活的事态画面时,便已在心中把小说完成了。
除去意象画面之外,小说的眼睛还可以是意境,甚至哪怕是一句话也可以担当眼睛的功能。这一句话(或者一段话)往往出现在篇末,无论是箴言还是悬念,都在结尾发力。冯骥才一向认为小说的结尾比开头重要得多,因为一件艺术品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在于它最后的工作是否恰当。尤其是创作小小说的时候,作家经常是先发现一个特别绝的结尾,然后紧紧抓住结尾这双“眼睛”,像古人写文章讲求的“凤头、熊腰、豹尾”那样,力求让结尾取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张力效果,甚至会先写结尾,把小说“倒过来写”。还是以《选主席》为例,他用打油诗“官儿多了不值钱……老牛无职却有权”作结,点出了作品的深层意蕴——嘲弄生活的人,最终都要被生活嘲弄;玩弄权力的人,自然也要被权力反噬。在这类短篇小说中,作家通常都会把浓郁的情节放在结尾部分,好像相声要抖响包袱一般。他对结尾艺术的重视,加上其简练的文笔、多样的手法、幽默的语言,最终锻造出“冯骥才体”短篇小说的文体特质。
从《哈哈镜》这类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作家的关注点始终是在人的精神世界,形成了对“五四”启蒙遗产的纵向继承,而文本中无处不在的幽默因子,既是对西方荒诞派文学的东方回应,也是对中国古典小说讽刺传统和游戏精神的现代重塑。同时,“冯氏故事叙述人”的口吻,包袱式的布局,地方词汇的强势渗入,使小说的现代性在“民间”的途径上成为可能。特别他的中短篇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传奇性”色彩,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包容性和象征性,一方面塑造了特有文化铸成的人文性格,另一方面也从这些故事中不断发掘出人类对信念的坚守、与命运不断抗争的精神。这是作家真实地与世界展开对话的方式,也是其作品的终极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