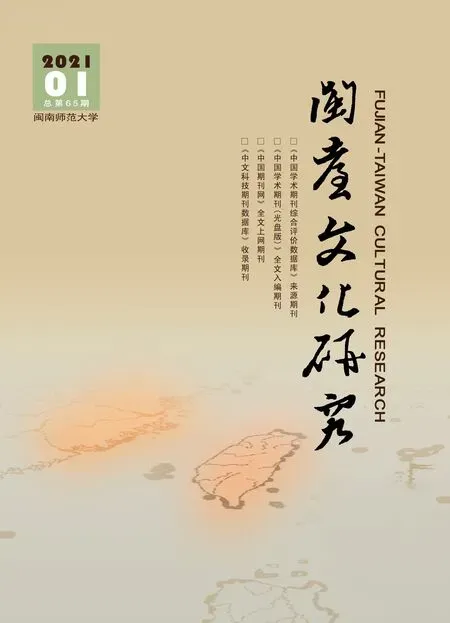身份认同与建构:林景仁《东宁草》解读
2021-11-11季金雷杨艳华
季金雷 杨艳华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漳州 363000)
林景仁(1893~1940),字健人,又字小眉,号蟫窟,著有《摩达山漫草》《天池草》《东宁草》三部诗集,均收录于王国璠总编《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合称《林小眉三草》。林景仁出生于台北板桥,为台湾首富板桥林本源家族掌舵人林尔嘉长子,幼年时因“乙未割台”随父祖避乱于厦门鼓浪屿鹿耳礁,后娶棉兰爱国华侨张耀轩之女张福英为妻,开始频繁在南洋游历与经商,中年时遍游欧洲,后客死东北。林景仁青年时期便浸润中西文化,精通多国语言且素有诗才,当代学者余美玲更是针对其诗歌当中大量的南洋书写,称其为“印尼书写第一人”。
目前两岸学界对于林景仁的研究成果不多,且大部分集中于其在南洋的活动与南洋诗,如台湾学者余美玲曾从“旅行书写”的角度探讨过其《摩达山漫草》与《天池草》。相对而言,学界对于《东宁草》的关注颇少,据笔者所知仅有林韵文《破碎与重构:林小眉<东宁草>的历史与地志书写》一文有专门论述,其余都限于各种原因论述不多或泛泛而谈。《东宁草》作为林景仁最后一部诗集,创作年份大致为1922~1923 年,内容绝大部分都与台湾相关涉,这就与之前诗作当中大量南洋书写形成鲜明对比,也暗含了诗人人生踪迹的变更与折返,以及通过诗歌积极建构对自己身份多样化认同的追求,这种寻找体现在《东宁草》中,主要包含“国族身份的认同与依归”“台湾记忆的缺失与寻找”“个体生命的迷惘与探索”三部分。
一、国族身份的认同与依归
自清政府甲午战败始,台湾便被日本侵略者殖民长达五十年,在山河破碎、大厦将倾的时代,林景仁虽未亲历乙未割台,但作为一名具有爱国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在诗歌中仍发出了“水仙致思慕,岛客吊头颅”的激愤之语,坦言羡慕屈原投水而死的忠贞与田横五百壮士自刎的气魄,这种于中国人身份的强烈认同与依归,具体就体现在《东宁草》之《咏史》三十首与《东宁杂咏》一百首中对明郑历史的吟咏与追思上。
(一)《咏史》中的国族身份认同
连横于《台湾诗钞》转引其于《台湾诗荟》为小眉所作的跋云:“林君小眉久寓鹭门,豪游南北,昨夜归里,时相唱酬;因取拙著《台湾通史》读之,作咏史诗三十首,亦少陵诸将之意也。”由此可见,《咏史》应是小眉返故里暂住,在阅读了连雅堂所著《台湾通史》后有感而发创作的作品,诸将则指的是杜甫于大历年间在寓居夔州时创作的政治组诗,意在总结安史之乱,告诫为将之人应吸取历史教训,不要重蹈覆辙。杜子美之诸将诗与林小眉之咏史诗,虽则一个在唐,一个已然步入民国,但联系时代背景,二者所表达的核心内涵却是相同的。在《咏史》三十首诗歌中,所吟咏的大部分人物都生活在明郑时期,如依附于台湾郑氏政权的遗老与郑成功旧部将:沈光文、朱术桂、辜朝薦、沈佺期、林凤、刘国轩等,林景仁在诗歌中均对这些于台湾有卓越贡献的人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例如沈光文,连横在《台湾诗钞》中将其排在第一卷卷首,并于《台湾通史·艺文志》有言:“台湾三百年间,以文学鸣海上者,代不数睹,郑氏之时,太仆寺卿沈光文始以诗鸣。”将其作为台湾文学发轫“第一人”,林景仁在诗歌中对沈光文也不乏溢美之词,称赞他“文章草昧开初祖”,肯定其巨大的历史功绩。对一些当时被清廷视为逆贼的延平部将,林景仁于赞美之外,更平添一抹钦羡与惆怅之意,如咏郑成功大将林凤:“天山三箭气如龙,白狄窥边屡挫锋。战垒尚標铜柱界,屯田遥辟玉门封。大呼想见千人废,单骑能排百尺冲。欢我鼓辇思将士,芗江极目满狼烽。”赞颂了林凤于鸡笼(今基隆)大败荷兰侵略者的英雄事迹;又如咏刘国轩:“汉鼎思凭一手扛,淮阴才调自无双。须知末运终难复,那有将军肯乞降。读史原心论功罪,登台回首慕旌幢。澎湖水战空千古,呜咽寒潮打怒江。”施琅率清军水师攻台,刘国轩力战不敌,遂说服郑克塽与群僚投降,在诗歌中,小眉对于刘国轩乞降一事给予了充分的同情与理解,称其“末运难复”,于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无力回天的怅惘之情。
综观《咏史》三十首对明郑历史的追思与吟咏,不能不说寄寓了一种“怀古伤今”的情绪,中国于近代所受西方列强的欺压早已在国人心中蒙上了一层阴翳,明郑政权最后的灭亡与台湾被迫割让的历史,两相对照,自然生发起一股自哀之情,但于这种情绪之上,小眉仍不忘勉励自身与国人,诗云:“中原日月存孤泪,荒外衣冠创局身。千载延平祠下过,古梅犹吐汉家春。”在咏郑成功之时,也对未来寄寓了美好的希望,这种作为群体意识的希望与决心也恰恰暗合了《台湾通史》自序所言:“凡我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孝,义勇奉公,以发扬种性,此则不佞之帜也。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实式凭之。”体现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
(二)《东宁杂咏》之爱国归依情怀
杂咏,近于竹枝词、棹歌一类风土诗,源起民间,属于民间文学组成部分,后经文人大量模仿创作,遂逐渐雅化,其书写对象多为极富地方色彩的景物、民俗等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小眉《东宁杂咏》之写作因由见于其七言诗所言:“同携铅堑掺奇语,追忆沧桑写旧闻,消尽胸中千磊块,一杯为我谢苏君。”苏君,即为苏镜潭,字菱槎,福建晋江人,为林景仁表亲,二人时有诗文唱和,小眉诗注清楚标明:“春日苦霖,约菱槎日课十绝句以自遣,间旬各得百首,题曰东宁杂咏,亦厉太鸿七子吊南宋之遗意也。”可见这一百首七言绝句乃是景仁带有游戏性质的诗作,虽是文人之间风雅的游戏,但于短短十日之间便能写出涵盖台湾历史沿革、山川、河流、民俗等内容且数量高达百首的作品,也足见小眉作为诗人的天才与知识涵养的深厚。但是,除却游戏这一表层写作动机之外,笔者认为小眉写作《东宁杂咏》更深层次的原因则体现在末尾“亦厉太鸿七子吊南宋之遗意也”所透露出的内涵上。厉太鸿,即厉鹗(1691~1752),字太鸿,号樊榭,钱塘人,在1723~1724 年间,其与吴焯、陈芝光、沈嘉辙、符曾、赵信、赵昱六人于赵氏兄弟位于杭城的春草园小山堂共同完成了《南宋杂事诗》的创作。《南宋杂事》共分七卷,每卷一百首七言绝句诗,内容涉及南宋都城临安(即今天杭州)方方面面,查慎行为《南宋杂事诗》做序,称其:“大而朝庙宫壶,细及闾阎风俗,或取诸志乘,或取诸稗史,或取诸名家诗文集,一篇之中,或专取一事,或连缀数事,网络散逸,巨细不捐。”可见其搜罗之广博,内容之繁杂,但是抛却《南宋杂事诗》作为“纪事诗”的历史价值,联系清前期时代背景,其写动机与反映的士人心态也是值得深究的,严迪昌先生在《谁翻旧事作新闻——杭州小山堂赵氏的“旷亭”情结与<南宋杂事诗>》一文中,明确指出《南宋杂事诗》创作的大背景乃是清朝前期,尤其是雍正年间文字狱高压下,浙江士人“异代梦粱的群体选择”,这也难怪小眉将其诗作与几百年前的《南宋杂事诗》相比,被日本殖民者强行掠夺的台湾,犹如刚被外族统治,士人认同感仍极度缺失的清初社会,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下,“梦梁”情结应该说是普遍存在的。在《东宁杂咏》一百首诗的篇幅中,大致有接近三十首诗作吟咏台湾历史,相较于前作《咏史》三十首大部分描写明郑时期人物,《东宁杂咏》中咏史的诗歌则涵盖了从元朝始设澎湖巡检司到清朝台湾收复、被重新纳入版图的所有历史脉络,显得更为完整,如诗言:“有元末叶隶同安,只向澎湖置牧官,终是羁縻荒服意,误人翻在版图宽。”景仁诗末注解:“元末于澎湖设巡检司,中国之建制于是始。”强调台湾自元代就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又如郑成功收复台湾、施琅攻台、朱一贵起义等台湾历史均有所涉及,但评价的重心始终不离“中国”这一概念。
林景仁自小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成年后曾多次于东南亚及欧洲各国游历,就是这样一个身上具有浓重西方色彩的知识分子,诗文中却处处显示出高昂的爱国精神,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也反映了传统儒家士大夫思想在小眉身上烙下的深刻印记,在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体悟与文化挖掘中,他也完成了大框架下文化心灵的认同与依归。
二、台湾记忆的缺失与寻找
板桥林氏垦殖台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乾隆时期龙溪县人林平侯随父应寅公渡海谋生,在居住台湾时期,林本源家族经过一代代成员的勠力拓展,已然成为台湾举足轻重的家族之一,林维源时期更是一跃而成台湾首富,可以说林氏发展的历史便是台湾历史的缩影,台湾的山川地理、人情风物都寓居了林氏族人深厚的感情,但林景仁年幼时便随家族迁居厦门,《板桥林本源家传》记载小眉“时清廷割弃台湾,从祖父暨父避乱于厦门”,故于他而言,关于台湾的记忆是缺失且为其所苦苦寻觅的。直到1907年随父亲林尔嘉回台处理家族析产事宜,他才第一次踏上祖辈口中魂牵梦萦的故乡。据《汉文台湾日日新报》登载,在小眉暂住台湾的这段时间,已经陆续发表了一些吟咏故园的诗作,如《咏北投温泉》《稻江晚泛》《秋感》《剑潭题壁》等,《咏北投温泉》发表于1908 年7 月26 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艺苑一栏。“北投”,位于今台北市最北部,地热资源丰富,在日据时期,北投温泉因日本人的大力追捧,遂成为当时著名的旅游景点,在诗歌中,林景仁以温泉之温暖比拟人世之温存,称赞道:“气自舒和水自春,花流竹影绝纤尘。爱他不作炎凉态,一样温存待世人。”台湾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则像小眉喜爱的温泉一般,时刻给予他来自祖辈的生活经验与记忆。如果说《东宁草》中咏史的部分是林景仁建构国族身份认同感与依归感的过程,那么其中大量描写台湾风土的诗篇(主要集中于《东宁杂咏》)则属于另外一种话语,这种话语厚植于民间,属于群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时刻发挥其强大的吸引力与影响力。按照内容分类,大致可以分为“地理、地形、气候”与“民俗、景物”两大类。
(一)地理、地形、气候
从地理位置上说,据日人川口长孺所编撰的《台湾割据志》记载:“台湾古荒服,福建海中孤岛也。在澎湖屿东北,故旧名北港,又名东番;因地势似弯弓,后有台湾之称。”台湾虽为孤岛,却与大陆属同一版块,其航行距离之近,正如小眉诗歌所言:“山连东野千余里,水接思明十一更。”所谓“十一更”,诗末注解云:“厦门至澎湖水程七更,自澎湖至台湾水程四更,一更凡六十里云。”如果按照这个算法,从厦门到台湾大约只需航行六百多里地就能抵达,按照现代观念测量,距离台湾最近的福建省平潭县到台湾新竹港仅需68海里,可见古人所言非虚,也从地理位置上确认了台湾与大陆的亲缘关系。
台湾多巍峨山脉,在《东宁草》中,小眉就吟咏了包括关潼山与白畎山、木罔山、魁斗山、观音山、大遯山在内的九座山脉。他称关潼与白畎二山为台湾诸山之龙,诗云:“关潼白畎两崔巍,万壑千峦此结胎。绝似吾闽浮海客,重洋遥长子孙来。”绵亘千里的山脉正如当时冒着滚滚波涛踏海前来台湾的祖辈先民;又如观音山与大遯山,林景仁在诗歌当中如此说道:“试看大遯抱观音,终老温柔共此心。莫便晏安笑公子,江山沉毒我争禁。”诗注有言:“观音山在西南,大遯山在东北,昔人每引此以嘲流寓不返者。”二山环抱,恰如母亲之手拥抱子女,但是又有多少往台湾谋生者能够按照原先设想衣锦还乡呢,期间难为人所言者实在太多。
台湾岛亚热带季风与热带季风气候兼有,故多台风与飓风,《台湾割据志》有言:“风涛喷薄,悍怒斗激,瞬息万状;子午稍错,北则坠于南风炁,南则入万水朝东,皆有不返之忧。”可见凶险万分,小眉在诗中也对这一台湾特有的自然现象做了描绘,诗言:“鱟尾悬空一片浮,伽蓝暴信近中秋。胡姬争唱公无渡,银浪如山黑水沟。”又言:“卷地黄沙扑鼻膻,细将风信测蛮天。秋台春飓长回忆,辛苦先民渡海年。”从大陆渡海前去台湾的船只经常因天气变幻莫测而导致沉船事故发生,先民谋生之艰难,于此可见一斑。
(二)民俗、景物
“台湾地,原土藩居之,不知所自始。至明季,漳泉人始徙而混居。”台湾自明朝末年才开始有大规模的移民发生,至清代中叶移民达至高峰,故此地大范围开发的历史并不久远,加之当地少数民族甚多,山脉广布,又属于亚热带以及热带季风气候,遂形成了于大陆难得一见的独特民俗与景物。
言之民俗,大致可以分为汉人民众的习俗与少数民族的习俗。往台湾迁徙的汉人,来自闽省的占大部分,而以漳泉二地居多,他们将祖家的生活习惯一并带入台湾,并与当地环境相适应,渐渐产生了独特的民俗习惯,如“端阳送蚊”,小眉在诗中就如此写道:“噆肤聒耳入宵多,佳节端阳一瞬过。今日积成负山势,空然稻梗奈君何。”自注曰:“五月五日清晨燃稻梗一束,向屋内四隅熏之,用楮钱送路旁名曰送蚊。”“送蚊”一词仅见于有关台湾的文献记录,如《台海使槎录》《重修台湾县志》,但其与所熟知的端阳节其它习俗,如烧艾草以驱蚊相类似,由此可知,因是大陆习俗在地化的产物。
台湾早期少数民族,书中有言:“种类甚藩,别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无酋,子女多者为众雄之,听其号令。土藩习俗,其性顽蠢,无姓氏,无祖先祭祀。自父母而外,无伯、叔、甥、舅之称……俗尚勇,好杀人……男女椎结,裸逐无所避。”这就是一般典籍里记载的当时少数民族的形象,带有强烈歧视与污名化色彩,甚至称他们会使妖术,这更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在《东宁杂咏》中,小眉一反传统士人高高在上,对少数民族大加贬低的态度,以八首诗记录了台湾当地少数民族的习俗。他称用竹木编制的番社“轮尔巢居少是非”,歌咏眉里社人民热情好客,则说:“告我至今眉里社,太羹醴酒尚人间。”对于深受儒家传统观念鄙夷的简陋丧葬习俗,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诗云:“鹿皮一里了尘缘,笑杀丧仪费简编。大得漆园生死旨,不私蝼蚁与鸟鸢。”他对“番人死或以鹿皮盖体,举而委诸山谷间”的习俗并不排斥,反而认为近于自然大道,这种开放态度实源于西方文明对其的影响。
再如景物,可细分为历史景点与动植物景观。在《东宁杂咏》百首中,小眉列举了诸如噶玛兰、赤嵌城、镇城土堡、鹿耳门港等极富历史气息,见证了台湾发展的地标景物,如鹿耳门港在清代因水深能泊大船,加之地理位置优越,遂成为台湾进出口贸易的门户,但时移世易,因泥沙淤积,逐渐失去了主要港口的价值。谈及动植物景观,台湾鹿港就因麋鹿滋盛而得名,小眉于诗中云:“爱看麋鹿走成群,白额生风古未闻。翻怪山前多哭者,不应别有猛于君。”又如人面竹、红金瓜、文旦柚等在外来人看来稀奇古怪的景观,小眉均作了有趣的描绘。
正如前文所说,杂咏源起民间文学,其内容也多记录当地独有的景物与民俗,作为与上层话语相迥异的民间语言,其所咏叹的也绝非限于帝王将相的光辉历史,而更多的是地方民众的生存经验与记忆,于林景仁而言,这更是对缺失的台湾记忆的寻找与建构。
三、个体生命的迷惘与探索
在《东宁草》自序当中,林景仁自言:“苍波万片,渺长古其安归。白月一棱,诉灵秋而何极。”如扁舟航行于大海,无所依傍,这大概就是小眉一生的写照,也反映了刚步入近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内心因时代巨变而产生的对人生的迷惘。小眉在诗歌当中也积极反映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其中既有因家国破碎所引起的身世自伤,也有因功业未成而带来的人生失落,正如其弟林希庄在《东宁草》序中所云:“仁人志士有所不得于家国之际,而有其盛衰隆污、成毁新故、存没聚散之感,忧愁幽郁之既久,一旦或触于外而动于中,遂藉山川城市月露风云草木鸟兽以洩其绵渺凄婉沉痛悲凉不能自已之辞。”这种上承诗骚传统,以诗言志的方式表明,诗不仅是他探索人生的方式,更已经成为其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家国破碎,自伤身世
在《七月望日渡台舟中作》一诗中,小眉搭船前往台湾,看见苍茫大海与被日本侵略者殖民的故园,不禁发出了“江汉东流迅,英灵正气徂。惘然念千载,何处问禹墟”的叹息,禹曾在南方大会诸侯,而今本属于中国的台湾岛却被异族统治,时移世易,又怎能不令人慨叹国事衰微呢?林景仁虽为富商巨子,从小衣食无忧,又加上未直接经历“乙未割台”这一屈辱历史,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感怀国事,但作为一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读书人,他必然已经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牢牢记在胸中,下层百姓固然应保有家国之志,又何言饱读诗书的士人呢?故其另一首诗所言:“忍将家世话台湾,一剑风尘岁月难。”将对家国破碎,故园不再的感伤与自身相联系,即使个人取得再大成功,也终究难以寻找到心灵的容身之处,所以小眉之诗,绝不是无病呻吟之语。台湾被日人占据,只是中国被奴役之一角,这一点,于国外游历多年的小眉体悟更深,在《示泗水旧侣》一诗中,他将华洋杂错,夜夜笙歌的印尼泗水描述为“云曼复星繁,喧闐九州市”的酒肉欢场,但在这样热闹的欢场,华侨所能得到的也只是喧扰过后的“断肠亡国音”与“颓哉陈元龙,豪气呼不起”的落寞感伤,荣华富贵只能麻木一时,但凡有爱国之心的人在麻木过后都会感受到难以言喻的刺痛。
(二)功业未成,人生失落
除却诗人这一重身份外,小眉作为板桥林本源这一世家大族的子孙,经商这一理想从小就成为其奋斗目标,小眉更是在诗中表明:“衣食与文章,民生难废一……吾爱鸱夷子,奇才古今杰。”他将春秋时期的范蠡视为目标,以文章经世,实业救国作为自己终生理想,但偏偏事与愿违,因一战影响,其岳父张耀轩在南洋的事业受挫并宣告破产,连带小眉损失惨重,不得不返回中国另寻出路,在这段时间里,他心情极度郁闷,如《咏牡丹》:“去年崇效寺,扶醉赏名花。今日毘耶国,牵愁似乱麻。恼人又春色,怜汝亦天涯,惜取眼前艳,翻嗟鬟际华。”颇有人事流转,年华逝去的感叹;又如在《次韵答文访》一诗中极言近况之愁:“近况惟诗可,奇愁赖酒迷。人间万刍狗,我辈一醯鸡。”但是在愁云笼罩的时候,小眉却并没有沉湎其中而丧失斗志,在《大屯山歌寄沈琛笙》这一首歌行体古诗当中,林景仁挥洒才情,展示了自己昂扬的斗志与对未来人生的希冀,他邀请自己的挚友“咏荷兰之陈迹,睢盱之遗风。吊朱明之块肉,延平之鬼雄”,字里行间,吐露风云之气,“天鸡一唱天下红,浮云纾散扫晴空”,正如红日初升,所有阴霾都被驱散,只留下朗朗天空。
无论是对于国族身份的认同,还是对台湾记忆的寻找,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个人,也唯有个体能将诸如国家、故乡等群体意识与个人理想、人生意义追求统一起来,而获得立体的感知与体悟。林景仁将自己当做“侧身天地一诗囚”,诗歌作为其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给予了他探索人生的通道,但是作为一名不能离俗的人,他的理想却并非只有诗,而是想凭借自身努力于天地间做一番不亚于其祖辈的事业,就是在这样矛盾与求而不得的曲折旅程中,小眉还是走了传统读书人的老路,在出世与入世的选择中徘徊辗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对个体生命的迷惘与不懈探索,同样隶属于其身份认同与建构这一大的框架。
综上,《东宁草》作为林景仁最后一部诗集,代表了其作为诗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与建构,其中既包括群体意识范畴的对于自己中国人身份的阐发、台湾回忆的寻找,也包含了作为个体意识的对于自身生命、人生的探索,他秉承“以诗言志”的诗骚传统,在吐露性灵的同时也对当时闽台社会做出了自身独有的描绘,从中亦可见出巨大的文化与社会历史价值。
注释:
[1]余美玲:《诗人在南洋:林景仁<摩达山漫草>、<天池草>探析》,《台湾文学研究学报》2017年第24期,第199页。
[2]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193页。
[3]孔昭明:《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台湾诗钞>》,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283页。
[4]连横:《台湾通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第379页。
[5][6]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13页。
[7]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14页。
[8]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19页。
[9]连横:《台湾通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自序”,第8页。
[10][11]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59页。
[12]厉鹗等撰:《南宋杂事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查慎行序”,第8页。
[13]严迪昌:《谁翻旧事作新闻——杭州小山堂赵氏的“旷亭”情结与<南宋杂事诗>》,《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第54页。
[14][15]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59页。
[16]王国璠编:《板桥林本源家传》,台北:林本源祭祀公业,1975年,第93页。
[17]林景仁:《咏北投温泉》,《汉文台湾日日新报》1908年7月26日,第3071号。
[18]孔昭明:《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台湾割据志>》,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1页。
[19][20]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75页。
[21]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76页。
[22][23]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77页。
[24]孔昭明:《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台湾割据志>》,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1页。
[25][26]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81页。
[27]孔昭明:《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台湾割据志>》,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3页。
[28]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86页。
[29]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87页。
[30]孔昭明:《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台湾割据志>》,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3页。
[31][32]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97页。
[33][34]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98页。
[35]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93页。
[36]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
[37]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188页。
[38]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193页。
[39]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300页。
[40][41]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58页。
[42]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139页。
[43]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49页。
[44]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46页。
[45][46]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204页。
[47]王国璠总辑:《台湾先贤诗文集丛刊<林小眉三草>》,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