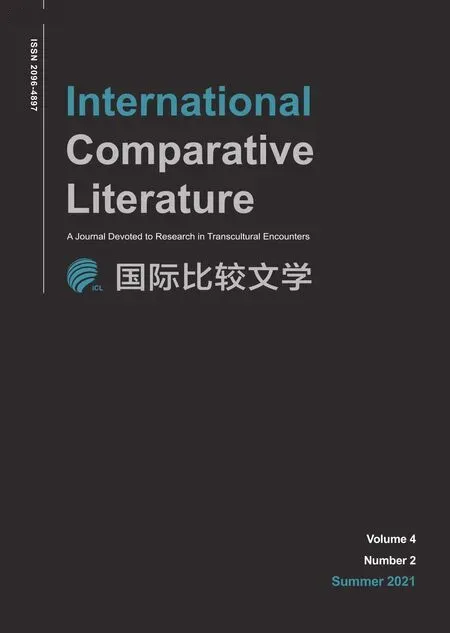吴真:《孤本说唱词话〈云门传〉研究》
2021-11-11许蔚
海内外有关道教文学之研究,历年以来多有累积。尽管学界至今对何谓道教文学并未形 成共识,但已有成果除个别作家研究外,大多围绕道教或神仙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体裁及文体)而展开。就此现状,所谓道教文学似乎首先是建立在对“文学作品”(或作家)甄选的基础之上,那么,与排除在外的世俗或其他宗教题材的文学作品相比,除了道教这一点外,似乎没有独自成为一个领域的特殊性。而就道教研究立场出发,对道教因素、实践或逻辑的关注,才是首要的,其研究对象既可是为文学史所接受的文学作品(或作家),也可是一般不被视为文学研究对象的仪式文本、文章片段或应用文体。从文学、道教两个方面来看,道教文学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无疑都存在着重视文学性或文学史意义,重视道教特质或道教史意义这两条或交叉或平行的路线。
一
吴真《孤本说唱词话〈云门传〉研究》系围绕明刊本《云门传》展开的专门研究。《云门传》系讲述李清入云门山洞府遇仙,还家后世异人非,行医济世,悟道成真的说唱词话作品,本身既是道教题材,也具有道教说唱文体的特质及说唱文学、白话小说等方面的文学史意义。
该书原藏北平图书馆,1933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列入子部道家类。吴真根据1930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展览会目录》、仓石武四郎1928 至1930年间拍摄的《旧京书影》均未收入该书,推测在1930年至1933年间入藏。此外,她也对该书的流转、复制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除了辗转上海、美国、台北,以胶片形式分身各地外,尤其提到马廉曾藏有据该本抄录的一个副本,但未及研究而去世,此后,该抄本虽经马彦祥递藏,也未见发表研究,最终就静默于首都图书馆的书库之中。
在此补充一些细节。一般而言,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在抗战中迁徙,经上海装箱迁往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移交台北“中央”图书馆,后转交台北“故宫”代管。不过,《善本书目》子部道家类著录的55 种,绝大多数留在了上海,随后都归藏北平,现在仍然保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而随军舰飘扬过海的7 种,根据当时的装箱清单及展览书录,除明嘉靖内府抄本《金箓御典文集》、《御制金箓大斋章表》及明抄本《徐仙翰藻》零册等3 种3 册系1941年5月临时选出装填的预备展览品外,明刊本《云门传》、明嘉靖刊本《观化集》、明抄本《缘遇编》以及明万历刊本《栖真志》等4 种系原装于百箱中的寄存善本。《观化集》是一种糅合了律、绝等诗体形式的丹道论述,《缘遇编》是外丹黄白之书,《栖真志》收录老子以下至莫月鼎、铁脚道人的传记,《云门传》则是就单一神仙故事敷衍而成的文艺作品,相互之间没有关联。4 种书形制都较窄小,篇幅也不长,尤其《缘遇编》是极小的巾箱本,《观化集》仅有10 来叶;未入选的50 余种中,有开本极大者,如明嘉靖刊本《赐号太和先生图像赞》。因此,不排除这4 种是为了填塞书箱空间而随意拣选装入。后来临时选入的《金箓御典文集》、《御制金箓大斋章表》虽形制较为阔大,且配有木函,但也没有就装入新增的第101、102 箱中,而是随30 余种其他书填入了原百箱中的第39、53 箱之中,很可能也是出于填实书箱空间的考虑。
王重民在美协助筹备展览,撰作提要,将《云门传》改列入集部曲类传奇,并对其各方面的特点,尤其是文体、句法、与变文及宝卷关系等提出意见。就文献目录的分类而言,从子部道家类调整为集部曲类,既反映编目者的知识储备与预流意识,也体现了不同的学术立场。对应目录分类的变化,学者对于明刊本《云门传》的认识自然发生改变。以道教研究或者道教文献调查为目的工作,很容易忽略《云门传》。而有限的研究也全部集中于俗文学、说唱文学或者白话文学方面。由此呈现的路线,即在“文学作品”中发现神仙题材的《云门传》,进而在文学史脉络中定位“失踪者”。
二
吴真指出,尽管李清故事早见于《太平广记》保存的《李清》,但并不存在一个“唐宋以来相传旧本”,不仅俗文学、词话书目中完全见不到踪影,在青州当地社会流传度也甚小。而《云门传》就其雕版字体来看可能是万历刊刻,书中出现的“银绞丝调”则兴起于嘉隆时期。为摸清《云门传》在嘉万时代“突然”问世的缘由,吴真观察了元明时代青州地区特别是云门山的全真道庙情况,并特别注意到在地藩王衡府的崇道行为,指出在嘉靖时期,李清故事的发生地云门山已经全面道教化了。尽管在地方碑刻文献与田野考察中,吴真并未发现李清祠庙或李清信仰痕迹,但《云门传》却称山上有“烂绳亭”,并称当地人“兴祠立像”、“春秋祭赛”。她认为在道观或道庙中与其他神仙一同供奉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倘若当地确实存在李清信仰,这一想法是合理的。李清既然在嘉靖时代已被历史化,要在云窟兴建道庙或者宫观,自应尊重本地原来的主人。道庙或宫观确有尊重地主的传统,通常做法是为原地拥有者保留一间地主祠或地主龛。而在当地祭赛网络中,也应有牌位或者神像之类的象征物被供奉或流转,并且也很可能制造经忏文本(《云门传》本身,是否可以承担经忏或者朝山曲子的功能?)。当然,倘若立祠、祭赛只是兴到之笔,以上推衍就只能是空谈。吴真的田野工作告诉我们“李清信仰及其口头传说,已经退出了青州的历史记忆”,那么,《云门传》的创作与地方信仰特别是当地的全真教究竟有何直接关系也就无法回答。
另就内容及形式,吴真认为四句谶偈可能受到《水浒传》影响;王世充登场可能受到说唐题材影响;尤其10 字句唱词与成化说唱词话及《大唐秦王词话》在句式上完全一致,无疑是具有文学史意识的敏锐观察。此外,她甄别出《云门传》中一些“当代语料”。她指出李清取得的《活幼全书》其实是弘治八年初刻的明代常识;李清提到的《大观本草》,11 种明刻有5 种刻于山东,且成为通行版本,确实“出在我山东”。
在此还想补充一点猜测。青州地区自唐代就已开掘煤矿,当地矿业巨镇颜神镇在明代隶属益都,而益都正是李清故事发生地青州城的所在。与源文本比较可知,《云门传》对李清自缒入云窟增加了许多细节描写,读来如临其境。李清让众人准备绳索,四根悬住大竹篮,中间一根系铃,以辘轳绞送,齐备后,亲眷奉酒,有老者建议“先取一个狗来,放下去看”,被李清拒绝。李清放入洞后,“岂知穴底,黑洞洞的,已是不见一些高低,况地下似有水的一般,又滑又烂。还不曾走得一步,早跌上一交”,“元来这穴底,也不多大,只有一丈来阔,周围都是石壁,别无甚奇异之处。况且脚下烂泥,又滑得紧,不能举步”,“却又去细细摸看,只见石壁擦底下,又有个小穴,高不上二尺”,“钻进小穴里去,约莫的爬了六七里,觉得里面渐渐高了二尺来多,左右是立不直,只是爬着走”。初刊于崇祯十年的《天工开物》,记载开挖矿井,除用辘轳绞送竹筐外,也意识到井下煤层会散发“毒气灼人”,有用长竹筒插入煤层向井外排气的措施。老者取狗的建议,山顶守候的子孙猜想“这老人家被那股阴湿的臭气相触,多分不保了”,或许可看作是矿井毒气经验的反映。而矿井必须加固坑壁,“其上支板以防压崩”;泥泞也是坑道中的当然之事。如吴真所说,《云门传》应出自青州本地的创作,那么,这一描写会否是面向在地矿民的定向写作?
吴真认为《云门传》有意在表演时抖包袱。这虽是对有关文字的细密推究,同时也源于她对该书性质的判断。《云门传》体式上韵、散并行讲述同一个故事,虽然可用“复调”理论来挖掘韵、散异同与修辞功能,但直观感受确实是拖沓重复而不堪读。而这却正是《云门传》意义与价值所在。吴真指出《云门传》不像明成化词话等俗文学刊本那样图文结合,全书无图,并且每叶都有难读、正读字注音,有的标注俗字,甚至标注音调,“很显然,如果它只是一本案头读物,则没必要连声调也标注出来,去声的标注肯定是服务于唱诵的现实需求”,而标注俗字则表明“有意面向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方便他们诵读甚至表演”。案头与场上是明代剧作者间实际发生过的创作争论。对于表演性的文本,学者除了阅读文字,也应该体会表演的需要。道教仪式研究也类似,仪式文本研究即需要注意实际运用问题。不仅仪式本身需要不同职能的人员参与行仪及念、诵、唱、赞,一些经忏、礼文在形式上也具有韵、散并行复述的特征。有些仪式还设置角色,安排唱词与念白,以戏剧或者“道坛戏”的形式来表现。吴真正是将视角从案头转移到场上,从而带来实质性的突破。她关于演唱、说唱并重、说主唱辅的体式演进;7 字句、9 字句、10 字句、11 字句这样长短句变化造成口头节奏的变化;28 段韵文每段一般40 个韵字全部按照《中原音韵》,且一段之内重复两次的韵字不超过五分之一表现出来的唱词押韵技巧,以及全部压平声韵在演唱时音调铿锵与清代鼓词接近、以儿字入韵的儿化韵、南北方音等方面的认识;尤其是对《云门传》中出现的以攒十字道情与散、韵结合,通过三种形式反复表演李清家道沦落的故事,认为是“现场表演的重头戏—听众最喜欢听的一段”;对侉调[银绞丝]顶针颠倒体式及表现“叹五更”的哀伤曲风,流播江南后曲风大变的论述;结合《金瓶梅词话》对道情表演的描述与苏州评弹、扬州弹词表演时的“双档”分工,指出“职业艺人上门演唱道情,表演形式为二人打着渔鼓同台合演”,说白艺人叙事,演唱艺人抒情,“在口头表演中,同义反复却有它独特的宣教功能”,不仅是对场上表演与语言运用的亲切体会,同时就文学史而言也是看来虽细小却极其重要的发现,如她所说是可以填补缺位的研究。
三
吴真提到她笺注时侧重抉发“宗教语言的本意与奥义”。她在注释词义的同时,提示同时代俗文学文本的共同用法,确实将单一文本充实延展,使得读者能够借助这一文本从而真切了解《云门传》的时代性、地域性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定位。在此就隐藏叙事再作申发。
李清还乡时“想我当初本向南门出,怎么指引归途北郭遐”,之后转城南,出南门,重上云门山,看见云窟穴口碑石题着“李清招魂处”,疑心自己已死。后文虽通过山中一日,世上千年打消了死亡疑虑,但为何指引向北郭却并未得到解答。实际上,《李清》中神仙就依然送他回南门,北门实为《云门传》特意的改写。这正是隐含叙事的标志。
仙乡淹留,表面上是讲述遇仙,但遇仙就意味着不归,对于乡人或家人而言,入山者就是死亡。杂剧《刘晨阮肇误入桃源》,刘、阮返乡时,刘家正宴请宾客,做春赛“牛王社”。“牛王社”即牛醮,是为祈愿耕牛不受时行疫疠损伤而举办的仪式活动,除醮献牛犅大王外,最重要的仪式内容是赈济孤魂。刘、阮入山不归,属于意外死亡,一般是不被允许在家族祠堂/神案享有祭祀,也即不得拥有牌位的孤魂,只能在醮祭时接受赈济。杂剧设定这一场合让刘、阮返乡,之后又觉悟返山仙去,相当于是孤魂在举行牛醮的坛场之上于寒林所/孤魂台接受赈济,经祭炼而得以完形复体,超生仙界。
《云门传》也有仪式性的类似考虑。李清入穴以前,家人就疑心他必死。他入穴之后,摔了一跤,昏死过去,“子孙辈只是向着穴口,放声大哭”,“到得明日,子孙辈重来山顶,招魂回去。一般的设座停棺,少不得诸亲众眷都来祭奠。过了七七四十九日,造坟下葬”。而李清自己苏醒后,发觉穴中空间甚小,仅一丈来阔,四周壁立,且满地是青泥,及至从小穴穿行,终到神仙观宇,“才有青衣童子启门迎。岂知不用人通报,早已识破门前那姓名”。尽管将云窟看作墓穴看似牵强,但青泥、仙境、童子启门等确能在墓穴环境与壁画中发现(青泥也是《云门传》所添加)。童子知他名姓,从显叙述层面而言当然是神仙预知,从隐叙述层面则是标定墓主人。之后李清被神仙接纳,从神仙故事的角度当然是留在仙乡,从墓葬或者死者的角度则是离开人世,居于幽壤,从此阴阳两隔。
神仙给李清定下的禁忌是不得开北扉。盖因打开北扉即看见青州城,便会生思归之心。这当然是从《李清》沿袭而来,但在《云门传》的改作语境中,应可看作是针对李清魂灵的禁忌,即不得“望乡”,思归阳世。生死须异路,不得复相干,魂灵过了“望乡台”就不当再返回,这是元明时代道教幽科、佛教水陆仪及一般冥俗中的通常逻辑。李清思归,即有挂碍,便成滞魄。《云门传》将他返回青州的路线改为走北门,无疑符合其北阴中游魂的身份设定。
李清归途中,除由青衣童子引导外,还有“神虎”的出场,“早把李清一吓,吓死了”、“单使指引归途都忘却”。跌倒醒来后忘却来路,是唐宋以来入冥文学惯用的习套。而宋明时代道教幽科坛场上有神虎堂,安置神虎司夫人、玉女及将吏,行仪时即以神虎符命追摄魂灵。虽然神虎将吏并非《云门传》的老虎之形(道坛画确实有绘成骑虎武将形的),但后者既然名之以“神虎”,又与引路童子配合出现,应当说对道教幽科的做法还是有相当的忠实度。此外,相应的韵文中甚至还出现了“消灾救苦我天尊”的表述。尽管这应该是指洞府中授予临行偈语的仙人,但既涉幽冥中事,对听众而言,只要稍有道教经验,便可联想到太乙救苦天尊。
李清返回青州后四处游荡,出南门,复上山,又转东门,过祖坟,不仅看见碑,还看见墓,认定自己“死已多时了。今日来家的,一定是我魂灵,故此幽明间隔,众亲眷子孙都不得与我相见”。接下他便到东岳庙听道情。如吴真所揭示,青州城东门内确有东岳庙,这一细节应是对在地景观的真实反映。而从隐叙述的层面来看,李清魂灵四处游荡,明白自己已死后,到东岳庙报庙,符合明清时代道教仪式思维。东岳庙前听道情是全书转折。这一部分用韵、散、道情三种方式反复讲述李清家族败落。就听众的立场而言,这当然是一曲“太上感应篇”,对表演者来说也具有强烈的劝善意味。
猜你喜欢
杂志排行
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的其它文章
- ICL人物
- 投稿须知
- 一流国际化期刊建设与中国期刊人的责任担当*
——第二届一流期刊建设高峰论坛暨人文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综述 - Charles William Johns.The Irreducible Reality of the Object:Phenomenological and Speculative Theories of Equipment
- An American Scholar’s Research on Chinese Wo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n Interview with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Gail Hershatter*
- 文学与瘟疫的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