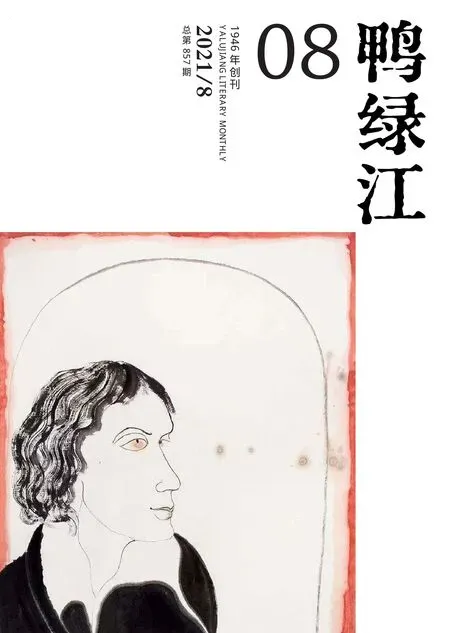烁烁金河(主持人语)
2021-11-11宁珍志
宁珍志
“一条大河波浪宽”,大河不是长江,不是黄河,不是辽河,不是大凌河,是金河,著名小说家金河。我20世纪80年代中期调入辽宁省作家协会,正值金河的黄金时刻,不数他身上集聚的作协主席、党组书记、辽宁省劳动模范、省委委员、全国党代会代表等诸多光环,单凭《重逢》《不仅仅是留恋》《打鱼的和钓鱼的》接连获得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1982、1984),《历史之章》获得第一届(1977—1980)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非凡成就, 金河就足以名列文坛高处、闪闪发光。
在那个闪烁无数亮点的时间,金河每每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竟能与原刊同期转载,达四五次之多。《新华文摘》转发金河短篇十余次,此纪录作为辽宁作家之最,即使置身全国,也罕见。《人民日报》连续两天用两个整版转载《打鱼的和钓鱼的》,开创了该报新时期文学发表篇幅的先河,前无古人。上述三篇全国获奖小说,加上《大车店一夜》《带血丝的眼睛》《白色的诱惑》《市委大院的门柱》等四篇小说,先后七次获得辽宁省人民政府优秀文艺作品奖,后无来者。
每一篇优秀的小说都是一波深邃、清澈、警醒的支流,汇聚成一脉思想艺术荡漾的知性干流。等风来,我把“风”比作读者、评论者鉴赏能力的眼光,深入其中即会掀动一场又一场的内心情感风暴,卷起千堆雪浪,会同作者一起,加入思想者的行列。掬起金河短篇小说若干细节的浪花,都能还原至时代、社会、人性的漩涡里去;而跟随或者发生在金河身上的一些生活细节,或许还未能被重新解构,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妨撷取几朵,尽管阳光周而复始,仍不会被蒸发,因为它们为金河独有。
诗人阿红,195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当年即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长命和清明》,1954年到《文学丛刊》(《鸭绿江》曾用名)做编辑,诗歌创作、评论成绩显著,全国有影响。金河不解,这样一位能人,怎么就只做到《鸭绿江》编辑部副主任?侧面打听,有人说阿红身上“有商人气息”。难道就因为创办了全国首家“鸭绿江文学创作函授中心”,便获取了这个印象吗?金河征求各方意见,决然“提拔”阿红为作协书记处书记。阿红、金河是邻居,近到每天几乎都能照面,但无往来,唯一一次还是阿红拿着“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才树莲诗歌作品清样,手舞足蹈的样子,举给金河看,“金河同志,这是咱们省的文学新人!”听,“金河同志”。
老作家邓立,又名梁山丁,“文革”结束返作协,多次表达自己加入党组织的愿望,申请书递上的就是一颗赤诚之心。金河向老干部支部了解情况,说正在进行。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金河问过几次,直挨到邓立住进医院,生命垂危,仍无结果。邓立长子找到金河,代替父亲又一次诉说心愿。金河感动,也尴尬,不宜再拖,哪怕追认。他立刻找老干部支部书记,询详情,对方面露难色,表情是邓立在东北沦陷时期发表的作品,立场把握……金河生气了:“邓立作品表现殖民地劳苦大众生活凄惨命运,有错吗?如可能,请马上召开支部会议,我参加。”会上陈述事实,历史说话,一致通过。党员获批,邓立竟奇迹般活过来。这还用感谢吗?是党组织生活的一次慢待与抢救,金河向邓立及家属致歉。清者自清,邓立把自己解放前的文学作品编辑成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鸭绿江》资深编辑吴竞错案平反,从辽西农村重回作协,仍操旧业老本行,执行编辑部小说组组长职责。当年为爱情毅然辞掉公职与吴竞一同奔赴乡下的妻子,回城工作成为问题,因不是“组织安排”,属个人情愿,没任何手续。吴竞拖儿带女一大家子,艰难程度一目了然。金河知晓原委后,决心为吴竞妻子找回工作,“落实政策”才算彻底。由于一些背景关系错综交织,遭遇阻力。金河奔走请示,多方沟通协商,所费时日不少。耽误了多少篇小说创作?金河没算,总算为吴竞妻子在作协“计划”到了工作。后来未能如期上岗则有另外原因,金河的努力化作遗憾。不过,他没后悔,当领导,该为群众平分“难”色。
金河也有被误解、被错怪的焦虑。身为党组书记、主席,小说创作其实是在业余时间完成,一部分时间又被分配给他人新著写序、给业余作者看稿,包括“鸭函”学员慕名寄给他的一摞摞小说,金河几乎“来者不拒”,只要信任。他认真,成败如何,都要写出个“一二三”来。因此,熬夜成为家常便饭,困倦时中午睡一觉难免。夏日一天,老诗人收到省里文件,急匆匆推门,未等金河蒙眬睡眼完全睁开,给跨栏背心罩上件衬衫、走到客厅,老诗人就高声读了起来……急性子还要快传达。事后有“风言”,说金河不尊重老同志,斜躺床上听汇报。传到金河这儿,愣怔两秒是无奈,没办法,作家圈的传话添枝加叶功夫可想而知。能追根寻源去当面对证吗?太小孩了,太没气度了。听的遍数多了,金河报之以苦笑。
苦笑释放的是一种胸怀,如同一条大河的“波浪宽”——我把这仨字理解为胸怀的形象化。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优缺点的放大与缩小是人性的两面镜子,照别人优点容易缩小,照缺点则容易放大;照自己的优点容易放大,照缺点则容易缩小。如果用这两面镜子照金河的胸怀,镜子会显得小。拿在手里的镜子,能不小吗?
著名作家写了部著名长篇小说,呈现的内容几乎能还原到作协的一些人与事,对号入座率很高。内有金河新感情生活的表述,是钦敬的文字,无贬义。可是,属于个人“私生活”影像,毕竟真实得太熟悉了。作家偕夫人去看望金河,无须注释,意义自明,彼此笑笑,心领神会。金河是过来人,看得开,能理解,不必多虑,创作自由,何种方式能驾驭自如,个人掌握就好。写实着,浪漫着,怎么方便就怎么来。金河的胸怀也许把控着自己,不必说出跳开生活拘囿,虚构与想象力,也是衡量一位作家创造力乃至生命力的重要维度。
《鸭绿江》一次托作协人员为金河捎去一沓A4纸打印好的材料,是装在单位的大牛皮纸袋,两个书钉封好的。不巧,金河外出,文件辗转三五天后被退回。到编辑手欲打开,却发现纸袋两个书钉钉眼的位置被扩大不少,就是说文件袋不知在哪个环节被人打开过,重新装订没有准确找到原来位置。经办人当年可是把沈阳公安局编写的厚厚两大本《卫士凯歌》翻得滚瓜烂熟,有点侦查与反侦察能力。把材料亲手交给金河,年轻人难免流露出点小愤懑,私拆信函、偷窥陋习、有失公德,该顺藤摸瓜找出来。金河笑了,急忙制止,给人留点颜面。也是,材料非机密,只是编辑部编创计划及内部管理意见而已。作协处于党组班子更替的人事变动期,偷窥者莫非想从中知道点确切消息?没想到大失所望。和嫉妒不同,偷窥或接近于本能,这是人的问题,更是人性问题。金河把人展开,为人性留有余地,望得深远。有的人不能,也不敢,因为心里装不下。
金河不再担任作协党组书记之后,周围事物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一些人的疏远、背离渐成常态。甚者甚至背地划清界限,托人表明立场,帮派观念根深蒂固。有的话语传来,金河不为所动,左耳听,右耳冒,就像鸟儿飞过蓝天。内心强大,刀枪不入,该来往还来往,该主动还主动,和为贵。东西南北,天高海阔,八面来风,何去何从,智者自明。《明史》金河读了十来年,眉批也有十来万字,世事沧桑,人情百态,金河岂能不晓得?
不过,金河真的很少写小说了,或者说他已经不写了。他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深处,写长篇纪实文学《平房魔窟》《烈吏于谦》《阎宝航传》。历史才是青铜器,经风著雨岁月磨蚀,拂去灰尘尚需要时日。现实的敏感度犹如易碎的瓷器,把控不当就容易掉落地上,而人际关系的利害更是薄如羽翼。现代小说的多种可能性提示我们,生活虽然不一定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但毕竟能为创作提供源泉性、细节性的素材——我以为的。至于金河为什么不再写小说,没与他深谈,不能随意揣度。
不再写小说的金河,对自己、对读者、对社会、对文学来说,都是一种损失。这损失对他(它)们来说,都能承受,而完全接受,则充满着惋惜和不舍。无数条小溪潺潺流淌,涌入宽阔的河面,阳光下波光粼粼,滋润四方,像人生的一幅幅灵秀的画面,像小说的一个个生动细节,给予满目满心的景致和情思,流向遥远。一条大河,曾经滔滔,能为新时期文学史册留下章节,够足金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