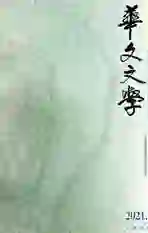小说家言、知识氛围与历史记忆
2021-11-10操乐鹏
操乐鹏
摘要: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蕴藏多重诗学资源:其以小说家言融接笔记与评书的叙事传统,挑战着现代小说的既有范式与审美惯性;在知识氛围中对小说与历史、真实与虚构进行辩证和质询,且同艾柯、高阳的小说构成对话关系;文本中对父辈、眷村及历史创伤记忆的书写亦接续着眷村小说的流脉;其叙事践行与二十世纪末台湾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既有绾合又有裂隙处。《城邦暴力团》由此熔铸生成了多音驳杂的小说构型,极大地引动和释放了现代小说的文体潜能。
关键词:张大春;小说诗学;小说文体;知识氛围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1-0050-08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台湾时报出版社版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城邦暴力团》,都在封底或腰封的宣传语中强调该书的武侠小说属性:“现代新武侠”,“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①。诸多论者即习焉不察地以武侠小说视之、论之。诚然,小说所叙,颇多武林江湖门派之人事,与民国武侠、新派武侠亦不乏照应相合处:如描写孙孝胥的轻功不脱老实和尚的身法(《陆小凤》);万砚方不愿将万德福收为徒弟,而只传给他调息运气的法子,全真教马钰赴大漠指点郭靖也是如出一辙(《射雕英雄传》);哑巢父李绶武博览群书,对武功身法招式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确乎有着王语嫣的身姿魅影(《天龙八部》),而李在自家茅舍前摆布的八阵图,也不由让人记起黄药师桃花岛与瑛姑黑龙潭的五行阵(《神雕侠侣》);居翼的曼陀罗汁碰巧扎回了邢福双失去的记忆,此类误打误撞机缘巧合更是武侠小说所擅的套路……文本中是类武侠因子层出不穷,无不使谙熟金古温梁的武侠迷们心潮澎湃,大呼过瘾。
《城邦暴力团》关涉的题材类型庞杂繁复,假如止于“武侠小说”的题材定位和阐释路径,势必挂一漏万,难免小觑了张大春的诗学追求与抱负。职是,不妨尝试从小说的诗学渊源与文体生成进入:追索《城邦暴力团》何以融接传统,游弋于笔记、评书等多种文体间,挑战着现代小说的既有范式与审美惯性;寻绎其在知识氛围中对小说与历史、真实与虚构的辩证和质询,且如何同艾柯、高阳的小说构成对话;考察张大春的诗学践行之于眷村小说的流脉以及台湾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思潮,究竟是别开生面,还是规行矩步。下文即就《城邦暴力团》的多重诗学资源展开论述,并结合张大春的创作心态、叙述策略,希冀揭橥其多音驳杂的小说构型,以及由此所引动和释放的现代小说文体潜能。
一、笔记/评书:小说的“叙”与“说”
“随手出神品”的笔记,对张大春而言,其要义绝不在于成为现代小说家的材料库进而能够被小说家加以吸收、改写。笔记本身即为中国叙事学的心脏,广袤的笔记丛林中内蕴着中国叙事学的重要精神,写作者“透过一种趋近于零的低度写作方式,一种近乎‘格物的方式,在叙述材料的过程中发现、寻觅、认知自我的方式”②。因此,笔记小说自有其叙事哲学,不待作家们对之改头换面、添油加醋。而如王安忆以现代小说衡笔记,认为笔记“一个奇人、一桩趣事、一点风月、一句警示名言,便成一篇”的构型“缺乏戏剧性,没有事件的过程。分量过于轻,过于轻描淡写,削弱了短篇小说的力量”③。这其实是对笔记南辕北辙的指摘。
张大春对笔记的体认,还可从他对汪曾祺的不吝赞美以及对鲁迅的误解中窥见一二。汪曾祺将唐传奇和宋以后的笔记看作现代短篇小说的两个传统,对无功利的、聊资谈助的笔记尤为偏爱,以为要接续笔记传统,但“不必着意模仿古人”,得有“‘现代的东西”④。这些概括均与张氏合。非徒如此,张大春更认为汪曾祺没有“取用”笔记,而是“打造”了现代味道的笔记。“取用”者,借鉴、模仿之义,失之于刻板、机械;“打造”,则是真正意义上融会贯通的创造。汪氏短篇《鉴赏家》,不正是一则随手出神品的笔记嘛⑤!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中引述并发挥陈振孙的看法,认为《太平广记》“……盖意在取盈,不能如本传所言‘极鬼神事物之变也。”⑥一向以为“鲁迅够聪明、够剔透、够冷隽”的张大春由此认定鲁迅跟着陈振孙瞎起哄,体会不到洪迈与异端知识的核心價值,也就忽略了洪迈所示范的写作理想⑦。不得不说,在对唐传奇与宋笔记的论说和定位上,偏好辞采的鲁迅确乎扬唐抑宋;但是,要说鲁迅体会不到笔记之价值,亦非实情。不必说周氏杂文中不胜枚举的对笔记的引述、摘录,单是鲁迅杂文文体的创生,其驳杂性与包容性本身就和笔记的特质与神理一脉贯通。
在《城邦暴力团》中,有直接引用笔记处,有伪造仿冒笔记处,亦有不少段落篇章颇得笔记之神采。试举一例,第9节“食亨一脉”是对“素烧黄雀”这道菜来龙去脉的介绍,牵引出无数周折。八侠之一曹仁父之逸闻、郑成功之史事参厕其间,《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与魏谊正的《食德与画品》一实一虚互为补充:笔记的况味满溢其中。第19节“铁头昆仑”中,还是这位大腹便便、痴痴呆呆的魏三爷,将魏氏绝学《无量寿功》赠与萍水相逢的欧阳秋,此类奇人奇事,依稀回荡着志人小说旷达飘逸的袅袅余音。
考察《城邦暴力团》的写作与成书,其在《中国时报》的连载常被论及,屡遭忽视的却是张大春同时还在电台“说”《城邦暴力团》。无疑,后者对小说文体的形塑和影响更为关键。“好故事、会说书”的张大春曾在电台广播说书,涉及的书目包括《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七侠五义》《东周列国志》等,也有自家的小说《城邦暴力团》。最初时,《城邦暴力团》评书听众的反响甚至远超通过文字书籍阅读的读者和学人⑧。批评家们的一度失语,泄露出对评书的陌生与隔膜。可以说,在作为表演艺术的评书上,张大春想必不只是玩票性质,而多有切身的感知。由是,其品评与承接作为小说传统的评书,也就多了份旁人所无的书场视角。
与成为案头阅读的定本小说相比,柳麻子(柳敬亭)、石玉昆等说书人在瓦舍勾栏中海吹神聊、闲中著色、精神百倍,书场给评书艺人留出了铺张增饰的余裕⑨,说书人给小说带来了充满闲情与野性、离奇与松散的叙述力量及质地。当抽离了这种说书人与听众同时在地在场的语境时,评书文本也就很难见容于当代读者。一定程度上脱胎于说书传统的《城邦暴力团》,却尝试着还原和再生的努力。于是,小说中出现的大量评书声口,也就顺理成章,如“闲话不提”、“闲话休提”、“且先说”、“话不絮烦”、“非得表一表”等。叙事中,不停地宕开摇曳,插说各类人物生平,补说“卷密游丝功”、“猴拳”、“八步螳螂拳”、“保密局”、“一清专案”等奇闻异事,解说魏延、苏轼、章惇、诸葛亮、王安石等典故……凡此种种,无不构成了《城邦暴力团》醒豁的说书姿态。
笔记和评书,看似是文人与说书匠人各自为政的一雅一俗两条小说脉络,二者实存有剪不断理还乱之复杂纠缠。如《太平广记》一度为瓦舍艺人提供营养⑩,笔记与评书同为小说家言,绝非壁垒分明。不唯在长篇小说《城邦暴力团》,张大春于《春灯公子》《战夏阳》《一叶秋》《离魂》等笔记体短篇中,早已开始了对创作原汁原味的笔记、评书的牛刀小试。《城邦暴力团》与《大唐李白》,当是于这条写作轨道上的延续与升华。
二、艾柯/高阳:小说何以造史
对于艾柯{11}的长篇小说《玫瑰之名》《傅科摆》《昨日之岛》,张大春均曾撰文论说,即《谋杀案外有玄机——简评〈玫瑰的名字〉》《理性和知识的狎戏——〈傅科摆〉如何重塑历史》《不登岸便不登岸——航向小说洪荒世界的〈昨日之岛〉》;《小说稗类》中的《将信将疑以创世——一则小说的索引图》和《预知毁灭纪事——一则小说的启示录》也涉及对艾柯小说的剖析:细腻的体悟与深入的读解可见张氏与艾柯的心有戚戚,《城邦暴力团》亦潜藏着与艾柯小说诗学层面的遥相呼应。
如张大春文章标题所言“谋杀案外有玄机”,艾柯的作品常常披着侦探小说的外衣。《玫瑰的名字》正是围绕着一起修道院谋杀案展开,《傅科摆》中卡索邦、贝尔勃、迪奥塔莱维三人有关圣殿骑士{12}“计划”的“发明”、“拼接”与“破译”,也充满着浓厚的侦探味儿。《城邦暴力团》里万砚方被杀、欧阳昆仑之死等,既关涉着全书的暴力主题,又是引人入胜的探案要素。小说中的“我”、万德福以及“竹林七闲”中的余下六老对万砚方所遗留的“菩萨蛮”的追索求解,也近似于卡索邦们对圣殿骑士“计划”的孜孜以求。在情節发展上,贝尔勃遭到了阿列埃、布拉曼蒂等人的要挟、迫害,后者企图得到本是无中生有的“计划”中的地图。而《城邦暴力团》中的“高阳”、“我”同样是受到企图求得谜底的多方势力的围追堵截。
《傅科摆》中的卡索邦曾将自己比作“知识的侦探”,作为大学生的他完成了关于圣殿骑士受审的两百五十页论文{13}。小说之外,现实中艾柯的博士论文《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观》也被答辩考官评定为“就好像是一部侦探小说”,艾柯甚至由此认为,“所有研究成果都应该以这样的形式‘叙述出来”、“每一本科学著作都应该带上几分侦探故事的色彩”{14}。巧合的是,张大春也将自身的求学经历化入小说中,其中的“张大春”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在一间破宅子躲避期间,于梳妆台上完成了毕业论文《西汉文学环境》。囿于逃亡在外而无可资参考的文献资料,“我”于是上瘾一般地“……就瞎编一个人名、捏造一个书名、杜撰一段看起来像是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说出、写出、且恰恰可以充分支持我的论理的语言”{15}。这种撰写方式,且恰恰就是卡索邦、贝尔勃们塑/伪造“计划”的方式,甚或,对书和知识的捏造正是艾柯写作《傅科摆》等小说的惯用伎俩。荀悦《汉纪外编》、刘珍《东观汉书拾遗》是子虚乌有的论文参考文献,而所谓李绶武的《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万砚方的《神医妙画方凤梧》、魏谊正的《食德与画品》等,何尝不是小说家的虚设之书呢!张大春深得其中三昧,方能会心点出,艾柯“他捏造了无数则几可乱真的材料,混杂在‘历史/小说之中,等待以‘考古为乐的读者去拆穿或覆案”{16}。
更深层来看,艾柯以小说化的方式寻绎、拷问知识与理性的极限:卡索邦们征实以构虚,虚拟却又走向破灭,确是触及以至戏拟、嘲弄了福柯关于历史的不连续性、知识考古等诸议题,尽管艾柯拒不承认《傅科摆》与福柯之关联。中世纪神学、哲学等知识的“清单”,经由重新拆卸、筛选与罗列、组合,建构出新的“历史”。贝尔勃在日记中不无恐惧,发明一个“计划”,而如果这“计划”真的是呢?那么,“为什么写小说呢?重写‘历史。然后你就成为‘历史”{17}。对于民间历史、民国历史的另类挖掘及打造,拆掉历史是一纵连续体的迷思{18},正是张大春及其《城邦暴力团》的旨趣所在。
这里还需提及高阳:不仅仅在于高阳与张大春如师如友的君子之交,也不单单因为高阳被张大春写进了《城邦暴力团》,二人在小说观上的趋同与分野,实则为重要关目。高阳在他的历史小说中屡屡纳入野史、逸闻、传说,且多自家的想象发挥{19},张大春称之为“重塑历史的雄辩技术与特质”。与其说高阳有其对历史的“发明”、“演绎”处,毋宁以为高阳是要“重新建筑一套可以和‘正史之经典地位等量齐观的历史论述”{20}。质言之,高阳的历史小说仍然意欲求“真”,自嘲为“野翰林”的高阳其实内心大有跻身正统翰林的渴求;而大头春一贯乐于做“撒谎的信徒”,也就不妨在历史和小说的虚实之间优哉游哉。
被艾柯诓进小说里的读者定会有上当之感,小说中引述的那一本本言之凿凿的书籍,多数不过是艾柯的信手捏造。同样,若对高阳之行迹、高阳与张大春之交游稍有了解,便不难识破《城邦暴力团》中对高阳的虚构,也即再度领略了张氏“大说谎家”的风采。将有考据癖的高阳编织进小说,可谓天衣无缝的巧妙对接。试想,能够从李煦稀松平常的两则奏折里发寻蛛丝马迹,为其“贾珍李煦说”张目{21},在《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还自陈能窥见陈氏此中隐曲者,“舍我其谁”{22}?有此“无中生有”本领的高阳,若面对与万砚方相关联的七本书,能不左右参详、探幽发微!这正是小说中魏谊正等人对高阳的期待:“……你有造史之才,必可为吾等沉冤丧志之辈一探究竟、再著汗青呢!”{23}
张大春将高阳的真实事迹加工改塑,楔入小说情节之中。高阳与张大春二人确有在《联合文学》组织的赴日旅行团中同游日本,高阳也着实在大阪脱团只身独往东京,只是没有关于《肉笔浮世绘》、中日建交等诡谲的经历。文本里的俞平伯、周弃子自然是实有其人,可现实中的他们也不会跟魏三爷、方凤梧等小说人物有何交集。小说中,“高阳”逝世后,留给了“我”七本书和一叠半影印、半手写的文稿。小说第45节“残稿”中,引用了这份高阳遗稿,在第46节“理想的读者”中,“我”又对高阳残稿作了一番拾遗补阙。
显而易见,就像《玫瑰的名字》假托偶然得到的一本书《梅尔克的修士阿德索的手稿》,高阳的遗稿一样出自作者的杜撰。小说中“高阳”的命运犹如贝尔勃,被卷入了一场虚构的解秘活动中不能自拔而耗尽心力,至死也未能解脱。文本内外,张大春对高阳及其历史小说都有着共通的评价,从魏三爷的评语“再著汗青”到张大春的文章《以小说造史——论高阳小说的重塑历史之企图》,无不蕴藏着张大春对高阳其人其书其忧愤{24}的致敬。在引述完高阳残稿的第45、46节之后,第47节“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作为整部小说的终章,以元小说的方式依次叙说六个开了头却未完成的开篇片段,不啻是在错综中对整部小说情节网络以及历史书写的重述、省思与诘问。与此同时,这也症候式地展露出张氏较之高阳在小说虚构上迈出的更远、更坚定的步伐。
三、“我”与“父辈”及眷村:历史的创伤记忆
实际上,《傅科摆》中眼花缭乱的中世纪神学知识和层层推演的圣殿骑士计划,往往冲淡了作为小说底色的现实背景。卡索邦和贝尔勃在七十年代初的相识,正是1968年前后的革命浪潮在欧洲如火如荼之时。二人在狂热的岁月中倒是有些隔岸观火的“多余人”味道,不时调侃着斯大林、马雅可夫斯基等人,间或发表些政治史与酒、胡须与革命的奇谈怪论。而当多年后从巴西再次返回意大利时,人们不再讨论革命,“人们引述‘欲望”,“后革命”的时代让卡索邦无所适从,“不再知道我是谁了”{25}。贝尔勃的日记赤裸裸地暴露了二战给他留下的童年阴影以及造成的无法愈合的心灵痛楚。这些都蕴含着艾柯对战争创伤、革命思潮和历史变迁的观感和认知。
同样,《城邦暴力团》中亦夹杂着此类动人心弦的历史创伤。第40节“风云渡海”,描述“我”的父亲母亲,如何不明所以地获得船票、糊里糊涂地登船赴台。尽管行程中依然还有关于“上元专案”的交代、有欧阳昆仑之惨死,可父母亲一路的惶惑和相濡以沫,不失为大历史变动中被裹胁着的个体浮萍式命运的写照。父辈们的定居台湾,以及“我”、孙小六、孙小五的成长,随即流向了眷村主题。彭师母怀揣着得过且过的心态,一遍一遍地对人说:“反正到了台湾来怎么样都是将就,怎么将就也就怎么都好了”,眷村的拆迁改建也无法在他们如死灰的内心深处激起涟漪,“我们村子里这些老老小小从来也永远不可能因为换了栋房子而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从来也永远不可能拥有另一种生活”{26}。他们既时时强迫自己不去回忆过去的生活,可又只能在对故乡人事的回味重温中感受到生存的实感。
于某个中秋夜热烘烘、闹嚷嚷的同乡宴进行之时,父亲和母亲搭火车北上竹林市另谋出路,“车行途中,家母指了指窗外那一轮黄橙橙的满月,说‘这月亮老跟着咱们呢!家父便哭了起來。”{27}不过是望月思乡的母题,可质朴简短的摹写,有股动人的力量。父亲的月夜痛哭,传递着邈邈乡愁。写到这里的张大春应该也是悲从中来,自然无暇像小说其它各处那般复又引经据典、钩稽史料。大概正是不忍让“背负着一部大历史,在炮声和弹孔的缝隙间存活下来”{28}的父亲在后半生无所事事,张大春在小说中让父亲与李绶武接头,钻研战争史料,助其完成《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垦掘和整理,揭秘隐藏在大历史角落中的另一种真相,想必也是对曾为土地测量员的父亲、对被历史无情虚耗尽残生的父辈们的安慰吧。
除却父辈的书写,《城邦暴力团》还有我和小五、红莲的爱情描绘。与红莲多涉及性爱场景,“我”异常觊觎其美色;同小五则多表现她的单纯善良,“我”也会反省自己的自私无情,“被小五努力翼护着的那个我其实是个因为拙于表达爱而失去爱的能力的人”{29}。不只是主人公丧失爱的能力,实为整部小说就缺乏叙述爱情的能力,就像《傅科摆》中卡索邦和安帕罗、莉娅,贝尔勃和洛伦扎·佩雷格里尼的爱情描写,同样淡乎寡味。
毕竟,爱情主题,并不是《城邦暴力团》《傅科摆》的擅场。
四、“汇入一鼎而烹之”:
知识氛围,或“跑野马”
至此,固然可以抽绎出笔记与评书、艾柯与高阳以及眷村小说等《城邦暴力团》的诗学渊源并分而论之,却也使得文本支离破碎,割裂了小说的有机整体性。易言之,小说家对多重叙事资源的摄取和化用,往往不是表面的加法式拼凑和蹈袭,而更是内生的化合式发酵与衍变。因此,这里尚需紧贴文本,在追蹑小说文体的动态生成中,体察张大春何以杂取种种“汇入一鼎而烹之”{30},将自家的诗学兴趣熔铸成多音驳杂的小说构型。
在“竹林七闲”一年一度的荷塘之会上,万砚方遭袭被杀,其余六人亦不知所踪。万德福为了找到真相,开始寻访六老;六老此时也故意留下线索,步步引诱万德福接近实情。在叙述万德福的追踪过程时,作者趁机交代了魏谊正、汪动如、钱静农与江南北八侠中曹仁父、吕四娘、周涛之身世关联:是为第8节到第13节的主要内容。第8节末尾,提及魏三爷要请万德福吃一客“素烧黄雀”,第9节“食亨一脉”,起首即是:“这‘素烧黄雀是一道家常菜,可是源远流长……当须自江南八侠曹仁父说起。”{31}接着便缓缓缕述曹仁父之行迹,与万云龙、郑成功之交游,以及后来改为魏氏之故。其嫡传曹秀才的素膳赢得过乾隆所赐“食亨”之号,小说家并将《清朝野史大观》对曹秀才“肚皮宽松”的记述追认作一门内功。这些正是魏谊正在《食德与画品》中所附的魏氏家史脉络。第10节末端,万德福见到了挂在门上的蟾蜍结,作者有言:“这个蟾蜍结也有一个绵远悠长的来历,不得不溯本而言之:否则不能明汪动如之传承。”{32}第11节“天医星来也”却从叶桂与张真人之轶事入笔,渐次涉及吕四娘刺杀雍正受伤后求医于叶桂,此后得到叶桂的传授,吕四娘又有“二汪”、“二王”两路传人。小说家不急不缓地插叙了汪硕民之一则医事,这才引出汪馥以蟾蜍结医治何桂清之事。
可以说,张大春极为老练地在章节收尾处设置了说书人常用的“扣子”,像“素烧黄雀”、“蟾蜍结”,以及第11节末的“回音壁机关”。在次章节的“解扣”中,张氏或述或引,在主线上不停地岔开支线,蔓延伸展,收放自如。其穿插的逸闻故实,如叶桂借张真人扬名、周涛为了因和尚作画等,都可谓是精巧的笔记段落。与此同时,张大春也不忘说书人的本能,甚或直接援引赞诗、回目。
张大春标举与践行笔记与评书的小说家言,自有其鲜明而尖锐的指向性:
“即使‘我们写小说的所写的小说被视为‘现代中国小说作品、‘当代台湾小说作品支流,究其实而言之:其实绝大多数只是用汉字所凑成的西方小说。论体制,论理念,论类型,论布局,论技术,皆由移植而来。真正的中国小说早已埋骨于说话人的书场和仿说话人而写定的章回以及汗牛充栋的笔记之中。”{33}
对于現代中国小说过于西化的担忧和警惕,在五四现代小说的初创时期,以及在大陆九十年代之后一批先锋小说家纷纷转型的后先锋时期,诸多有识之士争论不休。当年的先锋文学闯将如格非、李陀,现今一再表示要向传统小说回归。在台湾,近年来如蒋晓云的“民国素人志”系列尝试“回到小说的从前”{34}的写作实践,也是对小说过度西化的纠偏。以西方文论和西方小说的审美标准而论,高阳的小说或许只能承受着结构不够完整、人物形象不够鲜活的讥评。张大春对高阳小说的声援、体认与定位,恰恰在于抛开了惯常的西方式审美准则,直指高阳“‘挟泥沙、‘跑野马、‘走岔路、‘捲枝蔓以缔造的复杂叙述结构”{35}对现代小说的贡献。
张大春的诗学探索并未到此为止。现代小说既亟需摆脱西方审美惯性的宰制,同样要提防在“现代性”的名义下对传统小说的曲解和干涉。这里潜藏着张氏对“传统叙事资源的现代性转化”这一思路的不满与质询。就像笔记不单单只是小说家的取材仓库,当把传统小说视为低一级的“资源”,将小说家的写作视为高一等“创作”,此中居高临下的心态必然压抑着传统小说与生俱来的活力与性情。诸如笔记和评书的传统小说本身有其自主性和自为性,张大春的诗学践行,就是要引动和释放传统小说的蓬勃活力与能量。
《城邦暴力团》以小说家言融接传统,在知识氛围中捭阖出入。艾柯小说中繁复稠密的知识堆积,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式的书写。作为符号学家的艾柯“利用读者对‘推理情节、‘历史常识、‘英雄传奇、‘宗教启示等文本的种种成见”架设出相互质疑的符号{36},而张大春采用“跑野马”、“挟泥沙”等更为本土化的批评语汇指称自家小说,呈现出与艾柯的文本所不同的知识氛围。
一方面,这种“跑野马”,在于张氏还原笔记和评书本相时天然携带的叙述特征。说书人本就擅长在离题与合题之间拿捏收放,笔记本有述学、纪事、记人、摹写等驳杂功能。以文学史家历来的“定见”来看,作为台湾新世代作家群体中一员骁将的张大春,其叙事手法与方式的诡异和多变,自然是得益于小说家在八九十年代台湾文坛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思潮里的浸泡。张大春与蔡源煌谈论八十年代台湾小说的发展,既是在陈述黄凡小说的技巧与游戏性质,又像是二人夫子自道的理论宣言{37}。诚如鲁迅的“豆荚”与“豆”之喻,倘若不把张氏视为新世代作家豆荚中规整划一、大小无二的一颗豆子之一,那么,《城邦暴力团》中穿插藏闪着的各类预叙、插叙、倒叙等叙事手法,却与西方叙事学貌合神离,其精髓毋宁仍在笔记和评书的延长线内。
另一方面,从小说中呈现的知识类型来看,文史典故、武侠与会党、党政与战争,是为几项大宗。各类知识的引入,泰半是小说家自觉的追求,一定程度上也是张氏个人嗜好所在。张大春曾每天抄写、整理掌故,乐此不疲。与友人谈天吃饭时,也以对各类知识的互相竞猜为乐,这也让在场的阿城大为吃惊{38}。兹举音韵为例。对旧体诗创作兴味盎然且功力不俗的张大春在音韵学上也是驾轻就熟。第10节“杀出阵”中,万德福吼出了高手叫阵的一句话,张大春怎会轻易放过这一大显身手的机会,遂从用韵角度做了一番专业解说:“这番话听似没说完,可他每一断句,几乎都落在上平声八齐韵、上声五尾韵、去声六御韵和八霁韵”,“要之断句之字,尚齐口撮唇,如此则吐纳收束,不虞气息散逸。若上平声四支五微、六鱼、八齐,上声四纸、五尾、六语、八齐,去声五未、六御、八霁,与夫入声十二锡、十三职、十四缉各部之字,可以存元固本,不止于竭力嘶声之际,寝失真气”{39}。再如小说开篇第2节“竹林七闲”的谈话,充塞了满满当当的机锋、典故与隐喻,夹杂着《晋书》、庄子、《广陵散》、杜诗、金圣叹等知识“清单”。
在如是“汇入一鼎而烹之”的知识氛围下,《城邦暴力团》的历史书写,也是借知识进行虚构。江南北八侠本是稗说野史,其事迹在《清朝野史大观》中不过寥寥数语,而民间戏曲、评书、小说对江南北八侠却是不断添枝加叶。张氏的再度演绎,将八侠与魏谊正、钱静农、李绶武、施品才、康用才等人分别勾连,完成的是对野史的再度“野”化。为了使其信而有征,说起周涛、钱济之事,张氏便引钱静农《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建筑门”一卷为据,又言《旧庵笔记》《广天工开物杂钞》《奥略楼清话》中亦曾述及,貌似班班可考,实则这些不过又是小说家的虚构之书。
而把魏、钱、李、孙等人镶嵌进党事、国事、战事的大历史纠葛中,则是对正史的又一次“虚”化,“虚”写中掺杂着历史记忆介入的“实”感。小说中精确地使用了民国纪年,淞沪会战、蒋介石逝世等日期自然无法变动,可其“背面敷粉”,敷衍嵌入的如新生戏院失火、八博士被杀等新闻事件背后的隐秘,乃至电影的道具和上映都是帮会接头的暗语。第7节“老大哥的道具”提及了李行《婉君表妹》、宋存寿《破晓时分》、白景瑞《寂寞的十七岁》等名导佳作,以及唐宝云、江明等影星。在帮的张翰卿向“我”历数了手镯、印石、簪子等电影中的道具如何牵连到漕帮走私手枪的交易,道出了实存影史背面不为人知的隐秘。连李翰祥导演出走台湾的原因,也在小说中被魏谊正视作因在“周洪庆事件”中涉入太深,李翰祥才不得不离台{40}。又如蒋介石的日记也能被读解出明语与暗语的交织。是类虚实界限之破除,不过使历史的面貌更加混沌而又扑朔迷离。《傅科摆》结尾处的卡索邦仓皇逃窜,《城邦暴力团》中的“张大春”也对无法判断和把握的世界心生惶惑。历史的晦暗不明与巨大的反噬能力,让主人公们跌入了哀矜绝望的深渊:历史与小说,究竟何者是对方的倒错?{41}
毋庸置疑,张大春对民国史、抗战史、外交史知识的方方面面了然于胸,才能在虚实之间措置裕如。饶有意味的还有,《城邦暴力团》与《傅科摆》不约而同地涉及电脑和其数字化处理给知识的建构与解构、历史记忆的搭建与拆卸带来的便利和迷思。贝尔勃把他的电脑亲昵地称为阿布拉菲亚,多次利用它完成“计划”版图的拼盘;父亲的电脑也让从没想过去碰去用的“我”目瞪口呆{42}。尽管后者中的电脑并未像《傅科摆》里那样大显身手,但是,站在当下“后人类”的大数据和信息化时代回望,“技术已经介入其中,并且技术与产物的身份交织缠绕,以至于不再可能将它与完整意义上的人类主体分离开来”{43},两位小说家在八九十年代即敏感地意识到电脑对知识结构和历史叙述带来的变革和冲击,不得不使人慨叹小说作者的预言家本色。
概言之,《城邦暴力团》的文体脱胎于笔记与评书的小说叙述传统,并掺杂以眷村主题的历史记忆等,在浓密的知识氛围中游走于虚实两端。小说中无穷无尽的“跑野马”和“挟泥沙”都不免有逞才炫学和掉书袋之嫌疑。在试图靠拢和复原评书、笔记的本相时,张氏往往也接过了二者的先天缺陷,如评书中的套语赘辞。现代读者或许无法承受太“闲”、太“野”、“渐行渐远渐无穷”的“走马灯”{44},张大春的心存疑虑并非杞人忧天。因此,《城邦暴力团》多音驳杂的小说构型,既极大地丰富和激发了现代小说的文体潜能,也呈现出过于庞杂、生而未化的实验性质。然而,是类“未完成”性,正是张大春小说创作的诗学旨归所在:“把小说的定义,在那个知识疆域的边界上,踏出去一步”{45}。《城邦暴力团》如此,《大唐李白》亦如是。当然,有关张氏《大唐李白》的小说诗学及其新变,将待另文专述。
① 《城邦暴力团》时报出版社版的封底所印宣传语是:“现代新武侠 张大春江湖回忆录”、“继高阳之后,再掀台湾小说书写新境。集结现代与武侠、现实与传奇、暴力与爱情,以繁复迷离的线索,构成一部空前绝后的奇异武林史,是张大春近年来最具爆炸性、纯中国魔幻写实代表力作。”(张大春:《城邦暴力团》,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腰封上则是:“当代最优秀小说家 张大春扛鼎之作”、“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中国地下社会总史 世纪暗战江湖变迁”(张大春:《城邦暴力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② 张大春:《卡夫卡来不及找到——一则小说的材料库》,《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232页。
③ 王安忆:《我看短篇小说——〈心疼初恋:刘庆邦小说选〉序》,《故事和讲故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④ 汪曾祺:《早茶笔记(三则)》,《汪曾祺全集4》(散文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⑤{33} 张大春:《随手出神品——一则小说的笔记簿》,《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第122页。
⑥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传奇文》,《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2005年版,第107页。
⑦ 张大春:《猎得鲲鹏细写真·洪迈与异端知识的核心价值》,《战夏阳》,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301、302页。
⑧ 张大春在访谈中曾回忆当时的创作和说书情境:“我当时在电台‘说书,说的就是《城邦暴力团》,反而听众的反馈比较多。当时这部书在市场上卖得还不错,可是台湾报纸上的书评版面没多少反应,书评家几乎没有人碰这部书。来自文学同行的声音也很少,我大概能够体会,他们是不知道怎么来评价这部作品。”(张大春、丁杨:《张大春:〈城邦〉之后再无难事》,载2011年1月26日011版《中华读书报》)在《战夏阳》大陆版的自序中,张大春也提及说书一事:“以广播说书,昔年并不罕见,到上世纪末我开始做节目的时候,以台北或台湾为范围而言,却可以说得上是独树一帜了。节目初开,我说《城邦暴力团》,终篇之后又持续说了十几年……”(张大春:《无关的有关〈战夏阳〉简体版序》,《战夏阳》,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⑨ 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 宋元部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⑩ 康来新:《发迹变泰——宋人小說学论稿》,大安出版社1996年版。
{11} 台湾学界对艾柯的译介与研究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大陆,在研究规模和水平上也不遑多让。
{12} 艾柯小说中的人名、物名等专有名词在两岸的不同译本中有细微的差异,如大陆译本中的卡索邦、圣殿骑士,台湾译本中则为卡素朋、圣堂武士。本文所引《傅科摆》均据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13}{17}{25} [意]翁贝托·埃科:《傅科摆》,郭世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263页,第607、609页,第260、259页。
{14} [意]安贝托·艾柯:《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艾柯现代文学演讲集》,李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15}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叁),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93页。
{16} 张大春:《理性和知识的狎戏——〈傅科摆〉如何重塑历史》,《文学不安 张大春的小说意见》,联合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页。
{18} 张大春:《雍正的第一滴血·自序》,《雍正的第一滴血》,宝文堂书店1988年版,第2页。
{19} 蔡诗萍:《“古为今用”的现实反讽——高阳笔下“红顶商人”的政治处境》,《高阳小说研究》,联合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20}{35} 张大春:《以小说造史——论高阳小说的重塑历史之企图》,《文学不安 张大春的小说意见》,联合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1、90页,第84页。
{21} 康來新:《新世界的旧传统——高阳红学初探》,《高阳小说研究》,联合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2} 高阳:《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高阳说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23}{27}{29}{30}{40}{42}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肆),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08页,第181页,第55页,第366页,第284页,第76页。
{24} 张大春:《摇落深知宋玉悲——悼高阳兼及其人其书其幽愤》,《文学不安 张大春的小说意见》,联合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6}{31}{32}{39}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贰),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97、104页,第6页,第30页,第23页。
{28} 张大春:《聆听父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34} 张怡微指出,21世纪后的本土台湾写作者将“性别议题、疾病与隐喻、身体与国族、离散议题”等“哄抬至一个匪夷所思的高度”,“台湾的中文写作环境,已理论先行,以现代性、后现代的写作技法淹没说故事的小说创作传统”。时隔三十年,于2010年重返文坛的蒋晓云洗脱了翻译腔,还原了“民国话本小说的语气”(张怡微:《却看小说的从前——蒋晓云“民国素人志”系列小说》,《上海文化》2013年第5期)。
{36} 张大春:《谋杀案外有玄机——简评〈玫瑰的名字〉》,《张大春的文学意见》,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26、27页。
{37} 张大春:《80年代台湾小说的发展——蔡源煌与张大春对谈》,《国文天地》4卷5期,1998年10月。
{38} 阿城在为张大春大陆版《认得几个字》所作的序言中,第一段即着意突出描绘张氏对文史掌故的酷嗜:“1992年我在台北结识张大春,他总是突然问带他来的朋友,例如:民国某某年国军政战部某某主任之前的主任是谁?快说!或王安石北宋熙平某年有某诗,末一句是什么……我这个做客人的,早已惊得魂飞魄散。”(阿城:《序 小学的体温》,《认得几个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41} 张大春:《无关的有关〈战夏阳〉简体版序》,《战夏阳》,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
{43}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44} 张大春:《叙述的闲情与野性——一则小说的走马灯》,《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
{45} 张大春:《附录 小说家不穿制服——张大春对谈吴明益》,《大唐李白·少年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6页。
Comments of a Novelist, Atmosphere of Knowledge and Historical Memory---On the Poetic Origins and Narrative Generation of The Violent City Gang by Chang Ta-Chun
Cao Lepeng
Abstract: The Violent City Gang, by Chang Ta-Chun, contains multiple poetic resources. By combining a novelists comments in a narrative tradition of pen-notes and book comments, it presents a challenge to the existing paradigm and aesthetic habits of modern fiction. In the atmosphere of knowledge, the novel debates with and questions history, authenticity and fictionalization, forming also a dialogu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iction of Eco and Kao Yang. In the text, the writing about the fathers generation, the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and historys traumatic memory continues with the flow of the Dependents Village Fiction although there are connections and rifts between its narrative practice and the postmodern literary trends in Taiwan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a result, The Violent City Gang, through this amalgamation, has given birth to a fictional structure of cacophany, greatly initiating and releasing the genre potential of modern fiction.
Keywords: Chang Ta-Chun, poetics of fiction, fictional genre, atmosphere of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