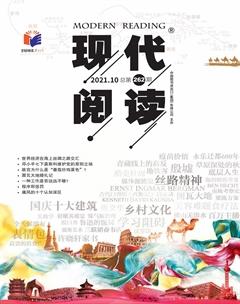世界经济在海上丝绸之路交汇
2021-10-21冯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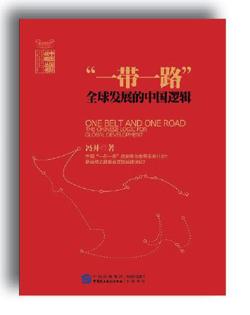
中国是陆权贸易国家,也是历史悠久的海权贸易国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样源远流长。中国的海权来之于和平贸易和2000年以上的航海历史,蓝色经济从来都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的陆权贸易是多元包容的贸易,惠及欧亚文明。中国的海权贸易同样是多元包容的贸易。在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带着中国与世界在经济相互融入中走向新的境界,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南北美洲在跨大区域经济合作中越走越近,真正使地球成为世界各国居民的地球村。
海洋对中国人来讲并不陌生。在宗教交流史上,唐玄奘是陆路去陆路回,隋代的法显是陆路去海路回,唐代还有个义净大师,是从广州出发,海路去海路回。一般认为,中国的大规模航海是从明成祖时的郑和开始。但海上丝路的开辟远早于这个时期。秦代的徐福出海虽然附丽于寻求长生之药且无可考其下落,但带来的历史信息是,中国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在秦代已经出现在东北亚地区。翻开《史记》,更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果、布之凑”的记载。据《汉书·地理志》载,公元前111年至公元前87年,汉武帝派遣专属于“黄门”近侍的“译者”,招聘“应募者”組成官方船队,带着“黄金杂缯”,从当时广东的徐闻、合浦三汊港和日南(在今越南中部)出海,沿着中南半岛,到泰国、马来西亚、缅甸,抵“黄支国”,最后抵达“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全程有5000海里(9260千米)。这是亚洲内陆与海洋的经济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之始。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已是繁华热闹的大港,《晋书》中有“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的叙述,《南齐书》有“南齐珍贵,莫此为先”的赞语,《新唐书·地理志》更有对当时最长的1.4万公里的航线——广州通海夷道的详尽记录。唐代的海船从广州的南海神庙启程,经南海过新加坡海峡,横跨印度洋,直至波斯湾。每年经由这条航线到达广州的阿拉伯商船就有四千多艘。到了宋、元、明时期,广州依然是中国陶瓷产品与丝绸的最大吞吐港。在清代,“一口通商”和“天子南库”的垄断地位更使广州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国际贸易中心。
然而,中国海上丝路的历史起航点不只是广州,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及靠海地区,至少还有8个海上丝路古代贸易中心。宁波(古明州)兼得江河湖海之利,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使之获得广阔的内陆腹地,“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这是上海未开埠前的中国东亚海上丝路的起始港。福州地处闽江下游,扼海峡而成为海上丝路的必经之地,在明清两代都被确定为内陆与琉球商品往来的最近港口和唯一合法口岸。公元14世纪,郑和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贸易扩展达到顶峰,福州是其重要驻舶地。清康熙在1684年设立的第一个海关是福州的“闽海关”,至今那里还有关于海上丝路的遗迹,如闽安歧东古渡、淮安窑古渡、怀安接官道等。通过福州,中国文化继续辐射到日本与东南亚。
明代的漳州也是国际大港,从月港(位于今福建漳州)出发的商船东达日本,南通菲律宾、马六甲,与欧洲人开辟的马尼拉盖伦贸易航线连接,构成了当时比较完整的环球航路,漳州窑出口的陶瓷产品在东南亚和欧洲时有发现,证明这条海上丝路的存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世界第一大港“刺桐港”泉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宋元时期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刺桐港”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与航海技术,是全方位国际贸易港口,北连朝鲜半岛、日本,南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西抵印度洋、非洲东岸,在马可·波罗的眼里,“货物堆积如山”,“商店数目比世界上任何城市的商店都多”,“可以找到来自世界最遥远地方的商品”。北海与合浦则是从汉代就开始指定的官方贸易港口。
海上丝路的经济核心区不仅是沿海海港城市,还有内陆靠海的大工商城市给予的物流支撑。如隋唐时代的扬州,因运河漕运而兴,成为南北物资的集散地,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在此交汇,成为“富甲天下”的大型国际贸易中心。唐代的扬州是双重城格局,即蜀冈上的“衙城”与蜀冈下运河两岸的“罗城”形成行政与商业分开的城市格局,犹如今天老行政区与开发区。扬州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陶瓷集散地,来自全国不同窑口的陶瓷产品在扬州集散,转运他地或直销海外。1996年,在印尼勿里洞岛附近发现阿拉伯古代“黑石号”沉船,打捞出6万件中国瓷器,均来自9世纪中国各瓷器窑口。专家们普遍认为,这艘沉船从扬州解缆出发,目的地是波斯湾的古代东洋贸易港口席拉夫。扬州在阿拉伯古语里的称呼是“坎茨”。
在中国的六朝时期,南京即古建康也成为海陆丝路和从东海走向东北亚国家、从南海走向西方的贸易中枢。远自中国三国时代的东吴开始,中国东南部造船业和航海业迅速发展,航线北通辽东与朝鲜半岛,南到中国台湾与南海诸国。及至明代,南京不仅是郑和下西洋的策源地、起点与终点,也是郑和航海事业的大本营和人生归属之地。永乐皇帝为了表彰他的功勋,在南京修建了“天妃宫”、净海寺,至今留有当时的官办造船厂龙江宝船厂遗迹。
扬州和南京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中心地位,不仅说明丝绸之路的陆路与海路,本来就是一个多方位开放的内部与外部的循环圈,或者说是一种钳形贸易经济循环体系,同时也给人们以启示,即海上丝路最大的硬件设施是海港,但真正支撑其运转的是广阔的经济腹地与高效的物流系统。21世纪海上丝路是海港城市要做的大文章,但物流区位和流通的便捷形成的资源集聚效应,同样也是篇大文章。
回顾历史,郑和航海是中国古代单次规模最大的贸易活动,尽管有人试图给它披上王朝权力斗争的神秘面纱,但如果那位失势的年轻皇帝真的跑到了红海之角,大概也不太值得人们同情,用郑和庞大的船队去对付一个形只影单的流亡者,从哪方面看都不合逻辑。某些外国论者以为可以用来做文章,是希望说明郑和不是在贸易,是特别行动,甚至连郑和打海盗也被说成是战争行为,那么颇为人尊重的麦哲伦在菲律宾杀了土人又被土人杀死,这又算什么?有人还企图论证马可·波罗在吹牛,如果论证者也能穿越到600年前,不知他是否也能吹出一条真实存在的贸易路线。郑和航海最远到达东非和红海海角,已经临近地中海与欧洲。他为什么不能到达地中海与欧洲呢?不是因为航海技术,更多的是因为地理因素,那时并没有出现苏伊士运河,当然也不可能走向地中海,否则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现在回看历史,不是郑和达不到地中海,而是因为他本身是中国的回族,有阿拉伯人长居中国的后裔的基因,他是循着中阿贸易的路线,也即厄里特利亚贸易的路线航行。他不仅去过霍尔木兹,还去过时称“阿单”的亚丁,甚至去过伊斯兰的圣地“天方”,也即麦加,对当时中东的形势不可能一点也不了解。14世纪中叶正是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为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相对衰落期,也是应付十字军东征的艰难时期,亚丁湾港口与贸易处于收缩期。如果他的航海再早100年,也就很难说是什么样子了。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厄里特利亚贸易的商品东集散地是广州,西集散地是红海通道,即经由西奈半岛走向的世界性商港亚历山大港。就海上通道来讲,我们只能比较他们的客观成就和他们能够达到的高度。客观地去看,东方和西方都一直在寻求相互接触相互贸易的路径,这是我们对在郑和之后发生了哥伦布航海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历史事件认同的理由。他同后来的达·伽马以及麦哲伦,同样都是开启了由西方主导的航海贸易序幕的历史人物。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直接动机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帝国对东方财富的追求,要寻找印度、寻找中国,这在后来的探险家们一路命名中留下的地名与国名里得到印证,如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等等。但我们还是要把他们并列为与郑和齐名的航海家。他们的探险活动开阔了人们的陆地视野和海洋视野,并直接导致了跨洋经济贸易,尽管这条路在哥伦布之后遍布杀戮与血腥,并且用他们在新大陆掠夺的白银换取丝绸和瓷器,以血的代价开启了跨洋贸易。这种几乎遍及世界的跨洋贸易,伴随着资本和技术资源的扩散,既为人类社会工业化打开了历史的大门,也为后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开辟了曲折演化的天地。环球贸易使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分布在沿海,最活跃的经济活动集中在沿海,形成了沿海与内地发展不均衡的格局,也形成了遍布全球的近代与现代的经济机体的经络与血脉。诚然,在哥伦布之前,走向资本主义的欧洲也曾试图打开他们朦胧意识中的陆上丝绸之路——那时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还没有出现,没有可能定义丝绸之路,即便有谁定义了,但多种经济力量与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最终打不开陆上“丝路”的大门。陆上有阻隔就转向海上,大航海贸易发生以后,陆上丝路渐次凋蔽,海上贸易也就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动脉和大通道。通过这些动脉与通道,东半球与西半球、北半球与南半球的贸易联系,在不平等向平等、局部向全方位发展的经济贸易走向里延伸,走向了今天。
历史上,海上丝路也是一种多元网状结构,近代具有持久影响的还是广州。雷州半岛的徐闻与北海市的合浦开始的两广海上贸易一直没有中断,就丝绸和生丝而言,一直到近代的1929年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中国的生丝业出口才受到严重打击而开始衰落。广东是中国四大蚕茧产区之一,历史上的“广东锦”以精细著名,甚至有“粤纱,金陵苏杭皆不及”和“广纱甲天下,缎次之”的口碑。据记载,在清光緒年间,广东年生丝出口4万担,约占全国出口量的40%,这一时期,桑市、蚕纸市、丝市和丝绸市产业细分,仅绸缎的年销量就达150万匹左右。20世纪30年代,中心产区的顺德织机近万台,历史上顺德桑田面积最大时达120万亩,全县90%的人口从事桑蚕生产。从丝绸生产与贸易可以看出,丝路贸易其实一直没有中断,主要的问题是贸易主导权与平等贸易权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访问印尼,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略构想;2014年访问了南亚三国,是对海上丝路建设的又一次有力的推动。郑和航海以来六百多年后的中国,终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大规模地开启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下的新的航海时代,这是实现海上“中国梦”的新的开端。2004年7月11日,中国设立航海日,“兴海强国”是主旋律。唤醒全民航海意识、海洋意识和海洋国土意识,是推动世界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国人实现强国梦必有的精神与意识。航海日的设立,至今已有十多个年头,实现从海洋大国到海洋强国的转变,不仅需要“海陆统筹、综合开发”,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度重视海洋生态保护,更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与世界各国相互贸易、投资与经济合作,在航海文化建设中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如果说,一些人对“亚洲的世纪”和经济全球化的命题看得还不甚分明,甚至是在时而看好时而看衰的同时心理游移,不妨把视线更多地投向贸易合作的全景图上。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亚洲和世界的机会,对于任何希望发展的国家来讲,都需要珍惜,也都会去珍惜。
(摘自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 作者:冯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