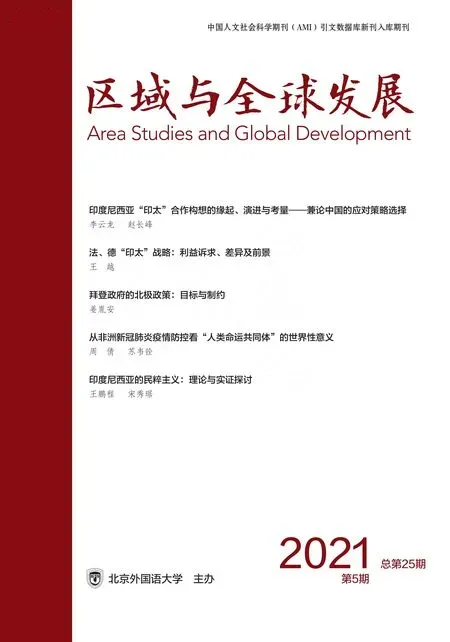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经济集聚机制比较*
2021-10-20谢剑锋
谢剑锋
内容提要: 本文在空间经济学的视角下,区分与比较不同空间尺度上的经济集聚动因、形式与效应,并对相关政策及影响进行评述。在城市尺度上,分享、匹配与学习等机制会导致集聚,提高了人力资本回报与技能的互补性,这在大城市体现尤为明显;在国家及区域尺度上,由前、后向关联等机制产生的集聚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层面的集聚与人均意义上的区域间平衡发展;在全球尺度上,集聚模式的类型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比较优势,并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转换。
一、引言
经济活动在不同的国家、区域、城市的分布与增长差异很大,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均呈现出不均匀的人口与财富分布特质。虽然经济聚集现象非常普遍,但对这些现象的一般性理论解释仍处于探索阶段。①藤田昌久等:《集聚经济学:城市、产业区位与全球化(第2版)》,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在全球尺度上,人类经济活动和生活水平在各大陆与国家、地区间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从统计上看,北美自由贸易区、东亚与欧盟是经济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近年来,由于通信成本与运输成本大幅下降,全球经济在增长的同时也在空间上更加集聚。2019年,北美自贸区产出占全球产出的27.3%,东亚①东亚在这里是指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国所在的区域。占27.0%,欧盟占21.9%,以上三大经济区域生产总值合计占比为76.2%,与1980年三大区域所占的70%相比又有提高。在国家或区域尺度上,其差异同样非常显著,少数省份或大城市拥有较大的GDP总量。例如,广东省的面积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95%,而2019年的GDP占比达到10.9%;长三角地区的面积只占3.7%,而GDP占比达到23.6%。一些大城市也拥有远大于土地面积占比的GDP份额。例如,北京地区仅占国土面积的0.17%,却拥有全国总人口的1.6%,GDP的3.4%。国外的情况也类似。2019年,纽约GDP达到1.03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5%,而其城市建成区面积却不到美国国土的万分之一。经济活动在区域层面的分布也是极不均匀的。例如,作为长三角区域的核心城市,上海只占该区域面积的1.8%,而GDP的比重达到15.6%。在城市尺度上,经济分布也不均匀,经济活动的构成与规模也极其多样化。例如,北京和纽约等超大城市容纳了很多并无直接关联的产业,呈现高度多样化。而某些城市会专业经营某几个产业,呈现出更单一的集聚形态,如技术或信息相互关联的企业组成产业区(如我国中关村或德国鲁尔工业区),以及企业城(如长春一汽汽车城)等。相对而言,它们更加地方化与专业化。深入到城市内部结构中,我们可以发现诸如商业区以及出售相似产品的店铺彼此邻近等更小尺度的集聚现象。
虽然集聚现象出现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但不同空间尺度的各类集聚主体在规模及性质上是迥然不同的,集聚赖以形成的各种向心力的特性也不同,因此,不应试图使用同一模型去解释各种空间尺度上的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由于经济在地理上的集聚总会导致生活水平空间差异的出现,而这种差异很可能会导致社会问题的出现。因此,它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城市结构特点、国内区域差异与全球经济格局对应着城市、区域及贸易政策的制定背景,因此,从不同的空间尺度或空间单元去划分集聚现象的类型、区别不同层面上经济活动地理集中的经济学机制是合理制定城市、区域及贸易政策的重要前提。基于此,本文将对以上三个空间尺度的集聚机制进行比较与评价。
二、各空间尺度下的经济集聚机制比较
(一)城市尺度的集聚机制
根据“空间不可能定理”,如果空间是均质的,运输存在成本,并且存在偏好,那么就不存在包含运输的竞争均衡。然而,在经济活动不是在完全可分的情况下,产品或人员在不同区域间的运送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个带有竞争机制的均质空间与城市这样的集聚经济体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在进行空间建模时,必须否定“空间不可能定理”的另一个假定——空间是均质的。比如,在传统的城市经济学模型对地租的讨论中,虽假设各区位之间的土地没有物理上的差别,但却会假定事先存在一个城市或中央商务区,从而地租上的差别在于每一区位与土地使用的外延边际相比的比较优势,而这是由该区位距离城市或中央商务区的距离决定的,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空间均质的假定。因此,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城市或中央商务区会存在?或者说,为什么城市这一尺度上的集聚会实现?关于城市的存在原因,一个标准的解释是“马歇尔外部性”,即集聚形成的外部性包括专业化投入品供应的便利性、专业化劳动力的可获得的可能性与面对面交流而产生的新思想。长期以来,相对于对城市外部性度量的进展,关于外部规模报酬递增导致集聚的机制解释却类似于黑箱,缺乏微观基础。然而,自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开拓性地建立了垄断竞争模型①Avinash Dixit and Joseph Stiglitz,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al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 No.7,1977,pp.297-308.后,出现了众多研究外部规模报酬递增导致集聚产生的文献,该类文献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学术流派——分享、匹配与学习机制。
1.分享机制
分享可导致城市层面集聚的机制可以描述为:更大的市场(如一个大都市,由集聚所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密度增加)可以提供更多的中间产品(包括服务类产品)与公共设施,而由更多样的中间产品所导致的最终部门生产力增强会使工资水平上涨,从而吸引更多企业与劳动力,形成集聚的因果循环。埃蒂尔(Ethier,1982)将这一经济学思想的前半部分(更多样化的中间投入品会增加最终部门的生产力)写成了模型。②Wilfred J.Ethie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2, No.2,1982,pp.389-405.竞争性企业的生产函数被设定为:

在此表达式中,ρ为介于0到1的数值,X是企业的产出,qi是第i种投入品的数量,M是城市中所提供的中间产品的数目(以连续体的形式表示)。可以看出,该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是不变的。如果给定所有中间产品价格相同(为),令E为购买中间产品的投入,可得解:。可知,产量X将随着中间产品种类数M的增加而严格递增,且ρ越小,即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程度越低,这一递增效应就越显著。以上述研究为基础,阿卜杜勒-拉赫曼等人(Abdel-Rahman et al,1990)使用了迪克西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型模型,假定每个中间厂商生产一种区别于其他中间厂商的产品(具有垄断性),且其利润为零(具有竞争性),证明了一个拥有更多劳动力的城市会拥有更高的最终部门生产力以及更高昂的均衡工资。①Hesham Abdel-Rahman and Masahisa Fujita, “Product Variety, Marshallian Externalities, and City Sizes,”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vol.30,No.3,1990,pp.165-83.关于城市层面的集聚机制,近年来学界涌现了一些高水平的实证研究。其中,以格莱泽(Glaeser,2009)的研究较有代表性,格莱泽以美国城市的经济集聚为例,提供了包括“分享”在内的集聚机制的一些证据。②Edward L.Glaeser and Joshua D.Gottlieb, “The Wealth of Cities: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Spatial Equilibrium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7,No.6,2009,pp.983-1028.此外,因为分享,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成本被分摊,由此产生的规模效应使大城市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质,因此,相当一部分群体向大城市流动并不是出于对收入的考量③Xing, C.and Zhang J., “The Preference for Large Citie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Rural-Urban Migrants,”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43,No.4,2017,pp.72-90.。也就是说,分享对人口集聚的作用机制并不限于经济层面,但是,相对于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与设施,收入和就业等经济原因仍然是更具决定性的集聚因素。④夏怡然等:《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载《管理世界》,2015年 第10期, 第78—90页;Pierre-Philippe Combes,Miren Lafourcade and Jacques-Francois Thisse,“The Rise and Fall of Spatial Inequalities in France: A Long-run Perspective,” Exploration in Economic History,Vol.48,No.2,2011,pp.43-71.
2.匹配机制
如果要考虑劳动要素的异质性,关于城市形成且得以维持的研究则有另一个路径——在经济活动密度更高的大城市,异质性劳动力与工作岗位之间的匹配性也更高。也就是说,会降低劳动力市场上的双向搜寻成本。赫尔斯利等人(Helsley et al.,1990)最初假设一个单中心城市,城市中央商务区(CBD)中存在M个企业。其中,有代表性的企业i的利润设置为:为企业i劳动力储备边界,N为异质性工人的数量),求一阶条件并将企业数量M与劳动力数量N的关系代入,可得长期均衡工资,其中,s为度量异质性与搜寻摩擦的指数。①Robert W.Helsley and William C.Strange, “Matching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a System of Cities, ”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20,No.3,1990,pp.189-212.从中可知,随着人口数量N的增加与指数s的降低,均衡工资将会增加。显然,一个集聚程度更高的地区会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指标的变化方向要求,使其工资率高于其他地区,使人口的单方向流动(集聚)在城市尺度上发生并维持。我们将“匹配”的微观机理与“分享”相比较可以发现,虽然逻辑起点与微观机理截然不用,但在城市尺度上导致集聚发生的结果却是一致的。蒙塞尼等人(Monseny et al.,2011)通过分析西班牙的新创建的制造业公司的位置选择,量化了“匹配”机制对城市层面集聚形成的作用并做出比较:在城市的尺度上,匹配是最重要集聚机制,在程度上要显著超过知识溢出。②Jordi Jofre Monseny,Raquel Marin-Lopez and Elisabet Viladecans-Marsal, “The Mechanisms of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Effect of Interindustry Relations on the Location of New Firm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70,No.3,2011,pp.61-74.除了匹配确属一种城市尺度的重要集聚机制外,匹配的作用超过知识溢出可以这样解释:第一,蒙塞尼等人的研究对象为制造业公司的集聚,而知识溢出效应更加集中于服务业(服务业被认为更加强调“面对面”交流的作用);第二,该实证结果证明,相对于匹配机制,知识溢出作用的空间范围更加局部化,只存在于城市内部的有限范围,这与理论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就现阶段的研究成果来看,量化各种集聚机制作用大小的实证研究结果仍应该谨慎看待,原因在于:各种集聚机制是共同作用的,难以被单独识别。例如,“知识溢出就很可能是通过员工流动或客户与供应商的业务关系而实现”。③Glenn Ellison, Edward L.Glaeser and William R.Kerr, “What Causes Industry Agglomeration?Evidence from Conglomeration Patter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0,No.11,2010,pp.195-213.这仍然是空间尺度上的问题——与溢出相比,员工流动和上下游企业间的业务往来而产生的知识传播可以发生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比如区域)。
3.学习机制
学习机制是指通过不同的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人员)在空间上的集聚而产生了信息的非市场化交流,从而促进了经济主体收益的提高。学习机制属信息交流外部性的范畴,即经济主体可从其他主体获得有用信息而不必支付,当然也无法因自身外溢的信息而获取经济回报,这与上文提到的通过员工流动和企业间业务往来的知识传播截然不同。由于是无意识的溢出,所以只有在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带上足够密集、主体间的空间距离足够近才能够更充分发挥作用。即使在通讯与交通成本急剧降低的当代,由城市的集聚所产生的面对面交流仍然是完成复杂沟通的高效方式。①Edward L.Glaeser, Triumph of the City, London, Macmillan, 2011, pp.65-66.
学习机制的重要成果可分为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理论研究集中于向他人学习如何促成企业和员工集聚。贝克曼(Beckmann,1976)最早构建了基于权衡交通成本与居住面积的经济模型:假定个体的总效用决定于该个体与其他人的平均距离和可以拥有的土地数量(平均距离越近,接受溢出信息的成本越低,但能够获得的土地却更少),在这样的偏好下,效用最大化的空间均衡是对称、单峰的人口分布,从而意味着城市中心的出现。②Martin J.Beckmann, “Spatial Equilibrium in the Dispersed City,” Mathematical Land Use Theory.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1976, pp.17-25.该模型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地租分布曲线也以中心对称并呈倒“U”型,这是伴随城市人口密度分布曲线而出现的结果。伯鲁霍夫和霍克曼(Borukhov and Hochman,1977)对企业间互动的结果做了研究,将办公用地租金与企业间互动成本(与距离成正比)引入利润模型,其中每个企业承担的互动成本与企业间距离成正比,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是会形成类似中央商务区的空间结构。③Eliahu Borukhov and Oded Hochman, “Optimum and Market Equilibrium in a Model of a City without a Predetermined Center,”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Vol.9,No.8,1977, pp.49-56.以上文献研究了个人及企业间的空间集聚,藤田昌久(Fujita,1982)则进一步探讨了企业和雇员在空间上的相互依赖,通过将每个企业相互靠近从而以较低成本获取信息的欲望作为向心力(集聚力),将由此造成的集聚中心地区的土地租金及工资上涨作为抑制集聚的力量,建立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了城市中心出现的必然性。④Masahisa Fujita and Hideaki Ogawa, “Multiple Equilibria and Structural Transition of Non-monocentric Urban Configuration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12,No.1,1982, pp.61-96.在该模型中,企业支付的工资和土地租金是由模型内生决定的(随企业的区位决策而变化),相较以往模型属于重要创新。此外,相比上述没有特殊界定关系的个体之间,同行业但分属不同企业的员工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于同事之间,不同企业间的员工相互交流更加依赖近距离的面对面方式,萨克森尼(Saxenian,1994)以硅谷的例子来强调这一因素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方面的作用。①Annalee Saxenian,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pp.136-146..理论上,学习机制的作用已无异议,而且由于个体只考虑到自身作为“信息接收者”的收益,而会忽略其作为“信息输出者”一面。②个体忽略其作为“信息输出者”的原因是在于其无法内部化这种信息输出,即由于知识溢出的外部性属性而无法获得相应回报。因此,从知识溢出的视角看,均衡的人口密度要低于最优的人口密度,这与社会网络经济学的相关研究结论是一致的。③Matthew O.Jackson,Social and Economic Network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p.152-158.此后,一些理论研究聚焦于空间距离上的接近对于经济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形成与加强的重要影响,研究关注到经济主体在社会网络中互动的方式与距离的关系。④Yannis M.Ioannides, From Neighborhoods to Nations: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Interaction,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57-98.这一部分文献也认为,空间上的接近很大程度上仍属“黑箱”状态,其中存在尚未发现或证实的微观机制。
实证研究集中于对学习这种外部性机制的测度上,其测度方法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概念紧密相连,其含义是知识水平的提高除了会提升个人收入外,还会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知识的外溢,使其他人收益提高,即产生正面的社会回报。有关美国的研究证实,在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城市(多为大城市),地租和工资收入水平也会更高。⑤James E.Rauch,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34,No.12, 1993, p.380.莫雷蒂(Moretti,2004)证实,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所在地的劳动力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呈正相关,并且城市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每增加1%,平均工资会提高6%—12%。⑥Enrico Moretti, “Workers Education Spillovers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Plant-Level Production Func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4,No.3,2004,pp.656-690.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人力资本存在正外部性的假设,刘(Liu,2007)使用1988年和1995年的数据,控制与个人收入水平相关的其他变量发现,城市平均学历增加一年,个人收入增加近6%。⑦Z Liu, “The External Returns to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61,No.3, 2007,pp.542-564.李晓瑛(2010)等对我国城镇的受教育水平与工资水平的动态关系的研究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增加1%,工资水平就会提升约1%。①李晓瑛等:《中国城镇地区高等教育外部回报率估算》,载《世界经济文汇》,2010年第1期,第76—91页。格莱泽等人(Glaeser et al.,2009)使用工具变量法,在有效解决了内生性后,采用2007年chips数据发现,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居民收入水平会提高约20%。②Edward L.Glaeser and Joshua D.Gottlieb, “The Wealth of Cities: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Spatial Equilibrium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7,No.6, 2009,pp.983-1028.以上研究说明,在各个阶段,中国城市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均存在,产生的外溢程度不断提高,而这与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及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有重要关联,③陆铭:《城市、区域与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和未来》,载《经济学(季刊)》,2017第第4期,1500—1532页。即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促进了知识溢出,强化了人力资本外部性。由于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且服务业更加依赖人们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所以学习机制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城市层面的集聚机制。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会通过分享、匹配和学习等机制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吸引该部分人群向城市集聚,同时提高了其时间的机会成本,从而高技能人群会将更多的简单工作外包给相对低技能的劳动者,进而衍生出更多工作岗位,尤其是消费型服务业岗位。
(二)区域(国家)尺度上的经济集聚机制
与城市尺度上的集聚不同,在更大的区域或国家尺度④本部分将国家与区域规定为同一空间尺度,原因在于:像中国这样的疆域广阔的大国的区域(如一省)从规模上已经相当于欧洲的一个中等规模国家。上,可以认为物理上的直接交流很难解释其集聚现象。这里,区域指更为宏观的地区,一个此规模的区域可为城市群或包括若干个一般规模的城市。
1.“中心—外围”模型对区域尺度集聚的解释
“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是为了处理宏观地区问题而建立的。克鲁格曼(Krugman,1991)构建“中心—外围”模型,将人员流动(集聚)所产生的效应在垄断竞争一般均衡模型中进行研究与解释。⑤Paul Krugma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9.No.4,1991, pp.483-499.研究发现,当运输成本在一定的区间内,两地区的实际工资差额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动力来源使得集聚是稳定的。在该模型中,实际工资差距来自于前后向关联:一方面,由于企业集聚,使得该区域当地生产的较多种类的中间产品可以降低价格指数(前向关联)——集聚区域生产的产品比在分散条件下更便宜,已被实证分析所证实;①Jessie Handbury and David E.Weinstein, “Goods Prices and Availability in Citi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82,No.1,2015,pp.258-296.另一方面,集聚地较大的当地市场会使名义工资较高(后向关联)。大的经济主体(如大开发者)行为可使得城市层面的集聚发生,但在区域层面,“中心—外围”模型的集聚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企业和工人的无意识结果,在“中心—外围”模型中,不完全竞争与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是关键因素,工人和企业的迁移会无意识地影响所有经济主体的福利。虽然“中心—外围”模型存在一些缺陷,但指出了区域之间存在差距(即集聚程度不同)的主要机制。针对“中心—外围”模型不能得到解析解的缺陷,佛斯里德等人(Forslid et al.,2003)通过在工业部门引入非熟练劳动力解决了这一问题。②Rikard Forslid and Gianmarco I.P.Ottaviano, “An Analytical Solvable Core-periphery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3,No.4,2003, pp.229-240.在“中心—外围”模型中,另一个问题是:模型预测当运输成本降低到临界值,(制造业部门的)集聚会突然发生,而这与现实中的集聚是渐进式发生的有所不同。然而,如果考虑到人口的迁移行为存在异质性,那么从分散状态过渡到集聚状态将是平滑、渐进的,这也正是在现实世界中很难发现某区域发生突然集聚现象的理论解释。
“中心—外围”模型的构建考虑了两种集聚力量,即前、后向关联,但没有考虑在城市经济学模型中非常重要的学习效应。此外,在“中心—外围”模型中的运输成本也不同于城市层面的通勤成本。以上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类模型考虑的是不同空间尺度上的集聚问题,在更大的区域尺度上认为,(面对面)交流与学习的效应要弱得多是合理的。此外,在区域尺度上考虑的产品运输成本在城市尺度上要相对小得多:在现代运输条件下,在城市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忽略运输成本差异是合理的;影响城市聚集程度与边界的是耗费大量时间与金钱的通勤成本;与产品通常只需要运输一次不同,通勤成本是大量重复发生的。与城市经济学模型相比,区域的集聚更接近于一系列城市网络所形成的区域,而城市地区模型聚焦于城市内部的集聚及构造,研究对象在空间尺度上是相对微观的。
2.区域集聚差异的倒U形曲线
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Krugman and Venables,1995)从理论上证明,制造业部门在区域间集聚的速度(或程度)与运输成本变化的关系不是单调的;①Paul Krugman and Anthony J.Venables,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0,No.8,1995, pp.857-80.随着货物运输成本的下降,经济活动在区域层面上向少数中心大城市集聚;而随着运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经济活动反而会向中小城市再分布,呈现出分散态势。具体机制是,如果土地供给缺乏弹性的话,企业和工人会在土地竞争中推高城市成本,急剧上升的通勤成本与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在模型中表现为区域间广义运输成本的持续下降)将触发制造业企业再度分散。根本原因是,由于其他地区相对于中心地区在地租方面产生了比较优势,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地区间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得企业即使远离当前中心区域也仍能够以较低运输成本向其提供产品。普弗鲁格等人(Pflüger et al.,2010)深入讨论了使再分散得以发生的一体化程度的临界值。②Michael Pflüger and Takatoshi Tabuchi, “The Size of Region with Land Use for Produc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40,No.4,2010, pp.81-89.运输成本与经济集聚的非单调关系为解释区域间不平等程度的动态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上的视角:在一体化过程的第一阶段,地区间差异会更大;而第二阶段,经济一体化会反而促进地区间收敛,经济效率和空间平等可能同时实现。③Michael Pflüger and Takatoshi Tabuchi, “Comparative Advantag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Trade Cost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109,No.3,2018, pp.1-13.关于地区间差异演变趋势的研究,一些高水平的实证研究出现,这些成果明确支持空间发展呈现倒“U”形曲线的猜想。④Julio Martínez-Galarragaand, Joan R.Rosés and Daniel A.Tirado, “The Upswing of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n Spain(1860-1930),” Explor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 Vol.47,No.2,2010,pp.44-57; Pierre-Philippe Combes,Miren Lafourcade and Jacques-Francois Thisse, “The Rise and Fall of Spatial Inequalities in France: A Long-run Perspective,” Exploration in Economic History ,Vol.48,No.2,2011,pp.243-271.上述区域间差异缩小(再分散)的过程与城市尺度上分散的过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机理:“中心—外围”模型是为解释宏观地区集聚而构建的模型,一个宏观地区可能包括多个城市群,再分散的主体是企业(机理如上文所述);而在城市模型中,通勤成本的下降对企业选址与工人居住地选取有相反作用——会使工人虽向外分散居住,但仍可以在中央商务区工作。这必然会使企业在地理上更加集中以在集聚经济中获益。
(三)全球尺度上的经济集聚机制
人员的跨国流动仍然是相对困难的,全球尺度上的集聚必然有截然不同的机制与表现形式——主要为产业或功能(产业链某一个或若干个环节)上的集聚。从单个企业的视角观察,企业的全球化通常表现为与垂直型外商投资相关联的企业内部生产活动的分散化,即现代企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组织和执行相互独立的生产活动;从全球的视角观察,为数众多的生产企业的跨国部署使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某一个或几个环节的较为集中的接受者。因此,全球尺度的集聚表现为不同产业或生产的不同环节分别在各种发展水平的国家的集中。
1.全球层面的集聚机制:公司总部与其他价值链环节的集聚
必须明确的是,在全球或国家尺度上,不同“层次”集聚的发生机理并不相同:公司总部在某些相对发达国家的集聚与普通价值链环节(如装配等生产环节)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国家集聚的原因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较高层次上,对于众多公司总部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集聚形态,用前后向关联、知识溢出等效应都难以给予准确与全面的解释。一般认为,只有能够同时提供广泛的生产者服务、金融服务和现代跨国公司要求的高效国际通信连接的地区,才能够成为总部集聚地,此类地区的优势是使本地和非本地的公司操作更加容易控制。这一论断有以下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将公司总部设立在这类地区可以更加高效的控制选址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分公司的经营活动;第二,公司可以拥有对重大事件更强的掌控能力。在通信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前者的实现已不是问题;对于后者,约翰·R·洛根与哈维·L·莫洛奇以公司总部应对收购与被收购为例指出,“此类行为需要极为专业的法律业务、银行业务以及会计业务的支持,当地资源(高水平律师、金融家等的有效聚集)使类似的行为变得更加可控和可行,虽然这并没有使当地的生产变得更加有效”。①约翰·R·洛根等:《都市财富: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格致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9—256页。可见,公司总部所要求实现的功能与一般价值链环节致力于对高技术效率与低成本的追求不同——总部更加重视所在地区所能够赋予的控制优势,公司总部会在那些与提高生产效率并无关系的活动中获益,这是由公司总部的功能属性决定的。由于控制优势的决定因素更加难以建模体现,尚无单一模型可完整解释全球层面上的公司总部集聚机理。
在较低层次,在众多企业分散化(跨国部署)的进程中,一些国家或地区成为某一个或几个生产环节较为集中的接受者,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则难以得到青睐。通过分析跨国公司选择分散化的动机与总结东道国的特质能够发现该层次的全球层面的集聚机制。在前述讨论的区域尺度上,(同一行业中)企业的集群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利用外部规模经济,虽然这一点在度量(或程度)上尚不明确;而在全球尺度上,企业的位置选择所考虑的因素既包括要素禀赋、“市场接近”,也包括集聚引起的外部经济。其中,要素禀赋是全球尺度上更加强调的因素。在国内的区域尺度上,由于要素流动相对无障碍,所以区域间的要素禀赋结构一般不会有太大差异,但在国家间则差异巨大。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的跨国企业会将价值链某一环节集中部署在某一国家或地区,正是为了利用当地较为廉价的某种要素,而该要素是这一环节中被密集使用的。除了要素禀赋差异以外,追求“市场接近”也是跨国公司的重要考虑因素。在全球尺度上,导致生产资源跨国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规避贸易壁垒,但此现象不属于纯粹由经济学机制决定的范畴,因此本文不做进一步讨论。
2.集聚或分散:信息传递成本、运输成本与规模经济的权衡
在全球尺度上,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经济活动使得经济的全球化得以实现。如果抛开贸易壁垒等政策性因素的作用而单纯考虑经济因素,全球尺度上的集聚(资源的跨国流动)是在信息传递成本、运输成本与规模经济的权衡中实现的。通信成本与运输成本对跨国公司的形成与活动产生不同的影响:信息传递成本的降低,使得公司总部与其他部门的信息交流变得更加容易,部门间对地理距离临近的依赖性逐渐降低,从而在客观上得以分离,每一个价值链环节的实现,部门都会选择其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这种价值链环节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集聚正是跨国公司生产活动的分散过程;而运输成本的降低则起到相反的作用,无论是中间产品运输成本(垂直投资型)还是最终产品运输成本(水平投资型)的降低,都使产业上下游部门互相临近、接近消费者变得相对不重要,存在抑制公司跨国部署的作用。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对公司跨国部署产生抑制作用的因素是规模经济——投资另建研发、生产或销售机构需要大量的固定投资,将使产品的平均成本上升。理论上讲,只有投资小于运输成本的临界状态时,跨国投资才会发生,而运输成本下降使这一条件变得困难。也就是说,固定投资与运输成本比值的大小是决定企业是否进行跨国部署(成为跨国公司)的关键,该比值越小,产业链跨国组织就越容易实现。从现实世界的情况来看,信息传递成本下降所起到的激励作用要大于运输成本下降所产生的抑制作用,除公司总部以外的生产环节的跨国部署与资源的跨国流动处于逐渐加强的态势。赫尔普曼(Helpman,2011)基于微观经营个体的异质性,通过引入企业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来解释为何有的企业选择跨国经营而有些只局限于国内经营;①Elhanan Helpman, Understanding Global Trad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70-78.藤田昌久等则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证明即使所有的企业都具备相同的技术水平,仍然存在不同的空间组织形式。②藤田昌久等:《集聚经济学:城市、产业区位与全球化(第2版)》,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157页。
与人员在国家内部的自由流动不同,劳动力在国家之间的流动阻力很大,所以使用解释区域尺度上集聚的机制来解释全球尺度的集聚是极不适合的。而且,在“中心—外围”模型中,当两区域对称均衡被打破后,典型企业将向经济活动规模占比超过一半的地区转移,这种转移是“整体式转移”,驱动的因素有前后向关联、知识溢出效应等。但在企业跨国部署中,大多数是部分价值链环节的转移。规避包括运输成本在内的广义上的贸易成本及降低生产成本,是其主要动因。
三、结论与建议
经济活动的分布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均呈现集聚样态,但其机理并不相同,深刻理解这种差异,从不同的空间尺度或空间单元去划分集聚的类型,识别不同水平的经济集聚,对城市、区域及贸易政策的正确制定非常重要。
城市尺度上的集聚动力来自分享、匹配与学习机制,城市的规模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回报有重要的正面影响,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理论上,城市的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之间的权衡决定了城市的最优规模与边界。但是,由于城市的规划水平、治理能力在不断提升(如降低规模“不经济”程度),并且城市的产业结构也在变化中(如改变规模经济程度),所以城市的最优规模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一般来说,服务业比重高的城市,最优城市的规模就比较大(王垚等,2017)。③王壵等:《产业结构、最优规模与中国城市化路径选择》,载《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2期,第441—462页。梁琦等人的研究指出,由于户籍等制度的限制,中国大城市的规模偏小,偏离了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①梁琦等:《户籍改革、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层级体系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36—58页。潘士远等(2018)在空间均衡模型中加入了人口流动限制的因素后,得出中国一线城市的规模过小的结论。②潘士远等:《中国城市过大抑或过小?——基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视角》,载《经济研究》,2018年第9期,第68—80页。实证研究证实,大城市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教育回报率、技能互补性;限制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政策,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与潜在的全要素生产率。③James E.Rauch,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34, No.3,1993,pp.380-400; Wenshu Gao and Russell Smyth,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Urban China, 2001-2010: Evidence from Three Waves of the China Urban Labor Survey,”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20, No.2, 2015, pp.178-201; Jan Eeckhout and Kurt Schmidheiny, “Spatial Sorting: Why New York, Los Angeles and Detroit Attract the Greatest Minds as well as the Unskille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22,No.3,2014,pp.554-620.
区域(国家)尺度上的集聚是区域间市场整合与区域专业化在空间上的体现。近年来,我国的人口与经济加速向少数具有向心力的区域集中,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的大都市圈。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集聚的发达地区有着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优化了我国的经济分布格局,这在人口红利逐渐弱化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为例,区域内各城市经济的协调互动促进了市场整合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④张学良等:《政府合作、市场整合与城市群经济绩效——基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实证检验》,载《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4期,第1563—1582页。此外,当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我国更应该全面打破区域市场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壁垒,促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借助国内的统一大市场,降低逆全球化造成的负面冲击。
全球尺度上的集聚可分为一般生产环节的集聚与公司总部的集聚两个层面。一国或地区的比较优势属性决定了集聚发生的类型。中国幅员辽阔、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不同区域的集聚类型并不相同,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转换。以上海为例,自2002年出台全国首个吸引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政策以来,截至2019年10月,上海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10家(其中亚太区总部114家),外资研发中心453家。上海能够成为全球层面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研发中心最多的城市之一,根本原因在于地区特质能够赋予公司总部以前文所述的控制力。以该视角观察,个别集中于生产阶段的外资企业撤出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属于比较优势转换升级过程中的正常情况。对我国发达地区而言,全球战略的重点应置于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等主导产业,引进细分领域产品或服务份额在全球市场名列前茅的跨国公司总部及研发中心。
各空间尺度上的经济集聚机制不同,但各个尺度上的集聚样态互相影响:城市尺度上的集聚形成大城市、都市圈。作为城市群的核心空间形态,都市圈的规模及发展质量是区域内经济增长及区域间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①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了都市圈发展对增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作用。区域尺度上集聚的重要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区域内大城市(都市圈)所产生的竞争效应与市场潜力;②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尺度的集聚与区域尺度的集聚机制的原因是相同的,而是指城市层面的集聚所产生的效应是区域层面集聚的原因之一。全球尺度上的集聚与更低尺度上集聚所产生的向心力有关,例如:对跨国公司总部或生产环节的吸引,取决于区域或城市的经济属性,是后者集聚质量和水平差异的体现。上述各尺度集聚的影响并非单向,例如,全球层面的要素集聚也会加强较低尺度的集聚程度,具有为因果循环加强的关系。
在各个空间尺度上,经济集聚必然会导致空间差异的出现,包括就业率、经济增长率以及公共投入等多方面,而这种空间差异往往会引发社会问题。因此,在深入理解不同空间尺度的经济集聚机理的基础上,探寻如何在促进经济集聚的进程(也是空间效率的实现过程)中解决空间平等问题、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